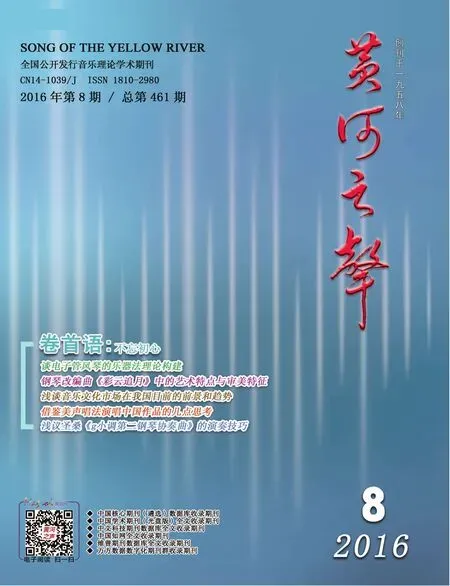彝族舞蹈体语与在不同语境的语意分析*
杨 俊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彝族舞蹈体语与在不同语境的语意分析*
杨 俊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在彝族悠长的历史发展中,舞蹈艺术永远伴随着彝族人民生活的转变而成长与发扬。艺术形式的演变往往揭示着一个民族社会的进化状态,而舞蹈艺术恰好最能充分展示一个民族的基本风貌和民族精神,所以舞蹈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社会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众所周知,舞蹈的呈现是综合性的,身体作是它的主体媒介,运用身体语言(动作律动)来进行舞蹈活动,同时结合身体辅语言(舞台、灯光、布景、服装等)元素共同呈现舞蹈表达的特色风貌。
彝族;彝族舞蹈;舞蹈体语;舞蹈文化
彝族作为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该地区的彝族人民素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其传统舞蹈丰富多样,独具特色。
一、彝族舞蹈及其类别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其舞蹈风格古朴凝练,种类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追根溯源,这与古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源自于古羌。彝族及其先民进入凉山之后,其舞蹈文化即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长期延续。因此,凉山彝族传统舞蹈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当地社会形态的痕迹。彝族舞蹈的形成期约在公元8到10世纪,那时庙会舞、巫舞、佛舞以及各类乐舞颇为盛行,至今有些歌舞还留存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据统计,有超过170多种彝族民间舞蹈,以及1900多种跳跃方法。
根据舞蹈的表现形式来分,彝族舞蹈主要分为集体舞与独舞,此中以集体舞为主,如“跳月”“跳歌”“跳乐”“锅庄舞”和“打歌舞”等。彝族民间舞蹈,按史学源流可分四类,即征战舞、劳动舞、宫廷舞与祭祀舞。从艺术表现可分为花灯、乐舞和歌舞三种类型(乐舞包括铜鼓舞、烟盒舞、阿细跳月等,歌舞包括罗作舞、打歌、四弦舞等)。从内容上可分为:娱神驱鬼舞、送灵舞、虎舞等。
二、语境中的舞蹈体语
人是环境的人,作为一种场景动物,所有的人的行为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人在不同的语境下说不同的话,而同样的话在不同的环境中又传达着不同的语意信息,所以,要确切无误会意人们语言传达的切实内容,必须结合其语言表达时所处的具体环境——语境。犹如美国语言学家Gilles Fauconnier所言:“语言表达形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确切地说,它有一种意义潜能,只有在完整的话语和情景中意义才能产生。”[1]语言如此,身体语言亦如此,舞蹈身体语言自然也概莫例外。
(一)身体语言
人类伊始,人与人的交流是由语言和非语言两类构成的。研究显示,人类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语言(口述的字和词)传播占信息总量的7%,声音(音量、语调及其变化)传播占38%,另外由无声的面部表情、动作、姿态等传递的占55%的比例。我们把这种无声的、非口头表达的“能够传递信息及观念的显意符号系统”称为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2]。
身体语言,也叫肢体语言(简称体语),指非词语性的身体符号。从语言学的视角说,身体语言其实是副语言(paralanguage)的一种类型,表示使用姿势、动作与动作群、表情来替代或作为口头言语、声音以及其他交流方式的辅助,以达到交流目的的方式的一个术语。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对身体语言进行研究,具体的任务是研究身体语言与审美之间的关系,重视的是身体语言的美是怎样产生的,如舞蹈身体语言研究。
(二)舞蹈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作为人类独特语言的一种,也与上述所受影响的因素一致。在通常的理解中“身体语言”仅指人的肢体,而在舞蹈身体语言中与舞蹈表演息息相关的因素,诸如服饰、道具与音乐等也是舞蹈身体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形成合力为最终的舞蹈作品传达思想与情感。
“舞蹈身体语言”即“舞蹈体语”,其概念的提出也是近代以来舞蹈理论和实践观念变革的结果。尽管“身体语言”很早就已经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可是把这门学科引入舞蹈理论界却还是在现代舞蹈观念产生以后。上世纪初,以“现代舞之母”邓肯为代表的现代舞前驱们从批判古典芭蕾程式化,反对足尖技巧对舞蹈表现情感能力的约束,主张把人类的情感表现放在舞蹈的首位之始。现代舞使舞蹈重新回归到服务人类情感意义上的原初动作本身。
(三)彝族舞蹈体语
在舞蹈艺术中,要正确理解舞蹈身体语言所传达的含义,同样离不开对其具体语境的联系与判别。舞蹈身体语言的语境不单表现于运动人体的姿式、动作及其服饰、道具等物质载体上,还同时表现在不同舞蹈类别的审美和感知氛围等综合体验当中。
彝族舞蹈体语是彝族舞蹈特有的身体语言,同时也是针对彝族舞蹈的种类、特点以及生态学意义的舞蹈研究的方法。不管是在传统还是现当代的彝族舞蹈中,由于舞种、语境、舞者性别差异等而展示出来的身体语言都始终保持着那份神秘与不可或缺的地位,彝族的舞蹈动作以独具特色、别有意味的样式展现了其特有的身体语言的魅力。
三、彝族舞蹈体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意
谈“语言”就离不开“语境”,将舞蹈身体语言放置于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研究,才能让我们更准确的把握传达者的语意。[3]身体作为传达媒介时,会因为这种表达方式的抽象性而显得多意,就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去理解,方能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彝族舞蹈身体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风格中所承载的文化传达、审美意义与历史价值均有不同。在不同语境中,彝族舞蹈身体语言的语意也自然会发生着变化,要正确理解交流对象语言的全部含义,就必须结合对方的语境因素,合理运用推理能力才可能获得对该舞蹈作品最准确的解读。
(一)彝族舞蹈远古时代的语意
舞蹈作为表现人的生活和情感的有节奏的运动形式,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欢庆胜利、祈求上苍或祭祀祖先。从圈舞这种人类古老的舞蹈形式就可窥见一斑。圈舞历经千年蜕变,在许多民族中已改头换面,汉族的鼓子秧歌以多种形式的跑场显示风采,傣族以双人对舞的形式独树一帜,维族、蒙族豪放多姿,不拘一格。而彝族舞蹈跟所有藏缅语族一样,仍保持着原始古朴的圈舞风貌,以连袂踏歌的方式诉说着他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老的圈舞文化在千百年中流传,奠定了彝族舞蹈文化的基础。透过彝族聚居区的火把舞,我们看到诸多原始舞蹈的特质,弥漫着强烈的原生态气息。火把舞在彝语中称为“米叠腾”,就是舞动火把的意思。通常火把舞是在火把节才跳。每年的火把节,彝族人民身着盛装,家家吃盛宴,纷纷聚集荒原,点燃篝火,唱着火把歌儿,联袂起舞,场面非常壮观。对于火把舞的源起,传说是很久以前一个叫阿史阿娜的彝家姑娘,因为美貌而声名远扬,被当时的一个汉人官员知道后,就把她的情哥杀害,抢走阿史阿娜,但是阿史阿娜宁死不从,最后点火自焚。后来彝族人为了纪念这位以身殉情、坚贞不屈的姑娘,就把六月二十四(她死的这天)定为火把节,每年到这一天家家都点起火把,亦歌亦舞,祈望与阿史阿娜的不死之灵魂相通相息。
凡是到民族地区参加过圈舞活动的人多少会有这样的感受,连袂踏歌、携手而舞的形式很容易给我们现代人一种强烈的内心冲击。在携手同舞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化解了人与人之间或多或少的“潜在的敌意情结”。彝族舞蹈联袂他哥的这种形式也不例外,当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围着篝火携手而舞时,能唤起现代人对团结、信任、互助、协作的和谐大同社会的原始理想。释放自己、回归自我,人类最纯真、最质朴的一面悄然流露,一片和谐祥宁之气。
(二)彝族舞蹈的田园农耕语意
舞蹈在传承的同时也继承了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在很多彝族舞蹈中都有生动形象地表现田园农耕生活的场面与语意。从发生学的角度讲,舞蹈的诞生绝非纯精神的产物,它具备与精神合为一体的实用价值。
彝族舞蹈动作的形成必然有其独特的客观环境和人文因素。彝族人民大多长期生活在山高坡陡之地,由于生产力低下,劳动和生活资料的运输主要依赖于人力,沉重的背负必然会限制上肢的活动。因此他们的腿部变得坚实而有力,腿和膝部变得非常灵活。我们通过彝族舞蹈体语中的分析,很多脚部动作都含有许多生产劳动的影子,舞蹈的表演也起到了传授生产劳动技能的作用。譬如织毡舞、荞子舞、包谷舞等,基本就是表现生产过程和模仿劳动动作。在撒麻舞中,直接再现了从开垦到耕耘,从播种到出苗,从锄草到田间管理,从收割到纺线,从织布到缝衣这一系列的完整的劳动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以及男女情感都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得以互融,劳动改变着生活的品质。
(三)彝族舞蹈的当代舞台语意
社会的变化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影响不可估量,跟所有民族民间舞蹈一样,根植于民间,带着厚重的朴素的民间色彩一路走来。而在田野院坝和剧场表演,舞蹈的身体语言需要根据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当民族舞蹈走进剧场,就已经不再是原初田园舞蹈的意义了。即使将其最大化的还原为“原生态”的形式,但由于时空的改变,整个气场也随之改变。也正因如此,舞蹈的剧场表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绎风格与表演样式。近距离、互动性和亲和力作为民间舞蹈表演的优势和特点,这时候在剧场中就很难得以实现。所以,在剧场表演中,由于舞台和空间的客观性将舞者和观者放在了对立的两面,形成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这使得舞蹈编导家们不得不从新的视觉入手去进行艺术创作。
20世纪50年代,当彝族舞蹈进入都市舞台后,冷茂弘先生创作的彝族剧场舞蹈《快乐的啰嗦》、《阿哥追》《翻身农奴把歌唱》、《红披毡》等,舞蹈皆因该时期的政治诉求所致,强烈的带着显明的时代特点,作品的审美意蕴也被意识形态的观念消失殆尽。最后仅仅依靠舞蹈编创者的择取吸纳手法,得以巧妙的将其与时政嫁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彝族舞蹈也逐渐通过视频与观众见面。观众通过现场与电视影像的接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情感体验。而另一方面,彝族舞蹈也在悄然的发生着重大变化,譬如马琳的《阿惹妞》、《阿嫫惹牛》,苏冬梅的《心之翼》等。通过对比这个时间阶段凉山彝族舞蹈的创编作品,发现有两个重大的转向:一是舞蹈从彝族人自己编创转向为他族人编创彝族舞蹈;二是彝族人自己跳彝族舞蹈转向他族人跳彝族舞蹈。彝族舞蹈的创编角度也多元化起来,从而丰富了凉山彝族的当代舞蹈精神与内涵。可以说,这是彝族传统舞蹈在面对现代族群观念变化后的一次重要革新。
四、结语
引发彝族舞蹈体语语意变化的因素很多。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网络数字技术的普及与运用,我们发现通过现场、电视、网络看到的各种舞蹈大赛中的彝族舞蹈作品,均在表现形式、内容、服饰搭配、细节处理等方方面面作出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整体逐渐进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断主动或被动的吸收着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从乡村走向都市,从田野院坝走向华丽炫目剧场舞台,融合科技可能的辅助表现,将现代人的人文与生活诉求均纳入其作品表现的内容。同一个作品不管是表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唯有将作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研究彝族舞蹈体语,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承传并发扬这门独具魅力的舞蹈形式。
[1] 亚伦·皮斯、芭芭拉·皮斯,王甜甜、黄佼译.身体语言密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2] 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3]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研究成果(YZWH1209)
杨俊(1980-),女,四川仁寿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民间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