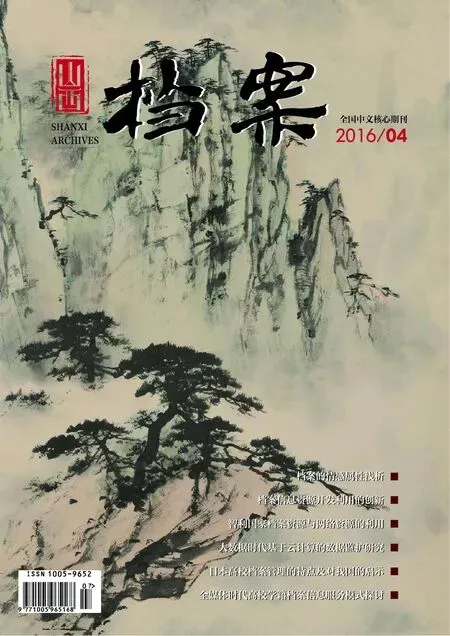试析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婚恋中的“旧道德”现象
文/王栋亮 Wang Dong-liang
试析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婚恋中的“旧道德”现象
文/王栋亮 Wang Dong-liang
An Analysis of the “Old Moral Concepts” in Intellectual Women's Love and Marriage during 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时期,不少知识女性的自由婚恋呈现新思想旧道德的特征。她们的婚恋行为虽以自由观念为外在表征,潜意识中以男权文化为特征的传统观念却依然根深蒂固的起着支配作用,致使自西方引入的婚恋自由观在中国发生异化。知识界虽然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但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其效果并不明显,足见婚姻自由和女性解放和是一个长期的历程。
五四时期;新女性;新思想旧道德
自清末以来,不少改革者认为社会变革应以女性解放为基础,而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婚姻自由。五四时期不少女性虽以新女性自居,但却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痕迹,从而摇摆于新观念和旧传统之间,呈现“新思想旧道德”的状态。目前,学界对于知识女性婚姻的研究多侧重于独身问题或婚姻思潮,对于其中存在的“旧道德”现象关注并不多。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尝试梳理知识女性婚姻“旧道德”的表征、存在原因以及时人提出的相关对策。
一、知识女性婚恋旧道德形态的原因
自由婚恋在五四时期被理论界预设为寻求人生幸福、推动社会进化的重要手段,但在某些女性那里却成为赚取虚名、满足某种心理欲望的工具,有的女性将接受现代教育作为改变自身命运的跳板;有的女性仍把婚姻当作职业看待,其所追求的婚姻生活表面看不同于传统样式,但在时人看来仍摆脱不了被供养的事实。有的女性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致其婚姻失时孤独终生;有的则仍将婚姻作为自己的唯一归宿。如此种种都是知识女性婚姻“旧道德”的表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女性就业困难及因袭的依赖心理
清末民初,现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为社会培养了一批职业女性,如女编辑、女记者、女教师、女护士、女店员等,但从整体的社会环境看,女性就业仍受到排斥,[1]贤妻良母的角色仍是多数男性对女性角色的最大心理预期。在此氛围中,不少知识女性除了依赖于男性之外,似乎尚无其它良策。另外,长期因袭的依赖心理和社会的引导使不少知识女性懒得去挣扎或奋斗于社会之间,新式教育的经历使其有资本嫁接于豪门或富贵之家,夫家的资本瞬间就成了自己享乐的源泉。对此有人评论说,“女性被‘现代化’武装一番无非是为了更理所当然地为男权中心社会所接纳,更好地为男人服务,从而也积累了更好地为男人所观赏和把玩的资本。”[2](p242)
(二)义务型婚姻观的延续
如果说传统婚姻是个体对于家族的义务,那么在清末知识界婚姻被视为社会性义务,它要为社会的进化与强化种族来服务。[3]因此,在五四之前的长时段中“义务型婚姻观”在国人心目可谓根深蒂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确立了新性道德基本框架,但它更多地强调婚姻结合方式的自主性,并没有否认其义务的色彩。不过,其义务的强调转向了对社会的改进。因此,其潜意识中婚姻仍是个人的必然之选。婚恋自由并没有抹掉国人对于婚姻的热情,那些新女性亦不能例外。于是乎,为了结婚她们不惜强行恋爱,甚至闪婚。
(三)恋爱法则的扭曲
知识女性在择偶时多要求男子要强于自己,以至于“高处不胜寒”而使其婚姻失时。追求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对于择偶为什么偏要带着不平等的眼光呢?笔者认为,这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男尊女卑”模式有关。这种格局形成了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夫妇二人在无论经济、权力、还是学识上都存在落差。女性的诸多自由虽受到限制,但在经济上由男人供养,在权力上由男人提供庇护,男性提供了保证其生存的诸多安全因素。因此,两性长期以来形成了这种带有落差的刻板印象,女性只有在“仰视”男性的状态中才能找到安全感从而发生恋爱。知识女性择偶之所以要找到自己“仰视”的男性,其心理即基于此。这是近代中国新女性个体意识觉醒与男尊女卑观念碰撞后结下的畸形之果。
(四)贤妻良母教育的塑造
教育本应使学生有自立的本能,具备适应、改造社会的能力,但当时的教育体制显然并非如此。女子教育多以培育“贤妻良母”为主要目的,故其培养的新女性很难有自立、自决的能力。针对知识女性的婚姻悲剧,时人曾大力质疑当时的教育。李毅韬在张嗣婧死后说:“人的所以贵于有知识,就是由于知识可以帮助他应付环境。而张君受了女师范的教育,得了不少的知识,然结果仍因不能应付环境而死,这实在是一件可怪而必需研究的事情。”[4]由于女子教育多停留在新知识旧道德的层面,它把女性塑造成新知识武装起来的旧女子,故从心理上讲这些女子很难摆脱家庭的束缚。
二、时人改造女性的建议与局限
知识女性的婚姻问题引起了知识界的焦虑,他们献言献策以济时弊。从其建议看,他们首先对婚姻问题本身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如“谨慎择偶”、“性情相合”等,并结合不少婚姻实例告诫青年人,其用心可谓良苦,对于解决婚姻问题不无裨益。另外一些人认为,知识女性在婚恋问题上的种种表现与其说是婚姻问题,倒不如说是女性心理及意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培养女子的健全人格。为避免女性自身的弱点,时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提倡女性经济独立,培育健全人格;第二,加强女性的教育和引导,完善女性独立人格,具体要求包括女性要树立自觉的意识、继续接受教育以提升自身文化素养、教育界要针对女性特点因人施教。
知识界提出的两条建议,其目的是要更换女性的知识结构,培育健全的心理机制,使女性具备自我反省的意识、遇事有冷静的头脑、长远的眼光以及坚强的意志,从而让她们成为兼顾传统女性美德与现代女性独立人格和能力的复合型女子。从理论上讲,上述建议可谓金玉良言,但在现实中却不容易实现:
首先,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地盘踞在社会结构中难以清除。自汉代已降,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儒学为主。儒学对传统政治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其伦理化,伦理与政治实现互动从而将家、国、天下连接为一体。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思想对儒家的政治伦理形成较大冲击,但社会改革的缺位使家庭伦理政治依然根深蒂固的存留下来。并且,文化本身的持久性、普遍性和独立性使其并不因政治制度的断裂而消失,这使得儒家的礼教思想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支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
其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难以给女性提供就业岗位。自西力东渐以来,近代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传统经济因素依然存在,新的生产要素已经产生,这为女性活动空间的拓展和就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催生了一些职业女性,如比较知名的有杨荫榆、郑毓秀、杨步伟等。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并不能有效地为女性开辟就业岗位,女子就业空间极为狭小,经济独立的意愿难以实现。[5]
再次,新观念中的“女权”意识的缺失。自清末以来,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培育“国民之母”,或有文化的“贤妻良母”。这是晚清以来女子人权进步的表现,但其中的不足就是“女权”意识的淡薄。在“国民之母”思维框架中,女子“为母”、“为妻”的辅助行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变化的只是“为母”、“为妻”的标准罢了。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也就难怪谌小岑批评女子教育为“闺阁教育”,陆秋心批评教育界的先生们思想守旧了。在五四时期的新知识界虽也强调男女的平等,但在1920年代的反帝爱国运动中,这种理念很快被争取人的权利意识所消解。[6](p19)在革命过程中,女性解放从属于阶级斗争,父权制家庭并未彻底打碎,也就未能实现男女的平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给知识界也带来了婚姻自由理念,但其“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7]婚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转变必须以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基础,仅仅依靠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显然无法推动婚姻的真正转型,这也决定了五四时期确立的婚姻自由观念的践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本文是国家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婚姻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5ZDB050)
(责任编辑:无尽藏)
[1] 何黎萍.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J].近代史研究.1998,(2).
[2] 刘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 壮公.自由结婚议[J].女子世界.1904,(11).
[4] 峙山.张嗣婧与天津女师范[J].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1923,(3).
[5] 何黎萍.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J].近代史研究.1998,(2).
[6] 李小江.关于女人的问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7] 杨奎松.五四有多重要[N].南方都市报.2009-4-19.
K261
A
1005-9652(2016)04-0168-03
王栋亮(1976—),男,山东诸城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