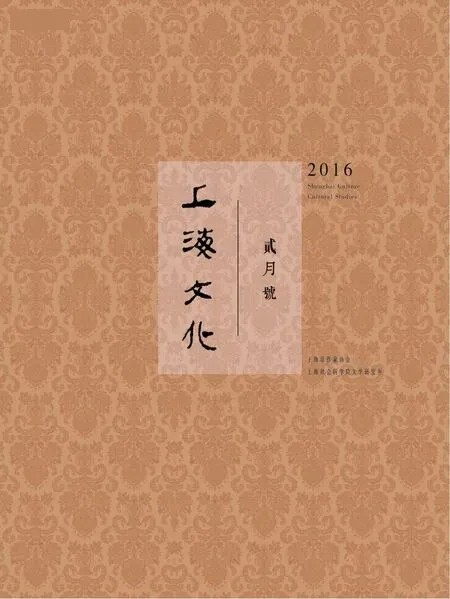何谓上海电影——电影产业视角中上海电影的历史与机遇
刘 春
何谓上海电影
——电影产业视角中上海电影的历史与机遇
刘 春*刘春,女,1983年生,陕西商洛人。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电影史、电影产业研究。
内容摘要 本文围绕不同时期对于何谓“上海电影”的理解以及不同的产业策略,梳理了上海电影产业的历史脉络与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当下讨论电影产业与城市产业环境的关系,在于电影资本是否在这座城市注册、纳税与运营;导演、明星、编剧以及产业链上相关人员是否长期在此生活与工作;是否在此形成新的电影潮流。换句话说,电影产业的中心,也即是资本的中心、人才的中心与美学的中心。上海电影产业的复兴,要在资本的优惠政策、人才的扶持政策、文艺的引导政策三方面发力。
关 键 词上海电影 电影产业 电影史
在电影产业的意义上,什么是“上海电影”?这是本文的写作主旨,笔者将结合上海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予以阐发。
一
回顾中国电影史,上海电影产业的开端几乎与世界电影的诞生同步,同时和其他许多产业类似,肇始于海外输入。据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介绍①程季华先生认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8页。及黄德泉的考证,②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电影艺术》2007年第3期。“电影在中国最早放映的地点是上海”,③于丽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4页。这一点可判定无疑。而1904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租下四马路(今福州路)茶楼“青莲阁”楼下一间房专营电影放映,上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固定电影放映点宣告诞生。④薛峰:《雷玛斯与上海电影产业之创立》,《电影艺术》2011年第2期。
同样,对于电影产业而言更为重要的制片、发行也首先由西方传来上海,“第一个登陆的是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其于1909年投资设立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开始在上海和香港摄制影片”。⑤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18页。而中国电影产业的萌芽——明星公司它的创办人就是脱胎于亚细亚影戏公司。①艾青:《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明星影片公司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16页。经历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传入、模仿与酝酿,上海乃至于中国有电影而无本地电影产业的历史,在1922年得以改变,而这正是源自明星公司的出现。明星公司得以问世的原因,鲜明体现出电影产业所密切依赖的资本推动:创始人张石川在1922年2月19日《申报》上刊登启事,向全社会公开发行公司股票,以股份制方式筹集资金。最终主要以合伙人集资方式成立“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由此上海电影产业进入新的篇章,它是第一个成熟的中国电影公司。②石川在《后编年体史述:多元体裁与深度阐释》中说“如果论及早期中国的电影经营模式,那就应该以1922年明星公司的成立作为历史断代的标志性时间节点”,见《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经过草创初期的努力,随后明星公司推出一系列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电影,如《空谷兰》(1925年)、《火烧红莲寺》(1928年)、《歌女红牡丹》(1931年)、《姊妹花》(1933年)等,奠定其在二三十年代电影产业格局中的龙头地位。在明星公司之后上海电影产业蓬勃发展,进入群雄蜂起的时代,大中华百合公司、天一公司等相继成立,稍晚几年联华公司经历一番合纵连横也迎头赶上。
在当时的电影产业环境中,界定“上海电影”非常简单——在制片的意义上,重要的电影公司都在上海,几乎所有的国产电影都是上海电影。1925年前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成都、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共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上海有141家。③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54页。正是因为其全方位的优势地位,何谓“上海电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当我们今天讨论何谓“上海电影”、讨论“上海电影”的复兴时,已经在潜意识中以一种区域性的框架来定位“上海电影”。而对当时的影人而言,“上海电影”就是“中国电影”,彼时对于“中国电影”倒有所讨论,如郁达夫写于1924年的《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陈君清写于1927年的《何谓中国电影》。这里的“中国电影”而不是“上海电影”构成讨论的视野,在于有强势的“美国电影”作为对位的参照,我们总是通过对于他者的指认来反身建构自己。不过那时对于“中国电影”的讨论,其关切并不在产业发展层面,而是于“启蒙论”的阐释框架中讨论电影的社会意义,如郑正秋认为电影在于启发“觉悟”,应该包含“创造人生之能力”、“改正社会之意义”、“批评社会之性质”;④郑正秋:《我所希望于观众者》,《明星》1925年第3期。或者在“民族国家”的阐释框架中强调电影对于国家的使命,如周剑云、汪煦昌认为“影戏虽是民众的娱乐片,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影戏的使命在于赞美与发展国家之悠久的历史、优美的文化、伟大的民性、高尚的风俗、雄厚的实业、精良的工艺。⑤周剑云、汪煦昌:《影戏概论》,《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1924年。无论郑正秋还是周剑云都是明星公司的创业元老,他们的观点都颇具代表性。由此而言,当时的上海电影尽管已经完成初步的产业化,但是对于产业化的自觉和讨论远没有展开,这些电影产业先驱者的自我身份认同首先是文化人而非商人。
尽管讨论的着力点不同,我们从今天回望上海电影产业的起源阶段,还是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电影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海电影产业和上海其他工业的发展类似,作为上海20世纪20年代经济奇迹的一部分,受益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与产业环境。如沈芸的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激起了资本家们扩大再投资的欲望,在传统产业竞争已经渐趋饱和的情况下,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新兴的行业”。①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第34-35页。
上海电影产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崛起,依赖于以下条件的齐备:民营资本投注新兴产业;资本的流动带来人才的流动;②如明星的创业元老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等分别来自浙江宁波、广东汕头、安徽合肥、安徽歙县。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得观众产生观影需求,提供新的美学体验的影院兴起,传统的茶园戏院渐次沦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电影产业在当时是自发的产物,看不到任何政府的推动。其时正是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割据,政府基本没有力量介入,既无官方的电影生产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直到进入抗战时期的1938年方告成立),也缺乏强有力的电影审查制度,这是在20世纪中国较为罕见的纯粹由电影市场逻辑起作用的结果。
二
在当下思考上海电影产业的复兴,很容易直接链接到“老上海”的产业传统,忽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80年代的“新上海”的产业传统,以及90年代市场化改革后面对的一系列新问题。无疑,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产业格局实际上叠加着“老上海”与“新上海”的传统,不能基于市场经济教条地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电影体制视为产业发展的负面遗产,只有深入历史的肌理去思考,才能寻找到真实、客观的再次出发的根基。
上海电影产业在二三十年代的肇兴期是去地方化的,产业格局不被行政格局所限定。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产业结构被革命性地重塑,一种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电影体制开始形成。“1949年以后,文化部中央电影管理局(改名为电影事业管理局)被国家政权确定为统管全国电影创作生产、经营的最高行政机构。为了对全国各地电影生产发行进行统一掌握和调度,电影局对内部的行政权力结构进行了‘集权’式的组织建设——将各制片厂的创作生产决策权、人事管辖权与剧作、影片审查权,以及发行放映的经营管理权悉数集中于中央电影局所属‘两委四处一所’——故事片的剧本创作、审批、投产权,导演分配权归电影局艺委会;编剧权属于电影局所属剧本创作所;电影的发行放映经营管理权归属电影局发行处。”③石川:《“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体制与观众需求》,《电影艺术》2004年第4期。在这种集中于中央的电影体制中,“地方”被建构出来。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钟敬之、夏衍、于伶等来到上海接管国民党在沪的电影产业,如中电一厂、中电二厂、上海实验电影厂等。在此基础上,当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私营的电影厂也逐步并入上影厂,在公私合营的背景下,1952年2月2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成立,该厂由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与文华、大同、国泰、大中华、大光明、华光等电影公司合并组成,于伶兼任厂长。1953年2月2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并入上影,厂名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①上影厂的组建过程参见吴贻弓主编:《上海电影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3-57页。而上影厂的成立,属于新中国电影事业在地方布局的一枚重要棋子。1949年底,电影局以及下属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厂,渐趋形成了一种新的电影产业机制。
只有在新中国的电影体制之中,何谓“上海电影”才有确定的答案:上海电影,也即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诚如石川的感喟,“历史仿佛溪流一样在这一刻突然转了一个弯,而在这一刻发生改变的还不只是上海电影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客观情形,随之而改变的还有人们对于上海电影的一种想象和定义。因为从这一刻起,上海电影由传统意义上一个驳杂、纷繁、激进而又不无市侩庸俗的文化概念,忽如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被充分国有化、体制化的文化与经济实体,一个边界清晰,内涵确信无疑的国营单位”。②石川:《“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体制与观众需求》。
直到今天上影厂对于上海电影产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尤其在50—80年代,上影厂完全处于垄断性的地位。抛开情况特殊的“文革”时期不论,在“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年)期间,与“文革”后的“新时期”,上海电影在上影厂这套体制中同样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在“十七年”期间,就影片的数量与质量而言,“粗略地统计上影厂在‘十七年’时期一共拍摄了约221部影片,‘北影’和‘八一’一共拍摄了165部;‘东影’为189部。从总体数量上来看,以‘上影’为最。”③龚艳:《重建与“十七年”电影基调的形成——北京、长春、上海》,《当代电影》2013年第8期。就影片质量而言,上影厂在“十七年”期间拍摄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家》、《红色娘子军》、《李双双》、《红日》、《舞台姐妹》、《阿诗玛》、《白求恩大夫》等一批佳作。“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上影厂的电影产业地位更胜于“十七年”,如刘海波的分析,“在全国电影创作整体繁荣的大环境下,上海电影更是独占鳌头,1977—1987年的黄金10年间共出产故事片159部,平均年产16部,在全国100余部的年产量中仍然保持了约1/6的份额。尤为难得的是,这10年上海电影几乎囊括了历届金鸡、百花奖,并屡创观众人数纪录,各种题材全面开花,在观众心目中打出了上影品牌”。④刘海波:《论上海电影的传统品格及其消长》,《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这期间著名的有《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庐山恋》、《喜盈门》、《城南旧事》、《咱们的牛百岁》、《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
尽管50—80年代上海电影产业不再像民国时期一样居于压倒性垄断地位,但在电影数量与质量上,依然是我国最重要的电影产业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彼时上海电影产业正逐渐面对越来越尖锐的挑战,“上海似乎已无法重新获得像1949年以前那样的绝对优势,那时的上海是一个在落后国度中的现代性孤岛。今天上海所面对的是全国的竞争”。⑤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459页。
三
上海电影产业在90年代至今天所陷入的相对困境,构成了今天讨论“上海电影”产业复兴的问题背景。在当下的市场化时代,当我们讨论“上海电影”或“北京电影”的时候,讨论的对象是什么?笔者以为在当下识别电影产业的归宿,在于电影产业资本是否在这座城市注册、纳税与运营;导演、明星、编剧及产业链上相关人员是否长期在此生活与工作;是否在此形成新的电影潮流。①比如上海电影产业肇始阶段的明星公司,相对成熟的产业化必然生产出引领性的电影美学,诚如电影史研究者艾青的分析:“明星公司凭借着它以制片带动发行、放映,初步建立起中国电影工业运作的雏形;郑正秋的‘长片正剧’引领了20年代中期的‘国产电影运动’,从‘家庭伦理片’扩展至‘通俗社会片’,使中国式的通俗情节剧模式逐渐成型,而弓娇川的‘武侠神怪片’又将20年代后期的商业电影浪潮推向极致,改良主义美学与商业美学这两种范型的交织,并且通过‘通俗情节剧’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了20年代中国电影的主流美学形态;并且,它始终紧锁住中下层平民观众趣味,在中西、新旧结合上达至文化平衡,因此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还是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积累,乃至中国电影文化样貌的塑形,明星公司以开拓者的姿态奠定自身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艾青:《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明星影片公司研究》,第285页。换句话说,电影产业的中心,也即资本的中心、人才的中心与美学的中心。在这三方面,上海电影产业全方位陷入困境之中。
无论在民国的市场化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电影体制时期,上海电影产业百年来的优势地位,核心在于两点:资本与人才。在民国期间这两方面上海的优势对于其他城市都是压倒性的,在50—80年代上海享受着发达的电影传统,集聚了大量的电影人才,而在国家拨款、统销统购的国营体制下,资本的因素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随着80年代末期娱乐片的兴起与90年代以来市场化的改革,尤其是世纪之交电影产业化正式启动、电影管理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上海电影产业的颓势愈发明显,和北京电影产业的差距越来越大。
其关键的原因,在于资本层面上的差距。这里的资本不仅仅指电影产业的国家资本,尽管2001年上影厂改制后成立的上影集团和1999年成立的、并入北影厂的中影集团相比,在产业层面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个差距要小于上海电影产业与北京的差距,而且由于中影集团在电影发行方面的垄断性地位,这种差距在现有电影体制中是无法避免的。上海和北京相比最致命的差距,是民营电影资本的差距。就最新的数据而言,2014年国产片电影票房为162亿,光线传媒、博纳影业、乐视影业、万达影视、华谊兄弟这五大民营公司发行的影片票房,占据全年的58%。而这5家影视公司的总部,不约而同都在北京。尽管传闻说万达集团即将把集团总部从北京搬到上海,然而万达集团方面表示万达影视将继续留在北京。与这5家公司相匹配的上海影视公司,目前还一片空白。
上海电影产业这种民营资本上的差距,受制于上海整体民营资本与北京乃至于深圳等城市的差距。上海资本发展侧重海外资本与大型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发展一直是软肋。不无讽刺的是,上海电影产业衰落的周期,恰巧与“浦东大开发”所代表的上海经济崛起周期同步。著名经济学家黄亚生曾比较尖锐地指出这种“上海模式”的弊端:“‘上海模式’是典型的国家干预、倾向外资的模式”。②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7页。尽管其批评有可商榷之处,但至少在上海电影产业层面上得到印证。而人才的流动,永远受制于资本的流动,北京成为电影民营资本的集中地,必然导致电影人才的集聚。至于北京所拥有的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艺术类院校,辅助性地放大了京沪的人才差距。
以史为镜,和近百年的上海电影产业的辉煌相比,今天的上海电影产业丧失了最重要的资本环境,而这曾经是民国期间上海电影产业致胜的法宝,50—80年代国营机制下的资本庇护也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思索上海电影产业的复兴,要在资本的优惠政策、人才的扶植政策、文艺的引导政策三方面发力。
必须创造便利于资本与人才的流动环境,而在相对弱势的竞争形式下,上海需要政府的介入,强力搭建市场环境。这不是反市场规律,而是破除对于完全自发的市场规律的迷信,改革时代中国乃至上海的经济奇迹,一再证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是围绕上海电影产业发展上上下下的共识,2014年10月27日上海电影工作会议召开,提出7项共26条电影产业扶持政策,7项政策分别是:加大上海电影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落实上海电影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上海电影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加强上海电影人才队伍建设;实行建设差别化用地政策;充分发挥区县在上海电影发展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上海电影摄制服务机制。这其中的重点落在前3条对于上海民营电影资本的扶持上,在具体的做法上提出对于优秀电影实行政府补贴,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进出口关税上有所减免,并进一步扩展投融资渠道,对投资提供一定程度的风险担保。
以激活产业资本为抓手,无疑是抓住了上海电影产业复兴的关键。理想的上海电影产业资本盘活模式,在于第一步政府构建平台,放权让利,风险共担,切实地推动产业环境的建设;第二步有效退出,在资本被盘活之后放手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在此过程中,要警惕国家资本的低效运作,哪怕在第一个阶段也要秉持由市场决定、向市场开放的理念,克制越界的介入。尤其需要警惕在政府基金—专家委员会共同体之间运转的“好电影”,那种封闭而既没有艺术创新又没有产业生命力的电影,除了消耗宝贵的资源之外,不会产生任何的正面作用。
同样,电影人才不能圈子化、封闭化,必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促进公开而公平的人才流动与竞争环境。最终,就电影的内容与美学而言,在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放宽,也不要以“上海题材”画地为牢,以“海派美学”矜然自喜。上海电影产业的复兴必然从上海出发,但这是从“地方性”达致“普遍性”,而不是安于作为防御性的文化策略的地方化,目前对此似乎关注不够。只有弱者才谈自己的独特性,而强者都是争夺对于普遍性的定义,这一点不可不察。
尽管百年此消彼长,上海电影产业需要提振,但上海目前是唯一可以挑战北京电影产业中心地位的城市。从上海到北京,未来谁会充当电影产业的中心,充当产业资本的中心、影视人才的中心与电影美学的中心,在电影产业化方兴未艾的今天,还没有最终的定论。海纳百川,风云激荡,这是电影产业发展最好的年代,也是危机中孕育转机的时代。
责任编辑:沈洁
文化批评
-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的其它文章
- “游泳”图释
- 殷商时代的巫乐考察
- A Song for Rosefinch with Passion and Tenderness: Bookview ofThe Wondering Man along Wu Chou River
- A Discussion on Jin Hong’s Syncretization and Variation and the Mondern Man’sConsciousness in the 1980s
- What is Shanghai Film: The History and Opportunities of ShanghaiFilm in View of Film Industry
-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