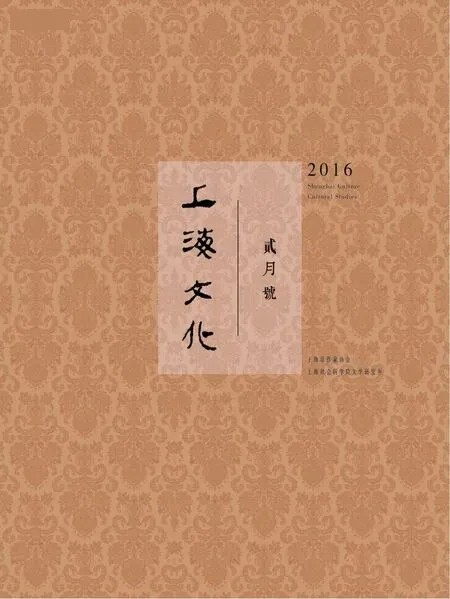历史的影子:探索中国古史的“巫文化时代”
夏锦乾
历史的影子:探索中国古史的“巫文化时代”
夏锦乾*夏锦乾,1951年生,男,浙江平湖人。《学术月刊》编审。主要从事文艺学与审美人类学研究。
内容摘要 本文提出“巫文化时代”的概念,并对此作了界定和论述。“巫文化时代”是指中国古史从颛顼经尧舜禹至夏商西周长达1500-2000年的特定阶段,它以巫为信仰,以巫占为行动指南的高度仪式化的时代,它以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结盟为基础,两者的结盟开创了这个时代的哲学、伦理和政治。
关 键 词中国古史 巫 家族血缘制度
一、题解
所谓“巫文化时代”,是指以巫为信仰,以巫占为部落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指南的高度仪式化的时代,特指中国古史从颛顼经尧舜禹至夏商西周的一个阶段,这个长达1500—2000年的阶段,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巫文化时代”所要揭示的,是巫文化的中国特色及其它对中华民族性的深刻影响。虽然巫术是人类早期世界各民族的普遍现象,但是世界各民族的巫术大多是作为一种日用技艺而存在,且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大多被宗教所替代。唯独在中国,巫文化上升到政治、哲学和伦理的高度,不仅关涉人的日用功利、吉凶命运,而且还涉及人的终极信仰和灵魂寄托,巫文化以极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了一个巫文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巫作为最高权力、最高智慧和最高美德的代表,压制了宗教的产生。巫文化所开创的大易之道和天人合一、敬天法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等观念与精神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神韵和独特性。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巫文化时代”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像影子一样追随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朝代、各个阶段,以至于可以说,不懂得中国巫文化时代,就不懂得中国历史传统。这就是本文把巫文化时代看作中国历史的“影子”的第一层含义。“影子”的第二层含义是,“巫文化时代”虽然对中华文化传统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加上受各种观念的影响,近百年以来对这一时代本身的完整研究、揭示还付阙如,因而至今它还只是一个“影子”般的存在,未露真相。这可分四种情况。其一,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巫文化时代”被认为“上古史事茫昧无稽”,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转引自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35页。因而只能是一个神话传说时代。胡适认为:“以现在考古学的程度来看,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①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从东周的老子和孔子开始,蔡元培称之为“截断众流”的方法。顾颉刚也认为,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只可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它们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②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所有关于“巫文化时代”的知识都是来自后起的时代,由此,“巫文化时代”的主体价值被彻底悬搁。
其二,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古史的“巫文化时代”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序列,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巫文化时代”便分别划入史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制社会,乃至封建制社会;③这样完整统一的“巫文化时代”被观念和主义所肢解,失去了它自身的本来面貌。
其三,考古学与人类学取得的成果,逼近对于“巫文化时代”的认识。考古学大量地下文物的发掘,特别是二里岗商代资料、二里头夏代资料及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以器物的直接证据回答了古史辨派的“神话传说”论。张光直的“青铜时代”,谢维扬提出的“酋邦时代”,叶舒宪的“玉文化时代”,卜工的“古礼时代”,以及苏秉琦的“重建中国史前史”主张,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都直接指向“巫文化时代”的探索,且成果显赫。在这些成果之下,“巫文化时代”确有呼之欲出,显露真身之势。但是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仅把巫作为一种原始现象,从而未建立起以巫为中心的观察视角,要么怀疑巫在这个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要么把巫孤立起来去研究,不与氏族制度联系起来,换言之,巫仍然被局限于日用技艺的研究,使得“巫文化时代”仍隐而不露。
其四,文化哲学的研究,提出了巫性和巫史传统的概念,真正触及“巫文化时代”的基本问题。王振复在20世纪90年代初连续推出《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和《周易的美学智慧》两书,提出巫学、巫性等概念,把中国巫术看作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文化智慧和美学智慧。李泽厚则在90年代末发表《说巫史传统》,他指出,“在孔子之前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王振复和李泽厚的研究超越了巫术的日用技艺层面,凸显了中国巫术的本质,真正为“巫文化时代”点了题。但是两人或是因设定的研究方向所限(王振复),或是停留于“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初衷(李泽厚),都未来得及对“巫文化时代”的内容作全面、充分的展开,使得“巫文化时代”的真面目始终难以彰显。
由上可知,百年中国学界对于“巫文化时代”的认知,通过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在不断地加深和逼近真实。如今是到了全面认识和揭示它的真相的时候了。
二、巫文化时代: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的结盟
中国古史的“巫文化时代”是建立在中国巫术的独特性之上的。中国巫文化的独特性决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历史的机遇以及中华先知们适时地把握机遇中形成的。这个关键的机遇便是发生在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距今约4500年)①关于“绝地天通”,原始文献见《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国语·楚语下》等三种。。在这一事件之前,中国巫术作为日用技艺可以说与世界各民族巫术并没有什么两样,中国的文明路向也是与西方一样,走在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共同路向上。因此,当时颛顼集团统辖范围内的“九黎之乱”,即部落民众各祀其神,不服从集团中央权力统治的抗争,表现的并不是中国的独特性,而是人类的共同性,它应验了恩格斯所说的私有制的兴起,必然冲击氏族权力的预言。但是它只应验了恩格斯预言的一半,恩格斯预言的另一半认为,在这场私有力量与氏族权力的冲突中,氏族社会必然解体。西方雅典、罗马和德意志的氏族社会都沿着这一路向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国家公共权力的建立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恩格斯曾带着强烈的历史辩证意识调侃道:“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然而,恩格斯预言的这一半在中国并未成为现实。“九黎之乱”并没有冲垮颛顼所领导的东夷部落集团,相反它被颛顼采取非常手段所平息,氏族(家族血缘)这个“美妙的制度”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巩固了。中国的文明路向在恩格斯指出的历史关头折向了与雅典、罗马、德意志完全不同的方向!大家知道,当年颛顼的非常手段就是著名的“绝地天通”。它是指氏族部落针对九黎之乱中“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乱德”现象,强制取消了部落民众祭祀神灵、直接与神灵交通的权利,把巫术祭祀权收归部落首领所有,由部落首领充当祭神的巫师,从此之后,民众只有通过巫师(首领)才能与神交通。“绝地天通”的实质就是争夺祭祀权的政治较量,因为有了祭祀权,也就有了挟神灵以号令天下的权力。颛顼的胜利,在挽救了中国的氏族制度的同时,也把巫术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此在这个舞台上,巫术从日用技艺,转为政治治理工具,巫术占卜成为部落政治指南,巫术仪式成为部落政治的意识形态。颛顼既是部落首领,又兼任公众巫师,意味着巫术的力量与家族血缘的力量结成了神圣同盟,它形成了神灵—巫师(首领)—民众三元结构的新的家族血缘制度,区别于以往二元的“民神杂糅”式的家族血缘制。
由颛顼所开创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家族血缘制度奠立了“巫文化时代”的基础。按照《国语·楚语下》的说法,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周宣王时代。③《国语·楚语下》说,颛顼绝地天通之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这就是说,颛顼的绝地天通模式贯通于尧舜禹和夏商西周,它们都因循于同一个制度。《论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大概是实有其事。
如果说,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的结盟所形成的三元结构(神灵—巫师[首领]—民众)构成“巫文化时代”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弄清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的结合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文化效应,它怎样主宰了“巫文化时代”的文化创造?这正是解读“巫文化时代”的关键,这也是以往巫术研究和家族血缘制度研究都不曾提出的问题。
毫无疑问,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的结盟是中国历史传统中最精彩而伟大的创造。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的相遇,使两者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彼此都带上了对方的色彩。从巫术而言,出于部落治理的目的,巫术从个体的日用技艺变为部落政治工具,实现巫术个人性向公众性的根本转变;又由于这种公众性巫术的权力掌握在少数首领之手,巫术的权威性、神秘性进一步加强,原先极为淳朴、简洁的巫舞、巫占、巫咒及其他仪式因此就极大地发展起来,它们的功能不再单纯地起到与神灵交通的作用,而是另有着规训民众、统一意志的作用;与此同时,巫术又发展出一套严密而精致的解释系统(巫术禁忌),每当巫术失败,巫师权威遭受危机时,解释系统起到缓冲、转移和补偿的作用(失败常常归因于民众触犯禁忌)。这套系统成了家族血缘制度最早的意识形态理论。同样,家族血缘权力由于借助了巫术的力量,使得权力带上巫的气氛。首先是部落首领兼任了巫师,成为了半神半人、亦神亦人,充满巫性的强权统治者。这样的统治者正如当年顾颉刚所说,它随时可以抬出上帝和先祖来,帮助他解决一切问题。顾颉刚称之为“鬼治主义”。①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见《古史辩》第二册。由此,家族血缘的祖先神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它们与巫术神统合起来(有些人认为这是先人们对家族血缘的祖先崇拜的滥用,这是没有看到巫与家族血缘联盟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家族血缘权力在巫术的推动下重建了自信,并不断膨胀。巫术从本质上说是意志对环境的控制术,坚信意志能改变一切。涂尔干曾说,“只要人类还不知道事物的秩序是不可改变和不可松动的,只要他们把它看作是反复无常的意志作用,那么他们很自然就会认为这些或那些意志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事物”。②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巫术正是人类在这种认知阶段的产物。巫术的这种自信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家族血缘权力。从本义上说,家族血缘制本当有极强的地域性,恩格斯曾说:“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4页。但中国的家族血缘权力却完全摆脱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地域偏见,它以天下为己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信“内心力量可以支配外物以至天地”。④李泽厚:《说巫史传统》,见李泽厚:《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由上可见,巫与家族血缘权力在相互配合协作中各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属于中国文化所独有的。除了这种改变之外,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由于两者的结合,巫的观念、原理和精神与家族血缘权力的意志、精神相互渗透,最后凝结为“巫文化时代”所特有的哲学、伦理和政治。
三、巫文化时代的哲学、伦理与政治
首先看“巫文化时代”的哲学。客观上讲,在绝地天通之前,巫与家族血缘制度早已存在,它们对于自然、宇宙和现实世界早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巫术意志在控制环境中对不可预测的变化极其敏感,他们“观象于天,观法于地”,看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便有了“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感悟,因而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去把握、掌控环境,这是早期巫术的一个天才发现,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就是这个意思。弗雷泽《金枝》关于巫术的两个原则:“相似律”和“接触律”,说穿了也是巫术对于“变”的认识。①弗雷泽:《金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9页。如果说早期巫术发现了“变”之道,那么家族血缘制度发现了“生”之道。作为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家族血缘制度完全依靠家族血缘的繁殖、生衍,这导致了对生殖的崇拜(包括生殖器崇拜)和祖先的崇拜。“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不息”概括了这个制度的信仰。在绝地天通之后,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的结盟,同时也就意味着“变”与“生”两种思想、两个信仰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构成了“巫文化时代”哲学的基调。这可分以下三点来说。
第一,“变”与“生”的结合推动了中华先祖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从“变”与“生”出发,就可看到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和生成之中,且变中有生,生中有变,每次变化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新生。这是中华先祖对世界的最高哲学感悟。这种感悟最充分地体现在被称为“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准”的《易》之中,因而《易》也成为“巫文化时代”的最高哲学。《易》原初是一本古老的占卜书,相传由伏羲创作,但只有到文王八卦,才真正形成了卦、爻、辞、象的完整体系。《易》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对应着现实生活中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的融合过程。更值得注意的是,《易》的结构64卦381爻,看似复杂,却严整有序,它是通过“—”、“- -”两个符号的不同组合而“生成”不同的卦象,可以说以“—”、“- -”两个符号来表述世界之变,“效天下之动”,是《易》最基本的思路。而“—”、“- -”两个符号无论是“一阴一阳”,还是“一阖一辟”,都是“生”的象征,是“本体的两性”和“本体两性的化育”。②见周予同:《孝与“生殖器崇拜”》,庞朴等编:《先秦儒家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155页。对八卦“一”、“- -”符号的解释,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有男女生殖器说、蓍草竹节说、结绳说和数字符号演变说等,但大多属猜想。唯男女生殖器说与当时制度与文化深刻相联,影响最为广泛。周予同和郭沫若都持此说。所以《易》在本义上就是以生释动,以生摄变。这也成了“巫文化时代”的最高哲学的本义。
第二,“变”和“生”的结合,既凝结为《易》的符号体系,这个体系又统制了人的感性世界。在这个体系之下,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 一切感性事物都不成为它自身,而成为了神的语言。比如,在我出门时乌鸦叫了三声或有一阵风吹过,这乌鸦的叫声和一阵风在当时人看来,就是神派遣使者送来的忠告。出门是福是祸?就得通过巫占问过神之后才能得知。《易·系辞》说:“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通过问神,识读卦象,知道出门的吉凶之后,方才决定行动。这样,通过《易》的符号体系和操作体系,巫的意志与家族血缘权力的意志实现了向现实感性世界的双重渗透。对“巫文化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渗透着神意的现实世界,其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含着神意的“象”,是人所追求的真实世界。
第三,最重要的,是部落首领推动了“变”和“生”的结合,他与巫的身份合一(圣人),主宰了“巫文化时代”的思想和哲学。《易·系辞》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效之、象之、则之,显现了“巫文化时代”思想和哲学的性质、特点,以及与其他一切文化思想和哲学的区别所在。
再看“巫文化时代”的伦理与政治。它们同样体现为受到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结盟的深刻影响。家族血缘以“生”为大德,以与祖先血脉的远近、长幼关系分出亲疏,确定尊卑贵贱。简括起来便是尊尊、亲亲。尊尊是等级,是秩序;亲亲是仁爱,是亲情。每一个处在家族血缘群体中的人员都在严格的血缘等级中确定自己的身份,下辈孝敬上辈,上辈慈爱下辈。《周易·家人·彖辞》说:“父父、子子、兄兄、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更具体地说,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不同的身份虽然要求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和情感表现,但归结起来仍然是尊尊与亲亲。一个家族人员有再多的角色:他既是父亲,又是儿子,又是孙子,又是丈夫……只要懂得了尊尊、亲亲,就不会搞乱自己的身份;同时,正由于他的多重角色,确保了他的身份责任付出多少,也会收获多少:当他作为儿子孝敬父亲时,他同时也得到了儿子对自己的孝敬。
在家族血缘制度中,上述家族血缘伦理就扩大为国家的和天下的伦理。家族血缘的父子关系等同于国家的君臣关系,尊尊、亲亲转换为国家伦理中尊卑有序、贵贱有别、亲疏有分的上下等级关系。这是任何家族血缘部落在绝地天通之前就已经经历的事实。但是从家族向国家乃至天下的扩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本质上它是对血缘和地缘的突破。通过征服和联盟,异族人员不断加入进来;通过垦殖和战争掠夺,地盘不断扩张。以颛顼所属的东夷集团为例,当时它就分布于“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的一大片土地上,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氏族的规模了。因而东夷之“夷”已包含了“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种。这种突破同时也威胁到家族伦理的解体:异族和异地的人们在尊尊、亲亲的秩序中既然只能处在最底层的地位,他们只能以抗争来发泄不满,触发绝地天通的“九黎之乱”正是颛顼集团所辖势力范围内地位较低的苗人部落向中央权力的对抗。巫术的出场有力地巩固了颛顼集团的权力,这表现在伦理和政治上,便是礼的确立。
礼的本质就是用制度形式确立的仪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任何违反家族血缘权力利益的行为,都被当作违礼、无礼而在被排除之列。但礼更重要的是仪式感,它是在仪式中“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它迫使个体与家族整体保持一致。因此礼比法更具有引导性和劝慰性,它强化了等级制度而又不失亲情,特别适合于尊尊、亲亲的家族血缘伦理。因此“巫文化时代”把“礼”作为政治统治的最重要的统治工具:“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①《礼记·祭统》。“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②《礼记·礼运》。“以礼治人”可以说是巫文化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而礼的建立,正是在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结盟的基础上实现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巫的自然神为家族血缘输入了强有力的信仰力量,自然神与祖先神的结合重建了家族血缘制度的信仰体系,从而为“礼”奠定祭拜的对象。据《礼记·祭法》,天子除了祭家族神③《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之外,还要祭天、祭地、祭时、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祭山林、祭川谷、祭丘陵、祭百神。这正显示巫的自然神的力量。另一方面,巫的仪式性装饰了家族血缘的权力意志,从而更加柔化了家族血缘制度的统治方式。巫术离不开仪式,仪式是巫术的存在方式,通过仪式与神沟通,并借助神力实现巫术意志,这是巫术控制环境的原理。④参见拙作:《试论巫术政治的仪式化》,《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因此,在巫的观念中,坚信仪式的极端重要性,它是巫的意志与神的力量的完美聚合,它使巫术意志带上神的色彩,具有了神圣性和崇高性,并能驾驭一切。当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结盟后,巫的这种观念便给家族血缘的权力意志带来了灵感。把巫的仪式转换为家族血缘制度的仪式,这就是“礼”的产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⑤《礼记·祭统》。家族血缘权力正是通过“礼”把它的意志抬高到“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的神圣高度,从而借助神的力量达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⑥《礼记·礼运》。的目的。因而礼在“巫文化时代”得到极大发展,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有周公“制礼作乐”,它们都体现了巫文化时代的伦理和政治。
四、“巫文化时代”的盛衰
中国的“巫文化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文化成果。以上仅从哲学、伦理和政治的简述,就已经看到它所达到的文明高度,是当时任何其他文明都难以企及的。精神文明如此,物质文明同样如此。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大量龙山文化的都邑遗址、祭坛遗址,以及陶器、玉器、青铜器和甲骨,它们仿佛在用同一种语言叙说着曾经经历的辉煌。这个一向被当作虚无缥缈的“传说时代”,现在正在撩开它的神秘面纱,显现它的惊艳丽姿。
从历史的过程而言,“巫文化时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完整过程。从绝地天通的颛顼经尧舜禹夏商,它基本处在一个不断上升、兴盛的时期,到商代达到鼎盛。殷周隆替,巫文化时代开始步入它的衰退期,直到西周末年。而春秋的礼崩乐坏,正是一个伟大时代结束的象征。为什么“巫文化时代”会从西周开始走向衰落?春秋的礼崩乐坏难道仅仅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吗?它与“巫文化时代”的发展逻辑没有关联吗?这些问题都关涉“巫文化时代”的深层次矛盾,应该作一讨论。
前文已述,“巫文化时代”本质上是一个巫与家族血缘权力结盟的时代,说白了就是家族血缘权力利用巫的力量加固自身统治的时代。巫对于国家决策的重大影响,可以从太史公的一段话看得非常分明:“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尚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①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这也正是“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礼而远之”②《礼记·表记》。的由来。当然,巫对政治的巨大作用,终究是以家族血缘权力主体为前提,以遵循家族血缘制度内在逻辑为职守。家族血缘关系原本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生物性关系,血缘之亲和血缘等级在动物界也很常见。但人类能够将这种原始性的关系提升为一种制度,借之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状态之下,凝聚血缘的力量,使自己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这是人类的创造。但是,将家族血缘关系作为制度,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是家族整体与个体的矛盾。家族血缘的存在、延续总是以个体存在为条件,但家族血缘制度却要把家族整体的利益和价值抬到至高的地位,要求个体献身于整体。其二,家族血缘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血缘的生殖力是无穷的,通过生殖使家族在空间上无穷扩大,在时间上绵延万世。但“家族”的本义正好相反,它是指一个有严格范围、界域的血亲群体。所谓“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③《礼记·丧服小记》。就是说家族血缘范围,以“我”与父母、儿女三代算起,直系的五代,最多是九代之后,就不能算作同一个家族之内了(亲毕),旁系也同样如此。家族范围的限制,意味着家族血缘制度始终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它追求自身发展的努力,在到达一定的阶段之后,这种努力也变成了瓦解自身的力量。
之所以说上述两大矛盾是家族血缘制度的基本矛盾,就因为它们贯穿于这个制度的始终。当然不同阶段,矛盾的重点亦不同。颛顼的绝地天通时期,“九黎之乱”是由于私有力量的壮大而向部落整体的挑战,表现的正是整体与个体间的矛盾。绝地天通可以说是借助巫术的力量,以凸显部落“一个人”的意志来回应家族血缘制度对于个体的呼唤,使矛盾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随着首领(巫师)的地位日益巩固,第二个矛盾就激化起来。它集中表现在家族继承权的争夺——一个对于家族血缘权力来说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从最初的禅让制到世袭制;在世袭制中,又从兄终弟及,无弟然后传子,改为舍弟传子;在子继制中,又从诸多儿子中选择,到嫡长制,确立嫡庶之法,立子必立嫡,立嫡必立长;同为长子(君王女人太多,同时有很多长子),则又看生母之地位,有“立子以贵不以长”一条管着。我们看到“巫文化时代”的权力继承,从宽泛的“选贤与能”,走向命定论,采用的是越来越严格的排除法,直到只剩下一人为止。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是把远亲、旁系都排除掉,确立世系(直系)的继承权;直系传承又以代际传承(父传子)排除横向传承(兄传弟);在代际传承中,又以嫡长传承排除所有庶出子弟;在嫡长传承中,又以母贵为先。排除法的目的在息争,王国维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①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由此,巫文化时代所谓“天命”,最根本的含义便是由这种“继统法”所规定的各人的地位身份。
但是,王国维的“定之以天,争乃不生”,事实证明是错的。继承权的争夺本质上是家族血缘制度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因而本意要平息矛盾的排除法,无法从根本上限制血缘生殖的力量,因此,它每排除一次,就把王权朝末路上推进一步。待到周代灭商之后建立嫡长制,意味着再无可排除了,除长子之外的大批子弟,就只能用分封制来把他们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以满足他们对于权力分享的欲求。可见分封制同样是家族血缘制度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②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中就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势也”。表面上分封体制平息了内争,又让分封出去的诸侯们为周朝王权开拓了疆土,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从而形成周代宗法血缘的大一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事实上,这只是周王室的一厢情愿。因为分封出去的诸侯们虽然与周王室有割不断的血亲关系,但是,经过三代五代,随着血缘繁衍的推移,他们与周王室的亲情渐行渐远,他们不愿再做周王室的“王臣”,周王室的共主地位由此衰落。这样,与其说分封,不如说周王室亲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削弱自身力量的对手。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们都已“六亲不认”,相互吞并,史称“礼崩乐乱”,实质仍然是由家族血缘制度基本矛盾激起的继承权争夺,只不过是从朝廷“内争”发展为“外斗”。
如果说家族血缘制度的两大基本矛盾主宰了“巫文化时代”的盛衰,那么,巫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毫无疑问,巫对家族血缘权力竭尽忠诚,且不说“九黎之乱”时期它凭借绝地天通横空出世,对家族血缘制的稳固立下汗马功劳,就是在此后整个“巫文化时代”,它都是历代君王执政的主要方式。《礼记·表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因此当“巫文化时代”处在上升、兴盛时期,巫与家族血缘权力也处在蜜月期,君王不违巫卜,而巫卜也把家族血缘权力当作自身最好的代理者和寄生地。④在整个“巫文化时代”,巫文化的高度发展,其中也包含了巫文化的多样性,其中巫礼、巫仪、巫卜、巫筮、巫史、巫医、巫乐、巫教等都空前发展起来。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巫性的发展,而不是巫的理性化。但是,巫卜的力量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本消除家族血缘制度的基本矛盾,当基本矛盾激化导致王朝衰落时,巫也从巅峰走向败落。具体表现就是人们
开始普遍地质疑巫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周灭商,在关键的朝歌一战,姜太公竟然违背巫术占卜,逆“天意”而获胜;相反,一向应顺龟卜的纣王却一败涂地,临死却大惑不解:“我生不有天命在天乎?”①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413页。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左传》记载了大量此类违卜的例子。②《顾颉刚日记》第11册,第23页。参见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87-391页。巫的权威的跌落,还表现在人们对天的不敬。《诗经》有数量不少的“怨天”诗,如:“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我龟既厌,不我告犹”③分别见《诗经》“雨无正”、“节南山”、“小旻”。等,这些都显示西周末年巫的神威已今非昔比。以至于到春秋战国时代,巫的欺骗性被彻底揭露。④《荀子·天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月食而救济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韩非子·饰(饬)邪》也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矣。”李斯说得更加直接:“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长久,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从此,巫卜逐步被排除出家族血缘权力的中心,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巫的衰落,也只能流落到民间。“巫文化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家族血缘权力依靠巫的力量来统治的模式行不通了。一种新的家族血缘制模式——郡县制正在周秦之变的历史动荡中酝酿着……
责任编辑:沈洁
海上观澜
文化理论前沿
-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的其它文章
- “游泳”图释
- 殷商时代的巫乐考察
- A Song for Rosefinch with Passion and Tenderness: Bookview ofThe Wondering Man along Wu Chou River
- A Discussion on Jin Hong’s Syncretization and Variation and the Mondern Man’sConsciousness in the 1980s
- What is Shanghai Film: The History and Opportunities of ShanghaiFilm in View of Film Industry
-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