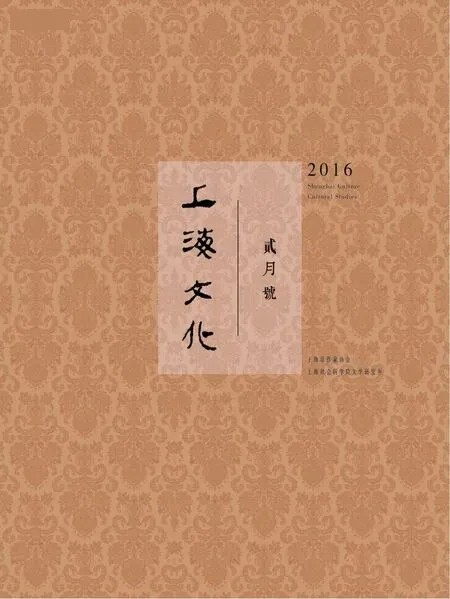信仰的重建,是为了重建的信仰——兼及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美学选择
范 藻
信仰的重建,是为了重建的信仰
——兼及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美学选择
范 藻*范藻,男,1958年生,四川成都人。四川文理学院教授,《四川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理论和文化评论。
内容摘要 新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而其中曾被我们忽略而又最关键的是信仰的重建。针对商品意识、务实心态和权力崇拜的现实,我们的文化建设在信仰的倡导上,应该是对真善美的本能式和无条件的信仰,为此的美学选择策略就应该是“为天地立心”和“为生民立命”,进而才能谈到“为往圣继绝学”和“为万世开太平”。
关 键 词信仰重建 中国文化 美学选择
一、引言:文化建设:补上信仰一课
那位从远古走来的信仰女神,以其绝对的自由承诺给每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心灵以绝对的自由选择。凡夫俗子的我们在凡俗的世界是不自由的,然而作为信仰者的人,在信仰的天地是自由的。而问题是,我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是天上之仙,还是地上之灵,是水中之妖,还是山中之狐,是庙中之神,还是寺中之佛;抑或是基督教之上帝、伊斯兰教之真主、佛教之释迦牟尼、道教之玉皇大帝,甚至就是理性王国之绝对理念、大同世界之共产主义。这里涉及一个带有世界本体论和生命终极性的话题,我们普通国民的信仰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的生活依然是浑浑噩噩地沉睡不醒,我们的人生仍然是懵懵懂懂地执迷不悟,我们的生命照旧是如动物般的行尸走肉。为此,潘知常教授在2003年就热切地呼唤:“要在美学研究中拿到通向未来的通行证,就务必要为美学补上素所缺乏的信仰之维、爱之维,必须为美学找到那些我们值得去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受难的东西。它们就是生命本身。”①今天,在中国文化建设向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际,潘知常教授又直指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并真切地倡导“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日益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30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①潘知常:《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上篇)——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上海文化》2015年第6期。
中国的文化建设,在经历了“启蒙”的沉重和“救亡”的艰难后,今天应该进入“信仰”的重建阶段了。或言之,中国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在面临“启蒙”的未竟和“救亡”的未完之现状,置身国际政治的“新战略”和国内经济的“新常态”之形势,信仰的重建,既是启蒙要义的新内容,又是救亡使命的新发展,当然也是文化建设的新要求,不用说,这还是美学重振的新启示;直言之,我们需要来一次信仰的重建!
二、重建信仰的因由:世界之夜将至半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在“人认识你自己”的希腊理性精神的烛照下,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完成了“三次还原”的伟大壮举:但丁在《神曲》演奏中,把人从上帝神灵的护佑下还原为世俗的人;培根在《新工具》的解析中,把人从蒙昧主义的笼罩中还原为理性的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的论证中,把人从高贵地位的膜拜中还原为自然的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就是当代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过程,一神教替代了多神教,知识论替代了信仰论,功利性替代了精神性,世俗化替代了神圣化。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匆匆走完了西方现代化数百年的历程,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政府崇尚GDP思维的唯我独尊到民众的“有钱的才是老大”。“历史中的人越来越认识不到自己,认识不到属人的天命,一味意欲去认识、利用实在的对象。”②刘小枫:《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诚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之夜的贫困时代已够漫长。既已漫长必会达至夜半。夜到半夜也就是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的时代甚至连自己的贫困也体会不到”,甚至“一个劲地渴求把自己掩盖起来”。③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在这“世界之夜将至半”的时分,信仰沉入了沉沉夜色里,呼唤着我们重建通往信仰的巴比伦塔。
(一)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消失
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上帝”不仅是全知全能的代名词,而且是先知先觉的代言人,甚至就是人类理想的化身和彼岸世界的象征。尼采在1882年撰写的《快乐的知识》一书中,借“狂人”之口宣称:“上帝死了!”它直接隐喻着人类悲惨的现实处境:高度的科技文明驱逐了信仰的存在,极度的此岸欢乐放逐了彼岸的意识,过度的世俗利益挑战着神灵的价值,世界变成了荒漠,人生成为了碎片,孤苦无告的人类已经彻底失去了永恒的精神乐园。是的,上帝死了,终极信仰的彻底失落,彼岸世界的不复存在,那么此岸世界的人类,依仗着科学精神的所向披靡,还有什么不能、不敢做的呢?
如果说,西方的“上帝死了”意味着彼岸信仰的虚化,那么我们的“上帝死了”则直陈主流信仰的弱化。20世纪的中华民族由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先知开启的现代启蒙精神,被因为民族要独立、国家要革命和人民要富裕的“救亡”行动长期挤压以至于放逐。在“向俄国人学习”中看到希望,进而一边倒向苏联尝到甜头后,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所有西方文化都贴上“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标鉴,只剩下一种美妙而虚幻的大同世界的信仰了。在这样的功利主义目标的引领下,直接形成了狂飙突进而又势不可挡的50年代的阶级斗争、60年代的文化革命、70年代的反帝反修、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市场经济,直到新世纪的全民娱乐。可以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更在乎此岸世界的民族,如看重眼前利益,关注身边琐事和强调感官享乐,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就有“不语怪力乱神”和“未知生焉知死”的意识。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从未诞生过,更何况死亡。对这种没有彼岸世界而只有此岸人生的中国文化,李泽厚说道:“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出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没有反理性的冲动和想法,哪里还会有非理性的信仰精神?
(二)主体死了,理性意识的消亡
如果说“上帝死了”意味着秉持信仰为上的西方古典文化的终结,那么“主体死了”则意味着坚持理性为大的西方现代文化的结束。主体之死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所宣告的:“‘人’完全是‘新近的创造物’,刚刚诞生,便迅速走向衰亡,他的存在不足200年。”②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01页。福柯所谓的“人”是作为知识对象和认知对象的抽象意义上的人,经历了近两百年的人文主义的熏陶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人已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理性力量,然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人类的文明和理性,导致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死亡。
既然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被人类引以为自豪的“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的人都“死”了,那么不论是作为人创造和发明的知识、规则和技术等理性,还是本身就是知识、规则和技术塑造的人,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如果说西方文化充满着尊重知识、服从规则和信奉技术的传统,那么中国文化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更崇奉的“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玄乎,“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玄机,如我们视之为“国粹”的中医、国画和书法即是,这其中的知识是靠默记、规则是靠师承、技术是靠领悟;及至近代则视西方的物理机械为“奇技淫巧”、政治法律为“异端邪说”。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后,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无畏勇气下,不讲科学,不要理性,不守规律,“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亩产出二十万”和“多快好省”、“多拉快跑”,这类的荒诞和谎言畅通无阻;甚至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竟然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禁锢创造、反对创新、贬斥创意的主体的人确实“死”了,唯有服从“最高指示”的愚昧主义大行其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势推进,曾经的权力崇拜置换成了金钱崇拜,曾经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变成了“跟着感觉走”,于是,“成功即是手段合理”、“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反理性和非理性,成为新的信仰,深入骨髓。而高贵理性精神、人文情怀和绝对信仰,只能向隅而泣!
(三)作者死了,创造精神的消遁
主体的死亡直接导致理性意识的分崩离析,而最能体现人类理性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当然是文学艺术,他们遵循真善美的最高价值,依据知情意的本真动力,创作了人类文明典型形态的文艺作品;可是,当代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1968年平地惊雷般地发出了“作者之死”!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大胆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和“读者的诞生”,巴特的“《作者之死》彻底瓦解了传统的作者主体地位,作者不再是作品唯一的主人,而仅仅是个临时的表述者”。①唐芙蓉:《论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作者死了”的说法与其说是一个文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理念,质言之,这是一个由文学创作问题而引发的文化创造话题。
如果说“作者死亡了”,那么文学复活了,然而事实是,文学依然被商品经济无情地放逐;如果说“读者诞生了”,那么文学自由了。然而现实是,文学仍然被权力意志冷漠地驱逐。由此可见,“作者死了”涉及的根本问题不是文学的存亡,而是文学的创造精神的有无。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一直是人类精神殿堂的高贵者、人类生命历程的引路人,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为我们探寻气象万千的心灵奥秘,也不仅为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艺术享受,更是以其自由的创造、大胆的想象和奔放的情感,为我们树立起了创造的精神、想象的自由和情感的本位意识;因为一部文学的历史就是作者对真善美无比服膺和热切追求的“天路历程”,其“九死犹未悔”的执着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就是创新,“原创这个词最好只能限于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艺术,用来特指生命的‘本源’绽放”。②王乾坤:《文学的承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03页。“生命的‘本源’”其实就是生命进化的正能量和进步的向心力。遗憾的是,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的联姻,加上互联网火上浇油,模仿盛行,克隆蜂起,曾经美丽的原创意识荡然无存,备受推崇的创新精神被弃如敝屣。由此可见,作者的死亡,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危机,也是文化创造的危机,更是人类创新信仰的危机。
“上帝死了”,人类生命依然青春不老;“主体死了”,大千世界还是五彩缤纷;“作者死了”,文艺园地照旧姹紫嫣红。但是,我们的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延年益寿;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为了抒发喜怒哀乐。这是由于在以理性精神和世俗观念为表征的现代化的强势挤压下,传统的宗教日益式微,曾经的信仰逐渐淡化。那么,我们需要信仰吗?更需要真善美的信仰吗?答案毋庸置疑!
三、重建信仰的要义:为上帝存在打赌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也许当地球上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太阳仍然照常升起。对于有意义的生命而言,死亡并非是坏事,而我们的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延年益寿;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衣食住行;创作的文艺,不仅仅是为了抒发喜怒哀乐。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借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说法,在“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的背后,应该是灵魂皈依的渴求,而灵魂的核心毫无疑问是信仰。那么,信仰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在哪里显现呢?为此,沉迷于声色犬马的路易十五说:“在我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沉醉于权谋机诈的魏王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马克思曾引述一位记者的话描述资本家的贪婪:“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于此,我们不禁要问,面对纸醉金迷,置身灯红酒绿,被有限与无限困惑着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它还真的存在吗?17世纪的天才哲人帕斯卡尔“毫不迟疑地赌上帝的存在”,就是赌信仰的存在,因为“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①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于基督教文化而言,上帝与信仰一样,是无须证明的先验之理;于当今中国文化建设而言,信仰之于人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此,我们要重建对真善美绝对而无条件的信仰。
(一)因为信仰真而求真
真理与信仰,孰重孰轻?这是一个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公案。坊间道:“信仰让人偏见,真理让人豁达;信仰让人快乐,真理让人痛苦。”两者究竟是何种关系?前者更注重科学性、可行性和集体性,看重的是改造世界的逻辑力量和实践效能;后者更注重非理性、理念性和个体性,看重的是塑造主体的意志力量和精神效应。一定意义上两者貌离神合,在人类精神文明的程度上呈现高度统一的状态,即客观功能的共通性和主观服膺的普适性。真理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圣性,最高形态的真理还有着前无古人的原创性,它能发挥出改造世界的无穷力量。而信仰呢?仿佛如“空穴来风”似的神妙,还恰似“君权神授”般神圣,更有着“神灵附体”样的神奇,虽不能理性分析但感性灵验,虽没有物理功效但心理应验,所谓“信则灵”。尤其是占世界人口总数33%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教的真理本身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它关涉人和世界的生命中心问题……信仰乃是整个生命的行为,基督教发出的号召不是要加入一种宗教,而是要人进入新的生命,因此,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在于他恪守宗教形式。”②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46页。是的,认定了真理的信仰价值,就无条件地服从信仰的真理意义。这就是因为信仰真而求真,信仰真是不需要理由和缘由的。
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在个体生命的丰富中,如何才能做到“因为信仰真而求真”呢?那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只以事情本身的是非为是非。既秉公执正,诚信守正,勇敢坚持真理,随时改正错误,如“虽九死犹未悔”的屈原;又虚怀若谷,博采众长,敢于挑战权威,乐于扶助后学,如现代中国数学泰斗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还自我反省,不断完善,大胆怀疑一切,接受他人质疑,如“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砍头不要紧”的夏明翰。他们在守护信仰和坚守真理的过程中,愿做真理之信徒,而决不做信仰之奴隶。以真理支持信仰,生命可得自由;以信仰支配真理,生命必将枯萎!
(二)因为信仰善而向善
就像信仰与真理的孰高孰低一直困扰着我们一样,信仰与善德孰先孰后也一直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信仰赋予人类积极乐观看待宇宙万物和人世规律的心态,因为有了信仰,人类才有了深刻的洞察力和仁爱心,才能看到光明的未来和体味到美好的存在。一个人具有了信仰,就具有了善良的情怀和美好的情操,就具有了大山般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大海般宽广博大的胸怀。正如卢梭说的那样,“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的美德”。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人类之所以向往善良和追求美德,是因为有“原罪”意识的先在性存在,人类的祖先或个体的前世犯了罪,后世的我们就必须乐善好施以赎罪,用今世的善来赎前世的恶,那么,今生今世或此时此刻的善,并不是现实的要求和环境的差使,而是发自内心、良知和本能,此情此景的善,早已不是一般道德范畴的品德含义,而上升为生命的自觉境界和自为状态了,直言之,就是因为信仰而向善,由于向善而才信仰。也就是不因为外在境遇的恶劣和所处环境的艰辛,都将善良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正如牛津大学法哲学教授约瑟夫·拉兹所说的:“道德善,不仅在于人们能按照道德规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还体现在:当环境极其恶劣,充斥着各种邪恶的诱惑和压力时,依然向善如故。”①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0页。好一个伟大、纯粹的“向善如故”!
信仰是一个人主体意识达到的最高境界,当他把善作为个体存在价值的首选和人生意义的基础之时,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直至舍生取义,就会变成他生命的自觉,进入无怨无悔、甘之若饴和助人为乐的美好境界,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方面堪称典范的是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巴尼亚籍的德兰修女,这位伟大的女性,放弃财产、地位、名誉、健康、青春,一生在世界各地行善,尤其是长年在加尔各答为贫穷人服务,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她说过:“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爱,已深入骨髓、融入生命,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三)因为信仰美而爱美
这里所谓的“美”不完全是一种形式愉悦的情绪感受,也不仅是一种意象美妙的意蕴感悟,而应该是像浮士德在经历了种种酸甜苦辣后由衷的赞叹:“真美啊,请你留下来。”即有限的人生存在与无限的宇宙时空、有限的生活形式与无限的生命内容之间的诱惑与憧憬、痛苦与无奈、欣喜与愉悦的综合性感受和本体性存在,实际上就是生命的自由与限制而导致的“悲本体”,尽管充满“悲”,但有意义的生命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必将置之死地而后生,奋起抗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遥遥无期的守望中,走向生命的圣境,在走向十字架的漫漫征途中,期待上帝福光照射,从而体现出生命力量的坚毅与顽强。因此,信仰视域中的美学是生命式的美学,更是宗教般的美学。正如潘知常教授所说的:“为什么审美活动和宗教有关?其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宗教是人类的信仰的最集中的体现。”②潘知常:《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命途多舛的人类犹如茫茫大海中的孤舟,夜空中的北斗星恰似指引航向的信仰,遥远的彼岸恰如美神的召唤,这种对美的渴望俨然成了人类生命的本能和全部,在崇高而神圣的信仰引领下,没有功利考量,没有现实目的,因为这是以人类生命的爱来体悟人类生命的美。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崇高的信仰,所有的在旁人看来苦不堪言的事务、三灾八难的经历,都会因为他的执着而变成兴趣,都会因为他的兴趣而变成“没有原因”的爱意和“毫无事由”的热情,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凭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唐太宗才有“三千宠爱在一身”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情怀。照常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甚至当事人本身也不能予以理性解说,当然也谈不上宗教意识了;但他们表现出来痴情与痴迷,就是一曲壮丽的生命永远的赞歌和信仰必胜的凯歌。
人类之所以要因为信仰真善美而追求真善美,是因为他们将真善美置于先验性的存在和本体论的高度,即不管这个世界如何肮脏、世道如何黑暗、人心如何阴鸷,他们都根据生命的进化原则和文明的演进规律,对真理、善良和美好的存在深信不疑,还甘之若饴地躬行,并坚信它们是不证自明的“道”,即《圣经》开篇所言的“太初有道”,于是我们就和万能的上帝打赌,看究竟是人类伟大,还是上帝伟大。这一豪赌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信仰获得了永恒的胜利。
四、重建信仰的意义:人诗意地栖居大地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东坡,仕途失望,人生失意,颇为失魂落魄,而一首《定风波》与其说是显示了他旷达的情怀,不如说是他的生命情怀的浓缩,著名美学家王世德教授说:“苏轼不同于白居易前期积极用世,后期闲适独善;苏轼是积极坚持理想与旷达超脱融合为用。苏轼也不同于陶渊明挂冠而去,悠然见南山,采菊东篱下,苏轼是身处坎坷而能旷达,坚持理想而不改其乐。”①王世德:《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8页。这与其说是诗意的情怀与情义,不如说是信仰的毅力与意义,因为他将既往的“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更新为了“乐天知命”的道家情怀和“超然出尘”的佛家胸襟。在这“出与入”、“隐与仕”、“去与留”的纠结中,抽身而起,他的世界顿时鸢飞鱼跃、他的生命为此春暖花开。由此观之,这就是信仰的魅力和魔力,这更是信仰的意义所在。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显现的呢?为此,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着“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醍醐灌顶”的神农喻示、释主妙语、上帝真谛。或许一旦拥有了它,我们的文化建设恰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的生命意义犹如“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们在苦难的大地上,尽情地享受着“诗意栖居”的美妙和欢乐。具体而言,信仰之于我们究竟有哪些意义呢?
(一)神学启迪:可“为天地立心”
信仰一词,本来自宗教,是任何教徒都必须具有的共同认识。从汉语词汇的构词法看,“信”是相信、信服的意思,“仰”是仰视、敬仰的意思,合起来,大概是指初民们对头上的苍穹和星云一类高远而深邃的东西探究和膜拜,以后慢慢变成了不同宗教的神祇,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释迦牟尼和道教的玉皇大帝。因此,要明白信仰须先明白宗教,要明白宗教须先明白神学。尽管本文要牵涉许多宗教知识和背景,但它的重点不是论证宗教的信仰意义,而是借助宗教的神学视界和境界,思考信仰之于神学的启迪,那就是“为天地立心”。18世纪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说:“人并不是感性世界的产物,他的生存的终极目的在感性世界里是不能达到的。他的使命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超越了一切感性事物。”①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与人的使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7页。天地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是指抽象的自然存在,所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而人之所以能感受到天高地厚,是因为我们为天地命名了,将之视为人格神的存在之物,即天为父、地为母,为天地立心,即为我们生命的起源找寻依据,并赋予天地以神圣的意义。这就是视信仰为“天命”所赋、“天意”所为,是人在茫茫宇宙中的神圣使命。
如何将这神圣的使命化为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和自为行动呢?首先,要明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作用是什么。即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必须抛弃曾经的“战天斗地”和“改天换地”的宏愿,换为顺应天地和敬畏天地,把人类的存在真正融入这经天纬地之中。其次,要明白我生长在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前者是为天地“立法”,那么这个就是为天地“立命”,尽管天地本无“命”、更无“心”,因为人的诞生而使得天地焕然一新,而如何做到与天地的和谐共处,应该成为神学意义上的信仰启示录。
(二)史学启示:能“为往圣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如孔子、孟子一样的圣人,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随着社会的变迁,如东汉印度佛学的传入和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传统的儒家学说面临中断的危险,于是,程朱理学家们要竭力恢复他们的正统地位。“往圣”是否具有今天的价值?“绝学”能否真正延续?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今天的我们对历史的态度。诚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清理“奥吉亚斯的牛圈”,固执于历史的陈年老账,而是清醒地看到“雅努斯的两个面孔”,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找到现实的立足点,这就是如“安泰的双脚”一样,不但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而且要让历史启示现实,这就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倡的:“实体被符号所替代,现实被关系所替代,意义被阐释所替代。从此以往,意义不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建构,一种‘创造’。”②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第77页。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过程中,与其说是“发现”历史的价值,不如说是“创造”历史的意义。往事如烟,曾经的爱恨情仇和生杀予夺,都会慢慢沉入时间的长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唯有珍视现实,珍惜生命!
也许,这是东方的看重当下的历史观,它以“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为理论前提,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基督教的道德观以人性恶为基础,否定人类获得美德的能力,将人类置于最软弱无力的境地。或者说,这种信仰就是以人类的软弱和堕落为前提的;因为善是外在的,是上帝赐予的恩典。只有辩证地扬弃过往的权威和过时的典籍,才能更好地沐浴时间的温暖神恩。由此看来,“为往圣继绝学”,并非是一件易事,一定意义上也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重建信仰的历史启示,就应该是也只能是让“往圣”们经历向死而生的凤凰涅槃,让曾经的“绝学”在历史的断崖处重新绽放现实的娇艳花朵!
(三)人学启发:能“为万世开太平”
人学应该是广义的人生哲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如何在一个充满危机与挑战、诱惑与憧憬、变幻与迷茫的时代,安稳而平凡地度过一生,所谓“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是芸芸众生起码而切实的“生活标准”,因此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才成为人们千年不朽的美好回忆。就这个意义而言,每个人的现实使命就是尽力完成一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任务。在这个人命运与时代机运的复杂交集中,我们是应该认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其实这是一个二难选择,因为我们都不是英雄,正如北岛在《宣告》中写道:“我不是英雄,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渴望太平的生活和宁静的日子。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人学现实或人生哲学的关键问题,即如何看待世界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因为“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若能够回答人关于生与死、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俗与圣的困惑,能够调整和理顺人的行为,人就感到生活的充实和有意义,反之,人则感到困惑、焦虑、苦恼、彷徨、沉沦,人的生存不能离开意义或价值世界的支撑”。①陈树林:《危机与拯救——蒂利希文化神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这个最高的意义或价值,毫无疑问应该是人的信仰。作为普通百姓,我们虽不能为万世开太平,但我们渴望万世太平,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应该体现在以道家的精神从事儒家的事业。
人生是什么,是人学哲学永远没有止境的思考。尽管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答案,也是每个生命要经历的不同遭遇,而人生为什么呢?我们的探索和思考永远在路上,更是期待每个生命给出的不同答案。在探索和思考人生意义的学问中,我们有了汗牛充栋的种种说法,但它们都是仁智相见,显示出相对真理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深信有意义的生命应该在纷繁复杂的对象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应该充满家国情怀和家园意识,将古老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信条作为我们的生命信仰。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生命没有义务和能力“为万世开太平”的,他唯有能做的就是坚信“好人一生平安”!
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哲荷尔德林低吟着:“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与其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生憧憬和境界,不如说是理想主义的生命情怀和信仰。在我们追求的种种信仰中,荣华富贵未免低俗,大同世界确实高远,而唯有“诗意地栖居”充满着生活的温暖和美学的神圣。它对我们重建信仰的意义,既不是形而下的“为往圣继绝学”和“为万世开太平”,而应该是形而上的“为天地立心”和“为生民立命”。看来,我们距离重建的信仰,只有一步之遥了!
五、结语:美学选择:为生民立命
是因为信仰真而求真,是因为信仰善而向善,是因为信仰美而爱美?还是为天地立心的神学启迪,为往圣继绝学的史学启示,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学启发?从文化建设角度看,它们都是必须而应该的。而文化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声势浩大的‘文化建设’多指向文化强国的国家目标而少有文化化人的个体要义……究其实,是它未能有效地树立并强调文化的个体意识,缺乏关怀个体生命的终极情怀。”①范藻:《打通文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那么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壁障的思想尖兵就应该是:我们期待并呼唤美学的闪亮登场。我们之所以在文化与美学之间找到了对话桥梁,是因为不论是文化还是美学,最终关注的都应该是个体意义上的人。
然而,这个“个体意义上的人”,自从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后,就开始了“精卫填海”的上下求索、“愚公移山”的矢志不渝和“嫦娥奔月”的超凡出世,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时无处不经受着肉身的沉重与灵魂的凝重的煎熬、入世的艰难与出世的畏难的考验、此岸的困惑与彼岸的诱惑的纠结。这种悲本体的生命犹如哈姆莱特一样,在“是生存,还是死亡”的迷茫纠结和煎熬中,微弱的希望之光在彼岸世界悄然呈现,那犹如上帝伸出的拯救之手——信仰!然而,对于一个缺乏“终极信仰”和注重“实用理性”的民族而言,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接地气”和“有骨气”、“体民生”和“济苍生”。
如果说无缘无故之爱是信仰产生的“先决条件”,那么求真向善爱美就是重建信仰的“先在因素”;如果说文化建设要引进的宗教启示是“为天地立心”,那么重建信仰要遵循的美学选择就是“为生民立命”。的确,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为生民的“安身”,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为生民的“立命”仍然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今天,由于美学,当然是生命美学选择的加盟,明天我们信仰的园地,一定会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因为这不但是符合个体生命的正能量意义,更是符合人类文明的主流性价值。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的彰显,而且是“国际价值”的体现。最近,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于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他向世界发出了重建人类文明信仰的宣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②《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工人日报》2015年9月29日。
那就让我们带着信仰出发吧!
责任编辑:沈洁
学术专题(中国巫文化时代的信仰与审美)
-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的其它文章
- “游泳”图释
- 殷商时代的巫乐考察
- A Song for Rosefinch with Passion and Tenderness: Bookview ofThe Wondering Man along Wu Chou River
- A Discussion on Jin Hong’s Syncretization and Variation and the Mondern Man’sConsciousness in the 1980s
- What is Shanghai Film: The History and Opportunities of ShanghaiFilm in View of Film Industry
-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