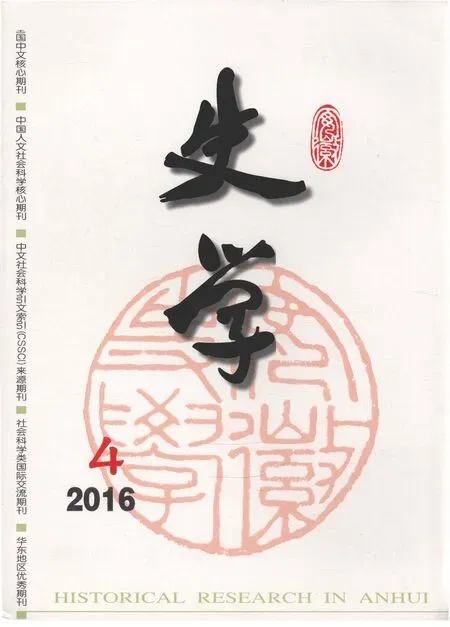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入职北大与“旧派”之动向
——以朱希祖为中心
程尔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入职北大与“旧派”之动向
——以朱希祖为中心
程尔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在民初北大的人事变动中,朱希祖作为正牌章太严弟子先于他人入职,颇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其入职并未引起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应,旧派众人其后渐次离开北大,与朱希祖并无直接关系,原因亦各自不同,但均对校长何燏时主政下北大未来的趋向怀有背离之感。虽然后来更多太炎门生进入北大,代替桐城派等旧派人士居于核心地位,但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评判,此番新旧更替实有“以旧易旧”的意味。这说明在民初数年里,新旧世界虽已有移形换位之势,但“新”、“旧”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朦胧,其清晰的标准尚在确立与制定之中。
关键词:北大;朱希祖;旧派;新旧易位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经历了一场重要的人事变动,一些旧学精英逐渐退出,一批所谓新派学人开始入职。这次变动的结果,“太炎门生派”代替“桐城派”,“夺取”了北大乃至京师的学术阵地,而北大校方欲去除桐城派势力多被视为最重要的原因*作近似表述的论著颇多,如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84页;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吴民祥:《由“庙堂”走向“讲堂”——“新思潮派”与北京大学的近代化》,《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等。另,王天根的《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提出是北大“校长何燏时、学长夏锡祺”在文科中引进太炎门生时,“对桐城派采取了打击压制的态度”。卢毅对太炎门生进入北大的原因做了综合评析,见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对此,当时就有人评论道:“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佚名:《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又见《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稍后钱基博亦认为:“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朱希祖在这场变动中,作为正牌弟子先于他人入职,颇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然而学界对其入职北大的过程少有细致追究,对其入职原因的论述亦稍显片面*这其中,多数学者将朱希祖在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上的突出表现视作其进入北大的直接原因,即是显例。如朱元曙云,“自‘读音统一会’之后,朱希祖先生等章门弟子在京师名声大振。4月12日傍晚,因沈尹默介绍,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访朱希祖,聘其为北大预科教授。”见朱元曙:《国语运动中的朱希祖及章门弟子》,《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周文玖亦云,1913年朱希祖“代表浙江省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国语读音统一会,因所提注音方案获得通过而受到学界瞩目,会议结束即被北京大学聘为预科教授,以后又担任文科教授”。见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本文借助新近出版的几种日记,旁及其他史料,详细梳理朱希祖入职北大的整个过程,并观察同时期旧派的反应与动向,在重构相关史事的基础上,重新检视“新”与“旧”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通过细部的讨论,展示出彼时北大新旧两派在发生易位之初一种颇为朦胧的状态。
一、朱希祖入职北大始末
1913年2月10日,朱希祖到达北京,作为浙江省代表,准备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与其同为浙江代表的,复有胡以鲁、杜亚泉、汪怡安、马裕藻、钱稻孙、许寿裳、杨麹和陈濬等人*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2页。。在这9人中,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及胡以鲁均曾在日本求学,并同受教于章太炎。
朱希祖到京后,先与沈尹默宿于西打磨场旅店,很快两人搬至海昌会馆,与一同来京的戴克让同寓*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0、96、97页。。次日,朱希祖至辟才胡同拜访了钱玄同之兄钱恂、钱恂之子钱稻孙,以及钱恂之女婿、时任教育部次长的董鸿祎。之后,又接连拜访了不少京城名流。2月15日,朱希祖开始到教育部参加读音统一会,此后几乎从不缺席。
2月24日,朱希祖在读音统一会上与汪荣宝、马裕藻等支持议长吴敬恒用《广韵》、《音韵阐微》的决定,认为当“先审定声母、韵母,以定反切之标准,众多默认”*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0、96、97页。。由于此次会议上的表现,朱希祖开始受得北京学界的关注。不过,其能够入职北大,却并不仅仅缘于此。会议之后的2月26日晚,董鸿祎邀请名流聚饮,朱希祖因故未去,同住的沈尹默则前往参加,很晚才回到寓所。朱希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他听闻北京大学校校长何燏时欲延其为文科大学教授,且似乎是因为钱恂和董鸿祎的“揄扬”,才有此机会*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0、96、97页。。实际上,2月21日,钱恂就曾索要朱希祖简历,“预备举荐至北京大学”*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7页。。
朱希祖没有说明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来源,但很可能是参与当晚董鸿祎宴席的沈尹默。因为沈尚在浙江时即通过许炳堃得到何燏时、胡仁源约请其往北大教书的机会*沈尹默:《我与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页。,所以他与这些消息人士距离相对更近。重要的是,上述这些材料可以说明,于朱希祖尚未在读音统一会上大放异彩之前,在钱恂的举荐之下,何燏时就已经有延聘之意。换句话说,朱希祖能够进入北大,并非仅仅因为其在读音统一会上有所表现,而是缘自“去旧”思路下(详后)何燏时、钱恂、胡仁源、董鸿祎等人的共同观察。这其中,校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的首肯自然是决定性的,但与钱恂一起“揄扬”朱希祖的教育部次长董鸿祎同样重要。董鸿祎于1912年7月出任教育部次长,其与夏曾佑、何燏时、钱稻孙、鲁迅等人颇熟识,上任不久即时常聚饮以增进彼此感情。8月31日晚,就曾“招饮于致美斋,同席者汤哲存、夏穗卿、何燮侯、张协和、钱稻孙、许季黻”*鲁迅:《鲁迅日记》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页。。民初教育部长更迭频繁,至朱希祖入北大时,已先后有蔡元培、范源濂、刘冠雄、陈振先四位部长,而董鸿祎自范源濂任职期间就职次长后,凡历三位部长而岿然不动,人事关系稳固,人脉颇广。虽任次长,却从某种程度上掌握着教育部的实际权力,故在朱希祖任职北大一事上,其所起到的作用可想而知。
在2月26日日记中,朱希祖提到马裕藻告其法政校长邵伯絅亦有请其任教员之意。面对获得两校延聘的情况,朱希祖谦逊地表示“自问学殖浅陋,不敢当此”,但同时,他感到原来就职的杭州教育司方面事甚烦扰,不欲继续参与其间,故决定暂时“混迹京华”*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第97、100、112、112、112—113、114页。。至于能否执教北大,则并不抱持过分的热望。
3月5日,朱希祖接钱玄同信,得知杭州方面事态愈发严峻,“不可一朝居”,便与钱恂商议,让钱玄同“亦来北京”。因为“大学校校长正有请中季任文科教员之意”*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第97、100、112、112、112—113、114页。。可见,此时盘桓于何燏时脑际的教员名单中,朱希祖与钱玄同是并存的。据钱玄同3月26日收到的钱恂来信云,下半年钱玄同即可入都,且“此行必多住,劝令将书籍尽兴携带”*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页。。4月3日,事情忽起变化。本来何燏时、胡仁源商议聘朱希祖为北大文科教员之事各方“均已允”,但钱稻孙向何燏时推荐叔叔钱玄同后,何氏改变了主意,舍弃朱希祖,“乃允中季与尹默教国文”*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第97、100、112、112、112—113、114页。。这种局面朱希祖未曾料到。他原本以为自己入职北大基本已板上钉钉,与钱恂商量让钱玄同亦北上时,万不曾想到会出现彼进己退的情形。朱希祖对此颇感失望。经过慎重考虑,朱希祖决计让贤,以“全中季之事”,“且全友谊”*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第97、100、112、112、112—113、114页。。随即,朱希祖给钱玄同写书信一封。
虽然决计让贤,但朱心中无比抑郁。次日上午,朱“心绪恶劣,百感交集,懒于行动”,竟罕见的“不至读音统一会”。4月5日,“上午枯坐无聊,心滋不乐”。4月6日,与沈尹默、戴克让在南味馆饮酒时“语甚不乐,怅归早睡”*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第97、100、112、112、112—113、114页。。显然,朱希祖一连数日心绪不佳,与无缘就职一事恐不无关系。先前未得浙江教育司第三科科长之职务(2月26日《日记》记此事),如今北大教职又只能“让贤”,去留皆不如意,心中郁闷,实在所难免。
4月10日,峰回路转,钱恂自浙江湖州给身在北京的钱稻孙发电报云:“大预尽先逷而后德”,意即大学预科教员聘任事,先朱希祖(字逷先)而后钱玄同(字德潜)。闻听此报,朱认为“中季已不允就大预国文教员矣,故推余去承受也”*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第97、100、112、112、112—113、114页。。4月11日,朱希祖接到北大聘书,请其担任预科国文教员。12日,校长何燏时来到朱希祖寓所,邀其就职。14日,朱与沈尹默至预科学长胡仁源家,不值,旋赴北大,顺利与胡仁源“接洽预科国文事”。随后,朱希祖特意到北大藏书楼借书数部,盖有开始积极“备课”之意。15日午后,在北大校内会见“校长何燮侯、预科学长胡次珊”后,朱希祖的任职正式开始。
二、“旧派”之反应与动向
从1913年2月26日有初步传闻,到4月11日朱希祖接到请其任职的北大信函,再到15日拜见校长、预科学长,正式履职,前后不过四十余天,事不可谓不急。由此不难看出何燏时、胡仁源等人希望更新换代的急迫心情。此后,旧派人士林纾、姚永概、马其昶以及陈衍等人,纷纷退出北大,似乎印证了所谓“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的趋势。那么,作为正牌太炎弟子的朱希祖入职北大前后,桐城派等“旧派”人士究竟有怎样的反应,他们后来退职的原因究竟为何?是否确与朱希祖关系密切?
首先必须看到,桐城派由于占据文坛多年,受到学人厌弃实由来已久。据周作人观察,“在清代晚年已经有对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动倾向了。只是那时候的几个人,都是在无意识中做着这件工作。”*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自张百熙主持复办京师大学堂后,聘桐城名士吴汝纶为总教习,桐城派开始在京师大学堂取得优势地位。民初时,桐城派在北大虽仍有较强势力,但学校内部对桐城派已有诸多不满,尤其集中在被视作桐城派一员的林纾身上,这种情况到何燏时担任校长时达到顶点。
何氏对林纾在北大“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沈尹默:《我与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223页。。林纾也知道何燏时对自己印象不佳,故在给五子林璐的信中称“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且“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但他认为何之所以这样做,乃“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李家骥、李茂肃、薛祥生整理:《林纾诗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72页。。林纾的观察基本准确,因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建不久,张百熙邀请严复担任副总教习*严复:《与张元济书》(十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7页。,后任命为译书局总办,当时林纾就在严复所掌之译书局任“笔述”。1904年严复离开京师大学堂赴上海,林纾留任,并于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经学教员,后又于1910年改教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授古文辞*张旭、车树昇编著:《林纾年谱长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91—173页。。林纾在北大任职逾十年,如今已入民国,学校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亦已去职,林纾却位置稳固,继续在北大课堂教授古文。新官上任的何燏时虽与林氏并非仇雠,但难免会产生厌烦的心理。朱希祖拥有太炎门生、留日学子、浙籍同乡等多重身份,恰好符合何燏时等人的需求,最终被选定为预科国文教员,讲授新式国文,以显示与旧式古文义法的不同。
不过,旧派人士对太炎门生隐然带来的冲击,感受并不相同。受到抨击最大的林纾反应最为激烈。1913年5月,京师大学堂文科学生毕业,林纾在赠言中表达了对当今“讲意境、守义法”文风受到挑战的愤怒,他呼吁诸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林纾:《畏庐续集·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林琴南文集》,中国书店1985年版,影印原书第20b页。。下半年离开北大后,林纾仍旧不忘讥刺对唐宋古文提出批评的章太炎等人“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撦为能,以饾饤为富”,并将太炎门生称作“庸妄之谬种”,说他们“腾譟于京师,极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扰蔑正宗”,实则不过“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而已*林纾:《畏庐续集·与姚叔节书》,《林琴南文集》,影印原书第16a-17a页。。不过,林纾的讥讽或许是对章太炎曾经对其轻蔑与羞辱的反弹。章太炎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嘲讽道:“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语甚峻苛。一向自视甚高的林纾岂能忍受一个后辈如此蔑视,所以才会对太炎及其门生反唇相讥。离开北大后,林纾一度进入徐树铮所办的正志学校,并担任校长。此后,其始终想借助徐树铮的力量反击曾迫其离职的北大新势力,但终未能实现,引得陈独秀谑称:“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罢。”*陈独秀:《随感录·林纾的留声机》,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相较林纾,其他在北大任教的旧派人士似乎更多地是在较为平静的心态中感受到,时代环境发生着变化,且正迫使他们脱离文化的主流方向。
若依时间顺序,与林纾同为福建籍的陈衍更早离开北大。陈氏于1907年在学部任职时,开始兼任京师大学堂经学讲席。其时“经学非校中正课,诸生科学繁,功之者盖寡”*陈衍:《朱芷青哀辞并序》,《庸言》第1卷第15号。按,朱芷青即朱联沅,乃朱希祖叔父,《朱希祖日记》中多有记载。,故教学所费精力并不甚多。1909年,陈被聘为分科大学史学教授。武昌起义后,陈衍离开北京,回到福建老家。但他挂念其在北京的书籍等物,同时想看看“乱后情状”,遂于1912年5月再至北京。不久,严复任更名后的北京大学校长,力邀陈衍“续主经史学讲席”,陈“姑诺之”,实际上却“雅不欲就”。不过,适逢此时福建有当政者欲强行启用陈衍,陈为避其锋芒,决定暂不归闽,留在北大任事,但显然这不过是权宜之计。1913年2月,大学分科考结束,陈衍即决定南归。此时北大校长已换为何燏时,他恳请陈衍“留任续班讲席”,还特意让担任文科教务长的桐城派人物姚永概来劝言,但陈没有答应。3月1日,陈衍出京,5日到达上海*陈声暨编,王真续编,叶长青补订:《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陈步编:《陈石遗集》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9、2020—2022页。。
同样离去的还有曾奉命劝留陈衍的姚永概。姚本在安徽大学任教,1912年大学堂改为大学校后,受严复之请,到校担任文科教务长。何燏时主掌北大后,姚起初并未受到触动。且何燏时曾当面向姚议林纾之长短,或亦说明姚在何的眼中或许并不那么“旧”。
1913年1月22日,姚永概“赴大学校,晤何校长、汪伯吾(馨,庶务长,黟人)、夏浮筠”*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224、1225、1227页。。31日“访董次长,小谈”*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224、1225、1227页。。此后几乎每日赴校视事,尽心尽责。2月24日,“校长令拟文科预算,先开哲学二门及中史、中文四类。”其后两天认真写文科预算,26日“交校长”*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224、1225、1227页。。从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几乎看不出其欲离开北大的任何迹象,但在姚永概简单扼要的日记文字背后可以看到,由于民国初建后北京政局不稳,家乡安徽又时有负面消息,其难以在京安心执教。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一时间,背后主谋引发诸多猜测。姚永概身处京城,对此有比较直观的感受。4月4日日记云“近日谣传甚多”。8日他说:“国会成立,先是谣传甚多,竟无他故。”19日,他又写道:“连日谣传甚多。”刺宋案后,种种乱象、流言蜚语致使人心惶惶。姚永概不欲多言,唯以“谣传”二字示其困惑,然已足见忧虑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朱希祖开始任国文教员,大概因其隶属预科,故对此人事变动,姚并未记载。
5月4日,陈卿云告诉姚永概,“报载电柏督在皖被刺,受伤甚重”。柏督即时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柏文蔚,“二次革命”爆发后,柏氏明确表示支持,结果遭到袁世凯的忌恨,此番被刺,令已深感忧虑的姚永概再次对时局产生怀疑和失望的情绪,颇有离京返回安徽一探究竟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恐皖有变,又久未得家书,心中殊念。”*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5月7日,姚永概访夏曾佑,夏氏认为南危北安,劝其接眷北来,姚为之心动。但他很快决定,不接眷北来,而是离京南归。5月9日,姚永概到北大请假,“并会议招生及预算事”。10日,至国民大学,“与吴君商辞”,随后又赴北大,“借支薪水”。11日,托人“转告政法功课请二兄代”。13日,姚永概赴北大辞行,17日晚乘“顺天船”离京南归*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
回到安徽后,姚永概走亲访友,处理各种事务,并曾应柏文蔚之召饮。6月26日,收到北大电催返校,略迁延后于7月15日返回北京。但其心中对故里诸事牵挂不已,返京仅5天,即因“连日未得桐耗,心念家中无人,妇聋妾孕”,于7月20日“决计南行一视”。于是“留书于校长,荐二兄暂代”*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21日,姚永概乘火车再次离京,于25日到达桐城。此时,安徽徘徊在独立与否的政治选择中,姚永概与马其昶等人观察时局,常至当地议会、自治公所议事。同时,不断与在京的二兄姚永朴等人通信,互通京师、桐城两地消息。
9月22日,姚永概再次返京,次日即赴北大,不意当日“忽闻部中议定停办分科”,文科作为北大分科之首,亦有停办之虞。9月24日,校长何燏时“约全堂议挽回停办”,但其方法姚并不赞成,无奈因为与何“甚淡泊,不便言”*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10月7日,“史生鼎来言,何燮侯闻停办之说乃余赞成,心殊介介”,且何做出回应,“已裁教长”。姚一直担任文科教务长,将此职裁去,显然似乎针锋相对,这令姚永概十分不满,但他不欲与何争论,只是表示此事“不值一哂”*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与校长渐生不和,时局长期动荡,姚永概感到身心已疲,北大文科惨淡经营的现状,更令其心生退意。10月18日,姚永概叹道:“文科生只十人,又有二人欲改学法政,其八人尚有日本一生焉。教习只二人,余门尚缺。”他痛感“校长既不专任之余,又不加紧办理,部中又有停办文科之说”,“余归心怦怦矣”*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23日,姚永概“闻部令已到校,停文科”*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最后的希望终于破灭。11月4日,姚永概到北大参加毕业式后,5日即登上火车*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4、1235—1237、1242、1248、1249、1250、1250—1251、1252页。。数次请辞北大教职的姚永概最后一次告别北大,辞职离校*《1914年5月北京大学分科周年概况报告》,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启程南返。
三、“入职”“去职”之分析
因具备了符合何燏时“改朝换代”要求的诸多条件,在钱恂、董鸿祎等人的“揄扬”和推荐下,在读音统一会上“大放异彩”的朱希祖进入北大*沈尹默或许也推荐过朱希祖,但沈氏自述中不曾言此,尚需更多材料予以佐证。。此后,太炎弟子陆续跟进,形成了新的核心势力群体。与之相伴的,是林纾、陈衍、姚永概等人的纷纷退出,全面让出了桐城派等旧派人士在北大的权势与地位。细绎这个双方易位的过程,盖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朱希祖作为首位进入北大的正牌太炎弟子,其入职过程颇可视为开启北大新、旧更迭洪流的象征符号。符号的背后,是旧派人士的渐次离开。此二者在时间上有重合关系,但并无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当事双方一开始也并未意识到彼此的进退是后来者所断言的一场“新旧之争”。不可否认,民初北大不断发生着新旧易位,朱希祖及随后章门弟子的涌入与桐城派等旧派人士的退出,的确在这个趋势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但如果细化到个体之上,促成此事的何燏时等人以及利害双方,其对于“新”、“旧”的判断恐怕与今日之推想不尽相同。
其二,林纾、陈衍、姚永概三人中真正与太炎弟子有对抗关系者唯林纾,但其更多是出于校长何燏时之判断乃至好恶,朱希祖等是被动地与林纾产生了矛盾。不过,并非仅仅何燏时(可能也包括董鸿祎)等浙籍人士对林纾不满,江苏兴化人李详时亦在北京,同样不满林纾及其他喜欢“望文生义”*此林纾语,见钱锺书:《石语》,《钱锺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的桐城文士。1908年,李在《国粹学报》刊发《论桐城派》一文,对清季自封“桐城派”者颇为不慊,他认为,自曾国藩及其门人之湘乡一支之后,“世之为古文者,茫无所主。仅知姬传为昔之大师,又皆人人所指名,遂依以自固。句摹字剽,于其承接转换,‘也’‘邪’‘与’‘矣’‘哉’‘焉’诸助词,如填框格,不敢稍溢一语,谓之谨守桐城家法。而于姬传所云‘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阙一’,则又舛焉背驰”,他甚至提出,桐城派之“源既竭矣,派于何有?”*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12期。李详这篇文章对清季自诩桐城派者极尽讥讽之能事,但从姚永概的日记来看,姚在京时,李常与其相过从,可知李本人对桐城派并无恶感。李自己亦坦承,“余与今之能治桐城古文者,皆在相知之列”,之所以写这样一篇文章,并非要批评那些能治桐城古文,其学又能在古文之外者,李氏此文的真正目的,“系专为奉桐城一先生之言而发”*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12期。,而这位先生,就是宗奉桐城文法,却不愿被纳入桐城派系谱的林纾。对此,在后来和钱基博的信中,李详明确说自己“时正见《畏庐文集》,胸中不平之气无所发泄”*李详:《与钱基博》四函之二,《李审言文集》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9页。,才有文中的激烈之语。不过,李详在《论桐城派》中对桐城派的批评实际有所收敛,在和钱基博的书信中也客气三分,唯与以书画名于世的陈含光通信时,将其对桐城派的负面看法和盘托出。他说:“详所恨者,渠辈概不读书,专致意于起结伏应,守为义法。”*李详:《与陈含光》四函之一,《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056页。李详精于《文选》学,其治学方法若以后来钱玄同等人的眼光看,恐怕也属于旧式,但就是这样一位大概会被趋新人士归为旧派的李详,也同样对桐城派略有微词,尤其对于林纾,更是有着“不平之气”,足见林纾当时树敌之多。由此,何燏时将矛头首当其冲地指向林纾,亦在几分情理之中。
其三,林纾等人离开的原因虽有所不同,但基本均对北大未来的趋向怀有一种背离感,且对于新世界心存忧虑,甚至不满。如林纾,其辞职并不仅仅因为何燏时“思用其乡人”以及朱希祖等太炎弟子的冲击,辛亥前后面对新、旧世界时所产生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变化,及其最终做出的更贴合内心感受却相对守旧的选择,恐怕是其离开北大的深层次原因。
庚子以后,读书人对清廷观感越来越负面,这种情绪在清末时期始终存在,且不断蔓延。林纾作为其中一份子,亦时感疑虑。宣统元年,林纾听说清廷拒绝各省咨议局速开国会的请愿,“慨然感叹,认为清廷将失民心”*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载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对光绪帝和戊戌变法深表赞成的林纾起初十分忧虑,携家眷至天津避难。然而随着民国的建立,清帝逊位,中国社会出现新的气象,他转而认为“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并期待袁世凯能主持新局。他自忖“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甚至痛斥“当多尔衮、鳌拜当国之时,旗族杀我汉人,指不胜屈”。清帝逊位诏书下后,他看到“报馆各张白帜,大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欢呼”,认为“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并欣喜地称赞说:“共和世界,无贵无贱。”*林纾复吴畲芬信,见吴家琼:《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页。这些言论,表现出林纾逐渐对共和体制的认同,及对新世界的无比期待。
但同时,林纾内心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的乱象非常反感。北洋军第三镇发动兵变引起北京社会的再次动荡,林纾曾因此被困于京城“小有天”酒楼不得回家,使其对军阀乱状几近无法容忍,不仅赋诗斥之,且愤言“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林纾:《畏庐诗存·自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75页。,对于革命、共和刚刚积累起来的好感几乎荡然无存,他又开始对旧制度心存想念。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带有旧式意味的严复去职,拥有日本学位的何燏时任北大校长,其对林纾的不满乃至羞辱,使林纾感到在日益趋新的北大已无容身之地。林纾自称:“余为大学教习十年,李、朱、刘、严四校长,礼余甚至。及何某为校长时,忽就藏书楼取余《理学讲义》,书小笺与掌书者曰:‘某之讲义,今之刍狗也,可取一分来。’掌书告余,余笑曰:‘校长此言,殆自居为行道之人与樵苏者耳,吾无伤也。’即辞席。”*林纾:《刍狗》,《畏庐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34—135页。可见,正依违于新、旧世界之间的林纾,由于何燏时的嘲弄,加剧了其对新世界的反感,最终选择与之诀别。
1913年5月11日,林纾独游陶然亭后,作诗一首,流露出离开北京南归故里的想法。诗云:“风苇摇凉动小涡,余春末尽尚清和。山客还作前朝缘,胜集长疑昨日过。尘外避喧原不恶,壁间求句定无多。南中果有行吟地,宁隐王城学老坡。”不久,长子林珪辞官南归,林纾作诗送行:“而翁半世落江湖,未遂功名丧本图。今日汝能抛薄宦,吾家本分是农夫。事难着手多方碍,人解回头一累无。旦晚裹书来就汝,琼河数曲狎鸥凫。”*林纾:《四月六日独游陶然亭》、《珪子大城受代率诸孙南归治田作诗送之》,《畏庐诗存》卷上,第202—203页。在复杂的心态变化之中,曾数次拜谒光绪陵墓并在墓前痛哭流涕的林纾辞去了北大教职。
复有一点必须提到,林纾1913年11月以践卓翁为号,出版小说集《践卓翁小说》第一辑。据黄濬云,因林纾“民国初元以北大教习事,与教育次长董恂士鸿祎忤,大怒”,故自号践卓翁。所谓“践卓”,“践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即董鸿祎*黄濬:《践卓翁与天苏阁》,《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页。。如此,林纾之去职,或与董鸿祎亦有关系。
陈衍之离开北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对革命前后北京社会环境的混乱“情状”感到不满。严复邀其到北大任职时,即曾“雅不欲就”。在掌握和了解了北京情况之后,留在北大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仅逗留一个学期后,即便新任校长何燏时费心挽留,陈衍依旧决然而去。
至于姚永概,当初因严复邀请才到北大任文科教务长,后来严复有以文科存经学的设想*严复:《与熊纯如书》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05页。,具有深厚旧学根柢的姚氏当亦赞成。1912年7月,教育部欲停办北大,严复向教育部上《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及《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姚永概也拟定文科改良办法,交部评议*严复:《与鸿翁书》,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但1913年9月以后屡有停办文科传闻,令姚氏忧心忡忡。此外,姚永概与何燏时关系日趋紧张,甚至何氏裁去教务长一职,更令姚氏愤懑,自认与北大发展方向渐行渐远,终与林纾同样因“不合以去”*姚永概:《畏庐续集序》,《林琴南文集》,影印原书第1a页。。
最后,若说何燏时之意在“去桐城”,毋宁说其意乃在“去旧”,只是桐城派在北大的力量仍甚大,故何燏时欲去旧人,难免会动到桐城派的头上。不过严格来讲,林纾、陈衍均非真正的桐城派。林纾自己坚持非桐城派的身份,以致后来《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并未将其收录*据钱锺书云,林纾著作中有“极诋桐城派”之语,并认为此乃林“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见钱锺书:《石语》,《钱锺书集》,第2页。另,有关林纾与桐城派之间关系的辨析,可参看王济民:《林纾与桐城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陈衍是公认的“同光体”诗领袖,且与林纾均为闽人,二人均颇重视闽学系脉的传衍*林纾曾撰《闽中新乐府》,陈衍在《福建通志》中亦对闽地学谱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清理,则二人恐怕更多怀有对闽人身份的认同。。唯有姚永概是真正桐城嫡系,却也并非因桐城派的身份而被迫出走北大。其二兄姚永朴时亦在北大,教授国文课,强调桐城义法,姚永概去职后继续任教。后虽曾一度离开北大,但不久复聘。因此,何燏时的真正意图是“去旧”,而此“旧”,大概主要是指与严复关系较为密切者。林纾、陈衍、姚永概,以及姚永朴、孙雄等人,均为严复所聘请,或可视作严氏“班底”。严复辞职后,其“班底”却并未一同离去。何燏时新官上任,颇思整顿,自然需要有一番汰旧换新的行动。因此,林、陈、姚、马等人的去职,恐怕便是何氏意欲去旧思路的体现,而难以“去桐城、立太炎”论之。
结语
以历史的眼光来评判朱希祖及其他章门弟子进入北大来代替桐城派等旧派人物之过程,看似新、旧更替,实则更近乎以“旧学”代替“旧式”*罗志田认为,太炎派“在其学术上实比在他们之前控制北大的‘文选派’和‘桐城派’更加合乎‘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还更‘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革命也更正统的一派与以前当权而又不够正统的一派争夺思想领域(及其重要阵地北大)的控制权的斗争。故林纾的不得不辞职,恰是为更‘正统’的旧派所迫”。详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因为章门弟子尽管大多留学日本归来,其所治之学却仍是极为传统的旧学,且在文法一面多宗汉魏六朝,甚至比桐城派、林纾、陈衍等人所宗法的唐宋古文更为古远。虽然章门弟子的治学方法,大概更接近后来所阐扬的“科学”的层面,带有趋新意味,但其“在论学价值取向上,皆以返古开新标示,所本的学术资源皆是国学。桐城派、章太炎弟子治国学的路径及方法都本着正本清源的朴学根基”,所以二者“只是在国故学表象上有所差异”,其分歧主要“涉及其时学界对国学精华的不同认识以及经典文本的不同选择”*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之“出”与“入”,表面上是新旧易位,但似乎更可谓之“以旧易旧”。只是此时的桐城派仍旧充满头巾气,在西方学科日趋替代旧式学科的形势下,失去其地位实属必然。
其实,章太炎本人对桐城派的总体看法实大体不坏,虽在品行方面不能苟同,但在学理上却并不排斥。至于后来思想较新的钱玄同骂“桐城谬种”,其最初的攻击目标可能只限于曾斥太炎门人为“庸妄之谬种”的林纾,其个人行为恐怕难以说成是代表“太炎派反桐城派”。其后,在更加“科学”且曾以林纾为“国故党”、“国粹党”代表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面前*语见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59—61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页。,倡言国故的章太炎及其部分弟子很快又被视作旧式人物,从而在北大掀起了更加猛烈的“新旧”之争。这些后续的变化,更加凸显出在民初的数年里,尤其是朱希祖及其他太严弟子入职北大之初,新旧世界虽已有移形换位之势,但与其后剑拔弩张的情形相比较,此时“新”与“旧”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朦胧,其清晰的标准尚在确立与制定之中。
责任编辑:方英
中图分类号:K252;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82-07
作者简介:程尔奇(1980-),男,河南临颍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Obscure Transloc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Zhang Tai-yan’s Disciples’ Entry to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Old Faction’s Tendenc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Centered on Zhu Xi-zu
CHENG Er-qi
(Institute of History,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the personnel change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Zhu Xi-zu entered the university before other genuine disciples of Zhang Tai-yan.His entry did not cause strong reactions of the old faction whose subsequent quit from the university ha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Zhu Xi-zu.The reasons of the old faction’s leaving were different,but all of them had the feeling of deviating from the future trend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charge of He Yu-shi.Although more disciples of Zhang Tai-yan entered the university thereafter and replaced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old faction including the Tongcheng School,the replacement had a implication of“old substitutes for old” if judging wi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is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the old and new world was on track of translo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has some obscureness,and the clear standards of them are still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Peking University;Zhu Xi-zu;the old faction;translocation of the“old”and“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