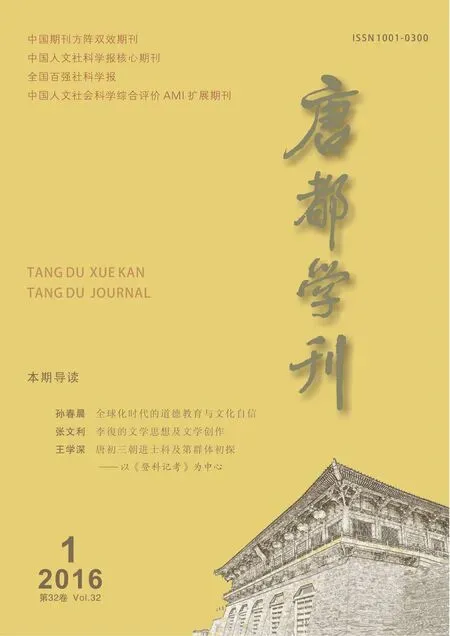司马光《书仪》的撰作及现代启示
潘 斌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司马光《书仪》的撰作及现代启示
潘斌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
摘要:《书仪》是北宋司马光所撰的一部士庶通礼,该书是司马光对北宋礼乐不兴的社会现状所作之反思,意在满足北宋家族伦理建设之需要。司马光对前代的礼书颇为重视,特别是对于集唐代礼制之大成的《开元礼》多有评论。司马光还充分照顾到了北宋的风俗,当风俗合于人情、有益教化时,司马光则从之;当风俗不合人情、无益教化时,司马光则弃之。《书仪》对宋元明清时期士庶通礼之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对于今天礼仪文明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司马光;《书仪》;礼仪文明
学界于司马光之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学、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司马光对儒学也颇有研究,他自己也被人奉为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司马光特别重视儒学中的礼学,他说:“夫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淫侈溢而无穷也。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1]583司马光曾撰《书仪》一书,为南宋朱熹编撰《家礼》所效法。《书仪》对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士庶通礼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士庶人礼仪和家庭伦理建设的文本依据。本文以司马光的《书仪》为考察对象,以见该书的撰作缘由、特点及对当今礼仪文明重建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一、《书仪》的撰作缘由
司马光《书仪》共十卷,《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合为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书仪》之撰作,是应北宋家族伦理建设之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与庶族之间界限分明,门阀等级森严。然而隋代以来的科举制,使很多出身寒门者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增大,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亦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士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到了北宋时期,家庭和家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很大的不同。有学者指出:“唐代以前的家族以北方地区政治型的门阀世族为主要形态,其主要功能是界定望族身份以取得世袭特权;宋代以降,家族以东南地区血缘型的家族组织为主要形态,主要功能是敬宗收族。”[1]2宋代有很多“同居共财”的大家族,按“二十四史”的列传所记,南北朝共25家,唐朝共38家,五代2家,宋代50家,元代5家,明代26家。[2]41大家庭的凝聚力主要不是经济,而是血缘亲情和道德教化。血缘亲情是不可选择的,然而道德教化的水平是通过努力可以提升的。北宋时期,不少人认识到,大家族要能够长久兴盛,道德教化是十分重要的。家庭和家族伦理建设,需要有相应的士庶通礼的撰作,《书仪》便应运而生了。
《书仪》之撰作,是司马光对北宋礼乐不兴之社会现状所作反思的结果。司马光认为,北宋民间礼仪与礼乐精神相去甚远。如北宋中期的冠仪,“生子犹饮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这就导致人们普遍“不知成人之道”[3]467的严重后果。又如婚礼,“指腹为婚”“轻许为婚”,招致“弃信负约”“速狱致讼”[3]474的恶果。此外,择婿、择媳慕富贵之风亦十分普遍,从而导致媳“轻其夫”、“傲其舅姑”,男子凭“借妇势以取贵,尽失大丈夫之志气”[3]474。
《书仪》之撰作,是司马光对“书仪”撰作体式的继承。书仪撰作体式出现颇早,20世纪发现的敦煌卷子中,有唐代婚丧礼俗的写本“书仪”。据学者研究,敦煌写本“书仪”适用于普通庶民,“在民间很受重视,广为流传”[4]。据现有的材料,可知在司马光《书仪》之前,晚唐郑余庆曾“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五代刘岳“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成《书仪》,宋初胡瑗“略依古礼而以今体书疏仪式附之”成“吉凶书仪”。司马光据《仪礼》,结合宋代的风俗,采用“书仪”体式,从而撰成《书仪》这样一部士庶人行为规范的礼仪蓝本。
二、《书仪》对礼俗的批判继承
儒家所讲的伦纲理常,是处理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这从孔子时起就有一套体系。特别是在《仪礼》《礼记》等儒家经典中,诸礼有极为细致的规定,可谓繁文缛节。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恪守礼书之记载。所以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根据前代的礼典,并结合当代的风俗,重新制定礼仪规范。司马光的《书仪》遵循《仪礼》所记之古礼,又能结合宋代的风俗、前代之礼典,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礼仪蓝本。
司马光《书仪》于冠、婚、丧、祭诸礼之仪节,基本上以《仪礼》为据。如《书仪》所记之婚礼之仪节,虽然于《仪礼》有所变通,然而最重要的礼仪仍然遵循《仪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与《仪礼》并无二致。又如《书仪》所记之丧礼仪节,初终、复、易服、讣告、沐浴、饭含、铭旌、魂帛、吊酹赙襚、小敛、棺椁、大敛殡、闻丧、奔丧、饮食、丧次、五服制度、成服、夕奠、卜宅兆葬日、穿圹、碑志、明器、下帐、苞筲、祠版、启殡、朝祖、亲宾奠、赙赠、陈器、祖奠、遣奠、在涂、及墓、下棺、祭后土、题虞主、反哭、虞祭、卒哭、祔、小祥、大祥、禫祭,亦基本涵盖了《仪礼》所记丧礼之步骤。朱子说司马光《书仪》“大抵本《仪礼》”[5]180,实非虚言。
司马光对前代的礼书亦颇为重视,特别是对于集唐代礼制之大成的《开元礼》多有论及。《开元礼》取法唐代贞观和显庆年间的礼仪,并对汉魏以来的礼制做了总结,使唐代的礼制臻于完备,并对后世的礼仪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杜佑称赞《开元礼》“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6]1122。司马光择《开元礼》可行于北宋者而记之。如复礼(招魂),《书仪》曰:“按《杂记》《丧大记》,复衣,诸侯以衮,夫人以揄狄,内子以鞠衣。今从《开元礼》上服者,有官则公服,无官则襕衫或衫,妇人以大袖或背子,皆常经衣者。”[3]483《礼记》认为诸侯、夫人、内子之复衣各有异,《开元礼》认为可制常服,司马光从《开元礼》,认为有官、无官、妇人可根据自己的身份服常服。
司马光在撰《书仪》时,充分照顾到了北宋的风俗。当风俗合于人情、有益教化时,司马光则从之。如亲迎,《书仪》曰:“于壻妇之适其室也,主人以酒馔礼男宾于外厅,主妇以酒馔礼女宾于中堂,如常仪。”司马光于此不取《仪礼》,而从宋代之风俗,他解释道:“古礼明日舅姑乃享送者,今从俗。”[3]478。又如冠礼,宾字冠者之后,《仪礼》无主人酬宾和赞者币之仪节。《书仪》规定“主人酬宾及赞者以币”。司马光解释曰:“端匹丈尺,临时随意。凡君子使人,必报之。至于婚丧相礼者,当有以酬之。若主人实贫,相礼者亦不当受也。”[3]470司马光从顺人情的角度增此仪节,以补《仪礼》之不备也。当风俗不合人情、无益教化时,司马光则表示反对。如司马光主张婚礼“不用乐”,并解释曰:“曾子问曰:‘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今俗,婚礼用乐,殊为非礼。”[3]478司马光认为婚礼用乐不合于礼,故主张从《仪礼》而不从北宋之风俗。
司马光《书仪》有很强的变通精神,比如其对《仪礼》等礼书所记载的年龄、数量等,皆有不同的看法。关于被加冠者之年龄,司马光认为“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并释之曰:“吉礼虽称二十而冠,然鲁悼公年十二,晋悼公曰‘君可以冠矣’。今以世俗之弊不可猝变,故且狥俗自十二至二十皆许其冠。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然后冠之,斯具美矣。”[3]467关于冠礼之年龄,《礼记》认为男子二十,然《左传》记载鲁君年十二行冠礼。司马光据《礼记》和《左传》,认为冠礼之年龄,十二至二十皆可;若是敦厚好古之君子,二十岁粗知礼义之方时亦可。
《书仪》对于《仪礼》所记礼器、堂室、仪节有所变通。如冠礼的筮日仪节,《书仪》曰:“古者大事必决于卜筮。灼龟曰卜,揲着曰筮。夫卜筮在诚敬,不在蓍龟。或不能晓卜筮之术者,止用杯珓亦可也。其制,取大竹根判之,或止用两钱掷于盘,以一仰一俯为吉,皆仰为平,皆俯为凶。后婚丧祭仪卜筮准此。《开元礼》自亲王以下,皆筮日、筮宾不用卜。”[3]468司马光认为,筮日仪节意在诚敬,卜筮的方式应当不拘一格,不必泥于《仪礼》之记载。又如冠礼的醴礼,《书仪》曰:“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则一献,酒则三醮。今私家无醴,以酒代之,但改醴辞‘甘醴惟厚’为‘旨酒既清’耳,所以从简。”[3]469司马光认为,北宋时期,私家无醴,故可用酒代替,只不过要将醴辞稍作变换。
《书仪》对古礼仪节有所简化,以求简便易行。如冠礼有宿赞冠者、请期、告期之仪节,司马光曰:“古文宿赞冠者一人,今从简,但令宾自择子弟亲戚习礼者一人为之。前夕又有请期、告期,今皆省之。”[3]468据《仪礼》,主人筮宾、宿宾后为宾邀请一位赞冠者。司马光认为,令宾从子弟亲戚中择习礼者一人为赞冠者即可,至于请期、告期等仪节皆可省去。
三、《书仪》的现代启示
五代以来,很多人对儒家礼仪文明茫昧不知,加之释、老的冲击,以致儒家纲常松弛、礼乐不兴,为改变时弊,司马光据《仪礼》《礼记》《开元礼》,并参考宋代风俗,撰《书仪》一书,为宋代士庶人确立了一套符合礼教的行为方式,并为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家族建设确立了样板。*据李昌宪统计,朱子《家礼》一半以上的文字出自司马光《书仪》,《书仪》所立影堂制度直接启发《家礼》创设祠堂制度。(参见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24页)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光是宋元以后家庭伦理思想和家族建设的创始巨擘”。[7]324
司马光《书仪》不仅于古代家庭伦理建设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礼仪文明重建也颇有启发意义。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由于受到释、老的冲击,儒学地位有所下降。李觏、张载、程颢、程颐等人试图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使儒学焕发生机,所以有人称宋代儒学为“新儒学”。当然,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已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对于儒学再诠释以求重建伦理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一些人毁绝礼义而不顾,从而导致不文明的现象屡屡出现。正如《礼记·经解》所云:“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时代呼唤中华礼仪文明的重塑。而司马光所撰《书仪》对宋元明清时期士庶家族和个人的行为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颇值得今人参考借鉴。
司马光在撰《书仪》时十分重视《仪礼》《礼记》等礼典,也十分重视《开元礼》等前代礼书。正是由于其重视传统,才使得《书仪》成为经典之作。在中国古代,礼学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治术意义,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普遍重视。而礼学的载体是《周礼》《仪礼》《礼记》等礼典。今人在从事礼仪文明重建时,对于礼学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等当须特别重视,因为只有明白《周礼》《仪礼》《礼记》等所记载的礼仪制度和礼乐思想,才能知晓礼仪的来龙去脉,也才可避免礼仪重建陷入无源之水的境地。
此外,今人在礼仪文明重建的过程中,对于历代重要的礼书也要有所研究,对于前人制礼作乐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加以吸取。儒学在汉代被推为官方哲学以后,礼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历代以来的礼学文献多达两千余种,这还不包括史书中的礼乐志和礼志典。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官方十分重视礼乐文化的建设。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和睦家族、安定社会,积极撰修礼书,这些礼书对中国中世纪以后民间风俗的影响甚大。在今天的礼仪文明重建中,借鉴和吸取前人礼仪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当是十分必要的。
司马光《书仪》之所以能为宋元人所接受,还在于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今天我们在从事礼仪文明重建时,一定要重视古礼的现代转换研究。
古礼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现代人如果亦步亦趋去推行古礼,则是不合时宜之举。实际上,古礼重要,其所蕴含的意义更重要。今天不必完全恪守古礼之仪文,而是要应时而变。《礼记》曰:“礼者,时也。”不同的时代,对礼的精神意蕴的理解基本一致,然而在具体仪节上却可以有所不同。古礼必须结合当今时代,实现其现代转化,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以冠礼为例,此礼是男子前十多年家庭教育的毕业典礼,也是男子的成年礼,表明该男子具有了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能力,并对他未来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礼记》所记八礼,而冠礼居首。《礼记·冠义》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由此可知冠礼的重要地位。《仪礼·士冠礼》记载了冠礼的仪节,包括冠礼前的各种准备,如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行冠礼的具体过程,如始加、再加、三加、宾礼冠者、见母;还杂记冠礼的变例及宾主所致之辞,如庶子和孤子的冠礼、宾字冠者、三加之辞等。今天组织行冠礼,若按《仪礼》亦步亦趋地去实施,必然是劳民伤财而不得其要。据《仪礼》,士行冠礼当在宗庙中,然而今天人们的居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城市中甚至偏远的山区,人们都难寻宗庙的踪影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行冠礼的场所作重新的考量。比如可以将客厅腾空,做一些布置后变为行冠礼的场所。若是家居空间不大,还可以在公共空间,比如小区广场或草坪,还可以租借会堂等。这些设想皆是冠礼组织者顺应时代的变化而作出的调整。
实际上,今人在面对古老的礼仪条文时,重要的是理解这些条文蕴含的意义。台湾著名礼学专家周何曾对冠礼仪式的现代转化谈过他的看法。周何不主张今人亦步亦趋去仿效《仪礼》中的繁文缛节,而是强调成人礼的意义十分重大,他说:“到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冠礼全亡。如今我们时常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懂事而感慨,或者为青少年犯罪率的增高而讶异,其实该感叹、该责备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做父母、做长辈的人,没有尽到教育子弟的责任,终使家庭教育濒临破产,造成时下年轻人不明是非,不知分寸的行为差失。仔细想想,成人之礼的久废,应该是重要因素之一。”[8]14周何认为,当今青少年不明是非、不知分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成人礼的丧失。这从反面证明成人礼对于今天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周何并非将成人礼限定在《仪礼》所记之冠礼上,而是将冠礼的意义做了拓展。其举例曰:“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也有表示成人‘笄礼’的举行,如今当然也不存在了。不过有些家庭为十六、七岁的女儿举办一次盛大的舞会,让女儿穿着正式的晚礼服,周旋于许多宾客之间,俨若成人。或许那是从欧美电影里学来的,仪式节目都与中国的笄礼不一样。那有什么关系,只要它确实表示成人教养的完成,无论是什么样式的庆典,都是非常可喜的事。”[8]14-15女子成人之笄礼虽不复存在,然而表示女子成人之礼的一些仪式或场合依然可以起到笄礼的效果。周何认为礼之精神意蕴是最根本的,至于古代礼仪的形式则须变通。
古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人心的安定、社会的稳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一种新的伦理秩序以匡正人心,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而传统的礼仪文明对于道德人心和社会秩序皆有着十分重要的规范意义。在现代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下,如何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的礼仪规范,是今天的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现代礼仪规范的建立,绝非要亦步亦趋地去恢复古礼。盲目回到过去,未免可悲,也注定会失败。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制礼作乐的成功经验,吸取历代礼俗中的有益成分,并将传统有益的成分进行现代转化,建构新的现代仪式,促使良善的美俗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司马光.易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邢铁.宋代家庭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司马光.书仪[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J].文物,1985(7):17-25.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李昌宪.司马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周何.古礼今谈[M].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1992.
[责任编辑朱伟东]
Sima Guang’s Composition ofShuYiand its Modern Revelation
PAN Bin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611130,China)
Abstract:Shu Yi, written by Sima Guang, reflected the social etiquette among ordinary peop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writer’s introspection upon the decaying rites. Its purpose w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thic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ima Guang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books of rites in the previous dynasty and made much comment on Kai Yuan Li. Sima Guang took the custo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to consideration, he accepted them if the customs conformed with humanity and moralization, otherwise, he abandoned them. This book had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social etiquette in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s flexibility also had great revel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day’s etiquette civilization.
Key words:Sima Guang; Shu Yi; social etiquette
作者简介:潘斌,男,四川通江人,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三礼诠释研究”(14CZX031)
收稿日期:2015-07-29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6)01-0083-04
【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