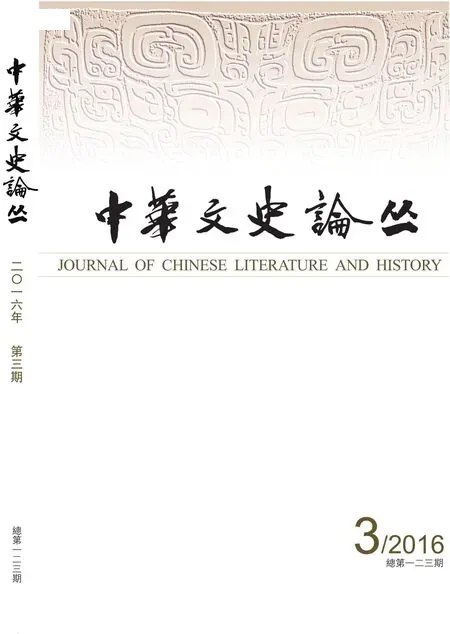不平常的平常風物:“閑居”姿態與韋應物的自然書寫
蕭 馳
不平常的平常風物:“閑居”姿態與韋應物的自然書寫
蕭馳
本文從討論盛、中唐之交的建中、貞元時代與劉宋、南齊時代的思想風氣不同入手,强調韋應物所謂“吏隱”是吏與隱二元關係之外的中道,是須經身心修養所企致之境界,其特别彰顯於詩人或作於郡齋或作於林水的“閑居”之作中。“閑居”開啓了詩人遊乎草木雨雲,霽月光風的生命世界。“閑居”是一種生命存有的姿態,一種“道行”的身體實踐。本文重點討論了其中兩種面向。首先,與刻鏤着歷史創痛的初期回憶詩作相比,“閑居”之作體現了詩人如何自歷史時間中解脱,融入自然時間而任運自在。其次,“閑居”與“吏隱”又令韋詩在空間書寫中忽略和虛化方域。在此,以空間之疏曠體現了詩人性情之疏散,而多重的甚至歧義的視境更直接體現了其神遊於兩重世界的“吏隱”者心迹。
關鍵詞: 吏隱閑居自然的時間模糊方域歧義視境
一 引 言
本文旨在探討韋應物(735—793)詩作中的自然山水書寫。在近人“山水詩”的討論中,韋氏被視爲唐代最重要的這類詩人之一。晚唐論詩名家司空圖最早即將韋氏與盛唐書寫山水的大詩人王維合稱。*《與李生論詩書》,祖保泉、陶禮天《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集卷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93。北宋蘇軾又將韋氏與另一位“山水詩人”柳宗元並舉。*《書黄子思詩集後》,《蘇軾文集》卷六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124。至南宋,不僅有朱熹以爲韋詩高於盛唐“山水詩人”王維和孟浩然,*《清邃閣論詩》,吴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112。且有劉辰翁以爲韋與孟“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並設譬論二人詩爲“如深山采藥,飲泉坐石”和“如訪梅問柳,遍入幽寺”。*明嘉靖太華書院本《韋江州集》附錄《劉須溪評語》,四部叢刊縮印本,147册,頁68下。王、孟、韋、柳四人並稱大概始自元末張以寧,*《黄子肅詩集序》,《翠屏集》卷三,吴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是對上述唐人宋人説法順理成章的延續,卻成爲近人討論“山水詩”被普遍接受的觀念。然而,與王、孟、柳的這類研究相比,對韋詩山水書寫的研究相對薄弱得多。究詰其中原因,或許是韋應物山水書寫的話語特徵頗不易描述。
韋應物寫了不少遊覽山水的詩作,據筆者觀察,計有近四十首之多。此外一些登樓、游宴、送别之作,亦涉及山水的書寫,這是今人撰寫山水詩史措意的面向。但是,倘若吾人特别屬意韋氏爲中國詩歌傳統中山水美感話語所增添的方面,就不會專注於以上諸類題材了。韋氏山水書寫的獨特美感,以本人鄙見,須在其所謂“閑居”詩作中去發現。蔣寅在探討韋應物詩作時曾提出: 韋應物作爲地方官詩人在中國詩史上“建立起一個基本主題同時也是一種詩歌類型郡齋詩”。以他的説法,“郡齋詩”表達了士大夫理想的生活方式“吏隱”。*《大曆詩人研究》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98— 99。而本文所謂的“閑居之作”即涵攝了所謂“郡齋詩”,因爲韋氏本人即有《郡內閑居》一詩。*白居易亦居於爲官之所而謂之閑居,見其所作《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昭國閑居》等詩。白氏是另一位“吏隱”者,且頗愛韋應物之詩與人,常將韋與陶潛並稱。除此之外“閑居詩”尚涵攝詩人數次罷任之後卜居和寓居佛寺時的作品,如其建中元年(780)在灃上即有《閑居贈友》,貞元元年(785)罷滁州刺史寓居佛寺時亦有《閑居寄端及重陽》。這兩類“閑居”或“燕居”,又被稱爲“幽居”。韋氏不僅建中二年卜居灃上時作有《幽居》一詩,且在滁州刺史任上所作《池上懷王卿》一詩中亦起以“幽居捐世事”。*孫望《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00。這後一類“幽居”或“閑居”,亦被他稱爲“野居”或“郊居”。重要的是,韋氏將罷任之後的詩作與郡齋詩作統稱作“閑居”或“幽居”,纔真正體現出他的“吏隱”觀念。
論到“吏隱”,筆者卻以爲以往的評説尚有可以商榷補正之處。的確,韋應物自初仕至歸休一直在重複着“仕—隱”的循環,然而吾人是否就該簡單地以其骨子裏仍流露出世俗之氣,或內心深處仍對功名利祿肯定和留戀來作判斷?如果作這樣的一種辯説是仍在仕與隱二元對立的邏輯中討論問題。然而對韋應物而言,“吏隱”卻真正是二元關係外的中道,是經身心修養所企致之境界。此乃韋應物與陶淵明、謝朓相比的不同之處,也是盛、中唐之交的建中、貞元時代與劉宋、南齊時代的思想風氣不同之處。在此,對“吏隱”的認知直接關乎對其“郡齋閑居詩”的論析和評價。
本文的討論將自辯説韋應物的仕隱中道開始,揭示由仙、道、佛禪的修養所塑造的韋氏人格以及體現此一人格的“閑居”生活之本質。以此爲基點,本文進而討論韋氏“閑居”中風物書寫的兩個重要面向。首先,與刻鏤着歷史創痛的回憶侍衛先帝歲月的初期詩作相比,“閑居”之作體現了詩人如何自歷史時間中解脱,融入自然時間而任運自在。其次,“閑居”與“吏隱”又令韋詩在空間書寫中產生種種忽略和虛化方域的現象,從而以風物書寫展示出其生命存有之姿態。
二 韋應物的仕隱中道與閑居
在苛責韋應物利祿功名之心未絕之時,論者不免想到了謝朓。如蔣寅所論,謝朓是大曆時代詩人的“普遍崇拜的偶像”,在此一時期的詩作中被多達四十次地述及。*見蔣寅《大曆詩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7—31。韋氏身處此一風氣之中,自然未能免俗。除卻蔣寅所舉《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一詩中的“高齋謁謝公”一句外,尚有《答秦十四校書》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一聯中的以謝朓自況。*《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九,頁457。然谢朓並未真正實踐“吏隱”,他不過是於仕而思隱,其詩“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直中書省》,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13。“既乏琅邪政,方憩洛陽社”,*《落日悵望》,同上書卷三,頁231。“胡寧昧千里,解珮歸山莊”,*《賽敬亭山廟喜雨》,《謝宣城集校注》卷三,頁236。“空爲大國憂,紛詭諒非一。安得掃蓬徑,銷吾愁與疾”,*《高齋視事》,同上書卷三,頁280。“懷歸欲乘電,瞻言思解翼。……無嘆阻琴樽,相從伊水側”云云,*《和宋記室省中》,同上書卷四,頁346。皆是在仕而思歸隱。在此,仕與隱是二元對立中遮此方能詮彼的選擇。《觀朝雨》一詩更直接書寫了其內心如何掙扎於仕與隱的抉擇之中:
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同上書卷三,頁215。
謝朓詩中表達了些許以仕爲隱觀念的是他離京守宣之初所作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和《始之宣城郡》二詩:
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囂塵自兹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同上書卷三,頁219—220。
棄置宛洛遊,多謝金門裏。……江海雖未從,山林於此始。*《始之宣城郡》,同上書卷三,頁222。
然而,倘若吾人回到詩人寫作二詩的語境,即會明瞭這其實主要在表達他離京外放從而游離出權力爭鬥中心後的心情。此處所謂“滄州”、“南山”和“山林”皆是對權力爭鬥漩渦建康的“囂塵”、“宛洛”、“金門”而言,主要體現了京城和地方的區隔,而非仕與隱的辨分。而且,小謝甚至對以仕爲隱的“朝隱”或“吏隱”不無微詞。其詩《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的結尾中説:
誰慕臨淄鼎,常思茂陵渴。依隱幸自從,求心果蕪昧。方軫歸歟願,故山芝未歇。*《謝宣城集校注》卷三,頁269。
有了謝朓這樣一個參照,令吾人更易觀察韋應物的“吏隱”觀念。首先,可以總結説,倘若謝朓心中不無“隱”的念頭的話,其動機亦無非是避禍、慰藉鄉愁和流連山水。這裏基本上不具靈修的成分,故而其所謂“隱”是不離行迹的。韋應物一生精神上經歷過巨大的轉變。其出身於顯赫世家,少時因門蔭成爲玄宗的御前侍衛。其中年作《逢楊開府》一詩追敍少年時代的紈绔生活: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提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六,頁267。
如此一個驕橫頑癡的紈绔子,居然成爲了而今吾人在詩中所見識到的立性高潔,悠閑澹泊之人,這其中的變化究竟如何發生的?今人曾歸結了幾方面的原因: 安史之亂後國家到個人境遇的變化、從政的失望、喪偶的打擊,以及疾病的影響。*見儲仲君《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文學遺產》1984年第4期,頁67—75。然而,這裏卻完全忽視了其個人主觀靈修的因素。同樣的客觀條件可以造就不同的人格。就韋氏的人格和精神轉變而言,很難想象沒有一個艱苦靈修的過程。當然,由於傳記資料不足,而韋氏又無文集傳世,靈修的真相頗難推斷。然唐人李肇《國史補》謂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坐焚香掃地而坐”,*李肇《國史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55。寥寥數語勾畫出一靜修之人的形象。應物詩句如“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異處”證實李肇所述不虛。*《曉坐西齋》,《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九,頁453。其詩時時透露出靈修和工夫的消息。細參之下,其靈修歸趨有大致三端。首先,靈修本即孤獨者的智慧,應物詩中不乏規避社羣,追求幽獨的表達:
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神靜師院》,《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四,頁196。
愚者世所遺,沮溺共耕犁。*《答庫部韓郎中》,同上書卷四,頁211。
挂纓守貧賤,積雪臥郊園。*《逢酬處士叔見示》,同上書卷四,頁214。
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浮。……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答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同上書卷四,頁223。
濩落人皆笑,幽獨歲逾賒。*《郡齋贈王卿》,同上書卷六,頁278。
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寓居永定精舍》,同上書卷九,頁477。
其次,靈修乃爲回歸內在本真而息機無營,養拙抱素。這一意識在韋詩中一再出現:
弱志厭衆紛,抱素寄精廬。曒曒仰時彥,悶悶獨爲愚。*《善福精舍答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同上書卷四,頁185。
我以養愚地,生君道者心。*《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同上書卷四,頁191。
閑居養痾瘵,守素甘葵藿。*《閑居贈友》,同上書卷四,頁197。
隱拙在沖默,經世昧古今。無爲率爾言,可以致華簪。*《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同上書卷四,頁201。
方以玄默處,豈爲名迹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沖襟。*《善福精舍示諸生》,同上書卷四,頁202。
人生不自省,營欲無終已。孰能同一酌,陶然冥斯理。*《九日灃上作寄崔主簿倬二李端繫》,同上書卷四,頁209。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幽居》,《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四,頁215。
日出照茅屋,園林養愚蒙。*《答暢校書當》,同上書卷四,頁212。
效愚方此始,顧私豈獲并。*《自尚書郎出爲滁州刺史留别朋友兼示諸弟》,同上書卷六,頁265。
棄職曾守拙,玩幽遂忘喧。*《答僴奴重陽二甥》,同上書卷七,頁368。
復次,正因爲靈修乃爲個體於孤獨之中向內的歸返而非向外的競逐,不必去刻意標顯。韋詩中一再作出不避自輕的表示:
息機非傲世,於時乏嘉聞。*《秋夕西齋與諸僧靜遊》,同上書卷四,頁182。
高士不羈世,頗將榮辱齊。適委華冕去,欲還幽林棲。*《答庫部韓郎中》,同上書卷四,頁211。
偶然棄官去,投迹在田中。……出入與民伍,作事靡不同。……貧賤自成退,豈爲高人蹤。*《答暢校書當》,同上書卷四,頁212。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始除尚書郎别善福精舍》,同上書卷五,頁231。
應物在此極力表示棄官不過適然隨性而爲的一件平常事,此不僅與隱居養望者李白全然不同,與潁川洗耳的許由、牽犢遠走的巢父判然,甚至亦與高唱“歸去來兮”的陶淵明有異。朱熹於此可謂慧眼獨具,他比較應物與淵明説過一段精彩的話,謂韋應物:
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 比陶何如?曰:陶卻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爲之,陶卻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清邃閣論詩》,《宋詩話全編》(6),頁6112。
在宋代理學家內聖學的語境裏,“有力”、“語健”皆與成聖之道所要求的“寬舒”、去“英氣”、去“圭角”相左。*詳見蕭馳《宋明儒的內聖境界與船山詩學理想》,《聖道與詩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頁3—19。而韋詩“自在……直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卻真正是寬舒無迹,以明儒王船山引《考工記》之語,乃“五氣俱盡,金錫融浹”,*韋應物《送鄭長源》一詩評語,《唐詩評選》卷二,《船山全書》(14),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970。故而是“氣象近道”。至於陶潛的“帶氣負性”則不妨以《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爲例: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悦。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誰能别。*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84。
古人讀此詩謂見詩人如松柏之凌歲寒之態,楮墨之間處處見洗耳、牽犢之意,即以固窮之節而傲物自高,自與應物的適然棄官的“自在”不同。

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爲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 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皆是道,道即是法界。*《馬祖道一禪師廣錄》,《新編卍續藏經》(11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頁812。
“平常心是道”一語之間就泯卻了染心和淨心的界限,其欲破除的“造作”、“汙染”,已不再主要是五根境界的汙染,而是分辨淨與染,聖與凡的意識。其在佛門造成的風氣,依宗密之説,則以“佛性非聖非凡”,而“不起心斷惡,亦不起心修道修道……不斷不造,任運自在”。*《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88。如此一種雙遮雙詮的思想方法,被應物用於關於出處仕隱的觀念之中。應物建中四年(783)或興元元年(784)有一首《贈琮公》於吾人確認吏隱與佛禪的關聯特别重要。其詩云: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暮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七,頁354。
由此詩可知: 應物即出即處,即喧即靜或即吏即隱的觀念中受到這位來訪僧人的點化。在此,洪州禪的“佛性非聖非凡”化爲了吏隱者的非仕非隱,亦仕亦隱和即仕即隱,而任何着意標顯的隱反而是“造作”,而對仕隱的不假分辨——所謂“偶然棄官去,投迹在田中”,“偶宦心非累,處喧道自幽”,*《答暢參軍》,同上書卷五,頁245。——反倒是謙卑和不負氣的“平常心”。應物一首題滁州琅琊寺詩的結尾,透露出同一信息:
情虛澹泊生,境絕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厭車轍。*《同元錫題琅琊寺》,同上書卷七,頁319。
故而,出與處或吏與隱根本不在行迹,而在經靈修而企致的內心之“澹泊”和“塵妄滅”。此一“澹泊”之“心”,爲應物一再强調:“心當同所尚,迹豈辭纏牽”,*《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八,頁383。“猶希心異迹,眷眷存終始”,*《城中臥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同上書卷八,頁393。“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同上書卷八,頁408。“腰懸竹使符,心如廬山緇”,*《郡內閑居》,同上書卷八,頁406。“名雖列仙爵,心已遺塵機”。*《和吴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同上書卷八,頁417。此一被反覆提及的“心”,證明上文所論,應物的“吏隱”乃基於靈修工夫。
以此,韋氏纔將其在郡齋爲官居停稱作“閑居”。不要輕看了這兩個字,這正是其吏隱觀念的流露。這裏要塑造的是一種人格,對中國傳統文化而言,人所能創造的最偉大作品即是人格。這一人格之中,融入了中國禪的般若智慧——“平常心”。以此“平常心”,所謂“隱”當渾然於“仕”;而所謂“仕”,亦不應熱衷於逢迎奔走,而應澹泊於功名利祿,所謂“榮達頗知疏,恬然自成度”。*《休暇東齋》,同上書卷二,頁119。喬億謂:“韋詩五百七十餘篇,多安分語,無一詩干進。……杜、韓不無干謁詩文,太白亦多綺語,試執此以論韋,卓乎其不可及已。”*《劍溪説詩》又編,《清詩話續編》(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122。以此,“吏隱”的理念甚至與其作爲清廉正直的官員去留意黎民疾苦不相扞格。*據丘丹所撰《唐故尚書左司郎中蘇州刺史京兆韋君墓誌銘并序》,韋“領滁州刺史,負戴如歸。……遷江州刺史,如滁上之政。……尋領蘇州刺史,下車周星,豪猾屏息,方欲陟明,遇疾終於官舍。池雁隨喪,州人罷市。素車一乘,旋於逍遥故園,茅宇竹亭,用設靈几。歷官一十三政,三領大藩,儉德如此,豈不謂貴而能貧者矣!”見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增訂本)》附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623—624。當然,韋應物並非聖賢,其詩作亦透露出“吏隱”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應然的理想。然這卻是以高雅隱藏功名利祿世俗之心所不能完全解釋的。有那樣的虛僞,也就不會有韋詩的恬和與情感的真摯了。韋氏的“散淡”,*參見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上編,頁108—113。是中國文化中的某種極致,是嵇叔夜、陶元亮、王摩詰均難以企及的境界。這全無遁世者驕矜之氣的“散淡”,本身即寬容了“俗氣”,因爲否定宗教彼岸性的洪州禪即以日常世俗爲特徵。這裏是洪州禪與莊學的界限。不過應物尚非白樂天的淺俗,而是王船山所謂“此作清不刻,直不促,必不與韓柳元白孟賈諸家共川而浴”。*韋應物《幽居》一詩評語,《唐詩評選》卷二,《船山全書》(14),頁969。廓清對韋應物“吏隱”的以上迷思,會開顯吾人詮釋韋詩山水書寫的新境界。同時,詮釋其山水書寫,又令吾人對其修身實踐有新一層的了解: 它雖然主要是基於佛禪的心靈轉換,卻又不乏身體經驗的向度。
三 逸出“歷史的時間”
韋應物生命中有一道深深的溝壑,橫在安史之亂前後之間。韋氏曾多次寫詩懷念其早年侍衛先帝的歲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詩多寫於大曆中期之前。其時詩人似尚入佛禪未深,即在他尚不能忘卻“前心”。這些回憶之作中總有一些情景似乎刻鏤在內心深處,鮮明而强烈。如《驪山行》寫明皇沐浴華清池侍衛儀仗即有:
千乘萬騎被原野,雲霞草木相輝光。禁仗圍山曉霜切,離宮積翠夜漏長。玉階寂歷朝無事,碧樹委蕤寒更芳。……翠華稍隱天半雲,丹閣光明海中日。羽旗旄節憩瑤臺,清絲妙管從空來。*《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一,頁1。
《燕李錄事》如此回憶其入仕宮廷的歲月: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一,頁26。
驪山扈從先帝沐浴的景象再次出現在《酬鄭戶曹驪山感懷》一詩中:
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翻翻日月旗,殷殷鼙鼓聲。萬馬自騰驤,八駿按轡行。日出煙嶠綠,氛氳麗層甍。登臨起遐想,沐浴歡聖情。朝燕詠無事,時豐賀國禎。日和弦管音,下使萬室聽。*同上書卷一,頁35。
《溫泉行》中,與先帝遊幸驪山的情景再次出現:
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玉林遥雪滿寒山,上升玄閣遊絳煙。平明羽衛朝萬國,車馬合沓溢四鄽。……朝廷無事共歡燕,美人絲管從九天。*同上書卷一,頁64。
詩人客遊江淮之時在揚州遇到一位樵夫,竟然亦曾執戟前朝。當年與先帝在興慶和華清宮中的景象於是再次浮上腦際: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冬狩春祠無一事,歡遊洽宴多頒賜。嘗陪夕月竹宮齋,每返溫泉灞陵醉。*《白沙亭逢吴叟歌》,同上書卷二,頁74。
所有這些追憶之作都提到了驪山下的華清宮:“離宮積翠夜漏長”,“雪下驪山沐浴時”,“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這些歷歷如生的場景,已成爲記憶中被句讀被孤立被凝固被彰顯的斷片,成爲“時間之點”(spot of time)。在漢語文這種擯棄了機械式關係機構,而更注重具體脈絡和意義場合的孤立語中,*這是德國著名語言學家洪堡特對漢語的看法,參見關子尹《從洪堡特語言哲學看漢語和漢字的問題》,《從哲學的觀點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頁269—340。這些形象鮮明的斷片格外凸出。西方抒情詩理論慣由時間特徵界定抒情詩爲“强烈的”(intensive)“當下在場”(presence)或令文本“輾轉於一個非持續(discontinuous)的場景(occasion)”或“鬱塞之點”(block point)。*參見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87. Northrop Frye, “Approaching the Lyric,” in Chaviva Hošek & Patricia Parker eds., Lyric Poetry: Beyond New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1-32.法國現象學家巴徹拉(Gaston Bachelard)曾提出抒情詩的時間是垂直的,是將詩人從時間的相續中抽拔而出,令“時間不再流動。時間迸發着”。*這是留法專攻巴徹拉的黄冠閔對巴氏Instant poétique et instant métaphysique一書有關論點的概括引述,見黄冠閔《巴修拉詩學中的寓居與孤獨——一個詩的場所論》,載蔡瑜編《迴向自然的詩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頁259—294。在韋氏以上詩句中吾人見識的正是此令詩人鬱塞並輾轉於此的場景和垂直的、迸發的時間。然在韋氏,又是個人與家國的歷史時間。歷史在個人心靈上烙下愴痛,在國族世代居住的“山河”上留下蝕痕——韋詩有“攜手思故日,山河留恨情”,*《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一,頁4。“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廣德中洛陽作》,同上書卷一,頁7。“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經”*《酬鄭戶曹驪山感懷》,同上書卷一,頁35。——皆揭示這愴痛和蝕痕之深。大曆十一年(776)應物又逢中年喪偶之痛。*此處應物喪偶時間乃根據陶敏《韋應物生平新考》一文,見《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頁18。伊人已去,不可復還:“斯人既亦矣,觸物但傷摧。”*《傷逝》,《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三,頁135。這是歷經個人歷史時間中的慘酷。這殘酷同樣是: 歷史是只出現一次的存有現實,歷史時間因而是線性和不可逆轉的(irreversible)。
上文所論應物的靈修活動,主要是在歷經了這一切令他“心事若寒灰”,感到“歲月轉蕪漫”之後發生的。*《秋夜二首》其二,《感夢》,《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三,頁148,149。本文的論題是在此一語境下討論他的自然山水書寫,即他如何藉自然風物去修復和重塑他的身心靈。應物在詩中多次肯認了自然山水對靈修的作用,謂“青山澹吾慮”,“閑遊忽無累,心迹隨景超”,“景清神已澄”,*《東郊》,同上書卷三,頁169;《灃上西齋寄諸友》,同上書卷四,頁180;《曉至園中憶諸弟崔都水》,同上書卷七,頁326。《答馮魯秀才》更將自己郡齋的日常事務與對方於山水中休憩身心作了對比:
晨坐枉瓊藻,知子返中林。澹然山景晏,泉谷響幽禽。髣髴謝塵迹,逍遥舒道心。顧我腰間綬,端爲華髮侵。簿書勞應對,篇翰曠不尋。*同上書卷八,頁416。
然而,應物靈修活動中的自然,卻並非其在滁州西山、江州廬山、蘇州靈巖山的遊覽中所見的山水,在那種“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建隼出潯陽,整駕遊山川”的氛圍之中是無靈修可言的。*《遊琅琊山寺》,同上書卷七,頁320;《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同上書卷八,頁382。能真正陶冶其身心的反倒是居所或郡齋附近的水木和雨雲。前引文學理論謂抒情詩的時間是“集中而强烈”的一瞬,是“不持續的”“鬱塞之點”,是“垂直的”和“迸發的”云云,皆不能適用於應物這些詩作。相反,在應物這些詩中,吾人所見似乎是其持續生活流中漫不經心的任意一段光景,如門前流水、頭上行雲。請一讀其《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尊中物,餘事豈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疏頑。日夕臨清澗,逍遥思慮閑。出去惟空屋,弊簀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頽志亦何攀。惟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郊居言志》,《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四,頁208—209。
此詩寫於隱居灃上時期。詩人在衡門之下負暄,可見是個無風或至少只有微風的日子。在這樣的日子雲朵在天上遊移該是多麼悠緩,而恒久地注視着這一切的詩人,其以“負暄”的身體展開的生命姿態又該多麼蕭散簡淡!此詩的以下篇幅皆在書寫詩人是如何疏頑和逍遥。除卻時當歲豐之時“閭里一歡顏”這樣微末的願望,詩人已不像一般人在生命中“等待”,因此也就再無期求與忍受,一切只是隨遇而安。詩人身心在此已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時間節奏之中,如歸雲一般從容不迫。此詩之題中有“言志”二字,不啻爲一頗具幽默感的反諷,因爲這根本不是主觀志向的表抒,而是身體與陽光、大氣與流水的遇逢中的體驗。《郡內閑居》寫於應物刺江州任內,與前詩有類似的情調:
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如廬山緇。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同上書卷八,頁406。
在宣説了自己吏隱生活的意念之後,此詩插入了詩人酣寢之後獨自怔怔看雨觀花的景象。“衆藥”在雨中綻放,一定是無比悠緩地開啓花苞,十分優美地伸展出花瓣的“幽姿”。詩人的身心在此刻亦隨之如此從容地伸展着,套用梭羅的語言,“如玉蜀黍在夜間長起一樣,我在季節變換中成長”。*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New York: Ne3w American Library, 1960), p. 79.在此,吾人再次見識了應物如何融入自然時間的節奏。在這樣一種生命狀態中,雲緩緩遊移,花苞乍然綻開,乃至雨滴墜落,皆是詩。陳衍説:“自韋蘇州有‘對牀聽雨’之後,東坡與子由詩復屢及之,‘聽雨’遂爲詩人一特别意境。”*《石遺室詩話》卷一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9—10。但此詩的“看雨”同樣值得注意。明清文人清言中屢屢有玩味雨的體驗。如謝肇淛苦雨挑燈夜讀,聞紙窗外“芭蕉淅瀝作聲,亦殊有致”;*《五雜俎》卷一三,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67—268。費元錄“坐閣中閱古談詩,而遥空濯濯,飄搖無際,門絕剝啄,心手俱適”;*寶顏堂本《晁采館清課》卷上,頁29。高濂以時令排比西湖畔“詩化生活”的“幽賞”,即有“天然閣聽雨”、“山晚聽輕雷斷雨”、“乘舟風雨聽蘆”;*見《武林掌故叢編》第15集本《四時幽賞錄》,頁4,7,13—14。石成金列《舉目即是美景》中有“看雨滴花階”,*見汪茂和、翟大閩校注《傳家寶全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24。等等,皆可以溯至唐世詩人對雨的細細品賞。作於滁州的《西澗即事示盧陟》是另一首寫到看雨的詩: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水生。永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可散煩纓。*《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七,頁312。
此詩寫詩人注視着門前澗水中雨點激起的圓文,這真真是一“澹忘情”之出神狀態,因爲其生命的節奏於此完全與雨滴同步,逸出了“塵喧”,逸出了歷史的時間。西方現代隱士莫頓(Thomas Merton) 曾有過類似的體驗:“我仔細諦聽雨聲,因爲它會一再提醒我: 整個世界都是根據一種我迄今還沒有學會的韻律在運行的。”*轉引自Peter France, Hermits: the Insights of Solitude,中譯本《隱士: 透視孤獨》,梁永安譯,臺北,土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頁350—351。這世界運行中的“韻律”,亦即本文所説的自然時間的節奏。“永日”二句暗示: 這不被打擾,不被句讀的時間之流,仍在進行,持續延宕着,如遠處樵夫不停的伐木聲。作於灃上的《幽居》以另種方式書寫了詩人如何在雨中融入了自然時間: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四,頁215。
此詩先以內無所營,外亦無物論説“幽居”,中間插入微雨春草、青山鳥雀四句。以王堯衢的解説:
此心晝夜安閑,無思無算,無累無拘。莫説機械不生,能使見聞都泯。夜來微雨,吾不知有微雨也。至曉知有微雨,而微雨已過。草經雨而生,吾忘吾生,而安知草之生。夜間冥心,何意忽曙,蓋見山之有青而始知天色不覺已曉。卻又於何得知山青?蓋先聞鳥雀之鳴聲繞舍而知之。夫微雨春草、青山鳥雀,悉皆外物,一有容心,即爲所牽。此純是化幾,正妙在不經意。*《唐詩合解》卷二,《唐詩合解箋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64。
這裏所謂“不知”,是畢來德解莊子時所説的“意識的時而適當消失”。*〔瑞士〕 畢來德《莊子四講》,宋剛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頁90。即詩人非以心而是以其身體作爲整體經驗的場所。若以佛禪的話説,是詩人對一切聲色不作解會,不作知見,不作判斷,是謂“對境心不起”。*臥輪禪師偈,見郭朋《壇經對勘》,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頁127,134。禪宗這樣的公案不少,如:
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普濟《五燈會元》卷三《南泉普願禪師》,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37。
鹽官會下有僧,因采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秖見四山青又黄。”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五燈會元》卷三《大梅法常禪師》,頁146。
應物當是無迎無隨,融入了大化的節律之中,因而只是應機接物,“任運自在”了。如其詩所寫:
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浮。閑居淡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篁抽。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答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四,頁223。
應物以上幾首詩,很難被稱作所謂“山水詩”,因爲他只用了很少篇幅書寫了詩人如何面對身邊的草木雨雲。詩的中心無疑是人,是人的身體在大自然中的姿態。然而,這卻是韋詩自然書寫的特色。這一特色,古人即已識出,喬億謂“詩中有畫,不若詩中有人。左司高於右丞以此”。*《劍溪説詩》又編,《清詩話續編》(2),頁1122。在水木雨雲中的“詩中有人”,明示詩人身心一體的存有已進入大氣流衍的自然,*這裏不妨再想到瑞士漢學名家畢來德對莊子的解釋:“要進入莊子的思想,必須先把身體構想爲我們所有的已知和未知的官能與潛力共同組成的集合。也就是説,把它看作是一種沒有確鑿可辨的邊界的世界,而意識在其中時而消失,時而依據不同的活動機制,在不同的程度上解脱出來。”見《莊子四講》,頁90。“遊乎天地之一氣”。*《莊子·大宗師》,《莊子集釋》卷三上,頁268。以應物的詩句説即是:“迹與孤雲遠,心將野鶴俱”。*《贈丘員外二首》其二,《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九,頁446。韋氏的“詩中有人”留下不少身姿入畫的清景,如“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摘葉愛芳在,捫竹憐粉污”,*《休暇東齋》,同上書卷二,頁119。“長嘯倚亭樹,悵然川光暝”,*《義演法師西齋》,同上書卷四,頁181。等等。然其詩呈現身體最多的姿態是“臨流”。“臨流”二字表現了身體與大氣、水流遇逢而發生的經驗。據筆者統計,韋應物在詩中共二十次寫到臨流,這就很難説全無意味了。如以下的例子:
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疏空掩門。*《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四,頁190。
臨流意已淒,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答長安丞裴税》,同上書卷四,頁207。
臨流一舒嘯,望山意轉延。*《晚出灃上贈崔都水》,同上書卷四,頁225。
簪組方暫解,臨水一翛然。*《晚歸灃川》,同上書卷五,頁242。
望山亦臨水,暇日每來同。性情一疏散,園林多清風。*《答重陽》,同上書卷六,頁285。
怪來詩思清入骨,門對寒流雪滿山。*《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同上書卷一,頁52。
置鍤息微倦,臨流睇歸雲。*《西澗種柳》,同上書卷三,頁171。
日夕臨清澗,逍遥思慮閑。*《郊居言志》,同上書卷四,頁208—209。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西澗即事示盧陟》,同上書卷七,頁312。何以詩人臨流之際即頓感“逍遥”、“翛然”、“道心淡泊”、“疏散”、“忘情”和人間萬事“若遺”呢?無論自傳統抑或自應物詩的文本而論,水流皆是一暗示着歷史時間之外自然時間之流意味的意象,應物有一首尋曹溪深禪師詩中即有:“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閑。”*《詣西山深師》,同上書卷六,頁291。應物又有詩謂:“浮雲一别後,流水十年間。”*《淮上喜會梁川故人》,同上書卷七,頁335。“逍遥觀運流,誰復識端倪。”*《答庫部韓郎中》,同上書卷四,頁211。流水在韋詩中有“人托命於所繫”的“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之周流不止大化的意味。*成公綏《天地賦》,《全晉文》卷五九,《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8年,頁1794下。臨清流而逍遥,翛然疏散,即如陶潛“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歸去來兮辭》,《陶淵明集校箋》卷五,頁391—392。是身心自人類和歷史時間中解脱,融入循環而無窮,率常而不被句讀的自然時間——即其所謂“無爲化”——中去。*《答崔都水》:“不遇無爲化,誰復得閑居。”《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四,頁213。沈德潛謂韋詩得陶詩之“沖和”,*《説詩晬語》卷上,《原詩·一瓢詩話·説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207。此“沖和”乃得諸陶潛生命主旨之“乘化”。此亦應物得以“自在”之由。以這樣的認知,再不妨一讀韋氏的名篇《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黄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六,頁304。
趙昌平先生解是詩謂:“‘自’是一詩之眼。澗邊幽草是自生,葉底黄鸝是自鳴,春潮帶雨是自來,野渡無人是自橫。”*《韋柳異同與元和詩變》,《趙昌平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95。這真是一個很到位的解讀,筆者其實很難再增加點什麼。只就本節的論題,筆者要補充的是: 以“幽草”、“深樹”和“無人”,詩人强調這是歷史時間之外的世界。只有在此事事皆漫不經意的世界裏,在澗邊幽草的枯與榮、葉底黄鸝的啼與停、晚雨和春潮去而復來皆適然而循環的世界裏,詩人纔享受到翛然疏散的心靈解脱。正如應物在哀悼石崇一家之禍的《金谷園歌》的結句所述“百草無情春自綠”,*《金谷園歌》,《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一,頁34。在自然的時間裏,是再無憂傷的了。
四 方域模糊的空間
已有研究者指出: 相比王、孟、柳的山水田園之作多具體地描寫景物,景物的特徵性、地域性,時間性都十分鮮明,“韋詩中的景物描寫卻比較虛泛,所描寫的景物似可以放到各種背景中去”。*沈文凡《韋應物詩歌對陶詩的繼承》,《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第18卷第4期(2001年12月),頁36。這一觀察頗有見地,其原因值得深究。然而,筆者須首先説明: 如果與西文詩作比較,以上所謂“虛泛性”和多出以“簡單意象”乃爲中國古典詩的總體特點。中國大陸境外的學者如劉若愚、華生(Burton Watson)、高友工和梅祖麟、葉維廉(Wai-lim Yip)、鄭樹森等先後都指出了這一點。如華生經對唐詩意象的統計得出結論説:“中國自然詩人是在草草描出一幅差不多一般化(generalized)的風景——山、河流、樹木、禽鳥——而非具細節的描寫。”*Chinese Lyricism: Shi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33.鄭樹森在總結了各家説法以及對中英詩在語法上的不同特點後指出: 唐代自然詩對讀者而言“不可能產生華滋華斯的山水那種整體印象的特定性”。*《“具體性”與唐詩的自然意象》,《奧菲爾斯的變奏》,香港,素葉出版社,1979年,頁54。即便如此,以非特定的簡單意象書寫常景在大曆詩人中,特别是在韋應物詩中的表現卻特别顯豁,如前引沈文所説,因爲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筆下的景物畢竟還是輞川、襄陽和永州的景物,而韋詩的景物描寫卻一般不能如此。
這種方域虛化的空間首先在於: 詩人常常使用遠超出視野甚至神思的空泛指陳。韋詩有“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二,頁82。“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遊溪》,同上書卷二,頁79。“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鐘微”,*《送元倉曹歸廣陵》,同上書卷二,頁116。“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同上書卷二,頁80。這些詩句中空泛的指陳如“楚雨”、“楚天”、“楚山”、“廣陵樹”、“淮甸”已令境象格外空廓。而漢語詩歌所容忍的時而乏動詞、時而無介詞、時而無主語,更將由動賓結構所展開的基本敍述形式破壞,這末一例已完全是意象的並置了。
韋氏更慣於以絲毫不作修飾渲染的文字,書寫缺乏參指特徵的再平常不過的景象,上節所引其所寫之山上雲、廊外雨、水上雨滴皆爲如此景象。再看他如何寫郡齋內外:
似與塵境絕,蕭條齋舍秋。寒花獨經雨,山禽時到州。*《郡中西齋》,同上書卷九,頁456。
對於“似與塵境絕”的齋舍環境的兩句書寫,竟如此平常。以致劉辰翁説:“‘山禽’句,人人有此等語,但此自是蘇州語耳。”*《須溪先生校本韋蘇州集》卷八,楊氏楓江書屋藏元刻本《須溪先生校點韋蘇州集》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5。其實,韋詩對風物的書寫即着意在以平常語寫此平常景。平常風物、人情的描寫在其筆下觸目可見,如:
秋塘惟落葉,野寺不逢人。*《答楊奉禮》,《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七,頁362。
劉辰翁謂二句“荒寒如畫”,然此豈非秋日郊野隨處可見的景色?再如:
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永定寺辟强夜至》,同上書卷九,頁478。
這又是平常語出此再平常不過的光景,是冬日寺院中天天頻頻發生的平常故事,在應物卻是詩。又如:
定向公堂醉,遥憐獨去時。葉霑寒雨落,鐘度遠山遲。*《寄酬李博士永寧主簿叔廳見待》,《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一,頁46。
“葉霑”二句寫别時景物,亦是平凡之極。下面一首《燕居即事》當是寫自其罷任居佛寺內的生活景象:

凡曾夏日到過佛寺之人,大概皆見識過此情此景。韋應物在閑居中書寫景物從不尚奇峭,但求平常。以矛盾修飾的方式説,平凡、平常在韋詩中竟然成了特色。
然此對“常”的追求,不啻爲一種禪意,內中可體味“平常心是道”: 既然成佛也罷,爲官也罷,歸隱也罷,率非驚天動地之事,率皆稀鬆平常,則筆下之雲影天光、風霜雨露、卉木山水,又焉能不稀鬆平常?此皆是歷史時間之外,流水時光中的平常一瞬啊!此與其對侍衛先帝歲月中“垂直”或“迸發”時間裏“强烈而集中”的場景——“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云云——可謂懸若霄壤了!

應物筆下不僅有此有墨無筆之山水,甚或時有“無墨無筆”之山水,且讀以下《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波起,冥冥日沉夕。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六,頁273—274。
此詩是詩人建中三年由長安出發赴滁州途中乘舟經汴水過盱眙縣所作。盱眙的位置西枕汴河,南臨淮水。在詩人筆下,帆似乎落在了水天之間。“浩浩”與“冥冥”兩句,分别自水與天着筆,渲染出似無邊際的迷茫。五、六句令讀者感到這是一幅單一顏色在畫面上的層次,表達的是山水之間的明暗關係而非色彩關係。再讀其《賦得暮雨送李胄》:
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鐘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海門深不見,浦樹遠含滋。相送情無限,沾襟比散絲。*同上書卷七,頁367。此詩緊扣題目中“暮”、“雨”二字來寫。首聯、頷聯上下兩句皆分賦“雨”與“暮”,五句再賦“暮”,六句復賦“雨”。首聯中兩句分别將表示方位的介詞與表示時間狀語的詞置於句尾,頗有空間化的意味。這是一昏昧迷蒙卻元氣淋漓的空間。然除卻第二聯以“漠漠”與“冥冥”一對連綿詞對此作渲染外,詩卻呈現,在這寥闊空間裏,尚能看到什麼?詩人舉目之間但見孤帆和歸鳥,以“重”和“遲”兩字分寫帆與鳥,彰顯出此乃空茫中景裏僅有的兩撮墨痕。遠景中“海門”不見了,“遠含滋”之“浦樹”似以濕筆漬出。此是以乾淡之餘的“虛墨”暈染而出的“無墨之墨”。清鑲白旗人布顏圖論此“無墨之墨”曰:“山水間煙光雲影,變幻無常,或隱或現,或虛或實,或有或無。冥冥中有氣,窈窈中有神,茫無定像。”*《畫學心法問答》,《畫論叢刊》上卷,頁280。
以上二詩之境,又皆籠在晚鐘聲中。韋氏喜寫晚鐘之聲,據筆者統計,凡二十六見。其意味即如其《煙際鐘》一詩所寫:

這是一首詠物詩,透露韋氏心中晚鐘意象的意味: 它“隱隱”不知起自何方,又“迢迢”隨落暉而去,在蒼茫之中復逐愁思與暮煙而蕭散。如此,其筆下的鐘聲如“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鐘時”、“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同上書卷二,頁82。“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秋景詣琅琊精舍》,同上書卷七,頁338。“微鐘何處來?暮色忽蒼蒼”、*《登樂遊廟作》,同上書卷二,頁86。“杳杳鐘猶度”,*《晚出府舍與獨孤兵曹令狐工曹南尋朱雀街歸里第》,同上書卷二,頁110。更以遲緩的流逝來凸顯空間的迷茫和曠遠。
韋詩空間書寫中虛化方域的另一特徵,置之於中國古典詩的傳統中很值得注意。宇文所安在《盛唐詩》一書中已注意到韋氏後期詩作中“經常出現對遠方情景的揣想”,並時常以“與詩人絕對分割的異地或異時的‘他處’”作爲閃回之景以結束詩作。*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p. 309, p. 313.另一位美國學者瓦薩諾(Paula M.Varsano) 則經比較此前山水詩人與韋應物的自然書寫之後指出: 後者不同之處在不再給出能顯示“文本中的眼睛”(eye in the text)所在方位的一兩個因素,即不再給出風景、詩人、生動而獨特視覺細節之間有直接和“真實”關係的印象。換言之,韋應物“常常拒絕容許任何確定性”。*Paula M. Varsano, “The Invisible Landscape of Wei Yingwu (737-79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4,no. 2 (Dec., 1994), p. 412.他進而提出韋詩時有“雙重視境”(double vision): 兩個視境的相互排斥終將讀者置於空泛之中。*Paula M. Varsano, “The Invisible Landscape of Wei Yingwu (737-79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4,no. 2 (Dec., 1994),pp. 414-415.瓦薩諾舉出的四個詩例中有兩首是韋詩的名篇。*該文的另外兩個詩例爲韋應物《寒食寄京師諸弟》和《南園》。且讀第一首《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七,頁363。此詩的三、四句,是揣想中的景象,卻最終沒有回到首句的“郡齋”以確認“文本的眼睛”之方位。詩人轉向了想象中被落葉覆蓋的空山,由此那一片揣想中的世界最終與模糊的郡齋世界聯接起來,而這片空山卻“既不可見(invisible)亦無從進入(inaccessible)”。*Paula M. Varsano, “The Invisible landscape of Wei Yingwu (737-792)”, p. 416.瓦薩諾對另一名篇《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的分析獨具隻眼: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九,頁434。這首僅有二十個字的小詩竟有彼此兩處分割的世界: 郡齋涼夜中的詩人和臨平山中幽隱的丘丹。夜靜山空,或許是爲詩人吟詠之聲驚動,庭院中一粒松子跌落下來。詩人由此揣想: 在另一空山中,松子落地之聲“應”令山中的丘丹不至睡去。這粒松子落地的聲響遂將兩處世界“疊合”(superimpose)起來。然而,難以分辨的是: 這是郡齋內詩人聽到松子落地,抑或他揣想臨平山中松子落地?抑或應物聽到松子落地聲後設想自己是丘丹在山中聽到了松子落地?*“The Invisible landscape of Wei Yingwu (737-792)”, p. 417.是詩的美感正基於此特别的“歧義性”(ambiguity)。
在瓦薩諾的詩例之外,筆者想再舉一例説明韋詩空間書寫中的歧義視境。請讀《淮上遇洛陽李主簿》:
結茅臨古渡,臥見長淮流。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寒山獨過雁,暮雨遠來舟。日夕逢歸客,那能忘舊遊。*《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二,頁83。
按孫望繫年,此詩是應物自廣陵歸長安途中所作。而由韋氏《送李二歸楚州》、特别是《答李澣三首》中“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兩句推知: 在淮上結茅而居的應是李氏。但此詩首聯、頸聯和尾聯皆非自詩人自身,而是以淮上結茅的李澣口氣説出他的記憶和當下感受。三、四句卻又是舟上“歸客”即韋氏的視點。這種視境的轉換往復在不設主語而無妨的古漢語詩裏毫無滯礙,卻悄然將悠長歲月的境象與眼前的境象疊合起來:“古渡”令人想到櫓聲中迎來送往的單調歲月,“長淮”中流逝的亦是日日如常的時間,這是結茅於此之人慣常到不免麻木的視野。而三、四句中的“人將老”和“樹已秋”卻是經由“古渡”、“長淮”而流逝的時光之結果,是乘舟經此地的詩人此時之所見,其中分明有某種驚異和憐惜之情。頸聯和尾聯則是單調如流水歲月中的某種意外之喜。這種種視境的疊合不僅自時間向度上擴展了詩境的幅度,且蘊含了複雜的情感,是詩人自主客的雙重視境去體驗結茅古渡的生活。
書寫被揣想的他方景象是應物詩作的一個特點,然詩中的他方人物——全椒山中“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的道士、杼山中“鳴鐘驚巖壑,焚香滿空虛”的皎然,*《寄皎然上人》,同上書卷九,頁441。親歷着“幽澗人夜汲,深林鳥長啼”的臨平山中丘丹,*《重送丘二十二還臨平山居》,同上書卷九,頁461。夜宿於“白雲埋大壑,陰崖滴夜泉”的琅琊山中法深、道標二釋子,*《懷琅琊深標二釋子》,《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六,頁295。“見月出東山,上方高處禪”的藍田山僧人,*《上方僧》,同上書卷二,頁96。以及淮上結茅的李澣,等等——皆是與腰纏竹符的應物所處場所不同的隱者。這種想象聯接起郡齋與山林,成就了其不拘行迹而基於心靈澹泊的“吏隱”。且爲詩人措意之他方景象,亦不過些許筆墨、些許物事,至如空山一粒松子,讀者須於聲色臭味之外求之。然惟其如此,其與詩人所處此地之間,方有無限清空,涵容了所謂“不可見的風景”(invisible landscape)。以此,吾人得以理解韋應物刺滁時何以會如此吟詠郡齋之內一片置石:
遠學臨海嶠,橫此莓苔石。郡齋三四峯,如有靈仙迹。方愁暮雲滑,始照寒池碧。自與幽人期,逍遥竟朝夕。*《題石橋》,同上書卷七,頁366。
詩人將郡齋中的尺山片水想象爲孫綽筆下天台山的莓苔石橋。憑藉這一片有依托的想象,一方大吏的詩人遂成爲隱居深山的“幽人”。這是白居易之前,元結道州瀟水“石魚”之後一重要的文人以片石幻化山水之個案。*參見蕭馳《從山水到水石: 元結、柳宗元與中唐山水美感話語的一種變化》,《中正漢學研究》2014年第2期,頁293—332。就本文的論題而言,這裏由“吏隱”者的心迹而顯示出韋詩空間書寫中一重要特徵。如其“吏隱”觀念强調“心”一樣,現實中的方域不妨被忽略。如佛禪所謂“芥子容須彌”,莊子所謂“知毫末之爲丘山”一樣,*《莊子·秋水》,《莊子集釋》卷六下,頁577。這是一種以心靈運思的空間,境界形態的空間,*讀者於此可參看潘朝陽《莊子逍遥遊的空間論》、《莊子的空間論:“秋水”的詮釋》二文,《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頁273—324。由詩所開闢的空間。置之於中國隱逸文化的傳統裏,它與輞川谷以及後世盤谷以在地形學上强調“宅幽而勢阻”以分割內外的觀念迥然有異。*參見蕭馳《問津“桃源”與棲居“桃源”: 盛唐隱逸詩人的空間詩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3月),頁1— 49。
五 結 論
學界討論韋應物“吏隱”一般主要措意於其出或處的行迹,以及與此相關的郡齋或山林的場所。本文以爲此中其實有某種迷思。
韋應物是一生經歷過人格巨大轉變的詩人。職乎此,本文提出探討韋應物的“吏隱”應關注其有基於佛禪、老莊和道教的靈修活動這一事實,而韋氏的詩歌文本及中唐的思想脈絡則爲這樣的觀察提供了依據。韋氏對出與處、郡齋與山林取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特别彰顯於其所謂“閑居”意識之中。對應物而言,歸隱是“閑居”,爲官亦是“閑居”。“閑居”開啓了其於郡齋附近或郊野中遊乎草木雨雲,霽月光風的生命世界。在此,“閑居”不止是一種人們時常愛談論的“心態”或道心修養,“閑居”是一種生命存有的姿態,一種“道行”的身體實踐。本文重點討論了其“道行”的兩種面向。首先是藉身體與陽光、大氣與流水遇逢中的經驗去回歸自然生命的節奏,以撫平歷史刻鏤在記憶深處的愴痛。以此,他令吾人不得不去顛覆近代西方對抒情詩的界定: 詩在此不復是高度强烈的,垂直而迸發的瞬間,而是流水般時光之流中的一瞬。此中亦蘊含了何以詩人面對自然時常常僅止於稀鬆平常景物書寫的緣由,使他成爲將簡散平易風物帶給中國景觀傳統的最重要詩人。其亦以其空間書寫中對方域的其他種種虛化微妙地體現了“閑居”的姿態。在此,空間之疏曠體現了詩人性情之疏散,而多重的甚至歧義的視境更直接體現了其神遊於兩重世界的“吏隱”者心迹。這頗令人想到巴徹拉借法國作家迪奧勒在荒漠中行走而想象空間溢滿水的經驗而説的一句話:“此地的存有被一個他方的存有所扶持。”*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 Maria Jola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 208.人謂韋詩悠閑澄澹,吾人斷難以“抒情”、“表現”論之。然韋詩的風物書寫,包括其“淡而緩”,*方回《柳州峒氓》評語,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88。“不迫切”,*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59。往往“以夷猶出之”的文行之象,*王船山對其《效陶彭澤體》一詩的評語,見《唐詩評選》卷二,頁970。皆彰顯出其生命存有的姿態。
(本文作者係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從德勒茲《差異與重複》來觀察
——德里達與胡塞爾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