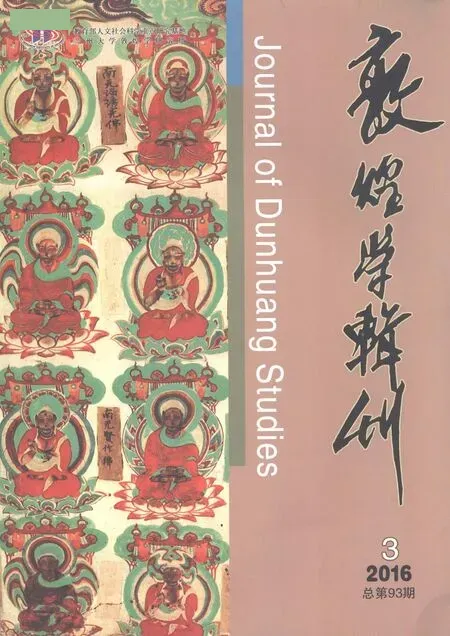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学
王晶波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本文试图从文化心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重释百年以来敦煌文化学术的发展历史。因中外往来而产生而繁荣的敦煌,也曾因往来中断而衰落沉寂,最终在新的世界文化交往中,成为丝绸之路上沟通中西、连接古今的重要文化坐标。百余年来敦煌文化学术的发展,也和两千年的敦煌历史一样,深深受到中外文化沟通交流的制约影响。归纳起来看,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敦煌学,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文化失守、文化保护(保守)、主动出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同时又分别对应着自卑退让、保守自立、自强自信三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敦煌学百余年来的兴衰历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国力强盛与文化自信的必然产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走向国际的学科,敦煌学也必将在这一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文化失守与敦煌学初兴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与丝路相伴而生,休戚与共。从西汉至宋元的一千多年中,敦煌在沟通中西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华戎所汇的一个重镇,它的兴衰命运也与这条通道紧密相关——当丝路畅通,国家强大,它就繁荣发展;而当丝路中断,动荡纷乱,它就衰败落寞。汉唐之间是敦煌发展的辉煌时期,元明之后,随着陆上丝路的中断,它也被世界遗忘,湮灭于历史的尘沙之中。敦煌再一次被世界瞩目,也同样是因为这条古老丝路的再次连通,焦点则是莫高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与流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西陆上交通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在一些西方学者及探险家的关注下,这条绵延数千公里,连接古代中国与亚、非、欧的陆路商业贸易外交通道,得到了“丝绸之路”这样的命名,重新引起世人的注意,不过,这时丝路的“重新发现”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带给中国的并不是像之前那样的贸易繁荣与文化交流。西方列强沿着丝路由西而东,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学优势,对衰落的东方古国进行文化侵略与劫夺,迫使中华文化一再的退让与失守,敦煌文献恰逢此时被发现,也就难逃被劫夺的命运。
从敦煌学的角度来讲,这一阶段的文化失守,首先表现在敦煌这个汉唐时期的丝路交通重镇文化重镇,长期沦落为文化荒漠与游牧之地,直至清初才重新设县管理,但人口稀少,民生凋敝;其次,与敦煌密切相关的新疆地区的文物文献被俄德英法等探险家大量劫夺;再次,藏经洞文献由王圆箓发现并保管数年,看守文化高地的角色,落到一个没有文化的道士身上,也同样是文化失守的表现。而中国官府及文人对敦煌文献的漠视态度,更是这种文化失守的突出表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传统社会风雨飘摇之际,封闭许久的国门,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已然洞开,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也行将崩溃。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并努力呼吁,但整个社会及学术文化界,尤其是官僚统治阶层,仍处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中,在巨大惯性的主宰下,麻木昏瞆,苟且偷安。国力衰弱文化落后,导致整个民族产生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与文化自卑心理,文化失守就在所难免。
所以,当王道士打开密藏千年的藏经洞,并把这一消息报告官府之后,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无论是当时的安肃道道台廷栋、敦煌县长汪宗翰,还是甘肃学政叶昌炽等,他们都先后得知了这个消息,并看到了藏经洞所出写经及佛画,虽然也赞叹其珍贵精美,但囿于观念的陈旧及学识眼力,均未能认识到这一发现的伟大意义,甚至连被称为“近代图书馆鼻祖”的缪荃孙在亲耳听到伯希和所说藏经洞消息后,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奇闻”来看待。这些堪称社会知识精英的学者、官员都未能认识到藏经洞文献的意义,也未有一人对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了解,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学术界,确实已处在一种极度僵化守旧的境地,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与时代,不了解时代学术潮流与学术的内容,也失去了鉴别其价值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和行动的意愿。自然,也就不会去保护这些珍稀的文物文献。
故而,当西方考古家探险家在新疆大肆挖掘古墓,盗割精美壁画时,人们毫不在意,甚或提供便利;当斯坦因、伯希和将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捆载而去时,学界浑然不觉;当西洋及东洋学者在书肆旧家广泛搜购古本时刊之际,人们仍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当1910年清政府将劫余的敦煌文献调运回北京,沿途屡经大小官吏豪绅的窃取,到京后又遭李盛铎、刘廷琛等官员的公然盗窃,凡此种种,其实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在政治、军事、文化屡遭挫败的背景下,整个社会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保护,有的只是一再的退缩与失守,甚至自暴自弃。
可以说,敦煌文献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吉川小一郞、华尔纳们劫掠而流散国外,这个历史罪责,更多应由那个时代、政府,以及知识文化界,甚至全社会来承担。王圆箓只不过是那个具体经手的人而已。历史选中他作为那个文化失守时代的象征,也算是他的不幸吧。
二十世纪初的敦煌文物文献流散的惨痛现实,激起国人长达一个世纪的强烈文化反应,也从另一面为中国文化学术重新走入世界开启了路径。敦煌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形成乃至确立的过程。敦煌文献的发现及敦煌学的建立,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中国学术界对敦煌文献的正式认识,有赖于东西方学人的一次交流。这就是1909年秋天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在北京的著名会面。这次文化交流的实质成果有三:(1)中国学界正式认识了敦煌文献,并立即开始相关研究;(2)了解到藏经洞的情况,清廷学部将劫余写卷提调至京加以保护研究;(3)开始了法国汉学界与中国学界的资料交流与研究合作。以这三项成果为基础,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从此起步。
这次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实在应该大书特书,它的重要性仅次于王圆箓开启藏经洞,正是有了这次交流,敦煌文献才正式为中国学界所知,也才有了后来的敦煌学。因而可以说,敦煌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和国际文化学术交流密不可分。
若说敦煌文献被劫夺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让国人真切认识到敦煌及其文献的重要,刺激起国人的爱国热情,奋起保护文化遗产,并尽力对之进行研究。
二、文化保守与敦煌学的发展
在敦煌学初兴后的数十年中,在文化危机和失守的背景下,国人从文化、学术、对外交往等不同方面,被迫融入世界,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对石窟壁画、文献文物进行积极的保护与研究。
如果说敦煌学初兴阶段的研究,还只是一些学者个人的自觉行动的话,民国建立后,越来越多的组织单位或派人去巴黎伦敦转录拍摄敦煌文献,或对国内所藏劫余文献进行编目整理辑存,或者由政府组织对莫高窟的调查编号,都表明敦煌学研究逐步进入了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阶段。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以敦煌为首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正式纳入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坚持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统一领导,为敦煌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尤其在敦煌莫高窟保护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这个阶段的敦煌学研究,虽然经历了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权交替的历史过程,但就其实质而言,可以概括为文化坚持与文化保守。
敦煌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动力,就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早期的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董康等人的研究及推动有此因素,后一阶段的学人也同样怀着爱国的情怀。无论是刘复、王重民、陈寅恪、陈垣、向达、姜亮夫的历史、文学、文献研究,黄文弼、向达、阎文儒、夏鼐等人的西北考察考古活动,贺昌群、何正璜、卫聚贤、谢稚柳等人的艺术研究,以及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张大千等人的壁画临摹与艺术考察,其根底里,都有世危时艰的情况下抢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初衷,这个动力支撑着几代学人或远涉重洋,去欧洲抄录文献拍摄照片,或在国内整理劫余文献,或冲沙冒雪,去敦煌临摹壁画,在艰难条件下不断取得成就。民国的短短几十年中,敦煌学与中国现代学术能够全面进步,从学术体系的创立,研究领域的拓展,到研究资料的取得与运用、研究方法的创新,等等,除了时代潮流、国际交往、学术自身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之外,爱国情怀与民族主义精神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保守。
这时期的学者,无论是固守传统反对西学的人,还是思想开明接受新知的人,在面对敦煌文化艺术时,所体现的文化态度其实是相当一致的。比如常书鸿,他在巴黎了解到敦煌莫高窟及其艺术,受其吸引而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受命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从此便守护在敦煌莫高窟,从事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无论家庭变故还是世事变迁政治动荡,都未能动摇他的决心。他后来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守护”二字,正贴切地反映出那一时代敦煌学以及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实质使命。
新中国建立至文革前的一段时期,在激进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下,敦煌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实际上也同样表现出文化保守的特点。首先,伴随着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掠夺的批判,敦煌劫经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材,包括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华尔纳在内的外国探险家的文化劫夺行为一再受到揭露与批判。其次,敦煌学研究的中外合作交流也大多中断,中国学者在一个逐渐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独立研究;再次,研究领域较前有所收窄,一些领域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禁区,诸多成名学者的研究未能在以往基础上继续拓展,而是集中在对早期已有成果的结集出版与修订上。有关文物保护、考古、史地、语言、经济、社会和科技史料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进步,尤其是敦煌莫高窟得到全面的加固维修,一改以往任其颓圮的局面,是当时最重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举措之一。
比较极端的“文革”时期,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敦煌学在内,几乎全都趋于停顿。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特点。
可以说,在敦煌学从起步初兴后的五十多年发展中,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无论在前期国际交流合作条件下敦煌学的全面展开推进,还是在后来隔绝封闭下的局部深入,构成其总体基调与特点的,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保守。这比起前一阶段的不自信与失守,无疑是一个进步。
三、文化自信与敦煌学走向世界
1976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革开放,国人认识到与世界的差距,中国的文化学术从不同的方面奋起直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文学术领域中最先具有国际学术视野与国际交往的学科,敦煌学也就率先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与先锋。
敦煌学重建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敦煌学重建也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前一时期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动力是对“伤心史”的回应,这一时期的动力则是对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说法的回应。这种回应,表面看来虽然仍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但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爱国主义,随着改革进程和国家的强大进步,这一时期不再将敦煌看作一个孤立的文化遗存,而有了更加广阔的胸怀与视野,将其看作整个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的一个节点,是中华汉唐文化强盛、繁荣、包容、开放、进取的象征。三十年来敦煌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中享有如此高的地位,也和中华民族渴望复兴的愿望和对它所象征的这些精神的向往有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再回头看百年前的劫夺史时,心态不知不觉中已变得平和了许多,不再只从一国一族出发,而是从人类的角度全面看待敦煌文化,这是中国恢复其大国文化自信,走向民族复兴的精神自信的表现。
出于这种回应,中国的敦煌学从国家到学者个人都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与自觉,很快完成了敦煌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的进程,并逐渐步入全面繁荣的新时期,在历史、文学、文献、语言、艺术、考古各个领域都有可喜的进步,走到了世界领先的位置。
以敦煌与敦煌学为核心,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分别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广泛展开。作为中西交流的文化标志,有关敦煌历史、文化、艺术、文献等各方面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欢迎与喜爱,如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率先走出国门,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带动了世界对敦煌及敦煌艺术的关注与热爱,成为展示敦煌文化艺术的使者,为中外文化交流拓宽了道路;敦煌文物壁画在国内国际的巡回展览,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走入欧美的大型美术馆,令世人更真切地感受敦煌的魅力。
学术研究的交流,也自80年代起就广泛开展于中外学者与团体之间,各种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参加者十分广泛,不仅是早期就有敦煌研究传统的国家地区学者如英法日俄德韩及中国学者的参加,近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广大丝路沿线的中亚西亚及东南亚国家学者也积极参与,使得这一学术影响迅速扩大加深;各国敦煌文献文物收藏单位通力合作,在中国国内出版了绝大部分的敦煌吐鲁番及黑水城文献文物图册,特别是,近年通过国际协作,建立了“国际敦煌项目:丝绸之路在线”的国际网站(IDP),“目标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写本、绘画、纺织品以及艺术品的信息与图像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地获取,并通过教育与研究项目鼓励用户利用这些资源”。这是老一辈敦煌学研究者所不能想象的一个巨大进步,当人们在互联网上自由获得这些收藏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材料并进行研究时,谁还能说敦煌学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而不属于全世界?这正说明,最好的遗产保护,就是使其重获世界影响,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学术研究组织机构的完善与提升,人才培养系统化。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敦煌研究院及一些大学及科研单位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使敦煌学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系统化的道路,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敦煌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堪称集大成的学术成果。资料方面,如大型敦煌石窟与壁画图录的编纂,以及英、法、俄、日所藏文献以及国内重要收藏单位藏品的影印出版之外,分类文献的整理释录也取得众多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都比较及时地得到译介;研究方面,在新老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研究的领域得到充分拓展,在历史、文学、文献、语言、艺术、考古、宗教等各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与成果,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做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这时的敦煌学研究,将反思传统与回应西方结合起来,将证明过去与阐释当下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意识形态下,着重强调敦煌文化所体现的强盛、开放、丰富,强调民族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敦煌及敦煌研究不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途径,也成为海峡两岸文化合作的一个平台,在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发展融合方面发挥着特殊的意义。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最终走出文化自卑与文化保守的阶段,显示出新的文化自信力,勇于走出去与国际学术文化接轨,敦煌学不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象征,敦煌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目标为敦煌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从文化失守、文化保守到文化复兴,这是个很大的转变,其中隐含着社会文化心理由不自信到保守再到自信的重大变化。
而在国力增强,经济文化取得重大飞跃,中华文化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提出,可看作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与趋势,是摆脱一百多年来落后失败的阴影,重振中华文化自信的体现。在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敦煌学,也必将在其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