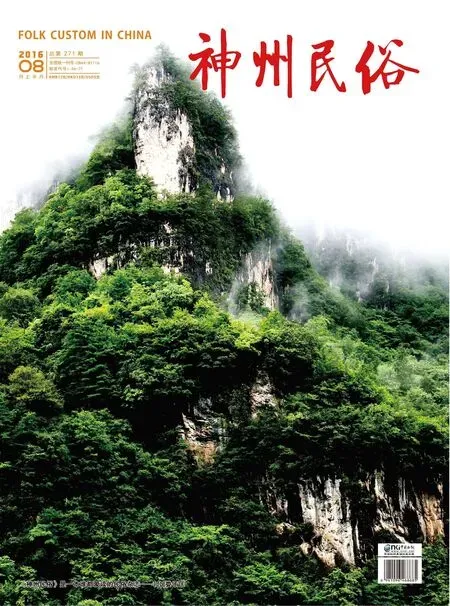审美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原创歌剧审美观照
陈维薇
(星海音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00)
艺术教育与研究
审美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原创歌剧审美观照
陈维薇
(星海音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00)
审美主义作为当代“时尚”的美学思潮,对包括歌剧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审美主义对感性审美的强调以及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赋予了艺术更多的本体性追求,但是在当代语境下,歌剧的审美与功利、泛审美化与艺术特质、精英意识与人民性缺失,则是审美主义对歌剧的深层影响的典型悖论。
审美主义 歌剧 泛审美化 艺术特质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的艺术形式都植根于这个时代的文艺思潮,中国原创歌剧作为西方歌剧理念的中国“产儿”,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一直与文艺思潮形影相随:1942年之后一直到80年代的《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等歌剧作品深受革命文艺思潮的影响,歌剧承担了较多的社会政治功能,可以说歌剧对意识形态的强烈“迷恋”,让这一时期的歌剧表现出了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80、90年代之后的《伤逝》、《原野》、《屈原》、《张骞》则是在文艺反思思潮的影响下,对中西文化交融、雅俗文化分化的理解和反思的过程中,对歌剧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产生了质的理解。而世纪之交直至现在的歌剧《红河谷》、《山村教师》、《咏·别》、《赵氏孤儿》、《米脂婆姨绥德汉》、《骆驼祥子》等,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在这其中歌剧的现代性问题是核心,歌剧既具有启蒙思想的强烈意味,又具有颠覆传统,着力于形式创新的歌剧探索与实践,中外各种文艺思潮的冲撞和交融是这个时期歌剧最明显的特征。而在众多的文艺思潮当中,审美主义作为当下比较“流行”的文艺思潮,对各种文艺形式的影响是深刻的,歌剧也不例外。
一、审美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对当代中国原创歌剧的影响
作为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重要文艺思潮,审美主义经过几十年的理论论证和审美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特征,审美主义既有对理性社会的反思,也有对个体存在状态的审视,叶世祥教授在《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四个层面》中对审美主义从四个层面进行了定位:从本体论上来说,审美主义强调的是审美的主体性;从功能层面来说,审美主义重视审美的精神救赎作用;从价值层面来说,审美主义重视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从泛审美层面来说,审美主义是功利社会里的,文艺“雅词”。[1]这四个层面是对审美主义精神要义的精准概括——审美主体、精神救赎、感性自由和自我印证。
审美主义思潮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有着深远的理论来源和现实土壤。审美主义一般将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作为发轫,尼采认为科学理性让宗教的精神救赎失去意义,而人感性存在的日神和酒神酒神在技术理性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在他看来能够拯救艺术,拯救人生的手段只有对审美的回归和张扬,而这一切从他宣称“上帝已死”开始——“宗教消退之处,艺术就抬头。它吸收了宗教所生的大量情感和情绪,置于自己心头,使自己变得更深邃,更有灵气,从而能够传达升华和感悟,否则它是不能为此的。”[2]
审美主义的另一大理论源泉是海德格尔,它将审美与人的存在之思联系在一起,在对“此在”和“彼在”的理解当中,将人的存在和“此在”世界结合在一起,试图在科学理性统治一切的世界里找寻人“诗意栖居”的途径,从而解决个体“被抛”的状态。因此,海德格尔对审美主义的强调是针对西方社会“异化”的一种批判——人生活在世界黑夜,人的本质被忘却,“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3]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强调的是对个体存在的重视,而这恰是审美主义重视个体感性审美的理论渊源。
中国当代对审美主义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五四”精神的回归,尤其是经历“文革”之后,自由、民主、个体存在感的找寻成为知识分子肯定和张扬主体性的精神依归,“审美主义通过彻底肯定人的感性生存来肯定人的主体性。”[4]这种主体性的精神依归既迎合了美学风潮,也契合了整个当代社会结构、精神理念的变迁,人不是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框定之下的理性存在,而是鲜活的生存个体。如果说审美主义思潮在中国是作为一种对“制度理性”突破的话,西方的审美主义思潮更多的是对“工具理性”和现代性的一种挑战。
中国当代歌剧同小说、影视等文艺作品一样一直没有脱离理性思维的窠臼,歌剧引进初期深受政治理性的影响,歌剧是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从选材、表演形式到音乐唱腔,歌剧承担着向大众宣传“新时代”、“新风向”的重要任务,歌剧《白毛女》正是政治理性的典型代表,它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直接孕育的一朵艺术奇葩,它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又在编剧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的革命斗争的现实因素,可以说歌剧《白毛女》开启了歌剧民族化的进程,但是,它以革命为题材,表现中国农村复杂斗争的社会现实的创作初衷以及它对民族风格、品等和中国农民精神风貌的展现,无疑是当时社会政治理性的艺术再现,歌剧《白毛女》以及经典唱腔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和符号,“关于《白毛女》的评价由最初的‘争鸣’到漫长的‘复述’,通过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复述’,不断丰富和补充了权利话语,构建出‘革命经典’,以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需要。”[5]
受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现代主义、审美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美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原创歌剧在戏剧创作理念和实践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倾向,歌剧审美功能的重新发掘,歌剧角色的个体存在感的强化,歌剧创作的个性化特征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是审美主义思潮影响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当代原创歌剧的工具性功能并没有改变,中国当代歌剧的主潮是严肃歌剧、民族歌剧和小剧场歌剧,其中小剧场歌剧通过对感性审美的重视以及对个体自由和个性的重视,表现出了明显的戏剧创新意识。而严肃歌剧、民族歌剧则坚持歌剧的雅化倾向,歌剧成为民族文化自我正名和表白的工具,意图在国际歌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取得歌剧的中国发言权,歌剧的这种工具化倾向仍然没有摆脱歌剧理性化的思路。
这种理性化的思路突出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这一时期的歌剧创作占主流的是对传统题材的挖掘上,《西施》、《张骞》、《原野》、《咏·别》、《骆驼祥子》等歌剧都是对既有文学作品的改编和创制,这一方面是对小说等艺术形式影响力的继承,从而间接的吸纳了部分受众群体的欣赏期待;另一方面也是歌剧通过对民族艺术形式进行改编而进行自我确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原创歌剧通过本土文化的挖掘,试图对西方传统歌剧的强势传统进行突围和变革,从而彰显歌剧的“中国化”,以取得与西方歌剧进行对话的权利,“戏剧的发展不是一味的移植强势文化作为唯一的出路,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要传承发扬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和合适的土壤。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6]四幕歌剧《咏·别》题材选择同电影《霸王别姬》一样,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同性爱情故事,这部孙戈璇编剧,叶小钢作曲的歌剧巨制,在传承中国传统戏剧的精致、含蓄、写意、唯美的艺术特色的同时,通过超强的制作团队和明星阵容,试图展现西方歌剧艺术的戏剧性的冲突和张力,站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眺望,是新时期中国原创歌剧的普遍现象,在这里歌剧并没有摆脱工具理性的枷锁,歌剧仍然是身份确认的工具,而不是纯粹审美的自觉。
二、中国原创歌剧的审美主义悖论
审美主义对中国原创歌剧的影响是复杂的,审美主义试图用张扬个体的审美精神价值来肯定人的审美感性,从而对传统的工具理性尤其是政治理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这表现在中国原创歌剧身上就是歌剧通过对自身审美特征的肯定,来表现个体的感性存在,展现工具理性时代个体争取自由和精神价值的努力,“现代工具理性文明对个体精神的物化作用催生了审美现代性,其思想的核心是,艺术对现实的否定与反抗作用能使个体产生一种内驱力,去质疑现代异化文明,寻得精神救赎并重新确立自我。”[7]但是,中国原创歌剧在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了诸多审美的悖论现象:歌剧的审美价值与功利目的、歌剧的泛审美化与歌剧的艺术特质、歌剧的精英艺术与人民性的缺失等。
其一,歌剧的审美价值与功利目的注定是一组悖论。审美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对审美感性的推崇,认为个体的审美感性是人 “诗性”存在的前提,在这里审美主义承载了启蒙主义的功用,它通过对当代社会人的理性存在的批判和感性的张扬,实现对人类精神家园丧失和个体精神价值迷失之后的艺术构建,也就是说审美主义通过对艺术“非功利性”的肯定来实现艺术的“功利性”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学悖论。
歌剧对审美属性的重视这是毫无疑问的,歌剧本身是综合了音乐、舞蹈、戏剧、舞美等元素的综合艺术,表现美,传达美,用美感染人,从而构建审美的理性世界一直是歌剧的艺术追求,歌剧通过音乐的戏剧性和戏剧的音乐性,通过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和合唱等固定的音乐体裁,让观众在欣赏歌剧时参与到审美体验当中,概而言之,“歌剧艺术具有高度综合美的戏剧性、音乐性的审美特征。”[8]因此,重视审美特征的展现,重视观众的感性审美应该是歌剧的必然要求,然而,歌剧并不是纯粹美的形式,它本身必然也具有社会意向性,对社会的关注,对个体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通过歌剧所展示的内容来实现艺术对社会、对人生的干预,也必然是包括歌剧在内的所有戏剧形式的必要归宿。“戏剧这门艺术,是如何扩大和优化人的生活空间,丰富和诗化人的生活内容的呢?戏剧是精神文化产品,它的天职是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如对自由、幸福的思考、追求与想象,对灵魂的慰藉、充实与鼓舞,等等。”[9]
受审美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歌剧表现出了明显的重视观众感性体验的艺术特点,通过国际联合制作将歌剧的打造的更宏大、更唯美、更有写意风格是当前歌剧的创作倾向,但是在处理观众感性审美和理性主旨两组悖论时,往往表现出了为内容而内容,为形式而形式的简单思维,这都是审美主义思潮在歌剧层面的表现。
其二,歌剧的泛审美化与歌剧的艺术特质也是一组悖论。审美主义的存在之思和精神救赎主要是针对当今社会的科学理性导致人的审美能力的丧失和人的“此在”精神家园的沦丧,它所提出的构建个体精神家园的努力就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因此审美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价值,它针对的不是特定的群体和国度,而是对人类整体存在的一种反思,是通过审美化的手段,实现人的“诗意栖居”,这也是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救赎的主要工具,被科学理性日渐剥离之后的唯一的救赎选择,这也造成了审美主义的泛审美化特点,泛审美化的突出表现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人有关的所有物体都打上了审美的烙印,商品的包装、商场的美化、住所的诗意构建等等,但是,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却丧失了审美的深度,就像陆扬教授指出的:“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征出来。美失去了它更深邃的感动人的内涵,充其量游移在肤浅的表层,崇高则堕落成了滑稽。”[10]
当前中国原创歌剧的这种泛审美化表现非常突出,歌剧逐渐丧失了它的艺术特质,而更多的沦为一种“功利主义、政绩主义和冒进主义的结合体”[11]歌剧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文艺符号,成为表现某一地域或者某一行业进行自我宣传或者获奖的工具,突出表现就是编剧粗糙、导演外行、音乐粗制滥造、舞美的“排场化”以及制作的“快餐化”,歌剧在功利性的驱动下,打着“泛审美化”的幌子,进行“车间式”的生产,在较短的时间内创作出大量的用来日常消费的歌剧作品,从历史典故的挖掘到日常生活的提炼,歌剧基本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歌剧审美性的关注在哪里,歌剧的艺术特质是否能够较好的坚守却成为问题。
其三,歌剧的精英意识与人民性的缺失是当代最突出的悖论。审美主义源自尼采的“上帝已死”,是对个体自我的极力张扬,他的“超人哲学”本身就是以文艺精英的姿态而出现的。海德格尔的通过对“荒原”的批判意图建立人类“诗意栖居”的场所,更是精英的文艺理想。直到现在福柯对“巅峰时代”人的工具理性的强力批判,试图重建人类自由的精神世界,都是精英意识的美学映照。在审美主义看来,存在之思和精神救赎是人类面对理性社会的时代反思。然而,审美主义所强调的审美的感性存在是直面现世的人的存在的,它的拯救对象是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这就决定审美主义是具有人民性的,以精英意识引领社会的感性审美的构建应该是审美主义的要旨,不过审美主义的精英姿态在当代文艺实践中只是简单的表现出了文艺引领的功用,而没有表现出它的普世功用,这在歌剧的创制上表现也非常突出。
中国的歌剧在工具理性时期表现出了明显的人民性特征,像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等,歌剧是大众获取解放理念和构建美好生活理想的重要手段,在审美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的当代,歌剧往往承载了“诗意”的符号功能,它成为艺术家展现自我艺术理念的重要载体,歌剧本身不再是大众娱乐的工具,而是“小众”的孤芳自赏,这突出表现在歌剧题材对现实生活的有意疏远上,几大歌剧院以引进外国歌剧或者改编已有的文学题材为主要创作思路,而对鲜活的百姓生活关注甚少,这种脱离生活现实的“孤芳自赏”,必然造成歌剧的精英引领和人民性之间的逐渐分离。
结语
审美主义的精神价值正在于它的存在之思和精神救赎,它融合了情感体验和崇高的价值追求,然而时代的冲突必然折射在各种美学思潮的理论分析上,审美主义也不例外,它的“非功利性”的“功利性”追求,虚幻的审美乌托邦的美学建构,在当代话语语境当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思想悖论。作为深受审美主义影响的中国当代原创歌剧,在将西方文化理念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在努力追求歌剧的审美特征,但是在泛审美化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是消费主义的蔓延,让中国原创歌剧在审美和工具性、精英意识与人民性之间表现出了典型的悖论特质,而这既是当代美学思潮的艺术反映,也是当代艺术生态的必然表现。
〔1〕叶世祥.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四个层面[J].文艺理论研究,2011(04);
〔2〕(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50;
〔3〕(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9;
〔4〕张辉.尼采审美主义与现代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1999(2);
〔5〕孟远.六十年来歌剧《白毛女》评价模式的变迁[J].河北学刊,2005(2);
〔6〕曹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第七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专家访谈录[J].艺术教育,2012 (07);
〔7〕杨霓.现代审美主义救赎刍议[J].学术探索,2009(02);
〔8〕黄长虹.歌剧艺术的审美特征[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9〕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25;
〔10〕陆扬.论日常生活“审美化”[J].理论与现代化,2004(03);
〔11〕景作人.强调歌剧本土化——试论目前中国原创歌剧存在的几个问题[J].歌剧,2005(01)。
陈维薇(1977--),女,中级职称,现任星海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