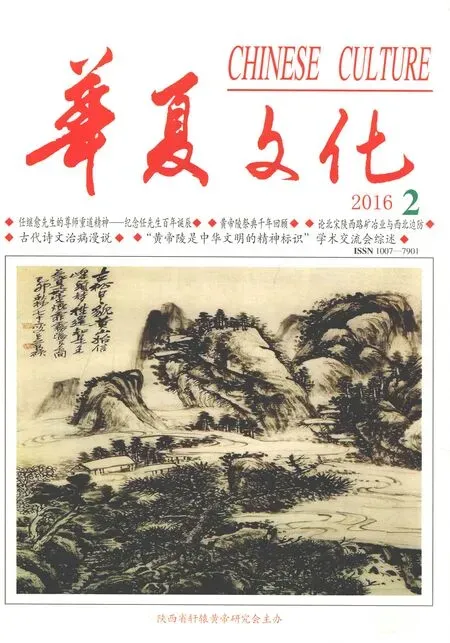贾谊与黄帝文化
□ 刘宝才
贾谊与黄帝文化
□ 刘宝才
一、贾谊与《新书》
贾谊,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年)生于河南郡雒阳(今河南洛阳)。十八岁时以文才闻名,被郡守吴公召到衙门任职。文帝刘恒即位初,吴公升任廷尉,便向文帝推荐贾谊,称赞他年轻有才,精通诸子百家。文帝征召贾谊来到朝廷,给他一个博士职位。当时贾谊二十出头,在同僚中最年轻。每遇文帝有事咨询,同僚回答不上的时候,贾谊就站出来回答,大家都很佩服。文帝喜欢贾谊,破格提拔他,一年内升任太中大夫。贾谊对修订历法、制定法令、改革制度、振兴礼乐提出一系列建议,还提出“诸侯就国”的主张。文帝打算再提升贾谊,给他公卿的职位,由于大臣周勃、灌婴等反对没有实现,便派他去做了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几年后,文帝又召回贾谊,接见长谈以后,感觉相隔几年,贾谊的学问见识更加令人佩服了,不久就让他做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胜的太傅。不幸的是,后来梁怀王刘胜骑马时掉下来摔死了。贾谊感到,作为太傅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哭泣了一年多,也死去了。贾谊的卒年是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十三岁。贾谊出仕从政,只有十多年时间,先后担任的博士、太中大夫、太傅都属于文化职官,或备咨询、掌论议,或为教师性质,始终没有完全脱离书生的身份。
西汉时已有贾谊的文集。西汉末年刘向看到的贾谊文集有72篇,刘向删定为58篇,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贾谊》一书。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称,《汉书·艺文志》的《贾谊》一书流传到南宋基本完整,只有《问孝》和《礼容语(上)》两篇的正文失传,篇题与正文倶存的56篇。今见《新书》与南宋时相同,是贾谊的著作没有疑问。今见《新书》十卷56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事势”,讲政事与形势,包括卷一至卷四,共32篇,都是呈送文帝的奏章。第二部分“连语”,引述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或人物故事,用来讽喻现实,包括卷五至卷八,共18篇。第三部分“杂事”,包括卷九和卷十,共8篇。“连语”“杂事”各篇,或解释经传古义,或记述礼仪程序,可能是贾谊任太傅时所用的讲义和笔记。
《汉书·艺文志》将贾谊的《新书》列入儒家类。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崇儒的班固将《新书》列入儒家,主观上是一种抬举,客观上不符合实际。贾谊活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是儒家,恐怕他本人不高兴。后代正统儒家人物也不接纳贾谊,朱熹说:贾谊的书内容“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历代二》)。“驳杂”自然是贬抑。该不该贬抑是另一回事,但朱熹认为贾谊不是儒家,我以为是对的。
二、《新书》述黄帝
观察《新书》中引述的黄帝的言论、身世和事迹,是了解贾谊与黄帝文化的关系的直接途径。
贾谊《新书》中有两处引述黄帝的言论,还有两处引述黄帝的身世和事迹。摘录如下:
一,《新书·宗首》:“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
二,《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三,《新书·制不定》:“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四,《新书·修政语(上)》:“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
第一条引文可能引自《六韬》。《六韬》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熭,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意思是:中午阳光正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曝晒,刀子握在手里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宰割,比喻说明做事要不失时机。以下的“执斧必伐”以及从反面作的更多比喻,都是同样的意思。学界对《六韬》的真伪性一直看法不一,成书时代也有多种说法。上个世纪70年代初,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残简,河北定县汉墓出土《太公》残简,证明《六韬》并非伪书,多数人认定它是战国时人的作品。
第二条转述黄帝的身世和事迹,来源比较复杂。先秦与秦汉之间的多种文献中有关于黄帝的身世和生平的记载,《新书·益壤》的这一条是一个综合转述,包含作者自己的理解。这一条中说黄帝是炎帝之兄,当由《国语》所说“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推测而来。说黄帝伐炎帝的原因是“炎帝无道”,则与《国语》所说的是由于二帝“异德之故”不同,而与司马迁说的是由于炎帝“侵陵诸侯”(《史记·五帝本纪》)相通。贾谊和司马迁的说法必有来源,这个来源我们现在找不到了。说黄帝伐炎帝之战发生在涿鹿之野,与其他记载不同。从《逸周书》到《大戴礼记》以及《史记》、《汉书》,一致说黄帝伐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发生于涿鹿之野的战争是黄帝与蚩尤之战。说黄帝伐炎帝战于涿鹿之野,可能是误记。《史记正义》以为阪泉即古涿鹿,也可备为一说。说黄帝伐炎帝之战血流漂杵,与《大戴礼记》所说“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都是言战争激烈,只是用语不同而已。
第三条也是转述黄帝的身世和事迹,内容与第二条大体相同。唯炎帝黄帝“各有天下之半”一说,为第二条所无。《国语》记载炎帝“成于姜水”、黄帝“成于姬水”。“各有天下之半”的说法也可能是由《国语》的这个记载演化来的。
第四条引文出处不明。《修政语》上、下篇,列举五帝及三代著名帝王有关治国之道的言论,并进行解说。本条列于上篇之首,以水为喻说明治国之道。《老子》尚水,言“上善若水”,多以水喻道。就表达方式而言,本条与《老子》一致。就表达的内容而言,本条与《老子》有不同。《老子》以水喻道,表达的内容是处下不争,柔弱胜刚强。本条黄帝之言以水喻道,表达的内容是涌流不息、追求不止的自强精神。
从《新书》引述的黄帝身世、事迹和言论中,我们看到贾谊的政治主张与黄帝文化有密切关系,黄帝文化为他的政治主张提供了依据。贾谊主张,君主要考虑安定天下的大事,不可追求虚名,不可拘泥于细微末节。主张君主做事要当机立断,不可优柔寡断贻误时机。主张君主治理天下要践行诚信与仁义,要持之以恒。这些都是黄帝文化的精神。
三、《新书》的黄老色彩
黄老这个名称见于《史记》的《孝武本纪》和《老子韩非列傳》。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以黄老名派,表明这个学派从老子出发又有发展。这个学派的形成不早于战国时代,在战国秦汉间影响很大,西汉初年成为支配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派别。诸子多数学派都与黄帝文化有关,但在学派名称上标出黄帝名号的只有黄老学派一家,表明这个派别与黄帝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观察《新书》的黄老色彩,也可以成为了解贾谊与黄帝文化关系的途径。
《论六家之要指》中说黄老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吸取了各家的长处。文中还指出了各家的长处所在,认为阴阳家的长处是研究阴阳运行,儒家的长处是列举“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墨家的长处是提倡“强本节用”,法家的长处是辨正君臣上下的名分,名家的长处是“正名实”。黄老道家吸取各家的长处,表现出综合诸子学术思想的意向。《新书》正是具有这样的倾向。有学者研究了《新书》以后,得出结论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六类学术著作,都在贾谊读书的范围之内。”(跃进:《贾谊所见书蠡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这个结论与当年吴公赞扬贾谊精通诸子百家是一致的。
《新书》广泛引述诸子著作。对道家著作有直接引述,如:
《新书·审微》引《老子》64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新书·君道》引《文子·上德》:“大道亶亶(坦坦),其去身不远。”
《新书·审微》引《管子·牧民》:“管仲曰:‘备患于未形。’”。
《新书·俗激》引《管子·牧民》:“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新书·无蓄》引《管子·牧民》、《撰度》:“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老子》、《文子》、《管子》,《汉书·艺文志》都列入道家,班固的自注还称文子系“老子弟子”。对儒家著作也有直接引述,如:
《新书·等齐》引《礼记·缁衣》:“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
《新书·审微》引《孔子家语·正论解》中孔子对于卫君允许叔孙于奚僭用君主礼乐的评论:“惜乎!不如多与之邑。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与之邑。”
《新书·保傅》引《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对其他各家的思想也有吸取,表现出既尊重又有分辨的态度。于墨家,《新书》有“仲尼、墨翟之贤”(《新书·过秦》)之语,又有“墨子见衢路而哭”(《新书·审微》)之句。于法家,《新书》赞扬商鞅“立法度,务耕织”(《新书·时变》),批评其“违礼仪、弃伦理”(同上),指出其迷信暴力、忽视礼仪伦理在秦统一后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恶劣。于阴阳家,称颂邹衍为贤士,认为邹衍入燕对于燕国安全昌盛、战胜齐国有决定性作用(见《新书·胎教》)。我们推测,贾谊还接触过马王堆汉墓中的简帛文书,包括被定为《黄帝四经》的黄老之学的典籍。这批简帛文书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墓主是汉初长沙王相利苍的儿子轶侯利豨。轶侯利豨与贾谊同卒于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卒年也是三十余岁,两人是年龄相当的同辈。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的几年里,与轶侯利豨一定会有交往,完全有机会阅读轶侯利豨的藏书。
黄老道家是从老子思想出发兼取综合诸子的,老子思想在黄老学术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论六家之要指》指出,黄老道家学术的宗旨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就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从事物本性为办事的实际原则。《新书》的治国之道与黄老道家的宗旨契合不违,在根本上体现出《新书》的黄老色彩。《新书·道术》说:治国之道,“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换个说法即,虚是治国之道的根本,术是治国之道的具体办法。接着解释说,以虚为本,就会像铜镜那样明亮,能够照见美丑;就会像秤那样无私,能够称出轻重。君主清虚宁静,发生了事端就公正地去协调,事物有好的开端就顺势引导它发展,养育事物成长完成。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君主的好名声就会四方传扬。又解释说,以术为末就是君主要躬行仁、义、礼、信,要维护社会公正和法律制度,要举用贤才、教化人民、广泛听取意见等等。依照贾谊如此解释,虚与术都属于道,它们是治国之道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两个部分的地位不同,虚为本、术为末,虚决定术、术反映虚。但强调虚具有决定作用,非谓虚可以代替术、本可以代替末;认为术反映虚指出术是建立在虚的基础上的,术又是虚的体现,非谓术可有可无,末无关紧要。贾谊《新书》这样讲治国之道,与黄老道家一致,与老子有同有不同,与儒家大不相同。
四、贾生未为不遇
司马迁写《史记》,将贾谊与屈原的传记合为一篇,题为《屈原贾生列传》。生,书生也,一般指年轻的读书人,有纯洁、正直、满怀理想的意蕴。司马迁称呼贾谊为书生,亲切、怜惜,充满暖意。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咏史诗也以《贾生》为题,诗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本人仕途困顿,是个终生不得意的书生。这首诗为贾谊叹息,与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有关,很可以理解。但以为文帝不识人才、不顾苍生、非常迷信鬼神,那是错怪人了。接见贾谊的时候,文帝刚才在“受釐”仪式上接受过鬼神的祝福,心中萦绕着鬼神之事的感触,见到贾谊便谈起鬼神来,未必能够说明文帝特别迷信鬼神。贾谊面对文帝是怎样谈论鬼神的,没有任何记载,但可以作个推测。贾谊最初曾寄身吴公门下,吴公曾向李斯学习,而李斯又是荀子的学生。贾谊读过荀子的书是可能的,他的鬼神观念也许与荀子一致,认为能够赐福降灾的鬼神并不存在,统治者祭祀鬼神只是为了文饰政治。谈话过后,文帝赞扬贾谊见解高明,原因何在?由此也可窥知一二。文帝临终遗诏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史记·孝文本纪》)他反对厚葬久服的陋俗,要求为他陪葬的器具只用瓦器,为他举办的丧葬仪式尽量从简。文帝与求神求仙希冀侥幸不死的秦始皇、汉武帝不同,不是那么迷信鬼神的人。
很明显,文帝是赏识贾谊的。二十来岁的贾谊应召来到长安,文帝立即任用,又破格提拔。文帝派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不能说明文帝不再信任贾谊,也不像是单纯的贬谪,似乎有更多考虑。长沙国地处南方前沿,地理位置很重要。长沙国是最忠诚于中央朝廷的封国。刘邦分封的异姓王国中,只有长沙国一直忠于朝廷,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传国五世,最后一代长沙王无子而绝。让贾谊去担任长沙王太傅,暂时远离周勃、灌婴一班大臣的攻击,是一个既重要也安全的安排。贾谊去了长沙以后,文帝并没有忘掉他。几年后将他从长沙召回,接见的时候一直交谈到深夜。李商隐的诗写的就是这次接见。不久,文帝又让贾谊作了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胜的太傅,还多次就朝政征询贾谊的意见。贾谊英年早逝,班固为之悲痛叹息,同时指出贾谊的建议文帝多已实行,贾谊“未为不遇也”(《汉书·贾谊传》)。班固的这个评论是公允的。
那么,在削藩问题上,为什么文帝不采纳贾谊的建议?为什么“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应该加以讨论。
汉初,分封与郡县并行,封国的疆域加起来比郡县的疆域加起来大得多。分封本来是为了护卫中央朝廷,强大的诸侯王国却不断出现分裂倾向,如何处理诸侯王国问题成为中央朝廷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刘邦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韩王韩信、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梁王彭越、燕王卢绾。由于中央集权与异姓诸侯王国之间矛盾很快激化,刘邦先后以谋反的罪名将七个异姓诸侯王国废掉了。为了控制局势,刘邦末年又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其中七个是他的儿子:齐王刘肥,赵王刘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还有两个:楚王刘交,是他的弟弟;吴王刘濞,是他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同姓王国建立起来以后,与中央朝廷的矛盾也随之产生,发展到对抗、反叛。直到武帝时,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贾谊当时,同姓王国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文帝三年(前177年),文帝兄刘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文帝六年(前174年),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长作乱。刘邦兄子吴王刘濞长期称病不朝,已经有人告发他在图谋反叛。贾谊从严峻事实看到,只要有力量,同姓诸侯王也会反叛,同姓诸侯王也是分裂国家的势力,发展趋势是“大抵强者先反”(《新书· 藩强》)。他建议文帝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同上)的策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贾谊看到的事实,文帝当然也会看到;贾谊指出的趋势,文帝必然也认识得到;贾谊建议削藩符合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文帝更不会误解。但是文帝不采纳贾谊的建议,不愿意主动出手,宁愿等到不得已的时候再采取行动,这也是有原因的。文帝只大贾谊一岁,当时也是年轻人,而身世、性格与贾谊不同。文帝是刘邦的庶子,为妃子薄姬所生,八岁立为代王。吕后去世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要立代王刘恒为皇帝,派人到代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迎接,他当时的反应充分表现出行事谨慎的性格。又是反复咨询群臣,又是占卜探测天意,又是派舅父薄昭去会见周勃侦察虚实,觉得万全无虑的时候才决意前往长安。行至高陵又休止不进,派近臣先入长安观察情势,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告才进入长安。即位后立太子一事,文帝又表现出另一个样子的谨慎。有司请立太子,文帝先说天下的事情还没有办好,不要先考虑立太子吧。后来又说,楚王刘交是自己的叔父,吴王刘濞是自己的哥哥,淮南王刘长是自己的弟弟,还有其他诸侯及宗室成员,都可以继承皇位,不一定要立太子吧。这些当然只是做个姿态,最后还是立了他的长子刘启为太子。但这也说明,以庶子和诸侯王之一的身份立为皇帝的文帝,并非一个强势的皇帝,大事总要顾虑皇室亲贵。削藩是对皇室亲贵开刀,他必须慎之又慎。同时,文帝还要顾及陈平、周勃等把他扶上皇位的资深大臣的态度。文帝不会不知道吕后时的旧事。当年吕后打算立诸吕为王,先问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说:高帝和大臣们立下誓约,非刘氏子弟不可称王。又问陈平和周勃的意见,他们却说,太后既然代行天子之职,封吕氏诸兄弟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过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逢迎吕后,他们回答说:“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汉书·王陵传》)这话意味深长。吕后死后,陈平、周勃果然除掉了诸吕,证明这些老臣的谋略和忠诚无可怀疑。他们不支持年轻的贾谊,文帝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晁错和主父偃是另外两位力主削藩的历史人物,可以作为评论贾谊的参照。
晁错,晚贾谊一年出生,景帝时官升御史大夫。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削藩策》,决定削夺吴、楚、赵诸封国的封地。事情的发展却有曲折:早已图谋不轨的吴王刘濞利用机会,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合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发动了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袁盎秘告景帝,主张杀掉晁错求得吴楚七国退兵——丞相陶青等联名弹劾晁错,说他“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景帝腰斩晁错于长安东市,时年四十六岁——气焰正盛的叛军拒绝退兵——景帝武力平定叛乱,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或自杀或被处死。最后,叛乱是平定了,晁错却死于他忠诚效力的景帝的刀下。这是贾谊死后十四年发生的事情。
主父偃,早年游说齐、赵、燕北、中山不遂。元光元年(前134年)上书武帝得到赏识,官至中大夫。后来建议武帝,令诸侯王施恩分封子弟为列侯,以削弱诸侯王国。武帝采纳他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于是诸侯王的支庶多受封为列侯,瓜分了王国的土地。而列侯隶属于郡,各个王国只能管辖被瓜分后剩余的土地,实力大为削弱,对中央朝廷不再构成威胁。这是贾谊死后三十四年发生的事情。主父偃得势以后骄奢淫逸,疯狂敛财。有人说他太横行霸道,他却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已经四十余年,困厄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大丈夫活着不能列五鼎而食,宁愿受五鼎烹煮而死。我已经到了日暮途远的岁数,就是要横行逆施。”最终,在官场倾轧中,有人告发了他的受贿行为,死在武帝刀下,被诛灭全族。
主父偃的下场大半是自作自受。晁错死于景帝刀下,则当了一只未能替罪的替罪羊。文帝谨慎的避免陷入没有必胜把握的对抗,也就避免了做出屠杀功臣的蠢事。朱熹说:“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历代二》)贾谊遇到懂事的文帝,算是幸运了,何必曰不遇呢!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