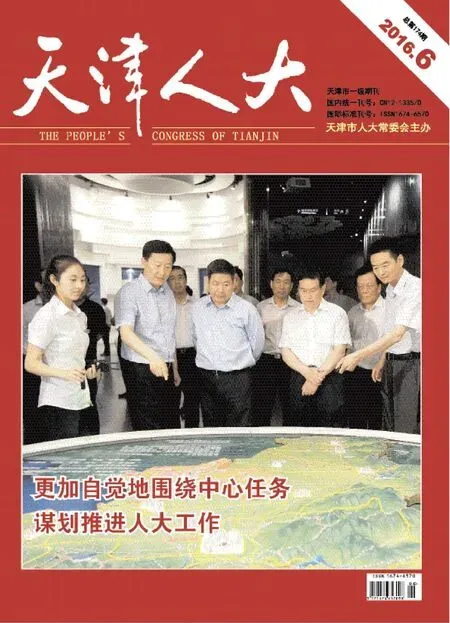七十二沽猜想
杨大辛
七十二沽猜想
杨大辛
天津地处滨海平原,河道纵横,洼淀遍布,素有“天津七十二沽”之说。人云亦云,已成定论,如果较起真来,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清人张焘著《津门杂记》(刊行于光绪十年即1884年),内有《七十二沽说》一节。文字不多,照录如下:
天津有七十二沽之说,实只二十一沽。曰:丁字沽、西沽、东沽、三汊沽、小直沽、大直沽、贾家沽、邢家沽、咸水沽、葛沽、塘沽、草头沽、桃源沽、盘沽、四里沽、邓善沽、郝家沽、东泥沽、中泥沽、西泥沽、大沽。此念一沽从西潞河名也。余则在宝坻、宁河两县境内。
后人探讨“天津七十二沽”,多以此说为圭臬。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行的《重修天津府志》亦从张说,并具体列出在宝坻的有二十九沽,在宁河的有二十二沽。21+29+22=72,总算把数凑齐了。但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疑点:一是既然天津“实只二十一沽”,不及七十二的三分之一,何不如实地称“天津二十一沽”?二是将宝坻、宁河扩大进来凑数,依据何在?如果说历史上海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曾隶属宁河,那么将宝坻扩大进来又如何解释?再说海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隶属静海,为何排除在外?
这个“天津加宝坻加宁河”的计算公式,不能令人信服。如前清举人徐士銮在《敬乡笔述》一书中就提出质疑:“未叙出见自何书,考证者何人,实为憾事。”也有人为扩大考证线索,将天津周边地区带“沽”字的地名一一排列出来,涉及静海、武清、玉田、丰润各县,如1927年出版的《新天津指南》就列举天津周边地区的沽字地名百余个,越发算不清楚了。地方史学者陈铁卿就曾讥讽地说:“前人要把这数凑得不多不少,真是刻舟求剑。”看来这道“七十二沽猜想”的命题,是无法解开的了。
其实,不算也罢。盖七十二者,是个约数,言其多也。天津地势低洼,大小淀塘多不胜数,总得加以量化吧。十个八个太少,百八十个太多,优选七十二,恰到好处。为何这么讲?因为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数字观念。古代先贤习惯于以“三”代表多数,如“三缄其口”“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吾师”皆是。后来感到“三”字似乎不够夸张,于是就以“三”的倍数“九”来形容多数,如“九霄云外”“九天九地”“九死一生”;如果再夸张一些,翻一番是“十八”,如“十八般武器”“十八层地狱”;再翻下去变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计”“三十六行”;如果还要增大一倍就是“七十二”了,如“孙悟空七十二变”“孔夫子七十二大贤人”“济南七十二泉”“衡山七十二峰”……到此为止就不宜再翻下去,因为“一百四十四”不但读来绕嘴,似乎也有点荒诞不经。也许有人提出,梁山泊英雄不是“一百单八将”吗?须知这“一百零八”是由“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加在一起组成的;还有个“三百六十行”哩,那不正是七十二的五倍吗!因此,“天津七十二沽”这个提法,说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景色诱人,厚重而不孤零,奇异而不一般,何其妙哉!
还可以再谈一点:凡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讲述天津时很少使用“七十二沽”这个词语,而诗人雅士却偏爱这个数字,如什么“七十二沽花共水”“七十二沽春水活”“七十二沽秋风阔”“七十二沽月独明”等等吟咏诗句。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七十二沽”属于形象思维而并非逻辑概念;或者说,“七十二沽”的说法属于修辞学而不是一道数学题。(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