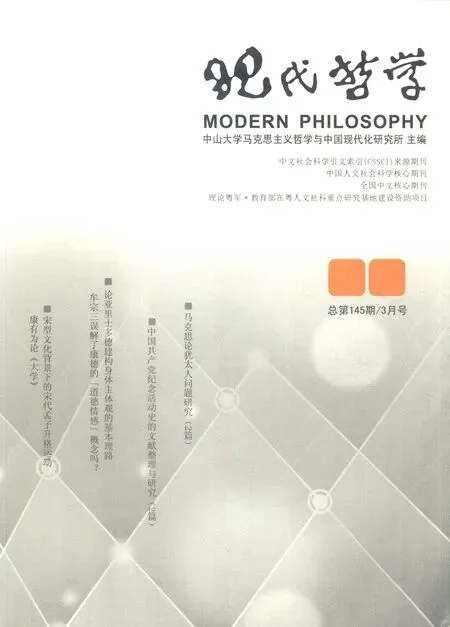自然与益生之间:道家道教生命态度比较的重要向度*
李友广
自然与益生之间:道家道教生命态度比较的重要向度*
李友广**
【摘要】道家倡自然,道教重益生。在生死立场与生命态度上,道家和道教之间发生重大转向与变化。它既与“道”在先秦诸子文化当中地位的下降有关,也与道教产生的思想资源之驳杂性密切相关;既是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人们应对和解决人与宇宙及社会关系的理论需要与精神诉求。
【关键词】道;自然;益生;生命态度
道家倡自然,道教重益生。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看,对于人的生命、生死所持的立场与态度,道家与道教之间确实发生重大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是本文着力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对道家和道教生命态度进行比较研究之前,我们先简单考察一下其对人的来源的看法。关于人的来源问题,《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皆根源于道,由道而生,“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第34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第51章)等等。既然道生万物,那么对于人而言最为合理的生存方式便是要效法道、合乎道,因而《老子》反复强调“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第16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在道家的哲学理论体系当中,“道”高于“天”,所以《老子》告诫人们不仅要效法地和天,最终还要效法道之自然。
在人的生命构成问题上,老子、庄子都认为人的生命形体是由气构成的*除了老庄,《管子》大量探讨了气(精气)与人之生死之间的关系,比如:“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枢言》)“凡物之精,此则为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内业》)。《老子》第42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知北游》更明确地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人的生命形体由气构成,人的生死便与气的存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人的生死本身就是自然一气的不同变化形态*除了老庄,《管子》四篇更将“道”与“气”等同起来,用“气”诠释“道”的生成(《内业》:“夫道者,所以充形也。”),“道”不只位阶下降,范围也缩小了(《心术上》:“道在天地之间也”“虚之与人也无间。”)。“道”由超越天地、高于天地、超现象,变成了天地间、现象世界的存在。详见陈丽桂:《近四十年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4页。。
既然作为有限性的存在,人是有生死的,而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性存在*《庄子·秋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那么,人想解决自身存在的种种有限性问题,就不得不在精神上试图超越“物”的层面,以与“道”合一,进而寻求超越生死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试图从道的无限性来加以超越及转化”*详见陈鼓应:《论道与物的关系问题(下)——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哲学动态》2005年第8期。。但是,作为有限性的存在,人是无法直接把握作为无限性存在的“道”的,必须经由中间环节和桥梁才能把与“道”合一变成可能,而这个中间环节和桥梁便是气。正因为道家道教多认为人是由道经气化而成的,所以他们在探讨养生和生死问题的时候往往与“气”结合起来言说。只是有所不同的是,道家更关注“道”及由“道”所显发的自然本真之样态,故其对人之生死的看法多立足于“道”,并以合乎“道”之自然本真样态的存在方式为人之本然合理存在方式。由于气是人生命形体的基本构成,较之“道”的形上性与超越性,气与人身之间的关系更为具体切实,故而道教虽然也尊崇“道”,但其在应对社会和解决个体生命问题的时候,往往将目光下移,多关注气之样态、功能与身体生命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对待个体生死问题的时候将道家的“自然”之立场与态度转向了“益生”。
一、道家、道教如何看待生死
关于人的生死问题,《老子》第55章有云:“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祥”指不祥、殃祸。意思是说,贪生纵欲就会遭殃,欲念主使精气就叫做逞强。事物过于壮盛就会变衰老,这就叫不合于“道”,不合乎常道就会很快死亡。于此,老子与“道”结合在一起来谈生死,他认为人要预防外界的各种伤害和免遭不幸就应该效法道,以合乎“道”之自然样态生活,否则就容易危害自身和他人的生存*《老子》第75章:“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顺此理路,《庄子》在以“道”的高度来审视人之生命与生存状态的同时,又非常关注人存在的有限性与悲剧性*《庄子·齐物论》:“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这里集中表达了人秉承天地之气形成形体后所带来的包括形骸衰竭、最终死亡等种种束缚、局限与悲剧性。,而且常常会将有限性的人投放到无限性的道和无穷尽的天地、时间之中*《庄子·盗跖》:“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庄子·则阳》: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这种做法突显了人的悲剧性和无可奈何性。由于人自身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在种种局限性当中最直观和最具体的是人处于变化之中,天地万物莫不变化:“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庄子·天地》)“万物皆化。”(《庄子·至乐》)在庄学一派看来,人的生死是天地变化的具体表现,终无所逃。,人们对于生死这一类问题是无法做到自我主宰的。对于这种不可更改的必然命运*《庄子·达生》:“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我们除了接受它别无选择。故而《庄子》为了化解或超越死亡的悲剧性,在对待和处理生命问题上持有自然式的立场,认为生命的生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认为人的生死是气聚散的结果,而气的聚散是自然的*《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气的聚和散并无好坏、高下之分,人的生与死自然并无质的差异*《庄子·大宗师》:“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至乐》:“死生为昼夜。”,因而人们不应该好生恶死,要安于命运的安排。正如《庄子·德充符》所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人世间总有诸多无可奈何之事,很少有人明知如此却仍能安于这种境遇,并视其为必然命运的安排,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根据庄子的思维理路,文本中的“德”显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德”,而是“玄德”*《老子》第10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庄子·天地》:“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承“道”而来,与“道”相合。当然,既然人本身存在着种种有限性,那么仅靠对生命的自然式理解来加以化解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这并不具有多少方法论意义。因而,在如何消解人生命的有限性对人存在价值所产生的冲击这一问题上,庄学一派最终不得不归之于道。他们发现,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道却是恒在的,人只要以合乎道的方式存在,便能超越生死的束缚进而获得内在的逍遥与自由,尽管这更多的是精神意义上的。至于怎么才能与道相合,庄子所谈论的“心斋”“坐忘”“吾丧我”等内容多少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尽管在具体如何去做上还是比较含混,这恐怕与“道”本身所具的抽象性、含混性有关。
后来的道教也意识到了这种悲剧性,所以除了使自己的养生修炼方法更为精致化以外,还融入了传统道德、儒家伦理和佛教教义以及事功等因素*“始创于东晋中期的新道派——上清派的成立和南、北天师道的改革,使道教从教义、修行道术到组织制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新问世的道经大量吸收佛教教义,如涅槃轮回、因果报应等等,加以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一部分。”参见周可真:《追求自然生命过程的正常进行——老庄生命哲学论要》,《学术界》2013年第1期。,以试图消解和克服人的这种有限性及所衍生的悲剧性。同时,道教还认为命运在我,道在体内,基于在社会面前的避害保全的目的,认为经由种种努力肉体可长生乃至成仙*《抱朴子·地真》:“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长生养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于勤,而终成于久视也。”,将庄子的内在式超越与解脱变成了对外在形体与生命无限性的执著追求,具有浓厚的功利性与世俗性。如果以庄子的理路来看,这无疑是将肉身形体置于社会笼牢乃至天地笼牢之内,加剧了人本身无法克服其有限性之悲剧性,无形中也消解了人的内在超越性和存在的哲学意味。由此看来,庄学所言“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庄子·庚桑楚》),可用于对道教汲汲于全生避害、长生成仙这类事情的评判。
二、道家道教:从自然顺生到养生益生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在这一历史阶段,天人关系是诸子从事学术思考的共同理论视域,再加上这一时期人文理性主义思潮的深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战争对人生命的危害,都让诸子们普遍关注与思考人在天地之间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性问题。从道家对“命”的理解来看,形体寿命、生死皆属命运的领域,是不可更改的。既然如此,那行走于人世间的人们其存在的合理性何在呢?老子是以对“道”的言说为起点的。《老子》第1章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道”为什么不可道?实际上,老子的“道”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让人难以充足把握,因为人的主观意志与知识智慧是有局限性的,以人的种种有限性自然难以把握“道”的无限性,或者说有限性的人是无法完全把握无限性的“道”的。
既然“道”是不可把握的,而道家又主张人的生命展开要合乎道,这不是矛盾吗?实际上,这确实在老庄那里体现了一定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实际上就是有限性的人与无限性的道及天地之间所彰显的矛盾,又突显了人的悲剧性和无可奈何性,这在庄子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既然是无可奈何的,那就不要过分作为,因为任凭你如何作为终究都是有限性、悲剧性的存在,只有“法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才能接近“道”甚至合乎“道”,只有合乎“道”了才能在某个层面上实现对人本身所具有的有限性和悲剧性的消解与超越。故而道家往往主张人们应以自然本真的态度去生活,换句话说,在道家眼中,抱持自然主义式的生命态度、人生态度才是最为合理的,所以《庄子·马蹄》云:“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当然,仅凭自然主义式的生命态度、人生态度还不足以应对人与道之间的这种矛盾性,所以《庄子》在强调“以天为宗”“以道为门”(《天下》)的同时,还强调内外的问题。对此, 《庄子·知北游》说:“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所谓“外化”,实际强调外在世界(包括天地)的变化是必然的,作为有限性的人只能随顺外界的这种必然性,“任何脱离和抗拒命运之必然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刘笑敢:《庄子人生哲学中的矛盾》,《文史哲》1985年第2期。。不过,光一味随顺必然性的命运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人的悲剧性反而更被突显。因而,庄子后学在《知北游》中对人的生命态度做了划分与区别性对待,故有了内外之别。他们强调在随顺命运的同时,还要内合于道之自然本真之特性,只有“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庄子·德充符》),才能不执著于生(因为“生”也是一种有情),才能“无情”,才能“常因顺着世俗以尽其天年”*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在对待生命和生死的态度上,道家因“自然”而强调“顺生”,道教则以“益生”的方式追求“长生”。两者之间为何会有这种变化呢?这应该从道教的兴起谈起。道教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其原因纷繁驳杂,并非一语可以道尽。在此,我们想说的是道教的兴起过程实际上就是道家的“道”地位下降、世俗性特征不断增强的过程*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先生将此称之为“‘道’的形而下化”。参见[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下)——以〈庄子〉为中心》,王启发、曹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道教是多神教,祭祀对象包括诸多鬼神精灵,此外,“它还吸收了中国古代人们所知道的种种礼俗方术,诸如祖先奉献牺牲,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禳灾避祸……它具有很强的世俗特征”*刘笑敢:《道教》,陈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页。。由此来看,道教所持“益生”的生命态度,无疑与其形成根源的驳杂性以及所具有的浓厚的世俗性特征是密切相关的,与道家的生命态度正好相反。道家是以合乎“道”、反向复道的方式来超越生死,故而认为人们没有必要追求长生。道家哲学的奠基者认为人不能也不应该在生死之间厚此薄彼,人应该超越生死的差别。与此相反,道教却把长生不死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视为其核心的原则,是一种悦生恶死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是对道的背离。正因为道教悦生恶死,具有浓厚的世俗性与功利性,所以导致了其强大的吸纳性和包容性,规定了其对君王的尊崇*《抱朴子·良规》:“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吸纳*《抱朴子·对俗》:“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抱朴子·微旨》:“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对医术修习的重视*《抱朴子·杂应》:“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以及对炼制丹药的迷恋*《抱朴子·金丹》:“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的丹药虽在特性上近于天地之久长(将人与天地类比,以天地之长久为依据来探讨人之长生问题,是道教的一贯做法。如《上清灵宝大法·序》说:“人禀中和之全气,故像天地之大体,及其气血运动,密契阴阳。”《钟吕传道集》说人“气液升降如天地之阴阳,肝肺传导若日月之往复”。),但作为气化形成之人体如何能化融此坚物呢?虽有种种炼药入体之法,但万物之性毕竟各有差异。故而由此来看,道家在延年长生之法的探索上仍显得不够精致自洽。。道教的世俗性与功利性,一方面决定了其对各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思想资源的充分汲取与吸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道教的理论水平与实践方法在根本上是受制于其世俗性与功利性的,因而其理论分析与形上建构并没有道家哲学那么突出,但道教将修道长生与积善事功密切联系起来,实则正体现了其欲弥合“道”本有的形上超越性与客观存在之社会政治之间的罅隙,故而这些人是“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在隐遁与现实中出入”*参见谢路军:《中国道教源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三、自然与益生之间的思想关联
从思维理路看,道家道教都从“道”和天地之长久看到人存在的有限性与困境,只不过在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与悲剧性上出现了较大差异。道家鼻祖老子认为人应该自然无为,尤其是他眼中的圣人更应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老子》第57章),“无为”“无执”“欲不欲”“学不学”(《老子》第64章)等等,以真正效法道和天地存在与变化的自然本真之状态。我们发现《老子》中“圣人”往往与“民”(有时候用“天下”)对举连言,非常具有“王”的色彩,而且在这种对比言说中更突显了圣人体道、践道的典范意义*《老子》中的圣人“是道之原则的体现者,可以为‘天下式’”。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可以说是天下万民的榜样,简直是“道”在人世间的化身。那么圣人践道何以可能呢?这是因为天地万物莫不由“道”而生、从“道”而出,故天下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重视“德”的*《老子》第51章:“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既然圣人有着“道”在人世间化身的一面,那他治理天下,往往是以合乎“道”的方式进行的,是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蒞天下”(《老子》第60章)。于此,老子以从上而下的视角推阐出“道”在人世间运转流行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从而告诉人们天下事物皆从“道”出,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应以“道”观之。不仅如此,老子还告诫我们,掌握事物和把握规律只是认知“道”的途径与手段,这并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还必须要回归和坚守万物的根本——“道”,从而就能终身没有危险。《老子》第52章云:“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同样,对于“道”和“天地”的无为,《庄子》给予充分关注。《至乐》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于此,庄子后学在强调道和天地无为的同时,还意在彰显万物的自然生成与变化过程,而在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过程中便处处透着“道”的精神与功用。以此知之,庄子后学在继承老子之“道”形上性与超越性的同时,还非常关注“道”与现实世界的结合问题,并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用“气”作为沟通两者的桥梁与纽带*《老子》虽三次出现“气”字(第10章有“专气致柔”,第42章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55章有“心使气曰强”等等),但主要指涉气或精气本身而言,尚看不出具有沟通“道”与现实世界的功能及意义。,从而在对“道”的认知和把握上便成为一种可能。可以说,在道家思想框架内虽然也有着强调养生、长寿的内容,但那也是在“道”的观照下展开的,因而道家对生死与生命的态度主要还是自然无为和顺生的,更何况道家所强调的养生、长寿都是以天道无为和因任自然为根本前提的。从思维理路上看,庄子后学对“道”之神秘性与宿命论成分所作的弱化处理,再加上又将“气”处理为连接“道”和现实世界的中介桥梁,这无疑为道家(主要指老庄之后的道家)持续而深入地探讨人如何在乱世中合理地生存与延长寿命做了学理上的准备,进而为道教对“道”所做的功利性、世俗性处理,为道教转向对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现实功用的浓厚关注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道家多强调自然、顺生不同,道教则往往执著于对生命形体的养护,并试图以把养护方法系统化、精致化的“益生”方式来实现肉体的长生不死,进而以之来化解因人之有限性所产生的困顿与悲剧性。在对待生命态度上,道家和道教之间产生这么大变化,原因何在?
在此,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就老子所开创的道论思想体系而言,“道”在道家、道教那里,本身就不同程度地含有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化生、生成的动力和根据*“道生万物之后,又内在于万物,成为万物各自的本性(道分化于万物即为‘德’)。”参见周耿:《“道生、物形”论:先秦道家万物生成论的基本模式及其理论意义》,《“黄老道家研究的新拓展”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及哲学院主办,2015年11月14—15日,第279页。;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等义项与内容。因而,道家强调自然、顺生,道教强调养生、益生,本身就包含在“道”所蕴含的不同义项当中,是符合“道”之外延的。所以道家多强调“益生曰祥”(《老子》第55章*“‘祥’,古时用作吉祥,有时用作妖祥,这里是指的灾殃、妖孽。《庄子·庚桑楚》:‘孽孤为之祥’,《左传》昭公十八年:‘将有大祥’,‘祥’字都是指的灾祸。”参见任继愈:《老子绎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脚注。另参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庄子·德充符》),“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而道教则悦生惧死,强调生对于作为类概念的人的重要性,故而衍生了一系列与行善、积福、炼形、长生等相关的重生理念与养生文化。
其次,汉代道家道教对“道”所做的“术化”处理,与这一历史时期尚用崇功社会风气密切相关。“汉人治学,经世企图强烈,闳博而大气,儒道皆然。汉代思想家重视对实际政治与人生事务之讨论而不尚玄虚。”*陈丽桂:《汉代道家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1页。这种社会风气进而影响到这一历史阶段的理论导向与治学风气,因而汉代道家道教崇尚“道”用,以术释道,是社会历史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具体反映。可以说,汉代道家道教注重“道”用,自然包含像《老子想尔注》那样将道与益生、长生联系起来的理论向度与现实需求。《想尔注》注解《老子》,往往有“行道致生”“行道者生”“能致长生”的话语。不仅如此,《想尔注》甚至还视“生”为“道”之别体,彰显了道教在东汉时期对长生的重视而将其抬高到了与“道”几无差别的地步。
最后,道家道教对于生死、生命态度发生的重大转向,还与道教本身成立之初的复杂情形以及实践形式大有关联。关于道教的产生情形和实践形式,“实与老庄之说并无太多的本质上的直接关联,而毋宁是作为思想形态的黄老之学、作为信仰形式的万物有灵、作为诠释模型的阴阳——五行以及作为实践方式的秦汉方术诸方面之协力互动而产生的一种结果;这一结果在原因上的复杂性同时即决定了其可能的理论诠释空间的广阔性”*董平:《庄子与葛洪——论道家生命哲学向宗教信仰的转变》,《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道教之所以能够在生命态度上发生如此大的转向,实与道教产生过程的复杂性以及道教实践方法的多元性密切相关。理论诠释空间的广阔性,自然就蕴含着学术理路发生转向的可能性。因而,在道家道教之间生死和生命态度上发生的这种重大转向与变化,既是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人们在应对和解决人与宇宙及社会关系的理论需要与精神诉求。
(责任编辑杨海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5XZX006)、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C009)、陕西省教育厅2015年重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5JZ0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友广,山东莒县人,(西安710069)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1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