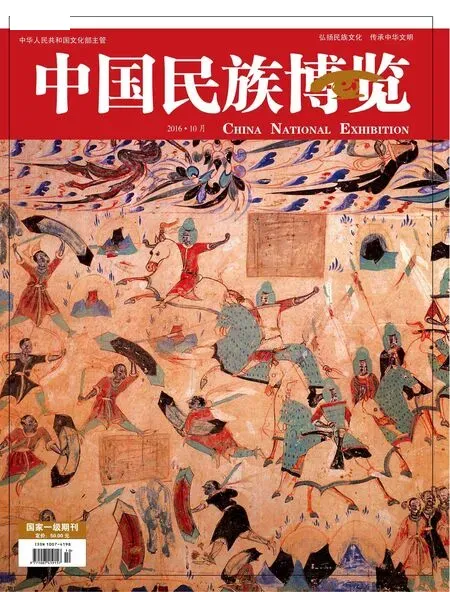略论布罗茨基的诗歌美学
陈子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略论布罗茨基的诗歌美学
陈子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20世纪最优秀的俄语诗人,也是一位世界性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美学涉及文化、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广泛而深刻。本文通过对布罗茨基诗学三个核心观点的分析,即“语言即存在”、“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来揭示其美学思想的宗教情怀和审美乌托邦气质。
约瑟夫·布罗茨基;诗歌美学;同义反复
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文坛一个传奇般的独异存在。他1940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15岁时由于身为犹太人而感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主动退学,步入社会后做过锅炉工、太平间看守、地质勘探队员等各种工作。24岁时,由于热爱文学、写诗、没有固定工作而被前苏联当局以“不劳而获罪”(寄生虫罪)判处流放北疆五年,后来在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著名前辈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营救下提前获释。1972年,他被前苏联当局强行驱逐出境,辗转欧洲,流亡美国。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一边勤奋写作,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教授诗歌和文学课程。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诺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1991年当选美国“桂冠诗人”。1996年由于心脏病突发,逝世于纽约。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深入研究并主动继承了俄罗斯黄金时代以来、尤其是白银时代的诗歌传统。此外,作为一名世界诗人,布罗茨基还从古希腊、欧美现代派、尤其是英国玄言派吸取营养,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美学特质。诺贝尔授奖词这样指出:“对他来说,俄语和英语是观察世界的两种方式。掌握了这两种语言,就像是坐在存在主义的山巅上,可以静观两侧的山坡,俯视人类发展的两种倾向。东西方兼容的背景,为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题材和非常多的观察方法。这一背景与他对历史文化透彻的领悟力相结合,孕育出了开阔的历史想象力。”
布罗茨基诗学享誉世界,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也有过不小的影响。自他获诺奖至今,国内不断有人对他进行评论或引述。但是限于翻译不足,汉语诗歌界对布罗茨基的了解还只能算散金碎玉,难以形成整体观照。直到最近两年,得益于他最重要的两部散文集《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的中译出版,我们才得以从中窥见布罗茨基诗学观的基本轮廓。本文试图对其诗学的三个核心进行分析,以揭示其诗学的基本特点和独特气质,也算作对布罗茨基逝世20周年的一份小小的纪念。
一、语言即存在
布罗茨基对语言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他说语言就是缪斯的声音。缪斯是不能被触摸的,因为她是众神中的一员。凡人只能通过聆听缪斯的声音来和她交流,缪斯向凡人显现自己的惟一的途径就是向这位通常是诗人的凡人来口授诗行,因为非诗人是没有资格聆听缪斯的。而诗人将听到的语言纪录下来,就是诗歌。在布罗茨基这里,语言显然是充满神性的形而上的事物,人类只有作为语言的崇拜者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在布罗茨基笔下,缪斯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实际上就是“嫁了人的语言”。在这里,似乎缪斯和语言是同一的,“正是她使得诗人痴狂地一心一意,将他的爱情变成了她的独白的等价物,”而诗人则必须永远保持对语言的绝对忠诚。有时人们容易将情人误认为缪斯,因为他们在特定时刻会给诗人带来灵感,从而让诗人创作出诗歌。然而情人是短暂的,缪斯则是不朽的。即使诗人离去,缪斯仍然会存在,她会在其她的崇拜者中寻找代言人。换句话说,缪斯会永远徘徊在语言的周围,或者作为语言本身而永恒存在……显然,这是一种充满决断性的尼采式的语言至上论,不同于语言学家精致繁复的逻辑论证,它完全来自于布罗茨基强烈的个人情感和独特经验。是纯直觉式的诗意表达,其合理性取决于受众心灵深处诗意的浓度和情感的强度。
流放让诗人对语言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和领悟。在流放期间,语言是惟一可倾述的对象,是惟一可靠的朋友,是心灵得到短暂安慰的惟一手段。投身于语言,就可以抵御全世界的荒芜。渴望拥抱语言,或是被语言占有,这正是诗人的命运。流放加深了诗人和语言的关系,也拓展了诗人和世界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布罗茨基后来回忆说,流放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而离开自己的祖国、流亡西方,对布罗茨基来说,则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对于一个视语言为生命的诗人而言,语言上的阻隔显然比地理上的放逐要严重得多。普通的肉体可以在另一个空间存活,诗歌的心灵则必须呼吸母语才能跳动。杀死普通人的方法是肉体消灭,折磨诗人的手段则莫过于让他丧失语言。布罗茨基的顽强和深刻在于,他非但没有因之而受损,反而通过自己巨大的心灵力量,将苦难转化成了难得的思想经验。他“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语言即存在,天才的布罗茨基打响了母语保护战。他意识到保护母语就是保存生命,而保存母语的最佳方式就是全力以赴地退回到母语的“密封舱”之中。像叶芝的一首诗所说的:“在没有梯子的地方,人要做自己的梯子。”在远离母语的地方,要让自己成为母语。布罗茨基成功了,他成为了20世纪末最优秀的俄语诗人,并被称为“当代普希金”。
二、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
在语言崇拜的基础上,布罗茨基还是一个“诗歌原教旨主义者”,他对诗歌进行了无尽地赞美,认为诗歌“乃是语言否定自己的质量和引力定律”,即语言克服了自身的缺陷,而做出的向上的追求。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但惟一能战胜语言的,就是诗歌,尽管诗歌以语言为基础,寄身于语言之内,但布罗茨基不满足于此,他认为诗歌是语言的加速器,是升华过的语言,因而是语言的极致和最高形式。
布罗茨基认为艺术就其天性和本质而言,是有等级划分的。相较于同样以语言为基础的散文艺术,布罗茨基认为诗歌远远高于散文。他认为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诗人能写散文,而散文作家却未必能写诗。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诗人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他认为诗歌是充满想象的,是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是通向想象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位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他认为诗歌由于其结构上的简洁、节约,语汇的精确、速度和密度,能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快速、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一部冗长的散文往往更容易使人萌生退意。另外,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的“同义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事实上,布罗茨基在流亡美国后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散文便于传播和阅读,对他在西方的影响力比诗歌贡献更大,但布罗茨基始终视诗人为自己的第一身份,贬低散文和其他语言形式,极力地推崇诗歌。
布罗茨基是一位修辞高手,他对诗歌进行了很多风格化的奇特比喻。他说诗歌是灵魂的导师,可以带领诗人抵达从未抵达过的地方。诗的写作是一种“死亡练习”,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感受能力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而一个处于对语言这种依赖状态的人就是诗人。布罗茨基认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翻译,是心灵被用语言翻译出来的一个方面。与其说诗歌是艺术的一种形式,不如说艺术是诗歌常常借用的一种形式。在本质上,诗歌是心灵观念的表达,由于心灵具有奇妙的合成功能,除了诗歌能将之翻译出来,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表达人的内心。他说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而是人类物种和遗传学的目的,是人类语言和进化的灯塔。他还说诗歌是时间的一种形式,诗歌如果不能让时间停止,那么至少可以让时间聚焦。写一首诗要耗费大量的生命能量,写完诗之后诗人会因此而老去一些,因此,诗歌是浓缩的时间,是时间转化成语言后的另一种存在,是通过语言对时间的重构。诗人的肉身是短暂的,但诗歌的生命是无限的。诗歌像一个时间的容器,超出时间,存在于时间之外,跨越时空,战胜虚无,从而进入了永恒。
显然,对爱诗如命的布罗茨基来说,诗歌不但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而且超出了语言和艺术的范畴,是一种最高的形而上的存在形式,具有马修·阿诺德所说的“诗歌拯救我们”的神圣性和宗教感。
三、美学是伦理学之母
在肯定了语言和诗歌的本体论地位之后,布罗茨基强调了诗歌、艺术、美学对人生和现实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艺术会激起人的独特性、个性,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而个性就是生命最高的追求,是人性伦理的首要目标。个性就是避免“同义反复”,就是让每个人真实彻底地拥有自我。他说“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他认为不是艺术在模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模仿艺术,因为艺术自身便构成一种更真实、更理想、更完美的现实。在布罗茨基看来,艺术毫无疑问是先于伦理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德性圆满的存在,其内在即是一种天然的善,因而是现实伦理的来源和摹仿的对象。他说诗人全都在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而字典中的语言就是生活对人的所言,它的功能就是去拯救下一个人,拯救新来者,使他不再落入旧的陷阱。让他弄清生活的含义,拥有更多心灵的自由。他认为美学对人具有解放的功能,因为阅读诗歌或写作诗歌,能使人远离俗套,远离平庸,远离恶。因此,诗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是社会所具有的惟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狗咬狗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词,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在诗人看来,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为一个人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人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趣味,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奴役的一种防护手段。而一个人的美学经验越丰富,他的趣味越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越准确,他也就越自由。布罗茨基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拯救世界”的看法,尽管他悲观地指出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他相信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
布罗茨基经历过前苏联集权政治的迫害,特别理解艺术对社会道德和国家伦理的重要性。他说“文学对国家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与无限对暂时和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为止。”在诗人看来,国家伦理和国家美学永远是“昨天”,而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而且时常是指向“明天”。由于艺术自身的特质所决定,使其善于对过往命运进行总结,做出一种本质上全新的美学解答,因而艺术和美学时常走在时代的前面。如果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建立自身的伦理,那就需要向美学寻求答案。因为“除了艺术所勾勒出的未来,人类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未来,”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过去,首先就是政治的、警察方阵表演的过去。诗人相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而“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
布罗茨基认为艺术比任何信仰都要更古老和更普遍,尽管艺术与信仰结婚和生孩子——但它不与信仰一起消亡。“艺术的审判要比末日审判更苛刻。”对布罗茨基来说,艺术审判就是他的末日审判。他在诗艺上的高标准和高追求,正是他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和信仰。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里这样宣告:“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四、结语
简而论之,布罗茨基的诗学涉及面宽,广泛而深刻。和传统艺术论在精神指涉和情感强度上有所不同的是,在心灵日益丧失家园的“机械复制时代,” 布罗茨基的诗学更加让我们感觉到浓郁的宗教情怀和审美乌托邦气质,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决绝地为诗歌辩护,为艺术、美学招魂,为人类宝贵的个性、想象力和创造力呐喊,这展现了他对艺术本质和人类存在的艰难思索和一片赤诚。对我们正所处在的混乱平庸的时代而言,布罗茨基的诗学无疑仍然是艺术和诗歌爱好者心灵的“加速器”和精神的“强化剂”。
[1]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小于一 [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2]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悲伤与理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3]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等译布罗茨基谈话录[M].东方出版社,2008.
[4]布罗茨基传.洛谢夫著,刘文飞译[M].东方出版社,2009.
[5]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布罗茨基著,王希苏、常晖译[M].漓江出版社,1990.
I512
A
陈子寒(1976-),湖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