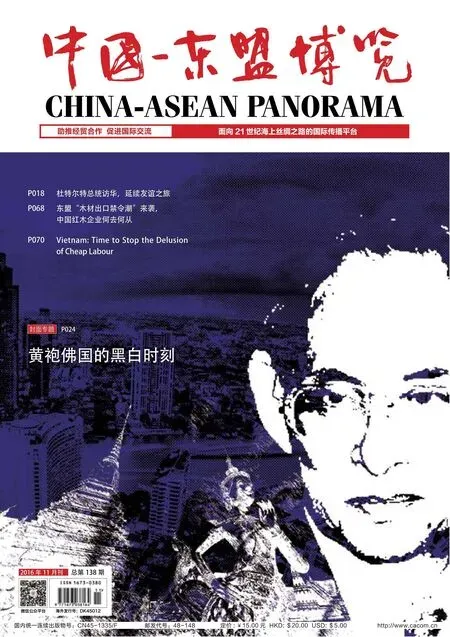长篇连载:国宝同仁堂
长篇连载:国宝同仁堂
谭鑫培戏唱得极好,索价也极高,在堂会上唱一出要五十两金子,两出就要一百两,再多就不唱了,不管给多少金子。这还不算,他的架子还极大。当年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杨莲帅听说他到了天津,托人请他到衙门里唱戏,他却一翻眼皮说:“我到天津是来玩的,哪儿有工夫干那种区区小事。”
杨莲帅碰了好大一个钉子。这杨莲帅其实就是当年掏钱让乐敬宇在山东办官药局的杨士骧,他从山东调到了直隶担任直隶总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位高权重,可是谭老板就是不买账。天津达仁堂开张这天,正逢谭鑫培最后一次到天津,受乐达仁之邀,竟欣然在天津广东会馆登台演出,为达仁堂的开幕仪式增色不少。当时的报纸介绍,“是日各界来宾,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
开业仪式办得红火,加上北京同仁堂在天津本来就很有影响,估衣街在当时又是津门最繁华的地段,天津人知道京都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的老乐家人开办的,更是踊跃登门。达仁堂因而一炮打响,开业第一天就赚了八十块大洋。从此,乐达仁把天津看作是达仁堂的发祥地,并奠定了天津作为达仁堂总号的地位。
在乐家四大房的昆季当中,大房的乐达康和乐达庄曾留学法国,四房的乐达义留学英国,而乐达仁本人又在德国学习考察过。因此,这两房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在这当中,乐达仁又是最能接收新鲜事物的,也最有改革精神。当年乐达仁在德国游历的时候,就注意观察和了解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情况。因此,和各房照搬照抄乐家老铺“前店后厂”的模式不一样,达仁堂很早就开设了现代化的工厂。
同仁堂开业的时候是十七世纪,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当时的“后厂”只能是手工作坊,因此有人称为“前店后场”或“前店后坊”。而达仁堂开办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已经相当发达,中国的工业,包括制药业远远落后发达国家。中成药能不能实现工业化生产,当时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乐达仁却敢为人先,天津达仁堂首先建起了一个占地八千多平方米的“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包括一座生产大楼和一座仓库大楼,开凿了深水机井并建立了水塔,还破除了“中药不能用洋机器制造”的迷信,使用现代化机器替代了一部分笨重的手工操作。乐达仁还进口了冷冻机,建立了冷藏室,用以贮藏容易腐烂变质的药材和药品。这时的达仁堂已经不再采用传统中药铺“斗房”“刀房”“碾房”之类的分工方法,而是采用现代企业的方式来划分职能部门,分成了“轧药处”、“熬药处”、“裹药处”、“切药处”和“印刷处”。这在当时的中药业来说,都是新鲜事儿。当“电碾子”飞快地转动起来时,那些推过石碾的工人们都高兴地说,“这回可好了,咱们当小毛驴总算当到头了。”
达仁堂在经营管理上继承了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和“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理念,以及同仁堂的一整套管理办法,但又有自己的发展和改进。乐达仁在德国参观过很多大药厂,学到不少管理方法,也将其融合在对达仁堂的管理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时中国的传统店铺里,员工都是在店里搭铺住宿,晚上搭,白天收。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需要,这种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现代化工商业的要求了,因此,达仁堂在离估衣街不远的五马路盖起了二十多间崭新的职工宿舍,既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条件,又便于管理,更能吸引有技术的工人到达仁堂来。乐达仁还鼓励员工们学英文,多接受新鲜事物。因此,达仁堂的资本也日渐雄厚,规模也迅速扩大。从1917年开始,天津达仁堂先后在长春、青岛、大连、福州、长沙、西安、郑州、开封、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号,连同原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开的店,最多时共有十八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达仁堂年营业额高达七八十万银元,资产增长了二十倍。
由于分号繁多,给达仁堂的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保证各分号的服务质量,就需要乐达仁以创新的精神来解决了。因为同仁堂从不设分号,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验可资借鉴。其他各房开的店虽有设分店的,但没有达仁堂这样多,分布地域这样广。为此,乐达仁动了不少脑筋,并且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主要有,所有的达仁堂分店都有一致的招牌,除正楷书写的达仁堂牌匾之外,两旁都有从同仁堂拓来的牌匾“灵兰秘授”、“琼藻新栽”。各分号的查柜(经理),都要按期向总管理处写号讯、汇报业务。各分号只能售达仁堂生产的成药,并且由总号统一配送。有条件的规模较大的分号,由总号供应统一配方、统一炮制加工的药粉,自行制丸、包装。包装方式和外观都要与总号的一致。各分号必须按市价出售,不搞二次批发,也不准代销,并且不赊账,更不打折扣。因此,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仁堂已经成为工商一体化的国药集团了。
因为达仁堂大获成功,乐达仁本人又尊老爱幼,他的三个弟弟乐达义,乐达明、乐达德都很敬重他,甚至把自己的后代交由他培养教育。除了他自己的长子乐钊外,乐达义的儿子乐松生、乐达明的独子乐肇基也都在乐达仁身边受到培养和锻炼,乐肇基和乐松生还参加了达仁堂的生产和管理。因为乐松生名“鏳”,达仁堂的员工还按他们的排名编了一句顺口溜:“越早(乐钊)越成(乐鏳);越着急(乐肇基)越打人(乐达仁)”。这顺口编得倒是好记,也表现了达仁堂员工的幽默。
第五节、你争我夺,乐家昆季开商战弱胜强败,输赢得失殊难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乐家四大房都开了自己的店,有了发展,于是兄弟之间的商战就开始了。北京是老乐家和同仁堂的发祥地,激烈的竞争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同仁堂的东侧开了个宏仁堂;同仁堂的西侧就开了达仁堂,一条不长的大栅栏街里竟有三家乐家老铺。乐达仁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决心到外地发展的。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因此有津门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争之地,乐家也不例外,马路西侧开设了乐仁堂,马路的东侧就开设了宏仁堂,再加上在天津雄起的达仁堂,三家都拿出看家本领在这里打拼,天津人说,“好嘛,亲兄弟打起商战来也不含糊啊!”
上海当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也是东亚发展最快的城市,这里自然更有一番鏖战,而且明明是输家,却赢得很险,明明是赢家却又输得很冤。这话怎讲?原来,乐达仁在南京路开设了达仁堂后,乐笃周是个天有多高,心就有多大的人物,专门喜欢和自家人唱对台戏。他就在不远处开设了宏仁堂。乐达仁为了应战,又在宏仁堂的对面开了一家“树仁堂”。于是一场商战就不可避免了。双方先是竞相降价,你九折销售、我八折优惠、你“跳楼”,我“牺牲”、你“减半加优惠”,我“五折带赠礼”。后来发展到药方中的犀角、羚羊角,人参等细料一概免费赠送,闹得有的顾客都不敢来抓药了,因为上海人生性谨慎,这么个“优惠”法,怕其中有诈,所以干脆躲得远远的看热闹。这场恶战直打得黄浦江翻浪,南京路震荡。最后,宏仁堂毕竟资金,实力都不及乐达仁开的树仁堂,再也玩不下去了。乐笃周痛心疾首,认为既然败局已定,剩下的就是考虑怎么清账关门了。不想,乐笃周正在愁眉不展地考虑宏仁堂的“后事”,大查柜突然喜出望外地冲了进来:“东家,东家,真是奇了。咱们这药涨价了,卖的倒火了。那边七爷的药降价了,生意倒冷了。您说怪不怪?”
乐笃周开始还不信,他到柜上看了看,果然买药的顾客络绎不断,又到账房查了查,真的销量大增,利润滚滚;再去树仁堂的门口看看,门庭冷落,一片萧条。他嘴张得老大,眼瞪得滚圆,站在那里发愣。有的伙计说:“坏了,东家惊呆了!”有的说:“不对,是东家乐傻了!”
其实乐笃周又是高兴又是惊奇。高兴就不用说了,简直有死里逃生的感觉;惊奇的是,这上海也太怪了,树仁堂不败而败;宏仁堂不胜而胜,是天意如此?是鬼使神差?还是乾坤颠倒?总之,此事实在诡谲,他怎么也搞不明白。
树仁堂同样感到奇怪,自己的药质高价低,怎么倒伤了自己?于是双方都请上海的“高人”指点,虽然请的是不同的“高人”,指点的结果却是相同的。他们都说:“上海人和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即使买最贵重的物品也要煞价,要的是质高价廉。上海人相反,上海人是买高不买低。东西便宜,他们倒不放心了,不仅是担心质量不好,而且担心让人知道自己买的是便宜货,有失脸面。”
乐达仁一是觉得再争下去没有意思,只能是两败俱伤,二来毕竟是自家兄弟,还是适可而止吧。于是“树仁堂”撤出,宏仁堂便稀里糊涂地赢了一场商战。
不过,这一时期,乐家四大房最大的一场风波还是因为开设南京同仁堂分店引起的。
按乐家的族规和与朝廷的约定,同仁堂不设分店。因此,在大清朝,谁要是在北京以外看见了“同仁堂”,那一定是假冒的。可是1929年,南京却突然冒出了一个同仁堂。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别说一般老百姓分不清,就连乐家的人也为这事儿争得脸红脖子粗。
原来,1928年6月28日,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叫了“北平特别市”,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曾经说过,“北平是一个封建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
北京人这个气啊!有人就拿着历史说事了:“自打南唐之后,金陵就留不住王气了,要不明成祖要迁都北京呢!他姓蒋的懂不懂历史?读没读过李后主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哼,只怕是将来有一天,这位总司令到了仓惶辞庙日,连一句歪诗都诌不出来呢!”
可是北平的百姓话能说上几篓子,气能生上一肚子,却顶不住当权者的一个印把子。政府要搬家,老百姓怎么也拦不住。大批的政府机构一走,北平的街面上一下子就冷清了,商业也萧条了下来。同仁堂斜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瑞蚨祥”绸缎店,1925年瑞蚨祥的营业额是六十万两银子,到了1929年已经跌到了二十七万两。这还算是好的,有的老板因为支撑不下去,竟寻了短见。
这时,乐笃周就提出,应当在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他说:“别忘了,老祖宗就是‘供奉御药’起家的,不然哪儿有今天的同仁堂?现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不管是叫‘委员长’也好,叫‘大总统’也罢,我看和皇上也差不多。他们既然也食五谷,就要得病,得了病就得吃药。咱们在那儿开一家分店,没准还能得到‘供奉国民政府专用药’的机会呢!咱们老乐家不又有了振兴的机会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