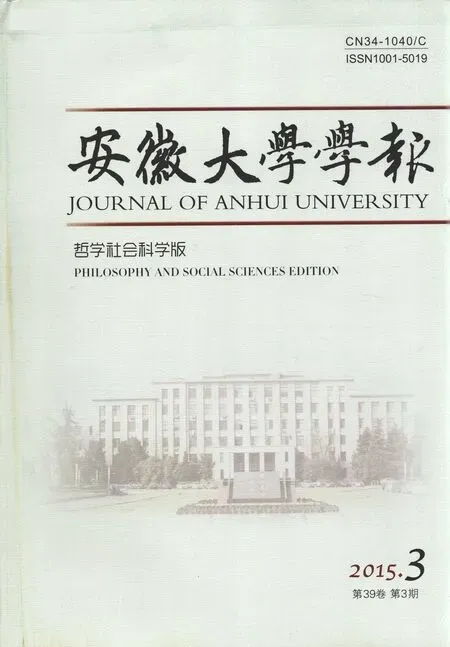20世纪初以来的村落调查及其学术价值——以社会学家吴景超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为例
王振忠
20世纪初以来的村落调查及其学术价值
——以社会学家吴景超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为例
王振忠
摘要:吴景超是20世纪前期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1919年撰著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该文献是一篇有关其人桑梓故里、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类型资料,从位置、沿革、物产、宗法、生活(含职业、衣食住、娱乐)、教育、风俗(婚嫁、丧葬、岁时、迷信)和胜景八个方面,对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作了多角度的细致描述,其中不乏精彩的刻画和珍贵的史料记录。此一文献独具特色,对于我们理解吴景超的生活经历及其社会学实践,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乡土社会,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梳理较长时段的村落调查之学术史可见,与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社会调查一样,吴景超的这篇村落调查文献对于当代的村落文化记忆和古村落之保护,亦颇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吴景超;徽州;风土志;社会调查;民族志;徽学
一、吴景超与《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
社会学家吴景超(1901—1968)系安徽歙县岔口村人,字北海,其家庭经营茶业,颇为富裕。父亲吴瀚云为晚清贡生,热心于公益事业,捐资兴学、筑路修桥等,一向不遗余力。吴景超于1914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翌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夏赴美留学,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俊可:《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歙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歙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48页;参见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2005)》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247页。。1928年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开展城市经济调查。1934年,他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达一起前往河北定县,参观平民教育工作。1935年,吴景超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1947年返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费孝通是他的弟子*吴景超曾发表书评,推介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George Rontledge & Sons, 1939)、《禄村农田》(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油印本,1941年)二书。他评价“《禄村农田》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在我们学社会学的人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而在评论《中国农民生活》一书时,他指出:“费孝通先生所写的《中国农民生活》,是根据他两个月的实地工作所得到的材料写成的。……据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的书籍中,描写一个区域里的农民生活,像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本书便是以人类学者所用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过去的人类学者,常以初民社会为其对象,最近才有人以同样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已经发达的社会。……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觉得中国各地,应当有许多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把各地民众的真正生活,描写出来,让大家读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更深刻,更广泛的认识。中国实在太大了,我们每一个人所知道得清楚的地方,只是中国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我们只能够从地理的著作中,从游记中,或者从旅行中去认识他。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是粗枝大叶的,不一定与真相符合。我们需要像费先生所写的这一类的书,来补救这种缺点。”(《新经济》1939年第1卷第11期)。吴景超曾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和编辑,深受胡适等人的推重。1952年以后,他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历经磨难后于1968年去世,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吴景超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曾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关于吴景超的个人阅历及其学术思想,此前的研究主要有:庞绍堂《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吕文浩《吴景超:被浪费的才情》,《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7日;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第八章第四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9~480页;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六章第一节《吴景超的为人与治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6~170页;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载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257~273页;马陵合《经济与社会之间: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载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2012年春季号(总第2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5~71页;邹千江《吴景超及其社会思想新探》,《江淮论坛》2014年第6期。。
关于吴景超其人,1947年,域槐在《自由文丛》上发表《吴景超教授回到北平以后》一文,其中指出:
吴先生是清华园的名人,从进清华当学生起到一九二二年出国,在七年的学生生活中,他是清华园里一名出众的人物,是当年的活动分子,他曾长期主编《清华周刊》,又是成绩优良的学生,高高的身材,轮廓可分,谈话使人觉得松适,还颇带一些诙谐口吻。留美归来后便开始了教授生涯,这正是传统典型的清华教育出来的人物。他一直是生活在舒适和安乐的环境中,从事着一种所谓的神圣的教育工作,他是一位社会学的专家,热心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然而由于生活意识的拘束,总不免带着一些传统文人和浓厚的经院习气,始终只是以观察人的身份去观察实际的问题。基于这种态度得来的结论,除了富于一点人类本性的同情和怜悯而外,是不易于对问题得到真切的发解的。
自然吴先生自己不会这样设想,而相反地正因为有他自己的结论,终于禁压不住自己胸怀的抱负远见,他不能再把自己局限在象牙之塔内,让自己生命之火在里面窒息,他要为他所从事研究的学问,寻求实践的机会,他要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找出路谋取改革,救助在穷苦中挣扎着的人民,他力主中国应该工业化以扩大生产的能力,从而吸收农田上剩余的劳力,普遍地提高生活程度,而更基本的他主张限制人口的政策,他觉得三民主义中提倡鼓励人口的增加,实在是一种盲目的见解。
这篇文章明显是站在批评国民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对于吴景超此前弃儒为官不无微词,不过,对于其人的才情以及学术贡献亦称赞有加。据说,梁实秋曾这样刻画他:“景超徽州歙县人,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记》,故大家戏呼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事公私分明。”*吴清可:《回忆我们的父亲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9页。
199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一书,这是吴景超博士学位论文的中译本。2008年,商务印书馆重印吴氏的文集《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据该馆1937年版排印)。此外,吴景超现存的文字为学界所知者并不太多。不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景超却是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早在1919年,他就撰有《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癸亥级刊》,1919年6月。,该文对于当前的“徽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之形成,与吴景超早年的经历有关。当时,虽然在外求学,但每到假期,他总要抽空回到故乡*1919年6月《癸亥级刊》上有吴景超所撰的《树阴农语》,其中提及:“吾家门外有广场一,老树数株立其中,为夏日避凉之佳所。去岁暑假归里,每夕必憩于其下,时则有老农名尚福者,为吾等说故事,其言颇多有味,记其数则于左,以备遗忘云。”此文述及当地捕虎、捕猴等方面的数则故事。此外,吴景超还写过一篇小说《死夫生妇》,也刊载于1919年6月《癸亥级刊》上。。吴景超曾对闻一多说过:“人生最完满最快乐的生活,只是诚心悦意地加入社会去活动,使我所居的社会,因为有我,可以向真美善的仙乡,再进一步。”从中可见,吴景超对于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充满了激情。在《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一文中,吴景超主张回乡组织“少年学会”,其宗旨有三:一是研究学术,二是修养品行,三是改良社会。他主张在假期要外出旅行,“调查社会,为改良张本”。他还拟定了社会调查工作的纲目,内容包括:(一)教育情形;(二)交通情形;(三)慈善机关的情形;(四)生活状况。此外,如农业、工业、商业、物产、人口和风俗等,亦受到较多关注*《清华周刊》1921年增刊7。。对照1919年《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的序言“是篇,首位置,次沿革,次物产,次宗法,次生活,次教育,次风俗,次胜景”,可见吴景超的这篇“风土志”与他较为长期的积累密切相关。对于岔口,他深情款款地写道:
昔仲尼去鲁,迟迟其行;汉高过沛,留连不舍。人无不爱其故乡,凡有血性者皆然也。岔口,余之生长地也,其地山清水秀,风俗淳朴,余自束发以至成童,皆度岁月于是。及长,离乡他适,然每逢佳日,心中辄怀故乡弗能忘。因就记忆所及,著为是篇。
可见,正是因为桑梓情深,再加上对于社会调查重要性的自我意识,吴景超撰著了《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该文作于1919年,当时吴景超不过18岁。从文字上看,其人的传统学术功底颇深。此处试以他对村中八景的描述为例稍加说明:
(一)梯云夜读:梯云草堂,今已焚毁,然荒烟蔓草间,犹令人想见当日情景,每当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之际,携书至其地,据磐石读之,令人抑郁之思,不扫而自去。
(二)虎阜涛声:两水合津,潮流陡急,泉石相搏,无风而涛,砰訇激跃,荡耳震目。
(三)龙门积雪:龙门尖,村前秀峰也,每交冬令,山巅积雪,霁日照临,光眩人目。
(四)长潭观鱼:长潭水碧,清澈见底,其下碎石棋布,罗罗可数,游鱼扬鬐,浮沉往来甚适。
(五)云碓夜舂:晚间万籁俱寂,惟风送舂声,若断若续,令人尘虑俗想,荡涤殆尽。
(七)飞桥卧波:村前有桥一,长数丈,连通南北,每当溪水涨溢,桥下水流澎湃汹涌,自远望之,有如彩虹饮水,至足观也。
(八)前溪柳色:春夏之交,前溪柳绿,千丝万缕,笼雾含烟,登高望之,一碧无际。
所谓“八景”或“十景”等,是传统文人赋予地表景观内涵最为常见的一种表述。安徽歙县岔口村大概是在清代出现了“八景”之说,列在首位的是“梯云夜读”。此处的“梯云”是指梯云草堂,为岔口村著名的私家藏书所之一,咸同年间毁于太平天国兵燹。之所以将“梯云草堂”冠于“八景”之首,显然是意在标榜岔口系“贾而好儒”的一个徽州古村落*《歙县民间诉讼案卷集成》(抄本3册)中,有“岔口吴姓人氏,吴姓世代书香”的说法。另外,在《联句集记》(抄本)中,记录了岔口的两副对联。其一为:“飞阁临流楼台近映双溪水,鲜花竞艳梅萼先开十月天。”其二为:“霜叶风涛异曲远谐天籁响,山鸣谷应清歌隔断石泉声。”后者为“岔口做会联”。以上两种抄本均笔者收藏,前一书名系据内容暂拟。。
二、从《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看传统徽州社会
歙县岔口村位于新安江上游,作为新安江支流的大源河与小源河在此汇聚,呈Y字形,岔口因此而得名。大源河自歙县周家村流出,而小源河则自井潭流出,两河在岔口村交汇后称为大洲源。在传统时代,岔口历来就是大洲源日用消费品和土特产品之重要集散地,是大洲源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图1歙县岔口村及周遭形势图*此图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中心李甜博士协助绘制,特此致谢!
(一)以茶叶为主体的乡村经济
大洲源一带是徽州茶业较为兴盛的地区,此前发现的反映大洲源一带社会生活的民间日用类书中,就有《卖方茶寄家信俚言》,其中的首段写道:
开船到威坪(正口茶叶下船到威),船破茶叶湿(威坪村头滩上,船只譬如撞破了,茶叶又受潮了),廿七到杭州(廿七上午九点钟到杭,茶叶未起行了),三篓看不的(方茶开篓出样,打样时,连开七篓,开篓茶叶受潮,三篓茶受潮最重的)。*何莲塘的相关文书不止一种,系笔者在皖南从不同渠道收集而来。其中之一封面题作“何莲塘抄”,为民国抄本,书中一份卖契有“自前清移居徽歙大洲ΔΔΔ地方”之句。另一为《类联集句》,封面除书名外,另有“何莲塘录”字样,其中包括“寿联”“创造联”“春联”“道场联”“学校联”“闲挂联”“演戏杂句”“挽联杂句”“黄鸟开会并做戏对联杂句”和“毕业联”。
威坪镇属于浙江淳安县,是徽商前往长江三角洲的必经之地。而歙县的正口则是新安江上游的重要码头,为进出大洲源、虎坝源的必经之地。此一俚言篇幅较长,内容颇为生动,上引的一段文字描述了晚清时期当地人由新安江外出,经歙县正口到浙江威坪再前往杭州贩卖方茶的过程。
动物试验表明:低镁饮食可导致大鼠冠状动脉内皮细胞损伤、肿胀和增生。用低镁饮食饲养的家兔可使其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加重及血脂升高。家兔摄入较多的天门氨酸镁使得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下降、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减少、动脉壁内膜/中膜比例降低。研究中发现血清镁同血清胆固醇的浓度呈反比关系,从而提示从饮食中摄入镁可能会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因此,饮食和水中镁缺乏与IHD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镁能够减少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心源性休克的发生率。
歙县方茶早在唐代就已相当著名,在唐人杨晔的《膳夫经手录》中即有记载。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在歙县南乡从事茶叶产销的村落相当不少。1919年,吴景超曾撰写过一篇徽州洋庄绿茶的调查报告:
谈徽州之物产者,必言茶叶,徽茶之名,几于中外皆知矣。业此者共分二种,曰店庄,曰洋庄。销于国内者曰店庄,销于国外者曰洋庄。店庄国人多知,兹无论矣。洋庄绿茶制法,与店庄大异……
徽州之茶号,约计二百余家,欧战之前,尚不止此,欧战之后,银根吃紧,航路阻碍,洋庄不甚行销,故茶号亦因之而减少。茶号最多之处,在休宁则推屯溪,在歙则推深渡、岔口等处云。……可由新安江运往杭州,茶叶抵杭,可由行家代运往沪,杭州江头有行数十家,皆代客运货者,如洪大房、曹泰来,其最著者也。运沪之途有二:一由沪杭火车,一由城河驳往拱宸桥,再改由轮船运沪。途虽二,而号家多愿由轮船。盖代客售茶之茶栈,皆在上海北市,轮船栈房亦在北市,其取货也便。沪杭火车栈房,则在南市。(近来沪杭、沪宁,已曾联轨,由杭运沪之茶叶,亦可在北市起卸,将来号家或因火车快利,改由火车运茶,亦不可知)*吴景超:《徽州之洋庄绿茶》,《癸亥级刊》1919年6月。
吴景超出身于茶商家庭,对于徽州洋庄绿茶的了解相当细致。在上文中,他提及绿茶运销上海的交通路线,这一点,得到了一些契约文书的印证*笔者手头有一份1925年“茶业公会”与“招商内河轮船公司总局”及“上海戴生昌轮船总局”订立的运茶合同,虽然年代稍晚,但所述与此可以比照而观。。歙县茶号最多的地方,除了皖南茶务的中心屯溪以及歙县深渡之外,便是自己的老家岔口。关于岔口村的茶叶贸易,吴景超指出:
茶之出类,颇为不少。村中有洋庄茶号六家,每年收集村中及他乡之茶叶,制为洋庄,运往沪上,销与外人。开设茶号,需资甚巨,而村人有充厚资本者,绝无仅有。曩时皆由沪上茶栈放水脚,或息借庄款,以应需用。年来金融紧迫,茶栈及钱庄多不愿放款,村中茶号以此停止或减少营业者,已非一睹矣。
由此可见,岔口虽然地处偏陬一隅,但却与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借此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观察近代国际贸易冲击背景下皖南山乡的巨大变化。
关于岔口一带的洋庄贸易,晚清民国时期的民间文献中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例如,抄本《杂辑》*此抄本系歙县南乡磻溪方氏的家族文献,是有关晚清时期徽商与徽州社会的珍贵史料。私人收藏,已另文探讨。中有《岔口吴锡蕃先生伯仲》条,其中指出:
岔口开设吴心记之吴锡蕃,兄弟五人,北岸支,扦岔口数世矣。父蔚文在日,家道康,因做洋行中落,锡蕃经理店事、田园,勤劳罔懈,守之二十年,重做洋庄而中兴。二弟咏霓,邑廪生,改生意。三入泮,后即故。四清泉。五瀚卿,廪生。子侄辈右武等二十余人,一一受约束矣。些微习气,太和元气充溢庭宇。自奉甚约,款客适中,早作夜息,家道井然,论南乡家庭教育,当推第一焉。同时,伊之本家有荣寿字俊德者,屡入经司有叔之子也,以坐洋庄,骤发至二十万,在屯溪为徽商领袖云。
文中提及的吴荣寿,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1934年。其人自童年起即随父兄在屯溪经营茶叶,光绪二十七年(1901)子承父业,在屯溪开设怡春、永原、华胜等茶号,精制“屯绿”。他曾与同好倡导组织屯溪公济局,于宣统二年(1910)在屯溪阳湖创办徽州乙种农业学堂(亦名崇正学堂),并先后担任徽州茶务总会会长、休宁商会会长等职,制定《徽州茶务章程》。因席丰履厚,被当时人称为“茶叶大王”(在上海滩,同行称之为“茶大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述的传记中称他为屯溪的“徽商领袖”。1914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前来屯溪,曾拜访吴荣寿,赴阳湖参观乙种农业学堂,调研茶业状况。当时,与吴荣寿合伙做茶叶生意的,还有岔口人吴汉尘、吴佩行等,他们的旧宅皆在屯溪阳湖一带,直到近年仍清晰可辨*安徽五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编:《徽商大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66页,“茶大虫”条;第230页,“茶商吴荣寿像”条;第614页,“吴汉尘”条;第615页,“吴佩行”条;第616页,“吴荣寿”条。。
另外,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诉讼案卷中,经常可见与岔口相关的茶叶贸易。例如,《歙县民间诉讼案卷集成》中,就有一份档案“为挟截凶抢侄遭殴伤叩验拘究事”,其中提及:“身侄荣华、正达、正益,于昨初六日挑细茶六袋,重一百九十五斤往岔口行卖。”另一份诉讼案卷指出:
具书人庄坑汪金魁,诉为奸贾勾谋,鲸吞血本,财命两陷,恳公赐追事。缘岔口吴长元仝弟祖元,开设吴怡泰洋庄茶号,曾托身代买茶叶,伊号亲自发出来袋皮、图章以为信记。身于左近各处代买春茶五十余担,茶银面经号内随时算讫,俟后又着身往六街各山收买,计春茶廿九担,现今发到念四担,归伊号内收数。讵元之弟兄奸诈百出,顿起狼心,魆向各茶户勾通舞弊,明则谓茶色不佳,不肯收号算账,暗则相帮各茶户私运别号代为脱售。身与理言,反逞凶横,频遭殴辱,且将身应付之茶户并挑茶担力现洋六十三元,元竟瞒身私自收入吞没,似此勾谋渔利,弊窦现然无疑。但应茶户之现洋,实身填出血本,若不恳公追究,势必财命两陷,文明商界,理法何存?为此迫不得已,伏诉贵府茶商绅董老先生台鉴,准情酌理,俯赐品评,俾得血本归原,不至财命两陷,身当顶感靡涯,谨诉。
这是一桩有关洋庄茶号的纠纷。从当代的《安徽省歙县地名录》来看,名叫“庄坑”的地方计有两处,皆位于歙县南乡。由此可见,岔口的确是周遭较大范围内的一个茶叶贸易集散地。
在《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中,吴景超首先概述了岔口村的位置和沿革,指出:岔口位于歙县南乡,属于当时的南一区,“村之四周多山,西有坝岭,南有繁实凹岭,北有江村岭,前有龙门米,四山拱卫,如围屏然”。接着,吴景超记述了岔口村的“物产”,并对当地的生计做了重点描摹,他认为:“欲知一村人民生活之难易,必先考察其人民之职业,此不易之理也。”对于村人的生计,文中有着相当细致的调查。
如所周知,从总体上看,徽州是商贾之乡,岔口自不例外:“村人又有经商于外者,其地多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及江西之景德镇,浙江之金华、兰溪、衢州、龙游,安徽之寿州、霍山等处,或为人作伙,或自设店业。其最远者则为日本,行业为茶、漆为多云。”关于这一点,也得到其他文献的印证。譬如,晚清民国时期《歙县深渡乾裕号信底录稿(1903—1913)》*此抄本为安徽黄山学院孙承平先生收藏,将收入笔者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预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收录了1903年至民国初年的信件抄底68封。信底作者为歙县岔口人,1902年曾在歙县深渡开设乾裕号南货店,后在浙江兰溪米店工作,该信底主要收录了他写给苏州吴秋舫、杭州裕德茶行方树棠、苏州乾丰祥南货号吴声之、屯溪豫丰祥茶号吴瑞常、苏州集成酱园方季高等亲戚朋友的信稿,从中可见岔口一带商人外出的情形及徽商之间的相互交流。
此外,留在本地的男子,从事的职业也相当多样,兹据《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的记载列表于下:

表1 岔口村的职业种类

续表1
上述记录对民国前期皖南山乡的一个村落,作了几近全景式的描摹。从总体上看,此一山村是传统徽州典型的农村社会,村中的居民绝大多数从事农作。关于这一点,吴景超写道:
岔口山多田少,务农者大半种山为业。山中所植者,曰小麦,秋末播种,夏初收割;曰黄豆,仲春播种,大暑收拔;曰粟米,曰苞芦,五月播种,孟冬收获。山中又多植茶柯,春茶立夏后收采,夏茶夏至后收采。田则无多,其中不过百亩而已,村人多以栽种蔬菜,如苋菜、青菜、白菜、冬瓜、西瓜、羊角、扁荚、韭菜、萝卜菜、马兰头、茄、芋、姜、葱,其最普通者也。猫能捕鼠,犬能守户,人家畜此者亦多。豕则家家皆有,以为婚嫁丧祭不时之需。家畜之禽,则有鸡、鸭等物,以为食品。绿豆鸟、画眉、八哥、竹鸡,则养为玩物。
此处勾画了当地农村家庭日用食料、经济作物和家禽家畜等的一般状况,从诸多侧面反映了皖南地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提及岔口的六家洋庄茶号,“每年收集村中及他乡之茶叶,制为洋庄”,这一点,与上引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文书可以相互印证。不过,及至20世纪前期,岔口村也逐渐受到与日俱增的外来影响。如药房所卖者,就有外来的金鸡纳霜丸等西药。此外,馄饨摊和面摊的设立,也反映了与茶叶贸易相关的外来流动人口之增加*关于这一点,在歙南的一些乡村中均有类似的情形,如新安江沿岸的璜蔚,当年茶市兴盛时期村落中出现的相关设施(如妓院等),其遗迹迄今仍依稀可见(此据2009年笔者的实地走访调查)。。
另外,从表1可见,岔口的算命先生和看风水先生,均为村民所深信。对此,吴景超指出:
吾村儿女婚嫁之权,可谓尽操于算命先生之手。村俗,凡两宅通婚,以换年庚(即问名)为第一步手续,所谓年庚者,即一人之生辰八字也。年庚既换,乃请算命先生来,命其卜之,名曰对年庚。算命先生曰吉,则两家乃为正式之谈判;算命先生曰不吉,则互退年庚,彼此无商量之余地。坐是故,而吾乡女子乃无真正之八字者,盖男子之八字不吉,犹有希望得妻;女子之八字不吉,则终身无人过问也。八字既如此之重要,故村人之善排八字者,乃不一而足。私塾之教师,即最善排八字者也。村人凡遇婚嫁丧葬及建屋出行等事,必拣一好日子而后行。村人之能拣日子者颇多,凡遇小事,村人则就决于彼辈;惟遇大事,则必求教于拣日子先生。所谓拣日子先生者,以拣日子一事为营业者也,吾村无之,惟六十里之外一村,有此辈一人,其营业颇不恶也。此外则看风水一事,村人以为一家盛衰之所关,对之尤为注意,凡祖宗营葬之先,必请看地先生,卜一吉壤。吾村附近,有所谓蛇形、驴形者,皆堪舆家之所谓好地也。村人对于堪舆家,崇拜颇深,虽其言多不验,然村人并不以此而灭其信仰也,亦奇矣哉!
关于算命先生和看风水先生,早在17世纪初的万历《歙志》中就有记载,徽州当地有阴阳家(算命)和形家(看风水)两类*万历《歙志》“艺能”七上—七下。关于万历《歙志》,参见拙文《万历〈歙志〉所见明代商人、商业与徽州社会》,《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志特别提及的阴阳家笙桥谢氏,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仍极负盛名,这些人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极大。譬如,万历《歙志》指出:“临河程珏妻石冈汪氏,年二十二,珏病瘵,吁天减算以益夫年,日者佥云其命不利于夫,乃慨然自决,曰:不能以算而寿夫,矧反以生而刑夫乎?则有一死,庶可以代夫耳。遂自经死。”*万历《歙志》“杂记”四十下—四十一上。文中的“日者”,即指以占候卜筮为业之人,相当于前揭的“阴阳家”,这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歙县亦称为“批命先生”。关于这一点,徽州文书抄本《居乡里》中有:“为人命里有穷通,端在时生格局中。限度运程分好歹,财官印绶不相同。四余七政兼诸曜,八卦三才并九宫。莫道世间无考驳,全归星士断精工。”根据当代的调查,在歙县的一些地方,算命所得结果如果不能满足相关人等的期待,人们通常会想出其他各种补救的办法,这显然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智慧*例如,在歙县里东乡,倘若男女八字相克,而女方仍有意联姻者,则多改年庚(如属虎的降岁,属羊的抬高年岁,谓之“羊抬虎落”)。当时有俗谚云:“十女九不真,改命作夫人。”关于这一点,详见柯灵权《歙县里东乡传统农村社会》,[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王振忠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5页。。因此,吴景超笔下算命先生的角色,不清楚是岔口当地的情况的确如此,还是吴氏只看到了一种表面现象?如果是前者,那显然反映了歙县境内的地域差异。
除了固定居住者之外,村子里还时常出现一些流动的商贩。如其中提及的“丝线担”,迄今还流传着民歌《卖丝线》,其唱词开首为:
担子挑起来,挑一个荡荡园,挑到了大家门,叫一声卖丝线一呀嗨。
担子放下地,恭喜又恭喜,花鼓呀摇起来,大家来卖[买]线一呀嗨。*金涛主编:《徽州记忆》(五)“歙县”卷,黄山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监制,2009年,第90页。
这首民歌以岔口方言歌唱,讲述小贩与姑娘的爱情故事,双方打情骂俏。不过,在歙县境内的其他地方,也都有以当地方言演唱的《卖丝线》,这当然反映了此类摊贩的流动性。
以上所述各业皆属于男子,有关妇女者则有六业:
(一)择茶。自四月至九月,为制茶之时,村中女子,入茶号择茶,每日可得工价自数十文以至一二百文不等,视择茶之多寡而差。
(二)养蚕。女子之为此者,其数不多,出丝亦甚少,只供自用而已。
(三)制扇。村中小女,能以麦杆编成各式之扇,名麦杆扇。此物为夏日人人所必备,需求甚多,村人既能自制,故外货不至侵入。
(四)做鞋。女子为人做鞋,每日可得工价约百文,作成之鞋,颇坚固耐用,故村人旅外者,多带土做鞋数双而行。
(五)锄草。农事忙碌之时,田多之家,多雇女子为除杂草,每日工价在六七十文左右。
(六)卖菜。田中所种之蔬菜,如有盈余,多以售之于市,销场颇佳。
综上所见,在《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中,吴景超在记述各类劳作时,都非常注意记录当时的工价,这是颇有价值的线索。以择茶为例,他在《徽州之洋庄绿茶》一文中也指出:“茶号收茶百余石,即可开工。工人有三种,多寡视号之大小而异。大号约有烚工二百人,拣工六百人,作工八十人。小号则烚工不过数十人,拣工不过百余人,作工不过十余人耳。……拣工皆本地女人,工价视拣茶之多寡而差,自数十文以至百数十文不等。”可见,无论是大号还是小号,拣工的数量总是最多的,而这些拣工都是由当地的女人充当。由于上揭的描述记录了各类劳作相关的明确工价,倘若我们结合文中的其他记载,便可作为比较的基础,从而对民众的生活水准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例如,《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中提及,当地猪肉价格一百数十文一斤,面、盐等物三四十文一斤,豆腐三四文即可购得一大方。相比之下,一般人只要勤于劳作,大概便可生活无忧。
此外,对于岔口村民众生计和社会关系的总体状况,吴景超指出:“吾村处丛山之中,民风朴野,故于政治、学术两界,露其头角者,实无一人。惟俗重劳而恶逸,民各能一技,且有田可资耕稼,失业之民,实不一觏。加以地当大小源之交,南一区之茶业,及他种贸易,皆以此为中心,故农商及劳动之业,有足述者。”可见,在上述各类生计中,茶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这一点,无论男女皆如此。另外,“村人相见,其称呼皆按班辈之高低,老者虽为劳工,细者遇之,亦敬礼有加,以故,外间屡见之尊富蔑贫、轻视劳工陋习,在吾村实罕见”。可见,迄民国初年,岔口村仍然保持着相当淳朴的民风。
(二)多族姓杂居村落的风俗
自明代以来,徽州就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岔口一带最早的居民为郑姓,明末,附近的凌姓以及昌溪吴姓相继迁入。及至清代,北岸吴姓开始迁入。到了民国时期,全村共有三百余户、一千余人,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吴姓。对于岔口一地的“宗法”,吴景超有专门的描述,他指出:当地有吴姓祠堂四所,即光裕堂、积善堂、彝叙堂和祥和堂。另外,还有属于凌姓的敬本堂。当地其他各姓(如王、郑等),皆以人数过少而没有祠堂。各祠堂中,以吴景超所在的光裕堂人数最多,为其他祠堂所不及。由于吴姓的四个祠堂源出一支,关系甚密,而且他们又与凌姓互通婚姻而为亲戚,所以村中彼此和谐相处,数十百年来都没有打过官司*不过,《歙县民间诉讼案卷集成》中提及歙县三十都七图监生张作云,控告岔口吴飞清引诱服弟寡妻郑氏成婚一案。按:三十都七图所属的各村包括虎坝山、武阳、光村、洽河、大坑、岔口、坝岭和抽司等。另,抄本《酬世汇编》亦提及岔口与金村争夺慈坑柴山,相讼数年,及至1937年才再次达成协议。这段记载虽然要晚于《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的年代,但它与前一个案例一样,或许都说明岔口与周遭村落的纠纷实际上并不罕见。。
关于祠堂的管理,吴景超指出:
每祠类皆置有田业,为祭祀之需,每年派二人轮当,并管理祠中一切事宜。一岁之中,如元日、清明以及各节,各房子孙多携酒菜及香纸入祠拜祭,诚敬之情殊足令人生慎终追远之思也。岁首及清明,又当共往祖坟扫祭。吾家祖坟,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亦二三里,岁首只至近处,清明则无论远近各墓皆当往祭也。岁首展墓所用之祭菜,除煖锅外,复有油果、春饼、茶盒、水酒等物。煖锅之数,有多至二十余者,排列一行,至足观也!祭时必放爆竹,焚纸箔。祭毕,各取煖锅于坟堂中,据地食之。于时则谈笑风生,庄谐杂作,其乐乃无比。清明至远处扫墓,亦多乐趣。吾家祖墓,有在歙之东乡者,有在绩溪县之宁[临?]溪者,非一日所能尽到,平常往返,恒以三日,大类学校之旅行也。清明所用之祭品,多以米果,为数甚多。祭毕,以此散之贫民,意颇善也。
宗族是徽州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徽州,宗族祠堂发挥着社会控制的重要功能,它通过举行祠堂祭祀仪式,执行祭祀制度,以增强宗族凝聚力,实现尊祖敬宗、合族收族、控制族人的目的*参见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上述这段记载涉及宗族管理的诸多侧面,对于祠产管理、祭祀及其相关食物,都有颇为细致的记录。对于宗族社会中的佃仆制度,吴景超亦有专门论述:“村中有伴儅数家,村人对之,多怀轻蔑之念,此则不平之举也。伴儅者,安徽细民之一种,其来由吾不得知。若辈之在吾村者,皆隶于各祠堂下,为各祠堂之人服役,大约男者多为吹手,女者则为喜娘,无执他业者。……伴儅在前清时已获国家同等之待遇。……然徽州各地,此习犹未尽除,吾村之伴儅,其托业于吹手、喜娘,服役各祠堂如故,此实吾村之玷,所当革除者也。”1727年,雍正皇帝发布开豁贱民谕旨,曾在徽州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此后,一些渐具实力的佃仆,纷纷通过各种手段寻找奥援,奋起反抗,以期尽快摆脱主家的控制,这在徽州的不少诉讼案卷中均有所反映*参见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载郑培凯、陈国成主编《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以〈钦定三世世仆案卷〉抄本为中心》,载拙著《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不过,主佃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伴儅的身份实际上与区域经济结构下的职业和生计密切相关,故而佃仆、伴儅问题直到民国尚未最终解决。
对于家庭生活,吴景超特别推重徽州的分家制度:“村中绝少三四世同居,虽兄弟亦多分爨,如一人有二子,则其子长大时,为父母者即为之析产。析产之书,多请族人签押,妨[防]他日之争执也。考家族制度中,惟数世同居一习为最恶,盖人口众多,则逢财相竞,遇事互诿,俭者不复俭,而勤者不复勤,终至人逸家衰,趋于贫困。吾村虽行家族制度,然能择其善而祛其恶,此村人所以多独立之精神,而少依赖之恶习也。”的确,分家制度促使徽州的个体能各自独立,发家致富。在笔者看来,此一制度与“打会”惯例,是徽商崛起的两个颇为重要的因素。而关于分家制度,唐力行曾揭示出徽州的“小家庭—大宗族”结构,根据他的研究,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与此同时,徽州的宗族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的裂变,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徽商资本一方面瓦解着大家庭结构,另一方面又加固并扩大了宗族血缘群体。家庭—宗族结构使得社会财产分为两个层次:家产和族产。家庭共有财产的无限分化,减缓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而宗族共有财产的不断扩大,也纾缓了宗族成员贫富分化的矛盾。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使得徽州社会更富于弹性和流动性,有利于徽州社会的稳定以及徽商的商业活动*参见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换言之,在大宗族的格局下,小家庭迸发出竞争的活力。
在论述了宗族和家庭的基本结构之后,吴景超认为:“风俗者,所以表现一地习尚之美恶,而政教所因也。”他将岔口的风俗分为婚嫁、丧葬、岁时和迷信四项加以论述。有关婚嫁,他指出:当地男子七八岁时,父母即择门第相当者,为之定婚。无论贫富,皆经过问名、贽定、行聘、请期、冠笄、迎娶等程序。迎娶的时间,大约富者在20岁以内,而贫者则在20岁外、30岁不等。此外,他还具体描述了婚姻嫁娶的基本情况:
迎娶之前数日,男宅即派人至女家抬嫁资。嫁资者,妆奁也。嫁资既抬至,即有小儿女多人,取嫁资中重要物件,如枕头、钥匙等物藏之,俟新人至,乃令其出果子赎归,以为笑乐。……新人既出轿,乃与新郎先拜天地,后拜高堂,继交拜,于是婚礼乃成。旁观者至此乃喧呼送房。所谓送房者,送新郎、新人入洞房也。新人居前,新郎在后,复有高年者二人,持蜡烛居先引之,由堂前至房中,沿途皆置布袋,令新人、新郎行其上,名曰传袋。传袋与“传代”同音,取延宗续系之意。
此处较为细致地记录了婚礼的整个过程,包括在男方的送房、传袋、吵新人、撒帐、吃交杯酒、拜灶师[司]、拜三朝等,以及女方家中的嫁妆、辞祖、分家饭、哭嫁、接回门等。其中的一些记载,还反映出近代以来婚礼程序上的细微变化以及岔口村婚俗的独特之处。例如,文中提及的“哭嫁”,在歙南极为普遍:
嫁女一事,吾村与外间亦多不同。未嫁之前数日,女子须入祠辞祖,及期,男宅发轿来,待嫁之女子乃放声哭,其母亦随之而哭。及良辰既届,女乃拜别父母,且食饭数口,名曰分家饭。然后由其兄或亲人抱之入轿,斯时女必大哭。轿既出门,家人乃持灯笼送之,及门外而返。女宅随轿同至男家者,有一喜娘,此喜娘三日后必返,报告男宅一切情形,及新人是否愁家等事。近来村人颇知女子嫁时号哭之无礼,皆相戒弗为。然而积习相沿,不哭似不合乎俗,女子畏羞,无敢破此例者也。
关于这一点,迄今仍留下了不少“哭嫁词”,可以与之比照而观。而所谓的“吵新人”,俗称“不吵不发”:
是日,村中复有吵新人之俗。吵新人者,请新郎、新人同立堂前,而嘲弄之也。吵之之法不一,有所谓撒帐者,以果盒所盛之果掷新人也。为此必有二人,一唱一和,其词多卑鄙,不堪入耳。又有所谓吃交杯者,以酒置杯中,强新人饮,惟不许咽下,移时复令其吐出,令新郎咽之。此外,复有唱歌者,有说笑话者,有作奇形怪状者,皆以博得新人一笑为目的。以一外村之女子,而无辜受若干生人之戏弄,不敢抵抗,不敢回声,亦大可怜矣!
与上述习俗相关的撒帐歌,有的相当俚俗乃至猥亵,这些,在众多的徽州文书抄本中有诸多生动的例证*如岔口一带的一首撒帐歌,与全国广为流传的《十八摸》颇为相似。见金涛主编《徽州记忆》(五)“歙县”卷,第89页。。此种“吵新人”的做法,甚至在明清的世情小说中也有记录,这对于理解旅外徽商的习俗亦颇有助益。
关于丧葬,《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指出:“丧葬诸节,颇为简单,然亦视贫富而别,贫者则丧事一两日即毕,富者有作祭等举,略旷时日。……俗礼,孝子于七七内,须衣麻衣,穿麻鞋,不进晕[荤],不剪发。七七后,易麻衣为白衣,麻鞋为白鞋,三年始除服云。棺厝于野,非长久之计,为子孙者于数年之内必为择地安葬,其礼颇隆。”歙县的丧葬习俗颇具特色,这在最近几年的民间调查中都有详细的记录。作为传统时代“徽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甚至被视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保护*胡亮、营娟:《徽州丧葬仪式音乐研究——以歙南岔口丧葬仪式音乐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此外,有关民间信仰,吴景超概视之为“迷信”,他认为:“迷信者,不辨事理之是非真假而妄信之也。村人不解科学,怪诞不经之言自易入耳,故迷信之风较之通都大邑为尤甚。”根据吴景超的描述,岔口村人“多信菩萨,凡遇菩萨生日,携香烛往祭者不绝于道”。
当时,岔口村中居民不过数百家,却有三座菩萨庙。其一为上帝庙,供奉玄天上帝。其二为上庙,也叫忠烈古庙,其中供奉着汪公大帝、八老爷、九老爷、东平王、太子、社公、社母等菩萨,这是村中最为重要的庙宇。“庙中有卦牌一,上载卦辞数十首,有上、中、下之分,村民多于岁首入庙求卦,以卜前途之吉凶云。”还有一座叫下庙(也叫水口庙),其中供奉着十余尊菩萨,重要的如关公、东玄坛、北玄坛、观世音、华陀、闻太师。以其中的“玄坛”崇拜为例,抄本《酬世汇编》卷5《财神札付》中即有一祭文:
窃以教设为三,自古儒林为首重;民生有四,而今商界居尊。欲应物以无私,回溯高风于端木;觉生财兮有道,可致巨富于陶朱。小往大来,实为人愿;恒丰大有,殊赖神功。今照得大民国江南徽州府歙县孝女乡延宾里岔口新宁社管居住信士弟子凌寿泰暨阖家男妇大小人等,薰沐三鞠躬,谨奉三坛正法,选于Δ月Δ日Δ时,天点神光,迎神附体,谨具醮仪,虔修法事,敢投词于正一龙虎玄坛赵大元帅之尊神而言曰:伏以正直无私,特授财神之职;威仪可敬,感钦元帅之称。秉九府之权衡,恒丰金窟;招四方之宾客,广辟财源。值此口岸开通,方幸经营便利,伏冀神灵永感,俾品物兮咸亨;虔祈圣泽宏施,庶春台兮共乐。行商则风顺鸿毛,快利畅销,喜扬归兮满载;坐贾则宾来雁序,轮流不息,欣日进夫千金。货随运而随销,具见新奇日著;财屡生而屡聚,堪为富有家声。克供厥职,大显威灵。依札施行,须至札者。
右札给付财神座下准此并及左右招财童子、进宝仙官照验施行。
从这份“札付”来看,“玄坛”信仰与商业经营密切相关。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商风气炽盛的岔口,还将玄坛分为“东玄坛”和“北玄坛”。根据徽州的都图文书,岔口村属三十都七图的孝女乡。从上揭文书来看,岔口新宁社所属的凌寿泰,此次奉祀的是玄坛赵大元帅。而该份《财神札付》中有“口岸开通”的字样,似乎反映的是近代的史实。不过,文中又有“大民国江南徽州府歙县孝女乡延宾里岔口新宁社”字样,从这一行政沿革来看,民国时期已无“江南徽州府”的建置,而“大民国”显然也脱胎于“大清”乃至“大明”,因此,此一“札付”至少从清代中叶开始便长期沿用,可以与《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中的相关记载比照而观。
除此之外,吴景超还提及,在华陀菩萨神座之前,放置着一个签筒,筒内置有百余根竹签,上刻号数,村民一旦生病,其家属就会到华陀菩萨跟前,跪在地上焚香拜祷,然后取签筒簸之,至有签落地为止。“村民得签,验其号数,告之药店中人,即可得药。”根据吴景超的观察,“药店中有签簿,凡某签得何药,上皆载之”。他认为吃这些药没有什么疗效,但也没有害处。不过,村里人都非常相信华陀菩萨,认为那是相当灵验的仙方。除了这三座庙宇外,水口庙外还有一根如来佛柱,凡是离乡前往别处者,多立柱前顶礼膜拜,“谓如是则得佛佑,一路平安,不遭危险也”。如来佛柱目前在徽州乡间尚有一些遗存(特别是在婺源,保存者颇为不少,歙县里东乡一带亦有所见),据说走夜路迷失方向,可以抱住如来佛柱,这样就可以神清气定,看清道路。
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是岁时娱乐,具体表现为众多的迎神赛会。《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有专节描述当地的岁时节俗:“元旦日,男女老幼皆衣新衣,黎明即起,先拜天地祖宗,次拜灶师菩萨,村人相见,亦各拱手道喜。前清之季,族人犹有拜年之举,今已取消矣。是日所食各物,皆锡[赐]以佳名,如鸡子则曰元宝,面则曰长寿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初二后,各携酒菜展墓,名曰拜坟年。元宵前后数夜,有嬉马灯之举,店户各家皆放花筒爆竹以助兴。”此外,文中还对二月二日接土地,三月三日嬉龙舟,清明祭扫挂纸,立夏食面,五月五日端午,七月十五祭祖宗、焚烧金银纸袋、作斋醮之会、召僧道施食,中秋食月饼、设宴赏月,九月重阳食角黍,十二月初八腊八节、二十四日送灶,除夕前数日送年节,除夕索压岁钱、坐三十夜等,皆有细致的描述。这些岁时节俗,在近年来出版的歙县白杨源、许村、里东乡一带的调查报告*参见吴正芳《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许骥《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柯灵权《歙县里东乡传统农村社会》,[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王振忠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3年、2014年。中也有不少描述,彼此可以相互印证。
关于“拜灶师菩萨”,从民间文献来看应作“拜灶司”。迄今,在岔口一带还留下《送灶司爷经》:“灶司老爷吟吟灶司经,灶司老爷一家之主你为尊,冬收白米罢仓仓满,红光落地罢遮灰尘,厌鬼别进来我家门,阿弥陀佛!”*金涛主编:《徽州记忆》(五)“歙县”卷,第94页。这是以岔口方言演唱的民歌,反映的便是“拜灶师菩萨”。再以元宵前后的“接菩萨”“嬉马灯”为例,吴景超在《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中还有更为具体的描述:“旧历新年,村人多闲暇,故娱乐之法亦最多。正月初十以前,村人多从事于拜坟年等事,无暇及此。初十以后,则接菩萨、嬉马灯、打锣鼓、唱曲等事,皆接踵而起。”关于“接菩萨”一事,岔口村多在正月十三清晨实行,所接的菩萨为东北玄坛,八、九老爷及太子菩萨等。通常情况下,每一个祠堂的人都必须接一两个菩萨,放在自己的祠堂里。接菩萨之时,用旌旗仪仗甚多,且放爆竹,有吹鼓手助兴,很是热闹。菩萨既接进祠堂,要宰杀一头猪进行祭祀。届时,村民皆需多备香烛祭菜前来祭拜。正月十三晚上还要“嬉马灯”,马灯是用纸扎成各种灯彩,让儿童手持着行走。此外,也有青年子弟装扮《三国》《列国》各剧中的人物,混杂在其中游行。又有人装扮盲者、跛者、骑者、乘者、乞食者、卖艺者等种种装束,“尽滑稽之能,极奇诡之态”。在歙县,“嬉”就是玩的意思,嬉马灯一共要嬉六天,到正月十八为止,其中又以元宵一晚为最盛。
此外,上述新年初十以后的“打锣鼓”,也就是集合若干人在一起练习各种乐器。晚间,村人多集中在祠堂里唱曲,所唱的则为徽调。在这几天,外村也有打锣鼓唱曲者到岔口各店家弹唱,店家则设茶及果子款待,临走时还要拿钱酬谢。这些人成群结队而来,数日内络绎不绝,每在一店弹唱,则其店之内外环绕聆听者众多,这也是新年的一桩乐事。
三月三日有龙舟之戏,龙舟是为了奉祀唐时张巡、许远和南霁云等人。现存的《姚寿山读(豆腐会用)》*抄本计3册,是有关歙县九沙新安大社的相关文书,私人收藏,拟另文探讨。等抄本,就是有关歙南龙舟会的文书。仲冬有报赛之举,大概是因为当时冬收既成,人多愉悦,所以要及时行乐,开场演剧。演剧一事,每年都派数人办理,演剧之前数日,村人即于溪滩中扎一高台,又聘“班次”前来演戏。所谓班次,是指徽州以演剧为营业者,每班约数十人,其人来往无定所,“一日夜演唱,多则七八日,少亦四五日”。这几天里,除店家外,手工业者都休业,学校皆放学,大家集中在溪滩上看戏,远近乡民也联袂而至,这大概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此外还有会场的布置,一般是十年一次。会场分为五隅,东隅以青色为标志,南隅以红色为标志,西隅以白色为标志,北隅以黑色为标志,中隅以黄色为标志。凡旗幡服色之类,皆以五色分之,相当壮观。会场中除戏台外,有祭场,有道场。其中,以演剧的戏台最为美观。此事从头到尾,要10天才结束。“村人每丁醵资一元,以成斯举,报赛则每人只醵资数十文而已。”在徽州,“五隅”的划分城乡皆有,可大可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它既是一种地理划分,又是一个迎神赛会的组织机构,并由此衍化而为处理超越单个家族的公共事务之基层组织,“五隅”或“五方”反映了地方基层组织较为原始的形态*参见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的保安善会与“五隅”组织》,(台湾)《民俗曲艺》第174期,2011年12月。。
(三)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
大凡风土志,对于一地民众的衣食住行均有细致的描摹。《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就有对当地“衣食住”的概述,其中的饮食部分这样写道:“村中居民,无不有田,又皆蓄鸡豚,以供不时之用,故仰事俯畜,无虞不继。市上米价甚廉,一元可得二斗余。肉只有猪肉一种,价一百数十文一斤。牛肉、羊肉,非购自他乡,不可得也。油有豆油、菜油、猪油、麻油四种,菜油、猪油多出自本地,豆油、麻油则来自外邑。他如面、盐等物,约三四十文一斤。豆腐价最贱,三四文即可购一大方,质佳、滋养之妙品也。村人每日率食三餐,以饭为主,面及他物佐之。夏日有食四餐者,即下午加食点心一道是也。点心之种类甚多,最普通者,为肉包、馄饨、烧卖、水饺、煎饼、煎菜、芝麻糕、白米糖、风车饼等物。要之,村人食物只求富厚,不求精美,此与杭、沪间人不同之点也。”这是对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描述,从中可见,市面上只有猪肉一种,牛肉难以见到,这可能与民间耕牛有限以及宗教信仰中对牛肉的禁忌有关。猪油可以自给,但在徽州,不少村落的猪油供给多来自外地。至于服饰部分,《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写道:
衣服多以布制,绝少用绸缎者,至于西装,则村人多未见之也。小儿夏日多赤足,不穿鞋袜,大人则多穿草鞋,或蒲鞋,以终日劳动,布鞋不适用也。大热之日,或袒其上体,或只穿坎肩,颇不雅观。天雨则戴箬笠,穿钉靴,或撑雨伞,踏木屐。冬日村民多戴瓜皮帽或毡帽,年老者间戴风帽,又有耳套者,以棉为之,旁缘以皮,严寒时儿童及老者多用之。此外复有一种御寒之物,名曰火笼,以竹编成,中盛炭屑,借以取暖,形与外邑之脚炉大同小异。女子多缠足,戴耳环,男子亦有戴耳环者,惟女子之耳环多饰以珠翠,累累如璎络,斯其别也。
上揭提及的服饰时尚,有不少已时过境迁。不过,“火笼”迄今在皖南农村冬季时还时常可见。另外,关于住宅,《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指出:“村中之房屋,较外间为宏壮,屋多为二层,墙以砖造,外披白垩,甚纯洁。屋中则栋梁柱壁,皆涂以漆。窗及格子门,则雕以山水花草及篆隶各字,甚美丽。而大门上之门檐,尤为他邑所罕睹,门檐为砖制,上雕云物花草鸟兽极工,多出自精巧砖匠之手也。村人于建屋之初,必先打地基甚深,下盛石子,上铺巨石,故能历久不圮,非若外间之以碎砖为墙,弯木作梁,一经风雨即有倒塌之虞也。”这是对徽派建筑的描摹,其中提及徽州老房子的粉墙,室内的梁柱、木雕以及门楣上的石雕等,均颇具特色。
此外,《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对当地的教育状况,亦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吴景超的记述上溯清初,下及民国。从中可见,当时由于茶业的兴盛,岔口教育的发展颇为兴盛:“自清初即崇礼教,重经学,雍、乾以降,有解元、举人数人,岁贡、廪生、生员十余人,武秀才亦有数人。科举废,学校兴,又设有师范传习所、国民学校,毕业其中者多设馆教授,称良师。”据《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记载:王茂荫“舞勺后,从双溪吴柳山游。先生为乾隆丁酉科江南解首,故名宿也,门下多积学之士”*曹天生点校整理:《王茂荫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舞勺之年,也就是13至15岁间,换言之,王茂荫是在岔口接受早期教育的*歙县民间流传着《王茂荫与鬼议钞》,说的就是王茂荫小时在岔口梯云书屋念书的故事。见金涛主编《徽州记忆》(四)“歙县”卷,第259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歙县岔口举人张云锦等人,依靠茶捐及私人捐助创办了双溪师范,不久改为大洲公学,这是清末师范教育早期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参见方光禄、许向峰、章慧敏等《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由于有着颇为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岔口人对于教育极为重视,当地的文风一向颇为炽盛。对此,吴景超分别叙述了岔口的私塾教育和小学。关于私塾教育,他指出:“私塾,村人称之曰蒙童馆,塾中之教师,曰蒙童馆先生。吾村有私塾三,其中教师,皆前清秀才,深于八股文者也,学生皆村中十五岁以上之小儿。一蒙童馆中,多者约二十余人,少者亦十数人。”接着对私塾的教材、行为规范、体罚措施、课程及教学安排等,作了详细的叙述。例如,关于私塾的教材,他指出,蒙童所读之书有深浅之分,浅者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深者为《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论语》《孟子》等书。塾师要求学生颇为严苛,故为后者所敬畏,“先生在,学生皆正目端坐,不敢作声”。而私塾教师之所以能够约束儿童,令其就范,主要的法宝就是戒方和烟筒两类工具。凡是“背书不熟,事师不恭,或互相争吵者”,教师就会以戒方或烟筒加以惩罚。“学生每日之课程至简单,早餐之前,入学诵旧书,名曰上早学。粥后,塾师即为学生上新书十数行,名曰上生书。生书须于午饭前背诵,不能者,每不许回家午餐也。饭后,学生皆习字,至三句钟,塾师乃教学生答对,答对毕,复温旧书,名曰念带书,须于晚饭前背诵”,这就是私塾课程的基本安排。对此,吴景超颇为不满,认为私塾的教育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除了私塾,他还记录了当地的新式教育:
村中有一小学,名曰大洲两等学校,此为南一区惟一之小学,开办于民国元年,校址在村西忠烈古庙,内有讲堂二,食堂一,厨房一,职教员办事室一。开办之第一年,有学生五六十人,现只二三十人耳。校中有职教员三,教授取启发主义,科目为国文、习字、算术、修身、历史、地理、理科、体操、音乐、图画等。校中经费不足,图画、标本、仪器,理科模型、器械等,皆未购置,以致儿童对于理科、地理等,皆不能十分领解,此其缺点也。授业时间,每日午前八点半起,至下午四点半止。校中无运动场,体操多至村外旷地上行之云。
作为新式教育的一种形式,小学与传统私塾的课程及教学安排完全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在皖南民间随处可见的旧书中,清末民国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各类新式小学课本为数最多,这些课本显然都是当年旅外徽州人寄回家乡的新式教材。关于这些情形,我们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商书信中时常可见。当年,除了教材之外,还有不少其他书籍也随之传入徽州。吴景超指出,岔口村中有藏书所数处,如梯云草堂、双溪草堂、山对旧书斋、霞峰别墅、自得山庄、能静轩和龙门草堂等,都是私家所设的藏书室。其中的梯云草堂,于咸同年间毁于火灾,及至民国初年,则以山对旧书斋、自得山庄藏书最为丰富。上述的诸多藏书室,“其中有用之书,无不具备,近今如名家小说、欧美小说,亦多购有”。揆诸史实,徽州素有藏书的传统,迄今在当地的古玩店中,仍可见到不少昔日庋藏古籍的红木书箱。及至近代,藏书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而是扩及晚近的小说等。文中提及的名家小说、欧美小说,显然都是由外出经商者购置寄回徽州的。这种情形,自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正是由于茶业的兴盛以及茶商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当地有不少人外出接受新式教育,成为知名的学者、文化人,吴景超本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结语
(一)吴景超曾主张模仿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蒲司(Charles Booth)所开创的“社会调查”之研究方法,他认为,中国的社会调查应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调查,另一方面则是城市调查。其中,农村调查可以依靠学生,由于中国当时的学生大半来自农村,他们可以返回家乡调查自己的村庄*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147页。。事实上,早在1919年,吴景超就在家乡岔口村做过类似的调查,以往学界尚未关注到他所撰写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第四种国家的道路》书末附录有“吴景超先生主要著作”,其中并未列有该文。,以至于有人认为“尽管吴景超积极提倡社会调查,他自己却没能亲身参与”*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148页。。而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对徽州村落的调查颇为全面,涉及传统村落社会的诸多侧面。
吴景超后来著有《社会组织》一文,强调在做家庭历史调查时,“写时要多叙述事实,少发挥议论”。关于家庭,他提出下列的调查提纲:家庭的背景,与大家庭及宗族的关系,家庭组织,家庭仪式,家庭经济,家庭教育,家庭冲突,将来的家庭等*吴景超:《社会组织》,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七种,《民国丛书》第四编第十卷;谷迎春、杨建华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1928年8月,吴景超以《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一文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它是吴“对本土关怀、实用主义立场以及实证性研究态度的兼顾”*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筑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这篇论文中,吴景超使用了包括中国移民问题联合调查特别委员会报告在内的政府报告、国会会议记录、法庭报告、法律文书、报纸杂志和政府统计数据等资料,又做了大量的调查与访问,收集了生活史以及个人传记。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偏重实际调查以及经验性材料使用的方法,是吴景超承自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心得*陈新华:《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不过,倘若我们对照《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就不难看出,有过先前村落调查的经历,对于从事更复杂社会的研究显然极有裨益。
(二)如果我们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以来较长时段的社会调查史料,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的学术价值。有关徽州经济、风俗的调查,比较系统的资料是清末刘汝骥编纂的《陶甓公牍》——光绪三十三年(1907),徽州知府刘汝骥委派当地士绅组成“统计学会”,将各类事项分民情、风俗和绅士办事习惯等类撰说,并经刘氏本人汇核编订。由于各县的调查出自众手,彼此的认真程度不同,故而史料的详略及其价值也颇有差异。不过,这是清末以前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的文献中最为详尽的一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徽州的民俗文化和社会变迁弥足珍贵*关于《陶甓公牍》,笔者最早作了颇为详尽的研究,发掘出该书的历史民俗研究价值。王振忠:《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陶甓公牍〉之民俗文化解读》,载《徽学》2000年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民国初年,根据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各期日本学生的实地调查报告,汇集而成的《支那省别全志》第12卷《安徽省》*[日]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大正八年(1919年),台北:南天书局,1988年。,共分安徽省总说、开市场及贸易、都会、交通及运输机关、邮便及电信、主要物产及商业惯习、工业及矿产、输移入品、商业机关和金融货币及度量衡十编,调查颇为细致,并附有一些相关的地图。该书原为日文,安徽省图书馆另藏有民国传抄本《安徽省志》*关于该书,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张小坡副教授的提示,特此致谢!,即该书相关部分之中译本。1930年代,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有《京粤线安徽段经济调查总报告书》(为“铁道部经济丛书”之一),该报告涉及旧徽州一府六县中的绩溪、歙县和休宁。稍后,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曾在皖南各县调查,先后刊印了当涂、芜湖、宣城、广德、郎溪、歙县和休宁七县的调查报告。其中,对1934年歙县、休宁的详细调查,收入《中国经济志》第2册*“民国史料丛刊”第9种,1935年版;台北:传记文学社印行,1971年影印。。这些,都是较大县域范围内的调查报告。至于专门的个别村落之相关调查,也有少量的案例。例如,《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作者,就以皖南僻远山乡的一个村落为视点,勾勒出晚清民国时期民间社会的风俗画面*参见拙文《一部徽州族谱的社会文化解读——〈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此外,曹诚英撰有《安徽绩溪旺川农村概况》*《农学杂志》特刊第三种,1929年。。这些,都已为学界所认知。不过,吴景超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则是尚未得到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岔口是歙南的一个山僻小村,此一村落,即使是在晚近的民国《歙县志》中,也仅作为地名出现过数次,倘若没有吴景超留下的这一风土志略,我们对于当地情况可能几乎一无所知*关于岔口村的情况,只在一些民间文书中稍有反映,如《歙县民间诉讼案卷集成》曾提及:“当今恶俗,惟赌为甚,惟岔口之赌风为太甚,若不禁赌,难免无事也。”。吴景超对故乡的调查,最终是以“风土志”的形式来展现。“风土志”的写法由来已久,“《禹贡》为风土志所自始,至《职方》而加详”*光绪《严州府志》卷3。。后来,“风土志”也成为方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民国时期,“风土志”的撰写逐渐由传统方志学的描述转向具有一定近代社会调查意义的资料,其部分撰写者也由传统士绅转向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这使得“风土志”的内涵更为丰富和细致。在这方面,吴景超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三)20世纪前期徽州村落调查资料,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当代村落文化的保护亦颇具借鉴意义。
1949年以后,徽州村落调查资料相对较少。管见所及,最为重要的成果当推1950—1951年的土改调查资料,此一成果目前见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所编《安徽省农村调查》*“华东农村经济资料”第4分册,1952年版。,其内容主要包括《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徽州专区农村情况概述》《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歙县潜口区西山村牛租调查》《祁门县莲花塘村公堂、祠、会调查》《皖南山区林山概况》《休宁花桥村竹、木、茶山调查》《黟县际村区卢村竹山、柴山调查》《歙县长陔区南源村树木情况调查》和《徽州专区黄山风景区情况调查》等。此外,数年前由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主持的“徽州的宗教、社会与经济”[Religio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in Huizhou (Anhui),2008—2011]项目,通过与徽州当地人的合作,以田野调查所获的口碑资料和地方文献,希望客观描述1949年以前徽州的传统经济、民俗与宗教。此一成果具体体现在由他与笔者合作主编的“徽州传统社会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歙县里东乡传统农村社会》等卷。这些成果,不仅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前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校:张朝胜黄琼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3.016
作者简介:王振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70017)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3-013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