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两个儿子:一个寓美,一个自尽
朱文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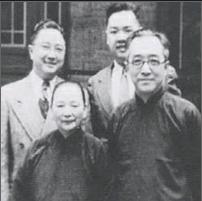
胡适与江冬秀1917年12月30日结婚后,1919年3月16日长子胡祖望出生,1920年8月16日女儿胡素斐落地,1921年12月17日次子胡思杜来到人间。江冬秀真能干,生产周期实打实十五至十七个月,不过四年时间,使得“无后为大,著书为佳”的胡适教授家室派生成一个五口之家,于是诚如他自己所说:“‘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无后主义”是胡适哲学中的一个板块,如今与生育、养育子女的现实主义发生撞击,便爆出一连串父亲主义的耀眼光彩。
家书絮叨,都是父亲的爱
胡适“糊里糊涂”地做了父亲,是怎样“负起一部分的责任”来的?因为他是大教授、大学问家、大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一年复一年地奔波于他的事业,兼程海内外,因此他的教子方式有异于他父亲手把手地教识方块字,除了让儿子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外,主要在书信中体现他的做父亲的责任。这在胡适家书中,语录式的诲导与常人般的父爱,俯拾皆是。
胡祖望堂堂皇皇地来了,哺育带养的责任全落在江冬秀身上。八年后,胡适迁家到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9号。1928年他就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从这年2月开始,江冬秀带了7岁的小儿子胡思杜,负胡适之命,去老家绩溪主持修筑祖坟,于是家中只剩下胡适、祖望父子俩了。只懂做大学校长和研究学问的胡适,如何与9岁的儿子做伴呢?他在信中对太太说:“从你走后,我把那篇红楼梦(按:系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写好了。共写了两万六千多字,三夜都两三点钟才睡……祖望寂寞的(得)很,第二天晚上哭了……”做父亲的同时还念着小儿子呢:“小三(按:次子思杜的小名)怎么样,他喜欢家里吗?”(1928年2月20日)过了三天(2月23日),他写信时又问:“小三喜欢徽州吗?”在这封信中胡适还告诉江冬秀,她的妹妹和徐新六(胡适好友)太太“怕我们饿死在替工厨子手里,常常送菜来吃,可感之至”。应好友丁文江太太的邀请,将于24日携祖望去苏州做演讲。
在苏州的日子里,胡适、祖望父子俩相处得很融洽,玩得开心,他尝到做父亲的滋味。他们住在丁太太任教的苏州小学里,受到很好的招待。“廿五日祖望跟丁大哥去上了一天课(按:苏州小学),他很喜欢那学堂,先生们也喜欢他。下学年似可以把他送到苏州去上学”(致江冬秀函,1928年2月29日)。
1928年2月带胡祖望去苏州时,发现他喜欢丁太太那个小学,于是到第二年暑假末,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将才10岁的儿子送去,过独立的寄宿读书生活。1929年8月离开上海时,不知道他夫妇俩怎样为儿子准备行李,又千叮万嘱的;送到苏州后,也不知道是如何难分难舍的(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从胡适的“苏州一号”(即第一封)给儿子的信(1929年8月26日)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抑制自己情感,下这个决心的。
祖望:
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你妈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离开家庭是最好的办法。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感觉用功的必要。
人格的独立在于自小就有意识地自觉地操练“独立的生活”,胡适在这封信中说——
自己能供应自己服事(侍)自己,这是独立的生活。饮食要自己照管,冷暖要自己知道。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功课做的(得)好,是你自己的光荣;你做错了事,学堂记你的过,惩罚你,是你自己的羞耻。做的(得)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的(得)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这是你独立做人的第一天,你要凡事小心。
“合群的生活”,就是处世立身,关系到做人的一辈子。这方面胡适是深受慈母教诲的,胡适将这一“基因”传授给儿子——
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能不想想怎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来好。人同人相处,这是合群生活。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以妨害别人的事。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人。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
谈到功课,胡适似乎延伸自己当年上海求学时“物竞天择”的精神了——
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个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但志气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功夫里;千万不可放在嘴上,千万不可摆在脸上。无论你志气怎样高,对人切不可骄傲。无论你成绩怎么好,待人总要谦虚和气。你越谦虚和气,人家越敬你爱你;你越骄傲,人家越恨你,越瞧不起你。
如此嘱咐儿子为人处世,岂不是胡适本人做人的写照?胡适生命深处,有一个了不得的光点,就是“徽州朝奉”的精神。绩溪是徽州府六县之一。自古以来,有称徽州地方人穷志不穷,“徽州人,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努力混出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朝奉”来。徽州人自立自强,自重自尊,做人韧性很大,认准一个目标,百折不挠攀进。胡适尚在美国留学时,禀母家书中曾保证道:“吾乡俗话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我现在真是自己保重了”(1918年2月23日函)。现在,胡适从箱底翻出这句箴言,送给儿子——
儿子你不在家中,我们时时想着你。你自己要保重身体。你是徽州人,要记得“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在这封给儿子编号“爸爸苏州第一号”的家信中,胡适还向儿子提出了六条保重身体的要点,诸如“不要买滩(摊)头食物”“不要喝生水”“不要贪凉”“有病寻医生”“防脚气病”“每日早起吃麦精一匙”,絮絮叨叨的,要他“千万不要忘记”,并加了重点符号。写到信的结尾,已是8月26日落下夜幕时分了,这位“无后主义”爸爸在灯下又长啸一声——
儿子,不要忘记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你,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胡祖望18岁时,中国全面抗战开始。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离北平南下,参加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江冬秀携次子胡思杜随叶公超、梁实秋等逃出北平,迁居天津。因为日寇轰炸天津南开大学,就读南开中学的胡祖望南下到南京,和父亲会合,一起住北平路69号“中英文化协会”会馆里。但是到9月初,蒋介石已要胡适和钱端升、张忠绂三学者以非正式使节身份赴美欧开展宣传中国抗日、争取外援活动。9月11日胡适携祖望和钱端升、张忠绂,由南京到汉口,原来想让他留在武昌珞伽山等候武汉大学二次招考,读旁听生。后来胡祖望到了长沙,成为流亡到长沙的南开大学(按: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一年级学生。
1939年8月,胡适出使美国还不到一年,胡祖望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工学院航空机械专业。胡适还写信给住在绮色佳的韦莲司(胡适在美国的女友),要求她照顾祖望。他十分关心大儿子的学业,与妻相隔万里,总是越洋告诉儿子的功课成绩。胡祖望换了环境,开始一个学期,功课“不很好”;第二个学期,七门课中“四门过75分,三门及格”;到了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居然有三门功课可以‘免考(平日的分数好,平均约有85分,就可以免去大考)。我想你听了也很高兴”(1941年2月27日函)。
但是在对儿子(指长子祖望)的家教上,夫妇显然有分歧了。对待传统观念上,江冬秀动辄责怪,以致造成隔阂。大概源头还是在1934年“蒙古王公出殡”那件事上,胡家的汽车受阻,接受胡适无神无后主义思想的胡祖望直愣愣地对江冬秀说:“妈,你死了就埋,绝不摆仪仗队阻碍交通!”江冬秀听了吃不消了。
正因为胡适将祖望当作“朋友”,祖望康奈尔大学毕业后,面对中国战后动荡的局势,对他也不怎么要求,让他与自己一起留在美国,直到1946年3月胡祖望先行返国,6月胡适离美回国主北大。
蒋介石溃败到台湾前后,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驻泰国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1953年迁居台北以后,往返于台湾美国间,曾任台“驻美经济机构”代表。这期间,他与韦莲司沟通,承袭了胡家第三代人与韦家的世谊(胡母冯氏与韦老太太通过信)。1959年7月,韦莲司曾写信给胡祖望的太太曾淑昭,就他们的独生子胡复患小儿麻痹症住院表示慰问。1960年胡祖望一家定居美国。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逝世后,韦莲司发江冬秀唁电、寄信,表示沉痛哀悼。后来,韦莲司得知胡适大殓丧礼的日子,送花篮和表示要赠款作胡适著作英译出版的基金,也是通过致胡祖望的信表达的。
中美建交后,台在美国的“官方机构”被撤除,胡祖望就在美国与朋友合股经营一家工商服务公司,他的一家就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栋花园别墅里。他的一家仅三口人:夫人曾淑昭,重庆丰都人;儿子胡复,独身主义者。胡祖望的晚年生活是平静安逸的,于2005年病逝于华盛顿,享年86岁,是胡铁花后人中创高龄纪录的第一人。
胡祖望夫妇只有一个儿子,因幼年患小儿麻痹症,留下跛足后遗症。祖父胡适是很喜欢这个孙子的,1960年1月9日,儿媳曾淑昭带了胡复到台北南港看望胡适,胡适发现他母语中不会讲国语(普通话),更不会讲徽州话,只会讲广东话。爷爷委婉地说:“可以用广东话作基础,将来可念中国古音,因为广东话中还有许多古音哩。”儿媳说:“孩子教不好。”爷爷说:“小孩子教不好,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缘故。你可以每天教他两个字,时常要他温习,没有教不好的!”
大概是胡祖望父子真的承袭了胡适“无后主义”精髓,胡复先生至今还没有结婚。他早年就读皮伯岱大学,学钢琴;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为美国华人中的一颗耀眼的星,但胡家(文化运动)皇皇事业,就因此没有下文了。
撰文演说,
老牛舐犊为这般
小三(胡适对思杜的昵称)一直跟在江冬秀身边。
胡适为小儿子读大学的问题伤脑筋了。没想到小三像自己当年那样,喜欢政治,而江冬秀是极力反对的,胡适就说,“小三要学政治,也不要紧。小孩要学什么,说不定后来都改变了”(致江冬秀函,1939年7月31日)。他要冬秀转告,既然学政治,还是国内为妥,“我想叫小三到昆明去上学。小三要学社会科学,应该到昆明去准备考北大、清华(按:即西南联大)。我此时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去美国上学。所以想小三跟一位朋友到昆明去,跟着泽涵(指著名教授江泽涵,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暂住,考进学堂后搬住学校”(1940年3月20日)。
紧接着他又同胡思杜对话:“你是有心学社会科学的,我看国外的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未必比清华、北大好。所以我劝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着舅舅,预备考清华、北大。”“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到内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况。”(致胡思杜函,1940年3月21日)但思杜就是想去美国留学。这一来,胡适十分尴尬了。他的大使月薪只有540美元。1938年12月他心脏病发作,住院77天,医疗费用四千多美元都是由好心朋友帮助垫付,欠在那里的。1939年9月祖望来美国读书,“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1200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不然,大儿子就得半路上退学。一个儿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儿子,就更不自由了。(现在要想从国内寄美金给儿子留学,是万万不可能的)”(致江冬秀函,1939年11月14日)。翌年(1941年)5月,受胡适之托照管胡思杜的竹垚生(胡适至交,时任上海泰山保险公司经理)去信说:“小二(按:指思杜)在此念书(按:东吴大学),无甚进境,且恐沾然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因此胡适还是让思杜越洋去了美国。
小儿子既然来了,胡适就得设法张罗。首先把他送到费城的海勿浮学院(HaverfordCollege)去就读。该院的院长康福教授(Prof.W.W.Comfort)是胡适当年康奈尔大学的法文教师,两人友谊甚笃。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筹款。“小三来了,至少四年,我要走开(按:指大使职卸任),就得替他筹划一笔学费、用费,那就不容易办了。就得设法去卖文字,或者卖讲演,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于是胡适目的明确地“从现在起,要替他储蓄一笔学费,凡我在外面讲演或卖文字收入的钱,都存在这个储蓄户头,作为小儿子求学费用”(致江冬秀函,1941年4月10日)。他希望小三用功读书,多挣学分,利用“三个暑假(期)学校”,把四年课程用三年半读完毕业,这样就节省一个学期的学费了。但是胡思杜并没有读好,后来转学到中部的印第安纳大学,用钱低了一半,但一个学期内他根本没有去上课,其间还到一家健康学校去减肥,把父亲汇给他的钱全部去跑马跑光了,欠了一身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差点被警察传去,被胡适的一位朋友救了出来,发现他的口袋里全是当票,其中一张是胡适回国时留给他的一台打字机的当票。胡思杜在美国读了两个大学,都没有毕业。
古城诀别,月有阴晴圆缺
胡思杜于1947年10月12日回国。胡适没有允许到他做校长的北京大学教书。山东大学历史系来聘他,胡适知道是因为自己的面子关系,只同意让他进该校图书馆工作。直到1948年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即将开始,平津各大学、研究院所罢课、罢研、罢工风潮此起彼落,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潮怒吼震撼古城,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胡思杜由青岛回到北平。8月30日,胡适安排“思杜今天到北平图书馆去做工”(《胡适日记》,1948年8月30日)。但父子相聚才不过数月——此际正是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动政权崩溃的前夜——便分离了,而且成了永诀。
1948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野战军联合发动平津战役,到14日,北平城已被团团围住,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谈判的条件,行将起义。14日,胡适寄出答复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函。蒋介石派来专机接他去南京。15日,胡适偕江冬秀决定离平南下。但他们身边的小儿子思杜呢?在北平读辅仁大学的程法德印象中的“思杜舅舅此时期沉默寡言,看书很勤,老气多了”,他明确表示要留在北平,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让我迎接北平解放,同时看管东厂胡同家中父亲的120箱书籍。江冬秀十分难过,立即整理了一皮箱金银细软给儿子。说是将来结婚时好派用场。这天下午6:45,胡适夫妇在傅作义派来的副官和军人的护送下,只带了26回《石头记》手抄本和正在考证的《水经注》,匆匆乘车到南苑机场,上了飞机,至夜10时,抵达南京机场。
北平解放后,1949年9月,胡思杜被安排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编在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组,与黄炎培的侄子黄清士同一个班。据说原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也在同一期学习。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浓浓的政治氛围熏陶下,胡思杜要求进步的愿望很强烈。据他舅舅江泽涵教授(1949年8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对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博士回忆说,思杜“去(华北革大)学习前,他把冬秀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等存放在我们这里。等他学习、改造结束后,他来把这一皮箱东西取走了,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北革大”结业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执教中国革命史。这时他也常去泽涵舅舅家,“说要与他父亲划清界限,并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他上交母亲留给他的东西,就是向共产党组织表示他的决心。他还写了批判他父亲的文章”(江泽涵回忆)。
胡思杜所说的“批判父亲文章”,是指他的结业“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不知何方决定,又通过什么渠道,在1950年9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发表了。
诚如胡思杜在该文中所说,他是“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来批判父亲胡适的。
胡适当然也读到了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公开反应,只是将该文剪了下来,贴在自己9月27日的日记页上,并附批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也许他感到奇怪,该文见报前十余天(9月11日),已迁居到美国纽约的江冬秀曾收到胡思杜的信,告诉她“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并希望父亲“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写如此有人情味的信,肯定是在那篇批判文章之后,因为文章是在“华北革大”改造后的“思想总结”。
1957年夏秋间,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中,胡思杜上吊自尽了。
胡思杜是哪天自尽的?据保存下来的“遗书”抄件碎片显示,“九月廿一日”,这个日子是胡思杜遗书的最后一行,那么他告别人世当在1957年9月21日这天,或者稍后一些时间。
胡思杜的死,在美国,以后到了台湾的胡适夫妇并不知晓。胡适是挂念小儿子的。1961年4月30日(星期三)在与秘书胡颂平谈大陆他熟悉的学者(在运动中)挨整时,谈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来信过,恐怕是免不了(挨整)”。过了半个月,适逢母亲节,胡适立即联想起1946年6月8日美国的父亲节,他乘船返国途中,打电报给小儿子。
“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胡适深情地说:“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傅斯年)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说着,早把四年前《对我父亲》那篇文章抛在一边了,哪知“这个儿子”的冤魂何时能飘忽到父亲跟前!
1979年胡思杜获得彻底平反,不过他的遗骸已无处可寻了。
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年会新老院士酒会上讲话劝酒时猝死。江冬秀闻讯从台北牌局赶回南港,抚尸恸哭不止。举丧期间,胡祖望从美国回来奔丧,江冬秀劈头问他:“小三知道了吗?可接丧报?”祖望浑身一阵寒颤,觉得再也隐瞒不下去了,低声说:“他,他先父亲离世了!”江冬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你,你在说什么?”“我是在美国听大陆上来的人说的,是真的。思杜弟弟自尽了。我们怕你太伤心,一直没敢告诉你……”江冬秀再一次昏厥,继之用徽州方言又哭又号。小三是会讲家乡话的,胡适为此赞扬过他。
胡祖望曾间接向在北大的江泽涵打听小三去世的情况。但那个尚噤若寒蝉的年代,有海外关系是非同小可的。直到“文化大革命”阴霾过去,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江泽涵才与胡祖望恢复正常联系。这时胡思杜已获平反昭雪了。胡祖望在一次返台扫墓时,在“胡适公园”墓园内,父母坟侧畔,为他那位枉死的胞弟半埋了一块“思杜碑”。“魂兮归来,小三弟弟,你生前没有筑巢,身后就到这里来安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