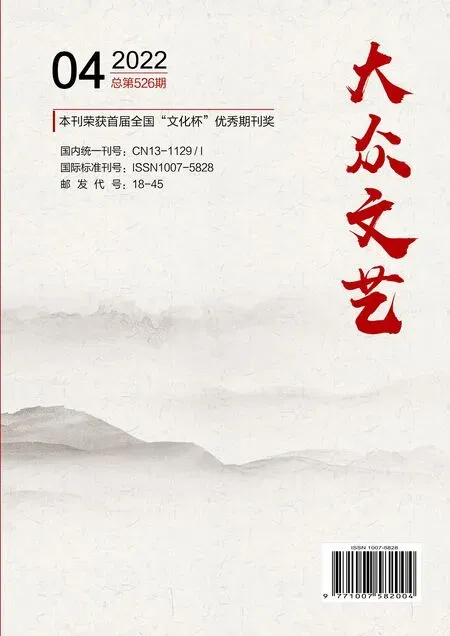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红楼梦》的悲剧美学
夏翩翩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570228)
《红楼梦》的悲剧美学
夏翩翩(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570228)
摘要:悲剧性是《红楼梦》最突出的美学效果,它在“见—生—入—悟”四个阶段的循环往复中,完成了美学上的悲剧效果。本文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来分析《红楼梦》的悲剧过程,从而体悟曹雪芹笔下“万境归空”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美学境界。
关键词:红楼梦;悲剧性;儒;道;佛;美学境界
悲剧有一种摄人心魂的魄力。叔本华曾提出三种悲剧类型,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悲剧。它的悲剧非偶然因素,而是那几乎无事的悲剧:冯渊对英莲的一见钟情却奏响了他的死亡之曲;王熙凤忌惮贾瑞便毒设相思局,使他命丧黄泉;尤三姐爱慕柳湘莲,他却仅凭流言蜚语拒绝婚事,最后落得一个挥剑自刎,一个冷入空门。
俞平伯在《紅楼梦简论》中提出:“紅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他强调了“色”与“空”的重要性,却忽略了“情”,有失偏颇。其实“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是不可分割的。起初人从万物皆空看见世间万态,这是“见”;其次人在世间万态中萌生了情,以此来维系世间万态的和谐,这是“生”:再次人把情赋予世间万态,一切便都有了情,这是“入”:最后透过有情的世间万态悟得万物皆空,这便是“悟”。而这一空通过色的呈现和情的维系,得到空的飞跃。《红楼梦》悲剧美学的最高境界是“空”,而要达到“空”的境界,必少不了“情”的维系。小说正是通过见-生-入-悟四个完整的过程的循环与归元,它的悲剧美学才跃然于纸上。
一、见:从顽石到玉石
贾宝玉是女娲氏炼石补天多出的顽石,在天上,他被造物主女娲氏抛弃,听说红尘中的荣华富贵,便乞求一僧一道携他去瞧瞧。刘再复曾说:“这是他经历的第一番‘空’,有了这次空,才想到人间来见色—女娲用五色土构造的色世界。这一经历便是‘因空见色’。”后来通过冷子兴与贾雨村的闲谈,作者道明了顽石的归宿:天上的顽石到人间变成玉石后,与贾宝玉合二为一,并记录下了他的红尘往事。再看贾宝玉,他是美玉的化身,又是曹雪芹理想的寄托,主要体现为第一,容貌的绝美。他“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有如倾城佳人。第二,行动的叛逆。长到七八岁便说起了孩子话:“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第三,思想的乖僻。对于情感,他更倾心于木石前盟;对于人生,他不走经济仕途之路,把官吏讥为禄蠹;对于世俗观念,他不仅颠覆了男尊女卑的理念,还以身践行,但最终还是被末世湮没。
因此,从顽石到通灵宝玉,一个天上,一个人间;一个无才补天,一个不容于世;一个凡心蠢动,一个偏僻乖张;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一个因空,一个见色。
二、生:从木石前盟到金玉良姻
王国维曾说《红楼梦》“壮美多于优美”,这里的壮美指各种悲剧美的总称。而小说的壮美则最集中地体现在从木石前盟到金玉良姻的演变过程中。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贾宝玉则是神瑛侍者,木石前盟的湮没是小说最为悲戚的毁灭,由宝黛的三世情缘逐步完成。
小说开篇讲述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第一世情缘。他们一个是神仙,一个是仙草,因灌溉之情结缘。后来绛珠草脱换成绛珠仙子,对神瑛侍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此为第二世情缘。正是这段情缘,才有了还泪之说的第三世情缘。有了前世姻缘的牵引,他们自然心息相通。不想薛宝钗出现了,但黛玉要的是与宝玉惺惺相惜的“情”,宝钗要的是芳龄永继的“姻”。宝黛的超脱世俗的爱情不为家族、社会、时代所容,相反,宝钗的合理之情才得到众人的拥护。初发美好的木石前盟,成了贾宝玉梦中的追求,而金玉良姻却成了禁锢他的枷锁。
从木石前盟的主动萌发到金玉良姻的被动接受,贾宝玉在这两种感情的转变中,由色生情,以大悲剧收场:黛玉泪尽而逝,宝玉空自悲戚,宝钗独守空闺。曹雪芹想让这块无才补天的顽石来末世补情,但他失败了,因为封建的末世容纳不了心心相惜的爱情。
三、入;从梦魇到无梦
《红楼梦》中专写梦的地方很多,有诗意的梦,也有让人措手不及的噩梦。据统计,全本小说大大小小的梦总共有三十二处。无论是太虚幻境还是人间的大观园,都可以纳入曹雪芹的大梦之中。“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是经历了一番人情世故后,了悟了色,抵达空的大梦。而大梦由众多小梦构成。所谓“传情入色”,便是入梦,在大大小小的梦中,人世的聚散离合纷呈上演。
甄士隐是小说中第一个登场的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骨肉分离、家离子散,最后遁入空门。曹雪芹利用甄士隐的小梦,同样隐射了大梦。小说最后一梦,也暗示了大梦的结束。小说以甄士隐的梦为开端,复以贾雨村的梦为结尾。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是很重要的一个梦。正是在梦里,他了解了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等金陵女子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的梦是沉重的,然而无梦的悲剧才最可怕。梦的结束,就是悲剧的结束。黛玉泪尽而逝之后,宝玉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想在梦里找寻她,却再无梦了。在贾府分崩离析之后,该去的去了,该离的离了,最后连做梦的寄托也没有了。正是这无梦的凄凉,为宝黛的爱情悲剧收了场,也完成了传情入色。
四、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荷尔德林说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曹雪芹寄希望于书中人物,想要为他找到生生死死的现实生活之上的诗意栖居的“空”,经历了世俗生活里的食、睡、爱的绵延不息,超脱生与死的困境,走向澄明之境,诗意地栖居在人世间。
《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与林黛玉有世俗的一面,也有超脱志趣的一面。在大观园里,他们结诗社、作诗词、猜灯谜,一起谈禅悟道,便有了《葬花吟》的千古绝唱,有了《芙蓉女儿诔》的哀婉悼念,也有了“无立足境,是方干静”的了悟。世俗的生活被他们过得有滋有味,这不正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吗?
但是这种诗意栖居的大梦在封建末世是昙花一现的,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在《红楼梦》这部“悲剧中的悲剧”里,父权、皇权、族权像无形的利爪,扼杀了每一个自由的灵魂。曹雪芹建造的临时天堂——大观园,为众儿女提供了短暂的诗意栖居,然而,当绣春囊事件一出现,那些四面而来的利爪便乘机拽住了欲(玉)的把柄,贾府这个显赫百年的大族,一层一层地被褪去浮华的表层,最后剩下一颗空心。
曹雪芹以儒理,窥视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以佛眼,勘破了世间繁华、过眼云烟;又以道心超越了俗世纠纷、生生死死。《红楼梦》全书弥漫在悲凉之雾之中,在一个又一个美好生命被淹没之后,我们看到了生的无奈,还有死的超脱。这便是了悟了生死之后,历经了“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悲剧体验,抵达了“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最高悲剧境界。《红楼梦》的美是诗意的,又是毁灭的,“见—生—入—悟”既是诗意美的始发因子,也是悲剧美的诞生结果。在这个完整的循环过程中,《红楼梦》完成了它在美学上的悲剧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2]刘再复.红楼梦哲学笔记[M].中信出版社,2010.
[3](清)曹雪芹.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夏翩翩,硕士研究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性别诗学。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