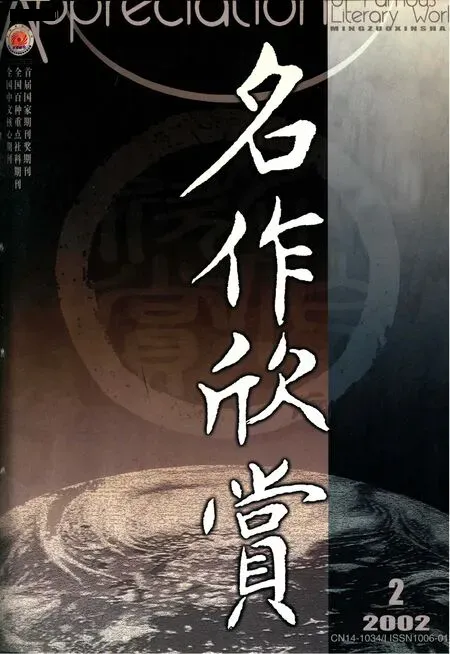废名用典与小说的涩味儿
⊙郎显奇[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废名用典与小说的涩味儿
⊙郎显奇[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废名的小说是对中国固有文学的展开,他辨析中西方文学,找到中国文学的“散文”特性与典故结合的写作路数。废名写独创性的小说,志在变庸俗之极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写作标准,兴起简洁生辣的文章。
关键词:废名小说散文用典涩味
一
关于废名小说的晦涩问题,反复被论及,这反映出废名小说的晦涩依旧值得讨论。然,从现有的相关成果看,尚未有论者从废名的创作心得来探讨其晦涩。本论文将根据废名的创作心得,探讨他小说的晦涩问题。
废名曾写道,读他的作品“不要轻易说,‘我懂了!’或者说,‘这不能算是一个东西!’真要赏鉴,须得与被赏鉴者在同一的基调上面,至少赏鉴的时候要如此”①。这句话,一则自我辩护,护他所开创的文学园地的合法性;一则告诫,告阅读者应持的鉴赏态度。废名写作《桥》的同时,也写《张先生与张太太》“于史家有用处”的作品。废名谈到这两类作品:前者的寿命当然要长过后者,而且不知道要长过几百千年呢。②《桥》属于“为艺术而艺术”,《张先生与张太太》则属“为人生而艺术”。他对后者不看重也可知了。那么废名因何倾心于前者?为了尽可能与废名保持“同一基调”,我们有两个方式接近他:一则他的创作心得,一则他师友知人论文的评论。
1934年11月15日,废名在《人间世》发表《新诗问答》,他追踪旧诗时指出:中国的文学是诗学传统,甚至《红楼梦》,曹雪芹开篇第一回用“贾雨村言”仍是作旧诗。而早期的白话诗,也是落入“旧诗”的行伍。他认为:旧诗之所以成为诗,乃因为旧诗的文字,若旧诗的内容则可以说不是诗,如是散文的。③他因此认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文字层面是诗,但是内容看去,是散文。④废名似乎对新诗,尤其是西方的诗歌有领会,然他没有形成理论描述。胡兰成也称赞道:“冯文炳的谈新诗,五四运动时代新诗是人与物的新相见,立地解脱了文字及定规了的感情。如禅宗有扫地掷石触竹的一声……冯之论诗自是写诗的基本。”⑤
废名以为,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才算诗歌,而古代,这样的诗属于例外。李商隐“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的意义不是散文的,是诗的。尽管他不明示,然而比对《枫桥夜泊》与《登幽州台歌》的文字,张继的诗确像散文,陈子昂的诗蕴含着现代诗的意味。看得出,废名的辨别非常敏锐。辨别“旧诗”之后,他指出“愈为旧诗的佳作亦愈为散文的情致,这一点好像刚刚同西洋诗相反,西洋诗的文字同散文的文字文法上的区别是很少的,西洋诗所表现的情思与散文的情思则显然是两种”。“新诗要别于旧诗而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⑥在这篇文章里,废名根据内容与文字,把散文与诗的文体泾渭分明。
他谈中外文学的小说文体差异,说“中国文学里没有史诗,没有悲剧,也不大有小说,所有的只是外国文学里最后才发达的‘散文’。于是中国的散文包括一切,中国的诗也是散文”⑦。他这一见解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这一卷时,就收下《桥》里七篇。废名的朋友同是观:
“如以小说论本书,便不免有许多缺点,但读者当它是一本散文集,便不失为可爱的书,从其中可以发现许多零星的诗意。”“这本书没有现代味,没有写实成分,所写的是理想的人物,理想的境界。作者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构造一个乌托邦,本书所表现的就是这个。”⑧
《现代》书评评道:“废名先生实在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卓绝的散文家。”“因为《桥》,与其说是小说,实际上却不如说是连续性的散文。”“就是在废名先生的短篇里寻,有严谨的短篇小说结构的实在很少。”⑨
另外,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废名于《响应“打开一条生路”》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篇章赞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不赞成完全走西方的道路。那么他将以什么文体写小说呢。
废名所走的小说道路,是以中国固有的文学为基体。⑩他的诗文小说,采取“散文包括一切”去写作。但是废名的展开还不止于此,他认为“中国文章里(包括诗)没有故事。没有故事无须结构,他的起头同他的收尾是一样的”⑪。照这么说,他要从中国固有文学里开辟出小说的一条路来,做没有故事没有结构的小说。废名将怎样做没有故事没有结构的小说呢?
二
废名几次谈到用典故,这对理解他的小说很有必要。他说“外国文学重故事,中国文学没有故事,只有典故,一个表现方法是戏剧的,一个只是联想只是点缀。这是根本区别,简直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中国文章里如有故事,则其故事性必不能表现得出,反不如其典故之生动了”⑫。废名认识到中国文章里其妙处全在用典。
然而具体是怎样论述以典故创造小说,废名也没有进一步明示——废名论中国文学的话非常简单,但是意思正确,包藏着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废名赞扬用典,他说典故使得文章生发意义,反过来,文章有意义了,文章自然成典。他讨论以典故作小说的典范,是崇庾信的《谢滕王赍马启》:
某启:奉教垂赉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谨启。
废名解析道:第一句等于题目,接着是无头无笔的文章,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文章,不多不少的文章。所用的全是马的典故,而作者的想象随着奔流出来了。柳谷句,张掖之柳谷,有石自开,其文有马;“紫燕”是马名。接着两句,“流电”“浮云”俱系马名,“争光”与“连影”则是想象,写马跑得快。争光犹可及,连影则非真有境界不可,仿佛马在太阳底下跑,自己的影子一个一个的连起来,跟着跑了。那么争光亦不可及,作者的笔下实有马的光彩了。笔者并不是附会其说,只看作者另外有这样一句文章:“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他的句子确不是死文章了。画眉之暇,走马章台;饮酒之欢,长驱金埒,可不作解释。读者试看,这样一篇文章不是行云流水吗?不胜过我们现在一篇短篇小说吗?他没有结构而驰骋想象,所用典故,全是风景。他写马,而马的世界甚广,可谓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连桃花源也做了马的背景了。在任何国家的文学里都没有这样的文章。⑬
尽管废名没有成文专论用典故作小说,然案例阐释却很清楚了。废名著《神仙故事(一)》《再谈用典故》二文说:用典故做辞藻,以辞藻见性情。刘西渭也指出废名小说是“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的抽象的绝句。⑭正是废名“用典”作辞藻,故而“句与句间最长的空白。他的空白,也最耐人寻味”⑮。由刘西渭的洞察,废名用典故作小说的语言、结构浑然一体可见。由点缀的字句,于所设空白之间,任读者联想,联想所适,小说的情节、结构、故事在读者的联想里完成。
孟实先生指出:“如果以陈规绳《桥》,我们尽可以找到许多口实来断定这是一部坏小说;但是就它本身看,虽然不免有缺点,仍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作品。”“《桥》有所脱化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看惯现在中国一般小说的人对于《桥》难免隔阂,但是如果他们排除成见,费一点心思把《桥》看懂以后,再去看现在中国的一般小说,会觉得许多时髦作品都太粗浅,浪费笔墨……读《桥》是一种很好的文学训练。”⑯这是对用典作小说很好的总结了。
从废名的创作心得来梳理他对小说的理解,一为散文就是一切,一为以典故作小说。废名的创作,是高级的抽象的“梦”,是中国固有小说现代化的一种出路,它开拓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品种与认识。
三
废名不只以典故写风景、故事、结构。在《再谈用典》里他说,像他这样白描一派的文章,可以不用典故,却用典故来想象;作文叙事抒情很难写的地方,每每借助于典故;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用典故才能表现出来;有时用典故简直不是取里面的意义,只取字面。⑰
据此,典故对废名创作的作用甚大。1957年作《废名小说选·序》,他说:“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的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⑱许多理解认为,这句话的重点在作者节制语言,或者放在以唐诗理解小说。然而,古诗多用典,就废名自己创作心得看来,所谓用绝句写小说,实际也就是用典故写散文,以典故作散文的辞藻、故事、结构。
那么,废名缘何以这样的方式写作?为何在小说中蒙上一层涩味儿?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文学写作普遍形成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比如“革命文学”,普罗作家把一些虚构的人物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⑲这种越来越简单而且整齐的创作方式,烂熟至极。然而废名的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晦涩”,乃是反抗当时流行的“于史家有用”的小说写法使然。故而知堂先生认为,造成晦涩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思想深奥或思想混乱,一是文体的简洁或奇辟生辣。知堂先生把废名归于后一种,以为“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俗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⑳于是废名用典造成小说文体颠覆,一反读者的阅读秩序,颠覆我们对“故事性”小说的接受惯性。然而,与其说废名颠覆读者对小说的惯性认识,不如说这是废名探索了中国文学的一条现代化之路。他相当明白中西小说的路数,他以中国固有文学写现代小说,因而把小说文体反得彻底,涩味儿十足。废名的创作具有开拓性,所以不能简单称之为“晦涩”。假如从“典故”进去,或者能胜任这坚实的风清月白——涩味儿。
①②废名:《说梦》,王风编:《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5页,第1152页。
③④⑥废名:《新诗问答》,王风编:《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6页,
第1326页,第1326页。
⑤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⑦⑪⑫⑬废名:《谈用典故》,王风编:《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9页,第1459页,第1467页,第1460页。
⑧灌婴:《桥》,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⑨《〈现代〉书评》:《桥》,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⑩所谓基体,是指中国固有的展开,也即指传统。见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5页。
⑭⑮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第85页。
⑯孟实:《桥》,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179页。
⑰废名:《再谈用典故》,王风编:《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5—1467页。
⑱废名:《废名小说选·序》,王风编:《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7页。
⑲艾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艾芜全集·第14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⑳周作人:《〈枣〉和〈桥〉的序》,见《苦雨斋序跋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郎显奇,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 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