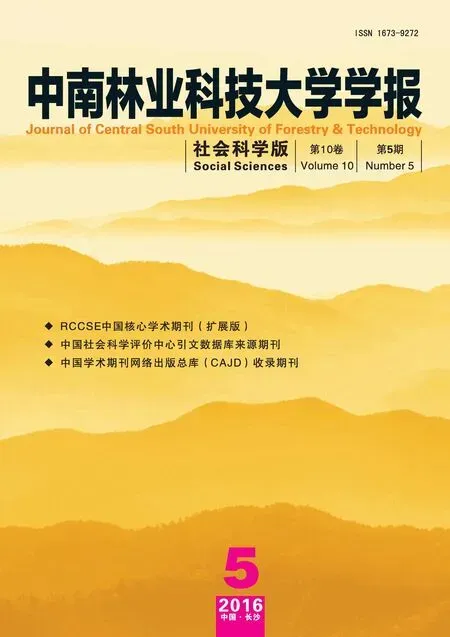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及其伦理基础探索
蒲昌伟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头 515041)
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及其伦理基础探索
蒲昌伟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头 515041)
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长期论战,这给国际环境法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理论上的困惑。澄清这个问题,并进一步确证出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及其伦理基础是很有理论和现实必要性的。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这个理论逻辑之上的。作为深具广泛共识性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正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最完美的体现,构成了国际环境法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基础。
国际环境法;伦理基础;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
一、问题的缘起
作为价值合理性之根据的伦理实体是指具有必然性的伦理关系体系,而伦理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关系,具有客观交往的规则系统。[1]这里的“客观交往的规则系统”就是作为规范的伦理。所谓伦理,通常地讲,是指人类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过程中经过反思所形成的具有价值合理性的原则与规则。也就是说,伦理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应该根据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和尺度来处理这些关系的问题,而维护和调整这些关系所需要的价值准则需要转化为具有自律性的道德和具有他律性的法律这两种规则体系,以调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规范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否则,应然的社会伦理秩序就无法得以实现。伦理秩序的生成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做好自己的本分,自觉地根据伦理原则和规范要求约束自己的言行和欲望。当然由于社会个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能力差异巨大,仅仅通过道德规范来约束社会个体的言行、欲望来维护应然的伦理秩序的生成会明显难以为继,势单力薄,需要将维持伦理关系体系存在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规则继续上升至法律规范,即通过这些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规则的法律化,来维持社会伦理关系体系的持续存在与发展。这里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就是被一些学者所言的底线伦理或社会道德。[2]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调整社会关系的应然伦理价值准则首先表现为道德,然后其中的一部分再表现为法律。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部分反映伦理价值准则的社会道德规范被法律化、制度化了;另一部分同样反映伦理价值准则的以彰显个人品德、操守的善恶准则,仅仅成为了不同的社会个体进行道德实践的自我抉择。所以,我们在提到伦理的时候,往往就不得不提到道德,也不得不提到法律。尽管有相当的学者将伦理道德连在一起不加区别地使用,但是伦理与道德毕竟是有区别的。伦理针对的是社会共同体,更强调客观方面;道德针对的是社会个体,更强调社会个体的主观内在的操守方面。[3]法律源于习惯和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就懂得把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重复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4]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法律,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相同的,均是特定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所以也无论法律的外在形式化特征如何明显,技术性因素如何膨胀,法律总是以伦理为归属,体现着某种伦理精神,追随着某些道德目标,遵循着某些价值准则的。[5]法律的伦理性是永恒的,伦理是法律形成、生长之根基。[5]法律与伦理之间的内在逻辑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为本文即将展开的论述,提供了逻辑思路。
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新分支自1972年诞生以来,其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可谓蔚为壮观,一日千里。追踪和考察国际环境法学的发展历史,笔者研究发现,环境伦理日益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价值来源与支撑的事实已经为学界所肯定。著名的国际环境法学家林灿铃教授直接把环境伦理作为国际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在中国建立起了逻辑严密的国际环境法学科体系,[6]并引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这门学科的研究之中。法律只能编纂和规范已经存在的公共道德,而非界定或改变某种道德。法对伦理主要是一种被动的反映,而不应是先在构建。从发生学上看,法是对既有伦理的确认和保障,总是先有伦理要求而后才有相应法律的产生。国际环境法的产生逻辑也一样,鉴于环境伦理的各种学说异彩纷呈,观点各异、交锋不断,笔者不得不提出如下问题: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以及伦理基础分别究竟应该是什么?相应的环境伦理规则又是如何得以法律化呢?本文接下来将围绕这些问题做一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二、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
国际环境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法的新分支,从理论的视角看,它的理论依据是环境伦理学。但是,自从环境伦理学科产生以来,有关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各派各家的伦理学说就一直处于多样化发展之中,这本来是一门学科繁荣的标志,但是,各种学说之间的长期争论不休,当然会影响这门学科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从而反过来又会制约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厘清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是什么的问题,无疑对研究和揭示国际环境法产生和发展的伦理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意识地推动相应的环境伦理规则法律化实践来促进有效地解决国际生态环境问题为己任的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的。
(一)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学依据应该是什么?——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或其他?
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学依据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抑或属于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是其他?伦理就其全部本质而言,是无限的责任和义务。履行这种无限责任和义务需要人类约束和限制自己的欲望与行动。我们为什么对环境负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为了谁的利益?自然环境有内在价值和权利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在环境伦理学发展史上催生了两类伦理学说: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说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说。尽管如此,这两类学说无论被学者演绎的多么完善、深邃,也似乎无法拿出解决当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案。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实践中成为了危害生态环境的帮凶。人类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和实践都极为有限。在实践中人类整体利益往往表现为以个人利益或者群体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目前来看,还仅仅是一个理念而已。所以这些假借人类利益之名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最大化正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就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而言,由于它仅仅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味消解人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忽视了人与人的关系,在理论逻辑上,在社会实践中一直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而始终无法走出书本,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制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问题,而非环境本身,而一味地给予并无反思能力、道德能力的自然万物以拟制人格及相应的制度设计,而不从人的方面切实地解决问题,在笔者看来实在是属于南辕北辙之举。在如何处理和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对关系方面,我们谁也无法否认“人”这个种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因为没有了人的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的维护和追求,今天的一切所谓文明之争,甚至各种社会问题的之解决都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法的调整对象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至于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面对自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自我约束以及所应有的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和态度也必须转化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后,才能进入法律领域。国际环境法也不例外。基于此,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所依据的环境伦理学依据既不可能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也不可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而只能是其他,即超越的环境伦理观。[7]
(二)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之理论逻辑及其内涵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尽管就本体论视角看我们谁也无法否认人是自然的产物的客观事实,因为人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我们人类自身的一切包括身体本身都属于自然界,[8]也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9]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它的自然属性,更在于它的社会属性即人的社会实践性,正是因为人的社会实践性,才使得人猿揖别,从此,人成为了具有主体意识的存在物,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的“人是符号动物”。也正是因为人具有这种主体意识,人与自然之间才形成了一种对象性的关系。[9]那么,这种对象性的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实质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人与自然的辩证的统一,是人道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即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8]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人类社会关系产生的过程,其前提条件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所有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属性上的人的本质都不复存在。逻辑至此,作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伦理理论就绝不可能是以前的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而必须有所超越,成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新型的伦理观。在这种超越的环境伦理观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就显得特别关键。因为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性特点致使人的活动不只是一种生命活动,而更是一种有目的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人能够运用理性的力量去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来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展自由。人是这个宇宙中唯一有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天赋和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的能力的一个物种。这正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机理所在。人类这个物种有能力,也有责任超越自己狭隘的物质利益追求,担负起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的神圣伦理职责和使命,否则就辜负了“人为天地之秀,万物之灵”的美誉。
至于超越的伦理观的真正内涵如何,如林灿铃教授所言,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环境伦理学,只能是一种能同时接纳和包容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雍容大度的开放的环境伦理学。据此,笔者认为,所谓“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性,在吸收、整合它们各自的优点的基础上以追求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和谐共生为终极目标的过程中人类经过反思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认为,人具有理性、能使用符号和明智地利用他周围的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良知和神经,可以担当起地球利益的代言人和其他物种的道德代理人的神圣角色。这种伦理观的主要观点包括在笔者看来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人是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代理人,能够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第二,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而非技术和经济问题;三是追求可持续发展,坚持代际公平原则;第四,人与非人类存在物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大自然的本质是维持各个物种的存在。维护作为人的生存根基的生态系统的生存,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不可抗拒的使命。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正是环境问题对人类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中心论非人类中心论之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所达成的最大共识,理所当然地能够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学依据。[7]
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既包括了人与自然的伦理观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观,无疑是指导建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人的利益和需要永远是所有这些伦理关系的基础。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强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本位地位的同时,并不否认其他非人类自然物种同样具有它们各自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那种以为人类可以任意处理自然万物的观念是愚蠢的,也是错误的。[10]在人与人之间,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在坚持作为全人类整体利益体现的生态环境利益优先(比如:环境法上有个环境优先的原则)的同时并不否认现实社会中各个层次的社会主体的局部的或暂时的利益,只不过,人类作为“类”的整体利益应当是人类所追求的共同的根本的价值目标。[10]处理二者的关系应然态度应该是:人们的各种实际具体的价值目标、具体利益追求的实现必须以不危害作为人类整体利益体现的生态环境利益为底线。[11]
总之,追求以某某为中心的伦理观都是要不得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于人与社会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都是这个大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应该成为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必将成为环境保护乃至于治理全球环境问题这一世界级难题的理论指南,从而充当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的准则和参照系。
三、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体现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可持续发展伦理
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不可能是形形色色的环境伦理学学说或理论,只能是具体的具有共识性的伦理规则。因为法所反映的伦理,只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社会伦理,而不应是停留在学术著作中有待实践检验的某种新奇思想。法律是社会利益的衡平器,不是各种伦理观念的试验田。一种新的伦理观点只有当普通人开始接受时,才能发展起来。[12]可持续发展伦理正确地处理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体现了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具有广泛的社会实践性和高度的国际社会认同度。该伦理原则一经产生就迅速被国际环境法律化,并不断地推动国际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基于此,笔者言及至此的结论是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就是可持续发展伦理。
(一)可持续发展伦理体现的正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思想
可持续发展伦理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在新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发展起来的用以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完美的体现。关于这一点,其实无需特别证明,从前面关于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内涵的相关论述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可持续发展既是人也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意味着人类需要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可持续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再生有限度性,如果人类不坚持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就可能崩溃而不能源源不断地支撑人类持续生存这个大厦。可持续发展伦理是在更全面、更合理的意义上既对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肯定,关怀人类现实的和未来的利益,[13]同时也顾及到了自然本身的规定性对人类的基础地位。在环境伦理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先后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观和超越前二者的环境伦理观。在这期间,冠以某某中心主义的这些多元的环境伦理观之间又长期争论不休,热闹非凡,但结果对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无济于事,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威胁。其实,冠以某某中心的环境伦理观是非常不可取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有学者为了调和二者的矛盾,提出了“人类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即坚持双中心或多中心环境伦理观。在笔者看来,这不但没有解决上述二者各自的弊端和缺陷,反而使得问题更乱、更无厘头。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最大的突破就是去中心化,兼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可持续发展伦理兼顾了自然的正当要求和人的正当需要,一经产生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并被迅速法律化而成为国际环境法坚实的无可置疑的伦理基础。人类是可持续发展关注的中心,任何具体战略与措施,都必须围绕着人的利益展开,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伦理也同时坚持“自然的尺度”应该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道德底线。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伦理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14]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最完美的体现。
(二)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可持续发展伦理的经典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5]随着看似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内涵和丰富的构成要素。就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内涵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伦理的目的是维护人的正当发展利益。它包括当代人之间和世代人之间的发展利益,其核心是公平与和谐,[7]即人与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在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的分配方面的公平,以及在人与自然方面的和谐共生。据此,可持续发展伦理并不否定经济增长,只是这种增长必须是良性的、健康的,具有可持续性。[16]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性,生态环境是脆弱性。要实现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最高利益,当代人类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应损害后代发展所需依赖的自然生态基础。[17]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人类正当需要的满足。人性的贪婪、物欲的横流是生态环境危机的人性根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要,人类自身必须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诸如人类基本的生存资料的需要满足、人类可持续的生存发展利益的需要满足又是人类这个种的延续所必不可少的,因而也是正当的。然而,需要的满足必须接受公平原则的衡量和制约,即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原则,否则,这个人类需要的满足就是一句空话。代际公平必须以代内公平的实现为前提。国际社会要努力调整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大对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最落后国家的发展援助的力度,消除世界贫困、寻求共同发展的伦理原则。为此,在国际社会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贫穷和不公正往往导致生态和社会危机,[15]已经成为生态恶化的首要原因。
第三,可持续发展在外延上应该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良好是基础,[18]经济发展不能以危害环境为代价,始终坚持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所有国家共同发展,同时关注代际公平,不能损害或危及后代人的发展。[19]总之,可持续发展伦理内在地坚持代际公平原则,始终维护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相对稳定性,从而持续供给后代,以满足人的可持续发展利益需要。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自诞生以来,就在《里约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权威文件中得到有力的体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所包含的内在要素也得到了最为完整的呈现。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所包含的要素包括实体上的要素和程序上的要素两个方面。
实体要素主要体现在《里约宣言》中的原则3至原则8及原则16。具体包括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权、在当代人内部和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追求资源的公平分配(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以及通过适用“污染者付费原则”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等。
程序要素体现在原则10和原则17。具体包括环境影响评估、获取信息以及公众参与决策等。这些程序要素都有使决策合法化的功能,并且,如果使用得当的话,它们也能够提高决策的质量。[20]
从这些要素的名称上来看,可持续发展伦理都充分体现了在坚持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基础上,人类应如何具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伦理使得一国对于自己国内环境的管理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更使得国际环境法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有了具体的路径取向。这些要素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具体规范标准,是人类进一步把它们转化为国际环境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
(三)可持续发展伦理法律化实践
作为效力最强、被普遍实施的社会规范,法只能体现主流的、成熟的、符合多数人意志、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社会伦理的要求。[12]当前,如何将可持续发展伦理转化成具体的国际环境法律规范和制度,正是国际环境法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挑战所面临的迫切任务。[21]事实上,作为国际环境法律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起点的可持续发展伦理一经产生,就已经在国际环境法制领域获得了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伦理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具有法律含义的概念。[21]
穷人中的环境问题,通过政治不稳定和动乱的传播,也会影响富人。[23]环境危机无人能够幸免。地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各个国家在生态环境上相互依存而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要逐步消除贫富的差别,则有赖于各国共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1]从1982年的《世界自然宪章》承认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到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到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和《可持续发展实施计划》,以及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宣言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22]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宣言和决议等纲领性文件,这一切都证明了可持续发展伦理已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作为一种已普遍化了的社会道德,而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在法律化实践方面,从已有的国际条约的实证考察发现,可持续发展原则已经转化成为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一。[6]国际环境法的其他原则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密不可分,后续行动和其他原则都是指向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是促进和确保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原则。[23]如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目标,那么其他几个原则是手段和方法。有学者指出,在国际环境法的地位中,可持续发展原则可以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原则,地位远高于其他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既是国际环境法的出发点又是国际环境法实施的落脚点。[24]笔者深以为然,国际环境法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25]比如,只有一个地球原则体现了自然资源有限的思想;预防原则体现了如何更经济、更成本效益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共同责任原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伦理中的代内公平思想;国际合作原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实现方式的思想等。[6]
就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实体要素的法律化而言,很多国际环境条约已明示地或默示地承认可持续发展原则或者将可持续发展伦理具体转化为具体的条约规范。如:1980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条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4年《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条约的相应条款都基本上是可持续发展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款的明证。
就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程序性要素的法律化而言,可持续发展伦理在《越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1997年的《国际水道公约》、2001年生效的《奥胡斯公约》以及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损失分担的序言和原则草案的标题和案文》等国际法律文件得到了切实的规定和实施。随着这些条约的实施与遵约,实现可持续发展伦理就有了程序上的法律保障。正如有学者指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标志着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的一种国际环境法律体系得以兴起,而非简单地产生了更多的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法律规则。《里约宣言》对于环境领域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的贡献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其重要作用。[21]
综上所述,从“可持续发展”伦理理念国际认可度、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持续不断的法律化实践、世界各国、国际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法律确信以及国际法院和WTO法律实践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司法适用,[26]等等证据来看,可持续发展伦理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国际环境法律化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同时,国际社会也必须尽快拟订战略,促使各国从目前的追求破坏性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转而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27]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内涵的界定还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可持续性的参照因素及其测度标准还有待进一步澄清。尽管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评估各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报告并决定今后的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地位,各国政府是否承担国际法义务以确保国内的发展政策符合可持续性的国际环境法要求仍有待国际社会的继续努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成员为了履行国际环境法义务,已经自觉地把可持续发展伦理确定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通过立法加以强制推行。
四、结语
人都具有自利性的一面。利益包括多个方面,其中经济利益是最基本的,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在西方叫做“理性经济人”。经济利益的获取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在某些人看来,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就是财富的增长;国家的发展就是GDP的增长,但是,无论财富的增长还是GDP的增长,是有一个假设前提的,那就是自然资源的无限性、环境容量的无限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平衡。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地球或许能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显然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贪念。[28]基于利己目的而存在的“搭便车”的心理,往往导致环境保护方面的“公地悲剧”,继而陷入“囚徒困境”。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发达国家只顾自己的环境美丽,却把污染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29]凡此贪念及不正义的社会实践的矫正都急切需要可持续发展伦理的约束和指引。
国际环境法作为一门国际法新分支,其一经产生就对传统的国际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提出了诸多挑战。其挑战的根源就在于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以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为理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这一伦理基础兼顾了法律维持秩序和实现环境正义的双重目的,一经被人类认识到就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并迅速引领国际环境法的蓬勃发展。如今可持续发展伦理不仅转化成了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还转化成了各具体国际环境条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条款。可持续发展伦理国际环境法律化的理论与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尽管可持续发展伦理在可法律化的进程中还不完善,但对于国际环境法的伦理基础而言,它是合适的、恰当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在坚守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本真的同时,很好地兼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将指引人类走向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也将引领国际环境法的继续发展和繁荣。
[1]高兆明.黑格尔“伦理实体”思想探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4):50-55.
[2]何怀宏.底线伦理的概念、含义与方法[J].道德与文明,2010(1):17-21.
[3]高兆明.制度公正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4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538 —539.
[5]陈秀萍.论法律的伦理性——变革时期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6:28.
[6]林灿铃.国际环境法(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
[7]裴广川,林灿铃,陆显禄.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2.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2.
[9]汤建龙.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控: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在价值学视野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10]陈映霞,李佑新.从类哲学的观点看人类中心主义[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28-31.
[11]肖中舟.人类中心主义辨义[J].人文杂志,1997(3):19-23.
[12]巩固.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对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思考[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8.
[13]黄 嫱,赵纪新.对人类中心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之解读[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2007(1): 22-23.
[1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80.
[15][印]S·R 乔德赫瑞.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权的基础[J].黄列译, 外国法译评,1998(3): 8-21.
[16]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13.
[17]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5: 452.
[18][奥地利]彼得·维特曼.生态可持续发展[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tk/dtzt/2014/31360/31369/Document/1377818/1377818.htm.2015-11-15.
[19 佚 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分析[EB/OL].中国改革论坛网站: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111/t20111130_128813.htm.2015-11-15.
[20][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国际法与环境[M].那力、王彦志、王小钢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2-90.
[21]丁明红.WTO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的法律基础:可持续发展原则兼析与环境有关的典型案例[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4(10):387-404.
[22]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王正平,金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6.
[23]徐祥民,孟庆全.国际环填法基本原则研宄[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57.
[24]潘抱存.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宏观司考[J].法学杂志,2000(6): 1-4.
[25]唐 洁.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和实践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4:17-18.
[26]肖金发.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及其立法实践[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4-28.
[27]邵沙平,余敏友.国际法问题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314.
[28]颜孟坚.当今人类反思的若干问题[EB/OL].http://www.xici.net/d24948000.htm.2015-09-04.
[29]刘建涛,贾凤姿.人与自然、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在私有制社会中的异化——生态视镜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54-58.
Explora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Foundation and its Ethic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PU Changwei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515041, Guangdong, China)
It has been debat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ba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To sum up, the long-term debate mainly has remained between Anthropocentrism and non -Anthropocentrism.This adds the theoretical confusion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It is very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dispensable to clarify this issue, and further confirm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foundation and its ethic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transcendence”.As the most perfect embodi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transcendence” ,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thical rule, which is a deep and broad consensus,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 logical basi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Ethical basis;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transcend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thic
DF969
A
1673-9272(2016)05-0025-07
10.14067/j.cnki.1673-9272.2016.05.006 http: //qks.csuft.edu.cn
2016-09-30
蒲昌伟,副教授,博士;E-mail:Pcwfmr@163.com。
蒲昌伟.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及其伦理基础探索[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0(5): 25-31.
[本文编校:李浩慧]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湖南农业绿色发展对策
- 生态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困境与对策
- 中国农村土地整理绩效研究:问题、进展及方向
- 智慧旅游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