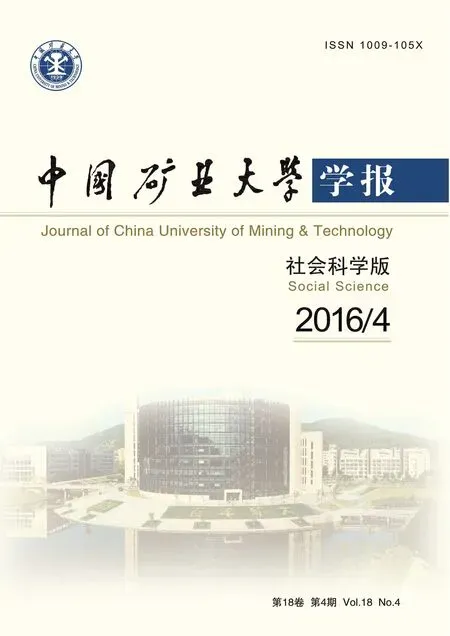经典的还原、阐释与重构
——孙康宜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述论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86)
经典的还原、阐释与重构
——孙康宜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述论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86)
摘要:孙康宜与她的美国汉学家同行们一道,将大量明清女性文学作品译介给西方学界,并借鉴西方性别理论的框架、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对中国明清时期女性文学文本中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诠释,从而重构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世界性经典意义。作为当代美国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孙康宜在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思路、方法及成果,无疑对于中西学界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研究;美国汉学;孙康宜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原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1946年随家人迁往台湾。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1968年移居美国,曾获英国文学、图书馆学、东亚研究等硕士学位,197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孙康宜研究领域非常广阔,仅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从六朝诗、唐宋词到明代文学史以及明清女性文学等等,广泛涉猎而且成就斐然*关于孙康宜教授的研究全貌,可参看宁一中、段江丽.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上下)[ J].文艺研究,2008(9、10).。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自明末至晚清,女作者多达3915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诗人,曾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多达2300多位[1]。孙康宜于19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明清文学、接触到这些作品,她惊讶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然而奇怪的是,近代的中国文学史却大多忽略了这个庞大的女作家群对中国文学传统所做出的贡献。一般人只知道唐代才女薛涛、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等,而曾经流芳一时的明清女作家诗词集,却一直被埋在图书馆和收藏家的手中;除了特殊的研究者以外,几乎无人问津。不幸的是,即使是对明清女性作品有过阅读经验的人,也常常以偏见的态度来评价这些女诗人。结果是,他们的观点更加深了文学史中所存在的性别歧视。”[2]针对这一现象,孙康宜在此后的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女性文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方面,积极发起明清妇女文学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组织编选与翻译相关文集[3];另一方面,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以英文及中文在北美及中国大陆、港台发表,在国际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孙康宜关于明清妇女文学的中文版论文主要收集在三本论文集中,它们分别是:《古代与现代的女性阐释》[4]、《文学的声音》[5]、《文学经典的挑战》[6]。其中,前两本在台湾出版,后一本在大陆出版,部分论文同时见于台湾版和大陆版的论文集中,有的题目略有差异。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散见于其他会议论文集或者期刊中,如《老领域中的新视野——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见于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7],《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见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8],其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9]则可以说是对明末清初著名歌伎柳如是的个案研究。由以上著述,大体可以概括孙康宜在明清女性文学方面的成就和特征。
孙康宜于1990年开始,和苏源熙(Haun Saussy)一起发起美国汉学界一项前所未有的翻译大工程,组织了60多位美国男女学者合作,编选与翻译《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诗歌与评论》,并于199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edited by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孙康宜说到编纂该书的目的及意义时说:“无形中我们走进了世界性的女性作品经典化(canonization)行列,希望通过考古与重新阐释文本的过程,把女性诗歌从边缘的位置提升(或还原)到文学中的主流地位。”[6]99-100事实上,孙康宜与她的美国汉学家同行们一道,将大量明清女性文学作品译介给西方学界,并在西方性别理论的框架之下,又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对明清女性文学文本中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诠释,从而赋予了研究对象以世界性经典意义。作为当代美国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孙康宜在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思路、方法及成果,无疑对于中西学界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 明清女性文学的“考古”挖掘
在《妇女诗歌的经典化》一文中,孙康宜指出,与现代人所想象的相反,传统女诗人并没有受到当时人的忽视。在中国古代,“即使一般女人的地位不高,但才女的文学地位却是很高的”[6]101。孙康宜还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指出,传统中国女诗人与西洋女诗人的地位构成了明显的对比。在西方传统中,写诗被视为“神职”(holy vocation),女人因为不具备神职人员的资格,所以一直扮演听众的角色,很少有机会展露诗才。在中国,“从上古以来,女诗人占有了一个主流的地位,尤其是数千部的诗歌选集登载了不计其数的女诗人作品。其数目之多、篇幅之广确是世所罕见。”[6]101
孙康宜曾在《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文中对中国崇尚妇才的传统进行梳理,又在《何谓“男女双性”?——试论明清文人与女性诗人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从六朝以来,文人就发展了一套才女观,以为理想的佳人除了美貌以外,还必须具有诗才。而这种才女观到了明清时代终于演变成文人文化的主流,促使明清妇女文学达到空前的繁荣。”[7]305此外,在《传统女性道德权力的反思》[10]、《道德女子典范姜允中》[11]等文章中,孙康宜还对中国传统女性才德及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中国古代女性所拥有的道德力量是福柯所谓的“权力多向论”中的一种权力,它可以使女性在逆境中获得一种“自我崇高”(self-suplimation)的超越感和权力感。
对于明清妇女文学繁荣的原因,孙康宜认为有女性识字率提高以及出版业发达等方面的原因,不过,更强调是男性文人与女性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孙康宜一再指出,与英美女诗人的遭遇不同,中国女诗人的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受到男性文人的排斥,反而得到男性的鼓励及表扬,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尤其突出。在明末,很多男性文人公开支持、赞赏女性诗才,他们帮助女诗人出版各种各样的诗词选集,并为她们撰写序跋,典型如:钟惺竭力提拔王微,称其为不世出之才;陈继儒亦称赞王微之诗“即须眉男子,皆当愧煞”。邹漪称赞名妓柳如是为“诗博士”。著名才女叶小鸾之父叶绍袁则在他为妻女等人精心编辑的《午梦堂全集》之序中肯定女性德才色“三不朽”之说,重申妇才之可贵。在明末,沈荃、葛徵奇、赵世杰等人亦极力标榜女性诗才[6]101-102。其中,赵世杰甚至认为,女性是由“灵秀之气”所构成,其作品优于男性。还有,周之标收录晚明14位女性词人的作品结集分两本出版,均题名为《女中七才子》,以比拟明代文学中著名的前后七子[6]190。这些文人不但收集当时女性作者的作品,而且对过去遗失的女性文本进行考古,比如说宋代最负盛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就是靠明清文人的努力采辑与考古,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较完整的李清照作品集[6]305。到了清代,更有袁枚延续晚明传统、“百般回护闺秀,力陈其作诗填词之权”[6]270。即使是与袁枚在女性才德观上有激烈冲突、以保守卫道著称的章学诚,“也并非皂白不分,一味攻击闺秀诗词”,只是从“内言不出阃外”的妇训出发,反对闺秀“炫才”[6]269-271。因此,孙康宜认为,明清时期流芳一时的女性文本的整理、出版及传播,主要是男性文人的贡献[6]304。
孙康宜指出,明清男性文人为了提高女诗人的地位,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其一,把边缘和主流逐渐混合为一,具体做法是,将女性的作品与《诗经》《离骚》放在一起讨论。其二,强调女性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认为女性本身具有一种男性文人日渐缺乏的“清”的特质。而来自男性文人的嘉许又对才女们的自我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本身就有诗的特质,于是她们纷纷努力表现出一种文人化的倾向[6]86-91。
对于这些男性文人不遗余力提携、奖掖女性诗人的原因,孙康宜亦从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context)中进行了探析。她认为,六朝以来崇尚妇才的传统发展到明清时代,以突发的方式演变成为文人文化的主流,促使明清妇女文学达到空前的繁荣。深层原因在于,当时一些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男性文人厌倦了八股文、经学及其他实用价值,转而发展出一种重情、尚趣、爱才的新文化观。在这种新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他们一方面崇尚妇才,迷醉女性文本,把编选、品评和出版女性诗词的兴趣发展成一种对理想佳人的向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才女尤其是薄命才女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认同感,“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的风气”[6]84。也就是说,明清时期,许多缘边才子在薄命才女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影子,进而将女性特征奉为理想诗境的象征,“于是文人文化与女性趣味合而为一,而男性文人的女性关注也表现了文人自我女性化的倾向”[6]305。
孙康宜也注意到,“明清女诗人并不完全依靠男性来提高她们的文学地位”,她们自己也积极参与了妇女文学经典化的构建,一方面,努力编选女性诗词集并自觉出版自选集,她们“不但希望得到当代读者的赞赏,也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永垂不朽”[6]103。如柳如是,她在双十年华,就刊行了处女诗集《戊寅草》,后来又编成了一部女诗人的诗选,被合刊在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里[9]70。她们不只是从事诗集的编纂,有的还继承李清照的传统,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6]191。另一方面,明清女诗人“喜欢通过写作来表达真实的自我”,“更以一种自我呈现的精神在序跋中很郑重地为自己奠定一个特定的”、“与过去的才女形象有所不同”的形象。在明清以前,一般女诗人并无出版自选集的习惯,她们的“诗集”大多是身后才由他人收集而成[6]103。在《何谓“男女双性”?——试论明清文人与女性诗人的关系》一文中,孙康宜比较具体地分析了明清女性诗人的“文人化”倾向,并将这种现象称为“男女双性”(Androgyny,亦译“雌雄同体”),以强调女性在精神上及心理上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认同。孙康宜还指出,在明清女性诗人中存在的“女扮男装”、“儒雅化”以及“书痴”现象都是女性“文人化”倾向的表现。前者如柳如是,她曾经打扮成儒生公子独自前往虞山拜访大名鼎鼎的钱谦益,一时传为佳话;她亦曾与陈子龙及其周边的松江文人群体自由往来、吟诗作词,不仅被诸子视为红粉知己,更引为政治同党[9]85。后者如钱惠纕、张柔嘉,分别有“不妨人唤女书痴”、“且乞闲身作壁鱼”的诗句,以书痴、书虫自诩,“用读书来诠释生命的价值”[6]307。
值得注意的是,孙康宜还澄清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五四”以来很多人都误以为传统中国是一个被“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统治的时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正是产生于大量才女出现于文坛的明末清初之际,“所以口号的产生不但没有反映出妇才受压迫的现象,它反而显示出一些卫道士对才女文化日渐兴盛所感受到的威胁感。”[11]102
综上,孙康宜对明清女性文学的“考古”工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到明清时期,在一些开明的男性文人和女性诗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六朝以来的崇尚妇才的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女性文学空前繁荣;并且,由于男女双方的互相靠近、认同,创造了一种可称之为“男女双性”或者说“雌雄同体”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文化形态中,男性对女性诗人有高度的认可,女性诗人对自身的才华和价值亦有高度的自信。毫无疑问,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在主流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 明清女性文学的多维阐释
据孙康宜介绍,《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精选了一百二十多位才女的作品,选录原则有“多样化”(diversity)的考虑,所以,作者身份包括歌伎、家庭主妇、史学家、画家、隐士、革命家、女遗民、寡妇、为情而死的痴情女子、经年感伤的弃妇等等,通过这些作品可以重新认识女性文学所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6]104。孙康宜从中选取一些代表性作品,从不同角度做了较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一) “才伎”与“名媛”的不同传统
在《阴性风格或女性意识?》一文中,孙康宜以柳如是与徐灿为典型代表,对明清女性文学中的青楼伎师与名门淑媛两种传统进行了阐述。
孙康宜指出,晚唐与宋代的诗人往往将充满瑰丽艳情的作品交给伎师们吟唱。到17世纪,许多青楼伎师真正成了在书画、诗词或是戏曲方面有所专精的艺术家,她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出版诗词作品,出入于江南各大城市文人荟萃之所,并常与男性文人结下浪漫姻缘。柳如是正是这类才伎的典型代表。她不再像宋代歌妓那样只是为男性顾客表演吟唱,而是以自己的声音吐露出“灵秀之气”。她以平等的地位与陈子龙往来赠答,以“自我表意铺陈”的方法,描写她自己如浪漫戏曲之女主角般的景况与感受。柳如是与陈子龙“借着运用当时戏曲中格式化的文学规例(literary convention),将自身转化成了作品中互赠情诗的男女主角。这在词的传统中是一项大胆的创新”,因此,他们“可说是挽救了词这个没落的文类”[6]194,而他们创造的云间词派也成了当时文士模拟的范例。
孙康宜从活动范围、文学境遇、词作主题等方面对青楼伎师与名门淑媛进行了对比。
从活动范围看,青楼伎师常常穿梭于“复社”“几社”等男性文人的文学会社,透过身旁的名士友人来建立自我意识;闺阁词人则经常和家族中的亲属共组诗会,并常常互为师徒关系,如徐灿就是当时浙江最著名的女性文社“蕉园诗社”成员之一。从文学境遇看,一方面如前所述,晚明女性文学的创作与作品出版受到男性文人的鼓励与支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男性文人在乐见青楼伎师享有文学声名的同时,却不愿见到自己女眷在文学上有过高的成就,一些名门闺秀为避免文才外显也主动将自己的作品焚毁,因此,对这些名门闺秀来说,《女四书》等妇德教科书仍是必修课,青楼伎师在这方面的约束则要少一些。从词作主题看,对青楼伎师而言,个人的意义取决于亲密的男女关系,因此,浪漫情爱是她们词作的基本主题,柳如是、王微、郑妥、杨宛、马守贞、赵彩姬等人的词作均充满了炽热的爱的激情。在男女之情方面,名门淑媛所表达的却主要是“弃妇”的哀怨与自怜,徐灿就是典型代表。她有良好的身世背景、教育环境,也有理想的婚姻,可以说是当时众多女性艳羡的对象,但是,徐灿面对丈夫纳妾的现实,在许多词作中将自身比作“弃妇”,直率地表达了内心的怨懑和苦痛。就弃妇主题而言,孙康宜强调,必须区别个人式自发的表现与公式化衍承效仿的不同。与屈原、曹植等男性文人奠定的具有政治寓意的弃妇诗传统不同,徐灿等人继承李清照的传统,“为中国诗词开展出一片新的向度——它们更为具体地吐露了个人内心感受,同时经常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最重要的是,她们以本身自发式的、真诚的、不蕴涵其他寓意的语言所写出。”可以说,她们达到了文学传统与个人原创力、女性传统与男性传统之间诗艺的美妙融合[6]198。
经过比较,孙康宜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同样面对被抛弃的命运,青楼伎师在其词作中所描述的往往是爱情的伟大力量与昔日恩宠的鲜明回忆;闺阁名媛则强调她们处身景况的无奈和被抛弃时的感受。至于徐灿,孙康宜尤其强调她在明清名门淑媛文学传统中的特殊价值,认为她开拓了另一种表达相思苦痛的方式,那就是将个人情爱转移到对国家的忠诚。徐灿面对明朝灭亡、丈夫纳妾且随即降清等家国变故,她在词作中有意将个人的失落与亡国的悲愤并置,感怀故国与责怪丈夫糅合在一起,她原本阴性的文风融入了豪放词派的阳性,其词风已超脱了闺阁词人的格局,“似乎已打破了诗词创作中文类与性别的界限”,“或可称是词中的女性主义作家”[6]201。后来以豪放风格见长的陈维崧对徐灿的词作推崇备至,称之为“本朝第一大家”[12]1833-1844。孙康宜指出,徐灿为当时的名媛词人创立了一个可供追寻效法的范例。受其影响,后来的吴山自称是“女遗民”,在词中流露出思念故国的情怀。直至清末,对秋瑾等爱国女诗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对柳如是与徐灿所分别代表的文学传统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孙康宜在“结语”中进一步指出了三点:第一,两种传统之间没有绝对的分野,但是,纯粹就诗词风格而言,阴性婉约与女性意识两种风格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它们对后世女性词曲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第二,青楼伎师与闺阁词人的作品在17世纪享受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18世纪,由于新理学兴起的关系,前者基本上被隔绝在文学界之外了。第三, 18世纪的士绅阶级女子吸纳了青楼伎师传统,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女性诗人群体由原本的边际角色跻身于正统的地位。而柳如是与徐灿,虽然有明显不同的差异,但是,“两人俱是词文学丰富而不竭的资源中重要的女性人物。”[6]205
(二) 女性的角色与声音
孙康宜曾说:“这些年来,我的梦想就是:努力捕捉古代文人才女的各种不同的‘声音’。”[5]2在明清女性文学研究中,孙康宜对三种女性“声音”的阐释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虚构的男性声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男性诗人常常借着“男女君臣”的比喻和“美人香草”的意象,通过虚构的女性声音来发言。孙康宜将这种托喻美学称为“性别面具”(gender mask),并指出,男性诗人是通过诗中的女性角色,借以达到必要的自我掩饰和自我表现,同时通过性别置换与移情作用,也能投入女性角色的心境与立场。因此,这种艺术手法使男性文人无形中进入了“性别越界”(gender crossing)的联想。相对而言,早期女性诗人从未建立这种“性别面具”和“性别越界”的传统,因此,女性的诗歌往往会被视为作者本人的自传。“然而,明清以后的女性作家却通过各种文学形式,企图跳出这种传统写作与阐释法则的局限。”[6]298在明清女性剧曲中出现了典型的“性别倒置”现象:女作家通过虚构的男性声音来说话,一方面可以回避实际生活加诸妇女身上的种种压力和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女性企图走出“自我”的性别越界,是勇于参与“他者”的艺术途径。典型的如,叶小鸾在杂剧《鸳鸯梦》中,把她们三姐妹的悲剧通过三个结义兄弟的角色表现出来,一方面颠覆了传统诗中的女性话语,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怀才不遇的男性文人的认同。此后,著名女词人兼剧作家吴藻将“性别倒置”的技巧用得更加彻底,她在《饮酒读骚图》(又名《乔影》)中,把自己比作屈原,女扮男装,唱出比男人更加男性化的心曲。孙康宜认为,屈原以美人自喻,吴藻却以屈原自喻,两性都企图在“性别面具”中寻求自我发抒的艺术途径,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角色、一种表演、一个意象、一种与异性认同的价值。而吴藻的价值是,她不仅把自己假想成一个传统男性文人的角色,还创造了一种有别于“男女君臣”的情爱美学,将传统托喻诗词中总是被动的男性变为情爱的主动追求者。孙康宜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藻的创作美学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开始追求的女性主体性——不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她们都希望像男性文人一样,不但有主动虚构的自由,也有文学想像的空间。”[6]301
二是寡妇的声音。在中国古代,寡妇一直是文学关注的主题之一,而在明清之前,寡妇的形象大多是男性文人创造出来的,如曹丕、潘岳都曾撰写《寡妇赋》。在这些代言体作品中,既有对寡妇孤苦无依的处境的深深同情,也有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牢骚。孙康宜注意到一个现象,明清以后,除了何景明的《寡妇赋》之外,很少再有男性所写的代言体寡妇诗,取而代之的是寡妇诗人们真实的自我表达与抒发。
据统计,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的3915位明清女作者中,早夭、所适非人、早寡等薄命才女的比例很大,以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卷八为例,165人中遭遇各种不幸者达73人,占总数的44.24%[13]。孙康宜指出,在明清的薄命才女中,寡妇诗人是最痛苦、孤独的一群,所以她们的文学成就也最大。
与男性文人“为文造情”的代言体寡妇诗相比,“明清寡妇自己写的诗常常传达了男人想象以外的很多信息。”[6]319在《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一文中,孙康宜敏锐地捕捉到了寡妇诗人们复杂真实的“声音”:
第一,失去依靠与认同的失落感。对于传统女人来说,失去丈夫就失去了依靠与认同,无论留在夫家还是归住母家,寡妇都是一个多余的人,都有一种无家感。方维仪、方维则姐妹都是不到20岁即丧夫早寡、在娘家一同度过了将近70年孀居生活,在她们的在诗作中自始至终贯穿着无家可归的失落感。
第二,死别的孤独与绝望。方维仪《未亡人微生述》《死别离》等作品描写了“死别”的完全绝望的心境,发出了“予生何所为,死亦何所辞”无可奈何的叹息,与《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努力加餐饭”的自慰心理形成了强烈对照。
第三,生计艰难与日常生活的负担。传统男性诗人所写的寡妇诗几乎千篇一律专注于独守空闺的苦楚,而事实上,对许多寡妇来说,比寂寞更难捱的是生计的艰难和日常生活的负担。如丁月鄰、孔瑶圃等人的诗作都描写了生计之艰。
第四,“恋生”的意义。对于寡妇来说,死节和守节是一种艰难的选择。明末商景兰将寡妇的选择与忠臣的命运相提并论,面对丈夫祁彪佳殉国的壮举,她在称颂之余,也从“儿女亦人情”的角度说明了“吾犹恋一生”的理由,肯定了“贞白本相成”的道理。孙康宜认为,商景兰悼亡诗的独特价值在于,用寡妇自己的声音表达了在生死抉择之间肯定了活下去的意义与勇气[6]321。宗婉《感示两儿》、张凌仙《岁末感怀》等诗作均写出了含辛茹苦、幽寂崇高的寡母形象;宋婉仙《后山春望》则以孤松象征自己历尽寒霜而傲然不屈的精神。
第五,寡居生活的正面意义。孙康宜特别指出,“五四”以来,一般人都把寡妇视为社会的牺牲品,以为女子一旦称为寡妇就成了“废物”,而事实是,许多明清女诗人给艰苦的守寡生涯赋予了丰富的内容和许多正面的意义:一则是更加积极地扮演母亲角色,成为精明能干的内当家,堪称女性“君子”,如商景兰丧夫之后更加不遗余力地作诗,其二媳四女咸工诗,她与家人及各处来访的才女互相唱和;二则集中精力勤奋读书,希望借此提高文才,抒发内心的愤闷忧思,如李因、顾若璞、薄少君等寡妇诗人的作品均透露出了自强不息的“女儒者”气息;三则追求道德上的美名,如早寡女诗人文氏在其闻名后世的《九骚》中俨然以“女屈原”的姿态表达自己对丈夫忠贞不二的节操以及自己修身与修名的强烈愿望;四则超脱世俗、寄情山水,如王慧《山阴道中三首》等作品从山光水色中提炼出了人生的哲理,王素娥《过钱塘江喜晴》等作品表现出“逍遥游”的生命境界,商景兰《中秋泛舟》等作品更是在写景中寄托了对大明的哀悼,等等。孙康宜认为,这些女诗人“提倡的是一种‘女文人’(female literati)的生活方式”,她们与男性文人有了共同的语言,“尤其对于寡妇来说,这种女文人的生活情趣使她们体会到名副其实的性别超越。”[6]332孙康宜甚至创造性地将寡妇诗人称为“性别遗民”,她们与男性的“政治遗民”一样,不幸失去了自己的“皇帝”,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她们发出的超越性别的文学声音,制造了某些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丰富了传统文人文化。
三是乱离中才女的声音。在《末代才女的乱离诗》[6]334-358一文中,孙康宜集中对明末清初女性诗人见证乱离的作品进行了分析。
孙康宜首先指出,以诗歌见证历史尤其是见证战乱时期的政治事件一般都会认为是男性诗人的专利,可是,在中国古代却有例外,汉末女诗人蔡琰具有自传色彩的《悲愤诗》可以说是最早的撰写乱离经验的典范之作,直接开启了杜甫“诗史”类作品。到了晚明,女诗人们由于生活面的扩展,创造了一种表现广大现实意义的“新文学”;恰逢改朝换代,许多才女也随之成了时代的受害者,于是,她们刻意追摹蔡琰与杜甫,以前所未有的自觉意识关注战争与灾难,在描写苦难、逃亡、挣扎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见证人生的、富有自传意味的乱离诗”[6]336。然后,孙康宜以举例的方式,对这些女诗人建构出来的新的、复杂的“时代”的声音做了深入的解读。
其一,从个人走向公共领域。毕著20岁时所写的《纪事诗》描写她自己率领精兵夜袭敌营、取回以身殉国的父亲尸体的过程,表彰和宣扬了妇人的丈夫气,这首诗既写孝女精神又是惊心动魄的战场诗,因此,孙康宜认为,“这是一首从个人(private)走向公共(public)领域的见证诗歌”[6]339。
其二,抒写黍离之悲,并将战乱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王思任之女王端淑身经战乱、饱受乱离之苦,尤其是在得知父亲殉国之后,著《吟红集》30卷,抒发黍离之悲,记录流离战乱的种种亲身经历,将一己之经历铭刻成集体的记忆,从而提升精神的价值。王端淑在其《悲愤行》诗中援用蔡琰的《悲愤诗》题旨,称清兵为“寇”,用“汉室”与“汉史”作为“明室”与“明史”的隐喻,将战乱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
其三,纠正“女人祸水”的偏见,将亡国的责任归为男性,甚至比男子更加忧心国事。蔡琰的《悲愤诗》充满了个人的“悲”的痛苦之感,王端淑在《悲愤行》中更加有一种“愤”的情绪,指出亡国的责任在于那些在国家倾覆之际尚“利名切切”的男性。孙康宜指出,王端淑所抒发的是明末清初许多才女所共有的一种普遍的挫折感和愤怒。其他如徐灿在其《青玉案》词作中亦对降清人士提出批评,并强调明朝的灭亡并非由女人造成的;黄媛介在其《丙戌清明》诗中亦以“漆室忧”之典斥责亡国之际竟然无动于衷甚至沉醉歌酒的男子们。五代后蜀的花蕊夫人曾在《述亡国诗》中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之语谴责降敌的男子们,明清之际以王端淑和徐灿等人为代表的才女们在效仿花蕊夫人的卓识之外,对社会政治的认知和投入其实更进了一步,许多生性洒脱的女杰表现出了比某些男性更加执着与勇敢的姿态,祁湘君、吴黄等均在诗作中对国事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
其四,以诗歌再现历史,见证个人与时代共同经历的巨大创伤。孙康宜指出,明清之际许多饱受乱离苦楚的女性,常常以文学作品见证个人与时代共同经历的巨大创伤,王端淑《苦难行》叙述乱离的笔调有如诗史,其反映现实的风格近似杜甫的《兵车行》《北征》等诗篇,“总是把个人的记忆与大众的情怀联系在一起,所以,她的作品既是诗的创作也是历史的再现”[6]345。孙康宜还分析了王端淑在其另一代表作《叙难行代真姊》中以代言体的方式书写记忆、见证历史的特色:一方面为“寡妇如何在战乱中存活”的研究课题提供了难得的“事实”材料,另一方面,与曹植等男性作家比,王端淑的代言诗更能捕捉女性的实际苦难,她笔下的寡妇真姊劈头即提出国难当头的问题,先说亡国之痛再说个人命运,“这个‘新女性’的形象可谓真正捕捉到了明清之际受难妇女的情怀”[6]349。
其五,同情、哀悼乱世中的才子,与失意文人相知相惜。孙康宜将王端淑的代言诗《叙难行代真姊》与当时著名的男诗人吴伟业的作品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无论男女在乱世中都有一种受尽伤害而又无能为力之感,他们的作品正是“本身在乱世之中的心灵写照”[6]350。孙康宜还进一步对吴伟业与王端淑的桃源情结所隐含的不同意涵进行挖掘,敏锐地捕捉到了王端淑对乱世才子们的同情、哀悼之声音。王端淑《青藤为风雨所拔歌》即是为哀悼明末文人徐渭及画家陈洪绶而作,她于乱离中入住徐渭之故居、陈洪绶亦曾小住一段时间的青藤书屋,见景生情,以雨中被狂风摧残的青藤意象象征在乱世中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徐渭与陈洪绶的命运,既哀悼才子又哀悼自己,哀人而复自哀。孙康宜对王端淑此诗中的青藤意象给了很高的评价,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文学声音”:“如果说,传统的男性文人一般总喜欢用‘美人香草’的意象来寄喻他们的洁身自爱,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王端淑所用的‘文人青藤’的意象正代表了明清女性逐渐走向男性的大方向。明清才女不但继承了蔡琰所传下来的女性见证的优良传统,也吸收了古代男性文人的托喻美学。”[6]358明清文学研究者一般只注意到当时男性文人对才女的题跋,却很少注意到像王端淑这样的才女对失意才子的同情。孙康宜的解读可谓别具只眼。
综上,孙康宜从身份着眼,对明清女性文学中“才伎”与“名媛”两种不同传统的特质与源流进行了分析,并对女性以“代拟男性”、寡妇、乱世才女等三种不同角色所发出的复杂、丰富、真实的“声音”进行了阐释。
三、 明清女性文学的价值重构
孙康宜关于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引入性别理论的视角,同时又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在《西方性别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创新》[6]245-267一文中,孙康宜对当代西方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发展过程以及性别理论对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从她的介绍以及她自己的研究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和她的一些美国汉学家同行并非简单从中国文学中给西方性别理论找注脚,而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来说,西方性别理论在哪些方面适用、在哪些方面未必适用。而通观孙康宜的系列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正是对那些“未必适用”的部分的关注和阐释,发现或者说重构了明清女性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经典价值,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明清女性文学的成就世所罕见,为世界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文本依据。
孙康宜一再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并进而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文学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五四”以来把中国妇女完全说成是封建礼教牺牲品的话语过于绝对化了。孙康宜与她的美国汉学家同行们惊喜地发现:“若能让西方读者看到传统中国曾有那么多女作家写过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这也是把中国文学提升到世界文学的经典地位的好方法。”[14]248于是,他们聚焦于明清女性文学,将其大规模译介给西方读者,并在当代西方性别理论的框架中多维度加以解读与诠释,为世界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文本依据,这些作品也因此被赋予了世界性的经典价值。
(二) 明清女性文学的成就对西方“性别差异”理论具有补充与纠偏的意义。
孙康宜指出,与明清时期许多男性文人对女诗人的支持与鼓励不同,19世纪英国女小说家也十分多产,而且她们的作品曾大批进入文学市场,但是,这些英国女小说家一般并没有得到当时男性作者的支持或帮助,相反,“对于备受威胁的男性小说家来说,这些女小说家好像在发动一场集体的性别战争”,“也正是这个性别之战,触发了19世纪女权主义作家在英国的兴起”[6]92-93。正如孙康宜所说,西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最强有力的策略之一就是强调性别差异[8];并由性别差异进而“将男女两性置于对立的两极”[7],强化女性受害者角色。这种差异概念“也被中国女批评家和女作家们广泛地借用”。不过,在1980年代男女两极对立论提出的同时,也有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过分强调性别的差异会误导性别的意义和两性关系。孙康宜与许多美国汉学家一道,亦对性别差异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们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体系中广泛存在阴阳互补、“男女双性同体”的现象。孙康宜明确表示:“在我看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阴阳互补的哲学,恰恰可以用来解决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关于‘差异’概念的争议。”[8]具体在明清女性文学领域,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闺塾师》一书中最早针对“五四”以来的传统妇女史观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化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14],此后,苏珊·曼(Susan Mann)、魏爱莲(Ellen Widmer)、毛伦·罗伯逊(Maureen Robertson)等汉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女作家的创作观念以及复杂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探索,她们的研究结论均“对根深蒂固的受难的封建女性形象”提出了批判或挑战。孙康宜无疑是这一汉学研究队伍中的佼佼者之一。与这一领域的其他汉学家相比,孙康宜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探讨了明清时代的男性编者和出版者如何运用各种策略来使女性作品“经典化”,并明确提出:“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种‘性别之战’”[8];第二,探讨了明清歌伎的自我塑造以及歌伎与文人文化的关联问题,并由阴阳互补的概念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交互发声”(cross-voicing)和“文化男女双性”(cultural androgyny)的概念,两者都强调男女两性互相之间的认同与性别超越现象。可以说,孙康宜和她的美国汉学家同行们的努力,纠正了西方性别理论中“唯性别是论”的偏颇做法。
(三) 明清女性诗人的多元声音有助于脱离性别研究中所存在的“脱离历史”的缺陷。
西方早期性别研究中存在将妇女预设为“受害者”形象的现象,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由于普遍性受到压迫,完全成了男权制度下的牺牲品。可是,在汤姆逊《英国工人阶级构成》及福柯有关“权力多向分布”观念的影响之下,以耶鲁大学Nancy Gott为代表的学者们重新检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生活,对女性的道德权力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女性从“道德母性”中获得了一种崇高的权威感,而且,历史上的女性同样参与了社会与道德制度的建造,女人是历史的参与者而非受骗者。孙康宜是美国汉学家中较早参与女性权力话语讨论的学者之一,她认为,班昭以及许多明清时代的寡妇诗人都是从自己的道德信念中获得了特殊的道德力量感和权威感。而孙康宜对歌伎、名媛、寡妇、乱离中的才女等明清时期不同女性群体的作品的细致解读,对于寻找真正的抒写心灵、建构主体、见证历史的女性声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她与高彦颐等其他汉学家一道,为更正西方性别研究中所常见的“脱离历史”的缺陷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支撑[6]258-259。
综上,孙康宜与她的美国汉学家同行们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受到西方性别理论的启发,同时又给西方性别研究界带来空前的震撼性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充和纠偏的作用,从而使明清女性文学进入了国际化经典行列。事实上,对于重构明清女性文学的世纪性经典意义,孙康宜有着高度的自觉。她在《西方性别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创新》一文的结尾语重心长地指出:
我们总以为只有西方批评理论会带给中国文学研究一个新视角,却忘了中国文化也可以影响西方。一般说来,无论台湾或是大陆的性别研究都有“全盘西化”的缺点,常常不假思索地套用西方理论,以为只要是西方的理论,一定是愈新愈好,于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解读也就变成了西方理论公式的重复借用。反而是西方的汉学家们更能站在传统中国文化的立场,会用客观的眼光来对现代西方文化理论进行有效的批评与修正。我认为有深度的“批评与修正”将是我们今日走向21世纪全球化的有力挑战[6]266。
毋庸置疑,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学界性别研究领域“全盘西化”的现象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明清女性文学研究亦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孙康宜等汉学家所开辟的、站在传统中国文化立场对现代西方文化理论进行有效“批评与修正”的道路还很漫长,明清女性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经典意义,亦有继续挖掘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孙康宜.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人诗歌的经典化//孙康宜.文学的声音[M].台北:三民书局,2001:21.
[3] 宁一中,段江丽.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下)[ J].文艺研究,2008(10).
[4] 孙康宜.古代与现代的女性阐释[J].联合文学,1998.
[5] 孙康宜.文学的声音[M].台北:三民书局,2001.
[6] 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7] 孙康宜.老领域中的新视野——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8] 孙康宜.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S1).
[9] 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M].李奭学,译.台北:允晨丛刊,1992.
[10] 孙康宜.传统女性道德权力的反思[M].台湾大学法鼓人文讲座,2005.
[11] 孙康宜.道德女子典范姜允中[J].世界周刊,2006.
[12] 陈维崧.妇人集//张潮.昭代丛书:己集[G].
[13] 陆草.论清代女诗人的群体性特征[J].中州学刊,1993(3).
[14]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收稿日期:2015-08-29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QN053)
作者简介:段江丽,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叙事学学会会员。
中图分类号:I20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6)04-006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