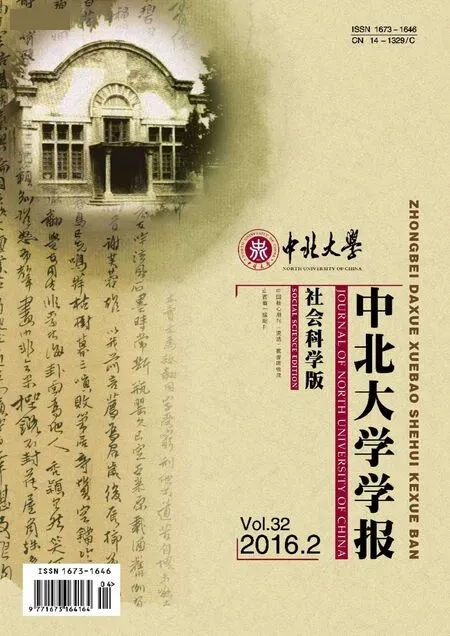刍议爱情视角下北美新移民的身份归宿
——以《丛林下的冰河》与《曾在天涯》为例
王 洁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刍议爱情视角下北美新移民的身份归宿
——以《丛林下的冰河》与《曾在天涯》为例
王 洁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北美新移民文学反映着北美新移民者在国外的生活境遇和精神世界, 它日益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为了探究北美新移民者的生活状态, 本文以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和阎真的《曾在天涯》为研究文本, 从爱情视角对其详细解读进而揭示北美新移民者的身份归宿。 本文抓住了两个文本类似的情节框架(从出国到归国)以及首要情节线索(爱情), 着重分析了两位主人公精神层面的共性, 最终把北美新移民者的身份定位为“边缘人”, 并加以阐释。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爱情角度分析人物的生活境遇, 最终用“边缘人”理论加以归纳与说明。
北美新移民文学; 《丛林下的冰河》; 《曾在天涯》; “边缘人”; 身份归宿
通常, 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国内移民至北美、 澳洲、 欧洲等地的作家称为“新移民文学作家”。 他们所写的关于移民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即称为移民文学。 移民文学就如同一面大时代的“镜子”, 映射出当时人们的生活、 心态等诸方面境况。 北美新移民文学恰是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 其代表作家包括查建英和阎真等。 本文将以查、 阎各自代表作《丛林下的冰河》和《曾在天涯》为例, 探讨北美新移民的身份归宿。
“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1],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如是说。 《丛林下的冰河》和《曾在天涯》无疑验证了这一观点, 它们都以爱情为主线, 从爱情视角看生活, 从生活境况反映移民者的身份归宿。 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最初都是带着美好期许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或加拿大, 然而却在北美的异国他乡经历种种坎坷, 最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 最后回国寻求自己的“根”。 由此揭示了北美新移民在不同文化撞击与文化融合中不断寻找自我身份定位的艰辛。
1 异国他乡的爱情羁绊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北美新移民文学有很大的发展, 其中与爱情相关的描写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 但不管如何变化, 爱情作为小说主线的构思总会被沿用。 这两篇小说也不例外, 爱情在小说中起着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作用。
1.1 无果异族恋
《丛林下的冰河》中, 在爱情上, 女主人公虽被捷夫吸引, 为他的殷勤和温柔所征服, 但她依然觉得这份感情不会地久天长。 究其根本, 女主人公虽然身体在美国游荡, 但灵魂依旧漫游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 所以她其实并没有如我们想的那样做着美国梦。 她经常会把美国的经历“映射”到她在中国的种种: 驱车走在美国春日的美景中, 她回想起杜甫的诗句“颠狂柳絮迎风舞, 轻薄桃花逐水流”; 身处美国南方温暖的气候中, 她却“老怀念下大雪, 刮西北风, 红泥小火炉焐白薯”[2]5。 她的这种汉式思维, 注定了她无法从心理上融入美国生活, 即使表面看起来十分融洽。 因此, 她和捷夫就无法达到深层次的默契, 而这种精神层面的差异使他们的世界无法实现根本沟通, 这也就导致了二人最终彻底分手。 这无疑是异族恋情的悲哀: 最初的吸引与爱恋打开的只是爱情世界的一扇窗, 窗的视野窄而浅, 表层的美好蒙蔽了双眼; 但根植于内心的异族差异性终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显。 换言之, 异族恋情如同带刺的玫瑰, 远观则绚丽, 捧在手心却难免受伤痛。
《丛林下的冰河》从第十八节后就开始转入回到祖国的女主人公对初恋男友D的追寻。 这算是一种逃避吗?笔者认为, 她的回国是顺应了自己的本心, 并非像《曾在天涯》中高力伟“逃离”国外的生活, 她是去追寻更美好、 更符合自己期望的生活。 女主人公的初恋男友D的死讯促成了她的短期回国, 此次她要去西北寻找与D的美好回忆。 这一切很像是一次冲动的梦游: 既浪漫又虚幻。 但就是在这次梦游中, 她意识到自己在异国满脑子的苦闷彷徨全成了说不出口的“闲愁”, 与周围人柴米油盐的基本生存问题相比, 就像是富人的炫耀。 书中描述的她对D的感情并不能算是爱情, 而是一种象征, 代表着她对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渴望, 而D的死亡自然也就代表着她原来的精神世界已经无法找回。 总而言之, 《丛林下的冰河》中的三段爱情: “我”与捷夫是因文化不可融合、 历史不可割舍而分手; “我”与D的分开是时代文化的选择, 即是文革的错误酿就的一场悲剧; 而“我”与巴斯克伦同是天涯沦落人, 惺惺相惜, 虽然互有好感, 但这却难以成为彼此拥有爱情的理由。[3]这一切暗示着不同国家地区、 不同历史时代、 不同文化背景之下, 人与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沟通往往缺乏有效性, 因而美好的异域爱情总是梦幻。 异族两面性, 一面是差异带来的新鲜感与诱惑性, 让人甜蜜入梦; 而另一面是差异内在的排斥感与游离性, 催人痛苦梦醒, 而梦醒了, 人也就散了, 虚幻的浪漫爱情随之消逝。
1.2 凄凄本族情
《曾在天涯》中, 高力伟与妻子林思文的爱情是败给了现实, 更确切地说, 是高力伟败给了现实。 不管是当时的加拿大还是中国都是一个男权社会, 男人有自己独特的情感需求。 高力伟坦言: “我出国之前有着心理准备, 在洋人面前我头得低一点, 他们的国家嘛!在自己人面前心里会有这种滋味, 却是没去想过的。”[4]356这里他所认为的“自己人”, 当然也包括他的妻子林思文。 高力伟是以陪读的身份来到加拿大的, 新环境下生存的艰辛和妻子的不体谅, 导致了出国前的他未曾料想过的地位的颠覆, 也让他开始去了解自己, 看清他自己的境遇。 他认为自己更需要的是一个柔弱的而不是一个强势的女性: 他想通过对柔弱女性的怜爱激起自己努力拼搏的斗志, 而不是让强势女性经常性地证明他的无能。 在加拿大, 他失去了自己最看重的自尊, 失去了斗志, 所以他像一个逃兵, 飞一般地逃离加拿大, 也顺便逃离了自己的婚姻和女人。
总体来看, 这两篇小说的爱情结局都是悲剧。 如小说所描述, 异国生活中的爱情存在诸多羁绊, 尤其是现实因素与文化差异。 在试图认同或接受异域文化过程中, 北美移民者的伤痛体验在爱情方面主要表现为: 异族爱情梦幻被文化冲突打破, 无法逾越的内在沟通障碍扩大异域生活的不适感; 本族爱情根基遭受生活现实动摇, 巨大生存压力之下, 心理层面的异国压力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毁坏原本的爱情归宿。 尽管如此, 国外生活终归让人在感受自身爱情时有了更贴近实际的领悟。
2 新移民者的身份归宿——“边缘人”
2.1 “边缘人”概念解析
在社会学中, 有一个概念是“边际人”, 指的是那些处于人格转型过程中, 种族肤色、 意识形态、 政治权力、 民族阶级、 性别差异的主体身份面临解体的个体。[5]社会学者金耀基认为, 人类学与社会学中所指涉的“边缘人”是在不同文化的边际游走, 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艰难生存的一类人。 作为“边缘人”, 新土和故土的两种文化, 一个充斥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个充斥着他们的物质世界: 两种文化都在撕扯他们, 都极力想要获得他们的认同以及像对本土文化那样纯粹的忠诚。 总之, 故乡需要他们留恋, 而新土又需要他们实现质变, 因此海外华人移民常常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认同危机。
查建英认为, 新移民们寓居海外后所生发的许多情感包含太多的矛盾与尴尬, 尤其是在重访故乡时, 发现自己已然生成了“回来人”的双重性格, 所到之处, 所思所感, 无不包含着身份不确定的尴尬与无奈。[5]
由此看来, 新移民就像是“四不像”: 既是不被西方认可的“边缘人”, 又是让中国难以接受的陌生人。 虽然查建英的说法并不是在张扬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世界观, 但却能充分阐明当新移民陷入中国与西方双向疏离的尴尬境地时, 他们所应持有的较为清醒的认识。 社会语境的单一和对过去历史的延续是人类产生永恒自我意识的根本因素, 但对“边缘人”来说, 他们距离家国越来越远, 也就与自己的过去越来越远, 那个曾经的自我不再是永恒不变的固定所在, 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逐渐分裂, 由此产生自我归属的失落与迷惘。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归属, 无法被准确地归在一个范畴里, 这样的人在精神上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彷徨与纠结。
2.2 “边缘人”小说性分析
《丛林下的冰河》中有这么一段:“D曾扶着我的肩膀说: ‘记着, 你将来就是爬着回来, 也是我的英雄。’现在我回来了, 回到了D生活过的土地, 却发现自己已经傻乎乎地被抛入了介于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两不管’地区, 既不能像D那样死去, 又不能像周围大多数人那样活着。 也许, 生存与‘两不管’地区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人, 不幸我却无法如此释然。”[2]22这种处在“两不管”地区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边缘人”。 这类人被夹在两种文化、 两种世界之间, 经历着两种各自和谐且封闭的现实与思维方式, 试图认同异国文化但又发现自己很难彻底融入其中。 最终他们只能表面和谐, 很难达到一种比较深刻的和谐, 这就是“边缘人”的悲剧: 就像是一个走钢丝的人, 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 只能战战兢兢地保持着平衡。 《丛林下的冰河》主要从精神方面刻画“边缘人”。 该小说不仅通过“我”的视角对比了中西社会与文化, 而且通过这些差异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矛盾, 还描写了“我”信仰缺失的渐变过程以及最终无法坚守信仰的慌乱和焦虑。
《曾在天涯》对“边缘人”的描写则主要体现在高力伟从国内到加拿大的身份的转变和地位的反差。 在国内, 处于较高生活层次的知识分子, 经常迎着周围人羡慕的目光而生活, 但当他们满怀着美国梦踏上北美的土地,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居然落到了最底层, 沦为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的“劣等人”。 这样看来, 从国内到北美, 就像物种被退化一样, 他们一下子变得还在为生存而苦恼, 更别提什么精神或是情感世界。 因此不难推测, 当一个人还在吃力解决生存问题时, 那么他的信仰和情感必然也是一团糟。
一般而言, 准备一展抱负的北美移民者初到国外, 往往会遭受找不到工作的打击, 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此外, 这类“边缘人”通常只能凭借自己的体力劳动而非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为生存奋斗, 此时他们精神上的煎熬远远大于身体上的。
“边缘人”的悲哀不仅仅是在国外。 一旦回国, 他们还要忍住内心的煎熬, 摆出一副荣归故里、 学成归国的高姿态, 无法坦然地承认自己在国外的失败。
这样的“边缘人”在两种文化下都无法以本我示人, 如此心理境地, 也是这两篇小说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给世人的, 这也引发了很多留学生或移民者的共鸣。 “边缘人”这一身份转换, 是新移民者在尴尬的现实和悲剧的爱情中慢慢确定的, 形成这样的转换或许不需要太久, 但是想摆脱“边缘人”这一身份, 却无比艰难。
3 结 语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6]文学是带有寓言性的文字, 不仅寓言着个人的命运, 也寓言着民族的命运, 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两部作品的出版时间都在20世纪90年代, 两位作者都是赶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那段出国热来到国外的。 那时中国刚刚从封闭走向开放, 处于一个落后的中国向先进的西方靠近的阶段。 一个落后的国家, 是没有资格谈文化的, 所以当两种文化冲突碰撞时, 弱势文化必须先行掌握强势文化的话语形式才能获得对话的资格, 但这样之后往往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这两篇小说均从爱情的角度, 描述了主人公“我”和高力伟在异国他乡的情爱挣扎。 他们在爱情上的选择, 更像是一个文化的选择, 即内心文化归属的选择问题。 因此, 这两部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可谓诉说着大众社会和文化在北美受到冲击的寓言, 并且历史性地展现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体现了社会文化心态的转变。 总之, 北美移民文学是在“行走”中产生的文学, 在“行走”中, 路旁的风景会改变, 社会在发展, 文化在交融, 所以文学也在发展。
[1] 袁静云. 碰撞与超越——论北美新移民小说中的异国婚恋[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3.
[2] 査建英. 丛林下的冰河[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3] 彭超. 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爱情”演变[J]. 华文文学, 2014(5): 119-124.
[4] 阎真. 曾在天涯[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5] 冯烨.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他者”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4.
[6] 张长青. 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身份”叙事[D]. 汕头: 汕头大学, 2005.
A Criticism of the Identity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TakeTheIcedRiverundertheForestandWanderingattheWorld’sEndas Example
WANG J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New Chinese immigrants’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has been reflecting both the life experiences and spiritual condition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 thus it has become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deserving our great attention. To explore lives of thos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this paper interpreted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mantic love delicately, namelyTheIcedRiverundertheForestby Zha Jianying andWanderingattheWorld’sEndby Yan Zhen. The identity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s figured out after a concrete interpretation. As the two texts share the main plot (both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going abroad and coming back home) and the major clue (affection),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study on basis of these similarities. It regards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 as “marginal person” and gives a profound elaboration. The innovative points of this paper li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on from which those characters’ situation is analyzed distinctly and the employ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ginal person” to deduce those immigrants’ identity.
new Chinese immigrants’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TheIcedRiverundertheForest;WanderingattheWorld’sEnd; “marginal person”; judgement of identity
2015-10-19
王 洁(1989-),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文学与翻译方向。
1673-1646(2016)02-0093-04
I207.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