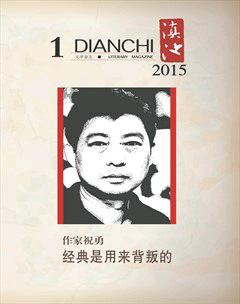雨夜
张树丽
这天傍晚,吴羽终于骑着自行车经过了建设巷。她骑得很慢,心脏却还是无法抑制地一点点缩紧,熟悉的隐痛扯得她胸口憋闷,皱了皱眉头,不自觉地,她想要腾出双手蒙住脸,蒙住那总是由心而出的不堪。
很长时间了,吴羽不愿意从建设巷走过,也不敢从建设巷走过,虽然这曾是她每天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这当然可能是因为一个清晨曾有个醉汉直挺挺死在那里,也可能是因为重修道路,通行不便,更多的却是因为雨夜,那个夏日里一反常态的雨夜!
吴羽本可以一直不经过建设巷,即使这样她上下班要多走五分钟的路程。可她是个有着完美情结的人,她不允许自己一直对建设巷有着心理障碍,不允许那样的心理障碍总像是个坏小孩似的,在她稍不注意时便溜出来弄得她情绪低落。闲暇时她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杂志,在那本名为《心理和健康》的杂志上,她了解到要克服对建设巷的恐惧,她只有硬着头皮一遍遍从那里走过,一次次经受自我拷问和否定,直到走在建设巷时,大脑变得镇定、心脏变得强大,能够坦然地直面自己、接受自己。她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被称为系统脱敏法的心理疗法治愈自己,把那个雨夜带来的,不时遮住阳光的阴霾从自己的天空驱散。
下雨的时候人的感情都会异常脆弱,如同月圆之日人的情绪会异常亢奋,更何况那一个夜晚下的又是那种细细碎碎,让人不易察觉,误以为不用打伞,不经意间却已淋湿衣襟的蒙蒙细雨。淋着这样的细雨,那个夏夜,吴羽坐在陆波那辆绿色的山地摩托上经过了建设巷,一进巷子,她就感到气氛诡异起来,灯光昏暗、四周幽静,更为不妙的是路的前方有一黑乎乎的东西跑过,一害怕,吴羽不由自主地紧紧抱住了陆波,把头埋在他的后背,想要寻求点安全感。陆波正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水坑和石头,想要快点走出建设巷,突然发现吴羽把温热的身体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一种女性特有的气息顺着身体的接触,像是一群有些讨厌的小蚂蚁一下细细密密地爬满了陆波的全身,一慌乱,陆波分神了,湿滑的路面加上一个小坑,连车带人,两人摔倒了,幸而车速慢,车身缓缓倒下,没压到他们。地上湿黏黏的,跌倒的两人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陆波有些沮丧地问吴羽摔疼了没,吴羽沉默了几秒,突然“咯咯咯咯”笑了起来,“笨蛋!”她说。昏黄的路灯下,陆波发现吴羽的眼睛亮闪闪的,嘴角奇怪地带着狡黠的笑,似乎有谁用狗尾巴草在他心里轻轻挠了一下,心里一动,陆波突然紧紧地把吴羽抱在了怀里。吴羽略为一惊,马上又恢复了之前的狡黠,依旧以那样的表情看着他,这表情显然给了陆波极大的鼓舞,一低头,他吻住了那狡黠地笑着的嘴唇。雨下的渐渐大了,激吻中的两人却丝毫也未察觉,只沉浸在雨夜拥吻的销魂间。
吴羽回到家时,全身已湿漉漉的,迫不及待地冲进了卫生间,当热水从头上淋下来时,她似乎才从刚才的魅惑里脱离出来:“天哪!我做了什么?”她羞愧地用双手蒙住了脸:“我们这算什么?他二十二岁,我三十三岁,我是他妈妈辈的人啊!”她想起了过年时和同事一起到陆波家吃杀猪饭的一幕:刚进门,陆波的妈妈就迎了上来,热情地招呼大家,吴羽走在最后面,手里拎着中午就准备好的礼物,陆波妈妈接过礼物,和她客气了一句:“他婶,来就行啦,这么客气干嘛呢?”这句话呛得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那一天因为加班,下班已经六点多了,因为快赶不上饭点,同事们就决定直接从车间到陆波家去,一天的劳累让这群穿着蓝色工装的女人更显憔悴和苍老。幸好陆波及时出现了:“要吃木瓜吗?”吴羽赶紧接过木瓜,从陆波妈妈身边逃离。平时吴羽最爱吃的水果就是木瓜,可那天的木瓜嚼在嘴里如同白蜡。这样难堪的回忆让一阵强过一阵的羞耻感包裹着吴羽,她用力地搓洗着身体,似乎这样能够抹去刚才犯下的糊涂。可乱七八糟的念头摁下一个,马上另一个就浮了起来:“我们不过是同事,不过是我常搭他的便车回家,最多也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似有似无的好感,我怎么就……”一向有些清高的吴羽虽然已年过三十,心思却还保持着小女生的矜持,这显然是不符合岁月流逝的逻辑的,可吴羽却偏执地坚持着,也许,正是这样的偏执,让她至今仍孑然一身。
雨夜,像是鞋底的一颗砂石,不时让吴羽有着种种的不适。第二天早晨上班打卡看见陆波的背影时,那颗砂石就狠狠地硌了她一下。在厂子里,陆波是维修工,平日里他常常要在各个车间里四处巡视机器有无故障。在吴羽她们这个女人居多的车间里,二十二岁的陆波就成了这些不断重复着枯燥工作的女人们娱乐的对象,插诨打科是少不了的,个性大胆的更是趁陆波不注意在他脸上、屁股上拍上一下,然后发出恶作剧之后满意的爆笑声。陆波倒也没当回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让女人们对于他的到来总是带有几分期待。虽然吴羽在这群女人中总是显得有些不一样,周围的喧嚣似乎都与她无关,也从不参与那样的恶作剧,但陆波到车间来的这短短几分钟,平日里也会让吴羽有着若有若无的期待,在那样的时刻,她那张略显苍白的脸上也会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雨夜改变了一切,它让这期待变成了一种煎熬,那颗小小的石头一直在心里瘆得她直发慌。快下班时,陆波进来了,照例和女工们嬉笑打闹,吴羽感觉到陆波的眼光朝她扫了过来,她连忙埋头做着自己的事,尽量使自己显得淡然些,她不想让陆波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能免俗的女人。终于,那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后移开了,用眼角的余光一瞟,陆波已转身走了出去,她这才松了口气,在心底里轻轻叹了一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羽发现自己和陆波间有了一种难于言明的默契,每次吴羽下班从车间出来,陆波就骑着他的摩托车经过门口那棵凤凰树,仿佛不经意的邂逅,陆波停下来说:“一起走吧。”吴羽便坐上他那辆绿色的山地车搭便车回家,有时会说笑两句,有时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直到下车。在那样的时候,吴羽想起最多的是高中时和男朋友骑脚踏车在城郊游玩的情景。有那么一次,吴羽想起男友为了给她摘一朵白莲不慎掉到池塘里,弄得满身泥水赤脚回家时,不禁在后座“哧!”地笑了起来。那天,陆波慢了下来,奇怪地扭头看了她一下问:“笑什么呢?”吴羽难掩笑意,直说没事。有些无趣的陆波突然加大油门,把车骑得飞快,吴羽一个踉跄,吓得赶紧抱住陆波的腰,靠在陆波宽厚的背上,吴羽心里突然有了当年坐在脚踏车上的甜蜜。那一丝甜蜜越集越多,终于在雨夜溢出。溢出的甜蜜自然是会变味的,更何况那是一个有着巨大障碍的甜蜜。就如现在,下班了的吴羽磨磨蹭蹭迟迟不愿离开车间,就是不想要去品尝那变了味的甜蜜。可糟糕的是,当她走出车间时,那棵凤凰树下,陆波和他的摩托车赫然停在那里。“快上车!等你半天,以为你先溜了,我刚要走呢。”陆波依旧是那个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气息,似乎对什么都无知无畏的大男孩。犹豫片刻,吴羽坐上了陆波的摩托,一路无话。
二十二岁的陆波自然不会如吴羽般煎熬。那个雨夜回家躺在床上,他是有那么一点小兴奋,眼前总浮现吴羽那饱满红润的双唇,不过没一会儿,浓浓的睡意便战胜了红唇,他沉沉地睡了。对于他来说,这样的一个吻并不代表什么,这样的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和朋友们到外面玩时,灯光、眼神、笑容和醉意到达某一个临界点时,大家一时兴起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第二天也没有人会想要追究什么。这也是他没有固定女友的一个重要原因,老是要承诺来承诺去,担负起那些莫须有的责任,多累啊!自由!他需要的是自由!或许他对吴羽是有好感,也每天载她回家,可那也不代表什么,那不过是顺路。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吴羽在车间那群聒噪的女人中间,总显得有些不同,衣服一尘不染,头发一丝不乱,那张白皙的脸总是冷冷的,偶尔露出一丝微笑时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出尘的美,和这样一个特别的女人一起回家总会让他觉得心里很熨帖。即使这样一来,一个谈过多年恋爱而无果的老姑娘和一个暂时单身的年轻小伙搭伴回家难免会传出些闲话来,他也无所顾忌,他做的只不过是当下让他比较愉快的事而已,对于吴羽他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他心里还有着更多的梦要去实现,岂能就终结在这昏暗狭小的车间里。
吴羽是个敏感的女人,陆波满不在乎、毫无反常的反应,让她有些受伤,但她无意去追究,也无法去追究。雨夜,对她而言似乎是和陆波之间的一个转折点,她想要像陆波般若无其事,却拼尽全力也无法像以前般坦然地面对陆波。那颗硌在心里的小小砂石,已折磨得她食无味夜难寐,那石头不断提醒她和一个小自己十一岁的男人接吻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接吻不是恋人之间才会有的吗?那应该是两个人的情到深处的自然表现。那么,她和陆波是恋人吗?不是!陆波爱她吗?不!她爱陆波吗?不!他们之间有往下发展的可能吗?没有!她一遍遍在心里拷问着自己,最后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之中,任由羞愧和耻辱撕咬着自己的灵魂。自从谈了八年恋爱的男友爱上她最好的闺蜜,两人一起残酷地背叛她后,这样的自我拷问自我否定就常常与她相伴,不到弄得遍体鳞伤不罢休。
夏天的酷热一点点散去,秋天有些漫不经心地到来了。在拷问和否定告一段落后,吴羽心里有了片刻的安宁。她终于又可以在阳光底下正常地工作和生活,她不再搭陆波的便车,有些刻意地,她也和车间的女工们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有时还带上些零食在换班的空隙和大家分享。一次,当车间的女人们稀里哗啦享用着又酸又辣的舂鸡脚,有人想起了陆波:“陆波呢?他最爱吃舂鸡脚了。”马上有人拨通了陆波的电话,吴羽的脸一下僵了,她没想到自己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买了陆波最爱吃的舂鸡脚。更为不堪的是,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起了厂里一个略有些姿色的女工:“这世界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个徐璐啊,不好好守着自己的老公过日子,竟然把自己倒贴给那样一个男人,既没钱又没势,长得也稀松平常,真搞不懂,她图的到底是什么?”“图什么?你也是,这都搞不清,还不是夜里那寂寞惹的祸!”“哈哈哈哈……”女工们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有人因为笑得太过忘形,被呛得激烈地咳起嗽来。吴羽也想要一笑,这时的她如果继续绷着脸,那就太不正常了,可那笑容却是比哭还要难看,费尽心思搭建的那个支架在不断回荡的笑声中轰然倒塌。那天夜里两点,被种种无以名状的情绪逼到想要发疯的她终于放下所有的自尊,给了陆波一个短信:“我是谁?”对于陆波是否回这个短信,她并不在意,她想要的只是找到一个出口,一个拯救自己的出口。这一夜很安静,安静得有些异常又很正常,陆波没有回短信。
当陆波在夜里两点被吴羽的短信惊醒时有些恼怒:多大点事啊!对自己躲躲闪闪不算还大半夜发短信,他对自己招惹了这样一个难缠的女人有些懊恼,当时不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吗?翻个身,他继续睡了。早晨到车间例行检查时,他偷偷打量了下吴羽,发现她眼睛有些红肿,一丝头发垂到了脸颊,是略显憔悴。有那么一刹那,他心里稍稍有些不忍。在这之前,吴羽在他心里多少有点神圣,有时看着她那修长的身形、高昂的头颅、清冷的眼神,陆波觉得她更像是一个舞者,一个在自己的舞台上忘我舞蹈的舞者。和车间里的女工们开玩笑时,他曾对她们的身材一一进行了评价,上身瘦下身胖的是鸭梨形,上身胖下身瘦是青蛙形,头小脚小中间大的是红薯形,瘦瘦扁扁的是闪片形,当有人要他说说吴羽是什么体型时,他看看吴羽突然沉默了,当时他嘴里想说的是:“她像一只高傲的白天鹅!”可这样肉麻的话在那样的语境中说出岂不是太滑稽,所以他宁愿被车间里的大姐们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也要选择沉默。现在,雨夜之后的白天鹅似已走下神坛,那一股支撑她的清高和孤傲被忧郁和怨艾所取代,和那群整天为柴米油盐鸡毛蒜皮所烦恼的女工几乎没什么差别了,这样的感觉让陆波多多少少有点失望,这样的失望甚至快要取代之前的不安。
下班时陆波刻意在凤凰树底下等着吴羽,最终他还是决定为这个可怜的女人做点什么。看到他,吴羽犹豫了片刻后上了车。陆波骑得很慢,经过清水公园的时候,他拐了进去。吴羽未做出任何的反应,只静静地坐在后面。这个时间段的清水公园清冷寂寥,几乎没什么游人,新种下的观景植物刚刚泛活,花坛里紫色黄色红色的花在风中摇曳,一派悠然自得的模样。没有传说中的荼蘼花吗?应该在这个季节开放了吧?吴羽想起了王菲的那首歌《开到荼蘼》,颓废而随性的旋律和奇怪的歌词让吴羽对这首歌一直念念难忘。荼蘼,这个词语让吴羽觉得听上去就有一种独特的质感,生生的让人迷恋。于是特意上了百度查询:“荼蘼,蔷薇科,落叶小灌木,花白色,有香气,夏季盛放。《红楼梦》里女仆麝月曾抽到了这样一个花签:“开到荼靡花事了”,荼蘼过后,无花开放,也正因为这样荼蘼花开代表女子的青春已成过去,也表示感情的终结。”这样一段让人惆怅的解释,让吴羽对荼蘼这一苦情的白色小花,产生了无比的怜爱。当她从神情恍惚中回过神来,陆波已在那个不会流动的人工湖边停了下来,她笑了笑自己的天马行空和陆波一起坐在了湖边的石头上,开始了和陆波的对话,那些话句句如针,刺在吴羽心上:
“昨晚你神经啦?”
“睡不着就胡乱发了出去,没吓到你吧。”
“那倒没。”
“现在能给我答案了吗?”
“你是谁?”
“嗯。”
“工厂女工吴羽。”
“在你心里。”
“是这样,吴羽,其实没必要那么较真,大家待在一起时很愉快,这就够了,没必要分清谁是谁的谁。”
“不行,我的心过不了关。”
“那么,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意外发生的小事故吧,过了就让它过了吧!”
吴羽一阵沉默,她突然觉得,自己和那个把自己倒贴给别人的徐璐相差无几。这时,陆波又说:
“你也可以把我当作你的亲人,我们把彼此放在心里,在需要的时候适时出现,给对方温暖也挺好。”
“召之则来挥之则去?”
“对!”
吴羽意识到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她突然豁出去似地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可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吃不下睡不着,无法正常生活,既然你可以做我的亲人,那么你能救救我吗?”
“其实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什么都会过去的,需要的只是时间,一天两天一个月,最多不超过两个月你就会好了,那时候你就会发现阳光又明媚地照耀着你了。”
吴羽又一阵沉默。陆波继续循循善诱:
“其实,我也曾迷恋过一个人,可我们之间没有发展的可能,她那时已经快要结婚,有段时间我对她特别痴迷,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想的都是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生活完全乱套,后来那个女孩让我把她当作亲人,我照她说的做了,时间一长真的释怀了,现在我们都还常常联系,像亲人般给对方温暖,你也……”
吴羽耳边嗡嗡直响,陆波接下来说了些什么,吴羽无法听清也无意听清,她弄明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意外!雨夜发生的一切只是个意外事件!她不知是该感激陆波朋友般的劝慰还是憎恨陆波局外人般的淡定。突然她笑了,笑自己的迂腐和矫情,都是谈过八年恋爱的老姑娘了,为何要和那样一个意外的吻过不去。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洒进来时,彻夜无眠的吴羽做出了一个决定:尽快把自己嫁出去!不断反复的煎熬让她迫切地想要把那颗一直硌得她生疼的石头找出来扔得远远的,而扔掉这块石头,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诚心实意爱自己的人!她买了辆自行车上下班,接着和同事罗大姐一直想要介绍给她的一个中巴车司机老刘见了面。会面是在罗大姐家,谈话看上去很轻松,老刘满口的段子乐得罗大姐哈哈直笑,吴羽却被老刘那一头油腻腻的头发和满身的汗味弄得直反胃,而老刘似乎也对她这样一个三十出头却还仍显娇气的老姑娘并不感冒,他需要的是一个马上就能接过家庭的重担,担负起照顾六岁儿子和七十岁母亲的贤妻良母,这样看来,吴羽显然是无法胜任的。第一次相亲失败后,吴羽又陆续见了商人老廖,公务员老黄,教师老张。最后一次,她交往的是高中同学。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不是一次相亲,只能说是一次偶遇后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的聚会,唯一有点特殊的是,那个男同学小伟,曾经暗暗地喜欢过她,可那时的吴羽心里只有着自己的男友,哪里还容得下别人。从小伟的眼神里,吴羽知道小伟对自己依然保留着昔日的好感,便试着和他交往了一段时间,小伟殷勤地照顾着她,也曾用他那辆黑色的小轿车接送她上下班。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吴羽以为自己快要实现把自己嫁出去的目标,但好景不长,没多久,车间里八卦的大姐们便告诉她,小伟是个有家室的人,吴羽无比沮丧地退出了,小伟心存不甘,断断续续纠缠了她一段时间,见她冷若冰霜再无回头的可能,也渐渐没了踪影。在努力想把自己嫁出去的过程中,吴羽一点点意识到:青春妙龄时,爱情到来的是那样的容易,可一旦没了花样的容貌,就必须有着种种的附加价值去弥补,比如工作、房子和票子。相亲时的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价值的等量估换,就连小伟也不例外,虽然他已婚,却因为吴羽的年龄和自己还算可观的收入想要从吴羽这里交换到学生时代未能完成的心愿。当自己的年龄、相貌、收入、家庭被赤裸裸地被摆在桌面上被人掂来覆去估量时,吴羽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也在这样掂量着别人。每一次见面,吴羽都要经历着一次痛苦的回忆,几乎每一个前来相亲的人,包括小伟,都对她三十三岁却依旧单身存在疑虑,或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都对吴羽的过去存在着强烈的好奇心,吴羽无意对他们一一解释和前男友之间的恩怨情仇,却不得不在心里一次次痛苦地回忆起那一些不堪的过往,一次次去揭开那被爱情和友情同时背叛后留下的疤疥。在这样的心境下,那些男人的面孔竟一个个变得猥琐起来,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嫁出去,竟然比上火星还要难了。折腾来折腾去,却也暂时缓解了雨夜带来的不堪,那一颗硌人的石头也渐渐被磨平,偶尔发作也能很快便平息。
在清水公园和吴羽谈过话后,陆波发现他和吴羽再无机会有任何的正面接触,吴羽总是能够很巧妙地回避着他,这无疑让他有些不舒服,甚至还有那么点失落。对于吴羽的动向,他都一一从车间饶舌的女工嘴里得知,他本想不予理会,但在看到吴羽上了那辆黑色的小轿车时,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吴羽的种种好处,三班倒的乏味工作更显无趣,甚至他已经开始在悄悄地想念吴羽坐在自己后座的时光,想念夏日雨夜的那个吻。如果说之前吴羽对他而言是一块鸡肋,那么当这块鸡肋渐行渐远,甚至快要落入别人口中时,他才察觉这块鸡肋在他生活里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留在这个日趋破败让人颓废的工厂里的原因,是支撑他继续从事这个乏味且毫无前途的工作的精神支柱。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让他有些惶恐,纵然他在想念着吴羽,可如果让一个大他十一岁的女人成为他的女朋友,甚至变成妻子,那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且不说老妈那里过不了关,就连自己都会觉得憋屈。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对吴羽有些不解了,不过就是一个雨夜之吻,怎么就让之前那美妙的好感都分崩离析了?代沟,也许这就是三十三岁女人与二十二岁男人之间的代沟吧!当想到代沟这个词时,他赶紧一点点收回着心里那根越拉越长越飞越远的线,他仿佛看见线那端的他正张开了双臂想要去紧紧拥抱在空中独自徜徉的吴羽。
时间也许是世间最为公平的,它不曾为谁停留,也不曾为谁加快脚步,就那么不紧不慢地,在一声声的滴答声里静静地走着。转眼就是年关了,家家户户忙着采购年货,大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刚领了年终奖的吴羽,也想要为父母和弟弟购置些礼物,便约了罗大姐一起上街。大红的福字是贴在门上祈福的,鞭炮和烟花是为弟弟准备的,父亲腰不好,就给他买一双养脚的皮鞋,爱美却有些挑剔的母亲得给她买一套漂亮合身的衣服。在商城里,当吴羽看上了一件起着暗红色大花的外套,想象着母亲穿上的样子时,听到耳边有人问:“给谁买呢?”那声音似曾相识却又略有生疏,抬头一看,是那一张年轻帅气的脸,脸上有着似有似无的微笑。是陆波!吴羽突然觉得自己的心怦怦直跳,花了那么几秒的功夫,吴羽让它平静了下来,转头寻起了罗大姐:“咦!罗大姐呢?你没见她吗?”似乎这不是她和陆波自清水公园谈话后的第一次对话,似乎忘了雨夜早已成功地屏蔽了他们之间信息的传递。陆波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会,然后好像没听到她的问话似的,转眼看着那件起暗红色大花的外套自顾自地说:“我辞职了。”吴羽一惊,心跳重新加速,不由得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要辞职?辞职了你要怎么办?”陆波无所谓地笑了笑:“今天递的申请。”吴羽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再问:“为什么要辞职?”陆波微微顿了一下说:“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过完年可能会跟叔叔到广州学做生意。”在陆波说话的间隙,吴羽已从错愕中回过神来,她再次成功地抑制住心里的那一阵隐痛,故作轻松俏皮地说:“哦,也是,小池养不了大鱼呢,嘿嘿,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有那么一瞬间,陆波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很快,这张旺盛地分泌着青春荷尔蒙的年轻帅气的脸上便又挂上了那无谓的表情。两人挥手作别,陆波朝左边楼梯口走了去,他慢慢走着,感觉后背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但他没有回头,他要到楼下买些老妈爱吃的墨鱼仔。就在刚才,当他远远看见吴羽在挑选衣服时,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她,便走了过去,至于原因,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当下自己最想做的事。看着陆波的身影一点点消失在楼梯口,吴羽也向右边的楼梯口走了去,当她有些仓惶地走出商城时,冬日的太阳正穿过厚厚的云层,明晃晃地照在她身上,那光亮刺得她睁不开眼,也让她一下子想起:她忘了叫上罗大姐,忘了给母亲买那件暗红色大花的外套。
责任编辑 李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