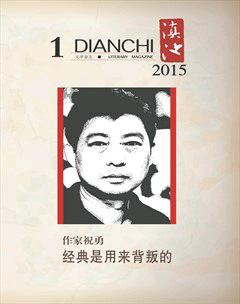有糖的日子
廖会芹
一
奶奶在去山上的路上被村里的光棍二狗拦住了。二狗奸邪地笑着,他称我二十六岁的奶奶为兰兰。兰兰,他说,昨天晚上我去敲你的门,你怎么不开呢?说着话,他的那双还沾着猪粪的手就朝我奶奶的胸口袭来。二狗那时正在地里给菜施肥,看到我奶奶,他就火烧火燎地拦住了我奶奶的去路。
那双臭烘烘的手让我奶奶恶心,她朝后退了一步。奶奶那时要到山上割茅草,她手里拿着一根皮条和一把镰刀,她把手里的镰刀举起来。你再敢靠近一步,我就杀了你,奶奶声音像冬天的白霜,冰冷而刺骨。许是这凌厉的声音吓坏了光棍二狗,他讪笑着往后退。你男人早被子弹打死了,你还为他守着干什么?我迟早要把你变成我的人,二狗朝我奶奶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然后逃之夭夭。
我奶奶身上的气力仿佛瞬间被风干了一样,她没有力量再朝山里迈进一步,她瘫坐在路边。她空洞的没有任何颜色的目光飘向村口的小路,她的男人,真得不会再从那里出现了吗?
四年前,国民党抓壮丁,当时正挑着一担柴往家里走的爷爷被抓走了。他这一走就没了音信。村里的人都说我的爷爷早吃了子弹了。对这些猜测,我的奶奶刚开始是表现出淡然的微笑,她不相信那么个大活人瞬间就能消失。可随着时光一天天对她心灵的侵蚀,当有人再说起这样话的时候,她的心漂浮起来,她仿佛置身一个无边无际的荒漠,她把干枯的目光一次次投到村口的那条小路上,她多么希望在那条唯一通向外面的路上能够看到那个高大潇洒的身影。
而此时,奶奶被村里的光棍二狗盯上了。二狗很小的时候爹就饿死了,只剩了他和老母住在村头两间狭小的茅草房里。因着穷,二狗三十五岁都还没有机会当上新郎官。眼看认识的女人一个个都有了男人,他每天都心急火燎,后来,他就瞄上了可能已经成为了寡妇的奶奶。以他的家庭和年龄,他只配得上一个寡妇。
每当浓鼻涕一样的暮色慢慢淹过这个名叫鸡屎塔的村落时,这个名叫二狗的光棍就会抹布样放在奶奶门前的碾子上。所以,奶奶每天踢着暮色回家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放在门口的这块抹布。
一看到我的奶奶,抹布就会把他呆呆痴痴的目光放到她的身上。自从在路上拦截我的奶奶被她手里的镰刀吓住后,他再也不敢靠近我的奶奶,因为从那以后,我奶奶走路时手里总是握着一把镰刀。
二
我爷爷的父亲,我的太祖父是个种庄稼的好手,他靠着租种地主的几亩田地,农闲时做点小生意而盖起了一所青砖瓦房。只可惜,太祖父在我爷爷只有三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太奶奶辛辛苦苦给我的爷爷娶了媳妇,在我父亲只有半岁时她也撒手人寰。
爷爷的大伯和叔叔们还住着茅草房,他们也想住进青砖瓦房里。随着住在青砖瓦房里的人一个个死去,他们的心动了,现在,他们只要把住在青砖瓦房的外姓女人赶出去,他们就能顺理成章住进去了。于是,他们就给我的奶奶做媒,对象是二狗。
一个寡妇,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能有人要就不错了,何况人家还是一个童男呢,爷爷的大伯说。我的奶奶不同意,她说孩子他爸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就出现在村口那条小路上了,那时她该怎么办?
四年都没有一点消息,肯定已经吃了流弹了,爷爷的叔叔说。
也是,或许真是在战场上哧溜一颗子弹飞来,爷爷就倒在了一块未知的黄土地上了吧,每当奶奶假设这样的情景时,她就会泪流满面。从今往后,自己就是一个寡妇了,奶奶想。但不管如何,她都不会嫁给二狗的,看看二狗是个怎样的人吧,身材矮小,暴牙,常年穿一件挂满补丁的衣服,不管什么时候走过总会有一股子难闻的味。
这样的二狗能跟爷爷相提并论吗?爷爷一表人才,他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吸引人的目光,奶奶常常能为嫁给这样的人感到骄傲。
我不会嫁二夫的,奶奶说,他还有儿子,即使我的丈夫不在了,我也会把他的儿子养大,让他的香火能够继续燃烧下去。
爷爷的大伯和叔叔无话可说。爷爷的儿子是李家的根,他们无法把这根抹去。
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回来了。就在爷爷回来的那个白天,我奶奶去地里的时候还朝村口的小路望了很久,只是她除了看见一只麻雀从眼前飞过,其余她什么都没有看到。其实她也不奢望能看到什么,只不过朝那条小路望上几眼,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可就在她已经绝望的时候,我的爷爷竟会突然降在我奶奶的面前。那个夜晚,夜色有几千米深,我的奶奶和我的父亲已躺在了床上,奶奶正给父亲讲狼来了的故事,这时,门就响了。嘟嘟嘟,声音穿透了浓稠的黑暗传进了奶奶和父亲的耳膜。刚开始,奶奶和父亲没有注意,后来,嘟嘟嘟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父亲听到了,他说狼来了。他知道狼是会吃人的,所以说完他就紧紧抱住了奶奶。奶奶不害怕,每天蹴在门口的二狗时不时会这样嘟嘟嘟敲她的门。
兰秀,兰秀,门缝里传来轻轻喊她的声音。二狗每次叫她都是兰兰,这会是谁呢?奶奶从床上爬起来朝门口走去。谁呀,她颤着声音问。是我呀,我是李宝才呀,门外的人轻轻回应。奶奶不相信站在门外的就是李宝才,她慌慌忙忙拔掉门闩。
门口挤进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真的是李宝才,奶奶眼里的泪哗哗哗就下来了,她紧紧抱住了李宝才的腰。你怎么不给我捎个信呢?奶奶哽着声音问李宝才。爷爷没有回答奶奶,他只是问奶奶,门前碾子上的男人是谁,半天不动一下,害得他缩在稻草堆里很长时间。
暗夜里,我五岁的父亲睁着亮亮的眼睛看着眼前两个模糊的黑影,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名叫李宝才的人是他的父亲。
三
爷爷的回来给我奶奶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她早早出去干活的时候脸上会有微微的笑。她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若有所思的样子,走着走着嘴角就会绽出一抹笑。最先发现这些变化的是二狗。自从我爷爷杳无音信后,我奶奶就很少现出笑容了。二狗堵住我的奶奶。你这几天脸色红润,是不是有野男人了?二狗问。
仿佛天边的朝霞瞬间粘到了我奶奶的脸上,她红着脸骂二狗不要脸。
我不要脸,我只想要你,二狗说着又想往奶奶身边蹭,我的奶奶举起了手,但她的手上忘记了拿镰刀。她举起了锄头。
没有谁知道我爷爷的回来,包括爷爷的大伯和叔叔。大伯和叔叔是爷爷最近的亲属,但他不敢出去,也不敢见任何人,他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要是被人报信抓回去是要杀头的,所以他回来之后整天就躲在家里,奶奶出门的时候,就从外面把门锁上。
爷爷回来的时候正是农耕时节,奶奶一个人忙着犁田插秧,还要记挂着给爷爷做饭。她几乎在路上都是小跑着。兰秀,你跑什么呢?村里人问她。忙着做饭给孩子吃呢,她回答,声音清脆响亮。
有心的人是会听得出她的声音里是含着甜味的。这有什么呢,她小跑着回家,就是想和自己的丈夫多呆一会,他们分开四年了,要是不怕别人猜疑,她真想大步跑回家呢。
而我的父亲,他对这个贸然的闯入者,充满了戒备。以前,母亲总是搂着自己睡觉的,可有一天半夜他起来撒尿,他发觉母亲竟然搂着这个男人;以前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把好吃的夹到自己的碗里,现在,好吃的都跑到这个男人的碗里了。这样,五岁的父亲狠狠地记住了他的样子:高个,俊朗的脸,更主要的,他的右眼角处有个豆大的疤。
现在他已经知道,这个总是躺在床上的男人是他的爸爸,村里和他一般大的小朋友都有爸爸,现在他也有爸爸了,可自己的爸爸和其他小朋友的爸爸有点不一样,他总躲在屋里,连屎尿都是妈妈帮他倒出去,他也不大和自己的孩子说话,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目光搁到外面的天空。有的时候,他也会逗弄一下自己五岁的儿子,但显然,四年的时间阻隔了他们,当爸爸要抱他搂他的时候,他总是把他推开,他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爱抚。
我相信,如果我的爷爷能够留下来,即使他每天都躲在床上,我的奶奶也会把他伺候得像皇帝一样。我父亲和他之间几千年的距离也会雪一样消失融化,可是,他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
四
我的爷爷是在他回来半个月之后走的。走之前,他仔细观察了二狗的行动。二狗一般是在夜幕降下的时候蹲在奶奶门前的碾子上的,他咕噜咕噜吸一个水烟筒,他的目光朝着我奶奶回来的方向。直到我的奶奶进屋点上油灯,闩上门,然后,他就离开。
爷爷站在楼上的窗子前静静地看着蹲在碾子上吸水烟筒的男人。他是不是喜欢你?爷爷说。奶奶的脸红了。管他呢,我又不理他,奶奶说。总有一天,我会要了他的命,爷爷说。
爷爷走的时候,他没有要了二狗的命。他走的时候天蒙蒙亮,奶奶已经早起到地里干活,他悄悄起床,看了熟睡的孩子一眼,然后,轻轻拉开门,瞬间就消失在了小路的尽头。很多年之后,我的父亲在想象爷爷离家的场景时,我的父亲会想,离家的时候,他有没有回头呢?
想要答案,父亲只要问一问爷爷就可以了,但父亲没问,他不想和自己的父亲说任何一句话。他只知道,那天,当我的奶奶急匆匆从地里赶回来给爷爷做饭的时候,家里已经没了爷爷。楼上,床下,甚至立在墙角装猪食的瓦罐,她都没有放过,但都没有找到爷爷。爷爷走了,和四年间的杳无音信一样,爷爷再次销声匿迹。他走时,还带走了奶奶几年间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十块大洋。
奶奶伤心欲绝,她坐在门槛上放声大哭。那一声声悲绝的哭喊声穿过云霄,也穿透了父亲的心脏,一辈子,父亲耳边时不时就会出现那悲绝的哭喊声。
直到许多年之后,父亲才明白爷爷离家的真正原因:为了一个寡妇,爷爷抛家离子。
爷爷被抓了壮丁后,他和好几十个村民被押解到附近一个村庄关押起来,第二天,一脸肥肉的排长命令他们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他们拿来的国民党军装,从此,他们就被迫背着弹药跟随部队四处征战。他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很多时候都没有东西吃;有时连喝的水都没有,而且很多地方的水,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患了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有很多死去的壮丁。死了的壮丁,被草草埋进土里,往往还有一条腿或一只手暴露在地面上,有的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他们的手似乎还在抽搐着。而那些野狗为了争吃壮丁的尸体血红着眼睛发着一声声厉声的嚎叫!
我的爷爷在野狗厉声的嚎叫声中魂飞魄散,这样的日子,他死也是不要去过的,所以,他总是寻找机会逃跑,只是他太胆小,怕逃跑不成被抓回去杀头,我的爷爷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一等就是四年。那天,排长到营部开会去了,几个当官的在一起赌博,爷爷和班长被派去山上放哨。爷爷就趁班长不注意的时候朝他偷袭,班长却是习过武的,他转过身来,顺势就把爷爷压在了身下。爷爷不甘这样丧命,他拼命反抗。后来班长拔出匕首刺入了我爷爷的胸膛。
爷爷是在第二天下午醒来的,班长的那一刀没有要了他的命。那时他的部队已经离开,他艰难地爬到半山腰上一户人家门口。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杨菊香,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她把几近要昏迷的爷爷搀进家里。她给爷爷端来了饭,帮爷爷包扎好了伤口。这样,爷爷在杨菊香家一住就是三个月。三个月里,杨菊香给我爷爷换药,熬汤。
五
爷爷的伤好了,可他竟然不想回家了。他只想和杨菊香呆在一起。他看杨菊香坐在小凳子上把一颗颗的包谷粒从玉米棒上掰下来。那是他们的粮食,杨菊香要用石磨把包谷磨碎,然后用筛子去皮,再放入甑中蒸熟透做成包谷饭。
落日的余辉静静地披在杨菊香的身上,她五官精致,稍稍上翘的睫毛低垂着。这个女人很漂亮呢,爷爷想,她该是要生在大户人家过好日子的呢。想着,爷爷就说了,你该是要生在大户人家的吧。
什么?杨菊香脸红了,我哪有那样的命哟,人生来不就是要吃苦的吗?
杨菊香仿佛确实是来吃苦的,她的父母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她独自一人随了些逃难的人来到了云南,然后经人介绍嫁了她的男人,可热乎乎的日子没过上多久,男人到集上卖土豆的时候被抓了丁,没多久部队给她传来了信息,说她的丈夫在队伍要开拔时病死了。
我爷爷喜欢看杨菊香稍稍上翘的睫毛,喜欢看她挑着箩筐腰肢扭动的样子。总之,和杨菊香呆在一起,他心里总会涌出一股欢喜,甚至吃包谷饭都能嚼出一股甜味。
他忘记了我的奶奶。
其实,我的奶奶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大得且水汪着的眼睛,苗条的且凹凸着的身材,可我的爷爷真真是忘记了我的奶奶,四年的时光,我奶奶在他心里只剩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可他是要回家的呀,他千方百计逃出来不就是要回家的吗?家里有一个叫兰秀的女人和一个已经五岁的儿子在等着他。
怎么办呢?他的伤已经好了,他可以下地了,他可以帮寡妇杨菊香劈柴了,他可以跟在杨菊香的身后下地了。
可他不想回去了,那个叫兰秀的女人,当时是由媒人上门提了亲,双方见过一面后就结了婚的,那一面还因自己太害羞而没有仔细看过,结婚仅两年自己又被抓了丁;儿子呢,自己被抓走的时候才一岁,自己和儿子也是陌生的。他现在果真要回到自己陌生的家吗?
你要回家了吧?杨菊香对身后的李宝才说,你的伤好了呢。
我的爷爷不知怎么回答,他在杨菊香的家又呆了一个月。该走了,再不走,他真不会走了,邻居的风言风语已经刮进耳朵了。
他悄悄潜回了家,而他在家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怕被人发觉告密,他整天整天就躺在家里。这种日子他是不要的,一个大男人,难道一辈子就躺在床上了吗?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更要紧的,他撕心裂肺地思念寡妇杨菊香。那时他才发觉日子和日子原来是不同的。和兰秀在一起的是正儿八经的日子,平淡,苍白,没有油盐;和杨菊香在一起,是加了糖的。那个时候,我的爷爷是多么想过加了糖的日子啊,所以他悄悄地来,又决定悄悄地逃离了。
就这样,我的爷爷去过有糖的日子了。
六
而我的奶奶和我的父亲只有过比黄连还苦的日子了。
没有钱买米,奶奶和我的父亲只有吃野菜;没钱买衣,奶奶只有一个补丁再压上另一个补丁。
可这些都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爷爷离开后没几天,奶奶就发觉出大事了。不管日子多么艰难,二十六岁的奶奶体内那鲜红的生命之血每月都会按时喷涌而出,可那个月没有,已经是月底了。刚开始,奶奶并没有注意,自从爷爷离开后,她整天以泪洗面,她丝毫都想不起来那个会自然到来的东西,直到偶然看到村里女人偷偷晒着的卫生带。刚想起那个东西时,奶奶马上就惊出一身冷汗,该不是出问题了吧?可奶奶转而又安慰自己,也许是记错日子了?要不是身上出什么毛病了?她只有惴惴地等待。
第二个月,奶奶是掰着指头数日子了,现在,奶奶更关心的已经不是爷爷,爷爷已经退到日子的后面。直到第三个月,奶奶才真真慌神了。她找了郎中,郎中给她把了脉,然后告诉她是有喜了。
奶奶觉得天都要塌下了,她该怎么办好呢?村里没有哪个人见过爷爷回来,她将要隆起的肚子会告诉所有人,她是一个淫妇,她是一只破鞋。她想一头跳进村里的塘子,可她就在要纵身一跃地时候想到了我的父亲。她死了,五岁的儿子怎么办呢?
她拖着重重的身子回到家。她搂过懵懂的儿子放声大哭。
奶奶用宽大的衣服把自己罩了起来,她挑很重的担子,她甚至用棍子捶打自己的肚子,她想把肚里的东西弄出来,可东西长得太牢固了,不管用什么方法,它都无动于衷。
村里已经风言风语。
有人猜说奶奶肚里的孩子该是二狗的,二狗每天都蹲在人家门口,女人守不住,终究给他沾了荤吧。
有人从奶奶手里提着的镰刀想到她可能是和二狗以外的哪个野男人做了露水夫妻,最终纸包不住火了。
爷爷的伯伯婶婶们再次上门,这次,他们有了正当的理由。他们骂我奶奶伤风败俗,把他们李家的脸都给丢尽了,他们希望我的奶奶趁早卷着铺盖滚蛋,不要辱没了李家的祖宗,要不然,他们就按以前的家法,把我的奶奶拖去填湖。
奶奶辩解说李宝才来过了,肚里的孩子就是他的。
他来过了,那人呢?爷爷的大伯说,他回来了怎么不去看望我们呢?
他怕再被抓走,奶奶说,他现在又走了。
他来了,又走了,这种话谁相信呢?爷爷的叔叔说,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呢?
奶奶沉默了,这种话谁会相信呢?谁看到他来了,又走了呢?
奶奶叫来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说他的爸爸回来了,他整天躺在床上,后来在一个早晨,他又没了。
伯伯婶婶们还是不相信,他们说我的父亲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撒谎,这一切都是源于奶奶的教唆,奶奶如果不离开,那就会强行把他们母子俩赶出家门。
奶奶跪到地上,她恳求各位长辈不要把他们孤儿寡母赶出去,要不然,他们会冻死在荒郊野外的,看在她为李家添了香火的份上,能够让她留下来,自己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
几个长辈不说话了,他们把目光投到了大伯身上。大伯咕噜咕噜吸了一口水烟筒,最后他说,孩子可以留下,你必须走人。
奶奶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她举起每天拿着的那把镰刀,她用刀尖指着自己的脖子,冷冷地说,你们不就是想霸占我家的财产吗?如果谁把我赶出去,我就死在谁家门口。
七
谁也不想让我的奶奶死在自家的门口,于是,爷爷的大伯叔叔们放弃了住进青砖瓦房的想法。
可这时,我的爷爷再次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那是秋天,一个寒风呼啸的傍晚,因为天冷,二狗在奶奶门前的时间减少,这时,我的爷爷又悄悄回来了。这个时间是他精心策划的,他不能让村里的任何人看见他。
我的父亲正把碾子旁的一个土坷垃搬开,一群蚂蚁从那石头下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他专注地看着那群蚂蚁,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影已经鬼鬼祟祟地靠近了他。你干什么呢?人影说。突然冒出的声音吓住了我的父亲,他吃惊地抬起头,他就看到了站在自己面前的人,这个人他曾经狠狠地记住了他的样子,高个,俊朗的脸,右眼角处有个豆大的疤。
你妈妈呢?人影问。我的父亲没有说话。我是你的爸爸呀,来人捉住了我父亲的小手。
我的父亲呆呆看着眼前自称是爸爸的人,他回忆起了右眼角下毛毛虫样的疤。
你想坐火车吗?我的爷爷问我的父亲。火车?我的父亲只见过马车、牛车,火车是什么东西呢?火车会着火吗?我的父亲问。
我的爷爷笑了,他不着火,他冒烟。
我的父亲沉默了,显然,他被火车吸引了。我的爷爷顺势拉起我父亲的手,走,我带你坐火车去。
我的父亲就跟着我的爷爷朝村里唯一的路上走了。我的父亲没有回头朝村里望上一眼。很多年后,当我的父亲回忆起这个场景时他就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不回头看一眼呢,那是他出生并且生长了的地方,那是他的家乡,那里有生他养他的母亲。但他没有,他心里只想着火车。
而我的父亲更不能原谅我的爷爷,每一次地离开,他都回过头看一眼那块他熟悉的土地还有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吗?没有,至少,那次,我的爷爷是那样的惊慌失措,步履匆匆,他拉着我父亲的手拼命地朝前走,他只想快速地走进夜里。
由此,我的父亲得出结论,我的爷爷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他为了自己的私欲,不顾别人的死活,特别是我奶奶的死活,他应该明白,他这样把孩子带走,会要了我奶奶的命。
我的父亲不明白,世上怎么会有那样的男人。
八
那时,我的奶奶背着我的姑姑到地里去栽菜了。她回来的时候,她没有看到每天都在门口玩耍的儿子。她问蹲在碾子上的二狗有没有看到根柱,根柱是我父亲的名字。
没有,二狗说。二狗非常高兴,我的奶奶从来没有这样友好地和他说过话。奶奶没顾上二狗发出的邪笑。有的时候,我的父亲也会和其他小朋友到其他地方玩。我的奶奶就四处呼喊根柱,根柱。她青紫青紫的喊声响彻云霄。
天黑了,她喊遍了全村,村里的人都说没有看到过根柱。我奶奶的心扑扑狂跳起来,莫不是孩子遭遇了什么不测?她哪知道,当年土地改革,为了多分一亩地,我的爷爷回来把我的父亲骗走了。
那个傍晚,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北风呼呼地撕扯着路两旁的荆棘。我的父亲跟着我的爷爷坐上了船,坐上了汽车,最后坐上了会冒烟的火车。父亲坐上的就是我们所说小火车,一排比我父亲还高的红色大车轮,冒着蒸汽,火车头后面拖着暗绿色的木车厢。我的父亲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他眼睛不眨地看着窗外广阔无边荒凉的黄土地,看着奔跑着的绿气腾腾的山野,看着潺潺的溪水,灿灿的野花,袅袅的炊烟,白白的羊群,湍急的水流……直到他在火车的哐当哐当声中进入梦乡。
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梦呀,以至于直到他最后离开那里,他都觉得那梦没有醒来,而他也多么希望那一切都只是梦。
九
事实上,那不是梦,那是真真实实的生活。也就是说,我的父亲睡了一觉醒来,就到了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地方。那是属于滇南的一个荒僻的山村,房子是茅草顶,村庄后面的山坡上种着大片大片的香蕉树。
杨菊香对我的父亲很热情,她摸我父亲的头,她给我的父亲搬来了香蕉。我的父亲没吃,他躲到了我爷爷的身后。
随后家里跑进了一个和父亲一般大的小男孩,我的爷爷叫他根宝。根宝,过来叫哥哥,我的爷爷从身后拉出我的父亲。这是根宝,我的爷爷对我的父亲说,他比你小,是你的弟弟,你们俩的名字中都有根字,这是缘分呢。
我的父亲哭了,他对我的爷爷说他要回家,他要找妈妈。
我的爷爷搂过嚎哭着的父亲。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我的爷爷说。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把那个家当作是家,在他的记忆里,他的家是青砖瓦房,门前有一块场,场上立着一个碾子。她的母亲,在天空蓝蓝的午后,会坐在门口,给他纳鞋。母亲忙碌的时候,他就是妈妈的小尾巴。妈妈挖地,他就在树底下看蚂蚁搬家;妈妈割稻,他就在田里追蚂蚱。
现在,他的妈妈没了,他的父亲让他喊另一个女人为妈妈。我的父亲紧紧咬着嘴唇。在那段日子里,我的父亲几乎成了一个哑巴。那个叫根宝的小男孩和他说话,哥哥,我们一起玩打仗,好不好?而我的父亲则站起来坐到了门口的石头上。
我的爷爷和杨菊香拼了命在香蕉地里劳作,有了我父亲的加入,家里多分了十亩地。香蕉似乎也知道有一个叫根柱的人进入了家里,所以,一串串的香蕉挂满了枝头。我的爷爷看着那些香蕉咧开了嘴巴。
可杨菊香没咧嘴巴,相反,她的眉头拧成了一股麻花。根柱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会不会憋坏呀?送他去读书吧,杨菊香说。就这样,我的父亲进了学堂。那个时候,很少有农民能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包括杨菊香的儿子根宝,他每天只有跟在我爷爷和他母亲后面到香蕉地里除草施肥,他的小脸大都时候都晒得通红,每天早晨,他都羡慕地看着我的父亲背着蓝黑色带盖的帆布书包走向学校。
我的父亲学习非常努力,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学会写字,他要把憋在心里的话写给远方的妈妈。在空闲的时候,他把年幼的目光搁到天空漂浮的云朵上,他常常在酝酿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封信。妈妈,亲爱的妈妈,这是他早已想好的开头。
妈妈是先笑还是先哭呢?我的父亲无法想象我奶奶收到这封信时的样子。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呼啦啦飘过,一只只小鸟扑棱着翅膀在云朵下飞。如果自己是天空中的一只小鸟那该多好啊,那样,即使是千山万水,自己都可以飞到妈妈的肩头,朝她唧唧啾啾。
妈妈早该以为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了吧,我的父亲想,她会想到是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儿子骗走吗?她接到这封信,听到儿子在一张薄薄的纸上对着她喊妈妈时,她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我的父亲无法想象那样的场景,他知道他是我奶奶的命,当一个人的命失而复得时,那该是怎样的呢?
但是,当我的父亲把自己的情况写在纸上想要寄给远方的母亲时,他突然才明白自己竟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名字写在纸上应该是怎样的几个字。
十
我的父亲那时还不知道,在他丢失后,我的奶奶就抱着我的姑姑准备跳湖自尽了。在离鸡屎塔七八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湖,湖水清澈见底,每年到了渔汛期,湖边的人家用篓就可以撮上鱼来。我的奶奶抱着我的姑姑,她想到那样的地方去死,那样的地方宽阔,干净,我奶奶觉得她活得太憋屈了,既然死,那就找一个让她的心能舒展开的地方。出门的时候,吹来的风尖刀样割着她的脸。到了湖边,她没有犹豫,她下了水,她白痴痴的目光坚定地朝向远方。儿子,我来了,你在哪儿呢?她眼里满是泪水。
怀里的婴儿仿佛知道自己的遭遇一样,她突然大哭起来。我的奶奶打了一个哆嗦,她朝怀里看了一眼,女儿粉嫩的小脸让她停了下来。
假如我的根宝还没有死呢?奶奶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有一天他回来,我不在了,那他怎么办呢?我的奶奶停住了脚步,后来她转过身,慢慢朝岸边走来。
她要回家去等她的儿子回来。只是这一等,竟然就是十多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的奶奶已不抱任何希望,她早以为她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
而如同当年我的爷爷一样,我的父亲突然就降落在她的面前。
那一年我的父亲已经是省城的一名大学生,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学生装,他朝村口的那条小路回家,小路没变,依旧是他离家时的样子,最后他站到了一所青砖瓦房前。青砖瓦房的墙已经显得破旧,他推开了虚掩着的门。门内却已不是他所熟悉的景象,原来一推开门就是一大个院子,现在院子已经用土坯砌成一个个的房间,有的房里传出炒菜的香味,有的房里传出猪哼的唧唧声。
这已经不是他记忆里的那个家,他以为自己走错了,可是门口的那块场,场上的那个碾子,那都是用刀刻在脑海里的,怎么会错呢?
一个小媳妇模样的女人出来倒水,看到了站在院子正中的人。你找谁呀?这个女人显出了惊讶。鸡屎塔何曾会出现这样的人呢,高高的个儿,健朗的脸。我找我妈,我的父亲说,她原来住在这里。
你妈?小媳妇不明白,自从她嫁到这里,她就和丈夫的几个堂伯兄弟住在这里,从没有听说过这里还住过一个母亲。
你妈叫什么名字?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年轻的男人,他应该是小媳妇的丈夫。
兰秀。我的父亲说。
兰秀,是谁呢?对于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女人,在农村,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她们的名字的,他们只知道某某的妈。女人有了孩子,就叫某某的妈。
门口已经聚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村里很少来外人,我的父亲一进村,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你是不是根柱呀?人群中有一个稍微上了岁数的人问我的父亲。我是根柱,父亲的眼泪下来了,我的妈妈,她在哪呢?
人们簇拥着朝村头走去。有人早早地跑去报信,所以,当我的父亲站在那矮小的茅屋房前时,我的父亲看到了他日思夜想的那张脸。只是,那张脸早已沟壑纵横,头上已是满头白发。他的母亲只有四十多岁,可看上去,仿佛就是六十岁的样子了。
你真的是我的根柱吗?我的奶奶一看到我的父亲就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他,何须多说什么呢,我的父亲,几乎长得和我的爷爷一模一样。
十一
我的父亲和我的奶奶跨进茅草房的时候,我父亲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身材矮小,暴牙,只是身上的补丁干净整齐。我的父亲疑惑地看着我的奶奶。
他是二狗,我的奶奶说。
我父亲记忆里出现了奶奶手里提着的那把镰刀。
我后来嫁给二狗了,我的奶奶又说。
我的奶奶抱着我的姑姑从湖边回来后,她本是要想好好地活下去的,她给自己煮了三个糖煮鸡蛋,她对自己说要好好活下去,一定要等自己的根柱回来找她。只是,她的生活由不得她做主。
看着我的奶奶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我爷爷的伯伯叔叔们又动起了脑筋。对付一个外村嫁过来的一个女人,他们轻而易举。他们找到二狗,他们对二狗说,他们有办法让兰秀嫁给他,但条件是,兰秀的那所青砖瓦房必须给他们。二狗答应了。
那天晚上,他们撑着二狗从墙头跳进我奶奶的院子,然后婶婶敲门,当奶奶从卧室出去开门的时候,二狗趁机钻进了我奶奶的卧室。当奶奶看到门口没人转回床上躺着的时候,二狗就压到了我奶奶身上。我的奶奶拼命反抗,她用嘴咬二狗的手,用脚踢二狗的下身。只是,那时,我的奶奶手里没有镰刀,她只有被二狗紧紧地按在床上。
之后,我爷爷的大伯叔叔婶婶们冲进房里。这样,我奶奶私通男人铁证如山。
我的奶奶只有嫁给了她最看不起的二狗,当她和二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奶奶妥协了。她开始给二狗收拾茅屋,给二狗缝补衣服。二狗,像一条忠实的狗,整天跟在奶奶的身后。他对我挺好的,奶奶对我的父亲说,比你爹强。
我的父亲,泪流满面。
十二
自从我的父亲和奶奶再次相聚之后,我的奶奶就想给我的父亲说一门亲。以我父亲潇洒又是大学生的条件,我奶奶所知道的适龄女孩子应该没有哪一个不想嫁给他,所以,当我的奶奶只稍稍流露出这个意思的时候,村里那些有适龄女孩的人家就托媒人上门提亲了。那是我奶奶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她左挑右选,最后终于确定了我的母亲。
我奶奶挑选儿媳妇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人好,在她看来,人好是作为儿媳甚至是作为人应该具备的第一大标准。人好,就会对她的儿子好,也才会对她好,总不能找个儿媳妇以后对她恶言相向吧?我外婆的家和奶奶家只一墙之隔,应该说,我的母亲就是我奶奶看着长大的,她知道我的母亲从小就懂事安分,温柔贤淑。第二点,一个女人要能里外操持一个家,要不然,即使男的能赚来一座金山银山,也做不起人家。我外婆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我母亲从小就开始计划家里的一切经济吃账,这一点,我的奶奶对我的母亲是相当满意的。第三点呢,就是相貌了,为了能配得上她的儿子,当然还是要有一点姿色的。我的母亲皮肤白里透红,就是个子有点矮,但这并不影响什么。
我的父亲不同意,他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跳了出来,他不想再娶一个连书都没有读过的女人做老婆。他对我的奶奶说,他还在读书,他不想那么早结婚。
在这件事上,我的奶奶却是深思熟虑。她对我的父亲说如果以后他娶一个外地老婆,那他就会和他的老婆回老丈人家,就会不来看她了。
对于奶奶的逻辑,我的父亲哭笑不得。我不管娶哪里的女人,我总会来看你的呀,我父亲对我奶奶说。
那不一样,我的奶奶说,你娶一个外地女人,逢年过节总会跟着人家去了,现在,你娶了桂枝,那逢年过节你们都会回同一个地方,我就能看到你了。桂枝是我母亲的名字。
父亲同意了这门亲事,父亲觉得,不管我的奶奶有什么样的愿望,他都应该满足她。
十三
父亲大学毕业了,因为户口在爷爷那边,所以他分回了那个他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但他很少回我爷爷的那个家。
和我母亲结婚后,我的父亲把我母亲带到他工作的地方,每月他要从30多元的工资中寄回15元给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成了鸡屎塔第一个能上邮局拿汇款的人。
我奶奶也成了一个让人羡慕的人。连她自己说话的时候,声音都高亢起来。甚至在某一个时候,她还站到已略显破败的青砖瓦房前对自己说,总有一天,要盖一所自己的青砖瓦房。
更高兴的是,在我的奶奶拼命劳作拼命攒钱盖青砖瓦房的时候,我的父亲给她捎信说,她要当奶奶了。要当奶奶了,我的奶奶兴奋异常。她买来了很多只母鸡,她一天天掰着指头数她大孙子出生的日子。
在我母亲快要生产的时候,她提着满满一篮鸡蛋上路了。她沿着我父亲当初走的路线先坐上船,然后坐上了汽车,再坐上了小火车。那是我奶奶第一次坐火车,她看着窗外广阔无边荒凉的黄土地,看着奔跑着的绿气腾腾的山野,看着潺潺的溪水,灿灿的野花,袅袅的炊烟,白白的羊群,湍急的水流……
她还要去看她的孙子。
但是,我的奶奶永远定格在了四十三岁。
火车轨道的上方,有一条沿半山腰而修的土路。奶奶出行的这一天,天上下了一点小雨。由于路滑,在土路上行驶的一辆拉着钢筋的大货车翻下了2米多高的土路,正好压在刚刚通过的小火车上。一根钢筋直直地刺穿我奶奶的心脏。
我的父亲拼命地用头撞墙。不可以,他哭着喊,这不可以。
送走了我的奶奶,我的父亲沉默下来,他不能接受奶奶已经走了的事实,他整夜坐在客厅。他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他眼睛血红。他把罪过归结到我母亲身上,如果不是你生孩子,那我妈就不会死了,我的父亲对我母亲说。我的母亲隐忍下来,她给我的父亲倒了一杯水。如果这样的发泄能让我父亲好过一点,她是不会有任何反驳的。
都是我害死了她,我的父亲哇哇大哭起来,像一个孩子。我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这怎么能怪你呢?许是妈妈的命运吧,我的母亲说。
这一切都怪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父亲抬起头来看着我的母亲,要不是他把我骗到这里来,那我的母亲就不会坐火车,不坐火车她就不会死,是不是?是不是?我的父亲一遍遍问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无言以对,世上如果有如果,那会怎么样呢?
我父亲最终把我奶奶的死归到我爷爷的身上,他对我的爷爷更是恨入骨髓。
我父亲不明白,那有糖的日子真就那么好过吗?
十四
我的父亲是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尝到我爷爷所说的糖一样的日子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师,当时他们学校有一个刚分来的女教师,长得眉清目秀。我父亲和她的办公桌相连,那个女教师经常找父亲讨论备课上课的事情。时间一长,那个女教师看我父亲的眼神不对劲了。没人的时候,她就拄着下巴,静静地看着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有时从学生的作业本上抬起头,就看到了那双痴痴汪汪的眼睛。
我的父亲就化在那双眼睛里了。他会突然间很高兴地就大声唱起歌来,他可是从来都不喜欢唱歌的一个人。他每天都盼着天亮,天亮他就能和那个女教师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了。我的父亲觉得他的生活好像加了糖,那是和我母亲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
他似乎有点理解了他的父亲,那个一心想过有糖日子的男人。
女教师在痴痴看着我父亲的时候,我的母亲正呆在学校里某间破烂的房里为他和三个孩子做饭。我父亲的工资已经不够那么一大家人吃饭,为了贴补家用,我的母亲把一家人的饭做好之后,她还要到学校的食堂帮忙做饭,学校每月给她10元钱的工资。每月,她还要背着我的父亲把节省下来的5元钱寄给乡下的爷爷。
刚开始几天,我的父亲沉浸在有糖的日子的美妙中,可接下来,他尝到了痛苦。他每天想的是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散步。现在,他却每天不得不走进有另一个女人的家,不得不和这个女人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我的父亲痛苦万分,他食不知味。父亲甚至有点嫉妒起我的爷爷来,我的爷爷不管不顾地去过自己有糖的日子了,自己能有那样的勇气吗?
父亲想离婚,但他知道我母亲肯定不会同意,于是,他和女教师相约着私奔。我的父亲悄悄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他对我的母亲说他要去省城进修。他和女教师上了车,他找了一个临窗的座位,这时,他想起了我的奶奶。
桂枝会去自杀吗?我走了,我的三个孩子怎么办?我的父亲想,我怎么能像那个人呢,我不是用了一生的大半时间来恨那个人,难道自己也要成为那样的人吗?
显然,这是他不愿意的。他下了车。车开动了,那个上海女教师流着泪从窗口不停地朝他挥手……
十五
现在,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他和我的母亲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地方。他们在城里买了房,他们老两口每天都一起买菜,一起散步。
我问我的父亲,有糖的日子是不是很甜?
我的父亲有点害羞,我们家里人都知道他和我爷爷有糖的日子的故事。糖吃多了,会得蛀牙的,我的父亲说。
那你爹不是早得蛀牙了?我的母亲反过来问我的父亲。
你没看见他死的时候满嘴都没牙了吗?肯定是蛀牙闹的,我的父亲回答我的母亲。
我们都笑了,我不知道我父亲和我母亲现在是不是过着有糖的日子,但我看到,我父亲笑的时候,他的嘴里满是蛀牙。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