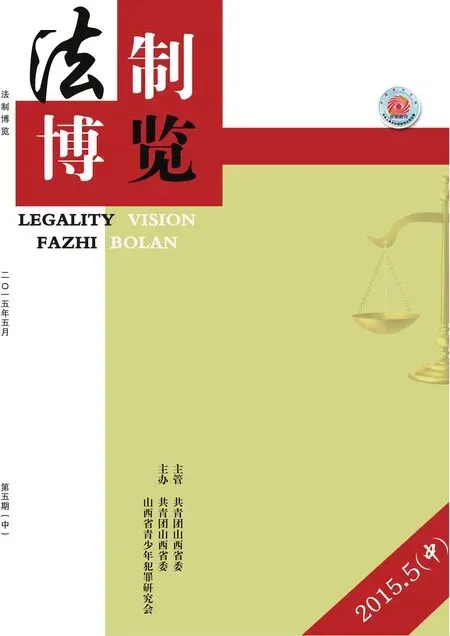引导协商式:当前形势下政府话语研究
引导协商式:当前形势下政府话语研究
周心怡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044

摘要:本文以话语理论为基础,研究政府话语的不同类型,从权利、利益、行为方式、话语特征四个维度分析不同类型的政府话语的利弊及其适用的场景,从而引入一种新型的引导协商式政府话语,站在大众立场上以一种正能量的引导来促进政府话语运行。通过对比以及从以上维度的分析,文章认为引导协商式比主导-霸权式、对抗式、协商式更符合中国社会现实。
关键词:引导协商式;政府话语;话语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4-0129-02

一、引言
政府话语是指由政府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实现自我利益表达、信息传递、与其他社会行动者沟通交流、控制或左右他人思想和行为等目的,借助声音、文字、动作等被他人所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切信息。政府话语权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发展,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开启了新的话语权平民时代。随着自媒体的更新,人们政治民主意识的增强,话语权的冲突也导致话语管理和协调的难度加大。本文通过对比中西方政治乃至文化差异中找出协商式政府话语的局限性,并结合中国当前社会情况中这种对话协商式的理想化,中国对互联网的大力整顿,大力通过网络、电视等传统和新媒体的结合,弘扬正能量,传播社会光明美好,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引导协商式政府话语。
二、政府话语模式
(一)不同政府话语模式利弊分析
1.主导-霸权式政府话语
主导-霸权式也可称为封闭独白式,“主导-霸权”也就是话语主体占据主导地位自说自话的主要特征,且是对话语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界定。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下,政府话语的运行主要是基于政治权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单向灌输,公众缺乏对政府话语的反馈传播渠道,因此只能一味的“被接收”或者“被传播”,在话语体系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随着网络等互联网的发展,公众沟通渠道被打开,话语民主意识增强,原有这种主导-霸权式的政府话语显然不能满足公众对话语民主的诉求。但在现实公共事件中,这种主导-霸权式的政府话语依然存在,表现为政府自说自话,公众自成一派。
2.对抗式政府话语
“对抗”也就是意味着抵触、抵制等意思。对抗式的政府话语一般存在有一个前提,即在公众内部形成多人关切的一致性话语。公众虽是一个大群体,但相对于政府来说却处于话语的”弱势“地位,因而只有当公众话语形成一定的舆论焦点时,才能够取得足够的话语影响力,才能够改变与政府在话语地位上的悬殊,从而以公众群体的力量对政府形成舆论压力。在公共事件中,政府话语明显失当、政府回应不及时等都会容易造成公众的对抗式解读,从而对政府进行负面的批评和指责。
3.协商式政府话语
“协商”是一种话语主体和接收者之间互动关系的阐述,即话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是进行协同商量的一种方式。协商式政府话语是在公众话语充分表达,政府与公众协商一致的一种“理想化”的话语运行模式,或者说是一定时间内,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政府与公众达成共识的状态。因为只要是相互独立的主体,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协商式是对公共事件中政府与公众存在沟通互动的抽象体现,也是以便与现实其他两种话语运行模式进行对比,并以因果性去理解、阐释他们。
三种话语模式从权利、利益、行为方式和话语特征四个维度进行对比,如下表1所示:

表1
(二)在中国实现协商式政府话语存在的问题
1.协商式存在的条件
作为西方协商民主思想理论之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公共领域理论都论述了相关的思想。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为前提,意即人们在交往中应该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也就是说交往行为主体之间非强制性的诚实的对话与交往,并且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达到谅解和达成共识。而在公共领域理论中,哈贝马斯提倡要重建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包含了公众、公众意见或公众舆论、公共媒介和公共场所在内,公众能够在其中形成民主的意见或建议,并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协商民主的思想大致从哈贝马斯开始兴起,之后的学术界就对此孜孜不倦,推崇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社会。
2.协商式在现实中的问题
在西方,民主思想早已经深入人心,公众的民主意识很强,理性主义较高。而在中国,首先公民理性精神有待培育。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留下的残余依旧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思想。加之中国人口众多,民众贫富差距悬殊,知识素养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想要在一定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政府与公众间的协商对话,几乎是不可能或者说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的。再者公共领域尚未形成。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那样一种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领域,需要的是公众、公众舆论、公众媒体和公共场所的多要素的统一。哈式所谓的公众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也就是说公众的这种社会交往方式是不受任何地位的约束,可以公平自由的交往。公众舆论则是以批判意识为核心,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与监督、控制为主要特征与目标的。当然这种批判必须建立在公众理性的基础上。如今互联网作为主要的舆论场所,网民的素质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阶段民众的整体素质趋势。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公共权力形成影响、约束乃至监督、控制的媒介和场所即是“公共媒介”和“公共场所”。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公众主流媒体是受上层意识形态主导的,公众自身素质有待提高,而公众舆论甚至只是乌合之众的情绪发泄,因此这样的一个公共领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形成。第三,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不高。政治参与度不高,民众认为政治与自己生活不太相关的想法还是存在。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以上三个条件都不满足不符合,纯粹的协商式政府话语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可以说它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土壤。
(三)引导协商式政府话语
引导协商,可以说是协商式的一种发展,即是政府话语主体在协商的过程中主要以一种引导劝服的形式进行。在权力方面,引导协商式是以民主集中为主,这与协商式的民主看似区别不大,但实则在民主的基础上又有集中。民主是纯粹的平等自由辩驳,而民主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也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中国自由的辩驳是容易失控的,因此完全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需要民主集中。在利益方面,引导协商式则兼顾多元利益,这与协商式的兼顾多元利益又有着细微的差别,协商式的兼顾多元利益要兼顾的是多方的利益,而往往会容易受利益集团的控制而偏向某一方。引导协商式的兼顾多元利益则主要还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从而使得政府话语不再一家之言而更有客观性和公信力。在行为方式上,主导-霸权式的政府话语是单向灌输,政府说,民众听;对抗式中政府与公众间的交流实际上也是缺失的。在协商式中政府与公众间建立起双向交流互动,而引导协商式的双向互动在此基础上则主要是引导式的互动,而这种引导是有目的的。一方面政府利用主流媒体以及新媒体等掌握舆论的主导权,但同时又要为公众提供可以民主参与的平台,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网络行为规范,以防止网络暴力等不健康因素混淆民众的试听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话语特征上,主导-霸权式的政府话语实际上是一种同质性的,所谓同质性也就是说政府话语发出民众只是单纯接受而没有更多不同意义的出现。所谓异质性则是政府话语在被民众解读时有不同的意思产生。而对抗式政府话语虽说是异质性的,对于政府话语民众有自己的解读,但是这种不同意义的解读很多时候没有客观理性在里面,甚至是一些乌合之众的言辞,也就是说对抗是想让异质性存在,但这些不同意见并没有被采纳或者考虑,因而这种异质性又带有不相融性在里面。引导协商式与协商式一样都带有异质相融性,但两者之间的相融却是不同类型的,协商式的异质相融是异质碰撞型,而引导协商式的异质相融却是异质劝服型。也就是说协商式是以民主为基础,它主要是一种自由的辩驳,各种意见相互碰撞,但在这种相互碰撞中没有一定得控制就一定会失控。而引导协商式是在融合其他意见的同时有政府的引导劝服的作用,从而使得这一种自由辩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于失控。
总的来说,引导协商式看似与协商式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比协商式更实际和可行。协商式需要的是完全的一个平台使得公众能够与政府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沟通形式来解决。而从上也可知,面对中国的现状和国情,这点很难实现。而相对而言,引导协商式需要的是政府在其中扮演好引导人的作用。
三、当前环境下引导协商式政府话语实现途径
(一)以正能量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我们称之为引导,意味着引领和指导,而不是强权。引导和强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强权是建立在统治者权力的威权下屈服,而引导是一种辅助,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引导。当然任何引导都不是盲目的,引导是为了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这种引导协商式所说的引导,重点是一种正能量的引导。“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当下,中国人为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能量”标签。它已经上升成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与我们的情感深深相系,表达着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期待。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传承,在政府话语中引导协商式所说的正能量的以引导意即在事件发展中或整个事件发展始末当事件偏离正常轨道时,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引导它回归正途。或者说从一开始就进行正能量的引导。
(二)提升话语能力与参与能力的制度保障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引导协商式也带有协商式的某些基础和前提,从宏观的层面来说,首先话语权分配必须均衡,也就是说不能政府话语主导,自说自话,话语主体悬殊要减小,必须要用制度规范来提升公众话语参与能力,提高公众话语意识,才能保证公众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有效的公众意见,从而有助于推进公共事务的管理。
(三)站在公众立场上,以公众利益为主
其实引导协商式政府话语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这种引导需要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不能完全是政府利益为主,如果单以政府自身利益为主去考虑来引导,那么这种引导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强权,也失去了引导的意义。因此,这样一个引导的标准必须是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以公众利益为主,才能使得引导有标准可依,也不会偏离人民。
[参考文献]
[1]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南京:学林出版社,1999.
[3]张扬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的几大关键问题评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