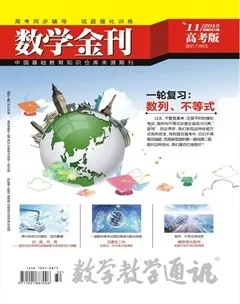吴文俊——大数学家的学术路
1956年,一位37岁的年轻人和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了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此之后,这位年轻人很快消失在公众的目光之外.45年后,当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的时候,人们突然又发现那位当年曾经获奖的年轻人再度站在了领奖台上,他就是著名的科学家——吴文俊先生.
伟大的数学让数学家们去求索,离开数学的范畴,我们尝试着随着吴先生和他周围的人们的回忆轨迹,试着勾画出一位杰出科学家的人生态度.
歪打正着走上数学路
“在上学时我最喜欢物理,因为离现实的事物更接近.但是现在想来,如果沿着物理的方向走下去,我不会取得什么大的成果,因为我不喜欢动手,而物理是需要动手的,”吴文俊说这话时,笑得非常开心.
将时间回拨.1933年,吴文俊在上海正始中学读高中.一次物理考试,题目特别难,但吴文俊的成绩极为出色,这引起了物理老师和校方的重视.但是这位物理老师坚持认为,吴文俊物理好主要是因为数学特别强,
以优异成绩结束3年的中学路程,吴文俊获得了学校特设的奖学金——每年100块银元的资助,在当年这笔钱相当可观,几乎是一家人一年的花销.如果没有这笔奖学金,家里支撑他读大学将会很艰难,但这笔奖学金有个条件,要报考校方指定的学校和系科,于是,1936年秋,吴文俊走进了学校指定的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因为这笔奖学金,我歪打正着走上数学这条路,可以说一半主动,一半被动.”吴文俊说.这第一笔奖学金拉开了吴文俊其后几十年获得各种荣誉的数学生涯:吴文俊曾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以及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等等.除了文革时期,基本上每隔几年吴文俊就会获一次奖,而这些奖项中的任何一个拿出来,就已经可以让获奖人受益终身了,
静下心来做学问
1947年,在陈省身先生的推荐之下,吴文俊去法国研读深造.他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10频道《大家》栏目采访时,沉浸在感慨中回忆:“陈省身先生没有让我去当时欧洲的数学中心巴黎,而是把我安排在法国的一个边界小城里,陈先生说,‘你是去学习,做研究,应该离那些繁华喧嚣的城市远一些’.”
在法国寂静的边城,吴文俊一如当地的学者,在咖啡馆的一角独自日复一日地进行缜密的思考和运算,埋头沉入到拓扑学中.在这一时期,他证明了4K维球无近复结构,在拓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年的拓扑学界大师霍普夫质疑这个结果,“他带了助手来‘兴师问罪’,在校园中坐下我们就开始讨论,最后他还是服气了.”时隔多年后,吴文俊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这段“官司”,并且为此而发笑,
“你要认真去做,不要去考虑是否得奖这类的问题.如果只想着我要做一个得奖的工作,那么你什么工作恐怕也做不出来.”在谈到自己屡次获奖时,吴文俊如此说到.
开拓一个新领域
在文革期间,吴文俊被下放到北京无线电一厂劳动,而当时的北京无线电一厂正在生产电子计算机.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计算问题,特别是寻找几何中自动机器证明的有效方法,计算机的性能引起了吴文俊浓厚的兴趣.于是,在近耳顺之年,吴文俊居然开始学习计算机,并且在后来上班的若干年内,他的上机时间都遥居全所之冠——经常早上不到8点,他已在机房外等候开门,甚至24小时连轴转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正是这番努力,使吴文俊开拓了数学机械化领域,也因此荣获了2006年度邵逸夫数学奖,吴文俊自己认为这个成就高于他早年的被引用多次的“吴方法”,他认为,开拓新的领域对今天的中国数学尤为重要.
英雄是落后的标志
“在老百姓眼里,获奖就和中彩票一样,值得羡慕的就是运气,但是对大科学家来讲,获奖其实是早已做足了功课.记得1983年我去法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问我,‘吴先生现在在做什么?’在听了我的简单介绍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吴先生做的,那一定是有道理的,’1986年,我推荐一名学生去法国深造,法国的教授在看了他要研修的方向后拿出了一些资料说,‘我讲课的这些资料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自吴先生的研究,你在中国学习会更好.”’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文志英教授的这番介绍进一步证明了吴文俊早年就享誉国外,
如今,早已诸多奖项加身的吴文俊,被誉为我国数学界的杰出代表与楷模.对此,吴文俊说:“对我个人而言,每次获奖都是高兴的事儿,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稍做出成绩,就被大家捧成英雄,像朝圣一样,这个现象不是好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坏事情.这说明我们的科研还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有个吴文俊,那能说明什么?要是在这一个领域,发现有十个、八个研究人员的工作都非常好,无法判定谁是英雄,那才说明我们发展了,进步了,”吴文俊说,“这可能是我的怪论,但确实曾有人说过‘英雄是落后国家的产物’,在科学界,至少在数学领域,我很认同这句话.”
做数学大国的功课
1999年,数学天元基金成立10周年时,吴文俊曾谈到中国成为数学大国的步骤:第一步是规划,规划当时已经有了:第二步是赶超日本;第三步是赶超欧美,时隔7年,吴文俊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谈到中国数学与日本的距离,“在一些领域日本做得还是比较有水平,但在某些点上,比如拓扑学,我觉得他们并不高明.但是,总的来说,日本能举出很多人做出了杰出工作,可以说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没有英雄的境界.”
由于近几年,国内一大批青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吴文俊非常乐观地表示,“数学界的学术风气还是比较正、洁净,我看到的年轻人都在埋头苦干,中国离没有英雄的境界很近了,已经能看到这个苗头,”
早些年,与吴文俊同辈的老一代科学家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现在我们做的工作很出色,但是,领域是人家开创的,问题也是人家提出来的,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工作,有些把人家未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在人家的领域做出了使人家佩服的工作,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这就好像别人已经开辟出了一片天地,你在这片天地中,即使翻江倒海、苦心经营,也很难超过人家,这片天地终究是人家的.”
那么今后做什么?吴文俊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开拓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域,创造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的问题.讲求效率的他也在不断地思考以何种方法、方式来完成这个目标.数学家多是单兵作战,吴文俊笑指着自己说:“我以前也是这样,但现在看到有一个多学科组合模式,我很欣赏.‘文革’期间,关肇直同志在思想上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他说的‘不要扎根外国、追随外国,立足国内’的这种思想是行得通的.起码在我这儿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外国人做的我不做,外国人没想到做的我才要去做,”吴先生说这句话时不由地提高了声音.
数学从娃娃抓起?
中国中学生多次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回好成绩,被认为是中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从一个数学家的角度看,吴文俊更同意丘成桐教授的意见.后者曾在相关媒体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奥数在中国陷入了一种盲从状态,小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没有任何研究性思维,他们往往随周围潮流、家长期盼而陷入被动学习.中国的奥数教学的现状是学习方法太片面,过分关注海量题目,这对学生系统学习数学很不利.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学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当过分功利.”
“参加数学竞赛获奖是很可贵的,但是不能过分重视,因为它不能代表一名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吴文俊说,国外曾有人做过统计,小时候参加竞赛获过奖的学生,日后在数学上有所作为的微乎其微.
但是,一个缺乏数学思维的民族,在国际科技竞争中也必会受到制约.吴文俊很赞赏历届美国总统对数学的认识和态度.1957年,前苏联抢先用火箭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看到前苏联的火箭上天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马上反思国民教育要加强,于是政府出台鼓励政策培养数学、物理人才”,吴文俊认为,这就是一个大国对数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