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午后
晓秋
童年的午后
晓秋
那时是一个静静的午后。奶奶在东厢房躺着,我几进几出东厢房,甚至毫无心计地拍了几下东厢房的门,大声地喊过几声奶奶。奶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被我吵醒,一边骂着“叫魂哪”一边从床上爬起来,吆喝着我,颠着小脚把我赶出她的房间。我家在村口,放眼望去,是连绵的稻田,稻田的中央,则是条实在说不上宽畅的大道,平常的时候,大道虽不见得繁华,却不断有人经过——那就是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那个午后,道上离奇地静寂,我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人从门前走过。我寂寞地坐在大堂的门槛上,双手托着双腮,无思无绪地望着远方正旺盛地生长着的庄稼。不时有寥寥的风从面前飘过去,传递给我丝丝缕缕的庄稼即将成熟的气息,这种气息使我无比地忧伤,六岁的我守着这样一个寂寞的下午,体味着莫名的与我年龄绝然不般配的忧伤。平日的疯狂像屋前十几米外的水沟里细长的水草,在温婉的秋阳下,沉着地岿然不动。偶尔几声犬吠和伙伴们的尖叫在耳畔隐约响起,如同失去法力的魔法,对我构不成一丝诱惑。我没有意识那午后有什么不同,我只是不想出去,哪怕是如此寂寞地守候在大门前,以我当时的年龄和意识,我断然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死寂的午后,奶奶已经去世,我是家中唯一一个守着她却没有守住她的亲人。
我极度无聊地发着呆,面对东厢房,忍不住又过去拍了几下敞开的门,我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等着奶奶从床上爬起来,说那句我听过千遍的话:你喊魂哪!每次听奶奶这样说时,我就忍不住想,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真的能被喊出来吗?就算被喊出来了,如果真的能,我能不能把所有人的魂都喊出来,那么多的魂在一起,是不是和无数聚集在一起的人一样,它们也会争执甚至会打架吗?魂长什么样?它很丑还是漂亮,大还是小?年少的我,根本不知道魂是很抽象的物质,它只存在人的意识中,是人精神深处的一种东西。我在咀嚼着奶奶的这句话时,用姐姐的话来说,是一付十分成人的表情。
我在家里的每个相通的房间里窜来窜去,一般很难独自呆在家的我居然没有动出门的念头,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力量将我拴在了家里。当我成年后,每一次回想起那天下午的情景时,我都泪流满面:我想那其实就是血肉相连的亲情的羁绊!和奶奶嘴里的“魂”一样,是无法很具体去物化的。
奶奶没有被我惊醒,依旧安详地躺着,置我的期盼而不顾。我想奶奶睡得是太熟了。我很沮丧地站到奶奶的房门前,穿透屋里淡淡的昏暗,愣愣地看着躺在床上酣睡的奶奶。奶奶的屋里有一股轻浅的腐朽的味道,屋里没有窗户,完全靠着屋顶几块陈旧的玻璃瓦透过的几丝光亮,每到黄昏的时候,我就不能进奶奶的屋,那里面完全的黑暗让我心生惧怕,而奶奶凭着她对屋里摆设的熟悉,不到天完全黑下来是绝不肯点亮煤油灯的。屋里没有我习惯的奶奶拉长的鼻鼾声,阴冷的气息使我只敢趴在门槛上,倚着门陪着此时跟生命再无关联的奶奶。
父亲是接近黄昏的时候才到家的。父亲当时是公社的一名干部。公社离家很远,大概有二十来公里吧,还要翻越一座小山。那时候,在农村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独轮车,但独轮车并不能给像父亲这样的男人带来什么方便,除了运送货物,就只能推着像奶奶这样的老人和我这样的孩子了。父亲每天都要从公社回家,除非工作需求,否则,不管多晚,他都不在外面过夜。父亲是个孝顺的儿子,他对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很严厉,可对奶奶,却低声下气,从不敢像我们一样偶尔在他和妈妈面前还耍耍小性子发个小脾气什么的,在奶奶面前,他永远是花开不败的春天,温暖得没有季节的更换,也没有新老交替。
因为在公社有个很大的合作社,父亲就时不时从合作社给奶奶买一些我和哥哥姐姐们都没有吃过看上去十分诱人的食品,但他常常是瞒过我们,偷偷地给奶奶,大概是怕我们不懂事,跟奶奶争了吃吧,那样的年代,能吃的零食是少而又少,能从合作社买回来的东西,一定是家庭的奢侈品,当然容不得一群人数张嘴的吞蚀。我不明白奶奶是不忍一气吃完还是不舍得吃完,我总是能在窜进她屋时发现她的食品。于是,我神秘兮兮地告诉哥哥姐姐,然后我们又一起摸进奶奶的屋里,用手沾点或掐上一小块跑出来,喜滋滋地。也有时奶奶正在吃的时候被我闯进去撞上,奶奶便一把拉过我,往我嘴里塞上一团甜津津的东西,并告诫我不要乱说。我一边吃一边唔唔答应着。可吃过后又忍不住地跑到哥哥姐姐面前炫耀。通常是哥哥姐姐的嘴随着我的炫耀不停地嚅动着,咕咚咕咚口水吞咽的声音比赛一样此起彼伏,绝对壮观。
事实上在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奶奶不喜欢我们兄妹四个的,不是我们对她不孝顺,是她不喜欢我母亲,在奶奶的意识里,是妈夺去了他唯一的儿子。可实际上,父亲母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父亲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奶奶身上,对母亲就像对待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冷淡和霸气。母亲当时在外地工作,总想让父亲调到她那儿去,可奶奶死活不愿离开老家,她对父亲说,你要去你去,不要管我,到你老婆那儿比留在我这把老骨头身边自在。我生死就这样了,苦了多少年了还怕再苦这剩余的几年吗?你去吧去吧。奶奶说完再不吭声,任父亲说什么也不理睬,最后父亲泪流满面,跪下说,妈,我不走,我就待在你身边侍候你。
父亲不走,也不让母亲把我们带走,他说要我们在奶奶身边好好陪着奶奶。为此我的哥哥姐姐们只能在离家有六七公里的大队上学,每天的来回还要穿过一片树林。有一回,我死乞白赖地要二哥带我去见识他的学校,二哥无法,便只好领着我。那一片茂盛的树林虽然花香鸟语,可那四周无人的空旷却让我胆战心惊,以至于我还没有走到学校便哭开了,而且一直哭到二哥不敢再带我往前走了,只好折回头又把我送回了家,当晚我便发了一场高烧。妈妈那儿有很好的学校,还不用多走路,但我们却因为奶奶去不了。然而,我们的被迫牺牲却没有让奶奶领这份情,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奶奶经常颠着她的小脚,迈着碎碎的步子,出其不意地站到我们兄妹某个人的跟前,一伸手,拎着谁的耳朵,像拎着小狗小猫似的。
比较起来,在我们兄妹四人当中,奶奶对大哥最慈祥,最不喜欢的是姐姐。但我们兄妹就数姐姐最为孝顺,也最懂事,家务活是干得最多最累的。大哥很有些小聪明,所以他干什么都有个道道,换句话来说,就是干什么都能偷得到懒,而且还不被奶奶骂。姐姐就很实在,尽心尽力地帮助奶奶干活。奶奶说属羊的女人命苦,她就是属羊的,而姐姐恰恰跟奶奶是一个属相,奶奶因此而特别不喜欢姐姐,觉得姐姐苦命,以后会拖累我的父亲。
姐姐是家里的老二,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而且学习也是我们兄妹中最好的。那个时候她在学校经常跟着学校的演出队去外村演出,当然那时也只有唱样板戏,她唱的是《红灯记》里的铁梅。母亲每次回家时总是嘱托姐姐把我照看好,姐姐很认真地听从着母亲的话。每当她出去演出时,我都会闹着要跟随着她去,奶奶为图清静也让她把我带上。于是,姐姐就哀求着性格内向、从不多话的二哥跟着她去看戏,二哥和姐的关系很“铁”,他躲不开姐姐的央求,只好无奈地拉着我的手跟着姐姐走了。但到了姐姐演出的地方,只看了一会儿,我就熬不住了,而二哥又不会哄我,到了这时候便很热闹,姐姐在台上亮着嗓子唱戏,我在台下声嘶力竭地嚎啕,二哥则在一旁一会儿大声训斥我,一会儿跟着我流着眼泪大声喊着台上十分投入戏中的姐姐。这时周围的群众十有八九不在看台上的戏了,反倒是我和二哥成了他们观看的主角。姐姐这时候就没有心思唱戏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唱错,却记得有一回台下轰然大笑,不是笑我和二哥,而是冲着台上,台上的姐姐泪流满面。
奶奶不喜欢姐姐,姐姐后来的命运就如奶奶所说属羊的女人命不好,她上学只上到了初中二年级便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而辍学了,当时学校的老师为此十分遗憾。可懵懂无知的我并不懂得珍惜,经常和她吵架,惹得她总是跟着我一块哭。也许人的一生真是天定的,姐姐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充满了坎坷与无奈。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奶奶不喜欢我们是因为母亲。因为她不喜欢我母亲,所以奶奶对我们的感情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倒是姑姑家的几个孩子,奶奶是舍不得的,一来便要将爸爸和妈妈回家带来的一些吃食悉数拿出来,最多的是水果糖,我们只是偶尔能讨来一两颗,而姑姑们的那些孩子,却几乎是要揣满口袋的。奶奶老说我们吃得多了,其实除了我因为年纪尚小,仗着得了父母的宠,要起东西来有点不管不顾的狠劲,还能吃上些外,哥哥姐姐们实在吃不上什么。更有家里我父母备下的很多物件,姑姑们总是借口我们家没有人种地而把各种农用具都拿走,甚至桌子椅子和堆在堂间父亲和母亲买下准备翻盖旧房子的木料,父亲每月给奶奶的钱,名义上是“借”,但从来只有借而未有过还。有时候,母亲问及这些事时,奶奶就要发很大的脾气。奶奶的脾气并不冲着母亲来,但父亲和母亲间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有一场战争。这是很多年以后母亲对父亲仍耿耿于怀的原因之一——父亲只顾及奶奶的感受,而从来不曾体恤过母亲在一个家庭被忽略被轻视的感受。
我至今都不明白,奶奶为什么不喜欢我的母亲,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又为什么一直不和。我父母的婚事是奶奶一手操办的,他们在结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父亲那时还在部队,奶奶就在家乡给父亲物色对象。长相俊俏的母亲在看了媒人拿来的父亲着军装、显得十分帅气的照片后,毫不在意父亲家境的贫寒,答应了这门亲事。母亲在选择这段婚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日后和父亲会相处得那样艰难。那时军人的职业是那样光荣,母亲对军人的盲目崇拜迷惑了她,我想我后来就是遗传了她的这份爱好,所以也选择了一个军人作为我的丈夫,但和母亲不同的是,我和丈夫之间的爱情是她和父亲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父亲也只是看过母亲的照片,不过这时奶奶已经替父亲定下了这门亲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父亲后来转业到九江一家中型棉纺企业后,母亲在我一个姑父的护送下,到九江和父亲完了婚。一段充满了硝烟的婚姻由此拉开了序幕。
母亲在父亲所在的那家企业当了临时工,她每天不但要努力地去工作,回到家还要悉心照顾我的父亲。父亲是个事业心特别强的人,每天只休息四五个钟头,余下除了吃饭的时间就都粘在了厂里。而在家不长的时间里,他又特别大男子主义,动则便用他在部队上的一套来训斥我的母亲,说母亲思想放松,行为懒散,丝毫不顾及母亲厂里家里的辛苦。后来,母亲怀了大哥,妊娠反应厉害,总想找些酸辣的东西吃,父亲丝毫不懂得体恤,说母亲打着怀孕的幌子,实际上就是好吃懒做。听到这样的话,可想而知当时母亲的反应,母亲气得差点去做了人流。好多年以后,我都有了女儿,母亲仍会说起这些往事,父亲在一旁听着低了头并不说话,但听母亲像控诉黑暗的旧社会似的,便和母亲犟起来,不停地翻着白眼看母亲,用鼻子“哼哼”,以示他的抗议。于是我和姐姐就一齐冲着他说就是他的不对,大男子霸权主义。父亲早已不轻易跟我们发火,却也不和我们争辩什么,又顶不住我和姐姐都站在母亲一边,便甩着手走了。这时的父亲已经被生活磨砺得再没有他从前的暴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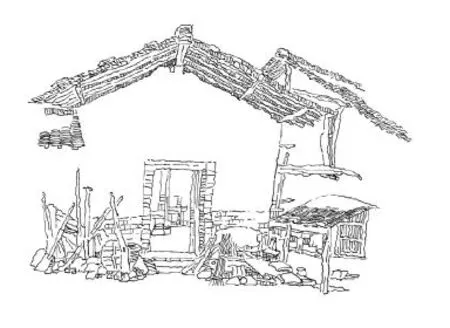
母亲的前半生是很少得到父亲关怀的,更不要说是一个男人的柔情。只有长大成家后,我才能体会母亲前半生那深深的寂寞和悲哀。母亲生下大哥,坐月子的时候父亲把奶奶接去照顾母亲,但奶奶却将别人拿来的鸡鸭鱼肉都做给父亲吃。父亲没有洗过一次尿布,月子还没有结束,他就要求母亲洗衣服、尿布,也就是那时,母亲落下了手一浸凉水便发烫的怪毛病。母亲生下姐姐的时候,父亲已回到老家。父亲是为奶奶才调回来。刚开始,父亲在县城近郊的一个林场当副书记,母亲是县新华书店的售货员。那时父母亲的生活是艰难的,因为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们没有房子住,在乡下一个叫梅林的地方租了房,姐姐就是在梅林出生的。应该说,父母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改善,因为母亲没有反对父亲回家,而且还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她在九江那家棉纺企业转正的机会,这或许使父亲有些感动,让他对以往的一些行为产生了愧疚。好景不长,随着奶奶的到来,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又恶化了,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奶奶看不顺眼母亲的任何行为,对母亲从不给好脸子。母亲由最初的忍气吞声到忍无可忍,就和奶奶吵了一架,结果奶奶便要寻死寻活,坐在地上一边嚎哭一边大骂父亲是不孝之子,不顾她怎样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反使她遭到媳妇的欺辱。父亲不辨是非,也或者在奶奶面前,他也永远不可能去辨是非,将母亲痛打了一顿。二姐和二哥出生的时候,奶奶都不肯来照顾母亲,说是月子,其实母亲的月子也只是坐了几天,几天之后,家里的很多事都由她亲自来打理。在母亲的眼里,奶奶总是在她最需要帮手的时候不肯靠近,她或许可以不计较奶奶对她的不好,却不能原谅奶奶抛弃她几个需要照顾的孙子,所以等到奶奶再从老家来到父亲家时,母亲就不再忍让奶奶对她动不动的挑三拣四。奶奶和母亲的关系再也相处不好,便执意要一个人回到老家。父亲挽留不住,只好随奶奶去了。为了照顾奶奶,父亲调回了老家的公社。这次母亲坚决不随父亲了,父亲只好带着尚且年幼的哥哥姐姐们回到了奶奶身边。
其实母亲离乡下老家也不算太远,坐上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再走上半个小时的路也就到了。刚开始母亲每个月都回家一两趟,后来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就将每个月的假期攒下,攒足十天或半个月,她就回家呆上一段时间。
我是唯一在乡下老家出生的孩子,也是母亲生孩子唯一受到奶奶照顾月子的一次。母亲对奶奶的怨气因此消退了不少,对奶奶也知冷知热的,两人的关系一下子从零度上升到零上三四十度。
父亲是独子,但我有三个姑姑,最小的姑姑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妹嫁到离奶奶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小姑姑的家在当时的农村应该算是小康,因为姑父养了一群鸭子,鸭子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经济上的补助。但即使这样,姑姑每次来奶奶家,仍恨不得把奶奶家翻过来,她几乎把家里能用得上的、好一点的东西都“借”走了。母亲自然是要问起这些东西的下落,奶奶便急了,恶声恶气地说家里面的事用不着她管。母亲备置的东西心疼是免不了的,后来见了姑姑就忍不住讨要,姑姑就在村里到处说母亲刻薄,说了母亲的许多坏话,弄得母亲在村子里几乎都抬不起头来做人。母亲在奶奶家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而父亲对此视若无睹,从来没有宽慰过母亲。父亲是个亲情浓厚的人,前半生的母亲或许还游离在他的感情之外,所以,对于母亲的辛苦和艰难,他无知无觉。母亲减少了回家的次数,孤独地在外面生活着。
父亲一回来我就告诉他,奶奶睡了一个下午了,我喊她也不起来。父亲没听完,一手将我拨开,跑着进了奶奶的房间,紧接着,一个很沉闷的声音从奶奶的房间响起,那是一种像什么东西破裂了一样的声音,然后那声音又像是被迅疾地收回扔在了某个角落里,弹起又落下又被弹起,这样反反复复。
那声音十分惊人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以一个儿童的好奇和敏捷迅速地冲进了东厢房。
屋里点了灯,父亲坐在奶奶床边,脸上的五官很奇怪地扭在了一起,像是我看过的变戏法的一样,十分滑稽。那种沉闷的声音正是父亲发出来的。我惊奇地看着父亲那张扭曲的脸,只见那张已布满了许多细琐皱纹的脸上像一块久遇干旱的土地又遭遇了洪水一般,沟沟壑壑里都填满了泪水。我被那张脸震撼住了,立定在父亲的身边,竟久久不敢动弹更不敢多说一句话。过了许久,我的目光才从父亲的脸上移到躺在床上的奶奶脸上。奇怪的是奶奶的眼睛却是瞪得大大的,目光直直地不知落在哪个地方,在她黝黑的脸上显得十分空洞。我从来没见过奶奶这个样子,心里很害怕。我看了看旁边自顾自坐着,依然一付展不开五官的父亲,怯怯地伸出手轻轻地推了推奶奶的身子。奶奶的身子僵直着,我的手却感觉到了从奶奶身上散发出来悚人的冰凉之气。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那其实就是一股死亡的气息,更不知道是那些分散在父亲脸上,致使他五官不匀的东西就叫着悲恸。父亲无视我的存在,而我却同时又被奶奶吓坏,我顾不上害怕父亲,一头扎进他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喊着“奶奶”。父亲抱着我,脸上的泪水漫延过他的脸淌到了我的头上、身上。全然没有他平时的威严。我被父亲从嗓子里出来的那种声音笼罩着,恐惧加上压抑,让我没法止住泪水。
我只能说,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奶奶是去世了,因为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的场景。我甚至还在一边哭的同时心里还一边埋怨奶奶为什么要一直躺在床上,而且还是那样一付惊人的样子,我一点也不喜欢。可是我不能在父亲那样的表情状态下述说我的观点,我害怕父亲,这种害怕一直延续到我结婚。
父亲是很喜欢我的。我不知道这种喜欢是不是缘于奶奶对我相对哥哥姐姐来说更多一些偏爱,而我因为和奶奶、父亲相处的时间长,见到母亲的时间少,所以对母亲的感情不像哥哥姐姐那样深厚。我对父亲的亲近感是母亲不能比的。但自从那个下午我目睹了奶奶的死亡之后,便无法再和父亲亲近。而父亲在我逐渐成长的路途中也失去了对我耐心和无微不至的关爱。我总以为他是过于偏重事业,以及与母亲关系不和等原因所致。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在一次暴怒中用一种带刺的荆条将我的双腿抽得鲜血淋漓,不仅如此,他还将荆条挂在墙上,瞪着双眼狠狠地说,他要让我记住这一切。我真的记住了这一切,记住了他的残暴,他的乖戾,在心的最深处。母亲为我做的是和父亲大吵了一顿,家里于是有了一些碎裂的碗盘,有了更深的冷漠和陌生。
我对父亲的惧怕形成了对他感情的疏远,而父亲对两个哥哥的偏爱却日渐加深,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摆脱不了那种作为父亲要在儿女当中树立起威严的想法,所以,一方面他寄希望于他们,把所有的关心都放在他们身上,另一方面,却又使出他的专制的手段来管制他们。母亲却不论是哪个孩子,只要父亲对我们当中谁稍有不满,她立马站出来护着,这几乎成了她的一种本能,护着孩子,对抗父亲。因为我的调皮,也因为我对父亲的惧怕和疏远,反而成了他最不能容忍的,因而挨打挨骂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而每一次挨打,我都会倔强地挺立着,直到伤痕累累。母亲则就此会引发一场和父亲的战争,最后最伤的、最痛的,不是我,是我的父母,我们这个风雨不断的家。数年以后,当依在丈夫身边,看到父母欣慰的目光,我忽然间为自己的年少无知而深深痛悔。
我和父亲之间的感情是在我结了婚以后才慢慢改善的。那时父亲已退休多年,在日渐的孤独中开始修复我和他的关系,女儿的出生成了我们关系和睦起来的支点。他似乎把以前对我封闭的爱全部释放到了女儿身上,并且对我也是那样的关怀备至。两年后,我和女儿跟着丈夫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来到了新疆,就这样成了父亲此后日子里最大的牵挂。我的离开,也成了父亲心上的一处痛,他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是殷殷切切的关爱,是为他当年对我过分严厉的歉意。
老年的父亲是十分孤独的,已全然没有了年轻时的霸气,在他慢慢变得平和的时候,他才真正完成他人生的转型,从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变得温和随意起来,他甚至替代母亲承担了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对我的侄辈们,他表现得更加宽容。母亲的脾气也改了许多,差不多和父亲调了个,她总认为自己年轻时受了太多父亲和奶奶的气,心里一直不平衡,和父亲再起争执时理直气壮得让人无言以对,她总认为错了却死不认错的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跋扈。其实母亲的这种想法遭到过我们兄妹的反对,但母亲对父亲的看法已根深蒂固,听不进我们劝的。父亲和母亲吵架,最后总是他自己偃旗息鼓,找个没人的角落坐着。那一坐,是很悲怆的样子,像多少年的风雨在那一瞬都已披挂在了他的身上,不但侵蚀着他的外表,也深深地伤害着他的内心。我或者姐姐,在轻轻地走向他,想以同样的方式陪伴一下他的时候,他在猛然中惊醒过来时,又总是深深地一声叹息,然后冲我们挥挥手,尽量以很平静的口吻说,你们忙去吧,我没事,我只在这儿坐一坐就行了。然后就那样一直坐着,直到天将黑下来或者到了要做饭的时间,才又沉默不语地走出他的角落。
我离开家乡后,父亲信里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我和你母亲都还好,现在已经不怎么吵了,不要挂念。他也知道,他和母亲之间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才是我最大的牵挂。
父亲对奶奶的怀念和歉疚一直没有消退,有一回也许是他实在耐不住内心里那蚀骨的孤独,在整封信里都在说奶奶,他说,他也知道奶奶对我母亲和我们兄妹过于干涉和牵制,可爷爷去世得早,作为她的儿子,亲眼目睹了奶奶为了抚养他们兄妹三人长大成人历经过的无数苦难,他无法不在她年老时让她过得幸福和满足而迁就她。看完这封信,我当时泪流满面,我的可怜的父亲!在他渐渐老迈的时候,我们兄妹又何曾有他当年的气度去迁就过他?动不动就耍着小脾气,一付已是十分瞧不起他的样子。年轻时他要适应奶奶,现在又要改变自己来适应我们。
父亲紧紧地抱着我,我的被惊吓致哭无意中安慰了父亲,至少,有我的哭声伴随着去世不久的奶奶。
哭到我嗓子差不多都快哑了时,家里已经来了不少人,都是村子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亲戚,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知消息赶过来的。他们嘈嘈杂杂地忙碌着。我红肿着眼睛坐在奶奶厢房的门槛上,看着父亲流着眼泪,替奶奶穿早已准备的寿衣。穿上寿衣的奶奶焕然一新,她黝黑的脸在微暗的灯光下闪着亮光,半睁的眼和微微张开的嘴,就好像她在冬日的阳光里笑着看我在晒场上奔跑一样。父亲用手轻轻向下抹着奶奶的眼睛和嘴唇,奶奶不笑了,安静而又安详的表情。我看到,父亲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奶奶的脸上和他那只在奶奶脸上游移的手上。奶奶终于合上了眼,也闭上了嘴。父亲说,奶奶已经安息了。
是的,奶奶已经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