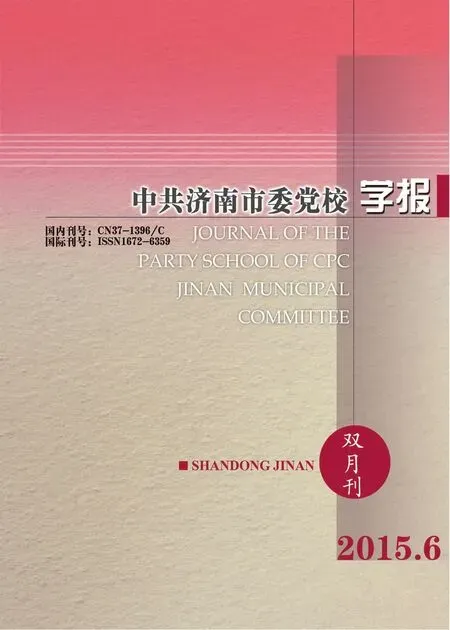匿方激避在派的共产主义迷思——以奈格里和哈特为例
刘亚平
匿方激避在派的共产主义迷思
——以奈格里和哈特为例
刘亚平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今天,以奈格里、哈特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派思想家们,正在重拾这一经典的判断,把拒绝社会主义、复兴“共产主义”作为他们的重要理论使命。
奈格里;哈特,共产主义
2009年3月, “共产主义观念”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会议的举行吸引了上千人参加,其中包括西方法国著名激进左派思想家阿兰 巴迪乌、雅克·郎西埃,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意大利的左派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美国的麦克尔·哈特和布鲁诺-巴斯蒂以及斯拉沃·齐泽克等一批极负盛名的当代左派思想家。此次“共产主义观念”大会的召开,不仅代表着西方激进左派思想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更是标志着共产主义观念的真正回归。虽都是西方激进左派思想家,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的解读,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路径。其中,奈格里与哈特把马克思政冶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结合在一起,得出l l『独具特色的“共产主义观念”。
一、拒绝“社会主义”
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都普遍接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实践方式。针对拉萨尔主义的社会主义倒退倾向,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在这个革命的转变时期,与之相适应的是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时期,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新生的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并未完全脱胎于旧社会;受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的不同限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与此不同。它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而是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在这个高级阶段里,“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超出资本主义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对于这种划分,所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有过质疑,并自然地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当做社会主义社会。也的确如此,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社会主义正是在资本主义长久的阵痛中产生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
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话语体系所宣称的不一致,西方激进左派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的界定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相反,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麦克尔·哈特明确表明,必须拒绝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一个阶段的观念,这样才能拯救共产主义的观念,才能让共产主义观念得到回归。奈格里在《告别社会乇义先生》一文中,提到“对我来说,1989年堪比1968年,l968年拆毁了封闭我们社会的墙,1989年拆毁了保护现实社会主义的墙。” 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让西方激进左派看到东欧各国并没有投向旧的民族主义,反而奔向了资本主义。
奈格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剖析, “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而是因为西方的封锁与压制和反人道主义的仇恨取得了胜利。”[4 奈格里针对许多人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总结为计划经济的失败,表示不赞同。首先,他承认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行性,但是指出,计划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同样是追求利率最大化的经济方式。尽管它具有可行性,但是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成功。所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在于其体制在经济上的失败,而在于没有根据人类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和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社会结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看不到人类在生产和生活条件上的变化,固守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和管理体制,导致损害了自由以及财富的生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种特殊的失败,它的失败并不是因为集中化地组织生产和分配不能够得以实现,是因为它没有建立在人类共同智力力量的自由发挥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上,而这些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
在激进左派思想家眼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成为了一种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齐泽克认为,如今社会主义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然成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的良药和工具,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性纲领。对此,西方激进左派尖锐的指出, “社会主义不能再认为是共产主义的不健全的初级阶段,而应该理解为它的竞争者和威胁者。” 面对着2O世纪西方发明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激进左派认为,它根本不是用来对付资本主义的,而是来对付共产主义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因此,奈格里更是喊出了要告别社会主义先生的口号。
二、复兴“共产主义”
告别社会主义,是为了拯救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共产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更高发展,它是人类自身内在主体性的自我表达和实现。这种共产主义,不应该从先验的立场出发把它当做是一种普遍的假设,而必须是历史主体内部的力量积蓄。他们认为,人类自身蕴含着共产主义的内在力量和趋势,这才是共产主义能够到来的根本原因。
其实,这种思考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趋势的条件的思考有某种相似之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自由自觉的人类活动,人们通过劳动来肯定自己,自由的发挥着自己的能力,这是人满足自身劳动需要的自愿的行为。但是,劳动异化使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异化劳动不再使人自由的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是使人肉体上受到折磨,精神上遭受摧残。不过,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说明自我异化的发展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创造了条件,自我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复归具有内在的自觉性。
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本质是劳动者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即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通过劳动的对象化、异化以及扬弃异化,通过革命使劳动主体实现对物质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垄断资本的集中,给社会的历史更迭提供了条件。工业化过程中创造出大量成熟的工人阶级,他们不仅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知识的掌握、技术的运用和纪律的规训成为了革命的主体,为未来社会的实现创造着条件。随着资本的集中使得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如何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成为这一时期革命主体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样,这个问题也被奈格里和哈特捕捉到,认为今天的全球化和信息化重现了历史的革命主体问题,共产主义能否实现也在这一问题的现实结构之中。
有些人提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已经消灭了阶级,并使得共产主义的主体性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对此,奈格里在《共产主义:概念与实践之思》中谈到,资本这一概念与资本的历史变量在缺乏无产阶级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虽然深受资本的残酷剥削,却从来都是资本的活劳动。这种活劳动作为历史运动变化发展中真正的本源性力量,它内嵌于资本的关系之中,并始终创造反资本的力量,不断的解构
一切资本关系。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霸权,它不仅导致剥削和不公正的加深,也为共产主义实现提供了条件,即主体性的内在生长过程。如:在全球化过程中,知识劳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中生产出共有之物,这正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条件,正在生产着更多的反资本主义的主体。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关系,正是这种阶级的对抗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在资本逻辑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奈格里认为“主体过剩与共产主义筹划之间的关系是经有大众的颠覆性与起义性运动而被给予的”,川在反抗中形成新的组织形式,生成反资本的构造性力量。
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就是指生产的主体与生产资料的普遍分离,与此同时创造出了克服这种普遍分离的客观条件。同样,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到处制造着公有与私有两种关系的对立,但也生成了能够超越这种对立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就是非物质生产或生态政治的生产,它将重塑共产主义观念的核心内容,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
在《共产主义之共者》一文中,哈特指出,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动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关系而是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关系。动产的形式强调的是谁去生产谁去占有的关系,非物质生产出的非物质产品强调的是共享的关系,共享本身决定了共有之物。相比私有财产对应资本主义、公有财产对应社会主义,那么共有物则是对应共产主义。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工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非物质的或生态政治的生产将取代工业生产。何谓非物质生产和生态生产呢?主要包括观念的生产、信息的传播、图像的传递、知识代码的解释、语言的交流、社会关系的联系、情感的表达,等等其他活动。在资本主义下的工业生产不需要劳动者情感的表达,而在非物质生产过程中强调生产者之间情感的交流是一种亲密的合作,生产过程中强调生产者的主体性,通过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生产出主体的独一性。非物质生产本身其实早就存在于资本的逻辑之中,资本的因素逐渐被劳动者抛开,其影响力慢慢开始减弱,而资本又无法占有所生产的非物质产品。虽然我们今天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进行劳动,要看到,这种劳动不单是生产出纯粹的消极面,而是蕴藏着大量的非物质劳动生产,这正是结束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力量。
哈特认为,资本如何对共有物进行剥夺并保证其进一步维持私有化,非物质劳动如何摆脱资本对共有物的占有的企图是当今社会的冲突的主要内容。在工业化生产中,肉体是被机器操控的配件,而在非物质生产之中,所有的东西都要投入到生产之中,不仅包括生产者的肉体,还包括灵魂。 “资本主义发展势必导致合作与共者之日益增强的核心地位,二者反过来提供了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工具,并且构建了替代它的社会和生产模式的基础——共者的共产主义。” E物质劳动生产出生命政治,这是抵抗生命权利的
一种方式。一方面,权利更加严重的剥削和控制着人,另一方面,人通过合作情感的交流各个潜能都被激发出来,使人有能力摆脱外在物对自身的控制。资本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生成了从资本中能够得到解放的工具,它将导向共有物并使劳动的自主性得到提高。
由此我们看到,在哈特的观念里,共产主义不再是对物的占有,要摆脱对物的占有的思维方式,我们一旦强调去占有某物恰恰表现了我们被物所统治的表现,而要选择从人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主体性、人性、人的本质的占有 物同人一样都是主体性的表现,人不应该为了占有物,而应该为了人内心的丰富、人性的提升、需求的增长而奋斗。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个人的劳动是与社会劳动相分离的,而在非物质劳动生产过程中,非物质的生产都是指向人性的,指向社会关系的生产者自主权,创造共有之物。它越来越摆脱资本及国家的控制,生产者主宰自己的生产过程,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
最终,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导致共产主义,通过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蕴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这个萌芽会逐渐长大,成为颠覆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
三、“回到马克思”
奈格里和哈特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派,坚信以共有物为特质的“共产主义观念回归”能够重识社会主义与拒绝今天的资本主义。这种理论的解读与信念既会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与实践方式,也使我们必须进一步重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写道: “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人也都是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 这是柏拉图探索出来的一套原始共产主义国家政体运行模式。柏拉图试图通过正确的分工完成国家正义,劳动的分工完全按照每位劳动者自身状况来选择所适合的工种进行分配。原始的共产主义观是在当时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提出的,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大胆构思和积极尝试。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结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欧洲社会提出了多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构想。其中,圣西门就提出生产的目的在于摆脱资本的操控,只为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类从事的生产劳动就是为了人们自己。这是对劳动的状况做出的合理的畅想,但却没有考虑到其背后所蕴藏的经济规律及资本逻辑,不能对劳动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所描绘的状况注定是“乌托邦式”的。
l842年10月,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主编,与《奥格斯堡总汇报》发生了一次有关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马克思“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对内容本身妄加批判”。_1 他首先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之后才可以进行批判。这表明马克思反对各种共产主义的空谈,而是对共产主义保持谨慎的态度。
针对当时欧洲国家和国内一些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抽象谈论,1843年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反对了这种抽象的做法。他说, “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_】 马克思认为,那些空洞的教条式的共产主义观念,无益于社会现实本身,不过是以抽象代替空想。
1 844年2月,恩格斯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德法年鉴 上发表,这部著作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私有财产为主要内容,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与现实指向提供了巨大的启示。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思想、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等重要思想进行广泛归纳和梳理,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在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行动哲学基础上,写下了充满丰富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在这部《手稿 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崭露头角。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发现,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在这种劳动异化的状况下,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是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发现了劳动者和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的异化、人同人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相异化等四种异化现象,这四种异化现象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表现出来的结果,不过是物对人的奴役,并非人对物的掌控与支配。所以,实现共产主义既:不能是粗陋的平均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应该是保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而必须是在劳动异化的过程中实现“私有财产即人的1 9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所以,对于马克思而言,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 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中介,但共产主义却是一种运动和必经阶段,是1 9我异化积极扬弃的结果。
作为1 9我异化积极扬弃的结果,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是以消灭私有制和人的自我异化作为基本要求,是以把属于人本身的劳动力量归还于人自身,以通过合乎自我意志的自由的劳动来达到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这才是人类最基本价值的体现,共产主义的目的无非就在于此。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共产主义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与积极的努力。他们与抽象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进行广泛的辩论,并直面现实的变革的路径。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来联系各国的共产主义者。1847年春,他们受邀加入“正义者同盟”并将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同时接受委托为该组织起草了一份新的党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Ⅸ共产党宣言》,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纲领,明确党的性质与口号:消灭私有制,并把党的最终目标确立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共产党宣言 一以贯之地继承并发扬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想: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n 的确如此。作为以实践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从来都是现实的运动,而不是放置在某处的理论与空想。
至此,我们就会发现,相比奈格里和哈特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派对共有物的思考和对主体性的过度宣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更为强调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不仅仅是摆脱对物的占有,而是希冀通过不断地运动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达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思想显然更具有丰富与深刻性。当然,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西方激进左派,他们都在为人类贡献着突破资本主义控制的方案,即解决资本逻辑的控制,实现被压迫被奴役的人的本质的重新生成。
共产主义从来不是人们口中的乌托邦,不是应束之高阁的空想,而应该是指引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刘亚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1 3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邮政编码51 0053)
B089.1
A
1672-6359(2015)06-004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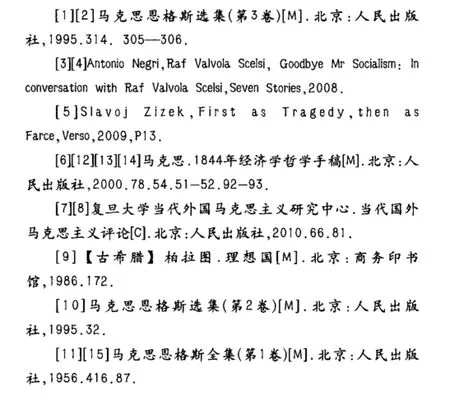
(责任编辑马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