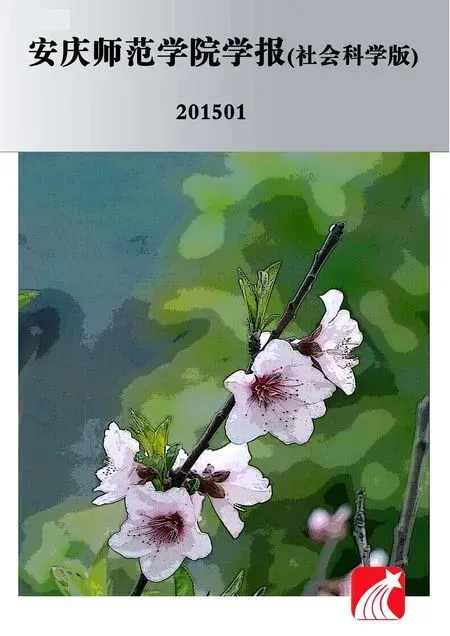澳华作家心水小说中的“中华文化母题”
古大勇,赖思榕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晋江市明江实验小学, 福建 晋江 362000)
澳华作家心水小说中的“中华文化母题”
古大勇,赖思榕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泉州362000;晋江市明江实验小学,福建晋江362000)
摘要:由于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心水(黄玉液)在创作中极力保存着母族的声音,表现出对中华文化母题的继承与变奏。其小说集《比翼鸟》建构了以三个中华文化母题为一体的叙说体系——围城母题、因果母题和圆缺母题,并从婚姻困境、社会困境和自身困境这三个角度来叩问“围城”所凸显的生存状态的悖谬;在道德规约和江湖概念的“因果”逻辑中进行福祸的叙述;对幸福的封杀和对侠气的消解中流动着“圆缺”的悲剧意识。这三个中华文化母题作为一个整体彼此牵制地负载着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
关键词:心水;《比翼鸟》;母题; 围城 ;因果 ; 圆缺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1.024
澳华作家心水,原名黄玉液,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越南,1978年举家漂泊到印度尼西亚,翌年移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定居。正是凭着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创作的执着,心水的微小说在澳洲文坛上独树一帜,作者本人也成为澳大利亚唯一当选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的作家。由于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心水在创作中极力保存着母族的声音,表现出对中华文化母题的继承与变奏。本文以他的微小说代表作《比翼鸟》为中心,分析其创作中体现的中华文化母题。“所谓‘母题’,作为基本问题的呈现,通常是文学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显著的、有独立自由度的成分。”[1]5而围城母题、因果母题和圆缺母题,都是中国文化背景和叙述风格的元素体现。本文从围城、因果、圆缺这三个母题的维度来解读心水与中国文化链接的代表作品《比翼鸟》。
一、“围城”母题凸显生存状态的悖谬
“‘围城’作为华文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不仅涵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两性婚姻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味和复合含义的‘能指’,婚姻、事业、人生、人性,都可能处在某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都可能被‘围城’母题所涵盖。”[1]123在《比翼鸟》中,心水突破时空表层的界限,再现了现实社会的人生百态和武侠江湖的风霜雪雨,借此来叩问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也就是“围城”这一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困境状态。
(一)婚姻困境
《比翼鸟》之“浮世篇”中,作者创作内容的主旋律是传统的“食、色”本性,因此,对婚恋故事的描写成了小说中集中表现“围城”母题的一个重要形式,而故事中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和矛盾心理恰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借苏文纨之口说的“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心水正是通过对世俗男女现实相处的关注来折射有关婚恋危机的理性思考。
如《宿命》,外表幸福的丁竹一心想反抗妻子婚后多年来的严厉对待,相信自己天生具有“双妻”命,整日幻想着命定的另一位娇妻的出现,最后终于如愿在网上娶得一名“网妻”,谁知竟是个患末期血癌的丑八怪。小说写丁竹企图通过婚外情来弥补现实婚姻生活中缺乏的自由和尊严,最终却徒劳无功,只能“脸颊再度僵硬”地在婚姻里徘徊。《谈虎》更是形象地暗示了婚姻家庭中内外纠葛的混乱状态。外人眼中温柔贤惠的妻子离家出走是为了报复丈夫的过失,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谈虎的太太是一个戴着假面具生活的女人,她与丈夫一样是偷情的种,甚至比丈夫更早步入婚外情的伦理罪恶中,只是她比丈夫更懂得伪装与掩饰。一对背妻偷人和背夫偷汉的可怜人在虚伪的婚姻中濒临毁灭的边缘,他们在婚姻的笼子里各自挣扎,企图摆脱夫妻间牢牢捆绑的表面关系。
除此之外,《盲卜》、《艳遇》、《比翼鸟》、《同床异梦》等篇目也都在不断地重复表现“围城”这一永恒的婚恋主题。
《比翼鸟》中所书写的有关红尘男女情欲的局囿恰恰暗合了钱钟书先生《围城》中混乱和盲目的婚恋状态,显然,这也就是婚姻“围城”的一种叙事符号,既是作者对奴役婚姻的世俗男女的控诉,又是对被至情至信的完美爱情所抛弃的人的悲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关于“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的论述中就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冲突、抗争与残酷的,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在心水看来,就连夫妻、情人之间也难逃这关系的劫难。
(二)社会困境
所谓“社会”围城,我们可以将其与法国杜尔干及其弟子的主要理论——“社会决定论”相联系。社会决定论认为个人与社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实体,因此两者之间形成紧张的状态,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就是那种从个人身外作用于个人的力量,作用于个人意识的压力。也就是说,社会压力不知不觉的强迫作用使人的动作状态处于一种被控制的处境。《比翼鸟》中关于社会“围城”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社会环境因素和文化冲突这两个方面,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环境使然”的关联。
就环境因素而言,小说集主要表现了在“围城”困境的背后,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在影响和感染着人们行为和活动的视角。在《樱花》和《战火》中,作者都嵌入了战争这一背景,战争所带来的生离死别往往使人陷入一种生存的困境,人在动荡的环境里必然走向不安的“围城”。《放生》更是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社会的纵欲现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人欲横流的普遍心理,佛门圣地的堕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这一社会环境的驱使,拜金主义的潮流使本应远离“十恶”的佛门也难逃沉沦的困境。
在文化冲突方面,心水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华人在传统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碰撞冲突下所产生的生存困境。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香肉官司》了,文中写了阮成等四个越南难民在澳洲因宰狗吃肉而被法院罚款的事,筑起了越南享用香肉的习俗和澳洲保护动物的文明之间的隔膜,揭示了异域文化彼此冲突和颠覆带给人的适性难题。这种在不同国度背景下关于文化认同和生存方式的“围城”,恰恰也是多数海外华文作家得天独厚的写作素材,海外华人的身份参照和生活体验让这一作家群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独特的思考张力,作为澳华作家的心水自然也不例外。
(三)自身困境
与前面所提到的社会决定论相对立,“自身”困境所要揭示的则可以说是有关“自我决定”的理论。自我决定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该理论强调个人在充分认识自我需求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作出行动的选择。由此可见,其实自我困境才是“围城”最本质的内涵,正如存在主义所提出的另一个哲学主张,人的本质是由自己所选择的行动来决定的。
纵观《比翼鸟》中的“围城”现象可以发现,所谓的婚姻和社会都只不过是人生存困境的表象,是促使人迷惘和困惑的催化剂,真正根深蒂固的危机是人自身的精神困境,或者可以说是自身人格的缺陷。或迎合,或迟疑,或错位,倘若改变一种态度,一种认知,“围城”的最终“突围”也不无可能。
《争如不见》中的梅嫂一度陷入“期望——失望——希望——绝望”的处境中无法自拔,真正困扰她的其实不是她口中念念不忘的恶缘,归根到底在于她内心深处对自身命运的否定。在梅嫂的意识里,初恋情人萧波的去留决定了她幸福的走向。我们说,正是这种男人主宰命运的错误观点使她的痛苦得不到解脱。《古玉》中处于“秋之恋”的“我”,在婚姻道德与非分之想中左右挣扎,既想爱又不能的绝望最终使“我”以死来守候对心上人的痴情和对妻儿的责任。在这里,性格的弱点和欲望的冲突成为主人公生死的归因,这不只是一个婚姻的“围城”,更是一个由于自我搁浅所造成的困顿。
“围城”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比翼鸟》正是通过对婚姻、社会、自身这三个方面困境的统一呈现,将“围城”这一内容推向人性的高度和哲理的深度。作者深邃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生活现象的表面描写上,而是站在一种哲学的高度来俯视社会和人生,把“食、色”本性的不易升华到人生中现象与本质的形态,展现了一种“围城”式的困境,从而集中凸显了人生存状态的悖谬,并揭示了人与这种困境之间的关系,闪烁着存在主义的哲学光芒。
二、“因果”母题关乎福祸的叙述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基本理念中,关于因果观的论述自古有之,我国历史上各成一家之言的儒、道、佛三教对于因果之说就已各有说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易经》就已提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因果教义。因果律更是三教之一的佛教最基本的理论之一,是佛法中十分重要的道理,其《三世因果经》中便有有关行善积德与行凶作恶的因果循环报应规律,佛教因果业报论强调个人的善恶行为必定会给自身带来前世、现世或来世的轮回报应,也就是说一切事物皆由因果法则支配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中国许多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也极力呈现这一规律,如《西游记》的邪不胜正、《水浒传》的官逼民反、《金瓶梅》的因果宿命、《雷雨》的悲惨命运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有关因果的叙事模式,于是,因果律就这样逐渐走进了中华文学母题的行列,成为文学反观人的行为,进行劝世说教的有力工具。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华文作家心水,在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追寻这一文学现象的呈现,以因果报应的观念为支撑去构思行文的框架。在代表作《比翼鸟》中,作家通过道德规约和江湖概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有关因果的表现机制。
(一)道德规约
面对浮华世俗、芸芸众生,心水在“浮世篇”的创作中选择把道德因果作为观察社会、审视人性的一个新视角。其中,《赔偿》和《月黑风高》都相继揭示了拜金主义、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使人丧失本性,游离自我,因果报应必给道德沦陷的人以沉重的打击,最后他们只能以“无路可走”的结局告终。试问,《赔偿》官司上败诉的古风和《月黑风高》下的赌徒九哥,他们的运气(或者说是命运)是被谁改写的?只能说是钱财的贪念在作怪。而《谈虎》一篇则是关乎所谓的“淫人妻者,妻必被人淫”这一关乎性道德的因果报应,这是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主旨句,《谈虎》所讲也是如此,它写的是男主人公谈虎在给别人戴绿帽子的同时自己头上也戴着顶绿帽子的讽刺行径,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欲与受罚的因果律。以上所举,作者似是基于现实人生的欲望基础,以财色之欲为出发点,在因果报应的逻辑下,让故事中人为自己肤浅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小说集中,最能体现佛家有关因果律的应是《烦扰的菩萨》,文中写道为了众生各种相关联的祈求而烦恼的观世音菩萨请释迦牟尼开示指教时,佛祖指示说:
“阿弥陀佛!让有带业障者受点苦,不就都完满了吗?”
“有求必应也得看来求者的为人,那些带业者向你祈求,是非分之求啊,怎能让为非作歹者因你的法力而摆脱得报应的天理呢?”
这些细节性的语言都体现了善恶业在因果律的作用下形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心理所求也在不断膨胀,在传统道德的规约下,因果报应被重构成寻求人性回归的准则,确实可以引导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尽力维持德福的统一。
(二)江湖概念
在武侠小说所虚构的江湖中,虽然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被削弱了,但在风风雨雨的较量和阴谋中仍存在着一套维护正义的权威,即江湖规律。而在这个想象的空间里,心水也极力叙述着邪不胜正的真理和偏执的江湖概念所带来的困境。
纵观武侠小说这一被誉为中华文学奇葩的创作,不管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还是倪匡、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其故事情节大都脱离不开善恶因果律,心水的《比翼鸟》之“武侠篇”系列亦是如此。
如《武侠》中,扬名南方的青年侠客“白面神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奸淫掳掠、恶名远播的“东北狼”孔武,验证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及“邪不胜正”的江湖秩序。但是,所谓行侠仗义的江湖概念往往表现出的是一种依靠杀伤来除恶的倾向,这与佛门普度众生的感化教育的思想相矛盾,理想的善业善果报应自然得不到完美的运行,文末白侠最后的茫然或许就是对此的悟觉。
在《柳含月》中也是如此,按因果逻辑,柳含月带有杀人的业障,但基于她复仇前的侠义行径,对等原则下作者为她安排的代价仅是断送了侠女的声誉,并未取她性命。柳含月为报亲仇,走火入魔胡乱杀人,在江湖上掀起一股血雨腥风,这就是江湖中“快意恩仇”的复仇观,在报仇中寻求血腥的快感也是武侠中人偏颇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文末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老尼姑,她的出现是为了扭转柳含月的命运。面对充满杀戮之气的女施主,老尼姑劝诫道:“你父母为何被杀,想必也是当初他们杀了别人吧?你报仇滥杀无辜,被你所杀者,他们的子女将来又会来找你报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最后以一股佛法慈悲的至柔之气成功地感化了柳含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其实老尼姑的出现正是对这种以杀伤为主的偏着的江湖概念的纠正与重整。
心水在“浮世”的现实和“武侠”的理想中再现和重铸中国传统因果观的基本内涵,呼唤个体对社会道德体系的思考和自觉意识的觉醒,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以因果之律为杠杆,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行善积德的心理寻求一个平衡和支点,更可以劝诫心存恶念的人改邪归正,迷途知返,实为善哉。
三、“圆缺”母题流动的悲剧意识
学者祁志祥认为,“以‘圆’为美 ,是佛教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的突出表现之一。佛教认为 ,圆形圆满无缺,是现实中最美的图形。涅,圆满无缺,因而称‘圆寂’;般若圆通无碍,因而称‘圆智’;佛法圆活生动,故称‘法圆’。如果说‘净’是佛典中频繁出现的道德术语 ,那么‘圆’则是佛典中频繁出现的美学术语。”[2]。可见,在佛家教义中,“圆”是完美、圣洁的象征,正如因果一样,“圆”的思想与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不谋而合,“以圆为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也对中华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们说,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隔着一条缝隙,或彼此共鸣,或不可逾越,由此便产生了“圆”与“缺”的纠缠,相对相依。就这样,“圆”与“缺”的对立统一组成了中华文学另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书写着艺术与人生的变奏。但有一点不难看出,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作品创作大多喜好以圆满的结局收尾,就连《窦娥冤》、《长生殿》、《赵氏孤儿》、《汉宫秋》等一系列被称为悲剧代表作的作品也是如此,这就是中国人的“圆满崇拜”心理。而对于这一大众崇拜心理,有许多大家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和批判,胡适先生就把这种“团圆的迷信”看成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鲁迅先生也于1925年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对这种 “瞒和骗”的国民心理进行了抨击。而心水对此又是如何抉择的呢?他依旧继承了“圆缺”这一中华文化母题的传统,在《比翼鸟》中探求完美和虚无的纠结。然而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哲学传承中,心水对“圆”与“缺”的选择同样有自己偏好和强化的痕迹,更多的是以一种残缺的情感倾向显现出一股流动的悲剧意识。《比翼鸟》正是通过一系列对人与社会的不完满的叙事,即“缺”,来对所谓的“圆”进行破坏与毁灭,对人类所淫浸的幸福进行封杀,对英雄本应具有的侠气给予消解,从而让人感受着强烈的哀痛和遗憾。
(一)幸福封杀
就这点而言,小说对“圆缺”母题的表现首先集中在对那些不美满的婚恋故事的叙述,这里的不美满又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残破的婚姻危机,这点本文在前面所论述的“围城”母题中已详细分析过,此处不再多作解释;另一种则是“圆”中见“缺”的爱情故事,粗略看来,有人会认为心水似乎也深受“圆满崇拜”心理的影响,其实不然。心水笔下的故事结尾有的看似圆满,其实亏缺不全,正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所表现出的虽化蝶成双却生而有憾的思想基础。
在“浮世篇”中,《常在常活》就表明了世间总有与人为难的遗憾。阿在好不容易从一段婚姻的恐惧中走了出来,与真心待她的沉诚意缔结连理,故事到此本可结束,可心水却笔锋一转,写阿在婚后发现老沉原来不能人道,只追求精神之爱的伴侣。《争如不见》中相思数十载的重逢,激动兴奋中却平添了一丝遗憾之情,虽如愿再见暗恋已久的情人,得知其同性恋取向的打击却无法弥补梅嫂心中缺失多年的情感。相似内容的还有《同床异梦》、《蓝子》、《网缘》等。心水对爱情婚姻“圆缺”的描写情有独钟,在他的笔下,跨越时空的故事里总是伴随着“圆”的虚幻和“缺”的实在,人们幻想的完整被无情地封杀,不断制造和产生着情感的空缺,将一幕幕遗憾的世情上演。
(二)侠气消解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对江湖侠士来说,“为国为民”才是他们最本质的精神标记,一旦丧失这一安身立命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便也就与“侠义”疏散,即使有另一种生活,他们的精神也是不知所终的。所以,对侠士最大的毁灭就是让他们飘然远遁,远离国民,迷茫困顿,在这方面,心水是从未手下留情的。除了爱情婚姻,《比翼鸟》的“圆缺”也与这“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有关,这主要体现在辑二“武侠篇”中。
《盅毒》就是典型的代表,被江湖视为群雄之首、具有扬名天下的大侠形象的剑神,本应是所谓的 “侠之大者”,却深陷爱情的泥潭,忘记了自身的使命。若单说爱情,剑神最后是得到的,可若说结局,我认为却不是单凭爱情就能衡量的,因为剑神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迷失了自己的侠士人格。剑神从笑傲江湖到守候裙下的转变,其生命意义已大大被削弱了。
《孤帆远影碧空尽》亦是如此,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都颇有名气——大侠一哥和兰子女侠。无奈他们一见钟情,在兰子远赴重洋弘扬峨眉武学的那一刻起,一哥就一蹶不振,最后甚而投身分别的湖畔,江湖再不闻一哥的侠义事迹。除了叹息男子的痴情外,我更惋惜一代侠士的丧失。不禁想起《神雕侠侣》中的“神雕大侠”杨过,他也曾承受过和小龙女分别二十年的痛苦,但不同的是,除了情,可为第二的“为国为民”同样在他心里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杨过行侠仗义的行径和他送给郭襄的三样生日礼物便可看出,所以即便后来隐居古墓绝迹江湖,“神雕大侠”的名号依旧流传千古。或许这就是情为第一的“侠之大者”与心中独有爱的一哥的区别了。此外,辑二中的《解药》、《玲珑》等文章也都是对武林侠士人格与精神的放逐,作为情的祭品,作品悲悯的是一种气质的蹂躏。
心水站在一个至高的立足点,在对“圆满”与“残缺”的宣判中显示了理想与现实这两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之间彼此的乖违,在不圆满中透视现实的本性。尽管人们往往心存夙愿,其实,“缺”才是世界的本真面目,正如往复循环的月缺月圆, 一月之中缺多圆少是自然的规律,没有谁可以让月亮常圆不亏,缺憾是生活与人生的常态,《比翼鸟》的寓意正在于此。
四、结论
围城、因果与圆缺,这三个母题是心水对中华文化认同与建构的依托,作为一个连接人与社会的符码体系,这三个母题不是相对孤立地存在于作品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彼此牵制地负载着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在一篇作品中往往同时表现了两三个母题的内涵,在一部小说集中,又是在三个母题的完美结合中来解读作者的思想逻辑的,从而提高了这三个母题鲜明的文化生命力,从“围城”到“圆缺”的叙事,起转变机制的便是“因果”的定律和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心水侧重于以一种独立于故事之外的旁观者身份去进行隐藏性的批判,在小说中,心水也没有直接对人物的善恶进行鲜明的爱憎表态,而是在冷静的叙述中巧妙地引导人们去发现生活,思考生活,领悟哲理。
参考文献:
[1]杨匡汉.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2]祁志祥.以圆为美——佛教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之一[J].文史哲,2003(1).
责任编校:林奕锋
网络出版时间:2015-03-02 2:51:2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302.0952.024.html
On the Motif of Chinese Culture in XIN Shui’s Novels
GU Da-yong; LAI Si-r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QuanZhou362000,FuJian, China;
Education Office of Cizao, JinJiang362000, Fujian, Chinaeducation offices)
Abstract: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XIN Shui(HUANG Yu-ye), an Australian Chinese writer, tried to preserve the voice of motherland in his creation, reflec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motif. His novelInseparable King Bird constructed three narrative systems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motif: motif of siege, motif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motif of weal and woe. In his narration, XIN Shui made inquiries about the paradoxical subsistent state of “siege” from three major aspects, i.e. predicament of marriage, social distressand own questions. He narrated the weal and woe within thecause-effect logic of moral protocol and vagabond concept.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weal and woe flows in his novelsthrough forcing out happiness and dispelling chivalrous. The three motif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s a whole carry the writer’s cognition to society and life.
Key words:XIN Shui; Inseparable King Bird; motif; siege;cause and effect; weal and woe
中图分类号:I6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1-0103-05
作者简介:古大勇,男,安徽无为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2013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FJ)。
收稿日期:201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