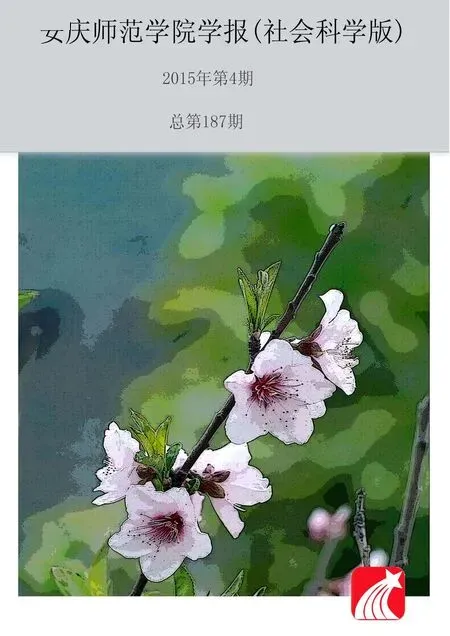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的精神流变及其文化表征
陈婷婷,王桂英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的精神流变及其文化表征
陈婷婷,王桂英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摘要:除了与传统的显著差异,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自身也经历了显著而深刻的精神流变:主人公形象完成了“边缘人-外倾性-向内倾型-软弱性”的演变,小说的主要矛盾也更多地由外在社会冲突转为聚焦自我内心。由此,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呈现出西方乃至东方其他国家相异的文化表征。
关键词: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思想主题;文化表征
一般认为成长小说这一概念起源于德语文学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是一种带有传记色彩的文学类型。日语《大辞林》等辞典将该词译为“教养小说”(日语汉字“教养”即“教育”之意)或是“发展小说”,可以看出是对原词的直译,意即描述主人公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历练,逐渐形成完善人格的小说。德语文学中的教育小说是成长小说最初的原型,这一类成长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合作者的过程”[1]。
随着时代发展,成长小说本身的内涵和形式也随之演变,在思想主题、主人公性格特征、人生际遇和文本结构等方面与传统有了显著差异,在保持着成长小说本质——反映主人公自我身份的确立,实现自我价值的努力和成长旅途上的严峻考验——的同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而日本文学中“成长小说”这一说法仍是作为“教育小说”的类义语来加以阐释的,并未体现出成长小说的当代特征。
日本成长小说兴起的历史文化语境、秉承的文学传统与西方成长小说不同,表现出的思想主题等也不尽相同。本文拟从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中选取几部较有代表性的成长小说进行探讨。这些小说发表的年份跨度约80年,大致反映了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的概貌。
一、20世纪初的成长小说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历经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口号。但日本的开化并非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内部自然发展而来,不彻底的改良造成社会意识方面的滞后。欧化的只是外表,没有把握到甚至压抑着现代精神的精髓。觉醒于近代的知识分子在外部压迫下渴望发展自我主体性,对“近代自我”的孜孜追求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可视作成长小说的岛崎藤村的《破戒》(1906)、夏目漱石的《三四郎》(1908)和《其后》(1909)均体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强烈的近代自我意识,着重描写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身份问题。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多见“边缘人”类型的主人公,他们通常经过与他人的冲突来获得对自我的认知发展。
由于牵涉贱民歧视问题,《破戒》主人公的成长包含了强烈的身份意识。部落民出身的青年教师丑松自幼便被父亲送离出生地,去城镇接受教育,目的是为了让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在社会中立足,打破下等阶层的人无法出人头地的命运。丑松遵守着父亲让自己隐瞒身份的戒律,却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属于特殊的阶层: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外界还是不会因为他个人的才能或特殊性而区别对待他。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丑松再也无法回到无知无觉的状态,他清楚地感到自己与身边的群体格格不入。
小说开头设置的冲突是隐性的,即让丑松目睹了一位部落民商人被撵出旅馆的事件。他听着旅馆住户对部落民的污言秽语,觉得愤愤不平,决定搬出旅馆。然而只要种族歧视普遍存在,冲突就不会因为他的刻意避免而消失。在学校,丑松因为同情部落民学生而遭到嫉贤妒能的校长与同事的怀疑,又因维护出身部落民的思想家而引发了争吵。丑松结识了这位亦师亦友的思想家莲太郎之后,受其感染逐步踏上了追求真实自我的道路,渴望表明身份的心情愈发强烈,然而就在他要打破戒律的时候,父亲去世前的遗言和殷切期望再次束缚了他。丑松一方面无法融入观念保守的大多数人中,另一方面又找不到对出身族群的归属感,一度陷入自我身份迷失的危机中,直到小说结尾,他因思想家兼引路人莲太郎之死而“顿悟”。 但是,思想上的妥协性使他无法真正改变什么,他终究做不到像莲太郎那样为底层阶级奔走呼吁,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能被迫远走他乡,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
同样,《三四郎》里的广田和《其后》中的代助都是社会转型期典型的“边缘人”,他们都持有明晰的社会观察视角,讽刺当时所谓“文明开化”带来的利己主义等道德伦理的堕落。这一时期属于日本由封建社会逐步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西方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也传入日本。然而作者夏目漱石认识到,西方社会倡导的个人主义并不适用于日本的文化土壤,他借广田之口道出:“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一举一动都未曾脱离开过别的人,一切都在为别人考虑……社会的变化终于使这种伪善再也行不通了,结果在思想行动方面便引入了自我为主的思想。这便使自我意识发展得过了头。”[2]123环境造就了众多自我膨胀、自私虚荣的伪善者,对青年的人格成长带来的影响极为不良。
《三四郎》中的主人公三四郎便切身地感受到这种影响。他从乡下来到现代大都市东京求学,这种“出走”是成长小说经典模式中的一环,“离开故乡的压抑氛围(以及相对的天真状态),独自在城市中前进。这是他真正的‘教育’过程的开端,是在为他的职业生涯与都市生活做准备”[3]17。然而他在东京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各色人等的不同价值观让纯朴的三四郎陷入迷惘,他一方面想要实现符合社会价值导向的人生理想(即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另一方面又视品行正直的“边缘人”广田教授为精神偶像。在两种思潮的夹缝中徘徊的三四郎未能像经典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能够坦诚地适应近代世界,脱离青春期,走向成熟”[3]18,而是在激变的时代中不知何去何从。
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体现出与欧美成长小说不同的文化表征:第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旧道德,如家父长制度。尽管“德国也是一个父母对子女拥有很大权力的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的父母近乎强迫地要求子女服从于自己”[4]93,吸收了先进文明思想的子女必然会与父辈在观念上产生冲突,然而受制于义理孝道,欲要打破父亲的管制极为艰难。《破戒》中,对于丑松而言,违背父亲的嘱咐坦白身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那些佛门弟子身着黑衣而苦守着的许多戒语,同自己的这一条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背弃父母的秽多之子,那就不是什么堕落,而是败家的逆子了”[5]。《其后》中的代助虽觉得“父亲不是一个隐蔽自己观点的伪君子,就是一个不明事理的愚人。……然而肚子里总觉得是对父亲的侮辱一般,很难平静下来”[2]298-299。第二,主角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往往不会有实际的反抗举动,而是对社会弊端采取妥协或是冷眼旁观的态度,侧重精神自由。例如《三四郎》中的广田,“嘴里叫着危险危险,而自身并没有置于危险的境地”[2]42。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抵抗,因此在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宛如“空中楼阁”的批判意识终将面临被倾覆的危机。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长小说
1929年至1933年,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并转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此后,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路旁之石》(1940)与描述女性成长的《放浪记》(1930)均体现出日本民族传统的勤劳、自强的精神。二者都叙述了主人公如何独立自主,在逆境中不认输,并坚持学习,最后终于过上安定生活的奋斗历程。在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苦的这一历史阶段,自我价值实现转为成长小说的核心主题。主人公的标志性成就是学会赚钱谋生,更大的成就则是过上体面的、受人尊敬的生活。
《路旁之石》的主人公吾一是以作者山本有三为原型刻画的。吾一出身贫寒,少有大志,不畏社会的世俗压力及富人阶层的冷眼鄙薄,忍受着父走母丧的孤独,生活带来的每一次艰难考验都将他的意志磨炼得更加坚强。吾一受到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劝学篇》的影响,坚信“人非生而有贵贱”,坚持读书、奋斗。之后他遇到了成长的引路人——漫画家黑田,使他认识到唯有自食其力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肯吃苦就是好事。……年轻的时候,不喝点苦水,是长不大长不结实的。我把辛苦当作老师,人要是不经过艰苦的磨炼,容易高傲自大。……要做时代的主人,就必须在艰苦环境中磨炼。”[6]黑田敢于挑战世俗、敢于揭露现实的勇气改造了吾一思想中懦弱的部分,使吾一坚定了追寻梦想的信念。这种叙事模式类似经典成长小说:“青少年主人公走上独当一面的成长道路,通常由于他自身的气质而遭遇挫折,偶遇种种引路人和指导者,在选择朋友、妻子和职业方面犯许多错误之后,最终通过找到能有效施展才能的领域来使自己以某种方式适应时代环境的要求。”[7]
《放浪记》中的“我”的原型也是作者林芙美子本人。“我”很早就被迫远离父母,长期生活在困境中,在报社打过短工,做过女佣,摆过地摊,当过文秘,甚至做过酒馆女招待。其中穿插着与数名男子的情感经历,但结局都是分道扬镳。然而异常坎坷的生活经历并未使“我”沉沦下去,而是顽强地怀抱理想,直面现实——“我才不喜欢那阴郁的曲调,我喜欢春天里的生命之歌。”[8]26“活着倒也是件愉快的事。虽然孤寂的心情如故,心中却燃起了生命的热情。”[8]69虽然生活与心境起起落落,但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从未消失,最终迎来了生活与创作的转机。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传统线性模式。
这两部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环境十分严酷,但在饥饿、屈辱不断威逼的困苦境地中,主人公却持有明朗真诚的生存态度,在家庭与社会的重压之下显示出非凡的生存力量。不仅彰显了成长小说最重要的文化表达——在物质和精神上寻求光明乃是生而为人的理想和使命,而且诠释了日本民族自古以来的强烈生存意志与精神至上的价值观。“明治维新后日本在短短三十年内崛起,跻身于世界强国,与这种决心与信念是分不开的。”[9]
三、二战后的成长小说
二战前的日本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大多通过奋斗来谋求社会与自我之间矛盾的解决,以达成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为人生目标,是一种“外倾型”的人生。而二战后的成长小说受到转型期混乱的社会意识影响,出现了自我意识过剩的思想趋势,主人公因为种种因素而无法融入社会,走上了“内倾型”的人生道路。“这类小说看似背离了成长小说的模式,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改造,赋予其新形式并深化了成长文学的主题,是对现当代人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的深切关怀,同时也彰显了作家们对当代社会中个人成长问题持久的兴趣和深深的忧虑。”[10]234
太宰治的《斜阳》(1947)和《人间失格》(1948)便是“内倾型”成长小说的典型。与20世纪初的成长小说的类似之处是作品均展现出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的自我身份危机。战争的残酷和暴虐是对人类文明和道德传统的挑战,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创伤,也为其成长提供了特殊的环境。二战后人们普遍丧失精神支柱,传统价值面临崩溃,“时代蚕食着年轻人的生命,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青年人只能用各种方式来准备自身的生存盛宴”[11]。
《斜阳》的女主人公和子出身贵族,随着战后贵族制度的瓦解,和子家道中落,不得不从东京老家迁居至伊豆的乡间,而迁居恰恰成为和子的成长出发点。搬家意味着离开贵族的土壤,彻底丧失贵族身份,“身为贵族曾有的骄傲与自尊心都被撕得粉碎”[12]。由于差点引发火灾,和子遭受了平民的辱骂,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挨家挨户道歉。她由此进一步意识到家族没落的处境,加上目睹母亲的逆来顺受导致的毁灭,和子不甘衰落至死,渴望打破原有身份消解的宿命,走上“为了爱与革命而活”之路,以“出走”和“逃离”来瓦解家庭空间。
战争带来了社会的转型甚至是发展的断裂。和子在历史的考验和磨难下,其身份意识、自我认同、情爱观念、生存动力等都在不断变化、建构和生长着,历史时间被分解在个人成长时间里。如巴赫金所言:“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13]母亲、弟弟对和子产生的影响,以及和子自身的战争体验令她发现自己不能从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中找到意义,于是追求反家庭生活状态,离家找到情人上原并与他共度一夜,怀孕后却毅然选择离开上原独立生活。她的自我解放精神不容许她重返闭合空间,回归原始身份。和子认为自己的革命在勇敢生下私生子时已经胜利,贯彻了反抗虚伪世俗,为新道德殉难的信念,“我为自己能满不在乎地无视旧道德而获得一个好孩子感到满足”[14]106。虽然执意摈弃传统的和子只能做一个心灵上的自由人,以自我牺牲的信念来走完这条对现实社会进行叛逆和抗争的艰辛道路,但是,“她不屈从于各种思想规绳,不以融入社会作为成熟的最终奖赏,不断反思、提升对自我的认识,由消极抵抗到逐渐把握人生目标,才能在如斜阳般没落的贵族阶级中迎来新生”[15]。
《人间失格》叙述了一个充满自我欠缺感的少年叶藏一步步走上自我放逐乃至自我毁灭的道路的故事,真实剖析了二战后日本青年一代中普遍存在的彷徨、忧郁、苦闷的心理状态。叶藏厌倦现代文明的虚伪和堕落,但又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感受到的只有焦灼、孤独与绝望。
从悲剧结局上来看,《人间失格》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反成长小说有相似之处,区别在于主人公看似颓废堕落,内心却始终坚守自我重构的价值体系,以一种自我破坏的方式来追求至善至美的绝对理想,从而扭曲地确立自我价值。叶藏一方面猛烈批判家庭、社会中他人的冷漠、虚伪和庸俗,另一方面又不想彻底脱离社会。但无论表面上如何淋漓尽致地发挥“丑角精神”来取悦他人,叶藏都无法真正改变自我来顺应社会。种种内心冲突使其自我不断内缩,转而以封闭和自虐的方式来隔断与他人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向外界关闭大门的同时却没有能力承负沉重的自我,这样反而容易把自己压垮。这种纯粹的秘密生活是出于对外界的惧怕和无助。”[16]因此,在唯一信任的妻子被人玷污之后,叶藏对他人最后的信赖之心也幻灭了,“对所有一切越来越丧失了信心,对其他人越来越感到怀疑,从此永久远离了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14]210。对客体世界的排斥使得他的主体性成长就此中断。
在明治时期,国家统一,把国家作为家族看待的家族式国家观就已形成,近现代社会因此出现形形色色的集团主义[17]108-109。在日本,从众心理较为普遍,明治维新之后的一些伪西洋化的行为即其证明。二战后同样产生了从众宣扬民主政治、摆出革命姿态的人,或者追求实利的拜金主义者,等等。太宰治的作品中尽管充满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却依然流露出日本人的集团主义道德观。《人间失格》里,叶藏见多了利己主义者,无法认同其价值观,却仍然“越想越困惑,最终下场就是被‘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攫住”[14]143。主人公在寻求集体归属感的道路上屡屡失败,挫折经历带来的是对真实自我的压抑,这与战后美国成长小说中青年人以反叛权威、放纵发泄来解放个性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反差,说明日本人注重的还是集团性。此外,社会转型期的成长文学尤其突出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现存价值观的否定和重估是现当代成长小说主人公的典型特征,他们多数都没能与社会达成妥协,宁愿选择分裂、异化、退缩,甚至死亡”[10]235。
四、20世纪60年代后的成长小说
日本社会经历了战后重建和经济高速成长期,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新时期的成长小说也开始走向多元化,女性逐渐提升了对自身的关注,小说主人公的年龄层次进一步降低,以大学生或是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为主。主人公的成长道路无论是曲折前进还是悬浮不定,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自我确立的软弱性。
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1987)中的主人公渡边等60年代的大学生以玩世不恭或是逃避现实的方式成为主流文化的放逐者。“六十年代性观念的开放,传统家庭意识的解体,人际关系的淡漠造成了普遍的孤独和不安。”[19]渡边的友人木月“非常在乎对现世规则的掌握……不能珍视那最珍贵的自我,却无限鄙视并最终践踏了不能最好地掌握现世规则的自我”[18],最终死于自我与社会之间无法调和的拉锯战。与木月截然相反,精通现实社会游戏规则的永泽纵情发泄,却同样无处依托高度情绪化的精神。渡边本人在与两个女子的情爱中成长,但到了小说结尾却依然徘徊、迷失在非现实与现实的交界之处。
如果说《挪威的森林》反映出社会机制发展背后人的异化感与流浪感,吉本芭娜娜的《厨房》(1988)却实现了自我和社会的调和。小说中的时代背景已经跨越了20年,“厨房”这一意象在小说里不仅是安全感的来源,更寄托了主人公美影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家”的渴望和美好想象。奶奶去世之后,美影才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着封闭式的家庭生活,鲜少真正与外界接触。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不得不竭力面对被打破的生活模式,这时,曾受过奶奶关照的同学雄一和他的变性人母亲惠理子收留了她。在这个看似病态的家庭中的生活经历反而使得美影能够以平等的眼光和包容的态度来看待身边的人。惠理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打动了美影,让她下决心走向自立:“我会不断成长,经历风霜,经历挫折,一次次沉入深渊,一次次饱尝痛苦,更会一次次重新站起来。”[20]美影不断从生活中汲取养分来完善自我,并通过学习一门手艺而找到了喜爱的工作,在惠理子遇害之后还帮助同样失去至亲的雄一走出阴影,实现了自我价值。
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2007)展示了又一个当代青少年的成长风景。主人公知寿从头到尾都像是个没有自我的模糊存在,每天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地度过。这种“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社交圈,甚至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的群体却是当下日本青年的典型”[21]。知寿的安全感并非来自亲人而是来自物件,不是活在当下而是依赖过去的回忆,揭示出了亲情缺失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情感需求遭到忽视,缺乏自我价值。好在老人吟子作为年长者,富有人生经验,或多或少能从旁观者角度来帮助知寿认识自身和世界。当知寿终于意识到自己终将独立生活,却又对外界感到不安与缺乏自信的时候,吟子只说:“世界不分内外,世界只有一个。”[22]点明了青年人需要走进实际生活当中接受磨炼和考验,才能深刻了解并超越自己的狭隘、无知与软弱。
现代成长小说体现出信息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传统成长小说中提供关怀和智慧的引路人正在消失,而主人公的焦虑感在增加。主人公在认识自我时遭遇的迷茫困惑反映出了日本人的“娇情”——“与父性的、男性的、攻击性的西洋人对比,日本具有母性社会的特征(女性的、被动的、调和的),拒绝上学与交际恐惧等社会问题的背景中存在这一特征。”[17]99因此日本青少年在主体性发展上体现出幼稚、被动、依赖他人的一面。正如《菊与刀》中指出的:“近几十年间,日本小说中反复有如下表现——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在愤怒即将爆发的当口,相反坠落至极端的忧伤抑郁之中。小说主人公处于倦怠之中。……日本人特有的这种倦怠,乃是一种过度敏感于受伤害的国民病。他们将孤立的恐怖引向内心,惶惶不可终日。……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发动攻击,当代日本人却将攻击的方向转到了内心。”[4]143-145因此,日本现代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对于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往往不去深究其背后的社会弊端或是自身的性格缺陷,而是消极地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事实上,能否获取经济自由、摆脱精神依附走向人格独立,超越心灵闭守,探求自我实现,走向真正的成长,关键因素在于主人公能否实现由软弱、被动、迷惘的客体意识到勇敢、坚定、自信的主体意识的建构。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现代成长小说的意识形态中,个人权利和发展、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涉及政治权利意识,中国成长小说里主人公的成长也往往是对时代变革的热烈呼唤,而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虽然也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主人公却对政治普遍缺乏关心,体现出日本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度低下的一面。政治始终不是青年成长中的热点问题。“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是由政治家来确立的,作家仍然保持了政治局外人的立场……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描写和反映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作品很少,一般都局限于封闭的个人生活”[23],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脱政治性”。
五、结语
大体说来,成长中的主人公必须面对“自主性(autonomy)”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矛盾带来的困惑。虽然二者的张力在各国成长文学中均有体现,但从以上四个时期的日本成长小说中可以看出,主人公所承受的压力往往性命攸关。溯源到日本历史上,封闭国家与单一民族等因素使得社会的融合与冲突并不激烈,而“集团意识”也在压抑个性。相对固定的国民性构建了稳定有序的社会,也削弱了变化与活力的可能。与崇尚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美利坚民族不同,日本人“‘外的客我’意识较强,因过分意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产生‘自我意识过剩’……‘集团我’就是个人通过与集团的一体化来实现的,具有强烈的从属意识和依赖意识”[24]。这一切造成了日本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就算内心抵制教化,却极少出现激烈大胆的挑战行为,而是以消极甚至自虐的方式来表达反抗意愿。
参考文献:
[1] 刘半九.绿衣亨利·译序[M]//凯勒.绿衣亨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
[2]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小说选[M]. 陈德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 Jerome H. Buckley. 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4] 露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魏大海,等,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
[5] 岛崎藤村. 破戒[M]. 柯毅文,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38.
[6] 山本有三. 路旁之石[M]. 王克强,等,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31.
[7] Susanne Howe. Wilbelm Meister and His English Kinsme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0: 4.
[8] 林芙美子. 放浪记[M]. 魏大海,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9] 李兆忠. 暧昧的日本人[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7.
[10] 孙胜忠. 英美成长小说情节模式与结局之比较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11] 島田昭男. 「斜陽」覚え書―直治の問題―[M]//久保田芳太郎.怒れる道化師.东京:(株)教育出版センター, 1979: 73.
[12] 矢島道弘. 太宰治ー法衣の俗人ー[M]. 東京:明治書院,1995: 13.
[13] 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32.
[14] 太宰治. 斜阳[M].杨伟,等,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
[15] 陈婷婷. 自我身份的消解与重构——太宰治《斜阳》的成长主题解读[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2): 116.
[16] 徐丹. 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M]. 上海:三联书店,2008: 44.
[17] 吉野耕作. 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8] 叶岗. 迷失自我的象征性森林——《挪威的森林》赏析[J]. 名作欣赏,2002(3): 45.
[19] 刘延红. 写给青春的墓志铭[M]//雷世文. 相约挪威的森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0.
[20] 吉本芭娜娜. 厨房[M].李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6.
[21] 玄田有史. 孤立無業[M].东京: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2013: 22.
[22] 青山七惠. 一个人的好天气[M]. 竺家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32.
[23] 王向远. 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57.
[24] 南博. 日本人的自我[M]. 刘延洲,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1989: 3-4.
责任编校:林奕锋
Spiritual Changes and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Initiation Novels
CHEN Ting-ting,WANG Gui-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Anhui, China)
Abstract: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ork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initiation novels have undergone obvious and deep spiritual changes.The image of characters has undergone the change from marginal man, extroversion and introversion to feebleness. The conflicts have also changed from social struggles to self psychological struggles. Accordingl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initiation novels are cultural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and other eastern ones.
Key words: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initiation novels; them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4-0040-06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10
作者简介:陈婷婷,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王桂英,女,安徽巢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本成长小说及其文化特性研究”(SK2013B217);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培育基金人文社科项目“日本近现代成长小说及其文化特性研究”(2012xmpy007)。
*收稿日期:2014-09-04
网络出版时间:2015-08-20 12:5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