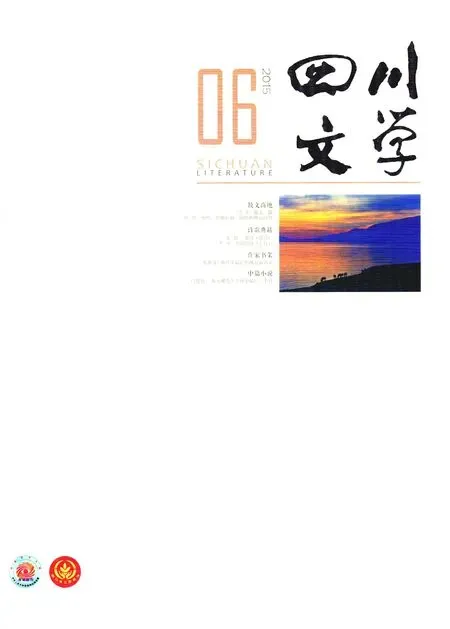散文二题
马 平
散文二题
马 平
马平,汉族,1962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运山镇双龙村。1998年7月调入四川省作家协会,曾任巴金文学院副院长并挂任青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文学创作一级。长篇小说《草房山》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
雪后的茶
雪停了。我站在窗前,没有看到一点积雪。楼层太高,树顶就太低。成都城里下了一场雪,树顶却没有挽住一抹雪白。那些低矮的屋顶,还有地面,更是生硬得可以,都拒绝留下一点雪来过的迹象。
窗外却是有过大雪的景象的。我在街上时,雪花就已经密起来。我匆忙赶回家中,不是躲雪,而是生怕错过了乱雪扑向高窗那一幕。窗外的雪还真是一派乱相了,那光景,可能十年二十年不遇吧。大雪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照这个样子下下去,不上一个小时,在街边堆雪人都不成问题了。
我泡了一杯茶,转眼工夫,雪却稀了。
我顾不上喝茶,守在窗前抓紧去看,雪却停了。
茶,也渐渐凉了。
我在窗边往下看了许久,好像雪会从地上树上屋顶上生出来。
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出去喝茶。他大概出门寻雪失望,转而向茶。他挑的那家茶舍离我家很近,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得见。
我下了高楼,向茶舍走去。我这才看见,街边其实是残留着雪的,星星点点。高空中铺张的雪,落地之后竟是这等可怜模样,还不如赶紧融化了干净。
朋友已经先到一阵。他穿得单薄,却搭一把竹椅坐在茶舍外面。茶几上那一杯茶,已经不冒热气。
茶舍背靠锦江,门脸朝向一个小水池。池边有几棵雪松,还有一棵银杏。树下过来的风还有雪意,有点割人。
我问他为什么坐在露天,他说他在等待。他还约了别的朋友。他们离这儿远,都还在路上。
我说,你是不死心,在等雪吧?
他说,我在等太阳。
他为我唤出一把竹椅,一杯茶。我成天坐得太多,不会放过站立或是走动的机会。我围着水池一圈一圈地走。我望了望天空,结果望到了自家的窗。
刚刚下了雪,太阳哪会说出来就出来。
朋友叫我坐下来。他说,你这样晃来晃去,池里的鱼就不会跳出来。他说,我并不想看你,我想看鱼。他说,鱼并不想看你,鱼想看我。他说,鱼是我的知己。
他就是这样,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喜欢来一点突兀。鱼怎么成了他的知己?因为我来之前,一条鱼从水中不时蹿出,看看太阳是不是出来了。就是说,他可不管那鱼愿意不愿意,认定人家和他一个脑筋,都盼着太阳尽快出来。
我依然围着小水池转圈,并且跟他较起真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换言之,你怎么知道鱼在盼太阳?你怎么知道,鱼跳起来,不是看看雪还在下否?
子非鱼,焉知鱼非我知己?
很快地,我们大概都意识到了,这样学着古人的腔调讲着老旧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乐趣。
但他是不肯轻易服输的。他说,鱼在空中用
力地折叠和旋转尾巴,以调整头的方向,而鱼头正是朝向太阳的位置。
厚厚的阴云罩在头顶,天知道太阳在什么位置。
他从竹椅上站起来,比划着鱼的飞翔。他那身段,怎么比得了鱼。鱼在水池中终于忍不住,自己跳将起来。他不好意思继续替鱼表演,当然也不好意思亲自到水池中去跳一回。
我却也看得仔细,鱼头是朝着西边的。这会儿是星期天的午后,难道已是夕阳西下时分?
他却说,他的知己不是这一条,是另一条。他说,这一条没有那一条跳得好。
一场好雪已经失去,那好,就认定那一条是好鱼吧。
我的那杯茶还没喝又冷了。我说,我今天就想喝一杯好茶。
他又在竹椅上坐下来,终于说到了雪,却又只开一个头就转到太阳身上。他认定从雪花到太阳不会是一个长长的过渡。他说,太阳是个明白的太阳,很快就会笑眯眯地露出脸来。
他大概舍不得为自己添一件厚衣。那个明白的太阳,你干脆出来好了。
一场大雪似乎就要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不料,还有一场小雪下给了我们。
一群画眉飞了过来,歇在附近的灌木丛中。
朋友说,画眉和鱼一样,也在我来之前就出过场了。它们当时就是从灌木丛中飞出来的,扑哧扑哧,上了一棵雪松,打翻了几片雪花。
这会儿,几十只画眉又开始新一轮表演了。它们嘈嘈杂杂地商量一阵,不等意见统一便胡乱飞出,扑上了那几棵雪松。雪松上原来积了那么多雪,倏然间被翅膀撩翻,被脚爪蹬翻,被碎语吵翻,纷纷扬扬从空中飘落下来。
接下来,画眉又分出一个小分队,扑上了那棵银杏。
我这才注意到,银杏树上还残留着一些叶片。那叶片也被画眉弄翻,在空中飞舞。天光依然晦暗,我看不清叶片的颜色,只觉得眼前砸下了大朵大朵的雪花。
这一幕先前为朋友预演过,在他眼里已是平淡,在我眼里却是稀奇。我在高楼上时,并没有看到哪一丛树顶有雪。这一下我知道了,就是一片银杏叶,大概也留住了不止一片雪花。
两条鱼一齐从水中跳起来。这一回,总该是出来看雪了。
画眉玩出了又一场雪,很小,却差点打翻我心中的某一场大雪。
我顾不上多想,还得抓紧看着眼前这一幕。我知道,残雪逗来的画眉,画眉播下的新雪,也会转瞬即逝。
画眉飞走以后,又有一个朋友赶到了。他对我们在这雪天观鱼赏鸟什么的不感兴趣,只顾着打电话催促另外一个朋友。
另外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说,他那边的街上积雪了,他得先陪孩子玩一阵雪,然后再赶过来。风似乎没那么割人了。我在竹椅上坐下来,招呼掺茶的美女,请把我的冷茶换成热茶。
农家鱼网
这是一道斜坡,有一条水泥公路滑下来。我们从一只铁壳船上下来,上了一辆在坡底等候的车。车弯来拐去向上爬,到了一户农家。
大水库已经被抛到脑后,看不见了。
我们一行几人从城里出来赏春,当地朋友把午饭张罗在这儿。这是一栋三层砖楼,面向公路。公路外侧有几株果树,大都开了花。
午饭还要等一会儿,一部分人上了楼,一部分人坐在院坝里晒太阳。我想随意走走,几只鸡为我让路,大都到了公路上。一辆摩托突然窜出来,把一只鸡惊到了一株花树下。
男主人抱着什么东西从屋里出来。我指一指那株花树,问他,那开的是什么花?
那不是花。
那有点像玉兰花。
那是枇杷。那汉子说,那是新发的叶子。
我出了洋相,赶紧埋怨视力。老实说,枇杷树长什么样子,我并没有确切的记忆。那新发的叶子朝上支着,看上去真有点像玉兰花,只是颜色不够鲜艳。前几年,在一条山谷深处,我看见一树玉兰花俏立在岩崖上,在那儿逗留了将近一个小时。那山谷中的美人,在这个春天里,不知是不是还那样风姿绝尘。
枇杷树旁边是一株梨树,这不会错,正开着花。
这次赏春活动分两天进行,第一天看水库,第二天看梨花。我们已经知道,成片的梨花离水库还远。我的老家盛产雪梨,这时节梨花正开得像大雪一样。梨花也是美人,但我从小就见惯了她,还因为饥饿和她闹过别扭,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有多么养眼。我倒是时常向人炫耀,自己从小就会嫁接果树。我嫁接的梨树,如果有幸存活下来,那么,这会儿,或者在梨园里热闹着,或者像眼前这一株,孤单而寂寞着。
汉子抱出来的是一团鱼网。他把鱼网丢在院坝里,在一只小凳上坐下来。
我问他,要去打鱼吗?
他说,刚刚打过。
我想,这是要晒网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这一行人,也算是出来晒网的。
汉子却没有把鱼网铺展开来,而是分出一绺一绺,折叠起来。晒太阳的朋友们已经在谈论国际问题了,其中一位扭过脖子,碰了一下鱼网的话题。他向我推荐一首题为《生活》的诗,正文只有一个字,网。我把这首诗一字不漏地背诵一遍,他立即坐正,回到国际上去了。
我不知道,那首诗所说的生活,是撒开的网,还是收拢的网。
地上这一团收拢的网,可以看作一份撒开的生活。这里的水库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在蓄水以前,这一带的农家大概是没有这一份水上生活的。
汉子一直埋着头,手上的动作不紧不慢。他整理过的小半团鱼网,看不出生了什么变化。他好像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我又问,这网要是弄乱了,还理得清吗?
他看我一眼。他大概有点纳闷,好好的网,为什么要把它弄乱。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提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我能够,你不能够。
我就是没有把叶子误认成花,没有胡诌什么诗,他大概也会这样说。
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这没什么。枇杷树的辨识度那么高,我都没有认出来。
我想换个话题,问问他会不会嫁接果树。话没出口,我就咽了回去。他就是认为我连梨花也不认识,我也不会和他较真。这会儿,我可不愿意去碰“我是谁”这样的问题,那可比弄乱的网麻烦多了。
几个朋友改谈历史了,我没有加入进去。我也没有走开,一直站在那儿看着鱼网,看着它在一个人的手里摇头摆尾。生活大概就是这样,缠缠绕绕,折折叠叠。我想了想一片水或是一缕浪,想了想昨天的浅或是明天的深。我好像什么也没有想,只不过就着一点简单,或是一点陌生,发了一阵儿呆。我有了这一份闲工夫,也就有了这一份耐心。这就像在山谷深处看玉兰花,我仿佛又听见了时光慢下来的声音。
我知道,并不是每一处开花,都能够让脚步停下来。
我也知道,并不是每一次撒网,都能够捕捞到一点什么。
太阳懒洋洋的。没错,我不是来打鱼的。这一团鱼网,不过是要缠绕一下我匆忙的脚步,并为我折叠一份消停。它就是撒开去,我也只要它捕捞上来的一点浅水,稀释一下过于黏稠的生活。
我仔细看了看那株枇杷树,今后,我大概不会再把它认错了。树下的鸡已经变成两只,我却又说不准最先到达的是公鸡还是母鸡。两只鸡的调情可能已经收场,也可能什么也没有发生。另外的鸡凑了过去,我就认不出原先那两只鸡了。鸡的辨识度不高,看上去都差不多。
这砖楼,这水泥路,这果树,看上去也和我的老家差不多。
这一下,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熟悉起来,亲切起来。
那些鸡又走过来,陆陆续续回到了院坝里。它们当然不会去啄那一团鱼网。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它们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