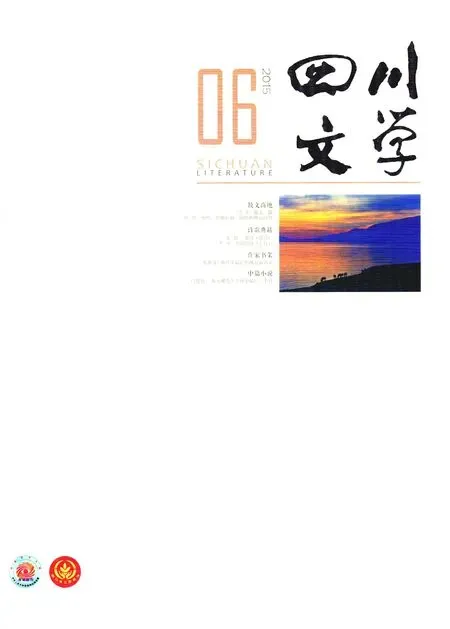玉兰花开
罗贤慧
玉兰花开
罗贤慧
罗贤慧,女,四川遂宁人。2012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散文选刊》《时代文学》《四川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20余万字,有作品入选《2014中国年度微型小说》《梦想起飞——2014四川群众文学创作笔会作品选》。
三月的阳光旋转着,大片大片地从天空飞落,纷纷扬扬宛如下着一场大雪。园子里的玉兰花开了。白色的花朵像阳光一样亮得直逼人眼,又像一只只凌空振翅的白鸟。风从耳边淌过,是谁在发出悠长飘渺的叹息?时隔多年,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玉兰花,可是那个玉兰花一样的女人,我却再也没有见到了。
玉兰是石匠从山里“带回来”的女人,刚到我们村里的时候,不过十八九岁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可论行辈我却该叫她“婶儿”。
在老家那个小村子里,像玉兰一样从山里“带回来”的女人并不罕见。村里的男人,因为样貌、能力、年龄或者家境等等各种原因,实在娶不到本地姑娘,就会揣上或多或少的一摞钱,跟着经常进山的“媒婆”走一趟,回来时就会“带”上一个女人。她们大多来自云南、贵州一带的深山,黝黑粗糙的脸上有大块大块的土板,不到二十岁的姑娘,看起来和身边四十来岁的男人面容上竟相差无几。她们是深山里的鸟儿,怀着天高地阔的梦想飞离故土,不曾想自己只是从“深山”飞到“浅山”而已。而在这地处“浅山”的小村子里,她们自小熟悉的乡音竟真的变成了无人能懂的“鸟语”,也成了她们永远扯不下洗不掉的标签。所以,如非必要,她们几乎从不和人说话,目光里也总是透着一种小心和惊惶——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鸟。
那年春天,年近四十的石匠眼见在附近娶亲已经无望,便整理行装,带了厚厚一摞钱找到进山的媒婆。一个月后,村里人就在一个深夜听见他家传出女人声嘶力竭的哭闹和哀求。对于这种声音,村里人早已听惯不惊了——几乎每个“带回来”的女人开始都是要哭一阵子的。不过,顶多几天过后,她们见哭闹也无济于事,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实,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习惯了整天低头敛眉闷声闷气地跟在男人背后下地干活;要是一年后再生了娃,那更是拿鞭子赶也赶不走的了。
不过,石匠带回来这个女人却哭了整整一个月!那一个月里,他家的院门不分昼夜都用一把拳头大的铁锁紧锁着,窗户也用筷子粗的铁丝扭了个遍。村里人每晚都能听见女人的哭闹,有时候是撕心裂肺的哭喊,有时候是凄凄哀哀的乞求,有时候是气断声阻的抽噎,中间夹杂着捶打门窗的声音,撕扯挣扎的声音,还有石匠好言安抚或者恶声训斥的声音。村口的麻脸幺婶说:“看他石匠出了名的暴脾气,这回可真遇到个烈货呢!”
不过,再烈的火也有燃尽的时候。一个多月后,村里的夜晚终于恢复了宁静。
这天,正是三月里的春闲时节——田里的种谷已经撒下去了,地里油菜却还是一片烟灰色,种和收的中间就有几天难得的闲日。从地里打望回来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麻脸幺婶家门口的老槐树下,摆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龙门阵。菜花早就谢了,槐花还有些日子才开,几朵云花在蓝汪汪的天上闲闲地泡着,明媚的阳光下,路边一块块小石子都开出了金色的花。
李二娃远远地看见石匠走过来,身边还跟着一个女人。他一口吐掉嘴里叼着的半截狗尾草,一边挥手打断正说得唾沫星子四下飞溅的喜旺,一边指向石匠来的方向:“诶!看!看!”人们都打过头去:“哟!可算出来了哈!”麻脸幺婶也停下手里正在纳的鞋底,往那边望去。
走近了,人们才看清那女人的样子。说实话,这女人真不像是从山里带出来的,倒像是石匠从哪个大户人家院里抢出来的小姐。一双桃花眼里汪着点点似有若无的泪花,波光盈盈的样子就像村口那片槐花塘——村里人都说那槐花塘里有摄魂的水妖,人往那水里一看,就会脑子发蒙心发虚,恨不能一个猛子扎进去不出来。女人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的罩衫,袖子下面露出一小截手腕。那手腕的皮肤是一种冰雕玉琢的通透的白,仿佛太阳一晒就要化掉,又像是刚从水里捞出的春笋,还带着一种隐隐的清香。
这么多人看着她,可那女人并不惊惶。她不说话,只把头转向一边,目光望向那些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山头。山头上是成片成片刚结荚的油菜,灰扑扑的,把她的眼神也映得一片阴郁。
石匠一边给男人们散烟,一边跟女人们打招呼,一张嘴笑得快要裂到后脑勺了。“狗日的石匠,艳福不浅啊!耗到四十岁上,居然抱了这么漂亮个婆娘!”李二娃晃着手里剩下的半截狗尾草,打趣道。石匠嘿嘿笑着给他点烟,嘴里不说什么,脸上却是掩不住的得意。招呼完了,石匠带着女人走向下面院子——自始至终,那女人竟没说过一句话,一张脸平静得像口老井,不带一丝波纹。
望着女人远去的背影,人群里有短短的一阵寂然。喜旺的喉结动了动,心里有点恨恨地:“妈的!山里居然还有这样水灵的妹仔!当年那张媒婆简直白收了老子的钱!”也有人惋惜:“可惜了,这么好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还是一堆老得快干了的牛粪!”麻脸幺婶儿噗呲一声笑出声来:“你怎么知道那牛粪快干了?没看人家开石头的时候那一身腱子肉——要我说,这牛粪还新鲜着呢!”李二娃立起身来,拿狗尾草毛茸茸的尖去挠幺婶的后颈窝:“怎么?心痒了?这牛粪管他新不新鲜都轮不到你了哈!有那么鲜亮一朵花儿等着他滋养呢!”人群里轰然一笑。麻脸幺婶挥手挡开那根狗尾草:“去!我看也没啥特别!鼻梁周围还有几个麻子呢,老话说‘十个麻子九个俏’ ,可见是不错的!”说完扬了扬脸。“算了吧,幺嫂!那老话是没错,可石匠女人脸上那是
麻子么?那叫雀斑。哪像你脸上那一摊‘麻雀屎’啊!”人群中哄笑更响了。幺婶儿一张麻脸登时涨红起来,扬起手里的鞋底就要去打带头起哄的李二娃:“砍脑壳的!瞧好吧!那女人能和石匠扛上一个月呢!好戏可还在后头!”不过她到底没打到李二娃,只好拍拍屁股上的土灰,悻悻地回屋去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女人叫玉兰——听说那是一种很好看的花,不过村里人从来没见过。然而村里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没见过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无论农闲农忙,玉兰每天都要仔仔细细地洗脸,完了居然还要用雪花霜在脸上手上又抹又擦——怪不得她一身皮肤竟像是用雪花捏成的,又白又透。又如全村女人都穿清一色的老蓝布,那衣服肥大的腰身即便要掩饰怀了九个月的肚子也不算难事;可她偏从集上买回各色花布来,自己缝成漂亮的裙子,裙子裁剪得很合体,刚刚凸显出她丰盈饱满的双乳、纤细结实的腰肢和浑圆挺翘的屁股。她穿着那些花裙子出门,也不故意搔首弄姿,那些娇艳的花儿们就在她巍巍颤动的乳峰上开得绚烂,裙摆上的蝴蝶也随着她腰肢有韵律地扭动一只只飞舞起来。还有,村里那些“带回来”的女人,哪个不是常年把头低着,一副卑微惶恐的样子?可她遇见人时竟然连眼睛也不垂一下,目光散散地从来人身上扫过去,仿佛她眼前的不过是一株狗尾巴草。最离奇的是,她虽然不太开口说话,可居然会唱歌!常常在她一个人割草打柴的时候,那清凌凌的山歌就悠悠地飞出来。虽然唱的还是她家乡的“鸟语”,可百灵鸟在林子里唱的不也是鸟语么?你听不懂,但你还是喜欢。
每次玉兰从路边走过,身后那些男人们的眼里都会放出灼灼的光。那些光像火星子一样,从他们的眼里哔哔啵啵一路燃下去,最后烧成熊熊的火,烈烈地烧到小腹,把这些男人生生烧成了一座座活火山。滚烫的岩浆在他们身体里奔涌勃发,白天里还能拼命压着,到了晚上就狼奔豕突地想要喷薄而出。
男人们的异样,总是女人最先感觉出来。那些矫情的,到了晚上,就裹床被子缩到床角,扔一个冷冰冰的后背给男人。男人着急,一把扯开被子:“疯婆娘,又抽哪门子风啊!”“滚远点!不要脸的!你以为我不晓得你每天晚上睡在老娘身上心里想的是哪个骚货?”“我说你这瓜婆娘,皮痒了是不是?”“咋的?想动手?赶明儿老娘收拾东西回娘家去,叫你三个月闻不见X味儿,看馋不死你!”男人心里的火腾地上来:“疯婆娘,我叫你狠!”翻身把女人压在身下,三把两把扯掉底衫裤头就在女人身上横冲直撞。女人一边挣扎一边叫骂,然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吟。那一漾一漾的呻吟让男人们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整个身子都泡在了日思夜想的那一汪槐花塘里,于是冲撞得更有力了,恨不能把埋在骨头里的力气都统统掏出来。整个村子都不平静起来,院里院外的狗也都赶着凑热闹似的,吠到半夜,连空气都弥漫着一种勃发的味道。
石匠把这好不容易带回来的漂亮媳妇捧成了宝贝疙瘩,三天两头给她扯好看的花布,买好吃的零嘴儿——那些钱,都是他实实在在用钢钎錾子一点一点敲出来的,从前哪里舍得乱花半分?
然而,好景不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村里开始有了一些流言。故事的版本各不相同,内容却大同小异——不外是玉兰什么时候在哪里又和
谁谁谁勾搭上了,如此种种。谁也不知道这些故事最先从哪里传出来的,就像谁也不知道这些故事有没有人亲见。然而人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并且故作神秘又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别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中又不约而同地加入一些“理所当然”的细节,让那些故事越来越荒诞却又越来越生动……以至于后来一提到玉兰,男人们的神情里立即显出一种难掩的兴奋和隐秘的满足,而女人的语气里则明显透出一种鄙夷和唾弃。
不过这些故事谁都不敢说给石匠听——那可是村里出了名的火药桶,一点就着。
直到有一天,麻脸幺婶请石匠去她家錾石磨。中午,幺婶炒了几个小菜给石匠下酒,她自己也陪着喝了两杯。或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幺婶竟然无意中说漏了嘴。经不起石匠一再逼问,幺婶选择性地说了几个刺激性不太强的故事,并且一再强调她“也只是听说,不知道真不真”。话虽如此,幺婶眼里流露出的坦诚和真真切切的同情,又分明告诉了石匠这一切到底“真不真”。
火药桶终于给引爆了,因为加了酒精,炸起来更是吓人。石匠黑着一张脸,冲回家里拖出女人就是一顿暴打——除了拳头,这个四十岁的汉子实在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来捍卫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平静了好久的小村子又不平静了。石匠家三天两头就会传出男人的斥问、暴打声和女人的哀告、呻吟。男人一遍遍要女人交代她的野男人,女人无可交代,男人就更暴烈地拳打脚踢,一直到深夜。
刚开始石匠只是为了让玉兰招认那些故事而动手。后来,挨了打的玉兰瞅着机会就往外逃,这让石匠更加暴跳如雷!村里那么多带回来的女人,哪个不是安安心心守着男人过日子?偏偏玉兰整天想着逃跑,还不是有了野男人?从此,除了在村子里打草捡柴,石匠绝不让玉兰一个人出门,并且从不给她手里留一分钱。一个女人,人生地不熟,身上又没有半文钱,即便是瞅空逃了,单靠一双腿,又能走多远?所以每次玉兰刚逃出门就被抓了回来,抓回来就是一顿暴打;挨了打就更想逃,逃不掉抓回来又是更狠的打。那些日子,玉兰竟没有一天身上不带着伤。
这时候村里人倒安静了——女人们虽然不待见玉兰,可谁也不敢往石匠暴怒的胸腔里再添加一星点儿火药;至于男人们,虽然平日里看着玉兰都眼馋,可谁也不敢出来惹那一身骚。
转眼就是秋天,村里教小学的老先生年纪太大,教不动了,乡里派来一个代课老师。新老师二十出头的年纪,说是邻村支部书记的儿子,还是附近几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
新老师跟老先生教书很是不一样,除了让娃们每天关在教室里念书,还会带他们出来打篮球,教他们唱歌。他有一根很漂亮的笛子,娃儿们唱歌的时候,他就把笛子横在嘴边吹出清越的曲儿。
玉兰是在一次打草路过学校的时候见到新老师的。初秋的天空又高又远,蓝得发脆。白杨树的叶子在太阳下闪着金光。教室里几十个娃儿正在扯着嗓子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张张小脸憋得通红。新老师侧着身子站在讲台上,那只竹笛就横在他的嘴边,一件雪白的衬衫把他的身材衬得挺拔而秀颀,就像窗外那一排白杨。
玉兰不觉听出了神,直到一曲唱完,教室里的人发现了窗外的“偷窥者”,她才低着头匆匆跑开。下课后,新老师悄悄拉过一个小娃,问先前窗外那女人是谁。“她是玉兰婶儿——娘不让
我叫她婶儿,说她是个骚货!”小娃转身跑出去玩了。年轻的老师望向窗外,一条小路平平仄仄地伸向远方。远方,是一大片红艳艳的山花骤然怒放。
后来,新老师总能在课间听到悠悠的山歌。玉兰在坡上沟下打草捡柴时,喜欢随口哼唱那些家乡带来的歌,就像她从山溪边走过时总喜欢随手伸进溪里甩起一串清亮亮的水花。
校园外那一排白杨树开始落叶的时候,新老师的竹笛更换了曲调。有人听出,那竟像是玉兰哼的山歌的调子。
这世间,秋天过了冬天必然会来。有些事合该要出,任谁也躲不过。
那年冬天,村里放坝坝电影,就在小学的操场上。那时候的电影可是个稀罕物儿,全村人都跟过节一样,早早吃过晚饭,搬根条凳跑去占位子。等夜幕一落,全村男女老少无一例外地聚到了那张白色的银幕下面。
电影放到一半,麻脸幺婶儿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站在人群边上高喊了一声:“石匠,你龟儿子还有闲心看电影,你老婆在草堆里偷人呢!”这话一出,就像滚油里落进了几颗水珠,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石匠这才发现,本来坐在自己身边的玉兰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不见了。
电影肯定是没人看了,大家都等着看一场“捉奸”的好戏。
一群人兴兴头头拿着火把赶往那个草堆。麻脸幺婶走在最前面,手里的火把高高举过头顶,像举着一面猎猎的旗。火光欢快地跳跃,映照着幺婶一张满是兴奋的麻脸。
人们赶到草垛的时候,玉兰和新老师正一边一个坐在草垛的两边。老师手里拿着那只竹笛,玉兰仰头靠在草垛上,一双眼睛笑得亮晶晶的,像夜空里的星子。
看到这么多人忽然围上来,两人一时没反应过来。石匠扔掉手里的火把,冲上去就要跟新老师拼命。玉兰猛然醒过来,一把拖住石匠的脚,对新老师喊:“你快跑!”——这句“鸟语”倒是人人都听懂了。新老师开始还想辩解什么,一看石匠怒不可遏的样子,先自乱了阵脚,竟然像是傻了。玉兰又连喊两声,他才回过神来,拔腿便跑。
石匠见玉兰这样护着“小白脸”,更觉得平日里听到那些闲话都坐了实,一腔怒火比幺婶手里的桐油火把烧得还旺。他一手扯起女人的头发,啪啪啪接连十几个耳光下去,然后飞起一脚就把女人踢倒在地,好一阵拳脚相加。玉兰起先咬紧了牙关不出声,后来实在挨不过,才嘤嘤哀告和呻吟。
一群跟来的人没有看到想象中男女野合滚草垛的精彩画面,开始还有点失望,但是石匠一动手,明显又让这出戏有了新的看头,所以一时间竟然没有人出来阻止。
半晌过后,玉兰的呻吟越来越低,再打下去怕是真要出人命了,这才有人大着胆子来劝阻。石匠看瘫在地上的女人,实在已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份,狠狠地停了手,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回了家。
出了这样的事,新老师在村里的课是教不下去了。不久就听说他父亲给他订了一门亲,当月里他就做了新郎官——这样匆忙的婚事,在我们老家可是从没听过的。
石匠以为揪出了“野男人”,又狠狠收拾了一顿,这回玉兰总该收了心,也就稍稍放松了对她的看管。
这天,邻村有人要建新房,请石匠去帮忙打基脚石。石匠想着玉兰有伤在身,跑也跑不远,就没有给大门上锁。等他在主人家吃过晚饭回来,家里大门洞开,躺在床上的玉兰竟然不见了!
石匠挨家挨户去敲门,问有没有人见到他女人。不到半个时辰,全村老少都出来了,拿着火把去帮石匠找人。可是玉兰这一次竟像是变成鸟儿飞走了,连半片羽毛都没留下。天快亮的时候,还是麻脸幺婶眼尖,发现槐花塘的缺口边躺着一只鞋。捡起来一看,鞋面上两朵白色的花开得正好,像是一对振翅欲飞的白鸟——那正是玉兰最爱穿的鞋,听说鞋面上绣的白花就叫“玉兰”。
石匠急慌了心,衣服都没脱就跳下塘去,可是在水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一星半点玉兰的东西。
在石匠的哀告下,村里稍有点水性的男人都下了水,摸的摸,捞的捞,槐花塘里竟是几十年从未有过的热闹。可是几天下来,一群人连玉兰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找到。石匠还想求男人们再找找,女人们却不干了:“早就说那槐花塘里有水妖,那女人多半是被水妖抓了去,说不定她自己就是水妖转世,不然哪有那么骚?再找下去,可别连自家男人都回不来了!”石匠没办法,想挖开缺口,把塘水放干。这回是村里几个老人一起出来阻拦,说那槐花塘管着这沟上沟下的风水,绝不能因为一个“带回来”的女人就让全村人遭了灾。石匠捏起拳头正要发狠,李二娃连忙拦着:“只凭一只鞋子也不能断定人就掉进塘里去了,说不定她是跑了呢——你在这里跟几个老头子较劲,可不是让那女人有时间跑得更远?”
石匠一听也有道理,这才没再打槐花塘的主意。
可是,后来的半年里石匠先是在附近十里八乡翻了个遍,又追到县城,还去玉兰山里的娘家找了一趟,玉兰竟杳如黄鹤,音讯全无。
村里没有了玉兰这个女人。
……
多年以后,玉兰在村里渐渐模糊成一个名字,只在老年人告诫小孩子不许靠近槐花塘的时候,才会淡淡被提起。而我也离开了家乡,在一个小县城里安了家。
在我住的小区里有一个花园。每年春天,园子里都会开一种清雅的白花。那些花仿佛在一夜之间开出来,白色的花朵在阳光下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鸟。它的花期很短,前后不过十来天。花期一过,它便整朵整朵地从枝头落下——即便是凋零,也是一种姿态决绝的美。
听说,那种花就是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