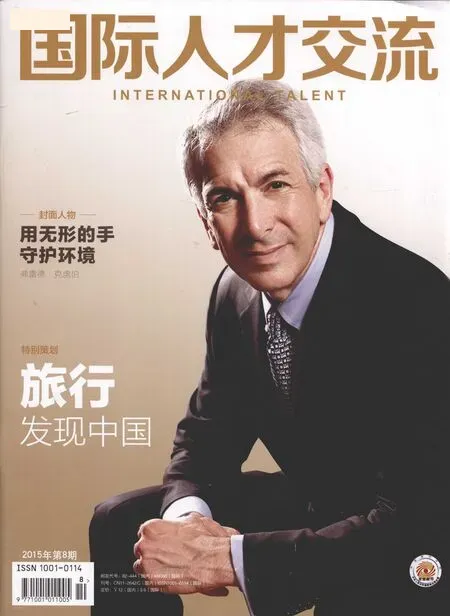“话别”象牙塔
—— 2015毕业季中外名校演讲汇
左娜 整理
“话别”象牙塔
—— 2015毕业季中外名校演讲汇
左娜 整理

这是一个自拍——还有自拍杆的时代
德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
这是一个自拍——还有自拍杆的时代。不要误解我:自拍真是件令人欲罢不能的事儿,我还特意鼓励毕业生们多发一些自拍照,让我们知道他们毕业后过得怎么样。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开始过上整天自拍的生活,这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呢?对于我来说,那也许是“利己主义”最真实的写照了。
在词典里,“利己主义”的同义词包括了“以自我为中心”、“自恋”和“自私”。我们无休止地关注自己,我们得到的“赞”,就像我们不停地用一串串的成就来美化我们的简历,去申请大学、申请研究生院、申请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自我放大”。
如同社会评论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都在不停地为打造自己的品牌而努力。我们花很多时间盯着屏幕看,却忽视了身边的人。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经历不是被我们体验到的,而是被保存、分享并流传于Snapchat 和Instagram 这些社交程序,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由我们所有人合成的自拍照。
适度的利己是我们的本性。正如我校的生物学家威尔逊教授最近写道的:“人类是一个充满无尽好奇心的物种——只要对象是我们自己和与我们相关的。”我想强调的是,这种自我迷恋会带来两个令人不安的后果。
首先它削弱了我们对于他人的责任感——一种服务他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正是哈佛大学的使命:让毕业生们不断成长,超越自我。这种成长并非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了他人和整个世界。我们的学生和教授已经通过服务周围的社区以及整个世界,身体力行地践行这种使命。从为小镇的中小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到去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病毒,哈佛人改变着无数人的生活。
除了削弱我们的服务意识以外,“利己主义”还有一种后果值得注意。过度的自我关注掩盖的不仅是我们对于他人的责任,还有我们对于他人的依赖。我们遗忘了高校和机构存在的目的和必要性,使我们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大学? 人们问道:我们就不能全靠自学吗?硅谷创业家们敦促学生们辍学,甚至还给予他们经济补助,让他们辍学创业——这其中也包括哈佛的一些本科生。从逻辑上来讲,马克·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都辍学了,他们似乎都很成功。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请大家别忘了:他们都是从哈佛辍学的!哈佛是孕育他们改变世界想法的地方。哈佛以及其他像哈佛一样的学府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商业分析师、律师和其他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正是Facebook、微软这样的公司中的中流砥柱。哈佛也培养了无数领导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人民公仆,他们的工作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使得Facebook 、微软这样的公司可以繁荣发展。我们还培养了无数的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新闻工作者,是他们的作品给互联网增添了“内容”。我们还要看到,大学是人类和社会技术革新的源泉,这些革新是互联网公司发展的基石。
主张大学已经没有存在意义的断言来源于人们对于机构的不信任,其根源在于我们对个人权利和感召力的陶醉以及对名人的崇拜。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都和大学一样,成为了质疑和批评的靶子。很少有反对的声音来提醒我们这些机构是如何服务和支持我们的,我们常常认为它们的存在理所应当:食物是安全的;血液检查结果是准确的;投票站是开放的;拨动开关一定会有电;航班的起落有条不紊……设想一下,假如所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停摆一周或一个月,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机构体现了我们与其他个体之间持久的联系,它们将我们不同的天赋和能力拧成一股绳,去追求共同的目标。同时,机构也将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维系起来。它们是价值的金矿——这些恒久的价值超越了每一个自我。机构促使我们放弃眼前的快感,思考更长远的图景。它们提醒我们,世界只是暂时属于我们,我们肩负着过去和未来的责任,真正的我们要比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自拍照广博得多。(摘编自2015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校长主题演讲)

杨念群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用“无用之用”对待残酷人生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
1981年,我刚上大学,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走出教条主义的阴影。一天,我在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一本叫《外国文艺》的刊物,里面有一篇萨特的演讲《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其中有一句话是:“存在先于本质”,看到这句话,我好像遭了电击一般。我们过去的生活都是被规定好了的,所有被看作“本质”的那些不容置疑的东西,到头来很多都是谎言,但当时我们却盲目地接受了。把自我存在和自我意识当作思考的起点,独立地思考并作出自我选择,而不是靠所谓“本质”规定我们的生活,这才是改变人生的起点。
所以,自我选择是第一重要的。但我们不是活在真空中,我们必须面对不同的人,学会如何与他们相处。享受过毕业的狂欢,脱下这身礼服,你们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对未来充满玫瑰色幻想,结果发现自己是操着卖白粉的心,挣着卖白菜的钱。最难熬的是,当你看见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CEO,你却还在老板的呵斥下每天累得生不如死。有个测验说,混得好的人爱养猫,因为能当猫奴就说明在单位没受太多老板的气;相反,混得不好的人爱养狗,因为在单位老受气,回家得养个摇头摆尾的宠物释放压抑。
如果你变成了养狗族怎么办?一种选择是去听励志故事,从奥巴马、乔布斯到马云。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小人物逆袭成英雄的故事。这些励志故事有欺骗性,让大家以为人人可以成为英雄。他们靓丽光鲜地站在那里,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英雄,而这些经验对大多普通人来说未必适用。普通人和英雄的区别在于,英雄奋斗享受荣耀赢得欢呼,普通人奋斗纯属默默耕耘,无人知晓。这个时代的英雄故事永远是由财富和名望堆积起来的,却没有人意识到“一将功成万骨枯”,一般人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资格。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该怎么办呢?
讲个故事,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和一个中国博士生住在一起,他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可是他的书架上总摆着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是一本很难读懂的文学理论书,他每天看一页。我说你一个理工男,看这东西有啥用呀?他说每天看一页,就有兴趣,就是享受,没别的什么理由。由此我突然悟到了,兴趣和有用不一定关联,甚至兴趣和成功也不一定成正比,对一件东西有兴趣,不一定能保证你成功,不一定能使你成为马云或乔布斯,却能让你从每天职业化的奔波中解放出来,从你老板和上司的那张扑克脸的淫威下解脱出来。
我是教历史的,最怕学生上了半天课,最后傻傻地问一句:学历史有什么用?那时我甚至会勃然大怒。如果你老是用这种功利心而不是释然的心态去读史,那么你还不如直接去炒股票。用物质和实用的标准给成功披上华丽的外衣正是我们教育失败的最大症结之所在,也是我们的生活缺乏诗意的原因。感受这种“无用之用”,学会用“无用之用”的态度对待残酷的人生,会使你的生命中洋溢着一种充实感。它不一定有镁光灯闪耀下的那般奢华绚烂,却可能长久流淌在你的心灵之中伴随一生。(摘编自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毕业典礼主题演讲)

娜塔丽·波特曼10岁出道,13岁被全球观众熟知,18岁暂退娱乐圈并考入哈佛大学,是好莱坞公认的才女
接受瑕疵,它让你与众不同
娜塔丽·波特曼(Natalie Portman)(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生、奥斯卡影后)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情与1999年初到哈佛时如出一辙。那时我觉得肯定是哪里出了错,感觉我的智商不配来这儿。我每次开口说话时,都必须要证明我不只是个白痴女演员而已。不过今天我在这里是要告诉你们,不自信和无经验也许会导致你接受别人的期待、标准或价值,但那也可以造就自己的路,一条由你自己来定义的成功之路。
《星球大战1》刚上映时,我就来到哈佛读书,我知道我得重新建立别人对我的看法了。我害怕大家以为我只是靠名声才进了哈佛,担心他们觉得我配不上这里严格的智力标准。事实也差不多如此,我来哈佛之前从没写过10页的论文。而对于我的同学,那些毕业于道尔顿、艾克赛特等名校的学生却说,跟高中相比,哈佛的作业量是小菜一碟。而我完全应付不来。我觉得一周读完1000页书是不可想象的,写出50页的论文是我永远都做不到的。
我从11岁起就开始演戏,但我认为演戏是轻佻且无意义的。我出身书香门第,非常在意别人是否把我当回事。在不自信的驱使下,我决定要在哈佛找到严肃而有意义的事情。
为了找到一条更加严肃和深刻的路,大一那年我选修了神经生物学和高等现代希伯来文学,因为我很严肃、很智慧。当我为了希伯来语和神经应答的不同机制挣扎时,我看到朋友们为流行杂志写文章,看到教授讲童话故事和黑客帝国。我从同伴和导师们身上看到,热爱才是人们做一件事的真正原因,而为了严肃而严肃,这本身就是一种虚荣。
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我花了许多时间寻找我自己做事的原因。我的第一部电影在1994年上映,那时我才13岁,至今我仍能一字不差地复述《纽约时报》对我的评价:波特曼小姐摆造型的功力比演戏强很多。这部电影得到的所有评价都是不温不火,票房更是惨败,这部电影叫作《这个杀手不太冷》。而20年后的今天,在我拍了35部电影之后,它仍是人们见到我时最常提到的片子,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他们最爱的电影。我首次参演的电影起初在所有的衡量标准上来看都是一场灾难,但我也很幸运,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学到,我的价值应该来自于电影拍摄过程的体验,来自触碰人心的可能,而不是行业最首要的荣誉:商业和影评的成功。
于是我开始只挑那些我热爱的事情来做,只选那些我能汲取到经验的工作。我拍了外国独立电影《戈雅之灵》,为此我学习艺术史,连续4个月我每天研读戈雅和西班牙裁判所。我拍了动作片《V字仇杀队》,为此我学习了所有和自由战士相关的东西。
拍摄《黑天鹅》时,我感觉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不怕别人怎么用嘴喷怎么用笔骂,也不在意观众是否愿意到影院看我的片子。对我很有启示的是,当芭蕾舞者技巧达到一定高度后,唯一能让你与他人不同的,就是你的瑕疵。有位芭蕾舞者因转圈的轻微不平衡而出名。从技术上说,你永远不能做到最好,总有人比你跳得更高,或者有更美的姿态。你唯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发展自我。
大家告诉我,《黑天鹅》是艺术上的冒险,但我觉得促使我去演的并非是勇气,而是我对自身局限的无知。当导演问我是否能演芭蕾舞者时,我跟他说我基本就是个芭蕾舞者,当时我真心是这样认为的。很快,我明白我离专业芭蕾舞者还差15年的功夫。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我绝对不会冒这个险,而风险为我带来了最棒的艺术体验。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变得更加现实,这包括对我们自己能力和缺陷的认知,而这种现实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好好利用“无知”,趁如今你还不那么怀疑自己!
(摘编自2015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主题演讲)
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读过上百本经典

徐沪生(上海一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前《外滩画报》执行总编辑)
我是做媒体的,首先我要给大家一个忠告:离开了学校、老师之后,你们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媒体。但是,千万不要跟着媒体去读书,去思考。
用我们哲学系的标准来说,媒体推荐、谈论的书,很多都是价值很低的,甚至是垃圾。但是这不是媒体的错,因为媒体不是学术杂志,它追求新闻性,它不会讨论康德、黑格尔。哪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媒体的读书版,也一定主要是推荐新书。那么多经典你都没时间读,那些时髦的新书,大可以不读。新书的比例,不要超过阅读总数的20%,甚至10%。反正我是基本不读活人写的书的。
我们现在的媒体里面,几乎没有几个读书人了。受了他们的影响,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傻瓜,而且是一个自以为会独立思考的傻瓜。
黑格尔说过,所谓常识,往往不过是时代的偏见。要超越这个时代的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阅读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没读过几百本经典,不足以谈独立思考。你读得越多,越和周围的流行意见格格不入,在你所在的那个行业,也许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最能独立思考的人。
其次,作为一个在大学里认真读过书,工作之后好几年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好书,最近这十几年才恢复了精神生活的人,我的第二个忠告是,切勿轻浮。
30岁的时候,我创办了一份报纸,办得还算成功,我还在各种报刊上写专栏,那几年,我是一个成功的主编,一个小有名气的自由主义专栏作家、一个快乐的虚无主义分子,朋友很多,每天都很开心。
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糟糕、最虚度的时光。
我后来回顾往事,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也是念过哲学系的人,怎么会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面,彻彻底底地丧失了精神生活,并以此为荣?除了自身的原因,时代与环境的腐蚀,真的是很可怕的。
有一次,我偶然读起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本科的时候读过,开了个头,就读不下去了。这部几百万字的意识流小说连主人公起个床都可以写两三十页。但这一次,我一读就读了3个月。
前前后后,我读了3遍。如果说,我们这些媒体人、专栏作者的那点小聪明,是茶杯里的几片茶叶的话,普鲁斯特这种人的才华,就是漫山遍野的茶树林。我发现,普鲁斯特那些又丰富又深邃的独特的感受,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这些东西,也同样活跃在我身上。那时我真的觉得,这说明我还有救,我还没有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
从此以后,我像重新回到大学时代一样,不需要老师管,也没有考试,也不写论文,每天坚持读书8小时,这样坚持了十多年。
毕业后,你们在 30岁前后,智力、阅历会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但是大多数人,却再也不读书、不思考,再也没有精神生活。也许他可以赚很多钱,但是精神上,却一天比一天贫乏。
恢复了读书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大学里读的那些东西,全都是杰作,甚至是真理。苏格拉底的话是真理,孔子的话是真理,康德说的是真理,黑格尔说的也是真理……都是大师中的大师。
那些伟大的著作,你只要认认真真地读上一本,就会立即发现,那种轻浮的人生哲学,是多么愚蠢。我后来在一首诗里总结过我们这一代人,在那几年经历的变化:
我看到对平凡事物的赞美,
变成了对崇高之物的嘲笑,
最后变成对卑贱之物的偏好。
最轻浮的奥斯卡·王尔德后来也说:“恶,莫大于轻浮。”他在牛津的时候曾说:“我要尝遍世界这个园子里每棵树结的果实,我要心怀这份激情,走出校门,踏进世界。”后来,他在牢里反省:“我一点也不后悔曾经为享乐而活过,我过着蜜糖般的生活。但如果继续过着同样的生活就不对了,因为这会限制心性的发展。”
在我的一生中,我觉得最幸运的事,就是进了复旦哲学系。虽然我没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但我在这里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学习过什么是反思。只是这种自我反思的本能,后来被遗忘了。但在某个关键的迷惘时刻,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又被重新激发出来,给我启示。
祝愿大家毕业之后,能过上蜜糖般的生活,充分地享受人生,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抽身而出,反思它,审视它。
毕竟,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摘编自复旦大学哲学系2015年毕业典礼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