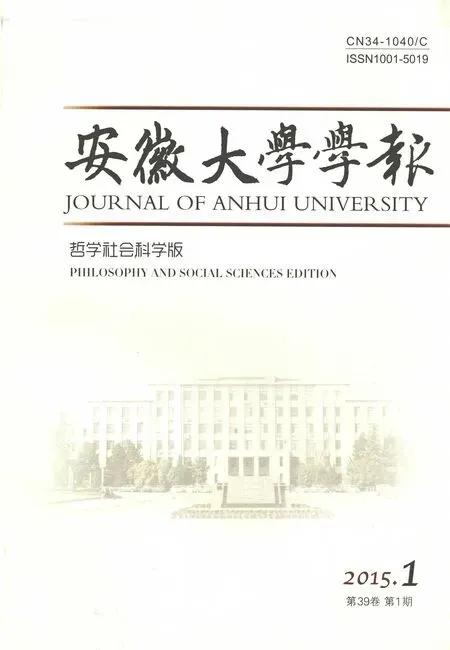论唐人对自己诗作的修改
方 胜
论唐人对自己诗作的修改
方胜
摘要:唐代诗人常常对自己诗作进行修改,通过他们的自述、流传于世的手稿以及后人的讨论分析,可以了解“自改”的大概情况;进而具体分析他们修改作品的原因,并讨论“自改”的特殊意义和影响。由于诗人的“自改”导致唐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异文,它们与后人删改唐诗而产生的异文不同,需要区别对待。
关键词:唐诗;“自改”;手书;异文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13论曰:
古人为诗不惮改削,故多可传。杜子美有“新诗改罢自长吟”,韦端己有“卧对南山改旧诗”之句是也。尝观唐人诸选,字有不同,句有增损,正由前后窜削不一故耳。*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这段话所讨论的正是唐代诗人对自己诗作修改的情况。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解释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时说:“改则弊病去,长吟则神味出。”*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48页。不断修改自己的诗作,以追求艺术上的臻美之境,几乎是唐代诗人普遍的做法。那么,唐代诗人是怎样修改自己诗作的呢?这些修改除了艺术审美的追求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后代读者和研究者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因诗人自己改作而产生的异文呢?我们注意到各种传世唐诗文本的差异,固然有很多是后代钞刻、选评、删改等因素造成的,但也有部分是因诗人自己的加工修改而导致的。已经有学者就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进行了深入分析*莫砺锋:《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我们不揆浅薄拟就唐人对自己诗作修改的情况略作讨论。
一、诗人自改作品的几种情况
在讨论诗人自改其作品之前,首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确认诗作是作者自改的呢?诗人修改自己作品,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们自己的相关叙述和留存下来的手书稿本,间接的证据是同时代人或后人的推测讨论。
(一)诗人自述
李白《大鹏赋(并序)》云: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李白在序中谈到了他创作、修改《大鹏赋》的经过。虽然李白的《大鹏遇希有鸟赋》没有流传下来,但诗人明确提到其“多将旧本不同”,是在自己早期作品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像李白这样,叙述自己修改作品的情况,在唐代并不少见。诗僧贯休,其《山居诗(并序)》曰:
愚咸通四五年中,于锺陵作山居诗二十四章,放笔,稿被人将去。厥后或有散书于屋壁,或吟咏于人口,一首两首,时时闻之,皆多字句舛错。洎乾符辛丑岁,避寇于山寺,偶全获其本,风调野俗,格力低浊,岂可闻于大雅君子。一日,抽毫改之,或留之、除之、修之、补之,却成二十四首,亦斐然也。*贯休著,胡大浚笺注:《贯休歌诗系年笺注》卷23,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73页。
这组诗的标题在《全唐诗》中作《山居诗二十四首》。贯休在序中详细说明了这组诗从初稿到改作的经过,其中第六首回忆了他出家为僧四十年的经历:“鸟外尘中四十秋,亦曾高挹汉诸侯。”这句诗无意之间透漏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它不太可能出自初稿,因为初稿写作于“咸通四五年”,当时诗人刚过30岁。由此可知,贯休对这组诗修改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有些可能是重新创作而成。
(二)手书流传
通过诗人流传的手书,来讨论他们自改诗作的情况,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据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8“诗词改字”所记,有人看到王安石《泊船瓜洲》的原稿,诗人曾用“到”“过”“入”“满”等十余字,最后才选定了“绿”字*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历代诗话笔记中也有很多关于唐人在手书中自改诗作的记述。如:
《漫叟诗话》记:“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李商老云:“尝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季炼之语?”*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9页。这是杜甫在手稿中自改诗作的例子。
张耒说:“世以为乐天诗为得于容易,而耒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魏庆之著,王仲闻校点:《诗人玉屑》卷8,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4页。周敦颐也曾说:“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袁枚:《随园诗话》卷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193页。不管白居易改诗直至老妪能解的故事是否真实,此处张、周所云是据白氏手稿而言,可信度颇高。
唐代诗人能书擅书者颇多,但留存至今的手书诗稿已经难得一见了,得幸金石书画文献和前人的论述中尚保留了不少资料。胡震亨《唐音癸签》卷33记:“唐人诗见于金石刻及自有真迹传世者,至宋尚多。如宣和内府所收藏载在书谱者,真迹班班可考。”*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43页。文中罗列了很多唐人手书的诗目,其中包括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许浑今体诗上下”。此即晚唐诗人许浑的《乌丝栏诗真迹》。许浑(788—860?)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三月自编诗集,名曰《乌丝栏诗》。这部诗集曾散佚,幸亏许浑的书法为人所尚,在宋代几位文人的努力下其诗集残卷才得以保存下来,南宋时岳珂得之,将其编入《宝真斋法书赞》卷6*参见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20页。。岳珂详细描述了许浑手稿中修改自己诗作的情况。略举数例:
《夜泊松江渡寄友人》:“清露白云明月天,与君齐棹木兰船。南湖风雨一相失,夜泊横塘心渺然。”岳珂在诗后描述:“内‘兰’字作‘栏’,涂去‘木’字添。”(按,指添上了草头)*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第628页。此诗又作杜牧诗《泊松江》,依真迹可知实属许浑作品。
《送萧处士归缑氏别业》:“醉斜乌帽发如丝,曾看仙人一局棋。宾馆有鱼为客久,乡书无雁到家迟。缑山住近吹笙庙,湘水行逢鼓瑟祠。今夜月明何处宿,九嶷云尽绿参差。” 岳珂记述:“内‘乡’字元作‘家’字,注改;‘山’字元作‘氏’字,注改;‘嶷’字元作‘疑’字,从山添笔。”*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第618页。按,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凡是《真迹》中留存的作品均以《真迹》为底本,但这首诗未按《真迹》校对,《真迹》与现存各本有多处异文。标题中“缑氏”是指缑氏山,在河南偃师。诗人改动的“乡”“山”两字在后代的各本中多遵从,但“嶷”字后人仍多用“疑”,是不恰当的。
手稿中有些文字经过多次修改才最终确定下来,如《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道中留题峡山寺四首》其四有“古木花生斛,阴池满种松”一联,岳珂记曰:“内‘花’字元作‘古’,改作‘高’,又注作‘花’。”*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第626页。这样的改动在《乌丝栏诗真迹》中还有不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行次潼关驿》: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
《唐诗三百首》收录此诗,题作《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岳珂记述:“内‘残云’‘疏雨’联,元作‘远帆春水阔,高寺夕阳条’,内‘阳’字,易字不成,上有补绢,已不存其笔画,犹隐然在纸上云。”*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第624页。从许浑手稿可知,原作中颔联是“远帆”“高寺”句,但他对其中的“阳”字不满,试图换字,但最终没有成功,于是诗人将这两句全部换掉了,改为现在常见的诗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4称赞此诗“尚有全盛风流”,卷5又说其“中四句居然盛唐”*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6、93页。。周永棠《唐贤小三昧集续集》在“残云”二句下评曰:“亦阔大,亦高华,晚唐中之近开、宝名句也。”*周永棠:《唐贤小三昧集续集》,清钞本。可见,这两句诗的改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整首诗增添了亮色,也获得了诗评家的普遍认同和高度赞誉。
(三)后人推测讨论
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两点直接证据以外,后人对唐人修改自己诗作的描述及推测讨论,有些颇有道理可以信从,有些别具新意亦可备一说。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讨论了多首唐诗“自改”的情况:“如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搜玉集》校金本,但‘少妇’作‘小妇’、‘音书’作‘军书’;《才调集》则‘卢家少妇’作‘织锦少妇’、‘白狼’作‘白驹’、‘谁谓’作‘谁知’、‘更教’作‘使妾’,不但工拙不侔,其乖调竟似梁陈。然《才调集》乃唐末人选,而犹未从改本者,盖彼但见初本,尚未见改本故也。”*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13,第150页。他推测沈佺期《古意》(一作《独不见》,又作《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诗中诸本并存的多处异文,是诗人自己修改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在李白、杜甫、王湾等诗中也曾出现。李白集中有两首《白头吟》,两诗语意基本相同,句式也很相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黄庭坚《题李太白〈白头吟〉后》认为:
予以为二篇皆太白作无疑。盖醉时落笔成篇,人辄持去,他日士大夫求其稿,不能尽忆前篇,则又随手书成后篇耳。杜子美“巢父掉头不肯住”,一篇内数句,参差不齐,亦此类。盖可俱列,不当去取也。*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1页。
黄庭坚认为是李白自改其诗而出现了一诗两稿的情况。自此以后,人们多赞同其说,如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按此篇出入前篇,语意多同,或谓初本云。”《千一录》亦云:“太白《白头吟》二首,颇有优劣,其一盖初本也。”*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四卷,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87~588页。王湾《次北固山下》在作者生前就出现了两种差异较大的文本,并行于世。一是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卷下所录《次北固山下》,一是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所录《江南意》。以许学夷为代表的多数学者都认为《次北固山下》是诗人自己的改定稿,现代著名学者施蛰存、刘学锴等均持同样的观点*详见方胜《王湾〈次北固山下〉“改作说”献疑》,《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3期。。
此外,唐代诗人有很多唱和诗作,这些作品常常仅在首唱或首和者之前列诗题,其他作品的标题为“奉和”“奉酬”“次韵”,或者只标“同前”等。当诗人自己编著文集时,为了说明当时唱和的情况,也为了读者能够理解作品,诗人多会将简化的标题重新改写。陈尚君先生在《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一文中专门讨论了“作者本人之改题”的现象,列举了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自己修改诗题的例子*陈尚君:《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陈致主编:《中国诗歌传统及文本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3~355页。。
总体而言,唐人对自己诗作的修改,从时间上来说,既有写后即改——“新诗改罢自长吟”,也有修改旧作——“卧对南山改旧诗”;从改动的幅度上来说,既有接近重新创作的大幅度修改,也有个别字句的推敲斟酌;从修改的动机上来说,既有求善求美的主动修改,也有迫于无奈的被动改作。
二、诗人改动自己作品的原因
毫无疑问,对自己作品不满,进而不断修改,以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这是历代文人自改其作的主要原因。但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具体到唐人来说,略有如下数端。
第一,推敲字句是唐人惯有的传统。唐代诗人把写诗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把诗歌创作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人虽小诗,必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信非虚言”*魏庆之著,王仲闻校点:《诗人玉屑》卷8,第241页。。不仅仅晚唐那些才力不济的诗人会“苦吟”,就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也同样重视“推敲”,做到字斟句酌。明人都穆《南濠诗话》云:“世人作诗,以敏捷为奇,以连篇累牍为富,非知诗者也。老杜云:‘语不惊人死不休’,盖诗须苦吟,则语方妙,不特杜为然也。贾阆仙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孟东野云:‘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卢延逊云:‘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杜荀鹤云:‘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予由是知诗之不工,以为不用心之故,盖未有苦吟而无好诗。”*都穆:《南濠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9页。
第二,唐人“苦心文华”,力求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达到了极高的境地。陈尚君先生曾推测杜甫诗集是他自己晚年编定的,并且还作适当修改、加注*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6~337页。,颇为可信。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李)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页。李白《拟恨赋》和《拟别赋》模拟江淹的《恨赋》和《别赋》而作的,现在只有《拟恨赋》留存了下来。可见,李白对自己的作品有着很高的要求,对于不满意的初稿要么毁弃,要么重作。白居易也曾认为自己的杂律诗艺术性不高,要求后人在编辑其作品时,把杂律全部删去。白居易与李白抱着相同的态度,不是优秀的作品宁毁不存,那么要留下精品,就必须如他自己所说,做到“好句时时改”。
第三,经他人指点而自改。唐诗中“一字师”的故事颇多,如郑谷将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中的“数”字改为“一”字*魏庆之著,王仲闻校点:《诗人玉屑》卷6,第191页。;又如,齐己将张迥诗“蝉鬓掉将尽,虬髯白也无”中的“白”字改为“黑”字*阮阅编著,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前集卷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2页。,这些改动都是非常成功的,传为千古佳话。但这样的改动,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自改”范畴,而应该算是“他改”。我们要讨论的是诗人在他人的指点下,对自己诗文进行修改的现象,其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他人直接提供了明确的修改意见。这种情况严格来说不属于“自改”,而是“他改”,流传至今的各种“一字师”典故多属此类。但也应该注意到,这种改动与后人对唐诗直接删改是有所区别的,它是修改者与诗人商量、讨论的结果,改还是不改的决定权掌握在诗歌作者的手中。流传下来的“一字师”佳话中,诗歌作者多接受了改动者的修改意见,但可以想知定然也有作者不愿采纳他人修改意见的情况。如贯休曾给吴越王钱镠投诗,其中有一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看到后要求贯休将“十四”改为“四十”,“乃可相见”,但贯休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断然拒绝了钱镠改诗的要求*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33页。。所以说,这样与诗歌原作者关系密切的修改,也可以算作是广义的“自改”。第二种情况,诗人在别人的指点下自己进行的修改。这毫无疑问应当属于“自改”,而非“他改”。《鉴戒录》记述了贾岛“推敲”的故事,贾岛在“推”与“敲”之间徘徊,拿不定主意,韩愈认为“作敲字佳矣”。这与他人直接修改的情况不同,因为“推”与“敲”二字都是贾岛提出的,韩愈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又,计有功《唐诗纪事》卷67记王贞白携《御沟》诗见贯休,贯休提示王诗中有一字不妥*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51页。,并没有说明哪个字,更没有说明如何改,王贞白经过自己思考将“此波涵帝泽”之“波”改为“中”,这更应该属于“自改”的行为。
第四,除了艺术的追求以外,还有就是因为社会、政治等因素(如避祸、避讳等),诗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如陈良运先生认为,“《次北固山下》是王湾自己改定的文本,抹去了《江南意》中颂扬新朝和张说之意,改成了一首旅外怀乡的诗”;并且推测,王湾之所以改诗,是因为该诗曾经受到张说赞誉,在张说被罢相后,王湾因“避祸”而改《江南意》为《次北固山下》*陈良运:《王湾〈次北固山下〉异文蠡测》,《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
除上述原因以外,唐人对自己诗作的修改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前面提到贯休因原作散佚,其诗在流传过程中为他人妄改,为了正本溯源,所以进行了修改和再创作。
三、“自改”的意义及其异文的处理
(一)“得失寸心知”:“自改”不同于“他改”的特殊意义
唐人在“自改”的同时往往也会请人帮助修改自己的作品,“自改”与“他改”各有所长。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这就是说,诗人在修改自己诗文的时候,往往不忍割爱,而请他人参加修改,才能做到繁简得当。但“他改”也不一定都能改出佳作,也有其局限性。贺贻孙《诗筏》说:“诗有长言之味短,短言之味长,作者任意所至,不复自止,一经明眼人删削,遂大开生面者。然明眼人往往不能补短,但能截长。”*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9页。指出了“他改”的优势在于“截长”,缺点在于“不能补短”。诗歌终究是诗人自己呕心沥血创作而成,其中的曲折隐微之处他人往往无法体会。欧阳修《六一诗话》记:
陈公(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欧阳修著,郑文校点:《六一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8页。
杨慎《升庵诗话》卷6记:
《孟集》有“到得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之句,刻本脱一“就”字。有拟补者,或作“醉”,或作“赏”,或作“泛”,或作“对”,皆不同。后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杨慎:《升庵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3页。
这两则故事固然说明了杜甫、孟浩然诗艺之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也说明了诗歌创作是个人心灵的独特书写,其中的兴会是他人难以感知的。设想如果是他人为杜甫、孟浩然改诗,恐怕也难以达到杜、孟所预想的效果。
因此,历代文人都强调要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胡震亨说:“不改不工。”谢榛说:“诗不厌改,贵乎精也。”袁枚说:“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论:
严格地说,诗文都只有作者自己能修改,因为旁人所感到的兴会不同,所见到的意象不同,所想到的语言自亦不同。拿这个人的意思杂入到那个人的作品里,总不免有不相贯注的毛病。杜工部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句,欧阳修也说:“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文艺作家都必须同时是自己的严厉的批评者。*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朱光潜先生接着还讨论了“他改”的重要性,但他指出了“自改”的优势。“得失寸心知”,这也正是诗人“自改”的独特意义所在。
(二)“作诗容易改诗难”:“自改”的效果及启示意义
诗人修改自己的作品并不容易,刘勰认为“改章难于造篇,易字难于代句”,戴复古也说“草就篇章只等闲,作诗容易改诗难”,袁枚进一步分析了“难改”的原因:“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竟有隔一两月于无意中得之者。刘彦和所谓‘富于万篇,窘于一字’,真甘苦之言。”*袁枚:《随园诗话》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9页。这是袁枚的创作经验之谈,从“不安”到“得之”是一个不断修改、自我完善的过程。
多数情况下,诗改而愈精,但也并非都是如此。郑谷的《雪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酒歌楼酒力微”,“乱”字可以描绘出大雪纷飞的气势;而宋孝宗忌讳“乱”字,改为“轻”字,这样和“密”字就失去了照应,使得整首诗气势顿失。又如,《陈辅之诗话》记萧楚才为张乖崖改诗,将“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中的“恨”改为“幸”,“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4页。如果单就艺术而言,“幸”字与下句“闲煞”二字不够协调,“恨”字似乎更好,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样的改动是必需的。
不仅“他改”会导致改而愈下的情况,“自改”也可能会如此。黄庭坚《小儿》诗中有两句:“学语春莺啭,书窗秋雁斜。”后来作者自己改为:“学语啭春莺,涂窗行暮鸦。”从对仗、用语来看后者确实是工于前者,但“小儿”的天真自然也就此消失殆尽了,所以胡应麟批评说:“虽骨力稍苍,而风神顿失,可谓愈工愈拙。”*胡应麟:《诗薮》内编卷5,第102页。徐增《而庵诗话》云:“余尝得佳句喜极,乃至诗成时,却改到不见好处歇手。乃知古人为了章法,涂抹佳句至多也。”*徐增:《而庵诗话》,见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31页。徐增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有时候为了顾及全篇会越改越糟,并据此推测前人定然也会因修改而抹去了很多佳句。
对于读者而言,学习前人对自己诗作反复修改的过程颇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可以从中明白一些道理,得到一些教训。杨慎曾挖苦晚唐诗人所作的五言律诗,云:“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捻断肋骨,亦何益哉!”*杨慎:《升庵诗话》卷11,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851页。这样“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无论如何也吟不成佳作,改不出好诗。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作的方法,汲取有益的经验。宋代朱弁《曲洧旧闻》卷4记:“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也,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识其用意所起故也。”*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2页。也正是因为如此,贾岛“推敲”、王安石改“绿”字等故事才为人们反复提及。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非常精彩的意见: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322页。
鲁迅先生认为,研究大作家的未定稿本和修改本是一种“极有益处的学习法”,因为仅仅看大作家的定稿,往往不能领悟他们的创作及修改过程,只有用心体会那些“苦心删改的痕迹”,才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应该那么写”而“应该这么写”,从而得到更多的收获。
(三)“求真”与“求善”:科学对待因“自改”而产生的异文
唐诗异文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倘若从修改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笼统地分为“他改”和“自改”两种情况。“他改”,包括钞刻者、选评者等有意无意地改动,情况异常复杂,我们将另作讨论;但如果仅从文献校勘的角度来说,因“他改”而产生的异文,当以恢复原貌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但“自改”产生的异文处理起来就不同于“他改”了。首先,有些作品在作者修改以后,即以改定稿传世。虽然初稿文字依然常常为历代诗歌评论家拈出讨论,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析字句得失对于诗歌艺术的影响;至于改而愈精的文字,当以诗人自定稿为准。但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后人认为有些作品修改并不成功,改动前比改动后更好,人们在评点、钞刻诗歌时常常会将初稿也一并提出;对于这种情况形成的异文,后人多会出校,但在文字的取舍上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外,有些作品在作者修改之前已经流传于世,故而出现了一诗两本甚至多本的情况,这就需要详细出校异文,加以探讨。
我们不妨就按照本文开头讨论的三种“自改”情况,来谈谈异文处理的问题。首先,对于诗人自述修改情况的异文,如李白《大鹏赋》、贯休《山居诗》等,当然应该以定稿为准,充分尊重作者的修改。其次,对于后人推测的某诗一为改本一为定本的情况,则应该审慎处理,因为他们的推测并非定论。如王湾《次北固山下》,霍松林先生就认为它与《江南意》是两首不同的诗作*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页。,我们也赞同“两诗说”。另外,即便有诗人手书真迹传世,也并不能将所有的手书都当成是确定异文的唯一标准。如杜牧手书的《张好好诗(并序)》,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幅作品极为精美,是诗人早年所书,书写工整,无一处涂改;完全有可能是诗人应他人之邀而书写,写完之后就被人拿走,后来流传于世。如果诗人若干年后修改了诗稿,但手书真迹不在身边就无法再改了,故此类手书真迹不能作为诗歌校勘的唯一标准。与此不同的是,许浑《乌丝栏诗》这样的手书稿本,反而最有校勘价值,可以将其作为校勘异文的有力证据。罗时进先生所著《丁卯集笺证》也正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样的稿本,诗人一般不会轻易将其赠予他人,且不断在上面直接加以修改完善,最终所改定的文字自然应该可以看作是诗歌的定稿。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认为修改旧诗作犹如炼丹,其《删改旧诗作》诗云:“笑同古炼师,炼丹穷昏昼。一火又一火,层层去粗垢。及夫将炼成,所存仅如豆。未知此豆许,果否得长寿?”*赵翼:《瓯北诗钞》(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8页。赵翼希望通过反复修改自己的诗作,能够让其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视诗如命的唐人更是如此。现代学者多重视研究唐诗“他改”的现象,对于诗人“自改”的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研究唐人非常普遍的“自改”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入开展唐诗的校勘整理等工作,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一首首唐诗佳作诞生的历程。唐人孜孜不倦地对自己诗作进行加工修改,他们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也正是这种精耕细作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才创造了唐诗无与伦比的辉煌。这也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校:刘云
作者简介:方胜,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安徽 芜湖241000),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安徽 淮南232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W05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1-0062-06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