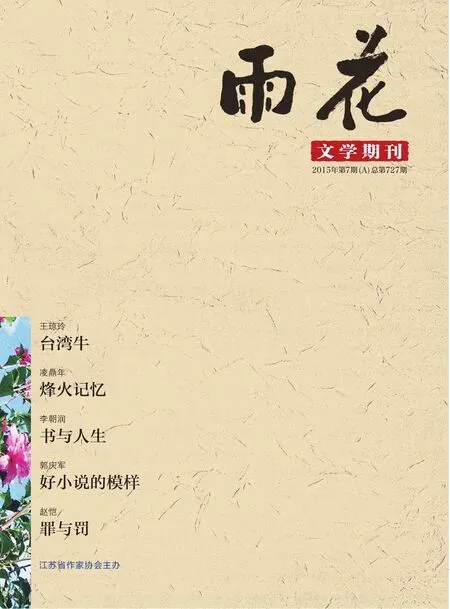命里女人
■卞优文
沟河里是个避乱的好地方。
沟河里是个小村子,离安家舍十来里路,是三镇交界处。村里的人要上安家舍赶个集,也没条像样的路好走。水路倒是发达,西边是得胜河,北通长江南连运河,北边是白龙河,南边、东边,都被村子里的一条叫扁担沟的小河环绕着。陆路只有东边一座小桥,可以通向外面。
世上的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就这么个不起眼的村子,日本人占领常州城后,却成了避乱的世外桃源。一时间,城里来逃难的人,有好多家,特别多的是姑娘媳妇小孩,几十口人。
当然,人们知道这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有一个大大有名的人家—中医世家许家。许家医术传承自清代著名的孟河医派。这里离孟河只有三四十里,不远。
许家在安家舍镇上有诊所,但一直没有离开村子,家里也给人看病。附近的村民主要来家里,镇上或者远道而来的病人,都到镇上许家诊所。说是诊所,到抗战初期,已是一个小规模的医院了。许家父子白天在诊所,晚上在家里,不仅看病忙,两头赶也辛苦。也有人提出只开诊所,不在家里营业。许老先生总说村民赶路不便。日本人打过来那一年,小许先生许开华已经二十八岁,无论医术还是人品,都已被人认可。
起初,日本人还没有力量深入到广大的乡村,沟河里也还平静。后来,避乱的人们舍不得自己的家,也就陆陆续续回去了。
只有丹萍留下来了。丹萍姓郭,那年十六。父亲已经带着后妈和弟弟逃到大后方去了。父亲临走前,把她郑重托付给许家,所以不是临时来避难的。丹萍永远不会忘记,父亲跟自己告别时,那双饱含热泪又不敢让后妈看见的眼睛。郭家住在常州城里,与许家是世交,虽然相距三四十里路,却没断过来往。
沟河里四面环水,东边小半部是村子,西边一大半是农田,再往西靠近得胜河边,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竹林。在这里,埋着村里人的祖宗,从没被打扰过。1940年前,日军一直没有在安家舍驻军,虽然也来扫荡扰民,毕竟不长久。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府,这年夏天,日军分三路来镇上设据点,砍树拆屋筑碉堡,百姓可遭了罪了。许家诊所一分为二,老先生在镇上留守,许开华回到村子里。为了不引起日军注意,老先生交代儿子:不上街,不上城,不出远诊。
丹萍经过近三年的学习,已成为熟练的护士,人也长开了,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姑娘。也有来提亲的,但都被她以父母不在、无人做主为由,婉拒了。许开华夫妇和三个孩子,早已把她当作一家人,也没有太勉强她。
这一年夏天,陈毅率新四军一部撤离茅山根据地,挺进苏北,路过沟河里一带。因为地形有利,陈毅和部分干部就住在了许开华家,聊到许家行医多年,尤其了解到许家中医外科很是有名,很感兴趣。一位军医姓翟,看到丹萍心灵手巧,护理也专业,就一直鼓励她参军。
但丹萍没有参军。
在以后的几年里,日军来过沟河里一次,是从得胜河里的船里上岸的。大概是汪精卫死的那一年,离抗战胜利已不远了。
那一天,一艘日军铁皮艇在村边靠岸,鬼子上了岸,有的坐在地上休息,有的三三两两溜达,也不知他们想干什么。这些恰好被村里一个村民看见了,这人还算冷静,放下手里农活,飞步回村报信。这时正好在中午,许多人尤其是老人正在午休。大家你喊我,我喊你,也不敢大声,不多久,就都朝村东移动了。这时的开华正好从邻村出诊回来,见到妻子带着孩子往东赶,连忙帮着抱孩子,走了一段路,突然想起丹萍,忙问,妻子一下子脸色蜡黄,吓得话也说不出了。这几天,丹萍正好身体不适,吃了几帖中药,就睡在后面的楼上了。开华妻子只顾着孩子,走时竟忘了丹萍了。开华一听,忙放下孩子,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转身往村里跑去,妻子想阻止,嘴里却发不出声音来。
开华叫醒丹萍时,已经能听到日本兵的脚步声了,咵嗒咵嗒,由远及近,离开是来不及了。开华拉起丹萍,赶忙躲进了后面的柴草房。丹萍把门插上了,开华急中生智又把门拉开了,等两人把面前的柴草遮盖好,日本兵已经到了门口了,开华听得有人在门口停了下来,见门开着,又没有值钱的东西,就走开了。丹萍这时才明白开华把门开着的道理。只听到前房翻箱倒柜,打打闹闹。丹萍一声不吭地倚在开华身上,身子微微颤抖。过了好一会儿,天色暗下来了,也听不到声音了,开华悄悄地想起身,却又被丹萍拉住了,她这次是完全赖在他身上了,像一个撒娇的小妹妹。
等天完全黑透了,开华才悄悄起来,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到河边确定鬼子的船已开走,才找人把村里人叫回来。村里的财物损失不小,开华家里,吃的、穿的,方便拿的也都被拿走了。
自这天以后,丹萍看开华的眼神里,仿佛又多了一些东西。开华感觉到了,开华妻子也看出来了。但都装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那个翟军医又来了。这次是部队北撤路过,他特意来的。原来,自那次见过丹萍后,翟军医就再也无法忘记丹萍。用他的话说,他的心被那个只见过一面的江南姑娘占满了。
这次他又动员丹萍跟他走。但丹萍还是没有答应。她也不肯说什么理由。
翟军医离开时那个眼神,许开华过了几十年都忘不了。
许家在镇上的诊所又红火了,并扩大规模,成了一所真正的小型医院。但许家还是没有放弃村子里的小诊所。有人说,许老先生是高人,想得远,永远留着退路。只有老先生自己知道,他心里有个秘密。他早年请一位高人给儿子算过一卦,命书至今还珍藏着。命书上说,儿子许开华“命不离血地”。血地就是出生之地。命书上还说,儿子是“两妻之命”。老先生一直注意儿媳,觉得不是福薄之人。
那一天,像往常一样,老先生巡视病房。他已经把一线的事交给了儿子。儿子开华正在给一个病人动手术,全神贯注,丹萍和另一个护士站在旁边帮忙,大概手术差不多了吧,她们已没什么事了。但就是丹萍抬头看开华的那个眼神,就那么一个眼神,被老先生捕捉到了。
老先生心里咯噔地一下。
老先生不便对丹萍说什么,便找来儿子。他最担心的是儿子与丹萍已有私情,那可真是对不起丹萍死去的爹娘。丹萍的爹也是学医的,战时死在了大后方,没能回来。丹萍已是孤女,如果是儿子勾引了人家,那不是误了丫头终身吗?
开华面对老父亲的询问,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先生纵然世事洞明、阅人无数,心里也砰砰直跳。开华看着父亲,说,老话说,知子莫若父,你看你儿子会做这种事吗?老先生没想到儿子会把球给踢了过来。他微微一笑,对儿子说,我们就不绕弯子了,你就说说你对丹萍的感觉,说说你对她未来的想法吧!
开华想,这老爹真够厉害的。不说真话,瞒不了他,说真话,即使是父子,也不大好说,毕竟自己是一个有妻儿的人了。丹萍从一个小丫头长成一个女人味十足的大姑娘,可都是在许开华的眼皮底下。开华不去动这个心思,完全是道德防线守着,作为男人,谁都不可能不动心的。尤其是那次躲日本兵,两人相拥在草堆里半天之后,开华对她的身子就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想亲近的感觉。
老先生看着儿子,三十多岁,帅气儒雅,正是最讨女孩子喜欢的年纪,天天朝夕相处,也难为了丹萍这丫头了。学中医的都特别懂得人的心理。村民们都说,有个小毛小病,只要到许家门槛上坐一坐,病就好了一大半了。其实是老先生的几句话,说到病人心里去了。老先生想,丹萍这丫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孤身一人,情感上依恋年纪大她一圈的开华,也在情理之中。
父子俩就这么默默地对坐着,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俗话说,田禾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家的好。老先生也是三十来岁才有的这么个儿子,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喜爱,甚至偏爱。坐着坐着,老先生脑子里像突然划过一道闪电:儿子命书上说的“两妻之命”,莫非就应在丹萍这丫头身上?一想到这里,越想越是像,这孩子仿佛与自己儿子是命中注定的。这么一想,心里对郭家、对丹萍的亏欠感,一下子淡去了一大半。
开华打了几个腹稿,还是不大好说,就又对老爹打起了太极。说,丹萍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早是你女儿了,她的事还是你老看着办比较好。
其实这时的许老先生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已经不需要儿子说什么了。那时,虽然民国法律规定一夫一妻,但民间富裕人家,一妻之外,纳妾还是常有的事。
老先生瞒着儿子,先找丹萍谈。问她婚姻大事有何打算,再一步一步,套出她心里的想法。果然是暗恋开华,再不能接受其他男子。当老先生提出成为一家人的打算时,丹萍一点没有觉得自己委屈,反倒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嫂子,心里愧疚。老先生大为感动,同时也信心大增。对自己的儿媳妇,他还是有信心的。这个儿媳妇是自己一手操办娶进门的,开华这方面开智晚,那时还不大懂这些事。至于儿子这一关,就更不是问题了。男人纳妾,内心里有谁会不愿意的?就像黄袍加身做皇帝,虽要推让一番,那不过是做给人看看罢了。
老先生只能硬着头皮找儿媳谈了。公公找儿媳谈给儿子纳妾的事,确实也够为难的。儿媳贤惠,又有儿有女的,怎么说呢?也真是天下父母心了,老头子居然想到了最原始的理由,那就是—命!他直截了当地对儿媳说,据某某半仙说,开华今年是本命年,命里有难。儿媳一听就傻愣愣地看着老公公,一看儿媳焦急的样子,他才慢吞吞开口说,也不是没有开解的法子,就是要亏待你了。儿媳一听,又是一惊。等了一会儿,老先生才缓缓地说,半仙说,开华是两妻之命,只有纳妾,才能过这个坎,保性命无忧。听到这里,儿媳的心也放下来了,起先她还以为是要休了她呢。接着,老先生又说,你看呢?儿媳赶忙说,那还有什么说的,爹定就是。老先生说,他纳妾,你没意见?老先生也没想到,儿媳竟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那有什么,皇帝还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
老先生长叹一声,说,死生由命,婚姻由缘,也真不能不信了。开华这事,我也直说吧,我想把丹萍这丫头给了他,你看她也老大不小了,在我们家这么些年,总不能在我们家做一世老姑娘啊!
儿媳妇听到这里,两行泪水沿着双颊缓缓地流下来。老先生说,你不愿意她?
儿媳妇说,不是不愿意,而是太愿意了。这回轮到老先生听不懂了,便睁眼疑惑地看着她。她这才抬起泪眼,慢慢地说,这样就可以、就可以还了那年躲日本兵的时候,自己心里亏欠她的了。
听了这句话,老先生也忍不住眼睛湿润了。
开华娶了丹萍后,新房就做在安家舍街上。每个周末回村里住。一时间,开华成了所有男人羡慕打趣的对象。特别是周末回村的路上,熟悉的男男女女会大声说:许先生,不要太累着自己啊!开华骑在自行车上,嘿嘿一笑,并不回话。每次回村,总有村民上门找开华看病。慢慢地,村民们发现,开华媳妇的脸色不如以前好看了。有时会当着病人的面,对丈夫说,礼拜天就是回家歇歇的,可不能累着了。开华知道,自己留给她的时间是太少了,所以不是急病,就都回了,不在家里看。
开华和丹萍恩恩爱爱,白天一起去诊所,下了班就一起回到街东头的小院—他们的爱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进这个新家,开华都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新婚那天夜里,他搂着丹萍,她像一团柔软的棉团,黏在他身上。半夜醒来,他见她也醒来了,就逗她,问,是什么时候有那个想法的,她不吭声,只是羞羞地往他怀里拱。他问,是躲日本兵那天吗?她摇摇头。他又问,是这天之后?她又摇摇头。又问,是这之前?她轻轻点点头。搂着怀里羞得浑身发烫的小女人,他又忍不住逗她,说,是一进我们家的时候?想不到她使劲地点了点头。
他眼里泪水忍也没忍住,就流了下来,一滴一滴滴在她热热的身子上。
老先生每周回一次沟河里,等于出诊一天,以示不忘老主顾。但也有遗憾,一年多过去了,丹萍竟没一点有喜的迹象。开华不急,丹萍却不能不急。开华已是有儿有女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自己的问题吗?自己健健康康的,是什么原因呢?
世事的变化忽快忽慢,无论快慢,你都得适应。慢时你要学会熬,快时你得学会赶。可对丹萍来说,还是赶不上,适应不了。从心里装下开华,到遂了心愿,比八年抗战还长一点。十六岁,老天把她带到他的身边,就像一颗种子,被春风带到到一片肥美的土壤里。但刚刚开花,还没有结果,风就把她无情地吹落了。丹萍也知道新中国的《婚姻法》是对的,一夫一妻制是进步的。但具体到自己身上,她又觉得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到第二年的年底,政府给开华的最后选择期限也就到了。
开华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原配妻子已经为自己生了五个孩子,父母亲虽然喜欢丹萍,但还是明确站在孙子们的母亲一边。丹萍结婚时已经觉得自己底气不足,好像是抢了人家的,加上又没有生个孩子,哪里还有一点争一争的勇气?即使“姐姐”让她,她也不能让开华对不起五个孩子。
办理离婚手续的最后期限到了,没有一个人明确说什么。但也没有一个人不明白结果是什么。这一天,丹萍早早下了班,回到小院,把开华用的东西全部整理好,把院子打扫得清清爽爽,又炒了几个小菜,炖了一锅鸡汤。等开华回到家,天已经黑了。但家里却是亮亮堂堂的,仿佛过节一般。
菜端上来了,酒斟上了,两人面对面坐下。
这是世界上最让人心痛的心照不宣!
丹萍先开口,说,哥哥,我敬你一杯,以后就不好这样了。话未说完,泪已双流。
开华一句话都没说得出,已是泪流满面。
丹萍见他这样,心疼得转过身来把他抱在怀里。两人哭作一团,开华的泪落在丹萍衣襟上,丹萍的泪滴在开华的头发上。丹萍心里想,就凭哥哥这把男儿泪,自己也值了。
两人没有吃下一口饭,就相拥着来到了卧室。
这里还是新房的陈设,人却要成为旧人了。
两人又是哭,又是说,又是缠绵,一直到后半夜才小睡了一会儿。
醒来时,天已蒙蒙亮了。丹萍一骨碌爬起来,光着身子,把自己昨夜穿的内衣裤和开华的包在一起。她看着开华,说,快起床吧,我想你陪我去个地方。开华想,去办手续还早呢。嘴上却装作不知,问,去哪里?丹萍说,我想回趟村里。
丹萍回村并没有回家,而是领着开华钻进了村西的许家祖坟。她要把两人昨夜穿的内衣埋在祖坟旁边,她说,这样也不枉做了一回许家媳妇。
这片长满树和竹子的地方,是祖宗安息的地方。两人把小木盒埋在开华爷爷坟旁的一棵槐树下,就算埋下了一段婚姻,也算在那个世界给了丹萍预留了一个名分。丹萍做完了这一切,站起身叹了口气,说,这个家我还是要来的,以后我就是孩子们的姑妈。
两人办完手续,回到小院,开华提起丹萍为他整理好的行李箱,想走却迈不开步,他看着她,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丹萍一下子又冲上来,死死地搂住他,说,我没能为你生个孩子,真是不甘心,不服气。开华放下行李,也伸手搂住她。只听见她幽幽地说,我看过医生了,我并不是一定不能生,而是我的肚子特别,是慢热的那种,再过几年,说不定就怀上了。说着,长叹一声,说,可惜等不到了。开华鼻子酸酸的,也找不出话来安慰她。
从这天起,开华要么回村子里住,要么在诊所里住,不再去丹萍的小院。起先有民兵经常巡逻,时间长了,也从未碰到他们违法同居,去得就少了。其实,开华这一段特别地想丹萍。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才这么几年,又还没有孩子,在开华心里,新婚的新鲜劲还没有过呢。每天下班准备回家的时候,开华就很不适应,有好多次都是往丹萍的小院走,走了一段路才想起来,那里不能去了。丹萍与他在一起的琐琐碎碎也都会涌到面前。丹萍长着一张瘦瘦的小长脸,眼睛眉毛细细长长,本地人叫做狐狸脸,秀气而媚。但她的身子却是丰腴诱人的,开华常常会在迷恋中夜不能寐。后来,丹萍的小院成了诊所里年轻人的集体宿舍,开华就更是去走一走的念头也不敢有了。
许家虽然几代行医,广结善缘,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谁也包庇不得。土改时,许家毫无悬念地被划定为地主。诊所公有化时,改为卫生院,开华勉强当了个副院长,只看病不管事,心里不免有点牢骚,有次跟人喝酒,说到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事业,说收就收了什么的。这话被人传到了党支部书记那里,政治上就更被边缘化了。
丹萍还在卫生院上班,是个护士长的角色。白天忙忙碌碌,晚上回到家,说不尽的孤苦。有过婚姻了,和以前就不一样了。晚上一觉醒来,被窝里冷冷的,一个人,忍不住就会泪湿枕巾。以现在开华的处境,两人接触得越少越安全。每天回到家,丹萍就关上门,少与外人接触,免得闲话。她知道,自与开华办完手续后,打自己主意的眼睛,不知在哪个角落藏着呢。她是一概不理。但有一个人倒是她常常会想起的,就是那位翟军医,他已经转业到地方,在县医院当业务院长,有时也会来这里检查工作。但不知道他的转业跟自己有没有关系。但愿没有关系吧。
其实,翟军医的转业还真跟丹萍有关。因为不是本地人,翟军医是可以在几个地方选的,就因为丹萍给他留下的,也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吧,他就留在了这里。他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爱人在战斗中牺牲了。知道丹萍的情况后,他又动了心思。当他跟亲近的人提起时,朋友反对,组织上也不同意,但以他那倔强而又自尊的知识分子脾气,又不甘心。
丹萍已经三十了,但依然像姑娘一样水嫩,还有着一种姑娘所没有的成熟和女人味。丹萍离婚后,也不免尴尬,天天看见开华,心里各种滋味都有。有时丹萍会偷偷地想,这女人结过了婚,就脸皮厚了,内心里存了欲望,没有姑娘时的痴情和单纯了。
过了不久,丹萍就调到县医院去了。开华和丹萍都觉得,这样也好,天天在一起,对大家都是一种煎熬。只是丹萍离开后,常会想起安家舍,想起沟河里,想起许开华。她有时会以看望老人或孩子们的名义回去看看,但也不便常去。
大家都以为丹萍会嫁给翟军医。开华这么想,丹萍自己心里也觉得,时间长了会接受他。翟军医三十六七,身长玉立,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革命资格老,医术又好,不要说在县医院,就是在整个县城,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丹萍却没有与翟军医结成夫妻。丹萍心里就是放不下开华,翟军医可能也难以接受丹萍心里装着另一个男人。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吧,反正就这么拖着拖着拖下来了,谁也没去捅破这层纸。
转眼到了1957年,开华因为早先表达过对诊所公有化的不满,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医疗队伍,回到沟河里当了农民。周边的农民却把他回村当做喜事,奔走相告,天天上门求医的络绎不绝。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实施后,周边上门请教的赤脚医生,更是来来往往,挡也挡不住。上级领导感到政治影响太坏了,就派了民兵在村口值班,遇见生人就上前盘查,只要是去许家看病的,一律劝回。坚持一段时间后,实在太麻烦,专为这些人记工分,社员也有意见,就改为群众监督,要求村民知道有人去许家看病,立即报告。村里人也知道,这是上级给自己找台阶下,谁吃饱了会去干这事?开华每天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免费为群众看病,有时病人也会送点鸡蛋蔬菜之类的表示谢意,推也推不了。
开华觉得自己的内科水平有提高,外科却因没有设备,也没有机会手术而生疏了。于是就在针灸上动起了脑筋,能用针灸解决的就用针灸,简单方便成本又低,很是受欢迎。1965年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开华的行医有了松动,名气也更大了。因为当时农村“赤脚医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二是草药,而此时开华的针灸已是出神入化,远近闻名。但过了一年,文革开始了,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开华的行医又受到了限制,村东小桥边也常有民兵转悠。
这一次运动来势之凶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尤其是许家父子。他们一直有一种信念,行医积德之人,什么坎都会过的。这次却“失算”了。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批身穿军装腰束皮带的年轻人,二话没说,就把父子俩绑走了。给老先生的罪名是:地主、历史反革命,剥削过农民,给汉奸、鬼子看过病。老先生刚辩解一句说,我也给新四军看过病呢,就被劈头盖脸一顿打。老先生八十多了,哪里受过这种污辱?从此不再开口,也不再进食。
给许开华的罪名也是现成的:右派,地主崽子。
当开华埋葬了父亲,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夜里,他把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一些收藏已经被当做“四旧”没收了,只剩下一些凌乱的文稿。在这些碎纸片中,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份自己的“命书”。命书是一位老先生的笔迹,上面陈述了他的属相、脾性,还说他“命不离血地”,是“两妻之命”。末尾写道:五旬又六载,一去料不返,夕阳西下数当终。开华大吃一惊,想,今年自己恰好是虚岁五十六,莫非命中注定自己的寿数就是这些,年内就该命赴黄泉?他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心意:他是不忍看着儿子先于自己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才绝食而死的。想到这里,开华不禁悲从中来,大放悲声。哭着哭着,一个念头从心的最深处,慢慢往上长,越长越大,占据的他的整个心胸。他想,他就是不能死,他倒要看一看,这命难道真是生下来就注定的?他抹干泪水,去厨房弄了点吃的,回到老父亲的床上,呼呼大睡,直睡到太阳升起,阳光照亮了房间,也洒满了他的心房!从此,他像变了一个人,各种批斗会,他都很配合,斗完回来,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批斗他的人,甚至是家里人,都怀疑他受了刺激,可能神经出问题了。
但也不是谁都能过得了这个坎的,翟军医这个老革命就没有挺得过去,反而落了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政治运动的狂热,就像暴风雨,终究不能持续太久。等风头过去,丹萍正想着怎么再回村子时,一件事使她不得不再回去了。那就是她自己身上的病痛。有一天,她很奇怪地发现,自己的左乳奇痒无比,一开始没太在意。过了一段时间,越发严重,由痒变成了痛,她就自己找医书看。一看吓一跳,书上说,这种乳腺疾病有癌变的可能,最干脆彻底的办法是切除。夜深人静,捧着自己没有给孩子喂过奶的乳房,丹萍又是伤心又是不舍。
她想到了许开华。只有让他诊治,才能使自己了无遗憾。他曾是自己的丈夫,又是针灸大师,更是自己心里唯一的男人。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医学上,都是唯一选择。
丹萍请长假回到了沟河里。这时候,对开华的管制放松多了。针灸是一个慢慢见效的过程,丹萍住下了,就像又回到了家。开华媳妇把丹萍当多年没回家的妹妹,这让丹萍感动,也让开华放了心。丹萍有时想,这世上怎么有这么大度贤惠的女人,换了自己,恐怕也难做到。其实,开华媳妇心里也有一个秘密,公公是跟她讲过开华“命书”的。开华逃过一劫活下来后,反倒比以前更开朗更健康了。她就在心里暗暗许下了一个心愿:只要是开华愿意的事,自己再受委屈,也要成全。何况他本就是“两妻之命”呢?丹萍来了,甚至成了她了却心愿的一次机会。
开华和丹萍在分开二十多年后,再次朝夕相处,仿佛是不久前刚刚分开,两颗心根本没有远离过。每次开华为丹萍治疗,开华媳妇都会悄悄走开。在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丹萍常常有一种幻觉,好像还是跟自己的男人在一起。有时她甚至会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自己的病不要太快地好起来。
丹萍的乳房痊愈了,没有伤口,完美如初。
那天早上起来,丹萍觉得很轻松,摸一摸自己的病乳,也没有一点不舒服。她又撩开衣服,对着镜子看自己,看着看着,心里竟然冒出了女人才有的一种得意:这哪里像一个四十多岁女人的双乳。她叫来开华,撩起衣服给他看,让他再检查检查。开华微闭着眼睛,摸过来摸过去,丹萍不仅没有了痛感,反而有了一丝痒痒麻麻的快感。
开华低头检查时,丹萍突然轻声笑了。
开华抬起头,说,你笑什么?
丹萍的脸微微一红,说,你、你都摸得我不好意思了。
开华有点奇怪的看了她一眼,说,这么长时间,不是天天这样么。你今天怎么了?
丹萍低下头,像少女般娇羞地说,今天觉得好了,不但不痛了,你还摸得、摸得我好像有那种感觉了。
开华一把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说,唉,你这一世人生,都叫我给害了。你要愿意,就还把这里当作你的家吧。
丹萍点了点头,不禁泪流满面。开华的眼睛也湿润了。
从此,丹萍就常常回到安家舍来。有点像嫁出去的女儿,有时又好像不那么像。虽然也免不了有人说些闲话,但当事人坦坦荡荡,谁都不理这些。
后来,政策变了,开华单独开了一家诊所,远远近近的病人都上门就诊,非常红火。
再后来,开华的老伴瘫痪在床四、五年,都是丹萍在照料。那时她已经退休了,但依然是一个风韵犹存的漂亮女人,不像是一个退了休的人。
开华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在某一个飘着大雪的日子,毫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丹萍又活了几年,也离世了。虽然没有再补登记的手续,但远远近近的人,都觉得他们是一对再合适不过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