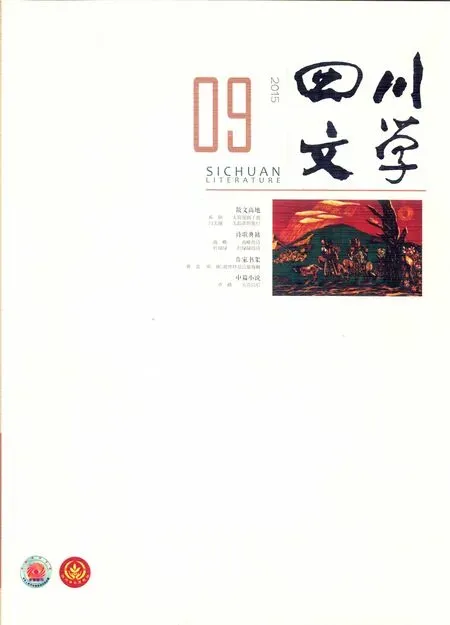廖品正:我亲历战败后的日本
蒋兮湄/文图
廖品正:我亲历战败后的日本
蒋兮湄/文图
【本期嘉宾】
廖品正,1938年出生在成都市正府街41号“廖家老宅”,成都第22中学校退休教师。父亲廖季威系抗战胜利后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1946年至1948年,廖品正随父在日本东京生活了2年。近年廖品正先生先后接受过中央电视台、中国台湾媒体、日本《读卖新闻》等数十家机构的采访,并长期关注和支持“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向日本正义申诉的活动。
【采访手记】
记得2011年的7月27日,是一个典型的“桑拿天”,数百人围聚于成都市人民公园“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周围祭奠亡灵、缅怀英烈。这一幕让人们回想起1941年的当天情形:108架日本飞机在成都上空投下了440枚炸弹,当场夺去689条生命,造成1368人伤残。被炸地点主要为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大慈寺一带,被炸街道82条,毁坏民房3205间,这是抗战中成都遭日军飞机轰炸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是成都绕不过去的惨痛记忆,也是二千余年来成都最深的一道伤口……那天,我在祭奠现场见到一位儒雅的老人,背一个大包在会场周围摆放有关“成都大轰炸”的老照片和文字说明展板,大约有几十幅,引得很多市民驻足观看。一见有人围观,老人立即就开始讲述这些图片背后的故事……此人就是廖品正先生,他义务做这一历史普及工作已经多年了。
几天前我与廖老约定了采访时间,他一口应允。采访当日我打去电话,才得知他因用脑过度在家突然晕厥,目前在成都空军医院治疗。我当晚赶到住院部,廖老师正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他一再声明,仅仅是突发事件,不碍事不碍事。他躺在病床上愉快接受了我的采访。
廖老师开门见山:“前几天你打来电话,希望我详细谈谈我随父亲在日本东京的那2年生活。这几天我一直就在回忆,查阅了一些资料,决定少‘炒冷饭’,我想给你讲一讲一个少年心目中的战后日本……”
“我的父亲廖季威,出生在成都市正府街41号。1936年6月,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南京步兵学校学兵队连长、湖南永州战防炮教导总队中
校教育主任等职。1942年夏天,父亲从炮兵训练部队调到重庆,在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任中校参谋,1944年升为上校参谋。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指挥机关,第一厅管作战,第二厅管情报;第二厅第一处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在重庆期间,父亲与宋楚瑜的父亲宋达是同事,宋达亦为上校参谋,与我母亲苏荣辉又系湖南同乡,两家关系密切。我父亲精通日、英、德文,很快投入到对日军事情报的收集分析工作当中。”
1945年10月,我父亲廖季威看到一份来自美国政府的公文,商请中国派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中方随后将曾经在越南河内担任受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的67师整编为驻日占领军,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一占领军未能成行,仅仅派出一个代表团。所以我父亲曾经感叹:“我是抱憾终生的中国占领军上校。”大量的准备之后,次年5月27日,由中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及家属飞抵日本。
廖品正郑重指出,在中国方面指挥下,父亲和同事海军少校钟汉波等人协力完成了几件大事:将两个参加“百人斩”的狂魔引渡回中国审判;另外还将甲午海战中“镇远”、“靖远”两舰的舰锚、舰链及炮弹等从上野公园索还,以消除国家、民族耻辱。这批被虏之物后来转到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用以陈列。1959年,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镇远”舰铁锚被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
事情的原委是:1947年5月,驻日远东特别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在1937年底的《东京日日新闻》(即后来的日本《每日新闻》)上看到一张可怕的照片:两名日本军官手持军刀并肩而立,他们完成了“百人斩超记录”。这是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相约劈杀中国人的比赛,从无锡“开刀”,当他们在南京会面时,“战绩”为106∶105,向井敏明“胜出”。因为分不清谁先杀满100人,两个恶魔重新约定以杀满150人为目标再竞赛……据此,中国政府向盟军司令部要求追捕并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1948年1月28日,罪大恶极的杀人狂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这件事,成都文史学者王大炜特意写了报道文章。
我问廖老师:“你从日本回国时,有没有带回什么纪念品?”
廖老师有点不快,他扭头看着窗外大声说:“实话说,我很不喜欢日本!那有什么可纪念的?但那时的同学和老师,倒是让我时时感到温馨……”
【实录】
中国占领军未能进驻日本的原因
蒋兮湄(以下简称蒋):你父亲是提前去往日本的吗?
廖品正(以下简称廖):父亲廖季威曾经撰文指出:日本将要投降,我们事前也有所知,但都是情报或判断,非正式消息。8月1 5日早上我到军令部上班之时,最先得到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来自军令部第二厅。
我父亲以及顾问李立柏、戴坚等13人,于1946年5月27日早晨7点从上海江湾机场出发,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乘坐B24美国轰炸机进入日本。后来有人曾经特意询问过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为什么要乘坐轰炸机去日本?朱团长明确回答: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日本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除不携带炸弹外,机关炮是不能拆卸的,以示我们进、出日本的姿态,必须显示国威、军威。
父亲廖季威晚年回忆说,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少将带着翻译去会见美军第八军军长艾克伯格。艾克伯格对他说,中国的部队到达后暂驻爱知县,隶属第八军的第一军团指挥。6月4日,戴坚拜见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给了我父亲两个任务:一是向美军要一份美军各级官兵的薪饷表,参考美军的薪饷,拟出一个中国占领军的薪饷表,可以相对低一点;二是要他抓住机会解决汽车问题,以便使部队全部实现机械化。6月6日,住在横滨的父亲立即着手实施这两件事情。在此之前戴坚少将提供了一份67师的编制装备表,计有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运输团,战车、工兵、通讯兵各一个营,师部还有一个特务连和其他后勤单
位。蒋:准备赴日本的67师的军事设备好不好?
廖:67师并不差,在“国军”里算很好的了。他们的装备的确有点“中国特色”,这成了美军眼中的笑话。
我父亲撰文回忆,炮兵团的第一营是加农炮,由汽车牵引;第二营是榴弹炮,由牲口马匹为动力;第三营是重型迫击炮,由骡马驮载。而运输团第一营为汽车运输营,第二营是兽力运输营,第三营则是人力运输营,号称“铁肩队”。当戴坚去见艾克伯格的时候,美国人就挪揄说,你们的部队驻扎在名古屋市内,因为有很多马匹,马粪就是个问题。当得知这样一个畸形编制的部队后,美国人的确非常轻蔑。
父亲写道,当时67师的装备在国内可算是佼佼者,但在美军眼里却成了笑话,借助商谈中国占领军的有关问题,盟军总部参谋部的上校科长柏奇故意带着迷惑不解的表情问他:“你们师的炮兵用了3种运动速度不相同的部队,使用3种射程不一样的火炮,你们的团长是怎么指挥的呢?你们的运输队也一样,汽车、马匹和人力又怎样能同时运用呢?”我父亲清楚美国人的用心,他不得不“编造”了一个堂皇的理由:“我们中国军队一般以营为作战单位,虽然3种火炮的射程、速度不同,但我们可以分割使用。运输方面也一样,我们的指挥官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不管情况怎么复杂都能运用自如。”
商谈的重要事情是汽车和薪饷问题。柏奇说美军有的是剩余物资,补充你们中国占领军没有任何问题。这让父亲很高兴,以为有眉目了。话锋一转,接下来谈炊事用的燃料问题,不料麻烦丛生。美国人却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做饭使用的燃料是木材,但根据规定,木材和柴火不能在日本征用或购买,必须全部从中国国内运来。父亲认为,军队在国内使用行军锅灶,到处都可以弄到柴火,现在到日本了,再使用木柴太原始,不雅观,也受到限制,于是他硬着头皮说,可以将此情况报告国内,建议将燃料改为煤炭。美国人说,煤炭也不能征用,因为日本是缺煤的,也必须从中国运去。
到此为止,父亲本来计划提出的中国占领军每天必需的蔬菜水果等问题,也就不提了。而对薪饷问题,柏奇说,盟军总部已经研究决定,美国方面可以代垫支付,但是必须记账,将来由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结算;而汽车,美国可以调拨剩余物资给中国占领军,原则上是作价调拨。
部队还没有出发,问题就来了一大堆,而且无法逐一落实解决。7月初,我父亲得到国内电报,中国占领军不到日本了。67师被投入了内战战场,1946年8月下旬在和栗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交战中被击溃。父亲回忆说,当时国内经济实力不济,本来十分荣耀的派出占领军的大事,因为纠结于生活开销等等问题,占领军进驻日本之事就搁浅了。遗憾啦!
儿童节当天,作家冰心买来好多冰激凌
蒋: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达日本的?
廖:国民政府后来颁布驻日代表团校级以上官员可以带家属到日本的规定,1946年11月,我和母亲跟其他代表团官员亲属一道飞赴日本。
我们乘坐的是C—47军用运输机。由于人多座位少,小娃娃没有座位。坐在我们旁边的是大作家冰心和她的小女儿吴宗黎(后改名为吴青),我在飞机上就跟吴宗黎熟悉了。她比我大一岁,活泼大方,我们在飞机上就成了玩伴。冰心赴日是因为丈夫吴文藻先生当时是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她个子瘦小而单薄,但很和蔼,很关心孩子。这也是战后中国第一位知名作家踏上日本的土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冰心第四次到日本,这一次去后,她和丈夫一直在日本待到1950年。
蒋:当时代表团的家属、小孩怎么生活呢?
廖:我是独子,母亲主要照顾我和父亲的生活。我们住在麻布区,虽然战争结束一年多了,由于遭受多次轰炸,东京市区仍然是一片狼藉,极度萧条。我印象很深的是,断垣残壁中,常常看到一些基本完好的铁质保险柜和家具,格外醒目,这样好质量的东西,在国内废墟里绝对见不到。代表团办公楼征用的是一栋三层楼房,据说过去是日本林业省的办公楼。楼上设了电台与国内联系,办公楼前有一个大操场,当中有一根大旗杆,中国宪兵每天进行升旗、降旗仪式和
换岗,很是神圣。我们的生活区域征用了当地一个官僚的别墅区,里面亭台楼阁,植物茂密,因为面积很大,就开辟出一部分作为学校。代表团有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成立了“中国驻日代表团附属子弟学校”,学校主要由冰心先生负责,部分家属本来就是教师出身,就出任老师教我们。学校分成小、中、大3个班,吴宗黎高我一个班,但平时经常往来。我当时称冰心为“吴伯母”。她当时没负责教学,不常在学校,但特意在1947、1948年和我们一起过了两次儿童节。当时的儿童节在4月4日,我特别记得其中一次,她给我们发了冰淇淋和糖果,那时候冰淇淋很罕见,特别稀奇,我们放开肚皮吃,真是高兴极了……
蒋:你们当时生活如何?
廖:代表团成员在日本的待遇比盟军低,但比国内高了不少。家父这个级别的官员,当时每人每月薪金有600多美金,这个标准按照汇率大大高于国内将官。官员夫人的待遇是丈夫的一半,小孩每人按父亲的四分之一发放。当时国内使用法币,贬值十分严重,这显得我们的待遇更高了。驻日代表团的每一个人,包括我,都有盟军发放的护照,有诸如免费乘车、看电影的特殊待遇。
我家的门牌编号是CMD11,吴青家是CMD9。我父亲使用的是一台美式军用吉普;吴文藻先生不会驾驶,特为他配备了一名司机,吴家的车是一辆“雪佛兰”轿车。我家当时就有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哦对了,我们根本不吃日本出产的东西,一是不习惯,二是从内心看不起。
当时日本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街头巷尾看到最多的是女人和小孩,蓬头垢面,乞丐一般,满眼凄惶之色,因为战争夺去了绝大多数男人的生命。他们每人每天只有4两口粮。又加上物资奇缺,日本人大多穿着拔掉了领章的黄色军服,因为绝大数男人都当过兵,看见盟国的军人走过来,他们都很自卑地低下头去,眼睛低垂;女人也是埋头躬腰迅速而无声走过。盟军士兵在街上扔下一个烟屁股,立刻有日本人去抢。一些美国兵看到日本人还穿军装,很是憎恶,一不高兴上去就飞起一脚,对方就像沙袋,不敢跑,只好站在那里干挨,而且一声不吭,不停鞠躬。美国兵酗酒强奸的事情经常发生,年轻女人为一点食品就委身于大兵的事情非常多……地摊上出卖的东西惊人便宜,我父亲就买了一台质量很好的德国蔡司相机,等于是白捡。父亲用它拍摄了很多日本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时期照相机和照片都被抄走了……我的印象里,当时的日本情况比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还要艰苦。
我每天痛打“小日本”
蒋:你在日本那两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廖:我们附属小学隔壁有一所日本小学,他们每天也要举行升旗仪式,奏乐、肃穆、敬礼……我们针锋相对,立即在学校修建了一根更高更大的旗杆,缝制的旗帜也更大。我们虽然学生少,仍然每天举行升旗仪式,高唱国歌。我们那时毕竟少不更事,过于简单地把民族仇恨化作具体行动,那就是下课之后,痛打隔壁学校的“小日本”。有些时候是单挑,有些时候是群殴,他们一般不敢还手。记得有几次闹得较大,打倒一大片,他们去找警察,日本警察就跑来乱叫一通,中国宪兵闻讯赶到,立即拔枪,宪兵是有权开枪的。日本人一见这个阵势,马上鞠躬、敬礼、赔不是,都灰溜溜地散了。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日本方面调整了他们的上下课时间……找不到人,我们就到街头去打。一天不打手就发痒……
蒋:你们平时也出去玩?廖:课余时间四处走,也没有什么危险。日本人一见衣着和气势,明白是中国人,就低头过去。我身上装有教室的粉笔,就在警察局墙头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一声不吭,待我们走了,再悄悄去擦掉。我们还到一些神社去游玩,那里也没有人看管,随便进出,我们也用粉笔写标语……
蒋:当时你家里一定宾客云集……廖:母亲苏荣辉是湖南湘潭人,擅长烹饪,四川菜和湖南菜都很拿手。当时家里经济状况较好,食物配给丰富,每到周末父母常常在家举行宴会,招待本组和代表团的单身汉。参与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当时没带家属去日本,独自与国际法庭的法
官们一起住在帝国酒店。他住的是一个套房,有办公间、会客厅和卧室。梅法官与国内的联系要经由驻日代表团,因此常常来代表团驻地。他平时住大酒店吃西餐,来代表团办事后和周末都常到我家来吃家乡菜。梅法官很健谈,每次他到我家做客,满屋谈笑风生。
印象很深的客人还有海军少校钟汉波,他经常穿一身白色挺阔的海军服。我们小朋友都喜欢和他玩,在他雪白的制服上留下很多“黑手印”,他也不以为忤。还有日本名流到我家来拜访,有时也参加家宴。日本客人常常称道母亲的厨艺,非常入品。父母知道当时日本家庭大多生活艰苦,有时特意分留一些食品让日本客人带回家去。我那时年幼,可惜没有记住这些人的姓名。
蒋:你离开日本时,有什么感受?廖:东京审判期间,父亲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成员有资格坐在贵宾席旁听。因此他和来自中国的首席大法官梅汝璈先生成了朋友。梅汝璈经常到我家作客,印象中很健谈,每次他来,屋里都是谈笑风生。2006 年9月,《东京大审判》在成都首映时,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还专程到成都拜谒我父亲……协助并参加东京大审判之后,1948年10月父亲奉命提前回国。回国后父亲反对内战,深知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干脆不去单位报到了,便举家悄然返回成都,最终脱离国民政府。家父日后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成为这方面的珍贵史料。我母亲病逝于1980年代,2007年4月20日家父去世,享年94岁。他生前很想念当年驻日代表团的同事,渴望祖国早日统一,渴望中日世代友好,不再重蹈内战、中日战争这两大历史浩劫。当年得知要回国了,我很高兴。临走当天上午我最后一次上街游逛,突然见到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冲上去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后一次痛打“小日本”。我知道,再不打,以后也许没有机会了。这一顿好打啊,酣畅淋漓,至今还记得!
记得我们当时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回国的。这艘海轮是上海—东京——旧金山航班,很多中国名人都曾乘坐这艘2万吨巨轮,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当年也是乘坐此轮归国的。离开日本前,我家两名日本女佣都恋恋不舍,洒泪告别。由于当时日本社会非常贫困,而我家享受盟军外交官待遇,父母不歧视她们,待她们友善,她们在我家服务收入比很多相似工作的亲友都高,因此很珍惜。她们年龄当时20多岁了,如果还健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阔别66年后与吴青见面
蒋:你父亲后来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情况怎样?
廖:家父精通日语、英语、德语等语种,1960年进入省图管理外文书库。“文革”中,他珍藏的关于东京大审判的图文资料被造反派抄走、销毁。他写出了《我任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官经历记》、《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见闻》、《常德会战与余程万》、《冈村宁次曾图谋入侵四川》、《“大川饭店事件”在南京解决的经过》、《不要忘记侵略战争带来的空前浩劫》等重要回忆文章。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他将右手手模留在了建川博物馆中国老兵手印广场上。后来我遵照父亲遗愿,将他那枚水晶印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2009年11月,这枚印章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蒋:你近年与当年在日本的同学联系过吗?
廖:听说他们一部分故亡,一部分留在美国。2013年,抗战史专家方军来成都采访我,通过他搭桥,我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吴青教授取得了联系。由方军安排,2014年3月6日,在北京眉山东坡酒楼,我终于与老同学吴青见面了。第一眼,我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我们的父母都去世了,我们也垂垂老也。中央电视台7频道拍摄了这一阔别66年的会面,让我感慨万端……
蒋:前不久,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索还中国文物,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掠夺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廖: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也将拉开民间索赔文物的序幕,我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正义事业。多年来,我尽其所能,恢复抗战真相、复原川军抗战事迹、为“成都大轰炸”正义诉讼案提供材料。日本要以史为鉴,知错必究,正视中日遗留的历史问题,遵守国际法准则,沿用国际先例,尽早归还中国文物,并对其无差别的“大轰炸”谢罪和赔偿。
【作家书架】作家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