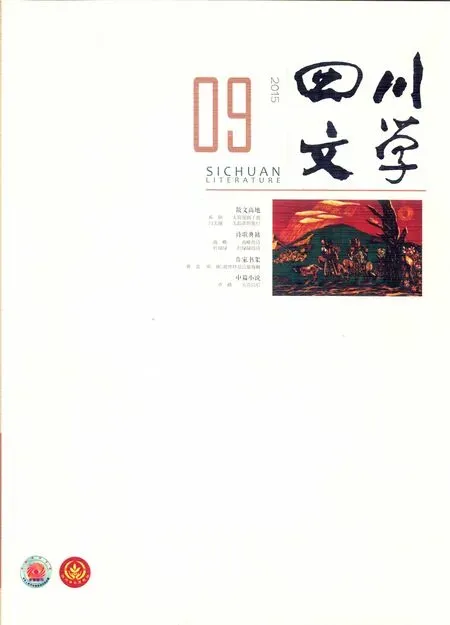唐朝的日头和人心
唐朝的日头和人心
我没有查阅过气象史资料,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唐朝的阳光比有文献记载以来任何其他历史时期的阳光都要烤人,仿佛越千年至今,仍然炎炎灼人。何以这么说呢?你想,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写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何以惟独唐朝诗人写出了?好像其他所有朝代的农民正午都不锄地,或锄地而不流汗,只有唐朝的农人例外。唐朝的农人正午不仅锄地,而且流汗,不仅流汗,而且还被诗人李绅看在眼里,不仅看在眼里,而且疼在心里,不仅疼在心里,而且发而为诗,写成千古名篇《悯农》。
不仅唐朝的日头比有文献记载以来的任何其他时代的都毒、都热、都烤人,唐朝的冬天似乎也比其他任何朝代的冬天要冷得多。不然的话,杜甫何以祈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何以梦想“万里裘”好使万民“俱不寒”?别的时代就没有寒士吗?就没有无衣无室的人吗?就没有诗人吗?我们怎么就很少见别的朝代的诗人“千间厦”、“万里裘”的祈祷和梦想呢?
是因为唐朝的日头太毒,所以诗人们才写出“汗滴禾下土”吗?是因为唐朝的秋风太狂、冬日太冷,所以杜甫、白居易才得以异想天开幻想广厦阔裘吗?气象史的资料无助于求证唐朝诗人的写作与气象的因果关系。其他朝代里农夫也要锄地,也要流汗,寒士穷人也无衣无室。之所以惟独唐朝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不在唐朝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而在于唐代文人诗家有一颗善良、善感、悲天悯人高出其他任何朝代一大截的皇皇人心!
自唐以后,中国人像江河的大浪回望源头一样频频举颈遥望唐朝。唐朝的确是值得我们民族回头望的一个伟大时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顶峰。唐朝并没有繁荣到庄稼人不用在正午锄地,贫寒者都有衣有房的程度。唐朝的农夫仍要锄地,锄地仍要流汗,寒士仍要被雨淋,穷人仍要受冻馁,可唐朝诗人伟大的人道情怀却空前绝后,历久不磨,至今仍然让人感到酷暑里的清凉和奇寒中的温暖。
不朽的唐朝,我向你遥拜!永恒的诗人啊,可有后乎?
几位来自河南农村的朋友在京小聚,偶然谈起“三年自然灾害”,不料竟引出各家的伤感往事。一位说:他一家六口人饿死四口,剩下的两个人,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另一位说:他家没有饿死直系亲 人。爷爷饭量大,饿得最厉害,全身浮肿,幸亏到三门峡水库工地大伯那里住了一阵子,才没有饿死。又一位说:他的直系亲人没有饿死的,旁系的有,一个十来岁的同曾祖父的堂兄就饿死了。还有一位说:他的邻居有饿死的。我们只顾倾诉,不料信阳光山县的一位朋友满眼泪光,说他家就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我奶奶就让我爹我俩吃了。奶奶饿得奄奄一息时,告诉我爹和我,她死了一定要我俩煮吃了她的尸首。自己不吃,别人知道了扒出来也是吃。奶奶断了气,我爹我俩就把奶奶煮煮吃了,剩下的骨头放到一个瓮里埋了。”这位朋友说,这么多年,这段伤心的往事他都压在舌头底下,不忍说出。
这次小聚已经过去些日子了,可是吃奶奶的故事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我的思索没有停止。我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人们要把这样的惨剧压在舌根下?
顾准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右派)劳动队是艰难的,比之农村,犹是天堂。”这里提到的农村,就是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