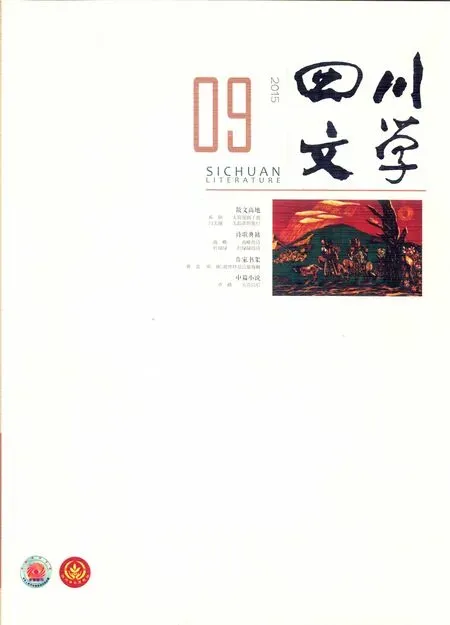乌为什么鸦会唱歌
○ 陶群力
当有些谜出现,如果你做类似于哲学的思考,问题将趋于复杂。
——题记
1
现在,我行走在江南的一个古镇上。确切地说,我是站在那个叫鸟啼儿街的夕阳中。阳光从房屋的背面,从树梢上穿过,眼前是细碎的、斑驳的影子——有点晃眼——我盯着落日,盯着眼前的景象,费力地寻找往昔鸟啼儿街的那些片断。可惜,我面前的高楼和街道,与我历史记忆中的老街已相去甚远,还好,临河的那些老屋依然较好地保持着原貌。肥猪在我的身边,迷惑地望着我那双迷茫、空洞的眼睛。
那年,我们鸟啼儿街又出了件怪事。毛头捉到了一只会说话的乌鸦。
夏末的傍晚,我端着洋铁碗坐在院子的门槛上吃饭。饭还没扒完,便见许多人急匆匆地从弄堂深处走过,神色怪异,嘀嘀咕咕的。“喂,你们去哪?——”我好奇地朝他们的背影喊。那些人脸皮都不抬,只顾走。
“毛头抓了只会说话的乌鸦!”走到弄堂口,有小孩回转头亢奋地连说了两句。我急忙回家放下饭碗,哧溜拐出了巷子。赶到毛头家的时候,一个个墨鱼似的脑袋像一张大网早将毛头家围起。我想挤到前面——我的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早已是铜墙铁壁。——我爬上了一棵梧桐树。
“毛头!毛头——”我摇动着我的小臂,我摇晃着树枝。
毛头一点反应都没。毛头家的大门外挂着一只鸟笼,毛头将鸟笼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毛头从脖子上取下红领巾,双手两个指头捏住两角,往外朝上抖了抖,里外翻转两下,像西班牙斗士似地对着乌鸦说,开始——。
乌鸦脖颈伸了伸——
不低头,不后退,
不许泪水腮边挂……
乌鸦喉结蠕动着。忽然停了下来,眼球望上翻去,呆呆的,像是在回忆唱词。
“操!乌鸦他妈的还会红灯记?”有人回过神来,盯着毛头说。“接着唱啊——笨蛋!”有人开始吹哨子,扔小石子了。
绍兴奶奶眯起眼把个红头拐棍举得老高老高。绍兴奶奶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拿着拐杖儿,戳戳乌鸦翅膀说,咦,奇怪搭煞,再来古——乌鸦!
“我有罪——,罪该万死——”,乌鸦开口叫了两声,拍拍翅膀。
人们又开始骚动、沸腾起来。“咦!这个乌鸦说话怎么像毛头老子的腔调?怪气死了。”人群中有人开始议论。
“出去,都滚出去。”毛头的脸色倏地变得靛青,眼珠子射出两道火光。
绍兴奶奶咕噜咕噜地,嘴角上泛着白沫泡泡;绍兴奶奶摸摸毛头的脑壳,说,“毒头西死!”,毛头啊——,连奶奶看看都不行?我看见绍兴奶奶的嘴巴嘟得老高,很生气的样子。
我不是“毒头”。毛头厌恶地把绍兴奶奶的手搡开,白了她几眼。
绍兴奶奶鼻孔“哼”了一声,“切力煞来……切力煞来,”绍兴奶奶喘着气,用那双鸡爪子似的裸着青筋的手捶捶膝盖骨。大家极不情愿地四散开去。绍兴奶奶慢吞吞地挪着那双小脚。一歇歇,又回头说,毛头啊,记得,不要忘了给乌鸦喝点水,吃点东西哦。
“我有罪……我交代……”乌鸦又叫了起来,态度诚恳,声调拖得很长,嗓音沙哑,带着哭腔。
我问肥猪,你听到乌鸦的声音了吗?肥猪朝我看看,说什么?乌鸦?哪来的乌鸦声,肥猪说。肥猪的那只白眼球从戴着的墨镜里透出一丝混沌的白光。“你再仔细听听,那声音好像就是毛头家那只乌鸦发出来的。”我提醒肥猪,诺,——四十年前的那只乌鸦。肥猪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寻找。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晚上,这条叫鸟啼儿街百脚虫巷聚集在一堆厢的人是“文革”以来最为壮观的一次“大串联”。这得感谢那只会说话的“乌鸦”,也得归功于那个夜晚的明月啊;月光将清辉洒满巷道,有几颗流星划过。大家做着猜测和想象。关于毛头家的那只乌鸦的来历,鸟鸣儿街的人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我不细说,我想,也没有必要深究。我只是想把毛头一家,以及一些故事告诉大家。那个夜晚,对于鸟啼儿街的孩子们来说不啻是一次比赫鲁晓夫下台还要让人感到兴奋的事件。
2
月儿朗朗。月光从树梢上仿佛水一般倾泻下来,人影憧憧。一帮小孩子钻到大人堆里,好奇,迷茫地昂起脑袋瓜子,听着大人们神秘叨叨地议论着“乌鸦”。提鱼儿兜巷的那个白眉毛、山羊胡须挂到胸前的老伯嘴刁黄铜嘴的旱烟管喷着一圈一圈的白雾,类似说书人的做派吸一口烟,眯起那双“虾米眼”,吐着云雾般的烟雾,捋着白胡须说,“乌鸦”说话并不稀罕——他小时候听老人说过,说是乌鸦是因为在吃死人的舌头的时候,死人忽然张嘴咬了乌鸦,开口说话,乌鸦胆儿虽大,魂灵也总归出了窍,受了惊吓;冤鬼把他的委屈告诉了乌鸦后,乌鸦就记住了,就会说话。
“诺,诺,日本人来的头二年那里的坟墩就出过会说话的乌鸦。”老伯用那杆烟枪指着远处永福桥西南面的吴家浜说。
那杆烟管子一明一灭。吴家浜那闪着幽幽绿光的坟墩仿佛乘着比水还深的雾气,袅袅娜娜向我走来,——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地连成一片。我外婆家就在那儿——我小的时候哭闹,外婆就说,小句,扔你坟墩头去!
“毛头他老子果真死了?”我迷惑地问。
老伯咧咧嘴不答话,用烟管敲敲鞋帮,手捋白胡须。走,去毛头家问问。我心说。
毛头家里黑咕隆咚。毛头家里也没啥吃的,蟑螂却出奇的多,蟑螂热得像无赖似的趴着;几只厚脸皮的老鼠叽吱叽吱呲着大龅牙露着绿幽幽的光,其中一只竟然蹿到我的脚背上。我啐口痰骂道:这些狗畜畜也欺负人家屋里厢没大人,真是!我看到毛头听了这话,后脑壳顶上的头发好像飘了一下,有几根头发像鬃毛一样奓开——毛头的头上有四个螺旋——我们小人家听大人说过,长三个旋的比一般人聪明两倍。毛头为啥却有点毒头兮兮的?厨房后门就是一条小河,月光好像在走动,河面上星星点点;有波浪涌起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堂屋里的乌鸦又叫了起来,我们听得分明——“我有罪,罪该万死!”我们坐在埠头的石阶上,光着脚丫子沁在河里,我的汗毛竖了起来,背脊冰冷,裤子也被吓出来的尿给弄得湿答答的。还好没有谁注意到我的窘状。
毛头迷迷瞪瞪地张开眼,坐起朝屋子的角落里望望。屋子黑黢黢。屋角一张蜘蛛网好像发出了一声冷笑,闪了下亮光。毛头侧耳,觉得有嘤嘤的声音从屋外传来。外头好像有人在哭。毛头心说。毛头想,三更半夜的,哪来的人?窗棂上有雨点啪嗒啪嗒的声响,风的尖叫声一阵紧过一阵,仿佛是谁发出的呻吟和哀号。毛头的心咚咚地跳。望着窗外黑魆魆的夜空,听着沙沙的雨点拍打声,毛头的心一颤。毛头把被头提了提蒙住脑袋。毛头说,阿爸你不要吓我呀——快要哭出声来了。毛头恍惚着,觉得这个黑暗中的房子像是在大海里的忽上忽下、飘摇不定的小船,被高高的浪头抛起——毛头听到了自己的救命声。毛头支棱着耳朵听了一会,夜好像没先前黑了;再也没听到哭声,外面的雨也静了下来。风也住了。毛头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黎明时分,临河的窗口下有一阵窸窸窣窣、噗噗簌簌的响动传来,毛头一个激灵跃起。淡蓝色的天空清澈透明,小河上笼罩着白色的雾霭,像仙女曼妙的云袖挥洒飘荡着。毛头发现窗下斜旁的石埠台阶上有一只乌黑乌黑的鸟在哆嗦着翅膀……毛头说到这儿,抬头望了望深蓝的天空,说困了;我正听得入迷,问后来呢?我摁住毛头肩膀子不让起身。
“诺——”,就是堂屋里的那只乌鸦,是我抱回家的。毛头打着哈欠说。
毛头说了一句让我大吃一惊的话,毛头把嘴伸到我耳朵边,说,知道吗,乌鸦怎么会说话?我教的!(毛头为啥要让乌鸦学说话呢?毛头真的很聪明啊,不过,这是我多年后思考得出的结论),——“乌鸦——是我教它的。”毛头又说了一句。
毛头的眼睛在黑夜中放出很神秘很深沉的亮光。这个夜晚,我稀里糊涂地回到家里的时候,还在努力地回忆毛头的那双让我捉摸不透的乌漆墨黑的、阴郁地闪烁着荧光的眼睛。
毛头家的那只会说话的乌鸦占据着我大脑的所有空间。我失眠了。
3
立秋过了,大地仿佛还在燃烧。我们鸟啼儿街像点着无数个火炉,空气里充满了树木、枯草、泥土的焦味;青石板上反射着白金的刺目的光;灰色的屋檐上冒着白烟,几只麻雀儿刚落下就拍着翅膀,叽叽唤了两声便飞了。
街上有行人走过。那些行人的步调我至今还难以用一种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有的人低着头,垂头丧气的;有的像是踏着行进曲,能清晰地听见青石板上的小石子被踩出的咔咔声(每人的胸前都挂着毛主席的红像章)。肥猪的爸爸骑着那辆“永久”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我看他回头朝我们看了一眼。一定是看毛头的,我心想,他眼里耀着像是对自己孩子慈爱的光环。这亮光像是从深邃无边的黑洞里闪了一下。大人们都去参加单位或街道的政治学习了。
树木、低矮的房子被落日拉出长长的暗影,有疲惫的蝉鸣声密密匝匝地传来,听去很辽远。
巷子疲惫地喘息着。晚饭后我们聚拢在毛头家的门口——大家都想让乌鸦表演说话——毛头似乎有些不太情愿——他把鸟笼子提到门前的一棵樟树下。我们对着乌鸦嚷嚷,“说话呀,快,说话!”乌鸦白了我们一眼,拉了几颗灰白的粪便,闭目养神一般地低垂着脑壳。大家心有不甘,我们便对着乌鸦说,“我有罪——,我该死——”乌鸦一副死相,转了个身,又拉下几粒鼠屎似的小粪。
“快让乌鸦说话!毛头,”肥猪命令道。肥猪敲了毛头一个头颈板。肥猪是我们的老大,在鸟啼儿街,在我们看来,他比杨子荣还要威风。我们曾经天真地想过:肥猪的号召力和威望是应该可以去北京参加国庆联欢会,是应该受到伟大领袖接见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就把他给忘记了呢?
“乌鸦喉咙哑了,”毛头委屈地说。毛头摸着脑袋,斜眼看着肥猪,说乌鸦昨天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毛头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毛头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像山涧溪水般响着。
“赤佬——算啦,算啦……来玩官兵和强盗,”肥猪说。肥猪不耐烦了。
肥猪开始实施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的游戏与外地的孩子玩的花样不太相同,游戏多少带有点反抗压迫的内涵:肥猪竖起大拇指对着自己的鼻尖说,我来当土匪老大;他说,让官兵被我们土匪捉才对。他选土匪的原则是,长得要人高马大,脸上最好带有邪气的那种;把一些病怏怏的、女孩子、看去弱不禁风的都划归到官兵行列里。肥猪那个时候已经是初中毕业生了(留级一次),他的嘴唇、两腮上长着一圈密浓浓的黑黑的茸毛。一点不像土匪——有个跛脚女孩提出异议,说,你不该是土匪老大,你是英雄杨子荣,或者洪常青!女孩崇拜中带着柔情;洪常青有胡子么?——你猜,那跛脚女孩是谁?是我的五姐爱华啊。她旁若无人漠视我们的存在的神态,让我至少一个多月没和她说话。爱华怎么也崇拜肥猪呢?我为这个问题曾经想了许多天。土匪们拿着木棍、弹弓;肥猪一声开始,官兵四下鼠蹿,凡是官兵被土匪的棍棒、弹弓打着的就算是胜利。天空里没有一丝风,没有一颗星星;街上散发着恶浊的从河沟里泛起的腥臭。我们的狼哭鬼叫声仿佛使整个鸟啼儿街变成了野兽们的一个落难场所。
我们靠在大樟树下,东倒西歪的。毛头家的乌鸦咕噜了一声,我们吓得跳将起来;任凭我们怎么逗乌鸦,乌鸦就是不开口。在许多日子之后,一个刮着大风的幽暗的夜晚,我用早些时父亲教我的方法诱捕获了一只乌鸦,我想起当时我撬开毛头那只乌鸦的嘴巴,想从中发现乌鸦唱歌的“秘密”。我仔细地查看过,我捕获的那只乌鸦与毛头的那只好像没什么区别(我多么想,我的这只乌鸦也能唱歌啊,为啥就不能唱歌呢?)。多年后,当我坐在父亲的坟头旁,有一群乌鸦唱着歌从我头顶盘旋飞过——歌若黑色的羽毛纷纷坠入——我恍惚着,一种令人痉挛的恐惧蔓延开来,我无法摆脱这奇异而凌乱的镜像。
“拿水来……”肥猪说。
“做啥?”毛头眨眨眼问。
“啰嗦,快去……”
毛头从屋后面的河里取来一瓷盆水。“把鸟笼打开。”肥猪脸上喷着热气,捋了一把汗说。毛头的眼睛盯着肥猪,毛头端水的手在打颤,我的心就一凛。肥猪把手伸进鸟笼,把那只乌鸦从鸟笼里捉了出来。肥猪把乌鸦的脑袋往脸盘里摁,摁,摁,死命地摁!
“不是没吃东西吗。不是喉咙哑了吗……”
“喝!你个死乌鸦——”肥猪脸上的肌肉无限膨胀。毛头朝肥猪张开嘴巴(毛头的嘴巴尖尖的,有两挂眼泪),朝肥猪扑去。“扑通”一声响,毛头跪在了地上。“不要——”毛头的声音像雷电在空中打了个闪电。
街上开来一辆大卡车。大客车在毛头家门口一个急刹车——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那声音,听上去比乌鸦的怪叫还恐怖,刺破了鸟啼儿街的屋檐,我看到有瓦片被震落下来。车上跳下几个戴红臂章的年轻人。有个戴绿军帽的人,两只指头夹着香烟,另外一只手上提着一条黄色的皮带,皮带头老大,老大,闪着“革命”的光芒。毛头的爸爸被拇指粗的麻绳五花大绑地从屋里拖了出来。我眼前到处是水,闪耀着像一把把刺刀的寒光。水从天上,从毛头爸爸的脸上流淌开去。忽然想起,去年的夏夜,毛头爸爸被押解出来的那刻,下佝的鼻尖上豆大的汗珠和惶恐的眼神——多么像一只被猎人射杀的乌鸦啊。毛头的爸爸被闻讯赶来的革命群众围着,刚好有几人提着水桶路过,那些水就如同革命的“洪流”将毛头的爸爸葬身在红色的浪涛中。现在我脑子是一片混沌——在全校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我再次看到了毛头的爸爸——我们的老师——这个反革命分子,曾经用恶毒语言攻击“林副统帅”,说林彪同志的眉毛像他一样不雅,有点像乌鸦的眉毛,嘴巴也是尖尖的,如果当接班人,标准像是个问题。
据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当毛头的爸爸被押解上永福桥的时刻,毛头的爸爸纵身跃入桥下。有人说,那天武装押解人员朝河里开了好多枪,第二天,河边的水草上还有被血染红的痕迹。我的眼睛里,耳朵里到处是水,白金色的,金黄色的,红色的;肥猪手中高举着的那个铜盆耀着金黄色的光,把肥猪那张脸映个通红;肥猪手里的脸盆仿佛李玉和高举的红灯。
“不要……”毛头又唤了一声。毛头几乎要哭出来了,他的眼泪像河里的水漫出来了。
4
毛头真够窝囊。肥猪实在是过分了,这个死肥猪。还是让我回过头来啰嗦几句吧。乌鸦真的是嗓子冒烟了呀,肚子都瘪了呀。这个下午,我一直和毛头坐在他家屋后小河的石阶上(水漫到我们的腰部)。河对岸是一片开阔的农田。稻田里东一处、西一处地躺着一些收割后的稻草跺;有的不知为啥还没收割,在烈日的照耀下耷拉着头,腰板都快要弯断了。毛头望着远处的稻田,或者是那更为苍茫辽阔的天空,眼睛眯缝着;嘴里不断咀嚼着,我想毛头一定是饿了。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个罪恶的念头。我说毛头我们凫过河如何?做啥?毛头回转头问。我的脸一下红了,我说游过河去弄点“武器”。
“武器?”毛头张开眼有些疑惑。
“稻谷呀——”我捂住嘴巴差点要笑出来,我说,“这不是革命的‘武器’吗?”
毛头脸色刷地一下白了,比小兔子的毛毛还白。毛头吓得晃到了河里。……在我的倡议下,我们从毛头家的小阁楼里拿出一个结满了蜘蛛网的渔网。我们打到了几条猫鱼。我和毛头打开火灶,我们把几条猫鱼开膛破肚后想来个油炸加红烧——毛头说,他已经很久没吃过油炸的东西了,毛头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就有了泪水。我说,毛头别哭呀,我晚上回家去拿红烧肉给你吃。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我家哪来的红烧肉呢?
毛头家的菜柜子里连个鬼影都没有。后来,我们就学绍兴奶奶的方法——白切(绍兴奶奶烧螺蛳就放一点点生姜和酱油的)。油炸红烧鱼当然不属于我们。锅盖上烟雾缭绕,噗噗的响声,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即将采摘胜利的果实了!你们一定会想到结果的,他妈的猫鱼最后是乌鸦都没看它一眼。乌鸦难道也像革命烈士那样?
毛头一定是和乌鸦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毛头说,就唱一支歌吧。毛头说这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毛头眼睛亮了一下,汪着水,充满爱怜;声音是恳切的。乌鸦没辜负我们,它在我们的殷殷期盼中毕竟还是唱了一支动听的歌曲(只是片断)——“唱支山歌给党听”。乌鸦唱得投入;我听得痴迷。
肥猪高举着乌鸦。他手里的黑乎乎的乌鸦,仿佛是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冒着狼烟。
5
太阳升起,天井里传来的声音如早起的麻雀的啼鸣,清脆,热闹。东方红的歌曲播放的时候我就醒了。我透过敞开的小窗,盯着刘麻子看。刘麻子洗漱完毕,挺直了腰板,像一位将要去会见外国元首似地把他的那件丈青色的中山装领子上的风纪扣扣上;粗短脖子显得愈发粗短,有点像我家养的那只讨厌的、翅膀上长着黑、红色长羽毛的喜欢抢食吃的“矮昂颈”。
刘麻子家原来不住我们的这个院子里。为了把乌鸦这个故事延续下去,我不得不费一些笔墨。这个刘麻子,不对,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年代,我还不敢这样放肆。
“兔子”,他用大巴掌示意,“你看到毛头家那只乌鸦说话了?”那褐色脸上的麻子闪着光,关切地问道。
“我……没……我没看到,”我低着头不敢看刘麻子,我有点儿紧张地说。
我说,那只乌鸦讲话我们听不懂的,是瞎猜猜的。我心想:你刘麻子还有脸上毛头家么?——刘麻子家早几年也住百脚虫巷,与毛头家算是街坊邻居。刘麻子家搬到我们这柳翠儿巷,是因为出了一桩让刘麻子难堪的事件。
那个空气污浊、闷热的下午,镇里的戏班子正在排练一出越剧《十八相送》,这位镇长(“文革”后,大家喊他主任)大人悄悄坐在下面的长条骨板凳上,出神地看着——那个扮相俊美、风流倜傥,动作舒坦流畅的小生——毛头姆妈的缠绵悱恻的、舒展洒脱的身段,步态。不料,一个荡气回肠的、嘹亮的哨声里夹带着一股混浊的气体呼啸而起,舞台上下一下子乱哄哄的,大家好像在寻找策源地。刘镇长站了起来,说,“同志们(他说的话镇上人听去像是说,兔子们),不好意思勒……我这个人就这个样,是个大老粗,——很粗,很粗的……——大家乐得捂住肚子笑,只有毛头的姆妈(那个梁山伯的扮演者)没笑。卸了妆,刘镇长方才认出这个女子是同个巷子里的那个人们都唤她小玉的毛头的姆妈。他紧握毛头姆妈的手,说,唱得好啊——小玉同志。绍兴奶奶说,刘麻子就是那天起被毛头姆妈把魂儿给勾去的。
水池里的水溢满开来,在青砖上跳跃着。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刘麻子的老婆用那莲藕般肥壮雪白的大手仿佛像老鹰叼小鸡那样迅疾凶猛地伸向刘麻子裤裆的那个镜头——刘麻子两腿间的那个蛋蛋哧地一声炸响,一道金黄色的液体如水花飞溅。
我偷偷地瞄了刘麻子一眼,露出不怀好意的奸笑。我想起绍兴奶奶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嘴角上黏着饭粒米子招摇地一抖一抖的,绍兴奶奶咧开的向下弯曲的嘴角似乎是带着丰富的含义朝我们这样笑了几次。
6
我斜挎破旧、发白的黄帆布书包走出院子。
毛头在弄堂左边的拐角处暗灰色的墙墩旁扯着嗓子喊我。到了院子门口,我回头望了一眼刘麻子,意思是,毛头来了,你可以问他的呀。刘麻子推着那辆轮轱辘发亮的永久牌自行车跨在大院门槛上。走出院子老远了,我又诡秘地回头笑了笑。我和毛头走过绍兴奶奶家门口的时候,绍兴奶奶颠着小脚手里挽着个小竹篮筐,喊住毛头说,毛头,早粥切过商呒有?毛头摇摇头,又点点头。
“索西?”绍兴奶奶说。绍兴奶奶从竹篮里拿出几只富强粉馒头,说,吃了去有力道。
“夺去。”绍兴奶奶命令的口吻里带着一种请求,她把馒头塞到毛头手里。
毛头的眉毛跳了几下;毛头的眼里汪着一包水。我记忆的相片里永远保存着这样一个镜头——秋天古老的小巷——太阳在毛头的脸上就像刷上一层淡黄色的水彩,背景是青石板、破旧的木屋。毛头鼻子孔儿翕动着,眼睛红红的盯着脚上的那双黄色解放鞋。胶鞋开了个小口子。绍兴奶奶叹口气,说,梅干菜蒸肉晚上吃。听到佛?毛头点点脑袋,说谢谢绍兴奶奶。一股诱人的香味在巷子里蔓延。肥猪不知什么时候已躲在我们身后,闪了出来。胖脸上堆着一脸的坏笑,说,喔唷,绍兴奶奶真叫绍兴奶奶,绍兴奶奶你蛮心疼毛头的嘛,啥晨光也给我家来碗梅干菜蒸肉?我看到毛头的腮帮哆嗦了一下。
“听讲,绍兴奶奶要招毛头姆妈做媳妇?”肥猪嘴里弄出吧唧吧唧的声音,“难怪——大方来——见你最近手脚灵光来西,老跑毛头家送东西吃。”
“造话!”绍兴奶奶歪憋着脖子呸了口痰吐水。
我幻想着绍兴奶奶颠着“粽子”脚,提着用草纸包、红带子扎的绍兴香糕走向毛头家的路上。乓铛——那只盛梅干菜蒸肥肉的大瓷碗在青砖上跳着舞蹈,梅干菜黑红色的浓烈的汤汁像污水般蔓延开来。我回过神来,毛头的影子在巷口那株桂花树下闪了下便无影了。绍兴奶奶眼里是愤怒悲苍的目光。绍兴奶奶气鼓鼓地瘪着小嘴。肥猪伸出带黑毛的猪手,捏了捏鼻子,擤出一长串“面条”。他一定是吃了狗屎,说,有句老话“师爷出绍兴,憨子在东北”——肥猪哪里是在赞叹绍兴人的聪明?话里处处是讥笑,讽刺,难道他与绍兴奶奶有着深仇大恨?
肥猪打着响指,头发一甩,走了。后来,当毛头姆妈被绍兴奶奶那个跷拐儿大块头儿子用自行车驮来柳翠儿巷的时候,我才想起了肥猪的那句话,想起肥猪留给我们那个具有预言性的狡黠的微笑。不过那是后话。到了学校,毛头始终没有露面。
我坐在课堂里,眼睛一直盯着教室的门;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冷冰冰的教室里被涂抹上一层刺眼的白光。白光在我眼前游来荡去。我眨眨眼,用小手搓,我的眼被白色之光扎着,我迷迷糊糊起来——毛头走在我的前头,他穿着簇新的卡其布蓝色的斜领子罩衫,肩头上挎着写有“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绿色书包,他的头发像一根根钢针立起,神气地昂首挺胸走在我前面……咦,我怎么听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好像从辽远的地方传来,那声音凄楚,哀怨,像毛头捉到的那只乌鸦。我的心突突地跳。一个穿深灰色咔叽长衫的高个子立在面前——啊,是毛头的爸爸。精瘦瘦的细个儿,脸颊深深凹陷着,狭长的面孔显得枯黄,苍老,憔悴,满脸的胡茬子(毛头爸爸以前的脸上没那种让我崇拜的胡须),两道剑眉横立,如两把寒剑,眼珠子突兀地往外睁着,嘴向下佝,蓬乱花白的头发披散开来。我吓蒙了——毛头的爸爸竟笑了起来——凄苦地、悲凉地咧着嘴。我大叫起来,毛头——,快来,快来——你爸爸在这。许多双眼睛朝我射来,哪里来的毛头?——学校楼顶上的大喇叭响了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喇叭里传出动听的男女生合唱,优美高昂的、豪情万丈的旋律在校园的上空如雄鹰盘旋着。原来我做了个梦。学校大喇叭每天都要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来段革命歌曲或播放革命语录。毛头究竟会在哪儿呢?
7
夜色渐渐浓厚。街道对面的高楼里灯火亮了起来。灯光照耀下的老街有了现代都市的情调。我将目光再次凝视天空,天空中那些乌鸦呢?我问肥猪,说你前面没看到乌鸦?肥猪给我一个头颈板,说,你气我啊。我大笑。肥猪那只“独眼龙”在黑夜里闪着浑浊的白光。看去倒是像在他眼里画的一个空心句号。肥猪说,你个兔子,忘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自从那个事件发生后,肥猪每回看到天上有飞行物呼啸而过,就会双手捂住眼睛,嘴里不停地“乌鸦,乌鸦”狂叫。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必然?我最后一次见到毛头的时候,毛头坐在永福桥的栏杆上。那时,我已是鸟啼儿街朝晖中学的一名初中生了。晚霞照在毛头的身上,远远望去,毛头仿佛带着一顶金色的无冕皇冠。一轮火红的圆球在石桥下的河水中放出万道金光;河水被染得通红,摇晃的河水把毛头搅得碎片一般。我喊了几声毛头,毛头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他的眼睛比河水还要迷乱。低着头,喉咙上下蠕动,反复念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声音形同“乌鸦”。毛头疯了吗?他血红的眼里映出老街迷乱的天空。秋天被剪得苍凉,空旷。
学校放学回家。一路上我的脑袋被毛头的影子盘踞着。路过毛头家,我张望了一下,毛头家的门上的锁都生锈了。毛头啊,你在哪里?听人说,在吴家浜见过毛头,毛头一到夜里就在那片坟墩头转来转去;也有人说,毛头说过,他阿爸没死,一定是在大运河的某个地方等着他。公共厕所外有许多人热烈地议论着;两辆摩托风一般飞驰而来。车上下来的那个人戴着白色大盖帽,绷紧着脸。肥猪两脚一并,“啪”的一个敬礼,像迎接解放大军那样带那人进了厕所。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心一凛。就看见大盖帽用火钳夹着一个红塑料的小本本出来,啊——,是红宝书!肥猪几天后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知道吗,新动向?”肥猪吐掉嘴里的烟头,得意的目光扫视着我们。
“啥叫新动向?”我那个缺根弦的跛脚姐姐爱华怔怔地盯着肥猪问道。
肥猪说:“毛头就是新动向!”
肥猪说,大盖帽说了——一定要追查到底,不管毛头跑到天涯海角。我吓坏了,担心真的是毛头干的。要杀头的呀。走,肥猪起身走向毛头家。肥猪翻进了毛头家的墙头。肥猪的大手卡住乌鸦——乌鸦好像已经知道他的下场似的,流着眼泪。肥猪给了乌鸦几个耳光,说,老子吃了你。肥猪开始拔毛了。乌鸦的毛在空中飘起,飘啊飘,飘啊飘。“操你个肥猪。”我在心里想,总有一天要修理你。我责怪起我的几个姐姐为啥不找男朋友呢。否则。哼!——几天后,一个小学生哭哭啼啼地来到派出所。据说,小学生在派出所的大门外呆了一个下午——一直到日落西山;小学生是跪在地上等民警叔叔出来后,哭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原委。原来是个毛选积极分子。还是再来说说肥猪的这只“独眼龙”吧。我不自觉地朝肥猪望了一眼——
鸟啼儿街的小伢儿最开心的就是看免费电影了。星星还没出来,许多孩子、老人已用长条板凳抢占了最佳“制高点”。那天,我和五姐的口袋里都装着“唐生记”南瓜子。肥猪过来,手掌摊开,爱华姐姐身子哆嗦了一阵,翻开口袋;肥猪很满意。银幕上一道雪亮光柱把黑夜照出一个很深的窟窿,李铁梅把那盏红灯高高举着。忽然,上空传来嗡嗡嗡嗡的声音;有一群黑压压的飞行物从我们头顶掠过。开始我们也没在意;我们继续盯着铁梅。几分钟后,嗡嗡嗡嗡的声音再次传来,比先前更响。
“敌机来啦——”有人慌乱地喊道。一架“飞机”俯冲下来。
“啊——”肥猪惨叫了一声。露天广场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我跑出老远后,听到露天广场的银幕里传来一阵枪声。李玉和壮烈了。爱华姐姐那个晚上,被我母亲一顿暴打——她的白球鞋少了一只。
“嘎的,嘎的。”爱华边哭边说。她一定是被“飞机”给晕昏头了。
晚上,我梦到了毛头。毛头的身边围着好多好多的乌鸦。毛头用赞许的目光巡视着乌鸦,说,“革命自有后来人。”难道,那只会说话的乌鸦真的如毛头所说的,是一只乌鸦王?不过,在第二天,医院住进了许多跌破头皮、摔断腿脚、磕破嘴巴的老人和孩子却是真的。这个晚上事情出得蹊跷。难道这里藏有什么玄机,抑或是一种暗示?母亲早上把稀粥端到我的床上的时候摸着我发烫的额头说,你又做恶梦了?“梦?什么梦?”我迷迷糊糊地问。母亲摇头叹口气,说你昨晚嘴里老是说什么“乌鸦为什么会唱歌”。“哦,”我翻了个身子。“乌鸦”像一个无法甩掉的尾巴紧随着我的童年。不久,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了农村(就是前面我提及过的吴家浜)。一身布衣的父亲,倒是不介意在乡下当老师,不过,父亲虽说被贬到村里当老师,实质上,他教书的时间极为有限,有时候,课上到一半,也常会被一些人押解到公社接受各种形式的批斗和检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雨夜,父亲被人抬回来的时候,已不能说话,他拉着母亲、我的手(大姐那个时候已经去了内蒙建设兵团支边),想说什么,母亲蹲下身子凑到父亲嘴旁,……几个姐姐早已哭成了泪人——我没听清父亲说什么。公社里的人说,父亲是畏罪自杀。母亲给父亲入殓前擦洗身子时,我看到父亲的身上到处是淤血和肿块。后来,父亲就被葬在吴家浜东南的那片坟墩里。许多次,我放学路过那片坟墓,总会下意识地看,是否有乌鸦;夜里,我老是做梦,梦见乌鸦啊啊啊,啊啊啊地叫着。可我总听不清,是唱歌吗?它们唱着什么?——有次,我发着高烧,说着胡话,我看见乌鸦在父亲的坟墩上飞起,降落,又飞起,降落,使劲地啄着坟上的青草,这样下去且不要把父亲的坟墓给捣毁?不要!不要!我大声地喊。那些乌鸦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乌鸦,把那些乌鸦引向别处——我像唱歌那样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8
我在一本《老街记忆》的书中,曾读到这样一段话:我少年时代居住的老街,紧靠着大运河;大运河的水日夜流淌着,有时夜里听去,如同母亲的低语,像是一首摇篮曲;有时,门前摇过的乌篷船在半夜里,那吱嘎吱嘎声仿佛像乌鸦般的呜咽声。那个年代,老街常常出怪事,我养过一只乌鸦,那只乌鸦对于老街的人来说也是一件怪事。在另外一个章节,作者提到,我曾经在一个麻子叔叔的庇荫下,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我看后,一直以为,书中记录的那些故事,就是鸟啼儿街所发生的故事。作者在自序中说,自从离开老街,他的耳朵渐渐地失去了听觉,以至于完全失聪。他说,这样不是更好吗?世上繁杂的声音于我何用?现在,我又一次地打量着肥猪,想想,有些好笑——肥猪自从被乌鸦啄去了一颗眼珠,倒是逃避了下放农村。后来,还和我那个跛脚姐姐爱华搞上了对象。我想,也许这是得益于乌鸦的缘故吧,肥猪才一门心思地开着小小的一爿杂货店,才有了今天这份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