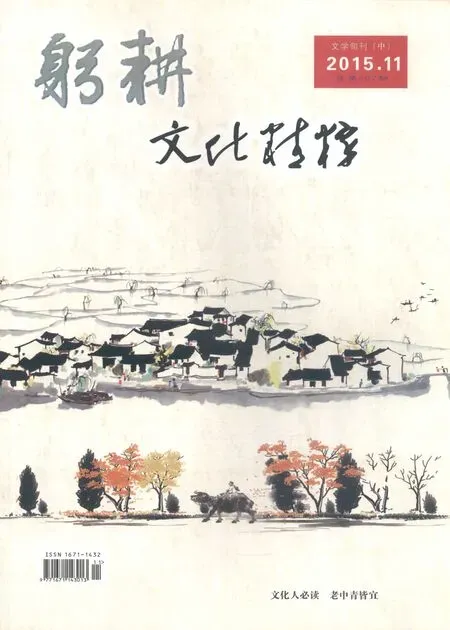秋风中,那间飘摇的草堂
◆ 宋 羽
秋风中,那间飘摇的草堂
◆ 宋 羽
诗人冯至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就是那一座孱弱的草堂,孤独地坐落在诗的意象里,一坐已有千年。它的轮廓像游移的烛光,像黯淡的背影,让人担心它会在一阵秋风过后再一次坍圮和消失……
1
关于杜甫的形象,我只能通过那些枯瘦、忧愁、无助和工整的诗句去揣摩。和他笔下长长短短而又规规矩矩的诗句一样,他的形象,大约亦是枯瘦、忧愁、无助和工整的样子吧。就像秋风中的那间飘摇的草堂——枯瘦的茅草、忧愁的呼号,终于无助地倾塌,工整的茅屋在沉沉暮色里写下满地凌乱多舛的人生。
杜甫的人生是一张地图,他的地图是黄色的,那是泥土的颜色,存在于低头俯视的目光里。年及弱冠,他便离开故乡巩县,先后游历了郇瑕、吴越、齐鲁、燕赵,长安、华州、秦州等地。游历,本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不料仕途坎坷,又频频遭遇兵祸,不仅满腹经纶与才华无处施展,还常常为一口饱饭而愁眉苦脸。他的目光惟有盯着脚下皲裂的、粗糙的道路,孤独地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诗的种子,祈祷遥遥无期的收获。
摆在诗人面前的,是一条近乎乞讨的路,路上写满了“生存”这两个字。这条路弯弯曲曲向西南延伸,直到与秦岭山脉间的蜀道相连。
秋风中草堂的故事,就从公元7 5 9年的蜀道开始。
我在中国诗歌文化史的大幕上努力寻找当年的古道,那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曾让李白发出“难于上青天”的嗟叹。就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一个面容憔悴、衣衫破旧、骨瘦嶙峋的老人正艰难地行走,灰色的长须在风中显得孱弱而忧伤,蹒跚的步履缓缓隐匿在山路的转折处,没有人注意到这渺小的身影正牵着的一部伟大的诗。
蜀道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在迎来了仗剑呼啸的李白之后,又迎来杜甫安静的身影。
中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诗人都在蜀道留下了自己生命的轨迹,像谶语一般,相逢在交错的时空。
他们都是寂寞的人,诗酒歌舞无非是给寂寞平添了几分恍惚而已。蜀道也是一条寂寞的路,自从他们离开,它便在秦岭云雾中隐匿了起来,沉沉睡去。对于蜀道而言,之前的千百年都是在等待,而此后的千百年只剩下了回忆。
蜀道的尽头是成都。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座四面环山的古城拥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波澜不惊、淡泊悠远,在历史长河里,成都向来是气定神闲的。
杜甫安静地来了,成都也安静地打量了一眼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故友严武打破了杜甫与成都之间的近乎漠然的安静,他向落魄的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茅屋。多年颠沛流离之后终于有了容身之所,难得的人情慰藉了凄风苦雨的心。杜甫的愁容稍稍舒展开来,茅屋虽然简陋,却是宁静而规整的,恰如他沉吟在胸中的未完的诗,一字一句对仗得严丝合缝。浣花溪畔,流水潺潺、芬芳袅袅,远离市井喧嚣,对杜甫来说,这里已是天堂。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抖抖衣衫上的尘土,开怀而笑。一间简陋的茅屋,足以让他安顿下疲惫的灵魂。
2
茅屋坍塌了。
突如其来的秋风劈开了茅屋,大手一挥卷走了屋顶的茅草,未等诗人从惊愕之中缓过神来,一夜苦雨接踵而至。屋漏床湿,书稿遍地,寒风冷雨折磨着诗人一家,他们只能紧紧蜷缩在墙角,在束手无策的等待中温暖彼此。
公元8世纪的那个秋天,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看不到花团锦簇,一场秋风使所有花木憔悴了容貌。天旋地转,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诗人正在无家可归的悲哀中孤独地站立。漫天飞舞的茅草像冬天的雪,阵阵寒意扑面而来,风在诗人的额上切割出思想的皱纹,却怎么也不肯说清困苦的尽头。就这样渐渐沉默,惟有叹息,惟有欲哭无泪的无奈,惟有重新俯下身子捡拾枯枝败叶。力透纸背的笔墨呵,此刻竟负不起一根茅草的重量。
水塘里、沟渠中、树梢上,支离破碎的茅草被吹散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草叶上沾满了淤泥和尘土,植物应有的柔韧的质地荡然无存。“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杜甫屈下膝盖,匍匐在泥泞上,用颤巍巍的双手捡回一根根茅草,仿佛捡起的是不甘和质问。
秋风破屋的捉弄还在继续,附近村里顽皮的孩子也来捣乱,他们雀跃地抱起地上的茅草就走,气得可怜的诗人破口大骂,连儒生的脸面都顾不上了。“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叹息。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字字都回响着欲哭无泪的叹息,读到“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时,所有的困惑和质问都已渐渐淡去,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唏嘘。他的苦闷,他的荒凉,谁能读懂?
他像一只漂泊的候鸟,衔来昨日的枝丫,修补着残破的巢。
这座茅屋——杜甫在成都惟一的栖身之巢——不知道被风吹破过多少次,不知道每一次倒塌后诗人又是如何将它修补。破了又破,修了又修,杜甫像西西弗斯一样重复地劳作着,只为呵护这仅有的能够散发出些许“家”的气息的居所。他逐渐习惯了修修补补的生活,甚少的欲求已让他忘却抱怨。春夜的雨打湿了他的宣纸,西岭的雪冻白了他的须发,他微笑地站在茅屋旁,在贫瘠的日子里写下一首又一首丰腴的诗。
杜甫是一株温情的、文雅的、安静的植物,世事变迁中,他练就了一种隐忍的性格,他选择以沉默面对人生无常,像植物一样固守脚下清贫的土地,默默地舔舐身上的伤痕。他宁可在淡泊中唠叨着柴米油盐,宁可在秋风后的废墟上重建栖身之所,然而命运总催促他提起脚步,催促他一次又一次在奔波与漂泊中陷入困惑的迷宫。长年累月的迁徙过早地消耗掉了一株植物的精髓和养分,这个充满植物属性的诗人迅速走向衰老,枯萎近在咫尺。
不久,严武调离成都,单薄的茅屋在秋风中愈发孤零。杜甫望了一眼风雨飘摇的茅屋,携着老妻幼子再一次走上的漂泊的路。
公元7 6 5年,在洞庭湖上,他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不久后,他因饥饿难忍吃下腐败的牛肉,中毒死在湘江上的一条破旧的小船里。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一无所有。
杜甫走了,诗寂灭了。
他沉吟着断续的诗句,离开了茅屋,离开了成都,离开了蝇营狗苟的尘世。他一直在思考,思考着这个他一辈子也想不透的人生。
浣花溪依旧宁静美丽,茅屋却在那个幽深的夜晚悄然消失。
3
先生真瘦。
草堂里的一尊塑像用凝练的线条刻画出先生的形象,他的头颅高高地昂起,眯着的眼睛似乎在吃力地张望。
他是一路张望着来到成都的。对于此时的先生而言,能在乱世中存活下来已是人生之大幸,他只求远离纷飞的战火,只求在巴蜀边陲寻找一处容身之所。理想在哪里?诗在哪里?那些隽秀的、飘逸的、优美的、洋溢着热情的诗在哪里?先生看到了散落在悬崖峭壁间的凌乱的残骸,那是死亡的诗,是死亡的理想。苍茫的风忽然发出冷峻的笑声,一阵阵刺穿人的心。抬头望去,憔悴的山峦犹如嶙峋的骨骼,夕阳埋头隐匿了在惨淡的暮色里。
那时候,没有人读得懂先生内心的苦。他不说,他把太多的目光投向了黎民百姓,却鲜及自身的困窘。他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晦暗,写尽了人世间的离别,可关于他自己,我们只记得那一声在茅屋倒塌时的哭诉。疼痛的草堂,泪眼汪汪的草堂,饥寒交迫的草堂,我多么希望此刻下一场雨,我会把雨当作先生的眼泪——哭吧,哭出压抑了千年的委屈和伤痛,哭出字字泣血的诗行。
少年仕途失意、中年丧子之痛、老年居无定所,困窘跟随了先生一生。他一直认真地活着,对于这个世界,先生从未敷衍过,可是世界一次次敷衍了他。
先生是一棵树。罗曼·罗兰说:“一棵树不会太关心它结的果实,它只是在它生命汁液的欢乐流溢中自然生长。”和先生一样,树也害怕秋天,害怕秋风,害怕凋零。愁是离人心上秋。秋,自古就是让人愁的。落叶载着先生的寂寞,在秋风中写就一行行无奈,终于在一场微凉的雨后凄然岑寂。秋后便是雪,如盐霜,有时候能够帮助伤口愈合。我很想知道,先生的伤痊愈了么?
无用的诗句像苦涩的药草,是先生医治创伤的仅存的依靠。
五代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先生曾经居住的地方,重结茅屋,从此茅屋得名草堂。堂者,大也,恢宏也。先生离开了他的茅屋,可千百年间,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让他回到草堂来。今日的草堂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所建,草堂内有工部祠,大诗人陆游、黄庭坚在祠堂内陪祀。生前连一口饱饭、一间破屋都是奢望,死后却被奉为“诗圣”,先生该哑然失笑了吧?
翠竹参天,笼罩出一片悠闲的绿荫。阳光宛如碎钻洒满假山池沼,剔透的光芒反射到成片的楼宇间,在一片花红柳绿的祥和中勾勒出魑魅的轮廓。精巧的窗棂和牌匾被正午的阳光涂上了一层虚幻的光晕,漫漶在盆地濡湿的空气中,点点滴滴,尽是连缀不成诗句的呓语。回廊曲折,溪流环绕,鸦雀啁啾,茗香袅袅,似江南园林,又似田园农居,恬淡得让人忘却了尘世间的烦恼。残留在纸页上的悲欢离合竟一点点模糊起来,终于杳无踪迹。
其实草堂早就坍圮,公元8世纪的秋风已吹散了先生心上最后一根茅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