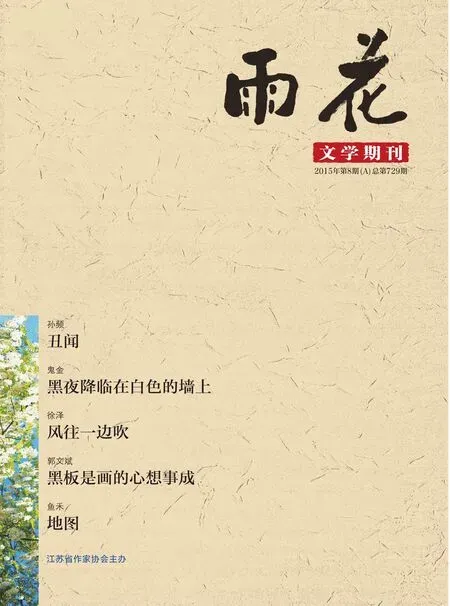地 图
■鱼 禾
地 图
■鱼 禾
1
不时会把整个下午的时间用在看地图上。不是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下午的长度,而是看着看着天就黑了。
看地图是一项旧嗜好。从看到地图的那一刻起我就迷恋上了这种奇异的书册。每一本地图册都被我翻看到糟烂。边界线,等高线,各种道路线,山丘的颜色,湖泊河流的颜色,沙漠的颜色,戈壁的颜色,以及没有任何图示的空白的无人区……地图上任何一个标记我都不会错过。地理课上,老师讲着讲着,突然说,来!你来画一个柴达木盆地。你上来,画黄河。画地中海。画赤道穿过的国家。我就上去画。几分钟,一个要素齐全的柴达木盆地,或者一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一片被二十个小国围合的海,或者肉串一样穿起许多国家的被扳直的赤道,就挂上了黑板。
由地图引发的迷恋一发不可收拾。
我曾用泥巴捏造过柴达木盆地,地中海,青藏高原。那些泥塑笨拙,却是比例准确,要素齐全,几乎是达标的地理模型。在青藏高原上挖出那些小小湖泊的时候,我兴奋得像害了病。那些高原湖泊,每一个我都知道,每一个都是我独自开挖的人工湖。在那些用小改锥开挖高原湖泊的日子里,我牢牢记住了羊卓雍错。开挖羊卓雍错最难了。它细长卷曲,汊口密布,像深蓝的珊瑚枝。这无与伦比的优美轮廓,给开挖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傍晚,湖岸线复杂的羊卓雍错挖成了。我用深蓝墨水为它填涂颜色,疯癫中把饱蘸墨汁的软刷伸向了饭碗。
2
无论住到哪里我的墙上都少不得地图。家里要挂,办公室也要挂,如果外出,必然要带地图册,带一张巨细无遗的目的地特写图。我选购的都是大比例尺的地图,全开不覆膜的那种,可以在上面随便勾画。
一直盼着能买到一个巨大的地球仪。要很大,大到可以在上面找到我所在的街道。
我估算过,要让门前这条四公里长的伊河路在地球仪上显示为一毫米(视觉上就是一个点),需要四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尺。按照这个比例微缩地球,地球仪的直径不到3.2米,勉强可以放到一间屋子里。
门前的伊河路干净笔直,梧桐成荫,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陈旧感,差不多算是赏心悦目。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象,在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上,我的伊河路微缩成一毫米,那会是个什么样子。被想象微缩的伊河路,以及伊河路上的一切—连接成片的房子,五颜六色的车辆,绿的梧桐树,蝼蚁般的行人—顿时变得渺茫,变得和我毫无瓜葛。
地图就像神秘的符咒。地图以大手笔的放大或缩小,规定着我的体量,我的有或无。
3
常常看到天黑的是卫星地图。
第一次从卫星地图上看到我家屋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和卫星电视接收器,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滚动鼠标前端的滚珠,把那一帧卫星图拉近,推远,再拉近,再推远,反反复复摆弄了好多遍。那点暗暗的惊喜该怎么描述呢?那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滋味,嗯,神仙下凡的滋味。
准确地说卫星地图不是图,而是另一种“眼见为实”,是来自天上的“遥看”。另一种眼睛在天上看这个日行八万里的圆滚滚的小东西。卫图就是天眼所见的即时景象,每一瞬间都不一样。由于依靠了强大的电磁波,天上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看数万米,也可以看得很仔细,看得见一个人的表情。
看卫星地图的人也在天上。一只在天上盘桓的鹰想必也是这样,可以随便对着地面上哪个目标俯冲下去。这只鹰非同寻常,可以在两秒之内从东非大裂谷飞到阿拉斯加。把地球缩小到一枚棋子大小然后迅速拉近,一秒钟你就从天而降,你下到凡间,到了地中海,上岸,贴地飞行,哦那座古老的圆型废墟……这样的“看”只能来自神。鹰还是不够高,不够自由。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有局限。视点当然也有局限。
4
仿佛一切都有形状,有一成不变的地理位置。一切都可以用地图来描述。
每当我迅速完成一桩计算的时候,脑中必然有地图般的影像联翩浮现。仿佛不是我在计算,而是在脑中预存的数字排列中,迅速检索到答案所在的位置。数字从来不是空洞无物的概念。每个数字都像小树一样,以特殊的秩序栽植在特定的位置,有疏有密,有高有低,它们构成的图形有平坦有崎岖,与地形图没什么两样。自然数从1到100,在一个平面上构成大写的M。M左端勾起,逆时针旋转45度。从100到1000,构成一个更大的左端勾起的M,比第一个M的地势要高一些,平缓一些……如此接连下去。
时间也是。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在我脑中一直是一幅曲别针般的地图。
非信史时代在曲别针的左端,呈现为模糊的扇形。到了先秦,扇形收缩为清晰的直线,由左而右,直到南北朝。只是三国时代地势降低了,三国有如一块盆地。这个曲别针在南北朝之后截然断开。第二条由左至右的线上,是狭窄的隋,源流广布、湖泊一样端庄的唐,竖直而褶皱的五代十国,平坦的宋,宽阔而干燥的元,洼地般真相不明的明和清。而到了清末和民国时代,这条线变得曲折无向。民国结束,线索复归为面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道路。在这个回环往复的地形图上,时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只有三百年长度的魏晋南北朝被放大到夸张的程度,线索丰富,细节确凿。我几乎可以看得见潮水般的胡服怒马,在这片地图上来来往往地迁徙;看得见棋子般布散在硝烟弥漫的北方平原上的坞堡。
四十多年的人生则构成了一幅貌若黄河的地图,一个“几”字。不同节点之间的落差十分醒目。“几”字的顶端,那一块小小的平地,是我的八十年代末,是人生中唯一的高原。
5
对远方的好奇是很久以前开始的。从那些画地图的课堂上,从那些独自开凿羊卓雍错的下午,抽象的“远方”变得历历在目,变成你不去看看就会不得安宁的所在。
有一天,我盯住了那些深嵌在藏北高原上的白色盐湖。在卫图上它们和藏北高原的背景色混为一体,要努力分辨才能看到。它们集中在柴达木盆地,位置很低,如白色镶边的小井。然后是别的:老茶山。瓷窑。
去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用红色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三条醒目的路线:一条线起自西宁,途经青海湖、茶卡、德令哈、小柴旦到察尔汗盐湖,再途经格尔木、诺木洪、都兰、共和、贵德返回西宁,绕柴达木盆地东部走一圈。一条线贯穿东南一带的陶瓷产地和茶产地:江苏宜兴,浙江龙泉,福建武夷山、德化、建阳和安溪,江西景德镇。一条线在云南境内,在景洪西南那一大片老茶山走一个复杂的之字,然后到建水。
然后,这几乎是必然的,我驱车数千里,环绕柴达木走了一圈。
大约有八年了,我一直在诸如此类的地方走来走去。有时候是为了追索某种古酒的踪迹,比如上窟春,百河台。有时候是为了一条古河流,比如溱洧河,旃然河,汜水。
每次出发前都会根据资料画一张简易地图。我的实地感觉迟钝,常常转向。阴天到了陌生地方,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在没有琢磨过一个地方的地图之前,我从不贸然前去。即或去了,所看所听的种种资讯,也因为没有具象支持而成了纯粹的概念,所有的讯息便是浆糊一坨。
溱洧河的地图是寅卯提供的。地图作为扉页装订在一本名为《溱洧源流考》的厚书里,就叫“溱洧源流图”。是手绘黑白地图。那一趟,我们七个人从溱水和洧水汇合的古城寨出发,沿河徒步三十公里,一路喝干了随身携带的五瓶烈酒。一向不爱走路的我走得兴致勃勃。我把寅卯的手绘地图在脑中做了背书。溱与洧,方涣涣兮。这条在《诗经》里多次出现的河流想必当时水势浩荡。如今水量虽然大不如前,我却由于寅卯的手绘地图,对它由好奇而至了如指掌。它在哪里有大弯转,哪一段是新郑和新密的分界线,哪里有一处断崖,哪里经过手工造纸的古城大隗,哪里经过有汉时吹歌留存的超化,我全知道。
一位以考古为业的朋友大感奇怪。莫非你要做本地的古河流研究么?
当然不是。这泱泱的匪夷所思的兴致,只不过是受了地图的勾引。
6
即便在百万分之一的卫星地图上,矩城缺口也是相当显眼的。
这个著名的地理缺口,处于北亚热带与暖温带、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淮海平原与南阳盆地、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华北地台与秦岭地槽五个自然分界线上,也是豫南盆地东北出境的要冲。由秦岭延伸到河南境内的伏牛山脉,由于乔端—鸭河口、朱阳关—夏馆两个地理断裂,自北而南形成三列大致平行的山脉,北列沿南召、嵩县和鲁山的交界带一直延伸到此。浅低山遍布沙河谷地南侧,形成了崎岖却并不险峻的地理形貌。草木密集的低山上物产丰富。有巨大的灵芝,有肉质厚实的猴头菇,有玉槌般挂在枝桠间的天麻,还有酷丽的金钱豹,有本以为只在传说里存在的麝,有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大鲵,以及大量的野生猕猴桃。
在我的视域里,矩城的特殊主要不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或物产。
每当这一带的卫星地图展现在眼前,总是有另一重幽暗的言语之门,也在心中悄悄打开。1970年,这个小小的县城曾经进行过一次绝密的政治清查。这次清查由县革委会下属的某个特殊部门操作。清查过后,一本白纸黑字的名单辑录成册。名册只印了三本,除了上报革委会的一本,余下的两本一直秘密存放在这个特殊部门的保险柜里,直到若干年后,名册的密级降低、解除,存放在保险柜里的两本名册中的一本辗转流落,在一个街边地摊上被我以三十块钱收入囊中。
7
在卫星地图上,山脉到了太行、太岳和王屋山一带,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一段山脉明暗对比强烈,主次山脊肌理清晰,山脊两侧,支脉纷披而下。大山的纹理随光赋形,或如琵琶横卧,或如树叶层叠,或如丝绸微皱,美轮美奂,变幻莫测。
我反复看那一带的卫星地图也不是要饱眼福。
就在那里,在那一片叫做卓罗砣的低山上,梁奚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小的石头屋子。石屋建在一处偏僻的低矮山崖上,北边山顶上是浩荡的草甸。
我不明白梁奚何以如此喜欢跑到山里去。他常去的那一片山处于太岳山中段的低山区,是群山,不高,规模不大,山间没有什么名胜。他怂恿我去住一阵,但我不感兴趣。梁奚便拍了照片给我看。石头屋子看起来坚固无比。屋子里只有一床一桌,墙面凸凹不平,黯淡粗砺,没有任何内装。但他礼佛似的,过一阵子就要去那所屋子里住一住。
我试图获得一桩疑问的答案。我曾把卫星地图比例调整到最大,二十万分之一。一厘米表示两公里。在这个比例的卫星图上,卓罗砣山顶草甸就像嵌在叶脉间的一枚小小的叶斑。把比例尺调小,去除路网,带着红色标记的山间草甸,或者不如说梁奚的石屋,嵌在凤凰尾羽般的太岳山间,显得格外触目。
想象他独自在那片杳无人迹的深山之间,在一所石头屋子里怎样度过那些漆黑的夜晚,心中若有悲忉。人与人再接近,也终究是隔膜的。人到了这个年纪,早已懂得了世事的崎岖,也习惯了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竖起屏障。这简直是无可奈何的事。
8
那本编辑于1970年的秘密名册,我只是作为旧物保存着。直到最近,几个朋友偶然聊起矩城,我才把它从书架底层的旧书纸箱里翻出来。
名册的编辑水准十分专业。扉页是红色宋体最高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接着是两页的汇编说明,以寥寥五百多字,介绍了汇编意图、范围、资料来源、注意事项和引用局限,实可谓言简意赅。后面是两个姓氏笔划索引。正文主干部分起自丁姓,终于戴姓,资料涉及2073人;副册是外逃无信人员,起自马姓,终于潘姓,涉及230人。
这本资料在编辑形式和文字意义上的精当,让我几乎消除了质疑的动机。即便是我这个精通公文的人,也不曾见过如此考究的文本和文字。纸张和印刷的简陋一点也没有影响它作为一份档案资料的品位。每一份记录都保持着体例的严格一致:姓名,性别,出生年份,籍贯,历史记录,目前情况。少则两行,多则六七行。行文分寸得当,用语简朴,绝无修饰也绝无废话。我甚至在其中找不到一处使用不当的标点。
这本资料辑录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对于正在风起云涌的一切尚无记忆能力。资料中不时出现的“伪”字,初看让我以为这是一份汉奸名册。直到一个出生于1929年的名字出现。这位成姓男子,到1945年也才16岁。他的历史记录和现状只有一句:“曾于伪矩城县工团任职。”再翻看,另一份资料中出现了这样的历史记录:“一九四七年系青年军陆军第**师干部教导营学生。”
“青年军”几个字令我瞬间想起梁奚。这个名字他提起过。这个名字似乎与他的父亲有关。这个人生于1922年,现状陈述为“在家劳动”,看来尚且平安无事。梁奚的父亲比资料中提到的人年轻大约十岁,但是在这本资料编辑成册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在当年人口不过几十万的矩城,被悄悄辑入这份名册的就有2300多人。许多人的历史记录都是一句话,1946年或其后两年在矩城县的国立机构任职,职位大多是当时的党政机构职员、部队军官或普通士兵,但也有国术馆教练、电台播音、军校学生、小学教员、镇政府会计等等。结局多是在家劳动、管制劳动、病死、劳改农场病死,或镇压,也有个别在某单位“工作”。
和一切印象深刻的资讯一样,这些名字在我脑中,也渐渐构成一幅特殊的矩城地图。
依然是下午。我打开卫星地图,试图把这些名字标记到矩城那片心形的区域图上。小小的矩城已经被放大到极致,但是,它还是很快就被这些名字填满。那颗嵌在伏牛山东端、豫南盆地东北、处于五个自然分区交界带的心形,显得伤痕累累。
9
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我才陪梁奚一起进山。
山里的夜晚安静极了。夜的黑铺天盖地。那附近并没有人家,可是,满山的风声里居然传来狗叫。在冬夜里狗仿佛也冷得够戗,狗叫声显得瑟缩凄凉。狗叫得诡异,我说,像狼。他听了,竟然赤裸着走出去查看。不是狼,他浑身冰凉地解释,是山那边的狗在叫。
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狗叫,我问这个胆大包天的人,你有没有怕过什么?他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7这个数字,这数字和我父亲的惨死有关。
梁奚的父亲,正如矩城那份特殊名册中的许多人一样,在1948年前后不过十几岁,曾在青年军的一所什么学院接受过培训。祖父母突然失踪之后,他们一家躲到了太岳山。他们家的石头屋子建在远离家乡的太岳山间,周围没有别的人家。
但他们的行踪还是被发现了。
1970年7月初,石屋里突然闯进几个人,父亲被抓走。梁奚说,就在这里。
我的身体开始莫名其妙地发抖。原来这间简陋不堪、我正置身其中的屋子,就是梁奚恢复起来的幼年旧居。1970年,正是矩城名册辑录的年份。仿佛被回忆带入了那个特殊的场域之内,梁奚的声音显得迟钝、凝滞,其中有一种凛凛的寒气。
10
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梁奚七岁。
每天一大早,梁奚都会悄悄跑出去,仔细查看他们的屋子。石屋建在山崖上,石头是父亲带着他们弟兄几个一块一块从山上采集的,都是石灰石,并不结实。七月的太岳山正是雨季,来一场雨,山崖的边缘就会向屋子的地基逼近一步。屋子山墙上有一道裂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宽。家里人担心着被抓走的父亲,谁也没有注意那两个令人胆寒的距离。
七岁的梁奚每天悄悄用手去量一量那道裂缝,再量一量山崖和屋子还有多远。裂缝增加一分一毫,或者山崖逼近一分一毫,都会让他暗暗惊恐。7月17日,天降暴雨,山沟里积水暴满。就在那种不断加增的恐惧中,父亲的尸体顺着山沟里的积水漂到门前。
11
每一次大祸临头都是有征兆的,梁奚说,狗哭是一切凶兆里最严重的一种。
父亲被揪斗之前的那个夏天,石屋周围老鼠出没,猫头鹰鸣叫。这都是不祥之兆,谁也不敢说破。后来,在一个深夜,他们听见了狗的悲鸣。一家人被夜半传来的狗哭吓得心惊肉跳。每个人肯定都想到了父亲,但是谁也不敢想将会有什么样的灾祸降临到头上。狗哭的声音凄惨无比。梁奚,那小小的七岁的孩子,整夜整夜地在床上发抖。
父亲被洪水冲到门前的时候,梁奚正在用手指仔细测量石屋山墙上的裂缝。已经死去的父亲眼睛睁着,满脸血污,身体被雨水泡得肿胀。只看了一眼,他的母亲就疯了。
父亲可能是被活活打死的,也可能是被打昏以后扔到河里淹死的。梁奚语调平静,仿佛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我再也顾不得担心屋子山墙上的裂缝。因为有更严重的事情要担心了—我们的生活断了来源,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风中的大山里,狗吠声依然一阵紧似一阵。我睁着眼睛,眼睛也就慢慢习惯了黑暗。尽管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黑夜本身,仿佛正在慢慢呈现自己的轮廓。在无边的黑暗里,梁奚说,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见过那样的死亡,就再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在无边无际的夜的地图上,在凤凰尾羽般的太岳山中,这小小的石头屋子有了标记。其中的惜爱也如巨痛,沉默,切肤。原来无关性情。潜伏在我们骨子里的痴迷,一切因由难辨的执拗,都只是对生之巨痛的抚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