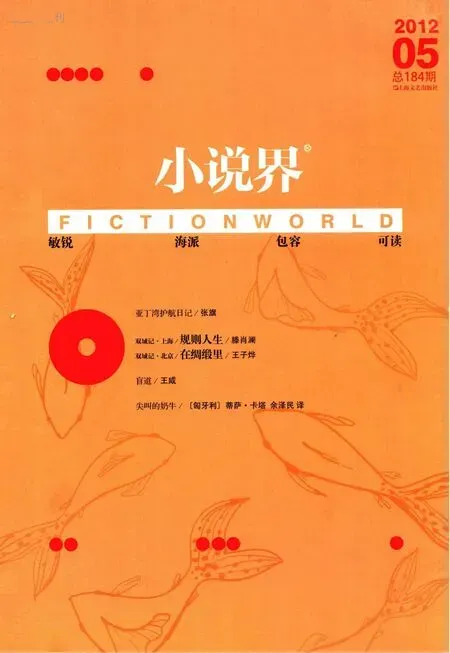爱丁堡观剧笔记
文/水晶
爱丁堡观剧笔记
文/水晶
水晶
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金融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
序:因为戏,爱上一座城
对于一个并不是特别热衷于旅游的人,爱丁堡却几乎成为我每年必去的城市,而且一定是八月,有两到三周时间,我会完整地待在那里。一年一度的爱丁堡艺术节,已经成为我这几年来每年的必修课。
八月间,这个苏格兰高地上有“北方雅典”之称的城市,街头充满了沉浸在艺术狂欢中的人群,肤色各异,来自不同国家,共同的特点是都在奔赴剧场的路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的重磅剧目,加上爱丁堡边缘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的三千多部作品,根本不能用“随意挑选”来简单形容,不识水性的新人,完全是要被艺术的汪洋大海淹没的感觉,几千部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艺术作品,会在爱丁堡的大小剧场甚至街头巷尾、酒吧、地下室里上演。
面对这么多的可选择对象,即使是拼了命地看,一天也不过六七个剧目而已。还必须精确计算各剧目的衔接时间与步行路程,稍晚到一点,就有可能被拒之门外。虽然艺术节期间很多剧场是由其他空间临时改建而成的,但在剧场管理方面,却是绝对专业的,有些戏,说不能进了就是不能进,不管来者多大牌。
不夸张地说,从上午十点之后到晚上十二点之前,我不是在剧场,就是在去剧场的路上。几年下来,看了近两百部戏,但附近的旅游景点,却一个也没专程去过。好在爱丁堡的老城当中,古建筑与街道都保留得相当完好,随处都是五六百年的老房子和被行人踩得浑圆而光滑的小石块路,而且很多戏都在一些老建筑甚至教堂当中上演,所以基本上不用专门去看景点,已经是身在景中行了。
如同喜爱甜食的孩子,走进了巨大的糖果店,惊喜不仅仅在于糖果,还在于可能偶遇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美味。其中的许多戏剧杰作,由我们邀请到中国,组成了为数万中国观众见证过的“爱丁堡前沿剧展”。戏剧,作为桥梁,连接起了远在东方的观众与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
一、爱丁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正如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的爱丁堡,也是有千种样貌、万种风情的。流连于剧场的我,每天忙于跟着长长的戏单穿梭于不同剧场之间,常常忽略了这座城市更深刻的内涵与情感。直到我读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爱丁堡笔记》,这部写成于1879年的散文随笔,用极细腻生动的笔触,带我们穿越百年风云,回到一战前安详清寂的英伦大地。
它将一座城更古老的历史与作者所身处的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带我们在那个时间的坐标点上回望,读出这“北方雅典”在苏格兰高地寒风中的卓越气质与精神脉络。你会知道爱丁堡作为苏格兰首府,它在英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一座高街公寓的倒塌,会令世界各地——伦敦、加拿大、新西兰——多少人惊叹:“我出生的那栋楼在昨夜坍塌了。”
宗教争斗、王权更迭、哲人辈出、民风强悍,此地的寒冷气候、高岭峻地以及勇敢的心,造就了其热烈与含蓄并置的风土人情,歌手们的唱词中永远不忘加入“寒冷的夜里,进来喝一杯吧,温暖你的身心”,城市街道与建筑却永远是灰、黑、米三种冷色交织,有一种“天越冷,我越要坚持”的矜持范儿。
正是在这样一种“外冷内热”的城市气质支撑下,爱丁堡艺术节这种包括了图书、电影、舞蹈、音乐、戏剧等几乎一切主流文化艺术形态的盛会,可以在这里密集发生。而在主流之外,军乐节、儿童故事节和打破传统桎梏的各种边缘艺术形式,同样也能大方登场,并迎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观众共同交流。正如地面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树有多高,取决于它的根系有多深。爱丁堡今日的繁复之美,离不开史蒂文森书中所述及的那些更久远的文化根系与历史积淀。
这个城市在进入现代化和国际化之前的那段岁月,民众的艰苦、知识分子的笔战、历史传说的光影,交织出古老的画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爱丁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从一个相对于欧洲大陆甚至英国本岛较偏远的城市,成长为一个世界的文化和艺术中心,并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来。
对于这种变化,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前任总监乔纳森·迈尔斯曾经说道:“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确实给爱丁堡、苏格兰带来了发达的旅游经济,但是,这个艺术节并不是从旅游开始的。它始于一个最艰难的年份——二战刚结束的1947年,却有一个最好的理由:让艺术缝合被战争撕裂的欧洲,让艺术赋予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

剧场里的墙上,是大量关于最近正在演出的剧目评论,供观众在选择剧目时参考。
二、爱丁堡新手攻略
今年爱丁堡的八月,天气不是非常理想,尤其是第二周,阴雨连绵,温度基本在十度左右,苏格兰高地的冷风一吹,大家纷纷穿上了棉衣甚至羽绒服。但即便是这样,也拦不住观众进场的热情,无论是上午十点早戏刚刚上演,还是深夜十二点夜戏未散,主要的剧场和街道上,到处都是悠闲的旅人和观众,大家像觅食的小鸟一样翻找节目册,互相探问看了什么好戏,或是相约去附近的酒吧或咖啡馆喝一杯。
在爱丁堡,大概有多少剧场,就有多少家酒吧或咖啡馆,看看戏,聊聊天,喝一杯,简直就是八月的爱丁堡标准套餐。
如果你是初到爱丁堡,那必须得到Royal Mile那条街道上去感受一下“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的戏剧节宣传风景。大量的剧团在那条街道上路演,各种扮相的都有,行人常常先是被突如其来的一些动作所“吓到”,继而莞尔,接过演员们递上的宣传单,说不定还会激起好奇心,走进剧场一看。
除了这条在艺术节期间被改为步行街的路上大量戏剧元素会出现,余下便是全城各处遍布的海报和宣传单页,定期会有人来把印有最新的媒体评星的小白纸条钉在海报上,风一吹,那些评星最多的海报上,小白纸条就会此起彼伏地飘荡,也算是爱丁堡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艺术节发端于1947年,当时二战刚刚结束,英国的艺术家们希望寻找一个地方,以艺术弥合战争的创伤,以节日式的聚会重振人气。他们最终找到了爱丁堡,这个在二战期间完全没有受到战火损毁的城市,并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而与此同时,另外八个未受到邀请的剧团却“不请自来”,在这里发起了完全自由与开放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与壮大,“边缘艺术节”已经一点也不边缘,不但在体量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体艺术节,每年有超过三千个剧目在此同时上演,在艺术创作方向上也无限多元、无所不包,以艺术水准论也不乏顶级之作,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全世界当代戏剧及表演艺术最大的展示平台和竞技场。
虽然我每年都来,已经算是略有经验,但面对庞大的戏单,还是有点力不从心。每天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当当的,一天下来,合理安排的话,至少可以赶六到七个戏。但即便如此,十天也不过看七十个而已,相比三千个戏的汪洋大海,也只是取一瓢饮。但毕竟是经常看,对有些团、有些戏、有些艺术家,多少有了些基础判断,加上在那边的朋友也慢慢多了起来,大家互相沟通有无、交换信息,看好戏的命中率肯定会比在街上随便抓几张单页乱看更高。

爱丁堡的夏天时雨时晴,热情的观众在雨中排队购买戏票。苏格兰巴罗兰德舞团的舞蹈剧场作品《虎生》结束后,小观众们进到舞台上,和演员们一起愉快地玩耍。

爱丁堡的夏天时雨时晴,热情的观众在雨中排队购买戏票。苏格兰巴罗兰德舞团的舞蹈剧场作品《虎生》结束后,小观众们进到舞台上,和演员们一起愉快地玩耍。
今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单元的剧目,品质都非常不错,有我错过但听好几个朋友反馈都相当好的《盖尼叙与第三帝国》(Genesh Versus the Third Reich,Genesh是印度教中的上帝)和《米内蒂》(Minetti),也有我自己看过的由英国国家剧院和苏格兰国家剧院联合制作的大戏《詹姆士王》三部曲(James I,II,III)和来自新西兰的舞蹈剧场作品《我是》(I Am)。这种场景巨大、演员众多、水准也堪称国际一流的作品,基本上只有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这种平台上才能见到,而且票还很不容易买到。
与国内相比,这种级别的作品,票价只能用超值来形容。比如在Festival Theatre主剧场演出的《詹姆士王》,只有三个价位,其中最贵的也才三十五镑,所以难怪当地的观众都习惯在开场或中场时再消费一本五镑的说明书或是几镑的饮料,顺带拉动一下衍生消费。确实,三十五镑对我们来说都算便宜,以他们的收入而言,就更是小意思了。
除了国际艺术节的大戏,我的主要精力多半还是放在看Fringe的中小型剧目上,一来是因为这些剧目带回国内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它们的实验性更强,比较符合年轻人的胃口。像今年就看到了几部相当不错的作品,如以经典写作为特色的Traverse剧场主推的《不忠》(Unfaithful)和《毁灭》(Spoiling)。
另外,苏格兰巴罗兰德芭蕾舞团的作品《虎生》(Tiger)也是给人惊喜的作品,这部舞蹈剧场作品在由四面观众环绕的舞台中间呈现,不规则网状的高架当中,是日复一日生活在平凡之中的一家三口,爸爸妈妈规规矩矩,要求女儿也规规矩矩,他们不允许那些野性与超出轨道的东西存在,永远在警惕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冲动,要做个正常人,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夫妻间的情感已淡,大家小心地不要太多露出自己的爱,在深夜各自睡去,又在清晨机械地醒来,唯有在梦境之中,久远的真实与热烈才会回来。当樊篱一点点被撕裂,终于有机会各自重新成为自己,新生再来……
整部作品以舞蹈和形体表演呈现,只有极少的几个单词,大量清晰准确的舞蹈和身体语言,充满变化的舞台运用,你看到这种作品,就会知道什么是好戏,整个人被艺术家牢牢地抓住,你跟着他(她),翱翔天际,翻山越岭,击节赞叹。
还有来自美国的《物件课》(The ObjectLesson),是一个将环境戏剧与魔术相结合的作品,不但有完整而风趣的剧情,也有深深令人感动的喻意,在如同仓库的观剧环境中,演员像魔术师一样,在一堆杂物中,不断翻捡出过往的生命历程,作品像寓言一样充满力量,发人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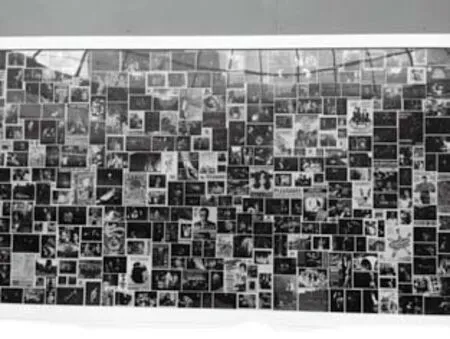
剧院里的海报墙
每次与这些好戏相遇,就忍不住兴奋,并立刻在剧场当中想象如何将其带到国内,要找什么样的合适场地,一些困难的、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技术环节该如何解决。当然,现场的判断都仅仅是初步的,真正要实现,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像2013年9月带到中国观众面前的《纸电影奥德赛》,在爱丁堡看的时候,觉得还挺简单的,真正接下这个戏之后,才发现细节上无比复杂。
当然,也有些戏,无需太复杂的道具与场景,也一样能量爆棚,如前年在爱丁堡挑到的好戏、2013年9月刚来到中国的《喀布尔安魂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极简的舞台和诗意的表演,为你呈现出长期战乱中,四个普通喀布尔人的生活与命运。那一声声灵魂深处的呐喊,让你明白,戏剧,是可以和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
你有理由在八月探访一下爱丁堡,在用双脚踏上那个城市时,顺便连接起它的过去与现在,也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它的未来。
三、有一种节奏叫赶戏
2014年8月11日,爱丁堡,天气阴。
一期一会,又到爱丁堡八月的艺术节。虽然行李是走的当天才匆匆打包的,但真正的行前准备数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爱丁堡期间的选戏清单和时间表。
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从1947年二战后发端到现在,每年都有超过两千五百个戏在三周之内同时上演,今年更是刷新纪录地达到三千一百九十三个。前天收到南京大学几个小朋友的邮件,他们是第一次到爱丁堡,初见“皇家一英里”的人山人海的兴奋,以及看到巨大无边海报墙之后陷入的深深选戏迷茫,算是爱丁堡新客最常见的初始模式。
一个“游客”或是专业观众,在爱丁堡一般也就待个五到十天,如何在这几千个戏里选戏赶戏,绝对是“体力+智力+经历”的多重累积过程——我戏称之为“大海里面捞金针”的经验。
今年因为很早就收到“创意苏格兰”(Made in Scotland)的邀请,所以这个剧展当中的三十多个戏,就优先排进时间表里了,第一周基本都在赶这些戏,每天大概五至六个的节奏,上午10:30就要开始出门看戏,大概到晚上11:30才能结束全部行程,回到住处。
再加上我们同时也是艺术节组委会的注册受邀代表,邮箱地址会提供给所有参加边缘艺术节的几千个剧团,大量来自各个国家剧展和剧团演出观摩的邀请纷至沓来,再加上其他有合作关系或认识的剧团邀请,因此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整理和回复邮箱中的邀请信。(So,南大的小朋友们,不要郁闷,你们“深深的选戏迷茫”是在爱丁堡的大街上,我是在提前两个月的邮箱里……)

作为“创意苏格兰”剧展和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受邀代表,每次一到爱丁堡,就要去组委会领取代表证和一大堆预订好的票。

爱丁堡的戏剧地图,绝对是必备良器。
尽可能选那些看上去“不错”的戏先码进时间表,是基础前提,但如何搭配这些戏的观看时间,就需要更多重的考虑。由于艺术节期间,爱丁堡有超过二百五十个(今年是二百九十九个)表演场地,如果你上一个戏在东边,下一个戏在西边,那就等着跑死吧,要么把大量时间花在路上,要么花钱打车。
重点是当你花完钱花完时间和体力之后,结果发现自己从东边剧场出来,大老远跑到西边看完一个戏,没准下一个戏又跑回东边的时候,瞬间就会有种“我好蠢”的自责感。所以一张爱丁堡地图是必备利器,上面标明了近三百个表演场地的准确位置,不仅仅可以帮你找到路,而且在选戏阶段就可以通过地图来建立方向感和脑中的“人肉GPS定位系统”。把选好的戏码在一起之后,按照相互比较靠近的剧场区域分分类,然后把一天当中相近区域的戏安排在可以相互衔接的时间段里。
但无论如何一定要算清楚间隔时间,把两个场地之间步行的时间加进去,不要太匆忙,更不做那种前一个戏必须提前离场的安排,对创作者和其他观众来说不礼貌(看的时候实在熬不住先撤是另一回事)。我这次出门前得了几天空,就把前三天每一部戏的开演时间、演出时长、几点结束、距下一个戏有多长时间间隔、步行时间多久、是否要打车等,都一一注明,对我这种偏执型人格来说,一表在手,相当无忧。
爱丁堡这个地方,通常在一个建筑物或在同一个场地里,也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剧场,即使是同一个场地里的不同剧场,观演时间表前后也不宜连得太紧,最好留个十分钟空当,这样万一前面的戏延迟了几分钟散场或是大家鼓掌时间太长,也不至于导致后面的戏迟到进场。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迟到比提前退场更不礼貌。
等你得到这些“排期”的新技能之后,一天当中至少可以省下两个小时在路上的时间、体力,以及大概十到二十镑的打车钱。这些时间和钱,可以多看一两个戏,也可以用来和新朋旧友在演出前后聊聊天,喝一杯。或者干脆找块草坪,躺倒晒晒太阳,看苏格兰高地的白云苍狗变化,眯瞪一小会儿。
哦,对了,坏消息是爱丁堡之前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本来就以凉爽著称的爱丁堡,这会儿风大,并且寒冷。像我这种本来就超级怕冷的人,已经小羽绒服加围巾上身了,还在后悔为什么没有多带一条秋裤来。
还没来过的朋友,但愿你能看到这篇,记得带点厚衣服来哦。

傍晚的Summer Hall,原来是爱丁堡大学的生物解剖学大楼,现在是爱丁堡大学最重要的综合类艺术展示中心。
四、等待被征服
2014年8月12日,爱丁堡,天气雨。
今天有点丢脸,上午第一个戏就把剧场搞错了(因为2014年版的地图上,部分剧场编号进行了调整,于是……)。等我们在雨中匆匆赶到正确的场地时,演出已经开始了二十分钟。
不幸的是这个演出偏偏是一个特殊表演形态的,制作人出来跟我们解释,因为观众坐在中间,演员在外圈,所以如果要进场,就要小心地穿过行动中的演员。为了不打扰演出,就还是放弃了。
其实害羞也是个重要原因,我一直是个努力避免在任何场合被人关注的人,想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迟到”,而且一看就是亚洲面孔,多少有点丢中国人脸的嫌疑。唉,好吧,我想多了……
内疚了半天。然后利用空出来的时间,把后面日程中所有的剧场地址和编号又全部再对了一遍,确保绝不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还跟自己说:你看,人就这样,你以为自己已经很有经验了吧,No!还是要足够认真和当心,不然就会出状况。也算是老天爷给的提醒吧,感谢。
后来全天就很顺利,看了四个戏,参加了威尔士的艺术招待会,又认识了一堆人,往下周的时间表塞了一个戏进去。见了南大的小朋友,见了壁虎剧团的制作人Roz和技术总监Nathan,把十一月中国巡演的相关技术细节和明年新戏的安排面聊了一下,还见了在英国搞创作的美女钢琴家安婷,聊了明年合作的一些事,以及各种中国人在一起会八的艺术卦。
好开心,爱丁堡的八月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次来,总是会碰到很多新朋旧友,看戏之余,见个面聊聊天也是一大乐事,所以剧场内外的咖啡馆和酒吧里面永远人头攒动。
从昨天早晨8:30落地到今天结束,看了六个演出了,还不包括昨天晚上在台湾演出季招待会上看到五个剧目片段。整体的形态和水准,还蛮代表爱丁堡特色的。这六个演出当中,一个是在滑冰场(同时也是冰球馆)看的现代滑冰,一个在Summer Hall露天庭院的现代舞,一个中规中矩的戏剧,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舞蹈剧场作品,一个相当伦敦西区风格的中产阶级戏,一个头戴无线耳机、站着看并且可以到处走动、音乐与表演混搭的乐队演出。
一天当中,你就有机会看到完全不同样态的作品。在爱丁堡,从来不缺独特的形式,也不缺好故事,但完成度高的作品,却永远只是最少的那一部分。
以在滑冰场看的那个现代滑冰为例(真的只是滑冰),其实是形式非常不错的一个作品,在普通的滑冰场内进行,不同于一般竞技类花样滑冰,它把形体戏剧的表演融入滑冰,有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也有灯光、音效的配合,有演员独特技能的展示,还有不少和观众互动的部分,演出结束后,有兴趣的观众还可以穿上冰鞋进入场地和演员一起进行滑行,有一个冰上派对。
其实所有这些要素都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对于一个有众多学员的冰场来说,这种节目的到来,无疑是极增添人气的。演出开始前,我在走廊上和演员们聊天时,一群八九岁的小学员路过,大声尖叫着冲过来,要跟那个大高个的黑人帅哥合影。原来之前他们在上课时,看到了在旁边排练的演员们,“惊为天人”,所以引为偶像。
所以你能看到,在国外“艺术教育”和“文化普及”这件事,简直是已经“渗入到骨髓”的一种无形课程,你不是只在剧场里才能受“教育”,你滑个冰,也有机会接触艺术。
但从我的角度而言,这个作品就还只能算是停留在“文化普及”和“艺术教育”这个层面上,它还没有精彩到我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把它带到国内。不过如果是万象城那些Shopping Mall里的冰场,大概就会有兴趣,毕竟在孩子们枯燥的日常训练中,这种更加幽默和生动的现场表演与教学,有可能会比职业运动员带给他们的兴奋感更多。
还有晚上在Summer Hall看的《等待时光(混音)》,现场绝对令人耳目一新,迷雾重重的大厅里,Z字形的步道式舞台,观众们在炫酷的灯光与多媒体中,戴着闪着蓝色小灯的无线耳机,跟随音乐,可以走走停停。演出当中有个人扮演巨大的兔子,和作为主角的女歌手,有一些剧情性的展示,女主角从小吉他到电音吉他,样样都算拿手。
可我还是没看完,就提前退场了。因为八首歌听下来,都差不多的感觉,无论是麦当娜风格还是乡村民谣,听着都差不多,像杯温开水,波澜不惊,那么嗨的现场设计,还是令人昏昏欲睡。
通常看到这种作品,我心中都有巨大的惋惜感——你看,你们已经那么接近成功了,有那么好的创意和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就是没能翻山越岭、奇峰迭起,你们从希望的高点,用软不拉叽、好多“洞”的表演,把本来八十分的起分,一分一分地减掉,直至成为一个七十分以下的平庸之作。
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演出,它比那些一上来就恶俗、低劣、让你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表演更让人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大部分有才华的艺术家,都停留在这个阶段。能冲破八十分的起分,并且一直刷新观众心中温度计的表演,永远是少数。
每次进剧场,我把自己扔在椅子上,等台上和那些幕后的艺术家们来抓。
为的就是,这被征服的一刻。
五、“猛戏”出没,请注意
2014年8月14日,爱丁堡,天气:晴,雨,晴,雨,晴,雨……
昨天和今天两天,一共看了十二个戏。三个音乐剧场的作品,三个舞蹈剧场的作品,一个手工装置类的戏,FERAL,有点像《纸电影奥德赛》,完成度不错;一个读剧本式的作品,全程睡着;一个名叫HUFF的纯装置作品,以三只小猪的故事为基础,每次“演出”当中,三个观众一起走入环环相扣的房屋,观看物件,听声音,感受“三只小猪”狼口脱险的惊险猪生。嘲讽的是最后猪没有被狼吃掉,都被人吃了。
然后就是几个值得一提的猛戏,因为各种原因,不太可能带到国内,也就只能在这儿跟大家聊几句了。
首先是一部盖尔语(Gaelic)演出的作品《麦克白》,并且没有字幕,进场时只拿到一张英文的剧情简介。盖尔语是苏格兰最古老的语言,公元三世纪前后出现于苏格兰。五世纪罗马结束对英国统治后,盖尔语已成为苏格兰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十九、二十世纪盖尔语逐渐被排斥出苏格兰学校教育和公众生活领域,到现在已经是一门接近灭绝的语言,在场的英国观众大概也跟我一样,能听懂的单词不会超过十个。
因为会这门语言的人已经很少,所以能用这种语言作精彩表演的,就更少了。盖尔语本身是一种曲折型语言,整体的音韵发声非常独特,变化丰富,因此昨天所看的这场演出,也算是一次珍贵而奇特的体验。舞台上只有两个演员,配合多媒体效果,将《麦克白》这一宏大背景的故事,以麦克白夫妇的视角重新诠释并呈现出来,对权力的贪欲与灾难来临时的恐惧,渴望控制一切与面对血淋淋双手的忐忑,纤毫毕现。
但,即使一句话都听不懂,也完全不影响你沉浸于超有魅力的麦克白扮演者David Walker的表演当中,他的声音超级动人,如同引力巨大的磁场,不看表演,光听声音都醉了(我后来查了一下节目单,的确,他同时是影视和戏剧演员,也是很多作品的声音演员)。整个表演过程中,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声音、形体、表演和那些微小的动作,每一样都在向外发射能量,同时也吸收像我这样趴在前面的小桌上无限仰慕凝视着他的人所回馈的能量,这些能量,与他内在的力量一起,成就了他的王者风范。
然后是今天下午在Traverse看的政治戏《破坏》(Spoiling),由Traverse艺术总监Orla O’Loughlin亲自执导的作品,今年八月在爱丁堡首演。剧中,苏格兰外交大臣Fiona(同时也是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将要在世界媒体前发表一个演讲,讲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但问题是她拒绝使用所在政党提供的演讲稿,而希望讲自己想要说的话。在与其他政客的角力需要和一位被派来的说客面前,她面临选择,是像玩偶一样言他人之辞,还是重新夺回主控?戏剧性的场面在她的办公室里接踵发生,言语的刀光剑影,此起彼伏。
虽然只有两个演员,但是精彩的剧本与极自如细腻的表演,让这部政治戏好看起来,也为铁血的政治斗争融入真实的人物情感。在现实中,苏格兰公投将于2014年9月18日进行(编注:公投结果已宣布,苏格兰不脱离英国),但关于独立之后的各种假设型作品,已经大量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剧场保留和沿续了“社会论坛”这一功能,它让观众在剧场当中通过剧情、人物和模拟辩论,进入更深刻与多元的思考。一个可以在剧场里讨论一切问题的社会,才能称得上是自由和民主的社会。
再就是在Dance Base看的舞蹈剧场作品《爱上弗里达》,以墨西哥传奇艺术家弗里达的故事为原型,但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表演者中,一位是侏儒(Caroline Bowditch),一位是只有一条腿的舞者,三位女性艺术家一起,在一个只有小型会议室那么大的空间里,以与观众极近的距离,释放出爱与痛的热力与一种奇妙的魔力。
弗里达是闻名世界的女艺术家,以风格独特的绘画著称,同时也以混乱的情感生活而常被人引为谈资。她从小就有惊人的美貌,六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十八岁时车祸让她的脊椎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后来她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人相信她可以活下来。她一生中做过三十一次手术,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
这样一个传奇女子,由一位身体特殊的艺术家、一位残疾艺术家与另一位健康秀美的艺术家一起,共同扮演,颇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意味。最初进场时,看一个身体异形的女子躺在桌上,心理上略有不适,但很快便被扫除。
喝下一小杯龙舌兰酒之后,看女子们欢笑、坠入情网,在甜蜜、忧伤、狂喜、焦虑、恍惚等种种情绪中穿梭,看那残缺的身体,如何优雅而自信地挪动,像弗里达充满痛苦与喜悦的人生一样,这两位特殊的演员,用身体的残缺与坚持,绘出了最真实的人生样貌。像另一位演员Nicole Guarino在自我介绍里说的一样: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与弗里达有着生命的连接,《爱上弗里达》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去爱上那个破碎的自已。
最后,我要说一下《姐妹》(Sister),这大概是这两天我们在观剧小分队里讨论最多的戏了,看之前就被告知各种超限,钢管舞、全裸、自摸,各种似乎极其“脏”的内容。这种“演前提示”让我们多少有点心理戒备,也有点小贼头贼脑的感觉,一进剧场,就躲着热情招呼的“姐妹”们,挑了一个最远最高的座位坐下,以免除被选到舞台上去近身互动的尴尬。
但是,近十分钟后,当全裸已经进行了片刻,该看的都已经看完时,我内心忽然生出另一种坦然与感动: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这样毫无耻感地,面对自己的身体,并在众人面前展示身体,如同纯洁的幼儿呢?
剧中两位姐妹艺术家,姐姐是性工作者,妹妹是一个剃光头的女同性恋,她们俩同时都是女权主义者,但这种女权,并不是那种要求某种女性特权的,相反,我觉得她们根本不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只是人权主义,作为人,她们首先追求清醒认知自己的权力,同时寻求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努力去成为的权力。当她们如此自然、坦率地在舞台上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喜好、日常生活时,背景中是她们幼年时的玩耍影像,让人内心况味复杂。
整部作品非常流畅,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之感,我最爱最后那段妹妹的独白:我不能选择出生的地方,我不能选择父母,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名字,我不能选择这个政府,但我可以选择我喜欢谁,我可以选择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她光着身子,坐在椅子上,自自然然地说着这番话,并没有当观众是窥探者,她把自己坦然地交给了观众。姐姐也同样光着身子,在后面开始收拾东西,拆除舞台上立着的舞杆,有时候会让妹妹过去帮一下忙。她们与常人常态没有任何分别,只是没穿衣服。
这一刻,我心中肃然起敬。所谓成功的人生,不是你有多少银行存款、你开什么牌子的车、穿什么牌子的鞋、职位升到什么位置,而是你知道你是谁,你真正的梦想是什么,并且,你有能力实现它。
这个作品,是由国家剧院工作室(National Theatre Studio)、巴特西艺术中心(Battersea Arts)等机构共同扶持的作品。
有些差距,以光年计。
六、高山之巅,人生碎片
2014年8月17日,爱丁堡,天气晴。
这三天,每天都是六七个演出在赶,其中大部分是音乐类的剧目,音乐+诗+歌、音乐+舞蹈、音乐+文学剧场,对我这种平时难得看音乐类剧目的人来说,完全是“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的好处是,可以一天看很多演出,效率高。同时,在高密度的观看过程中,会对演出的整体水准判断特别敏感:好的、差的,会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如果一个月才看一个的话,大概每个都会觉得不错,饥饿状态下对食物肯定不会太挑剔。
坏处是会审美疲劳,不那么容易享受演出当中那些普通的美好。这种类型的剧目,应该是在周末,万事不愁,吃饱喝足,极放松地坐下来,好好享受这个晚上。辛劳了一个星期,不用华服豪车,在家附近的社区就可以享受这个晚上。
我记得有一个演出,是周五的一个下午,在一间不太大的教堂里,听一个室内管弦乐的作品。阳光从西侧的窗户里穿进来,照在吹奏长笛和黑管的金发女孩身上,如同光环一样闪闪发亮,很像油画的画面。前排多是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太,安静地坐在那里,度过他们生活当中普通的一个周末,平常而自然。于我是暴饮暴食的日子,于他们是细水长流。
也是那天上午,在另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模样的场地里,看一个由乐队伴奏故事朗读的活动,中间还有舞蹈的伴演。那个节目是有小朋友参加的,好几个七八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大概两岁左右的黑人混血小孩,坐在专门为小孩准备的小椅子里,有点不老实,时不时地站起来,挪到妈妈怀里,还会在朗读的间隙忽然大声地发表一两句自己的见解。后来又爬下来,去到后面一个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小帐篷里,戴着绒毛手套自顾自玩起来。
并没有人特别地去干预他,连责备的眼神都没有。他也就安静地在帐篷里待着,继续听故事。之后又不耐烦起来,妈妈大概怕他太闹,就带他出去了。他走了之后,继续坐在场内的我们,都有点略感落寞。大概觉得这样的节目,如果没有那么小的小孩在场,多少有点减损意义。艺术,文学,这些前人与今人共同凝聚的种子,不就是为了在那些小小的心田里播下么?
那天朗诵的作品,是一个苏格兰作家的诗歌和儿童故事。我好希望有一天我的朋友兰晓龙,也能为他的女儿创作这样一个作品,然后让更多的孩子以这种方式听到。哪怕他或她中途不耐烦,戴着毛绒手套跑出去玩了。
要细水长流,细水长流。
三天看了十多个戏,印象不够深刻的,几乎转瞬就失忆了。但肯定会有些作品,画面和气息,一直深深地在脑海中,而且愿意一再地向人提起。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新西兰剧目《我是》算是一个。这也是我们观剧小组“深夜吐槽趴”上的重点话题之一,对这个剧的观看反应非常两极化,现场有看哭要再看一遍的,也有称之为“超极大雷”和恨不能提前退场的;有当面向我表示“好喜欢、好喜欢的”,也有写信来说“很费解……感觉是一场行为艺术”的。
的确,这部由新西兰艺术家领衔、多国艺术家共同合作的作品,在简洁冷酷的德国波兰系视觉风格之下,有着一种神秘的气质。这部作品的创作者有一种惊人的勇气,他们常常在极大的“画幅”上,如Play House的巨大舞台空间中,以单个人物作为行动和表演焦点,表演手段包括演唱一种近似于巫者祈歌式的原生态曲调,或是在接近舞台最上面的部分,有人以极柔和的方式缓慢移动,精致清柔的光将这个人物在巨大的灰色空间中提亮。很多时候,舞台上的画面如同静止,人物的行动如同飘移,你以为将要发生什么,但并没有,时间继续定格下去,直到你从下一次瞌睡中醒来。
对于这种作品,我完全不愿意用好或差来评价,我只能承认它在我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我也确实睡过去好几次。尤其是每次刚从瞌睡中醒来时,两眼还没有对好焦,会以为舞台上又多出了一个人,定下睛来,发现还是刚才睡着前的那一个——他们如同站成永恒,无比笃定。
光这份笃定,就难于上青天。
这部为纪念一战中两千万死者而做的宏大作品,同时也是为生者祈祷。在人类历史巨大的灰幕与高墙之下,有人立于山巅,在风中歌唱,虽然我们未必明白那歌的深意。
另外也有小而动人的作品,像今年巴西的爱丁堡Showcase中的《小丑叔叔的鞋》(My Uncle’s Shoes),默剧,讲述一对相依为命的小丑戏班叔侄,共同拖着一辆小车到处巡演。叔叔是成功的小丑扮演者,侄子是胖乎乎的小跟班,有点懒、有点馋、有点笨,但也仰慕叔叔的精彩技能,总想偷偷学艺。随着叔叔的老去,侄子一天天成长起来,在剧烈的咳嗽声中,叔叔开始一点点把手艺教给侄子,生命的轮回,也由此开始。没有台词,却表意清晰,很多欢笑,也有很多细节令人心酸落泪,最后出人意料的温暖的结局,又让人心中平复。是一部适合小朋友和家长一起观看的剧目。
从去年在爱丁堡选的《喀布尔安魂曲》,到这次《小丑叔叔的鞋》,还有另外几部今年上演听说反响都非常不错的巴西戏,都让我再次感受到巴西的戏剧魅力。那种质朴、深沉、温婉的气质,扎实的功底,真的令人羡慕。你说咱比不过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戏剧大国,算正常,但面对巴西的这几部戏,我们都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来抗衡,就真是悲哀了。
另外,今天晚上,看到了迄今为止今年的最佳演出,《物件课》(The Object Lesson)。你可以把它称为环境戏剧,也可以划到魔术的范畴,但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剧场作品,并且是观众深度参与的作品。演出开始前,当观众进场时,如同进到一个堆满杂物的阁楼或是储藏室里,没有固定的座位,观众需要自己去旁边的犄角旮旯里拖出折叠椅、沙发、纸箱,或是一切能坐的东西,自己找地儿坐下来。然后演员从某个角落出来,在人群里穿梭,在周围的废纸箱里一一把相关道具和家具、物件“刨”出来,布置成需要的样子。
通过一通现场录音之后再二度完成的“电话对话”,观众会初次体会到这个节目的“巧妙”,而观众会不断地被拉进演出当中,配合完成一些动作和安排,并渐渐地被“拉进”对自己身边物件的“思考”与重新审视中。一段由观众配合完成的情节之后,故事开始渐入佳境,你会看到这个男主角如何经历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感情,又如何失去,如何试图重建连接,却被挂断电话。面对过去留下的种种,人已去,情已去,只余物件。
最后的一个片段,是不断让人感到意外和惊诧的过程。他在一个魔法般的箱子里,依序翻出了他的整个人生过程,那些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物证”被一一翻捡出来,又被无可奈何地扔在一旁。没办法,时间就像后浪推前浪一样洗刷着生命。岸边满是搁浅的人生碎片,它们从记忆的箱子里一直一直地被“掏”出来,直到生命的根,被连根拔起。
这是一个从创意到完成,都堪称完美的戏。美到令人心痛。
而且我知道,我们永远做不出这样的戏来。由于语言的障碍、表演空间的限制和现场字幕的难以实现,我们甚至连把这种戏带到国内来的可能性都非常非常小。
一想到这个,就更痛了。
七、艺术家与公主病
2014年8月21日,爱丁堡,天气晴。
如果说上周的时间表是整齐有序,那这周的时间表就可以用“乱七八糟”来形容。因为各种邀请,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戏并调整日程,还有国内外的各路朋友陆续到来,各种相见。每天晚上的“深夜吐槽趴”欢乐进行中,最夸张的一次,到早上八点才结束,基本是眯一会儿就洗把脸出门看戏了。
不过大家放心,没有大麻什么的,那个东西很贵,做戏剧的人都好穷,消费不起的。爱丁堡超市里的红酒很便宜,四五镑就能买到相当不错的酒,配一点水果和芝士,加上各种笑话,足以欢度一晚。若没有这深夜的欢乐,还真不能抵挡白天奔波看戏渐渐生出来的倦意。
在增加日程的同时,也会从日程表上划掉一些传说中的“雷”。不过有些雷还是不可避免地踩上了,比如今天下午看到一个烂戏,想死的心都有了,但剧场实在太小,又有摄影机挡道,实在不好意思当众离场。只能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坚强点、坚强点……好在戏只有四十五分钟,总算活着出来了。
爱丁堡就是这样,三千多部戏,绝不可能都是好戏,大量的戏都是一般水准,要看十个二十个,或许才能碰上一个极好的,肯定也会碰上一两个极差的。好戏的好法,各不相同,差戏的差法,却大同小异。我在看戏时的随手涂鸦主要包括以下金句:
1.她哭的时候,你却想笑(一个控拆保加利亚医疗体系的作品);
2.这音乐和多媒体是放错了吧(一个台湾现代舞蹈剧场作品);
3.现在是二星,要是演员不说话,就是四星了(一个威尔士的舞蹈剧场作品);
4.这戏已经不是一星、二星可以形容的了,简直就是负分好吗?(一个民族特色剧场作品)
上述体验,估计大家在碰到烂戏时,都曾有过相似体验。
但即使有这种10%的踩雷风险,爱丁堡也绝对是值得探险的地方,毕竟整体的平均水准放在那里,而且风格极多样化,所以总还是不断有惊喜的。这几天水准之上的作品包括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单元的大戏《詹姆士王》三部曲(James I、II、III),同一个导演、同一个编剧、同一拨演员、同一个舞台,却是三部风格上差异非常大的作品。“一”经典稳重,是标准的国家剧院级作品风格;“二”则轻灵跳跃,流畅精致;“三”现代时尚,有点西区风格加重口味。
这三部曲以十五世纪刚刚建立的苏格兰王国为背景,讲述三位国王自我的成长历史以及这个新生国家的成长史。由英国国家剧院和苏格兰国家剧院联合制作,挑选了众多新生代演员,来完成这部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人精神层面展现相结合的作品。舞台设计非常有特色,在舞台上搭建的观众席,同时也是演员们多维度的表演空间,整个舞台上没有任何一件多余的装置或布景,所有的东西都可移动,并一物多用。
这样一部有强烈“政治意识”的作品,世界首演出现在苏格兰公投之前的“敏感时期”,使得《詹姆士王》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不但在爱丁堡的演出一票难求,在伦敦的演出预售也大受欢迎。这种“成功”,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在英国的舞台上,一切皆可讨论。对我们这种“局外人”观众来说,最大的感受则是深切体会到英国和苏格兰国家剧院艺术家的深厚功底,那种经受过扎实的古典训练、同时在精神层面又对现代舞台创新孜孜以求的融合能力,令人感慨。
另外也有几个不错的动人小戏,像新西兰的木偶戏《小鸭,死神,郁金香》(Duck,Death andthe Tulip,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讲一个伤感又温暖的小故事,小鸭遇见死神,初始担心死神会把自己收走,没想到死神如此温柔,陪它喝茶,去水池里游泳,去爬小山上的果树。当小鸭累了,在死神怀里睡着,安祥地离开了世界,结果反而是死神伤感地离开,耸着肩,叹息道:It’s life。

在街头路演的日本鼓演员
小而动人的一个戏,在上午十点看的,足以温暖内心很多天。
另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是一场日本鼓(Japan Drummers)的演出。不但场内从头嗨到尾,更令人惊讶的是结束之后,全体演员从剧场门口到走廊,再到大厅,依次向观众握手、道别、感谢。身着单衣的演员和我们这些穿着羽绒服的人一起站在寒风中,满脸都是真诚的笑容。隔天在街头,又看见他们身着戏服,分立在几个街口打鼓路演,散发演出宣传单页。虽然在爱丁堡街头艺术家和演员们亲自发传单、做街头路演和宣传是常态,但像日本鼓演员这样热忱和敬业的,还是不多,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说到如何在这样一个超过三千个戏同时上演的地方推销自己,实在是一门再大不过的课程。除了把戏做好之外,各个剧团所要付出的努力是难以想象的,不仅要在路边和各个剧场尽可能多地铺宣传单和海报,还要争取在各种评论杂志中露面,更需要在人流量大的路口直接发宣传单,以吸引可能的观众,我在Fringe的杂志上,还看到过一篇专门介绍如何提高散发传单技巧的文章。
每次在一些官方的聚会上,也会见到各种演出的导演和制作人,带着宣传单和资料来主动介绍自己和剧目,邀请你去看戏。那种主动,既没有讨好,也没有骄傲,就是一种简单而真诚的交流。如果你确定下来要去看演出,一定会有后续的邮件及时到来,以及各种靠谱的日期确认邮件等,而且这些邮件都是导演或制作人自己处理,没有助理,没有跟班,一切皆需亲力亲为。
事实上,在爱丁堡,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普通人,他们需要像所有普通的白领职员一样,细致地处理好无数琐碎的工作,并积极地向世界张开怀抱,宣介自己。那些总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有“公主病”的艺术家,在这里是很难存活的。
一方面是因为只有戏好才会吸引到观众,你自己作高冷状是没用的,剧团也很难操纵评论,更没有办法像国内一样靠发新闻通稿来影响舆论;另一方面是,你拉着脸满脸不高兴,也不会有人来惯着你、哄着你。这是一个人人奋力奔跑、物竞天择、各自欢喜的世界,你只有真诚地与他人分享和交流,才能获得关注。
从这点而言,爱丁堡真是一个大的艺术竞技场,比拼的不仅是艺术水准,更是艺术家的人品、情商和行政能力。国内戏剧界的“公主病”重度患者们,很有必要来这里治几个疗程,以便学会说人话、做人事、演人戏。
八、空间自由与创作自由
2014年8月22日,爱丁堡,天气晴。
经历了上周的时雨时晴之后,这周爱丁堡的天气终于稳定了下来,气温回升,大朵大朵的云彩浮在蓝天之下。连续走了几天的路之后,懒惰已久的身体也被打开,走起路来有点健步如飞的感觉,碰到要走四十分钟的最远的剧场也感觉不在话下了。
其实,艺术节期间,基本上所有的表演场地,都可以在步行四十分钟内抵达,一路穿街走巷,身边随处是五六百年的古迹和石块铺成的街道,草坪、大树和家宅门前的花儿,串成一路的风景,让这四十分钟走起来一点也不无聊。
如果把这个步行区域对应到北京,基本就是东北二环和东北一环之间这么大的一个小四方块区域,其中有两百多个会场,而每一个会场当中,又有多个表演空间,少则两三个,多则像Summer Hall这样有四五十个。正是这种密度,为每年三千多个剧目的同时上演提供了硬件上的可能。
每次在爱丁堡看戏,都会特别注意他们是如何把一个普通的空间变成“剧场”的,教堂、教室、大楼的中空区域、酒吧,甚至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都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由Truss架或流动灯架提供灯、悬挂布景或是音响,而且所有的演出场地都有专业的场务人员提供服务,很少出现因为隔音、场外杂音等因素影响演出的情况。可以说,在边缘艺术节期间,绝大部分演出,都是在非剧场形态的“专业剧场”里进行的。
像昨天在New Town剧场看的一个巴西的戏,The Day Sam Dead,讲述巴西医疗腐败的故事,医院里的医生因为工作压力大,会通过职务之便注射刺激性药物来缓解压力,病人家属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会通过金钱贿赂甚至性贿赂来达成目的。整部戏风格极为彪悍,摇滚加酷帅的表演,再度让人惊叹巴西的戏剧水平之高。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是在一个旧教堂里演出的,坐在观众席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演员在布景背后行动时,几乎是贴着台上巨大的管风琴在移动。所有灯光、布景和音响,也完全依靠Truss架搭建,可演出效果依然是一流的,没有任何损耗。
此前在老城的另一个教堂Old St Paul当中,一家在爱丁堡颇为著名的国际演出公司Aurora Nova(著名的《反转地心引力》一剧,就是由他们代理的)举办了他们的特别活动,邀请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女艺术家,在现场以油彩涂绘方式(和沙画有点像),在教堂的主墙面上,投影出圣经故事。配合巨大的多媒体投影和现场音乐,将古老宗教建筑与现代艺术极巧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美得令人叹息。整个表演并不长,只有半个小时,但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在爱丁堡参加艺术节的大咖们都去了,这种场合,同时也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交流的好机会,大家可以把最近的一些创意火花相互沟通,一些艺术创作组合很可能就此诞生。
回想国内,政府一直大把花钱建造各种规模巨大的剧场,却很少在如何将现有场地改造成为表演空间上动脑筋。同时,由于戏剧微观生产的不足,又造成大量原有的、新建的剧场低效运营甚至空置浪费。
以一个从经济学和金融背景入行的“外行”角度观察,我一直觉得中国戏剧是由国家高度垄断的生产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国有戏剧院团的生产、创作垄断,对表演场地的经营和准入权垄断,对具体剧目演出许可的行政垄断,已经导致中国戏剧创作和观演的民间微观生态基本处于灭绝状态(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但即使以北京、上海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和世界上同等当量的城市相比,戏剧生态也堪称寥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有一条朴素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会影响经济基础。”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特别是针对戏剧类表演团体的管理体制,已经极度僵化、落后,这反过来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戏剧的整体水准,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整体水准,基本已经滑落到世界末流的水准,连巴西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比不上。
从去年到现在,我在爱丁堡看过六个巴西的戏,从《喀布尔安魂曲》到《小丑叔叔的鞋》,再到前文提到的The Day Sam Dead,风格多元,而且无论剧本、表演和导演,都在水准之上。要知道,这些戏全部是来自巴西民间的自由剧团,没有任何国有剧团的背景和政府资助,但他们以自己高水准的作品,在爱丁堡这个世界戏剧的竞技场上,成功地赢得了文化与艺术上的自信。这些成功,与他们长期的自然生长、自由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要自然生长、自由创作,首先意味着艺术家需要成长和呼吸的空间,这不仅需要文化管制和演出审批尺度上的放宽与管理者的自我约束,更需要在表演场地管理政策上的巨大变革。
我非常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了解到目前这种表演场地管理政策的巨大抑制性作用,未来能够放宽对小型表演场地的管制,应该鼓励民间将各种可能的空间改造成可能的表演场地,而不是拼命花钱盖新剧场。希望能放松乃至解除所谓“消防检查”和剧场资质审批,这类政策更多是出于文化管制的需求,而不是鼓励创作和演出的需求,当然,官方管理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也是主因之一。
表演场地的单一形态(目前国内只有镜框式和Black Box这两种形态),使得创作者的创作观念长期被固化。他们几乎从接触戏剧开始,就以为只有这两种演出形态。而当他们有任何一点点突破性想法的时候,又不得不服从于政策对于演出管制的限制,慢慢地大家也就放弃了尝试的冲动。现有表演场所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也使得戏剧从业者们不得不只能创作出那些能够通过商业方式达到平衡或获取利益的作品,而放弃任何暂时无法平衡或获利的创意。
所以当我们在国内屡屡见到“大师”们努力凑齐各种明星班底在大剧场巡演,小剧场新锐们则“坚持不懈”地呈献爆笑、白领、爱情等肥皂快餐剧,别忘了,他们也是这种管理体制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别的活法。
试想,如果大家可以在更多元化的、成本更低的场地里进行创作和演出,不用由于场租等各方面原因而那么着急地寻求商业上的平衡和回报,中国戏剧的创作局面,应该会有更多新的可能吧?
尾声
爱丁堡的两周旅程很快就要结束,我们在结束了戏剧的饕餮盛宴和“暴饮暴食”之后,终究要告别苏格兰高地的蓝天白云,回到国内,在北京时不时的雾霾中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也与我们同一时代的戏剧人同呼吸、共命运。
好吧,那我们一起努力。
借用“文艺连萌”的一句话: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