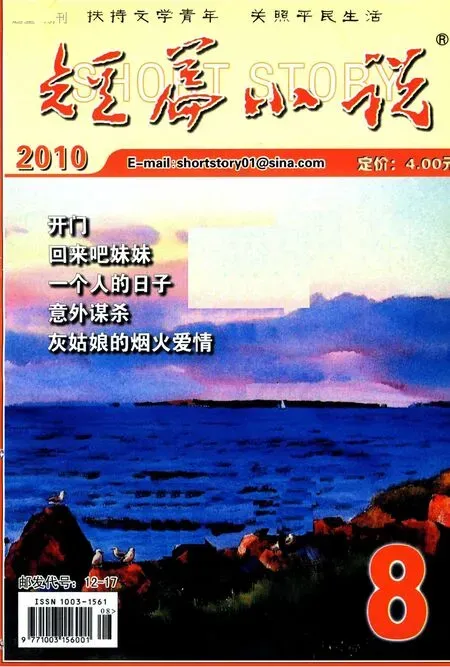老味三题
◎不雨飞霜
老味三题
◎不雨飞霜

一 “军统”就是“长统”
牛皮塘生产队队长万年青是大队书记万春山的堂兄,万年青爱讲直话,万春山当了大队书记之后同样成了土皇帝,全大队只有万年青敢当着万春山的面讲万春山土皇帝几句直话,而且只有万年青讲的话,万春山还能听得进去,因此,万年青有一个“大直套人”的美称。
“大直套人”万年青其实是一个少有的很会做人的生产队长。
康德仁原来是省人民医院的名医,但因为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医生,“文革”开始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说成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一家大小被下放到牛皮塘生产队监督改造。
当时总是讲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军统特务”康德仁和牛家湾生产队的地主分子“唱大胯”一起,经常被押上大队会上接受批斗,以此促进牛头山大队生产的大发展。
但在牛皮塘生产队,作为队长的万年青却从不为康德仁的难,尽管万春山多次在大队会上号召广大贫下中农社员不要去找康德仁看病,说康德仁根本就看不好病,并举出种种例子说很多人到康德仁那里看病,无病被看成了有病,小病被看成了大病,大病被看成了死病……可是,如果有人找正在劳动中的康德仁去看病,万年青照样还是批康德仁的假,因为康德仁完全是义务替人看病,连一根烟都不抽人家的,万年青便暗中告诉记工员陶自力,康德仁离开田间地头去病人家里看病时,不要扣他的工分。当年人们在生产队劳作都是记工分,工分是一家大小分粮吃饭的命根。
早春时节搞秧田的时候,贫下中农社员不怕冷,都是打赤脚下田,康德仁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就像牙疼的人一接触冷水就钻心般地疼一样,他的腿脚对冷水也高度敏感,他只好穿着长雨靴下田,这让家里根本就没有长雨靴、也舍不得买长雨靴的贫下中农社员眼睛红得冒绿火,很是看不惯,这些人不敢对万年青讲,就以自己“阶级觉悟高,对敌斗争观念强”为由,直接把问题反映到大队书记万春山那里,万春山听了,自然十分气愤,这像什么话呢?国民党“军统特务”竟然比贫下中农社员还有优越感!
借开全大队生产队队长会议的机会,万春山特地把万年青叫到一边,以非常严肃的口吻质问万年青:“你怎么能允许来接受改造的康德仁穿着雨靴下田?你对阶级敌人——国民党‘军统特务’,怎么能这样仁慈?!”
作为堂兄的万年青抬起头看了一眼万春山,也是一脸严肃地回答:“对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我们除了要好好监督他们、改造他们之外,也要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康德仁有风湿性关节炎的病,能带病参加劳动,还是服从改造的表现,他穿雨靴下田,并没有影响他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更没有影响其他社员的劳动,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一定要让他打着赤脚倒在田里,甚至死在田里,贫下中农社员才会高兴吗?康德仁是一个很好的、也是非常难得的反面教材,国民党‘军统特务’不仅我们大队只有这一个,听说全公社也只有这一个,我们要把这个难得的活靶子尽量保留得时间长一点,以便更好地教育青少年一代,让青少年一代都知道国民党‘军统特务’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不然的话,青少年一代就只有到电影里去看国民党‘军统特务’了。”
听到这里,万春山书记也不禁笑了,连连说:“那是,那是,只要康德仁还活在我们牛头山大队,青少年一代就都知道国民党‘军统特务’,其实就是穿长雨靴的特务!”
生产队长会议后的第二天,就康德仁穿长雨靴下田劳动的问题,万年青特地把他对万春山书记讲过的道理在牛皮塘生产队的社员会上又讲了一遍,同时也讲了万春山书记所做的精辟概括——“军统特务”就是 “穿长雨靴的特务”,用稻草垫着屁股,坐在晒谷坪的三沙地上开会的社员们听了,不少人笑得满地打滚。
从此以后,在牛头山大队就有了一个“军统特务”就是“穿长雨靴的特务”的说法,当然也就再没有人就康德仁的事情到万春山书记那里打万年青队长的小报告了。慢慢地,“军统特务”就是“穿长雨靴的特务”,又被简化成“军统”就是“长统”,社员们也都恭维地把发明创造权归属于万春山书记,书记自然欣然接受,社员们甚至发现从此以后春山书记对康德仁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眼里似乎也多了一份仁慈。
后来,万春山书记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病了,万春山的大姐把老母亲接到省人民医院治了半个月之后,病越发重了,春山书记只好按医院的要求,把老母亲接回来准备后事,可是他总是有些不心甘,便偷偷地托堂兄万年青请康德仁在晚上悄悄地去看了他母亲两次,老人家服了康德仁开的几剂中药之后,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万年青抓住机会,又在春山书记面前讲了康德仁很多好话,这之后,康德仁就很少被当做阶级斗争的靶子押到大队会上去接受批斗了。
二 因为刘少奇而改名的刘长青
高原白的满姑高秀英嫁在戚家山公社的和平大队石磨山生产队。
满姑有三儿一女,满姑父像莫言的岳父一样是石匠,他技艺高超,声名赫赫,在邻近的望化县一带都有名气,高原白家的麻石猪食槽就是他一锤一锤凿出来的,一般石匠凿出来的猪食槽,里面总难免有点凹凸不平,他凿出来的猪食槽,里面却光滑圆溜,像磨出来的一样。满姑父身材高大,力大无穷,他用一截硬实的圆木串紧一对两百斤重的石磨,双手举起来竟然毫不费力,就像举两个大饼一样地轻松。他说起话来声若洪钟,声震十里之外。他上嘴唇留着一撮黑黝黝、硬扎扎的胡子,人们都说他天生一副武官相,酷似从国民革命军转投共产党后成了大元帅的贺龙。
满姑父有一身好手艺,也有一身好力气,但他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一天挣满十分工却只值二角五分钱,而他到靠近省城红枫市、耕地少、社办企业红火的望化县做一天石匠却可以挣到一块五角钱,而且还包吃包住,因此他愿意用一块钱买生产队的十分工以便能换到一家人在生产队的口粮,但生产队长硬是不同意,后来他干脆说愿意用一块五角钱买生产队的十分工,生产队长还是不同意,生产队长在管控生产队社员上拥有绝对权力,他以威严的口吻教训满姑父:“如果生产队的劳动力都像你这样外流,那队上的农活让谁来做?!何况外流挣钱,作为生产队的一个社员却失去了生产队的控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自由散漫的表现,是可以押上台开批斗大会的……”
满姑父姓刘,原来名叫刘少希,因为和刘少奇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而且在花西话里,“希”和“奇”读音非常接近,语速快时念起“刘少希”来,似乎就是念的“刘少奇”,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满姑父因此受尽了生产队长和革命社员的嘲讽和羞辱,不得不想办法改个名字。最初他也想像红花江公社的刘家冲大队改名叫反修大队一样,改名叫刘反修,但又觉得再怎么反修,刘字还是去不掉的,“刘”字后面带个“反修”,也还是容易让人把他和刘少奇扯到一起。于是,他把他看过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的名字都过了一遍,他认为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的主要英雄人物、党代表洪常青的名字最有寓意,“洪”的读音与“红”相同,“洪常青”就是“红常青”,因此,他准备把自己改名叫刘常青。然而,他又觉得把英雄人物的名字直接变成自己的名字也未免太偷懒了,甚至也可以说太不严肃了,他想起自己在两兄弟中居长,而“常青”的意思不也就是“长青”吗?最后,他决定把自己改名叫刘长青。改名叫刘长青之后,虽然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当党代表看,但嘲讽和羞辱确实也绝迹了。可是,生产队长一说满姑父外流挣钱是“资本主义自由散漫的表现”,“可以押上台开批斗大会”,满姑父害怕再把他和“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总头子”刘少奇扯到一起,害怕真的把他“押上台开批斗大会”,因此就再也不说话了。
为了一家人的口粮,满姑父空有一身好手艺,只能死死地困守在生产队,如果不在生产队出工,而是执意外流做石匠的话,不但一家人都分不到队上的口粮,而且还会受尽生产队长和革命社员的歧视、排挤和刁难,挣到的那点工钱也买不到任何粮食,因为粮站的米、面都是凭粮票购买,供销社的副食品同样必须凭粮票购买,而粮票只有吃国家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的人家才会有,一般吃国家粮的人家粮食同样不够吃,又哪里还会有多余的粮票出售呢?何况当时的粮票也是绝对不允许买卖的,否则就会要背上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罪名。
由于儿女多且都年幼,加上满姑长年多病,满姑家自然就穷,一家六口一直住在满姑父兄弟分家时分的两间茅草屋里,家里的两张床都是土砖架起来的,她家的淘米水、洗饭锅的水都要烧开来当米汤喝掉,地上更是不会掉下一粒白米,家里任何一点能吃的东西都被格外珍惜,收藏得连老鼠都闻不到一点气息。满姑经常说,因为老鼠窜到她家总是捞不到一点好处,后来老鼠就像开了会一样,竟然都不去她家了,她家也就再也看不到老鼠的踪迹了。
三 姚家风水学和姚家男人
姚秋阿婆家是地主,她有四个儿子,除了大儿子讨过一房满脸麻坑的女人后来又病死了之外,其他三个儿子都是近30岁和30岁以上的人了,因为家庭成分是划入了另册的地主的缘故,虽然都长得标致又能干,但都讨不到老婆。她四个光棍儿子和他大儿子的三个子女都和她住在一起,虽然四个儿子都很孝顺,家庭也很和睦,但她像当时的学生作文里经常形容的地主婆一样,火烧芭蕉心不死,总是痴心地做着一个梦,希望还有女人不嫌她家是地主,愿意下嫁到她家,再为她添几个孙子孙女。因此,她对队上的年轻妇女——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都总是笑眯眯的,表现得特别热情,她总认为年轻的妇女们能催旺她儿子们的桃花运。队上的年轻妇女自然也很喜欢到姚家落脚休息,喝上一杯暖心的热茶,很多时候还能吃到姚秋阿婆殷勤奉献的她亲手做的酸浸菜、酸枣粑粑、红薯片子和炒米、炒黄豆等美味可口、独具风味的姚家零食。
姚家不愧是地主,不仅很会过日子,而且有一套祖传的颇具地方特色的姚氏风水学,据说姚家的祖上最初就是靠风水学发家的。
姚家的房子建在靠山的台地上,那个台地土质坚硬而又长年干燥。房子建好之后,姚家又根据“饭桌下藏粮食,不怕没有吃”的姚氏风水学原理,就在灶屋正中的饭桌下挖了一个口小肚大的葫芦状大地窖,里面能藏用大箩筐装的十几担红薯,地窖口上盖上和地表颜色一样的厚木板之后,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姚家饭桌的地下还有那么大一个内容充实的宝葫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专窖红薯的宝葫芦,姚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既可蒸煮当饭的红薯,又能切片熬汤加点红干椒丝当菜的红薯,还能吃到切片烫熟晒干后再油炸当零食或者一整个煨熟当零食的红薯。按照姚氏风水学的原理,因为长年得益于宝葫芦里蓄积了山土灵气的红薯的滋养,所以姚家的男人个个身强体壮,就像宝葫芦里出来的红薯一样生猛、棒实,又脆又甜,让一些女人看了就流口水,自然也就都带上了桃花运。
高原白在牛头山学校初中班的同班同学、朱大福的大女儿朱秋兰就曾承认,她家移民牛家湾队上之后,她就暗恋上了姚家兄弟中最小的老满。
高原白上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有位个高体大、成绩不好的大嘴巴女生也曾在同学中主动揭露说,她曾亲眼看到她的母亲跟随姚家兄弟中的老二进了老二的房间之后就顺手带上了房门,好久都没有出来。
姚家兄弟中的老三姚自华,更是很有故事。
老三个子高大皮肤白,五官俊朗人精神,衣服也总是穿得整整洁洁,请著名的王一裁缝做的中山装穿到他的身上就显得特别有款,他上衣的口袋上总是喜欢别一支象征文化和涵养的钢笔,他平时确实也喜欢看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因此他看上去很像城里下来的极有修养的知识型干部。老三常和姚家屋背后韶光公社新桥大队农场的知青们换书看,因为那群知青里有一位就是姚家的亲戚,是老三的表弟。一位从子江市下放来的女知青,在农场的知青宿舍见过几次老三认真看书的神态之后,觉得沉浸在书中的老三简直就是从九天仙界下凡的男神,因此就鬼使神差似的迷上了老三,比我们前面讲过的原牛头山学校里的张明媚对牛头山大队诊所里的王贝迟还要迷得深,女知青曾在送给姚自华的日记里写道:“自华啊自华,我真想不顾一切地死在你温暖的怀里,我即使一辈子做你的鬼,也是一个幸福的鬼、甜蜜的鬼!”因此,女知青暗地里总是想方设法翻过山头往姚家跑,哪怕在晚上她一个人翻山时,她也不怕碰到鬼。
城里下来的女知青可不同于土生土长的生产队女社员,她们在农村是受关注最高的人群,是受到了特别保护的人群,除了掌握她们前程命运,要为她们招工进城写鉴定评语的农村干部可以关起门来找她们个别谈话,或者因为劳动需要和掌握思想动态的需要可以光明磊落地带她们中的个别女知青上山砍柴、点穴播种之外,包括男知青在内的其他男性都是不能过分亲近她们、不能和她们单独相处的。如果让人知道了一个城里下来的女知青,竟然迷恋一个农村的地主崽子,总是往一个地主崽子家里跑,那可不仅仅只是一件让人笑话的个人小事,而是一件涉及阶级立场、必定会上纲上线的政治大事,是一件绝对会影响女知青前程,也绝对会把姚自华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时还会让整个姚家受累的大事,姚自华越想越怕,他害怕背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罪名,害怕牵累自己一家人,也害怕牵累那位女知青的前程,他只好主动向当时的生产队长牛金富申请到离家十几里路远的公社煤矿去挖煤,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
挖煤的男人们在几里路深的煤井下,除了头上戴顶柳编安全帽之外,浑身上下都是一丝不挂的,那位女知青也就不好意思再追到煤井下,去看挖煤的男人们汗水和着煤灰的黑屁股了。
责任编辑/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