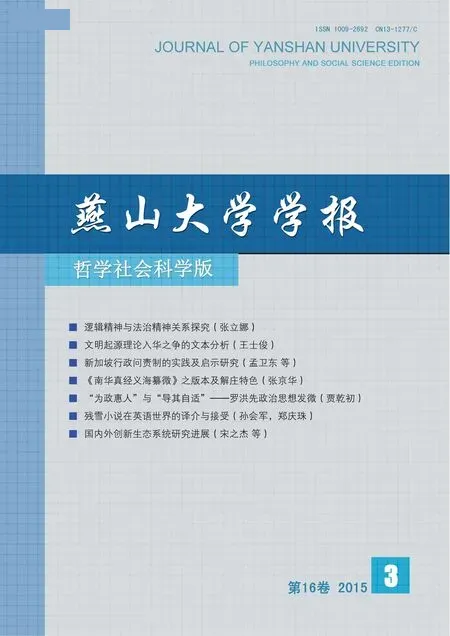元代江南文士的游谒与文坛风气
[摘 要] 元代江南文士以诗文为主要谒具,游谒于杭州、大都两个主要的文化圈中心。通过序跋、赠答、结社、唱和等方式,提高了异族统治下南方人文学创作格局的影响力,巩固了江南文化圈。在北游构建江南文士京城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融入大都文化圈,带来了题材、风格、文学理念的互动,奠定了南北融合的诗文走向基础,最终促成了多元文化融合下大一统的文化与文学,体现出元代文学以地域文明取代单一民族文明的发展特征。
[文献标识码]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50310107
[收稿日期] 2014⁃10⁃30
[作者简介] 张婉霜(1989—),女,河南温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生存命运总是与仕途穷通紧密相连。在儒家关注现世的主流传统思想影响下,积极入仕、追求功名成为绝大多数文士普遍具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儒者、文官、诗人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品格。纵观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 ①宋代以来,由于科举取士的扩大、官私学教育和印刷业的发展,士人阶层得到了空前的扩大。蒙元灭宋后,仍然保持延续态势,这从元代书院的数量和规模上便可见一斑。 ②但元初并未开科取士,科举之制废止达三十余年之久,即使恢复后其录取名额也非常有限。“宋代每届进士及诸科往往少则三百人,多则逾千人。元朝则汉人、南人总计不超过五十人。” ③元代的科举,就仕途的开辟而言,对于汉人儒生尤其是江南文士的仕进几乎是无足称道的。何况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无论统治阶级取士的制度有何种变化,干谒始终与文人的求仕相伴随。
元朝四等人的划分,使得江南文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远不如汉人文士,求仕之路更为艰辛。科举之路既被堵塞,而元代“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 ④的人才选用制度又在客观上为江南文士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和仕进机会,其谋生方式和职业选择呈现出较为宽容的多样化状态。在这种环境下,不少有意仕进的江南文士,便投入了游历干谒的大军,“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于用世,不用于科则欲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 ⑤。事实上,自南宋中后期始,以江湖诗人为代表的游士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元初江南文士的游谒在时间及地域上与其有历史的衔接。对于元代士人游谒之风盛行的背景原因、干谒方式、干谒对象以及干谒结果,已有学者详细探讨过 ⑥,为我们了解元代士人游历之风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不足之处在于,这些研究关于干谒对整个文坛风气的影响较少涉及。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元初江南文士的游谒与整个文坛风气的关系。
一、游谒杭州——对江南文化圈的巩固
元初科举既废,江南文士乃肆力于诗,如戴表元《陈晦父诗序》所云:“科举场屋之弊具革而诗始大出。” ⑦亦如何梦桂《王石涧临清诗稿跋》所云:“近世学子废举子业,好尚为诗。” ⑧对于元初的江南文士来讲,诗歌除了抒情言志外,一方面是交游的工具,另一方面便是获取名声,藉以干谒的工具。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干谒本身是一种主动的信息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功利性。而文人之游,以诗文为谒具无疑成为最现实最主要的干谒方式。“近世士大夫多失故常,拔出流俗,用文辞致声誉。” ⑨不难看出,元初江南文士以诗文干谒之风的盛行和对以文求仕的主动和重视。
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上层的高官贵族天然地具有意见领袖倾向,但其大多很难接近。尤其结合到文学风气传播来说,地位不够显赫但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成为文人士子心目中理想的意见领袖和干谒对象。刘诜《送欧阳可玉序》中的一段话颇能代表文士的普遍心理:“今之王公大人居则高堂重阶,陛犴守阍,出则崇牙大纛,武夫千群,介马填拥数十里,吾固未易见也。而以道德文章重海内者其人差易见也……其足有以诩予之进而策予之不逮也。” ËJS因此江南文士游谒杭州,其干谒对象一般为东南文坛大家或是在江南长期做官的北方文士。
元初以来,作为南宋旧都的杭州,文化底蕴深厚,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优美,加之战争对经济冲击较小,恢复很快,所以一直延续了其江南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由宋入元文人的集聚之地和活动中心,如方回、周密、戴表元、赵孟頫、仇远、白珽、袁桷、邓文原等都长期盘桓于此。而较早到江南任职的“北人”,如胡祗遹、卢挚、高克恭、鲜于枢等,也十分倾慕江南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柳贯曾说:“游仕于南,而最爱钱塘山水者,余及识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彦敬、梁贡父、鲜于伯机、郭佑之。仲芳、彦敬兴至时,作竹石林峦,伯机行、草书入能品,贡父、佑之与三君俱嗜吟,喜鉴定法书、名画、古器物,而吴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数人。” ËJT他们活跃于杭州、吴兴及周边地区,多与江南文士聚会唱和,往来频繁。如鲜于枢,字伯机,渔阳(今天津蓟县)人。至元十四年(1277)于扬州出为江南诸道行台御史掾,次年在扬州与赵孟頫相识,成为友善终生的莫逆之交。至元二十四年(1287),鲜于伯机以材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改江浙行省都事,与戴表元相识。 ËJU此时,仇远、白珽、屠存博、张仲实、邓文原等江南好友亦皆在杭,可谓是群贤毕至,戴表元五古《客钱塘赠鲜于伯机邓善之诸君,兼讬善之书剧达寄赵子昂》描述了众友相聚的情景。至元二十六年(1289)高克恭的杭州之行,也与鲜于枢交往甚密,还一起参加了李仲方的葬礼。 ËJV后退隐杭州西溪,死后也葬在这里。又如高克恭,字彦敬,占籍大同。至元二十五年(1288)被桑哥提拔为右司都事,次年以“遣使江淮省,考核簿书”的身份被派往江淮,成为“钩考”钱谷文簿的使臣之一,至元二十七年回京。此间高克恭卓然独行,不屈权势,在江浙坚持“一用平恕”做法,得到了江南士人的认可与好评。尤为难得的是,他广泛搜求江南贤士,或积极举荐,或就地任用,典型的如任职杭州时结交的江南“五俊”均被其荐于元廷任职 ËJW。至元二十八年,出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再次来到杭州。自至元二十六年(1289)起,高克恭的仕宦生涯和文艺创作均与以杭州文士群体为中心的江南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周密、赵孟頫、“江南五俊”等人渊源甚深。周密在宋末元初是杭州乃至江浙文人的中心人物,博雅多识,诗词兼擅,精通书画鉴赏及博物之学,又谙悉宋朝史实掌故。宋亡后,“亢节遁迹”,不仕新朝,日以著述、鉴赏和雅集酬唱优游岁月。据其《云烟过眼录》载述,高克恭的藏品有“金儒鸣玉”古琴、“唐摹《兰亭》一本”、“蒲序墨一笏”、五代画家周文矩的《韩熙载夜宴图》和宋代画家赵昌的《折枝》等。可见,他们必定经常在一起赏玩、雅集。赵孟頫与高克恭相识于大都,相知于江南,二人之间有大量的相互题诗,如赵孟頫《题高彦敬画二轴》、《题高彦敬〈树石图〉》、《题彦敬〈越山图〉》,高克恭《赵子昂为袁清容画春景仿小李》、《题管夫人竹窝图》。可以说,高克恭长期宦游江南尤其是杭州,与杭州一带诗人、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等颇多往来,使杭州成为南北艺术家共同活跃的舞台,作为元代多元民族文化融合和大一统下南北文化交流的典范,引领了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文化风气。高克恭虽为北人,实际上已深受江南文化的浸染,其对于江南文士的同情理解和真诚帮助以及本身的文学艺术成就均获得了江南文士的普遍好感和极大认可,已然成为掌握一定话语权力的江南文坛领导者和极佳的干谒对象。
“江南五俊”之一的邓文原便受到高克恭的知遇之恩:从邓文原的履历看,“暨科举事废,遂一意务为圣贤之学,行益修、业益茂。开门授徒,户履常满,中州士大夫多慕而与之交。徐文献公琰、高文简公克恭知公尤深。” ËJX邓文原由于清修苦学、开门授徒,学问名气影响很大,以至在杭州时就受知于中州士大夫。据邓文原《故大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说:“文原自公为都事使杭,首受公知,亦与在举中。” ËJY可知邓文原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被杭州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一职,是受到了高克恭的举荐。虽然路儒学正一职低微到没有品级,其任命甚至也无须得到朝廷的认可,但对于当时科举制废除之下的读书人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邓文原受知于中州士大夫,从而与他们之间进行诗文上的切磋,提高了异族统治下南方人文学创作格局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这实际上亦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开始。与此同时,邓文原在这一时期得到中州士大夫的推崇,也为后来北上被京都文士如阎复、姚燧、王构所认可并融入大都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另外,江南士人在杭州的干谒活动与唱和群体、文人集团的形成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杭州为南宋旧都政治、文化中心,宋亡后聚集着大批的遗民文士和南下宦游的“北人”。尤其是前宋进士,声望地位较高,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宋元诗社盛行,元初江南诗社多由前宋遗民组织参与,杭州的诗社有西湖诗社、西湖吟社等,虽说此类诗社重在联系、团结广大遗民以砥砺名节、抒发亡国之痛。但也不排除有借助诗社结交名流,通过唱和、品第、标榜等常见的诗社活动扩大社会影响,达到干谒之目的者。卫宗武《为吟友序饯行诗》云:
钱塘吟社光价远扬,几使江浙倾动,其间笔力雄迈,可相颉颃者,指不屡屈,湛溷其一也。……白君,守儒也,不肯枉道以徇俗,荣禄又何足浼然。则时乎时乎,而遂已乎?蠖屈必伸,龙蛰始奋,当不止以诗名世而已也。 ËJZ
白君,即白珽,其“所交南北知名士,如文本心、何潜斋、刘须溪、牟献之、方万里、夹谷士常、闫子静、姚牧庵、卢处道诸公,莫不礼遇,相与为忘年之游” ËJ[,可见其交游范围之广。“当不止以诗名世而已也”,概指其有志于世,以交游行干谒之事。为求干谒也好,为求精神寄托也罢,总之,江南文士对诗社的浓厚兴趣,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诗社的繁荣和文学创作群体的壮大。南宋末年,临安的诗社只有西湖诗社和西湖吟社两家而已,而到了元初,诗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月泉吟社诗》注,仅杭州一地,有名可考的诗社就有杭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两湖社等。不仅数量众多,规模较之宋代诗社也有所扩大。在杭州诗社的影响辐射下,江南其他地方较著名的还有越中诗社、山阴诗社、汐社、月泉吟社,以及浙江庆元遗民群一月一集的唱酬会等。
通过结社、唱和、干谒、交游,这些掌握着文坛话语权力的意见领袖,与围绕在其周围的江南士人切磋诗文、探讨义理、燕集聚会,由此建立起具有一定组织性、自觉性和代表性的江南文士社会群体网络。他们虽然政治地位低,但在文化上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通过与南来的“北人”平等切磋,不仅显示出江南文化不可忽视的优秀潜质,而且在“诗社”和“朋友圈”的团体认同下,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途径,不断获取文化归宿感和话语建构权,从而完成异族统治下对江南文化权力秩序的维护,对于巩固彰显江南文化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游谒大都——与大都文化圈的融合
“京师,风雨之所交也,文献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辏也。……遇则能使吾贵如瑚琏,通则能使吾明如秉烛,尊则能使吾重如九鼎,进则能使吾荣如春华,然则舍京师无适已。” ËJ对于游谒以求进身的江南文士来讲,大都无疑是最理想的干谒之所。
江南文士北游大都,有幸运得售者。据《元史·陈孚传》载:“陈孚,字刚中,台州临海人。幼清峻颖悟,读书过目辄成诵,终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为转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 ËKS前宋进士李洧孙(字甫山)元初“屏迹海上,箪瓢晏如……达官贵人有知先生者,强起而致之京师,先生因作《大都赋》以进,一时馆阁诸公,咸共叹赏,交荐于上,擢教授杭学,而其赋遂为人所传诵。” ËKT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范梈“年三十余,辞家北游,卖卜燕市,见者皆敬异之……已而为董中丞所知,召置馆下,命诸子弟皆受学焉。由是名动京师,遂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ËKU这些事例说明元代“仕进多歧”的入仕方式确实为江南文士之游走干谒提供了相对便捷的条件和相对广泛的选择空间。如袁桷所说:“自骋举之法疏,人得以易售。” ËKV方回《送仇仁近溧阳教授序》亦云:“昔之仕也,难于仕而易于达,今之仕也,易于仕而其达则难。……何易于仕而难于达?学校之士,自县教谕,为山长、学正,一任即可,入路府州教授以入流,路府州县诸司存吏以年劳,为吏部且提控,考满则外省咨内省以入选,军功随军,此不可论,似乎入仕之甚易也。”“入仕之甚易”的说法值得商榷,但面对成功者的幸运,江南文士既心生羡慕,也倍受鼓舞,极有可能成为其北上游谒的一个心理动因。
游谒大都,其干谒对象一般为大都江南籍官员和倾向汉法的蒙古、色目高官以及北方汉人官员。元朝统一之后,一些倾向汉法的蒙古、色目官员如廉希宪、余阙等比较重视收罗举荐江南文士,这在江南文士的成功仕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一些江南文士应召到京城中书省、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国子学等处做官,如赵孟頫、张伯淳、袁桷、邓文原等,大多为名望或势力根底深厚之人。由于地域和师承上的联系,江南文士很自然地与这些拥有诸多共同兴趣爱好的大都江南籍官员交游往来,建立起江南文士京城社会网络,进而更快更好地融入大都文化圈。前面已经提到邓文原知遇于高克恭而被荐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1298),成宗召金书《藏经》,邓文原又以才名被征,第一次离开杭州随赵孟頫入京。此行,不仅增加了他在元廷的知名度,更在南方文士中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他本人也由此开始了几十年的仕元生涯。在与京都士人的交游中,邓文原积极融入大都文化圈:大德五年(1301),邓文原擢为应奉翰林文字,“承旨阎文康公复于僚友少所假借,公独见推重,凡大撰著,必属焉。”且元代的馆阁诗文风格,也是肇源于邓文原,“当大德、延祐之世,独以词林耆旧主持风气。袁桷、贡奎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 ËKW。东平人王士熙曾师事邓文原,“博学工文,声名日振”,论者以为有元盛世之音也。王士熙诗歌中的盛世之音,很明显是师承邓文原而来。
事实上邓文原为官期间,反过来又作为受干谒者提拔奖掖了很多江南士人,如虞集、黄溍、泰不华、吴莱等,为元代中期大都文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后继人才。检索虞集的诗集可知,写给邓文原的诗歌有《次韵邓善之游山中》、《柬邓善之游山中》两首。借《柬邓善之游山中》一诗,虞集表达了希望邓文原引荐的愿望:
山雨不来喧静夜,江云犹为护晴朝。一群青雀墙花老,几个黄鹂苑树遥。何有深心期管乐,独无高步接松乔。未能径去成飘忽,且可相从慰寂寥。
“何有深心期管乐,独无高步接松乔”,虞集在这里将邓文原比作松乔,而将自己比作墙花,干谒的意味相当明显。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受干谒者是文学传播的受众。传统文人入仕心理的内在契合,前辈先达之士的荣誉和社会责任感,使得多数受干谒者愿意积极鼓励、引荐和延誉后进晚生。经过受干谒者的反馈过程,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双向互动,其过程中传达出的文学思想和处世见解,更是提高了文学传播的附加值。
邓文原作为东南诗文风格的坚守者,北上后又成为大都文坛盟主主持风气,一生往返于杭州与大都之间,在衔接南北士人,融合南北诗文风格,元代初期文坛向中期文坛的过渡中,都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干谒在元初江南士人社会地位不高和仕途受阻的情况下,不是一般意义上小人投机取巧的行为,他是士人反抗不公平命运的举动,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至少使得元大都有了江南士人的声音,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和诗文理念,不仅为元朝的汉法取向提供了舆论支持,也为元代中期以来江南文士大量北上入仕大都奠定了舆论和社会基础。对于选举制度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三、奠定南北融合的诗文走向基础
关于地理环境与文风的关系,早有前人论述:“某尝谓气类近,风土远。气类才绝,便从风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来皆做出婺州文章,间有婺州州乡谈在里面者。如吕子约(祖谦)辈是也。” ËKX人的气质对文风起主要作用,地理环境起次要作用。在气质相近的情况下,决定文风的是地理环境。清人张金吾在《金文最》序言里说道:“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先后相望。惟时士大夫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后之人读其遗文,考其体裁,而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脆。”一道秦岭、淮河和无形的政治、军事高墙分裂了南北,使南北文风各自朝着柔脆和坚强单方向发展。金宋入元以来,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文坛风气逐渐改变。
元代江南文士在南北大一统局面下北上游谒,伴随着山河激荡,视野大开,逐渐改变了宋季以来南方文坛江湖诗风弥漫下的狭窄委琐之气和门户之争,风气为之一变。
汪梦斗入元后,被荐至大都,不受官而还。虽然没有接受官职,但纪行之作却使其作品增色。纪行之作《北游集》自序中说:“余生于南,自少至长,冉冉老矣,而未尝得至于南之极。岷峨在吾舆图,而生平未尝西行。冬至云间见海矣,自以为东之极。今天下东必至登莱,才为极,足亦未至。而北乃直至秦长城下,则此游可以为北之极。且以余有生时言之,北至淮极矣,借得在全宋盛时,北亦止极白沟耳。今逾淮,又逾白沟,信乎此游为北之极。吁,其亦可喜也夫,其亦可悲也夫。” ËKY所谓“宏才博学,必待山川之胜有以激于中而后肆于外。” ËKZ
对于主动北上游谒的南方文士来说,失意而归也是常事。对理想的追求、美好的期待与严酷现实之间的落差足以激起江南文士的不平之鸣,在登临吊古中极易引发故国之思和历史咏叹。江山之助与家国之恨交杂,其可喜亦可悲的复杂情感体验,扩大、丰富了诗文创作题材内容,推动了诗文风格的转变。
宋末元初的张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故宋时为王孙公子,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宋亡后家道中落,渐次窘迫。至元二十七年(1290),43岁的张炎与曾遇、沈钦一起应诏北上大都,为元廷缮写金字《藏经》,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旧人,“庚寅秋九月之北,遇汪菊坡,一见若惊,相对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因赋此词。” ËK[次年,未得官南还。这从舒岳祥、戴表元等对其北游的记述中可以得到印证:“玉田张叔夏,与余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于是风神散朗,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强仕,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 ËK北游之后的张炎,自称“把秦山晋水,分贮诗囊” ËLS。迥异于软媚秀丽的江南山水,北方地理地貌和气候的差异带给诗人极大的审美惊奇。其词作中北方山水自然意象的苍凉粗犷宏大,与词人自身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悲融为一体,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沉郁深厚,境界也更为开阔,对其清丽有余而气魄不足的词境有所突破。以《壶中天·夜渡古黄河,与沈尧道、曾子敬同赋》为例:
扬舲万里,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须信平生无梦到,却向而今游历。老柳官河,斜阳古道,风定波犹直。野人惊问,泛槎何处狂客?
迎面落叶萧萧,水流沙共远,都无行迹。衰草凄迷秋更绿,唯有闲鸥独立。浪挟天浮,山邀云去,银浦横空碧。扣舷歌断,海蟾飞上孤白。 ËLT
清代词论家陈廷焯盛赞此词:“高绝、超绝、真绝、老绝。风流洒脱,置之白石集中,亦是高境。结更高更旷,笔力亦劲。通篇骨韵都高,压遍古今。” ËLU
除了北上游谒大都之外,宦游南来的北方文士集中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圈,为江南文士游谒南下北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北上南下的过程中,南北诗文风格的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张之翰,字周卿,号西岩,邯郸人。中统初,任洺磁路知事,官至松江府知府。其以北方之士宦游江南、八闽等地,由北到南的经历,使他曾对当时南北之诗作过如下评价:“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 ËLV“欲兼之者”,方是创新之举,可谓别具只眼。在《跋<草窗诗稿>》中,他既赞赏南方后学建安刘近道诗歌“风骨秀整,意韵闲婉”的一面,又希望其能游历北方山水之雄奇,以燕赵、邹鲁之风扫却腐熟:“中原万里,今为一家。君能为我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华,历汾晋之郊,过梁宋之墟,吸燕赵之气,涵邹鲁之风,然后归而下笔,一扫腐熟,吾不知杨、陆诸公,当避君几舍地?但恐后日之草窗自不识为今日之草窗也。” ËLW明显寄寓着以游历学习北方之长补救南方诗坛气骨纤弱之弊,兼融南北诗风之意。在晚年给白珽的送别诗中,对白珽自愿学习司马迁的游历精神给予了由衷赞扬:“今年复何年,邂逅松江边。梅花欲开雪欲落,问君胡为北趋燕?君言南北久分裂,混一光岳气始全。平生眼界苦未宽,要看中原万里之山川。恨余无文宠赠盖邦式,喜君有志愿学司马迁。渡江踰淮入泗汶,指日可系都门船。昭王一去年几千,黄金台上荒秋烟。视吾胸中耿耿然,浮薄宦,奚足怜?行囊不妨无一钱,从今满贮观光篇。” ËLX除了鼓励江南文士北游外,他也主张中州人士游历南方,“至元癸未,余来山阴府,从事张从之以《止轩诗轴》相示,盖渠乡中时所得也。余谓中州诸名軰如此,老天假之年得见混一,使之登会稽、探禹穴,其所作岂止此耶!” ËLY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与江南文士方回、戴表元、赵孟頫、白珽等谈文论道,在创作中自觉地融合南北风格,为北风南下、南北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其《菩萨蛮·暮春即事》词:“梁间双燕呢喃语,想曾知得春归处。问着不应人,芹泥香正匀。翠阴庭院悄,手摘青梅小。天气恰清和,越衫犹薄罗。” ËLZ动静相合,意境幽婉,读之清新爽朗,实为南北文风交融之作。
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古代社会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媒介手段,文学风气的传播主要依靠诗歌等单一静态的传播形态实现。诗歌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人的情感的延伸和生命的表达。通过序跋、赠答、雅集、酬唱等形式,诗歌成为了文人之间最好的沟通传播媒介和消费方式。在元代大都、江南两个最主要的文化场域内,伴随着江南文士的游谒,大量的文人及其作品被迅速认知,诗文理念得到互动,促进了南北诗文风格的凝聚与融合。
四、结语
由于地域广大,但建国时间并不长,所以元代诗文发展与唐宋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历史分期,但这恰恰使其呈现出渐进性、层次性和长期性的复杂特点。同时,由于元代之前长期存在的南北对峙状态,使得元代文坛有显而易见的地域特点。元代有籍贯可考的511位文学家集中分布于北方燕赵文化区和南方吴越文化区。可见,南方虽然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但文化优势依然存在,这是文化相对稳定性的体现。而北方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则明显由关中、中原地区转移到了黄河以北,即燕赵、河东地区。从前的关中(长安)——中原(洛阳、开封)——齐鲁(济南)这一东西走向的文化轴心已经被燕赵(北京)——河东(太原)——齐鲁(东平)——吴越(苏州、杭州)这一南北走向的文化轴心所取代。 ËL[
中国古代的文学运动,大多是自北而南的走向。南渐之后,由南方唯美唯艺的丽辞写作范式对其改作重构,从而以审美代功利,刚柔兼济。元代江南文士北上大都,融合南北精华,取北诗之豪宕、南诗之清丽,弃北诗之粗笨、南诗之纤细。南北文化的迁移扩散、碰撞交流,在文人之游历干谒中得到了实现。发展到元代中期大德、延祐年间,南方文士最终取代了北人的文坛主导地位,将南北文风的融合推向了高峰。这一过程,不拘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多元文化,在近一世纪间融会成横贯南北的“大一统”的文化与文学,体现出元代文学以地域(区域)文明取代单一民族文明的发展特征。
注释:
①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1页。
②根据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的统计,宋代有书院711所,元代则有书院296所,但相比较而言,宋代立国300余年,而元朝立国则不足百年。由此可见,元代书院在宋代基础上是有很大发展的。
③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④宋濂:《元史》卷八一,志第三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16页。
⑤⑩李修生:《全元文》卷六八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册,第58页。
⑥可参阅丁昆健:《从仕宦途径看元代的游士之风》,《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印行;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史伟:《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黄二宁:《元代南人北游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⑦戴表元:《剡源集》卷九,四部丛刊景明本。
⑧李修生:《全元文》卷二五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册,第134页。
⑨牟巘:《陵阳先生集》卷一二,民国嘉业堂刊本。
(11)柳遵杰点校:《柳贯诗文集》卷一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12)《困学斋记》:“丁亥之春,余识鲜于伯机于杭。”戴表元:《剡源集》卷二,四部丛刊景明本。
(13)《故大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李仲方,公故人也,以两浙运司经历卒于杭。公为卜地,葬之西溪,且为文志其墓,与郭佑之、李仲宾、鲜于伯机、王子庆等祭之,哭尽哀。”邓文原:《巴西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五俊”为:邓文原、敖继翁、姚式、倪渊、陈康祖。
(15)李修生:《全元文》卷九六九,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0册,第183页。
(16)邓文原:《巴西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卫宗武:《秋声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周暕:《湛渊静语序》,白珽《湛渊静语》,丛书集成初编本。
ËJ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宋濂等:《元史》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38—4339页。
(20)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八续稿一五,元钞本。
(21)揭傒斯:《文安集》卷八,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2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处士黄仲正甫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2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集部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6页。
(2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四〇,中华书局,1986年版。
(25)李修生:《全元文》卷六一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册,第680页。
(26)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中庵集》卷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张炎撰、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28)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第116页。
(29)张炎撰、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页。
(30)张炎撰、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31)陈廷焯《云韶集》卷九,孙克强、杨传庆点校整理《云韶集》辑评(之二),《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24卷第4期。
(33)(34)(36)张之翰:《西岩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张之翰:《西岩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张之翰:《西岩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12页。
Jiangnan Scholars′Lobbying and Literary Circle′s Climate in Early Yuan
ZHANG Wanshuang
(CollegeofLiberalArts,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In early Yuan,Scholars in Jiangnan distric take poems and proses as main lobbying form and are ac⁃tive in the two literary center Hangzhou and Beijing(the Capital).They expand the influencing power of south⁃ern people′s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fortiy literary circle in Jiangnan distrcit.These scholars keep trying to fit into Beijing(the Capital)litaraty circle by connecting with social network in Beijing which bring interaction of liter⁃ary themes,styles and philosophy.The bedrock of merging northern and southern literature gets laid and leads to unite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hich signify the developing character of regional civilization replaing mono ethnic civilization.
Key words:early Yuan;Jiangnan Scholoars;lobbying;literary circle′s climate
[责任编辑 董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