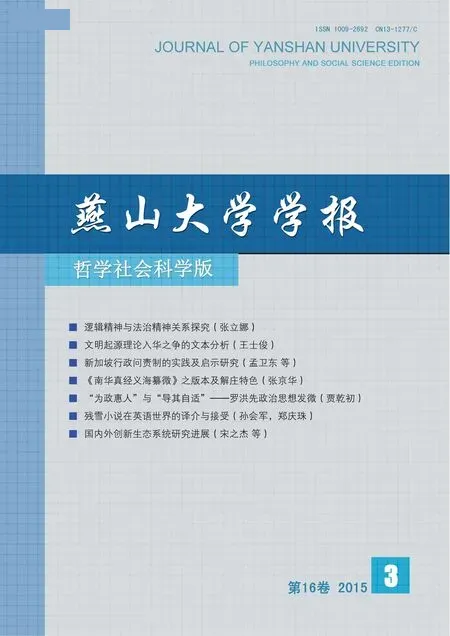《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之版本及解庄特色——以三教会通为外,道迹辨析为内
[摘 要]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零六卷,征引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之说。宋以前解《庄子》者,赖是书以传。褚伯秀,又名师秀,字雪巘(一说号雪巘),号环中子,又号蕉池道士、蕉池叟,宋元间钱塘人,为杭州天庆观道士。近年学者的相关研究,于《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之版本,多不言其详;于作者著述宗旨,多仅言及三教会通、以儒学理学入庄而止。兹略加梳理,抛砖引玉,以启来学。
[文献标识码]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50305705
[收稿日期] 2015⁃06⁃15
[作者简介] 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
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之版本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书,有《正统道藏》抄本、《四库全书》抄本、朱得之《庄子通义》(附刊)三种,近年均有影印出版,故为学者常见。明李栻有《南华真经义纂》十卷,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云:“纂集并删并褚伯秀《南华义海管见》及朱得之《庄子通义》二家之说而成”,明万历刊本,在《道书六种》中。其书未见。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的刻本,迄未见官私著录或学者论及。如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著录《道藏》、民国影印《道藏举要》及《四库全书》三种,陈品卿《庄学新探》(1983)附录《历代庄学版本及其现藏》著录《道藏》本一种,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2008)著录《道藏》及《四库全书》二种。
仰蘅《武林玄妙观志》卷二《人物》称此书“梓于咸淳乙丑之岁,奉旨入《道藏》”,“咸淳乙丑”显据刘震孙、文及翁、汤汉三《序》而来,“梓于”一语则系臆加。卷四《褚伯秀武林诗话二则》注云:“出王云谷所刻《义海》”,实则王云谷并未付之刊刻。推测此书的存世流行始终只是抄本。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抄本,最早当在道教道观中。北宋前后五次纂修道藏,即如书首“诸家注义姓名”所载“颁行入《藏》”、“陈详道注:《藏》本”、“已上五家并见《道藏》”之类。南宋不再续纂,所以褚伯秀此书没有机会颁入《道藏》,但仍然会在道教道观中传写流行。元代《道藏》今亦不存。今所存明代《正统道藏》中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抄本,最可能是源于道教道观。它也可能自民间学者搜集而来,但至少与《四库全书》抄本不一来源,二者文字差异较多。(《四库》本所据原本有误处,《道藏》本多不误,可知其原本不同于《道藏》本。)故兹假定《正统道藏》本系出自道教道观的历代传写。
《四库全书》抄本,《四库提要》谓出“浙江巡抚采进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谓出天一阁藏明抄本。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云:“《庄子义海纂微》一百六卷:天一阁写本,宋中都道士褚伯秀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74页)天一阁明抄本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至今仍有部分尚存。据骆兆平《天一阁散书访归录》所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存十卷。元褚伯秀撰,明蓝丝阑抄本一册。全书一百另六卷,部分散出,劫后存四十七卷,今又访得卷八十二至九十一。”(《文献》1990年第1期)兹假定《四库全书》抄本系出自民间学者的历代传写。
《四库全书》之编纂,四库馆臣王太岳等纂《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内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考证一百零三条,多称“据别本改”、“据别本增”、“据别本删”,其“别本”不知何本,是否别有其它抄本未可知。
官私著录论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也往往为抄本。如阮元《文选楼藏书记》云:“《庄子义海纂微》一百六卷:宋中都道士褚伯秀辑,抄本。”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一下云:“路小洲有抄本。”此外日本静嘉堂文库十万卷楼旧藏本著录云:“《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六卷:宋褚伯秀撰,写,十二册。”日本公文书馆昌平阪学问所本著录云:“《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宋褚伯秀,江户写,四册,存二十六卷。”
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又号参元,室名浩然斋,靖江人,为王阳明晚年客居靖江时弟子。《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称:“其学颇近于老氏,盖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光绪《靖江县志》卷十四《人物志·儒学》称:“大抵得之之学,体虚静,宗自然。”著作有《庄子通义》十卷(嘉靖三十九年刊)、《列子通义》八卷(嘉靖四十三年刊)、《老子通义》二卷(嘉靖四十四年刊),合称“三子通义”,均朱氏浩然斋刻本。又著《宵练匣》十卷、《印古诗说》一卷,纂修《靖江县志》八卷。
朱氏《庄子通义》一书,《四库提要》评价极低,认为“议论陈因,殊无可采。至于评论文格,动至连篇累牍,尤冗蔓无谓”。其书完全因循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而来(全取褚氏“管见”、“总论”,而不取其十三家集注),朱氏仅在正文处加旁注,题下及章末加“通义”,又书首有《读庄评》十三则而已。
今检《庄子通义》各卷下题名云:“参元朱得之旁注并通义,附钱塘褚伯秀义海纂微,云谷王潼录校刊。”又《读庄评》第十二则云:“褚氏伯秀《义海纂微》作于胜国时,因避地遗于滇南,其《自序》可考也。余同门友钱塘王云谷游览四方历三十年,穷乡绝岛莫不探陟。嘉靖初至彼,见之,手录以归。乙卯疾,将革,以授余曰:‘烦兄图广其传,毋使褚氏之心终泯也。今刻从其情,得失不易字,信褚氏、信云谷也。’”又《庄子通义目录》下小字注云:“褚氏《义海纂微》其籍自拟篇目,自为《后序》,今刻既附其籍,因亦附注其目于篇目之下,并存其序于后。间有脱简、重出,俱仍其旧。”
观此可知其书亦由保存褚氏而起,原本并未隐去褚伯秀之名,而文字亦多循旧不改。所谓“附钱塘褚伯秀”云云,著作家不得不如此说,其实乃是以褚伯秀为底本而以己之“通义”附之,故其书由四库馆臣而言为“陈因无可采”,由褚氏而言,所谓“得失不易字”、“脱简、重出,俱仍其旧”,正赖此而得一传本,实为褚氏之功臣。
比较《正统道藏》本与朱得之《庄子通义》本,其褚氏“管见”、“总论”部分,往往《道藏》本有误,而《庄子通义》所引不误。但也有《庄子通义》缺失而《道藏》本完好者,如《庄子通义》卷六《至乐》篇末云:“此篇褚氏不为总论,意其指无不明也。”今《道藏》本褚伯秀总论尚在。
而二者最大的文字差异,在于书末的跋文。
《道藏》本《天下篇》卷末没有“跋”或“后序”之类标题,内云:“竹溪林公鬳斋先生,乐轩之嫡嗣也。”中隔陆德明所论及刘概统论二节,另外分章云:“南华著经,篇分《内》《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礼乐刑政之大纲,内圣外王之道有在于是”云云,文末有“咸淳庚午春,学徒武林褚伯秀谨志”署款,体例即不严整。
《庄子通义》本书末题《褚氏后序自撰》,内云:“竹溪林公鬳斋先生,乐轩之嫡嗣也,其《口义》有所受。序曰:南华著经,篇分《内》《外》,所以述道德性命之几微,内圣外王之指决,礼乐刑政之大纲。”(“所受”二字草书,谢祥皓《庄子序跋论评辑要》未读出,而连读作“《口义》有□□序”,谓不知“究竟谁人书写”。仰蘅《武林玄妙观志》卷四读作“所受”。)《道藏》本分章处,《庄子通义》所引前称“序曰”,后署“咸淳庚午春,学徒武林褚伯秀谨志”,首尾完整。草书制版,并且文字多出,意义优长(如《道藏》本“见谓僻诞”,《庄子通义》作“读者俱谓僻诞”。《道藏》本“莫窥端涯,与《列子》”,《庄子通义》作“觉其与《列子》”,皆以《庄子通义》义长)。特别是《庄子通义》的标题,所谓“自撰”云云,当即“手书”、“手迹”之意。按《庄子通义》书首有《刻庄子通义引》,署款“皇明嘉靖庚申腊日,嘉靖朱得之书”,行书,风格瘦硬,当为朱得之手迹。《褚氏后序自撰》为草书,书法圆润,与之不类,而字体雍滞,似为反复摹写所致。是则可以推测此文源出褚伯秀手迹,而《庄子通义》所本亦有可能为褚伯秀手订之稿本。
王潼,号云谷,生平不详,但其为钱塘人,当熟知天庆观(玄妙观)、褚伯秀事迹。朱得之《读庄评》称王潼得见《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于滇南,“手录以归,乙卯疾将革”,授朱得之。可知王潼卒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实未及见其书刻成,《庄子通义》各卷下题名云“云谷王潼录校刊”亦著作家语,以志其能存抄本也。(《四库提要》亦谓:“《义海纂微》未行于世,王潼录其遗稿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于每段之下,先列《通义》,次及《义海》。”)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于咸淳元年(乙丑1265)纂成,而褚伯秀大约到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始卒,中间三十年应当会有誊抄的正本,保留在天庆观中。而褚伯秀的手稿本可能由褚氏自行安排,后来辗转流散到了云南。
但《读庄评》又称《义海纂微》“遗于滇南”,“《自序》可考”,而《道藏》本及《庄子通义》均未载《自序》。若指《后序》而言,则《后序》亦未言“滇南”事,未知何故。
又《武林玄妙观志》卷四《褚伯秀武林诗话二则》引王云谷题记云“友人从滇南来”,而不言王氏自往滇南,亦未知何故。
《武林玄妙观志》卷四录《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跋》全文,文字与《道藏》本不同,而与《褚氏后序自撰》全同(个别草字辨认有误),但又未言出自《庄子通义》,所称褚伯秀《诗话》及刘震孙等三《序》亦不见于《庄子通义》,似乎王潼本亦别有流行,其书后当有《诗话》“附刊《义海》之后”。兹推测仰蘅所录《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跋》出自《褚氏后序自撰》,仰蘅所云“出王云谷所刻《义海》”即《庄子通义》卷目所题“云谷王潼录校刊”,而仰蘅所录三《序》则另有所本。([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六亦仅录三《序》。)
二、《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之体例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书体例,乃是集注体与著作体的合璧。集注体也应当包含作者本人的见解,但是褚伯秀此书由其书名分析,“义海”似专指汇纂前人批注,“纂微”则专指自己所注的部分。
其中“义海”按照前后一定的次序排列各家批注,各家均单列一章,无论其见解裁断是否,均隐括出完整的大意,有似后世“长编”的做法,(但所抄录文字多有缩节,对比今存郭象注全本可以推知。)从而使得各家批注基本完整地得到保存,乃至于可以赖以“复原”出若干单独的著作,是其集注方法颇有优长。
“纂微”实际上包括“管见”、“统论”两部分。《正统道藏》及《四库全书》抄本,《庄子》正文顶格,集注退一格,“管见”与“统论”再退一格。章末为“管见”,卷末为“统论”,各自分别抄写,或标出“褚氏管见”、“褚氏总论”,或略而不标。其中“管见”又分为疏通大意与训诂字句两部分,中间以圆圈符号分隔。可知褚伯秀本人著作这部分,其体例亦较为完备,亦可不必依附各家批注而独立。(朱得之《庄子通义》称“统论”为“总论”,其书只录褚伯秀一家而标为“义海”,恐误,当标为“纂微”为宜。)
其书集注部分,征引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之说。又多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从陈景元《南华真经解义》间接引用徐铉、徐灵府、张君房、文如海、张潜夫、刘得一及成玄英诸说。其中宋人集注,今多失传,仅林希逸《鬳斋口义》等少数著作完整保存,故而价值极大。如四库馆臣所论,“盖宋以前解《庄子》者,梗概略具于是。其间如吴俦、赵以夫、王旦诸家,今皆罕见,实赖是书以传。则伯秀编纂之功,亦不可没矣”。(《四库提要·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四库馆臣又论:“是书主义理,不主音训也。”此语殆由清学而论宋学,按宋人治学,往往兼包训诂、义理二者,甚至如朱子之醇儒,集注《四书》亦未尝不训诂字句,惟不以训诂字句为极致。盖读书在于明理,而明理当先明字句。今读褚伯秀“管见”,其中辨析版本、句读、字义,往往一言而开悟积疑,其精辟处足成一家之言。清儒穷尽搜讨,苛察缴绕,碎义逃难,其弊使人误以训诂为极致,治学渐失宋人之弘阔。
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之解庄特色
学者又称褚伯秀主于义理而援儒援佛,弥缝孔老,此则亦待申论。
马臻为褚伯秀弟子,读其诗文,不似道士所为,《霞外诗集》卷六《咏田横》二首云:“汉家天子招遗臣,恰是恩多虑转深。忠义自能轻一死,可怜门客尽同心。”“海日荒荒海气凉,一思前事一心伤。繇来匪石终难转,不是将军畏郦商。”殆乎确为逸民之心。
释文珦与褚伯秀唱和往来,读其诗文,亦颇不似佛门中人。如《潜山集》卷十一《观禹贡九州岛历代帝王国都地理图》云:“万里江山几废兴,览图真合拊吾膺。三王二帝皆难问,两汉六朝何所称。此日中原全拱北,异时深谷或为陵。看来古今皆如梦,梦境虚无岂足凭。”其诗文集卷一开篇为《尧任舜禹行》、《天地无穷行》、《天道夷简行》、《天道虽远行》,卷二有《事君尽忠行》,深于经史,蒿目时艰,屡屡可见。四库馆臣已有此见,故评价云:“即事讽谕,义存劝戒,持论率能中理。观其《裒集诗稿》一篇有云:‘吾学本经论,由之契无为。书生习未忘,有时或吟诗。兴到即有言,长短信所施。尽忘工与拙,往往不修词。惟觉意颇真,亦复无邪思。’其宗旨品格,可以具见矣。”诗见卷四,同卷《吾生》云:“吾生少壮时,穷力在经教。一心融万境,颇亦能致效。”卷七《喜故人来访共论易》又云:“读书无与娱,日夕友猨狙。喜悦深交至,参同未画初。”亦皆可与馆臣所举《裒集诗稿》一首相印。又《潜山集》所酬答亦往往不限于僧人,儒、道皆兼而有之。咏儒则有《吾心》(卷二)、《箴放心》(卷二);咏道则有《游仙》(卷三)、《怀隐者》(卷六)、《赠隐人》(卷六),《有思归隐》(卷六);或者咏僧亦兼咏隐,如《行山逢隐僧语》(卷四)、《赠隐僧》(卷八)、《送僧归隐》(卷十二);或者咏佛而兼咏道,如《仙佛辞》(卷二)。这种态度与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的著述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窃论褚伯秀解《庄》最重要的特色在于,以“三教会通”的形式为外,“道”与“迹”的辨析为内。
《内七篇》“褚氏统论”云:
《逍遥游》之极议,当归之许由、宋荣,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齐物论》之极议,当归之子綦、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养生主》之极议,当归之老聃、彭祖,以纠过养形骸之谬,知生道所当先也。《人间世》之极议,当归之蘧瑗、接舆,明出处去就之得宜,勿撄逆鳞以贻患也。《德充符》之极议,当归之王骀、申徒嘉,言内充者不假乎外,德盛者物不能离也。《大宗师》之极议,当归之孔子、颜回,有圣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觉斯民也。《应帝王》之极议,唯舜、禹足以当之,讴歌狱讼之所归,应天顺人而非得已。此南华企慕往古圣贤,笔而为经,标准万世。
《天运篇》“褚氏管见”云:
孔子见老聘而语仁义,无异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故聃以‘播糠眯目’、‘蚊虻噆肤’喻仁义之愤心,盖借是以针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浑然之真,则化物也动之以风,治身也立不失德。奚必杰然自标仁义之名以为道之极致?若建鼓求亡子,无由得之也。夫鹊乌之不待浴黔,则白黑之实知之审矣,故不必辩。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于仁义之誉,何足以为广哉!犹涸鱼之相濡沫,非不亲爱,视江湖相忘之乐为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微爱为仁,而不知圣人不仁,为仁之至也。孔子见老聃,归而不谈,目击道存,不容声矣。龙之成体、成章、乘乎云气、养乎阴阳,则动静不失其时,德泽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测者也。故古之论圣人、神人者,皆以龙为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当夫子之喻。然二圣人者,皆人伦之至,显仁藏用,更相发明,无容优劣于其间也。
并称孔老为“二圣”,不仅没有诋訾孔子之言,并且对于儒家所宪章祖述的上古圣贤尧舜禹等,均称道为“标准万世”。
《列御寇篇》“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一句,“褚氏管见”云:“释氏说‘五种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显成德之效,此‘心眼’戒败德之原。不戒乎败,曷臻乎成?二家之论,相为表里。”又“朱评漫学屠龙”一章,“褚氏管见”云:“‘单千金之家’,即是空诸所有。至于千日功成,而无所用其巧。则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龙为何物、屠者何人也。禅宗有云:‘龙牙山中龙,一见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田子方篇》“老聃新沐”章,“褚氏管见”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则先圣不言之秘,真人已详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会而不可以言尽,即禅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风火既散已后’。虽因师指而入,终焉直须自悟,所谓‘说破即不中’是也。”不仅援引禅宗语录解《庄》,并且亦可见褚伯秀平日对于佛理颇为谙熟。
盖天下之大,至理则一,老庄与孔与释,本不当有所分别。天道运而无所积,屡迁而变动不居,与其论儒道之互补互绌,不如论道与迹之流变。
凡治学术,当论道与迹、源与流。由源与流而言,源为本,流为末;由道与迹而言,则源近迹,流近道。溯源得其本,循流明其变,通古今为一体,此所以谓之为“道”。学者固不可以不知本源,亦不可以不知流变;不知源则不知所本,不知流则可谓之不知“道”。
荀子曰:“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亦此意。杨子《太玄》:“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汉书·董仲舒传》:“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盐铁论》:“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清儒章学诚亦云:“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章学诚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云:“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文史通义·原道中》)又云:“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文史通义·原学中》)。所谓“前人陈迹”一语,实本庄子“《六经》先王之陈迹”之说。章氏服膺《周礼》似古文家,纂修方志似今文家,所云“《六经》皆史”意谓昔之史为昔之经,今之史则为今之经,其治学宗旨亦可谓超于今古文家派之上。
所谓“大义”必为“今义”,非“今义”则不足以谓之“大义”。由后世今古文家派言之,今文家之“大义”、“致用”本在古文家之“章句”、“求是”之上,故“道迹”之辨更当驾乎“源流”之辨之上。(“伪今文”则不在此列。)
《在宥篇》“褚氏统论”云:“此段自‘贱而不可不任’至篇终,乃《庄子》中大纲领,与《天下篇》同。东坡云:‘庄子未尝讥孔子,于《天下篇》得之。’余谓:‘庄子未尝不知精粗本末为一之理,于此篇得之。’”
《天道篇》“褚氏管见”云:
孔子为见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书藏于周之藏室,以俟后世圣人。盖不得已而托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许者,谓道既不行于当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济乎?
又“褚氏统论”云:
至若孔子欲藏书而翻经以说,成绮问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狥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许也。唯至人知仁义为道之末,礼乐为道之宾,能天能人,极贞守本,而神未尝有所困,故虽有世而不足为之累也。终以遗书得意、糟粕陈言而寓之于轮扁,盖恐学者狥迹遗心,舍本趋末,则去道愈远。但当究夫圣人有不亡者存,则学者当自绝学,而入传者当得无传之传,而天地圣人之心见矣,何以古人之糟粕为哉!
《渔父篇》“褚氏管见”云:
南华寓言于渔父、孔子问答,与‘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意同。盖孔子为人心切,则经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拟议,故渔父告之以去疵远患、修身守真而还以物与人。
又云:
凡渔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过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华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则所谓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经訾孔子,余谓南华之于孔子,独得其所以尊之(妙)〔实〕(朱得之作‘之实’),‘正言若反’盖谓是也。
故庄子既推本天下方术“皆原于一”,又申论古昔圣贤与《六经》之言为“陈迹”,为“糟粕”,为“土苴”,为“尘垢”,为“绪余”,每下愈况,反复不置。郭象承之,一则曰:“仁者,兼爱之迹。”“德者,神人迹也。”一则曰:“夫有虞氏之与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者也。”“尧实冥矣,其迹则尧也。”“夫尧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圣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
褚伯秀及所纂集宋人之说,大体皆着意于“道”与“迹”之辨,盖以“道”观之,则老庄、孔孟、释迦无一非过往之陈迹;既皆为陈迹,又何有不可会通之处。
褚氏之解《庄》,明义理,推天运,为《序》于宋,为《跋》于元,其道不积,其义不居,“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读《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当于褚氏“道迹”之辨致思。
[责任编辑 田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