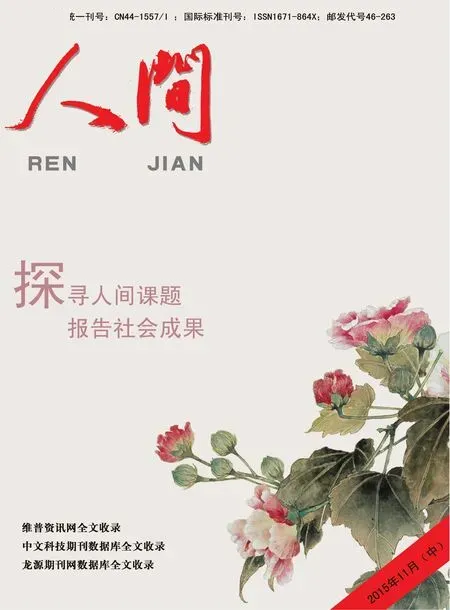一曲潦草的女性悲歌
——试析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苦难意识
张颖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0)
一曲潦草的女性悲歌
——试析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苦难意识
张颖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0)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作家之一。萧红在小说中常以不动声色的笔触,冷静地书写女性的苦难境遇和悲剧结局。本文以其代表作《生死场》为研究文本,从男性与女性施虐与被虐的关系、女性之间围观与被围观的关系两个角度,进行具体阐述,并探究其女性苦难意识的成因和意蕴内涵。
萧红;《生死场》;女性;苦难意识
在萧红小说《生死场》的读后记中,胡风这样写到:“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中评论《生死场》说:“由《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我们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出了东北民众抗战的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胡风和周扬都将《生死场》理解为民族兴亡、抗日救国的层面。但如今,当我们以褪去时代印记的视角再次阅读这部作品时,会发现仅仅从抗日战争救亡图存的角度来阐释《生死场》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萧红在《生死场》中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更多的是花大笔墨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女性形象,如金枝、麻面婆、月英、李妈等等,这些女性或经受生育的苦难,或囿于生存的困境,与之对立并存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话语的剥夺和对女性尊严的践踏。下面,笔者将从男性与女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角度,对《生死场》中的女性苦难意识作一番解读。
一、男性与女性:施虐与被虐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亚·克莉丝蒂娃说:“我知道女人不能代表什么,不能说什么话,她被排斥在术语和思想外,而确实有些男人熟悉这种现象。”在克莉丝蒂娃看来,男性对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利占据有中心地位,女性连拾捡男性边角料的能力都没有。萧红在《生死场》中将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为施虐者与被虐者的关系,揭示男性对于女性的漠视和凌辱,反映出女性深受束缚与残害的苦难人生。
兼论两性指称的明晰与模糊,我们可以发现《生死场》中的女性多数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小说中的女性除了金枝、月英,大多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妇从夫姓的命名方式,她们没有具体的名字,只被简单的叫做“麻面婆”、“李妈”、“李二婶子”、“老王婆”……暗示这群女性没有独立自我意识,她们无法逾越封建无法言传自我,“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按照西蒙·波伏娃的说法,她们只是作为一群被规定者,注定要处于“被限定的存在中”。从称谓中,我们无法看见女性自身的特点,无法参悟像当今时代父母对于女儿取名的寓意,更多的读到的是女人依附男性而存在的偏见。女性对男性的地位和待遇是不对等的,是功能性附庸性的。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不难理解小说中众多女性不约而同的悲惨结局。
再来看有男性出现的场景。在《生死场》第一章“麦场”中,二里半因为寻羊踏碎了白菜与人动了打,又被地邻的女人拿着一支搅酱缸的耙子吓得抱头鼠窜,但是这个懦夫一回到家,竟装起大丈夫将满腔怨气发泄到妻子麻面婆身上。二里半骂她“混蛋,谁吃你的焦饭!”,麻面婆挨了顿臭骂却忍气吞声全然接受,“过了一会,她到饭盆那里哭了”,哭的竟然是羊走丢了,对于自己的境遇一点没有反抗和愤怒!萧红写“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拢烦她时,她都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女性作为被虐者的苦难面貌和灵魂的全然麻木昭然若揭。丈夫、邻人、小孩对女性都有颐指气使的权力,女人只能无声地承受。
在《生死场》中着墨最多的女性莫过于金枝。金枝是一个单纯、善良、美丽的少女,她对于爱情有着天真浪漫的向往。当听到成业的鞭声和口笛声时, 她会“涨裂一般的惊慌”,她追随成业的行迹, 就像“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但金枝的爱情并不甜美,更不诗情画意。成业见到金枝,“只是本能支使着想到动作一切”,诱惑金枝未婚先孕并毫无选择地嫁给了他。婚后的成业回到家因为看到金枝还没烧菜便厉声嚷嚷,哪怕对于自己的女儿,成业也是丧失父爱的:“小金枝来到人家才够一个月,就被爹爹摔死了”。婚姻的不圆满让金枝对男性的想象全然破灭,她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会渐渐地诅咒丈夫”。金枝后来成了寡妇又受尽来自男人们的种种欺凌。金枝的悲剧是由成业的占有欲造成的,“就像捕猎者逮到了猎物”,女性的苦难正是那个万恶的男权社会造成的。
《生死场》中另一个美丽的女性月英——她患了瘫病,丈夫起初还替她请神、烧香,但面对病入膏肓的妻子,她丈夫没了耐心,骂她“娶了你这样老婆,真算不走运气”,并将被子换成了砖块折磨她,排泄物淹浸月英小小的股盘她丈夫也不清理,致使她身体腐烂生蛆命丧黄泉。男性主义在这里突兀地彰显出来,女性只是男性发泄的工具而已,男性对于女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全然漠视的,甚至认为“自己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便放任妻子的生死于不顾,女性的悲剧宿命读来让人愤怒更让人悲哀!
在《生死场》第六章中,萧红将女性生产的日子写作“刑罚的日子”,传统观念中繁衍后代的欣喜、微笑、幸福和希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女性生产时苦难的放大和亲临死亡的恐怖体验。怀了孕的女人在田间劳作,男人对她们并不多一份体恤,在这个时候也还不断骂着“懒婆娘!懒婆娘!”五姑姑的姐姐深受生产的折磨,在全家都开始为她准备葬衣的时候,她的酒鬼丈夫非但不关心其安危,反而将长烟袋投向她、把冷水泼在她身上。这个“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的女人”正是萧红所要描绘的被虐者的女性典型。那一个个“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的女人”在男性面前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尊严和最基本的自我保护的能力。萧红将施虐者的理所当然与受虐者的麻木屈辱二元对立起来,体现出罕见的女性意识和力透纸背的深意。
在《生死场》中,萧红采取冷静的视角审视女性的生存状态,以不动声色的残忍再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女性的存在生态。男人女人们忙着生忙着死,蝇营狗苟地残喘余生。在这肮脏污浊的环境中,女性如蚊虫如蝼蚁,被男性中心的社会所被边缘化、扭曲化。女性一方面为了取悦男性而存在,另一方面将自身的麻木内在化,表现出萧红对待男性场中的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怆和苍凉。
二、女性与女性:围观与被围观
当《生死场》中的男性将淫威发泄到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身上时,女性或多或少地受到男性的影响,在有意无意中将自身所受到的种种压迫强加到同类或比自身更为弱小的孩子身上。孩子的夭折是小说中常有的意象,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王婆形容自己孩子的死亡:“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著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以后麦子收成很好,麦子是我割倒的,在场上一粒一粒我把麦子拾起来,就是那年我整个秋天没有停脚,没讲闲话,像连口气也没得喘似的,冬天就来了!”面对女儿小钟的夭折,王婆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中伟大、崇高的母亲形象,她没有悲悯孩子的身世反而更注重麦子的收成,她围观新生命的死去如草芥,甚至比茅草还不如,母爱神话就这样无情地破灭了。
对于死亡,萧红是这样写的:“三天以后,月英的棺材抬着横过荒山而奔着去埋葬,葬在荒山下。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预备着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 人们看着生命的陨落心中再也泛不起波澜,反而忧虑起生计的艰难。在这看似活人充满活下去的希望气氛中,恰恰反衬了萧红内心深处对女性生命的悲悯与不平,也透露出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凉。
萧红在写金枝与母亲的关系时也是颇具深意的。金枝在告诉母亲自己怀孕时,“母亲似乎是平息了一下,她又想说,但是泪水塞住了她的嗓子,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母亲并不体恤金枝的遭遇和人生,反而将羞辱感不断放大,落井下石地轻慢女儿的人生。金枝因为怕挨母亲的打,“连在黑暗中把眼泪也拭得干净。老鼠一般地整夜好象睡在猫的尾巴下。”而她母亲每次翻动时,都要对着金枝的枕头骂一声“该死的”或者吐痰,“可是她并不把痰吐到地上;她愿意把痰吐到女儿的脸上”。后来金枝成了寡妇,从乡下到了哈尔滨做女工,男主顾故意多给她一点钱,对她提出性要求。当金枝回到乡下把钱交给母亲时,她母亲尽管知道这钱来得不干不净,依然乐得合不拢嘴,甚至迫不及待地催促女儿快回哈尔滨去。金枝的母亲和她身边的女人们明明有着同样的遭遇,这些女性却并没有站出来安抚和关心金枝那支离破碎的心灵,反而是静静地围观,围观完又散去:“旁边那些怒容看见金枝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人们慢慢四散,去睡觉了,对于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新奇和注意。”个体女性围观其他女性的痛苦,各个独立的女性又被视作展品被围观,女性自身缺乏内省意识却将被驯化的悲剧世代沿袭下去。萧红在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同时,深刻地传达出对女性个人生理角色、潦草命运、社会地位的反思。
三、成因分析
萧红在作品中直接书写了女性的苦难意识:“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没有代价”,“王婆因为苦痛的人生,使她易于暴怒,树枝在马儿的脊骨上断成半截”。面对女性的苦难,萧红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所揭露的不仅是施虐者的单向残忍,更在于受虐者反向的犬儒心理。比如女人自身想要取悦男性时,“过去拉著福发的臂,去抚媚他。但是没有动,她感到男人的笑脸不是从前的笑脸,她心中被他无数生气的面孔充塞住,她没有动,她笑一下赶忙又把笑脸收了回去。”因为“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当女性将自己行为的决定权主动悬置于男性时,还能奢望两者的平等身份吗?
萧红在《女子装饰的心理》中写:“虽然近年来有男女平等的法律,但在父权制度之下,女子仍然是受动的。因此,男子可以行动自由,女子至少要受相当的约制。”《生死场》中的这些女人始终无法在精神上觉醒,无法挣脱男权社会带给她们的逼迫,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贫困使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母亲们麻木地看待孩子们的生死,甚至在她们眼中,“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的价值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
另一方面,女性最大的悲哀并不是她们经历的苦难有多坎坷,而是对所经历的逆境的屈服和认同。随着男权文化无时不刻的浸润,男性压迫并捆绑了自由独立的女性,女性的自我意识被蒙蔽,其自身也渐渐将这种强加于自身的束缚内在化,在无意识中认同男性制定的标准,使之成为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这导致女性们内在精神的麻木与受虐,沦为填充男权社会边角料的物品,更可悲的是女性们冷眼围观自己的同类及弱小者,对自己的帮凶身份浑然不知,最终沦为封建秩序下的殉葬品。
四、小结
通观《弃儿》、《生死场》、《呼兰河传》,我们不难发现萧红终其一生都在书写女性的悲剧和苦难。女性怎样才能恢复独立的地位和人格的尊严?怎样才能彻彻底底地获得解放?在《生死场》中“尼姑庵”一节萧红做了回答,但是庙庵已经空了,金枝没有地方可以去。这似乎象征了女性自我救赎的虚幻和不可能性。《生死场》中的女性无论是附庸于男性还是自主独立,终究都没有摆脱其充满苦难的命运,这些直至今日读来仍不免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恐惧和深入骨髓的悲凉。但在小说女性苦难意识的深处,读者的心被“扰乱”了,给予了我们一种“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在女性苦难意识的背后,我们发现女人绝不是“奴才”,她们对于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有着永恒的追求和渴望。
专著类
[1]萧红.生死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卡勒.论解构[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析出文献
[1]萧红.女子装饰的心理[A].萧红全集下卷[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2]胡风.读后记[A].萧红全集[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239.
[3]周扬.现阶段的文学[A].周扬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学位论文
[1]余娟.读解萧红小说中的女性立场[D].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5月.
期刊类
[1]吴晓佳.萧红: 民族与女性之间的“大智勇者”[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增2期.
[2]黄晓娟.萧红的生命意识与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年9月.
[3]李美慧.“被虐”与“虐人”的双重困境——从《生死场》看萧红的女性写作[J].昌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4]董玉芝.用心灵折射蛮荒世界的苦女人悲歌——试论萧红小说中女性的苦难困境[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1卷第8期.
[5]王璐姝.沉寂的女性悲歌——论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J].剑南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06期.
[6]柳怡汀.宿命生死场,浸血女人花——读萧红《生死场》[J].名作欣赏·中旬刊.2011年07期.
[7]金小玲.女性人文主义视域下的萧红——有关《生死场》[J].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
[8]王叶青.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
[9]刘丽奇. 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J].北方论丛. 2002年第5期.
[10]赵影.从《生死场》看萧红的女性意识[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
[11]景浩荣.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8年4月.
[12]燕晓鸣.解读萧红小说中特有的女性意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
[13]何晓晔.论“萧红式”女性的悲剧美[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4月.
[14]緱英杰.《生死场》的现代主义批评——关于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J].美与时代.2003,(11).
[15]左文,毕艳.试论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
[16]陈红丽.浅论萧红小说的女性苦难意识.徐州教育学院学报[J].2007年3月.
I206.6
A
1671-864X(2015)11-0001-03
张颖,女,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在读,生于1995年11月2日,籍贯汉族,目前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