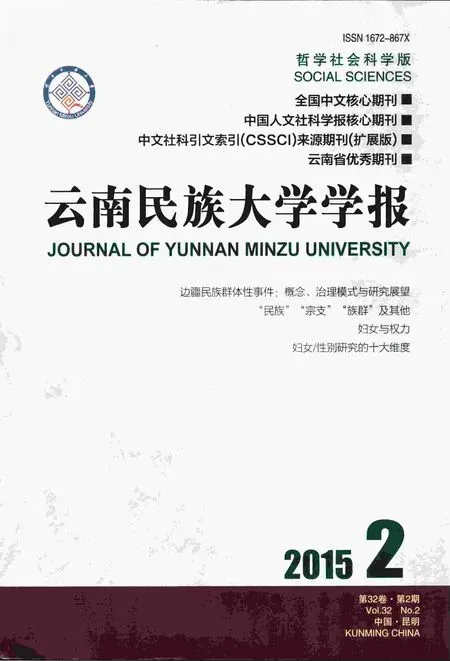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民族因素论析
刘建华
(内蒙古科技大学 网络舆情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内蒙 古包头014010)
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民族成分众多的国家,各民族较为集中的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历史、文化以及自然条件的差异,在频繁的民族交往和社会接触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矛盾和冲突。在边疆民族地区,涉民族类的社会冲突和利益纠葛与社会性公共危机遥相呼应,再加上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分裂势力以及反华势力等很容易借助互联网的舆情煽动,把民族因素和非民族因素相互叠加,使得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影响比一般的舆情事件投射力更大、舆情事态更为复杂,其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所造成的破坏性将更为严重。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民族因素,对于防范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事件危及社会安全以及公共安全,有效消减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民族特性内涵
边疆民族地区是指地处国家边境、民族成分极为复杂、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除了具有网络舆情所共有的开放性、交互性、聚焦性和即时性特点外,还具有反应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性、敏感性、政治性和跨境复杂性特征。其中,民族特性是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突出特征之一。
第一,舆情传播空间的民族特性。“我国有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毗邻16 个国家,由9 个沿边省区(民族自治区),135 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其中民族自治地方107 个。无论从历史、地理、文化,还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边疆地区是一个异于内地的特殊地区。”①陈为智:《论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特性及其启示》,《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4 期。由于受历史上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因素以及现实中自然条件和区位劣势等因素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一个不断受到境内外各种因素挤压的场域空间,日趋复杂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现实中的难题在境内与境外、历史与现实、先进与落后的双重驱力作用下,成为中国现实发展中最为敏感的区域,也是最易发生问题的区域。当这些地区的问题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向外扩散演变为网络舆情时,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讯息,而是置身于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思想和意识,是少数民族群体的不自觉的呼声,是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在、理想与现实的抗争和呐喊,是对边疆民族地区区位劣势的一种不自主的喧嚣。当这一呼声、抗争和呐喊借助于开放性的网络传递时,其传播空间不只是个体对个体、群体对群体,还包括了民族对民族,以及弱小民族的集体性意识,因而也就烙印着空间和地域上的民族特性。
第二,舆情传播主体的民族特性。网络舆情传播主体是指“众人之论的社会公众,或者说是参与网络舆情活动的人,包括公众、社会团体以及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的人。”①刘建华:《赛博空间的舆论行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11 年版,第69 页。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历史上不合理政策不公平社会待遇的影响,以及现实发展中出现的社会贫富悬殊以及不科学的政策的实施,对于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公民个体或群体身上的任何意义上的人身侵害、资源掠夺、文化剥夺、信仰阻碍都会借助互联网这个共享和开放的平台加以呈现和放大,因而也成为众多网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这些话题最初可能是点对点的传递,随着事件本身的涉众面和牵涉主体的扩大和增多,信息的传播由最初的点对点会向外扩散,呈现出面对面、跨越群体、跨越地区、跨越性别、跨越民族甚至是跨越国境间的传播。众多网民主体之所以聚合和围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在心理上自觉和不自觉地产生这样一种倾向: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强势者的排斥。对于舆情传播主体而言,他们可能不分地域、性别、年龄、身份的差异,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网民主体自身的民族属性,特别是对本民族群体和个体事宜无形中产生的同情和关注,于是在民族共同心里意识的驱使下所采取的共同的行为和行动,因而,也使得舆情传播主体的民族特性更加鲜明。
第三,舆情传播客体的民族特性。网络舆情传播客体是指网民所要关注的特定事实和状态,是网民借助网络媒介发布信息、进行议论的对象。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而言,能够成为网络舆情传播的客体有:(1)由自然灾害问题衍生出的社会性问题。诸如灾难救助、应激程序启动、当地政府反应时效、救助对象、救助实效、灾后重建及其相应的社会监督等问题; (2)由经济事件衍化为社会性政治性事件问题。诸如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征地拆迁、自然资源开发、人口迁移、环境污染、植被破坏以及经济补偿到位及其相应的公开、公平性问题等; (3)发生在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间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冲突、财产纠纷以及历史积怨而引发出的群体性事件等。 (4)由境内外分裂势力、极端势力以及反华势力鼓动和怂恿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等。上述事件一旦发生,如果处理不公、处置不力或者延时处理很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在一个人人都是麦克风和个个都是媒体记者的网络社会里,同情弱者、扶危济困是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既有现实。边疆民族地区发生的任何意义上的事件一旦借助互联网向外发布就会瞬时间被放大和扩散,有些情况下甚至会把毫不相干的过时事件耦合起来,因而会使原来的事件更趋复杂化。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地区,它纠结着历史与现在、族群与族际、境内与境外、民俗与宗教、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自然与社会、地域与地域,现实社会中任何意义上的变革与变动,必然会在边疆民族地区打上民族特性的烙印,因而在这些地区发生的任何冲突、矛盾和纷争或多或少地体现着民族性特性,随之网络空间所传播的客体性事件或事实也就必然烙印民族特性。
第四,舆情消减话语的民族特性。舆情消减是指舆情指向对象和事实所凸显的问题和矛盾得到解决,舆情状态呈现出递减或衰弱的态势。舆情消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矛盾和问题得以解决的原因,也有新的舆情事件出现使得原有舆情产生的视觉疲劳而消退的原因,还有的是舆情本身的社会意义指向不明所致,或者是舆情本身所反应出的目的已经达成而使舆情得以消减和衰退。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而言,无论是哪种原因所致,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舆情事态的宣称者特别是问题的受害群体常常是用“民族”作为搭建社会问题框架的话语词汇。当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发生时,网民们之所以发表意见、表达观点推动舆情的向外传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借助对弱势群体或弱小民族的关注,以此通过他们作为问题的代言人,向社会、向媒体、向上级政府寻求帮助,他们往往以“民族”“少数民族” “边疆民族” “民族地区”等话语用以在网络舆论场域中获得公众、媒体和上级政府的关注。许多情况下,问题本身的民族成分或民族因素可能不很明显,但是假以“民族”“边疆”等话语很容易博得社会和公众的同情,因而更容易促使问题得到解决,矛盾得以化解,目标得以实现。对于舆情事件的主管部门而言,当遇到以“民族”或“边疆”词汇为话语体系的舆情发生时,“民族”或“边疆”作为问题的话语符号多数会被当政者或主管部门提升到政治性的高度加以看待,因此引起高层的重视,也很可能会使问题和诉求得到快速地解决,使舆情得以消减。因而,体现出舆情消减话语的民族特性。
二、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民族因素辨析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之所以发生和迅速传播开来,是多种因素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多种矛盾相互激荡的过程。其中,民族因素是不可回避和忽视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因素具体指向为:在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中,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历史积怨、利益纠纷和民族分裂事宜等因素是网络舆情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驱动和外在影响。
一是民族文化差异。舆情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网络舆情就是作为网民公众在网络平台上的社会政治态度。对于特定的网络舆情事件,不同的网民主体会表达不同的社会政治态度。对于网民主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差异,“除了缘于不同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所产生的差异和网民间的差异外,不同网民间的舆情差异背后还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民族文化内涵,或者说,不同的舆情主体都包含着不同的历史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受制于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民族的独特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特征的综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其它民族的标志。”①林竹:《舆情的民族文化内涵探析》,《社科纵横》2006 年第4 期。在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性格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对于具体的舆情事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政治态度,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话语形态,从而对舆情本身及走势产生影响。譬如,有些属于边疆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个体交往中的冲突而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单就事件本身而言,并非不可调和或者本身不可谓发生事件的事件,只是源于忽视或者没有顾忌到对方的风俗习惯和禁忌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以至于发展成为网络舆情。其实事件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由于民族间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冲突,如果在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交往中,能够懂得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和文化差异,就会减少冲突,消减舆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文化差异是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必须要分析的因素之一。
二是民族历史积怨。在各民族的交往和接触中,还存在着因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袭下来的许多历史性积怨。这些积怨的形成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在特定历史时期民族交往中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也在现实发展中成为民族正常交往的障碍。这种冲突和障碍成了现实发展中民族融合和各民族进步的重大障碍。长期形成的民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和旧的观念没有完全消除,一遇突发事件,有些民族的个体和群体总是念念不忘历史旧账,便会借助突发性事件爆发出来,形成激烈的对抗,以致酿成群体性事件。当这些事件借助互联网平台向外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时,一些别有用心者就会把相干的不相干的民族间的既有积怨和矛盾借机加以炒作、放大,以此去影响社会的整体性意识,进而去影响和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民族间的正常往来。然而,就事件本身而言,可能就是民族与民族个体间的家庭琐事和个体间的利益纠纷,一旦纠结民族历史积怨、揪住历史旧账不放,在互联网这个开放的虚拟平台进行渲染和炒作,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很难想像,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事实上,民族间的历史积怨并非民族个体间的矛盾,即使个体间有过矛盾也会因时间的流逝和当事者的作古早已灰飞烟灭。而民族群体间的历史积怨本身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政策和旧时代作用的结果,时代已经进入到新的轨道,民族间的历史隔阂、矛盾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早应释怀,除非重蹈历史性覆辙。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已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基本政策,现实中民族间的交往远远超越了旧时代的歧视和隔阂。民族个体间的矛盾和纠纷虽然不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消除,但民族历史积怨的土壤已经不会死灰复燃。因此,当面对因民族个体或群体间冲突而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时,历史积怨中的民族性因素也是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民族权益纠纷。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民族权益和民族利益往往成为各民族关注的焦点和重点,各民族的成员总是尽可能地去维护本民族的民族权益或民族利益,一旦本民族的权益或利益受损或者不能很好地得到维护,矛盾和纠纷便会得以出现甚至形成冲突性事件。特别是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因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所造成的民族内部心理上的落差不可能因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而消散,每当本民族权益和利益受损而得不到维护时,这些因素就会重新泛起,极易刺激他们脆弱的神经,而当这些事件在互联网上呈现时,很快会演变为网络舆情事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民族地区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敏感区域,尤其是人的心理特别敏感。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而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异常活跃。”①罗安平:《民族地区突发事件中传媒应对原则探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 年第5 期。就某种意义而言,民族间的权益纠纷许多情况下可能是发生在少数几个人身上的问题,但却与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意识相联系。特别是对于处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其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心理特征的影响,一旦本民族个体利益和权益受损,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整个民族的受损,因而发生在他们成员身上的任何权益或利益纠纷,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以危机形态向外扩散和传播,有些情况下会上升到“民族歧视”或“人权侵犯”的高度。
四是民族分裂事宜。民族分裂是相对于民族团结而言的,是以维护“人权”和“民族自决”为借口,汇聚部分民族势力或反动势力,并接受境外反华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和帮助,以破坏国家统一和团结,违反本民族利益制造并加剧各民族间的隔阂与纷争的民族分离活动和行为。从事民族分裂事宜的民族分裂分子是民族极端主义的产物,他们与暴力恐怖主义分子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冷战结束的产物,他们打着维护“人权”和进行“民族自决”的旗号,利用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民族间经济利益纠纷和民众情绪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妄图搞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以至于分裂祖国。他们在一些国外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把一些与民族问题相关的不相关的、个体的群体的事宜加以放大和渲染,借助互联网平台制造网路舆情,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破坏性活动。并通过“东突信息中心” “自由亚洲网站”、哈萨克斯坦“解放电台”等②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4 页。网站对中国国家大政方针、内外政策、发展动态、社会事务以及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妄加评论,同时蛊惑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制造网络谣言、煽动群体性事件,进而制造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的正常社会经济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和繁荣稳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互联网的特殊传播机制在改变舆论的生成规律,也在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影响着政治生活秩序与政治规则的建构。因而很容易成为有组织的反动者制造反动舆论以达到分裂国家、组织发动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③[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武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0 页。
三、民族因素对认识和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启示
民族特性是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突出特征之一,民族因素又在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中发挥着非常明显的驱动和社会影响,这就启示我们在认识和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传播时,民族因素是无论怎么也无法回避的一种重要分析视角和理论参照。
其一,民族特性是消减舆情问题的一个基本概念。2005 年中共中央的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讲,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特性是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基本内核存在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中的民族文化特征的最高抽象,也是本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核心和灵魂。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因素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积极作用方面而言,舆情事件往往是民族群众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当他们借助网络平台宣泄不满时可以产生减压的功能,同时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和反映的问题对于社会管理具有警示作用,因而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影响;就消极作用而言,民族因素渗透到网络舆情事件中,可能会使网络舆情事件更加复杂、消减舆情将更加艰巨。诚如民族概念所言,民族性不单单是一个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问题,它还牵涉着民族心理、宗教、社会发展以及历史渊源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边疆民族成分众多、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以及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复杂社会现实中,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任何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跨境民族之间的任何意义上的问题和矛盾都会产生诸多的社会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极易引起网民的注意而引发网络空间的议论和围观,如果在处置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进而危及社会的稳定。这就启示我们在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事件时,要意识到,边疆社会与民族因素的密切联系以及民族因素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族特性与边疆社会问题的紧密关联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和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所应秉持的一个基本概念。
其二,民族特性是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问题的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常研究网络舆情问题的分析视角更多的是把舆情产生的动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进而从舆情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去分析舆情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进而探讨舆情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舆情事件的动因去探讨消减舆情的对策,也就是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而言,由于舆情发生和发展的特殊地域以及独特的民族特性,使得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内外空间以及传播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仍然以分析一般性网络舆情的分析方法并不必然会揭示出问题的实质,也并不一定会使舆情事件得以彻底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的民族特性启示我们在分析舆情时,不仅要从舆情自身发展的动因、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出发,去揭示其发展和变化的规律,通过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舆情发生的内在动因,进而去构建消减舆情的对策,更要透过舆情事件表面探究其背后的民族因素,诸如民族地理、自然条件、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文化、民族心理状况以及民族历史渊源等去剖析舆情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此同时,还要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出发,分析影响民族舆情的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社会管理以及民族文化建设等方面着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民族矛盾,消除历史积怨,合理的解决民族利益纠纷,使那些试图借助民族问题而引发网络舆情去制造民族分裂事宜的民族分裂分子丧失机会,进而去化解舆情事件,为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特性的切入是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问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分析视角。
其三,民族特性是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参照。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不仅具有一般网络舆情危机传播的特征,而且由于民族问题和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从而也使本地网络舆情呈现出舆情传播的民族性、敏感性、政治性和跨境复杂性特征。这启示我们在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的过程中,其引导原则、采取措施和方法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网络舆情的引导方法,而是要以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空间、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舆情消减话语的民族特性作为重要参照,正视“民族特性”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采取切合民族社会实际的引导策略。一方面利用网络媒介的互动功能,适时建立舆情事件的对话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少数民族话语权,创造的民族文化氛围,充分调动少数民族民众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另一方面,利用网络议程的设置功能,设置与舆情事件相关的议题,诸如事件进展情况、管理部门意见和建议、民族权益、以及事情真相等,议程设置的形式可以是图片、视频、评述等,引导网民受众自觉明辨是非、主动杜绝谣言和留言,消除民族隔阂,区分个体事件、个别事件与民族事件的异同,积极代表舆论并引导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