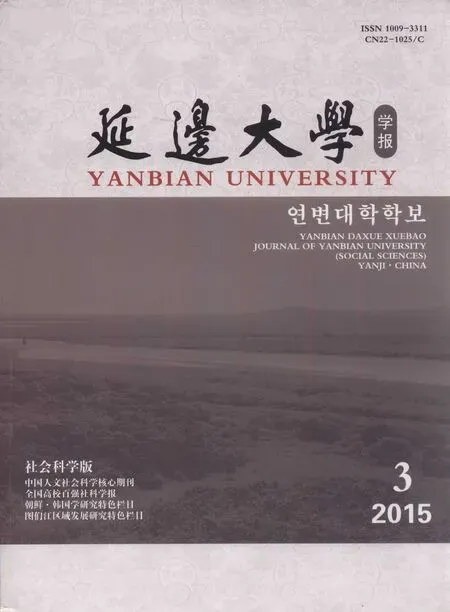“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与章炳麟的国家观和救亡观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是章炳麟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讲中声明所要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呼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出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动机。章炳麟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寄予厚望,也使这一口号成为他对国家观、救亡观和国学观的集中表达。有鉴于此,深入探究章炳麟的这一口号,既有助于客观剖析章炳麟迥异于严复、梁启超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又有助于全面把握章炳麟与康有为针锋相对的国学观、宗教观。
一、“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救亡路线与缘起宗旨
中国近代是救亡图存的时代,爱国主义、群体观念被许多人搬来作为号召国民抵抗外侮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对于为什么要爱国,国家有何可爱?严复、梁启超等人利用社会有机体论解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凭借个人依赖群体、国家而自保来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思路截然不同,章炳麟反对将个人视为构成国家这一有机体的细胞,并且批驳了当时流行的国家观念。《四惑论》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四惑”(错误观念)逐一进行反驳,作为四惑之一的公理中就包括国家观念。此外,章炳麟在1907年10月专门作《国家论》,在文中详细阐释了国家的本质、功能,厘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他看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绝不等同于细胞与生物有机体的关系,不能将个人视为构成国家的细胞,最简单的理由是:细胞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只是生物有机体的一部分,离开生物有机体便无法存活。个人是独立的实体,离开国家也可以生存;尤其是在舟车大开、民主盛行的时代,人们不必囿于天然地理环境或民族风俗自然形成的国家,而可以自由选择国家而居。这凸显了个人对于国家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也证明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与细胞与生物有机体的关系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在此基础上,章炳麟从个人、国家两个方面重新透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期消解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第一,从个人方面来说,个人是生而独立、自由的,不对他人、国家负有责任。这便是:“然则人伦相处,以无害为其限界。过此以往,则巨人长德所为,不得责人以必应为此。”[1]第二,从国家方面来说,国家原本就无任何神圣性,对于个人也没有任何权利。章炳麟在《国家论》中揭露国家为虚幻,在消解国家神圣性的同时,抵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倡个人为国家减损自由的做法。章炳麟在文中写道:“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若以原子为实有,则一切原子所集成者,并属假有,何以故?分之则各还为原子故。自此而上,凡诸个体,亦皆众物集成,非是实有。然对于个体所集成者,则个体且得说为实有;其集成者,说为假有。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2]在章炳麟看来,既然国家是由个人集合而成的,那么,作为个人的集合体,国家便没有自性,因而是虚幻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积聚而为国家这一点上,章炳麟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章炳麟不是像严复、梁启超那样证明个人不能自保,全赖国家、群体庇护;而是以佛教的因缘逻辑证明国家建立在个人之上,作为个人积聚而成的假相绝非实体,没有自性,因而是虚幻的。正是沿着这个思路,章炳麟接着写道:“其(指国家——引者注)功能仍出于人,云何得言离人以外别有主体。然则国家学者,倡此谬乱无伦之说以诳耀人,真与崇信上帝同其昏悖。世人习于诞妄,为学说所缚而不敢离,斯亦惑之甚矣。”[2]按照章炳麟的说法,既然国家的作用出于个人,那么,绝非像严复、梁启超等人所讲的那样个人离不开国家而存在,恰好相反,国家离不开个人而存在;假设有主体的话,那么,主体也应该是个人而不应该是国家——这正如讲实有,个人是实有而非国家是实有一样。
议论至此,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秉持佛教尤其是唯识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旨趣,章炳麟恪守“万法唯识”,认为人作为识的显现也是假有。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所谓我者,舍阿赖耶识而外,更无他物。此识是真,此我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一倒见也。”[3]循着这个逻辑,人的身体由细胞凑合而成,故而没有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的存在也是虚幻的,与国家一样并非实有。章炳麟本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因此改变个人为实有而国家为假有的观点。对于其中的原因,他解释说,个人与国家虽然都是假有,但是,个人之假有与国家之假有的“分位”有别,相对于由个人集合而成的国家而言,个人“近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炳麟设问并回答说:“问曰:若尔者,人亦细胞集合而成,云何得言实有自性。答曰:以实言之,人亦伪物云尔。然今者以人对人,彼此皆在假有分位,则不得以假有者斥假有者,使吾身之细胞,悍然以人为假有,则其说必非人所能破。若夫对于国家者,其自体非即国家,乃人之对于国家。人虽伪物,而以是单纯之个体,对于组合之团体,则为近真。故人之以国家为假有者,非独论理当然,亦其分位得然也。”[2]
经过章炳麟的论证,国家的虚幻性已经破坏了其神圣性,个人对国家的“实有”、“近真”更使个人为国家牺牲成为荒谬绝伦的事。他进一步指出,国家之设立和存在不仅不神圣,反而极其龌龊,是迫于外力的不得已之举。章炳麟宣称:“……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2]章炳麟认为,无论是从设立还是功能上看,国家都与神圣原本就不搭界,国家纵然有功亦应归于全体国民,而不应归功于国家元首。现实的情况是,国家元首往往将“集合众力以成”的功劳归于一身,“以团体居其名誉”。元首的欺世盗名实际上是将集合为国家的每个人的权利攫为己有,最终结果是增加了国家的罪恶。
章炳麟对国家尤其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论证凸显了个人对于国家的优先性和独立性,对于纠正社会有机体论的单向决定论具有积极意义。随之而来的是,爱国从近代社会的主题话语成为大可怀疑之论。道理很简单:所爱对象——国家并非实有,并且是制造罪恶的渊薮,甚至龌龊不堪,国有何可爱!既然如此,国还要不要爱?更为尖锐而迫在眉睫的是,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还需不需要救?在论证国家的本质之后,章炳麟对爱国主义作如是观:“爱国之义,必不因是障碍,以人心所爱者,大半非实有故……此何因缘?则以人身本非实有,亦集合而成机关者,以身为度,推以及他。故所爱者,亦非微粒之实有,而在集合之假有。夫爱国者之爱此组合,亦由是也。且以各各微粒,捣和成器,器虽是假,而其本质是真,其爱之犹无足怪尔。亦有别无本质,唯是幻像,而人反乐观之者,喻如幻师,幻作白兔青雀等像,于中无有微分毛羽血肉可得,乃至石磨水漉亦不可得,而人之爱玩反过其真。”[2]在章炳麟那里,国还是要爱的,然而,爱国并不应该是个人做出牺牲,个人也不应该出于功利动机而爱国。换言之,章炳麟的《国家论》是针对严复、梁启超借助社会有机体论让个人为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之权有感而发的,目的是纠正两人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本末倒置,并非反对爱国主义本身。
鉴于近代救亡图存的迫在眉睫,章炳麟尽管极力揭露国家的假有虚幻和龌龊不堪,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爱国的意义,而是对爱国进行了限定。他写道:“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亦如自尊之念,处显贵者不可有,居穷约者不可无,要以自保平衡而已。”[2]如此说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中国人,爱国观念不仅不可无,反而要加强。问题的关键是,在破除了社会有机体论,否定了个人是构成社会的被动细胞,个人不必依赖国家而存在之后,如何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如何救亡图存?这是章炳麟无法回避而必须要回答的现实课题。“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便是他作出的回答。扭转严复、梁启超沿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路,出于功利目的的被动爱国局面,使国民出于情感而积极地爱国,是章炳麟呼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缘起和动机。他提倡国粹,就是要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强化中国人的爱国观念。为此,章炳麟的具体设想和步骤是:在破除是非观念、涤荡外欲的同时,弘扬国粹,引导国民在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的熟悉过程中,发现本民族之可爱。至此,章炳麟凭借对国学的弘扬开辟了一条救亡之路,这条路与严复、梁启超基于社会有机体论的致思方向迥异其趣。对于章炳麟来说,促使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动机和动力源于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了解基础上的热爱,而不是基于个人是构成国家细胞的“被迫无奈”,使人由细胞不能脱离社会存在而必须依赖群体自保的被动爱国转向发自内心爱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则是国学。
章炳麟所讲的国学既有爱本国之学的强烈意图,又有以国学救亡图存的鲜明动机。有鉴于此,国学的立言宗旨是救亡图存,目的是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以此来保群保种。“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理论初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章炳麟所讲的国学不是一种书斋学问,而是饱含强烈的时代呼唤和救亡宗旨,从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不排斥西学,却绝非以西学为主,以西学为尚;即使借鉴西学,也是为了“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国文化沟通之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不只是学问,国学研究的宗旨和重心不是对国学的审视,而是对本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沿着这个思路,通过弘扬国粹,宣讲国学,可以达到爱国的目的。他本人称之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第二,用以“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国学指对国故的整理,尽管对国故的整理可以参照西学,却不是以西学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固有之学何为“国粹”,甚至何为“国渣”。在对“整理国故”的理解上,章炳麟与胡适等人的观点相去霄壤。对于章炳麟来说,一国之学是可爱的,根本就不存在“国渣”的问题。他所讲的“整理国故”与作为新文化运动者而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用怀疑的眼光、历史的眼光,以西学为标准审视、评判国故之学具有本质区别。即使在近代思想家中,“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也使章炳麟的思想特立独行,与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等人渐行渐远。
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具体途径与国学理念
章炳麟在申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同时,就已经将国学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三项,即“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4]从他的一贯主张和思想侧重来看,语言文字无疑在国学中始终占居最显赫的位置。这一点体现了章炳麟对国学具体内容的界定,也拉开了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学术分野。
章炳麟将语言文字列为国学三大组成部分之首,足见其对语言文字的重视。在日本东京讲国学时,他就以《说文》、《楚辞》、《尔雅》、《广雅疏证》为主要经典。语言文字始终是章炳麟国学的重心,更是其中的亮点——不仅体现了迥异于他人的国学理念,而且还展示了有别于他人的救亡路径。在章炳麟看来,语言文字不仅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文化的载体决定着不同文化的存在样式和形态,并且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在中国近代的文化多元和全球背景下,坚守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汉字对于坚守中国本土文化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最早以孔教应对西方文化的康有为、谭嗣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秉持文化进化理念宣称语言文字遵循进化法则,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有优劣之分,进而提出了全球同化、同一语言的主张。在谭嗣同看来,语言文字是进化的,进化的法则是由繁杂到简洁。由繁入简的语言文字进化法则使难认、难写、难学的中国象形文字在西方的字母文字面前相形见绌,也使简化乃至在大同社会中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样,在康有为那里,世界语的创立处处本着同一语言、由繁入简的语言进化原则。他主张:“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具体办法则是:“不得有异言异文。考各地语言之法,当制一地球万音室……惟中国于新出各物尚有未备者,当采欧、美新名补之……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写之,则至简速矣。”[5]由此可见,康有为提出的创立世界语的方案与谭嗣同一样因循语言由繁入简的进化法则。循着这个思路,两人宣称,在自由、平等的大同社会,同一文化,同一语言文字,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到那时显然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在康有为、谭嗣同设想的中外平等的大同社会中,由于取消了国界,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的文化载体汉语同样荡然无存;随着汉字的消亡,中国文化也必将化为乌有。
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观点具有本质区别的是,章炳麟不是从进化而是从地域性、民族性的角度理解语言的。章炳麟早年笃信进化论,后来鉴于善与恶、乐与苦的俱分进化而公开主张退化,《俱分进化论》、《四惑论》和《五无论》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思想主张。而无论主张进化还是退化都不影响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的重视和热爱,语言文字也成为章炳麟国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章炳麟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理念,主张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文野、优劣之分。循着这个思路,中国的语言文字不仅不存在与西方字母文字相比的繁简、难易或优劣问题,反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极富民族特色和独特意蕴,足以激起中国人对使用汉字的本民族及民族历史的热爱之情。对于这个问题,章炳麟解释说:一方面,应该承认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其他各国殊异;另一方面,绝不能认为这种殊异表明中国文化落后。恰好相反,中国语言文字有别于其他国家之处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所在,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国学作为一国固有的特征。中国与其他各国文字的殊异之处具体表现在: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一字一义,中国的语言文字则一字多义。具体地说,其他国家语言文字的引申之义通过词尾的变化表现出来,变化之词与原词已属两词,中国文字则不然。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字既有本义,又有引申义,本义却与引申义同为一词。这样一来,中国的语言文字一字多义,既在写法上完全不同,又在不同语境中意义完全不同。这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内涵丰富,变化多端。不仅如此,中国的语言文字极富魅力,有别于其他国家语言文字的特殊情况使它凝聚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也使中国的语言学承载着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意蕴,远非西方的“比较语言学”可比。对此,章炳麟列举具体例子解释说,中国的语言文字隐藏着社会学的诸多信息,由于古人造字有个时间先后问题,因此,后人可以根据这个字出现的时间推断出此字所代表的事物出现的先后。例如,兄、弟、君等字的出现较晚,表明这些字都是转注过来的,古人造字时还没有兄、弟和君。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古代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这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原本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正是章炳麟解读中国语言文字的这个视角决定了语言文字在国学中的地位和意义,正如他本人所言,这一点“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也解释了章炳麟将语言文字列在国学首位的原因。
与此同时,章炳麟指出,文章优美才能够感动人。进而言之,文章之所以优美,秘密“全在文字”。例如,唐代以前的诗文之所以感人,是由于那时的人精通小学;北宋之后,小学渐衰,文章便“没有什么可以感人之处”。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可以感人,关键在于语言文字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潜移默化,约定俗成。正因为如此,“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明白了这个道理便不难想象,在中国人的眼中,屈原、杜甫这些中国诗人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写出来的诗优美感人,无论是希腊诗还是印度的《利俱吠陀》永远都无法与之媲美。基于上述思考,章炳麟将提倡小学,推动“文学复古”,奉为激发中国人爱国保种力量的不二法门,并由此将语言文字置于国学的基础与核心地位。[4]
这使章炳麟在小学方面卓有建树,也使他的国学研究具有了鲜明特色并且落到了实处。诚然,为汉字注音并非始于近代,更非始于章炳麟。元代早在进北京之前,就请国师——西藏喇嘛八思巴创造新字拼音语和蒙古语,编成我国第一本拼音韵书《蒙古韵略》。与元代统治者试图借助汉语拼音学习中原文化不可同日而语,章炳麟是在取消汉字之声嚣然尘上,汉字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为保存中国的语言文字殚精竭虑的,并且将保存汉字作为保存国粹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章炳麟始终凸显语言文字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对最能突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方言情有独钟,在借鉴中国地理语言学先驱——扬雄的方言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新方言》。《新方言》的特殊意义在于,不是像扬雄那样以中国境内的不同地理要素划定方言的范围和类型,而是在全球文化多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突出中国语言文字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进而彰显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性、自主性和特殊性。章炳麟的这些活动与其说是为了学问,不如说是为了用乡音激发中国人的爱国情感,归根结底离不开“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初衷——也就是说,是围绕着这一宗旨展开的。
三、“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宗教理念与佛教情结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集中展示了章炳麟的救亡路线,也凝聚了他的宗教观。这只是章炳麟所要做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便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1906年章炳麟刚东渡日本,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讲了两件大事: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在他那里,宗教与国粹一样是最重要的事,两者不仅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件事。这一点从章炳麟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思考中明显地体现出来:“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的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4]凭借精神的力量来救亡图存是近代思想家的共识,这种精神力量在章炳麟看来便是热度情感。他之所以膜拜情感,增进感情,目的有两个:一是“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增进爱国的热肠”;前者的办法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后者的办法则是“用国粹激动种性”。与激发爱国热肠一脉相承,章炳麟推崇“感情”即心的力量,声称“独尊法相”就是为了引导人在对心、识的推崇中膜拜自心的力量。在他那里,正如净土宗近于祈祷,使人生畏惧心、退屈心,禅宗于唯心胜义不甚了解而被弃的理由一样,“独尊法相”是企图以万法唯识强调一切皆阿赖耶识所变,引导人在对万物和“我”并非实有的觉悟中“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不依他力”。
基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初衷,循着以宗教增进情感的思路,章炳麟将宗教与国粹联系在一起,所讲的国学从出现之日起就与宗教密切相关。这不仅因为他提倡国粹是针对康有为提倡孔教有感而发,而且因为“用宗教发起信心”的需要。章炳麟不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入手来论证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弘扬国粹来激发爱国热情。“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表明,他试图以道德和民族情感为纽带将个人联结起来,而不是像严复、梁启超等人那样以利益为诱饵呼吁人们爱国群以自利。这是两条泾渭分明的致思方向和救亡路径。章炳麟净化人心、提高革命道德的方法和途径则离不开宗教。他断言:“但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麨子,怎能团得成面?”[4]通过对各种宗教进行审视和批判,章炳麟得出的结论是:孔教、基督教“必不可用”。
章炳麟一面极力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观,一面将孔子的思想与宗教相剥离。章炳麟具有宗教情结,曾经作《建立宗教论》阐发自己的宗教观和判教标准。尽管如此,他所推奉的宗教并不是孔教。更有甚者,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宗旨来看,章炳麟提倡国学,弘扬国粹,就是为了反对康有为提倡的孔教。章炳麟甚至将国学的不振归咎于康有为将国学归结为孔教,并在国学讲习会的《制言》发刊宣言中特别强调:“今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帐簿也。”[6]这就是说,章炳麟提倡国学,目的有二:第一,反对欧化。欧化派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民族自卑心日盛一日,人心涣散,全无爱国心可言。第二,反对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文化进化主义。文化进化主义盯住中西文化的文野之别,秉持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传统越走越远,用中国文化去攀援西方文化,最终丢掉了中国文化的精华。章炳麟强调,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尽管立论的角度不同,却都对中国的救亡运动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鉴于这些教训,若要救亡图存,必须舍此路径,另谋他途。在此前提下,他找到了“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救亡路线。
对于章炳麟来说,“汉种的历史”是国学的灵魂和根基;离开了“汉种的历史”,国学则无从谈起。正因为以中国自己的历史为灵魂,章炳麟突出了国学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学虽然为中国所固有,但是,并非中国固有的都是国学,只有国粹即作为“中国的长处”的,才是应该“提倡”的国学。第二,国学既然为一国所固有,便带有本民族与生俱来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国学的内容以有别于其他国家学术的“我中国特别的长处”为主,而不必与西方的异质文化相同,更不应该强求与后者相同。章炳麟甚至指出,自己提倡国粹,本意之一就是反对康有为等人以公羊三世说攀比西方的进化论以及论证自由、平等的做法。
孔子与儒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章炳麟对儒家的蔑视预示着对孔子的微词。有人甚至说,章炳麟的《订孔》打响了近代反孔的第一枪。章炳麟使康有为极度神化的孔子急剧祛魅。按照章炳麟的说法,孔子不是康有为所讲的创立孔教的教主,而是传播古代文献的学者和教师,孔子的思想包括先秦诸子的思想在内不是宗教。如此说来,孔教一词难以成立,更遑论立孔教为国教了。既然孔子的思想不是宗教,也就彻底排除了章炳麟推崇孔教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章炳麟极力排斥基督教,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展开批判。与国学为一国之固有的思路一脉相承,章炳麟提倡的宗教不可能是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4]可见,章炳麟反对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理由是,中国人若信仰基督教则会导致“崇拜西帝”的后果,这不仅关涉信仰问题,更严重的是关涉中国的救亡图存。他似乎并不在意中国人信仰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而是不能容忍由信仰基督教引发的对西方列强的敬畏——“崇拜西帝”。为了抵制“西帝”,克服中国人的畏洋心理,章炳麟作《无神论》,集中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上帝(“耶和瓦”)“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故为众生之父”进行讽刺和反驳。这清楚地表明,章炳麟对宗教的审视和选择秉持救亡图存的初衷,也决定了无论是中西的强弱对比还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都使他极力排斥基督教。他用于发起信心的宗教并不包括基督教。
对孔教和基督教的批判表明了章炳麟的宗教立场,预示着他寄予厚望的宗教不可能是孔教或基督教。换言之,“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宗教既不可能是康有为所推崇的孔教,也不可能是引起中国人崇拜西帝的基督教。在他看来,既能增进革命道德,又能“成就”情感的宗教只有佛教。对于佛教可以增进道德、推动革命,章炳麟多次分析和解释说:佛教教义与戒律兼备,具有最广泛的受众基础;华严宗普度众生的牺牲精神最有助于革命道德,唯识宗的万法唯心有助于彰显心的作用;佛教与世界的哲学趋势相符,特别是与康德、叔本华等大哲学家的思想相合;佛教属于无神论,故而不崇拜外界神圣,而崇拜人的自心,引导人“自贵其心,不依他力”,在“依自不依他”中勇猛无畏、蹈死如饴;佛教重视平等,痛恨君权,与革命党人提倡民权、追求民主的宗旨也最为契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表明,佛教足以堪此“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重任。他对佛教的推崇具有强烈的现实动机,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救亡路线息息相通,甚至是救亡方案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形象地展示了章炳麟集学问家与革命家于一身的风采。此处之国粹,也就是国学。章炳麟是近代最著名的国学家之一,国学研究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学问家。必须强调的是,章炳麟并非为了学问而学问,国学在他那里并不是僵死的历史陈迹,而是承载现实需要和鲜活动机的武器,是为救亡图存的火热斗争和社会现实服务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国粹作为武器,通过弘扬国粹开辟了一条迥异于他人的救亡路线。至于隐藏在这条路线背后的国学观、宗教观同样不仅有思想启蒙的维度,而且有救亡图存的意义。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将章炳麟定位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一面对作为革命家的章炳麟赞誉有加,一面对作为学问家的章炳麟含有微词。鲁迅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这样写道:“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7]不难看出,鲁迅对章炳麟的概括和评价明显将学问与革命截然分开,其实,将章炳麟说成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并不到位,因为他同时还是“革命的学问家”。事实上,章炳麟以学问——也就是鲁迅所讲的“经学和小学”作为革命的武器,对于苦难的现实既有批判的武器,又有武器的批判。这表明,章炳麟的学问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要明白这一点并不难,想想章炳麟宣布的所要做的两件大事便可一目了然:“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也正因为割裂了章炳麟的学问与革命,鲁迅将此归为“仅止于高妙的幻想”。
[1]章炳麟:《四惑论》,《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00-301页。
[2]章炳麟:《国家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9-360、361-362、362、359、366、367页。
[3]章炳麟:《建立宗教论》,《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4]章炳麟:《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6、276-277、271-272、272、273页。
[5]康有为:《大同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6]章炳麟:《制言发刊宣言》,《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
[7]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5-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