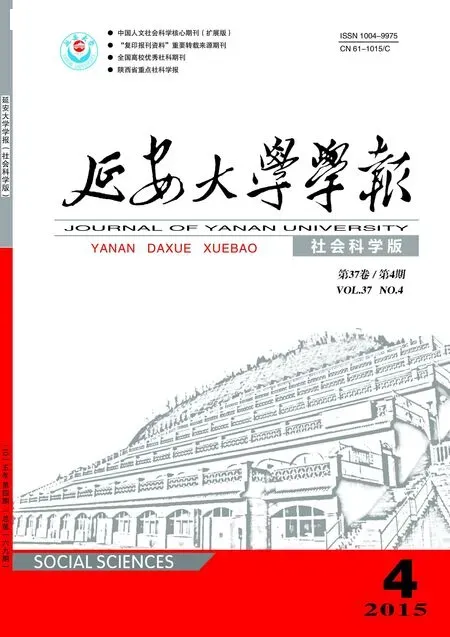“人作为手段”在人的自我实现活动中的意义探讨
项欢欢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072)
“人作为手段”在人的自我实现活动中的意义探讨
项欢欢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072)
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经典论述,作为类群体的终极道德理想,一直备受议论和关注。相较而言,“人作为手段”的意义和价值在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经常被忽视。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需求本性和社会本质为“人作为手段”提供合理性基础。人作为内含目的性、创造性的手段存在,与“物”作为手段真正区别开来。实践证明,“人作为手段”在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目的;手段;自我实现
实现自我,是每个人的使命,也是真正哲学的最终使命。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将镌刻在阿波罗神殿门楣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最高使命。德国哲学家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提法将“认识你自己”更加向前推进一步,即“实现你自己”。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和对象,更是价值的承载者、追求者和实现者。康德基于特定时代现实的“人是目的”提法,偏于在人的类特性上肯定人是绝对和终极目的的理想,致使许多人仅看到手段与目的的对立,过分强调“目的”的作用,而忽视了在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作为手段的一面。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从“人作为手段”的现实基础展开论述,重点回答人应当作为什么样的手段而存在以及“人作为手段”在自我实现活动中的价值体现两大问题。
一、“人作为手段”的现实基础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在全部造物中,人们所想要的和能够支配的一切也都只能作为手段来运用;只有人及连同人在内的所有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目的本身。”[1]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拥有“自在目的”的“绝对价值”。人不应该像物一样单纯被用作工具或手段,而应该高扬其目的价值,凸显人之为人的尊严。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论述是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后来的研究者们也多聚焦于“人是目的”作为伦理道德要求的理想主义倾向,很少谈论“人是目的”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和应用。这种“一边倒”的聚焦方式也许会妨碍对康德目的论的深入思考。
康德在论述中提到,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必须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可见,“人是目的”作为一条道德律令,不仅作用于人自身,也作用于其余一切理性存在者,“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2]康德“人是目的”思想中的“人”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指每个人,包括自己与他人。每个人作为自主的存在者,在认定自己为目的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人同样作为自主存在者的目的价值。“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3],在实际生活中,“人作为目的”和“人作为手段”相比较而存在。除非目的和手段指向同一个东西,否则这种没有限制的“人人目的论”缺乏实践的可能性。即是说,康德并未否认人在实际生活中会成为“手段”的事实,只不过他的侧重点在于肯定人是目的的崇高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人的本质不仅在于人的理性、自由,也在于人的社会性。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各种既成社会关系的存在者。与康德的先验前提和原子式个人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关注的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能够进行现实的、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活动的发展着的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物质和社会关系中,受它们的规定和制约。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最终实现的。以下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展开论证:
首先,“人”作为有肉体、有生命的现实存在,一方面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57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具体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5]363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不仅具有吃、喝、繁殖等纯自然的需要,按照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更有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等社会性需要。现实的人在需要本性驱动下,会凭借自己的能力,向所处的自然界谋取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6]由此,“吃”这样一个简单的生理性需要转化为复杂高级的社会性需要。人的需要只会随着人的进化、社会的发展在更大范围内、以更高形态产生出来,随之开展一系列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活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超越本能的能力体现。其次,人的需要的满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作为一个社会人,人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存在者。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各自特定的角色。“与人打交道”这不仅是正常人进行社会交往和沟通的需要,更是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适应社会规则和运作的需要。如前所述,基于个体生存和繁衍的自然生理需要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个人需要。个人满足需要的方式也已成为一种社会行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4]82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中,一切人是一切人的目的,一切人也有可能是一切人的手段。俗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根据“人”各自的特点和才能,任何一个“他人”对我都可能产生手段价值,我对“他人”也同样可能产生手段价值。“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类的本质”。[7]在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只有彼此依存、合作,才能生活。
人自身需要的满足、社会关系的维持和社会生活的开展都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进行的。实践是具体的,每一个实践都有其目的。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普遍实践规律作为航标,能导引人们向“善”的意志、终极意义趋近,却很难说服人们放弃眼下能创造实惠的具体目的。现实中的人总是通过追求具体目的的实现,不断趋近乃至实现人的最终目的。社会的发展、人的自我实现,要依靠人,要以人的活动为手段。“人对于创造来说就是终极目的”。[8]人,作为有意识、有理性、有思维的存在物,在面对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时,不仅要认识之,更要主动选择或创造实现需要和利益的条件。在人的需要、目的提出后,这种需要、目的只是人的观念性产物,是预先形成于人脑的主观印象,唯有人借助各种手段甚至以自身为手段,主动向现存世界索取,才能改变自然界的原有形态,从而改变自己的境遇。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知情意行统一的整体的人,是实现自身目的的现实力量。
二、“人作为手段”和“人是手段”
“人作为手段”区别于“人是手段”,我们要将对“是”的关注点转移到“作为”。“是”意为“等同”,将“人”和毫无生气的“手段”等同起来,也就是将知情意行统一的人单一化为只剩下躯体的人。在此层面上,人和动物无异。“作为”意为“当作,充作”,含有“创制”之意。首先,人可以凭借自身自由自决的能力,主动将自己充作手段。其次,在人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作为手段的这一方首先应作为主体的人被尊重。“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其作为一个存在者,必定是要把它自己当作是从意志的所有规则中制定普遍规律的存在者,以至于他可以从这个观点去判断他自己和他的行为。”[9]“物”不具备理性,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只能听凭人的支配。在实践活动中,在与他者、社会的交往过程中主动发挥中介作用的人,是一个知情意行统一的整体的人。
除了自由自决的意愿能力,“人作为手段”应当以“人是目的”为前提,这和以“物”为手段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无法实现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直接导致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人的类本质及他人的异化。人作为手段如果失却人作为目的的基础,那么,人就会沦落为同物一样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是工人生产出来的,却由资本家享有。工人生产的越多,自身越贫困。劳动者所期待的实践理念并没有在实践活动中得以现实化。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没有丝毫愉悦感可言,实践活动也不再是劳动者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是成为劳动者的负担。人的类本质只有在人自由活动,充分运用人的机能时才得以彰显。现如今,劳动者的劳动已经完全沦为其谋生的手段,人之为人的本质消磨殆尽。在资本的逻辑里,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都是手段,唯有“资本”才是真正的目的。人与人通过商品交换建立社会联系,个人摆脱社会环境的束缚,获得形式独立性的同时,实质上仍然受着“物”的支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较之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更朝前的资本积累方式。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过渡阶段。对于良性运作的社会和个人而言,自我和他者之间应该互为目的和手段,并且对自己的角色保持高度的自觉。“人作为手段”和“人是目的”的最终分裂,导致劳动者自己的体力、智力乃至生命,都不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而是转化成为反对他的力量,人在自我实现上陷入瓶颈。
另外,“物”作为手段,仅能发挥其特定的专属的功能,“人作为手段”则是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充分体现。“物”作为手段,其功能是确定的,比如,锄头用于耕种、除草,疏松植株周围的土壤;钢笔用于书写等。“人作为手段”,在其对象性活动中,善于运用自己的思想、想象,在尊重“物”的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0]人以自身为中介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相统一的层面上。“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58动物仅在本能的支配下生产自身,人可以在尊重客观物质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目的、需要、期望,创造实践活动的材料、对象、工具,不仅生产出自己的需要,他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也生产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马克思曾对人的实践和动物的行为做过一个形象的对比: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固然很高,却始终不及最蹩脚的建筑师,因为建筑师早在筑房之前,就已经在脑海中形成了对尚未现实存在的房屋的概念,“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5]202显然,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体现着人的创造性,最后也是这种创造性的现实化而告终。“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意识的调节方法,表明了主体行动具有合目的的自觉性”,[11]人作为手段,总是不断地将自在的自然界转化为自觉的属人世界。
三、“人作为手段”在自我实现活动中的价值体现
目的和手段是统一于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在现实操作层面,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并不一定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在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恶劣的原始社会,人类要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温饱和安全问题。吃、穿、住、生活是原始人群极为紧迫和现实的需要,尽管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种对目的和手段的自觉意识并不高;到奴隶社会,奴隶沦为奴隶主手中的劳动机器和玩物,是奴隶主任意摆布的棋子。奴隶主甚至可以随便剥夺奴隶生存的权利,这时候,奴隶主作为目的,奴隶作为手段决然对立;到封建社会,农民通过租佃地主的土地,获得有限的生活生产资料,至少争取到了维持自身生命的目的和权利。到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的独立性和独立意识增强。尽管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劳动者和劳动是分裂的,但劳动者对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独立有了更深切的渴望。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将自己分裂为目的、手段两个维度,也不代表着目的和手段在人的实际生活中是分裂的。只要这种分裂以统一为最终基础和归宿,这就是实践本身。强调“人作为手段”在自我实现活动中的意义和价值,是考虑到大多数人误将“人作为手段”的工具价值等同于“工具性”,对其持漠视态度。
人的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包括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人是什么样的人,就要看人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了什么。“人作为手段”的意义在对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的自我价值,是作为客体的人的所作所为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效应。人作为价值主体所进行的选择和创造不仅要面向世界,更要面向自身。人自愿自觉地将自己作为手段,已经体现了人自我规定和自由自决的能力。它的恰当运用,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对此,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持有精辟的论说:“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是他设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愿意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他自己造成的。”[12]人作为手段,旨在从具体现实的意义上,真正践行从“自我”出发,通过“自我设计”、“自我创造”使自己内在本性得以显现的实际活动。人只要脚踏实地投入自己的实践,行动起来,不论环境如何,能力如何,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自己的成绩、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之大限——死亡来临之前,人永远在存在中,人实现自己有多少,就有多少的存在。同样,在死亡这个最终的可能性到来之前,横亘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有无数可能性,人只有展开对诸种可能性的领会和筹划,才能真正彰显人之为人的独立自由。“自由是人参与他自己的发展的能力;是我们塑造自己的能力”,[13]人作为手段,在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之后,其承担的责任也具有了新的意义。人有自由,所以人不再是自然因果链条上被决定的一环,而是自律的。一个人如何行动以及行动的原则都由自己决定,从而通过自己的行为赋予自己独特的价值。接受对自己生活的责任,不再是作为一种重荷和负担,而是作为对自我选择的肯定和尊重,来自外界的约束转化为自我内心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人作为手段才成就了自我价值的完整性。
人的社会价值,是作为客体的人的所作所为对于作为主体的社会的需要的满足效应。马克思对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关系做过辨证的阐释,核心旨意就是:“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14]人不可避免地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特定的位置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一个人身上往往扮演着多个角色,是个“角色丛”。个人的利己性本能也无法改变个人与他者、社会之间不容分割的依存关系。不论个人是否愿意充当他人的手段,人的社会性本质已经决定了其必然性。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互相充当彼此的手段,也是人的社会价值存在的必要性。值得肯定的是,社会中不乏有这样一些人,出于公众的福祉,理性地、自愿地成为他人的手段。譬如,美国研究蛇毒的科学家,鲍尔·海斯德,一心想要研究出一种抗毒药,造福人类。从15岁起,他就在自己身上注射微量的毒蛇腺体,并逐渐加大剂量与毒性。他身上先后注射过28种蛇毒。经过危险与痛苦的试验,终于试制出一些抗蛇毒的药物,成功救治了很多被毒蛇咬伤的人。在完全知情、理性的前提下主动充当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作为手段的同时也作为自为的存在,履行着人之为人的庄严使命。在为社会谋利、为人类造福,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成就了自我价值。强调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旨在还人以真实。如果割裂了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将人作为手段从“人是目的”的深刻内蕴中分离出来,无异于否定了人类活动的必要性。但这个目的之为目的的根基在于它必得借由手段来实现。我们常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真有,也必得由人自己去挖掘和发现。
[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9.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7-358.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7.
[8]康德.判断力批判[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05.
[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11]陈新汉.论自由向必然的转化[J].学术月刊,1998(10):11-17.
[12]王恒伦.人生的理性思考[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7.
[13]罗洛·梅.人寻找自己[M].冯川,陈刚,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2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4-196.
[责任编辑 高 锐]
B023
A
1004-9975(2015)04-0026-04
2015-06-10
项欢欢(1991—),女,浙江金华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