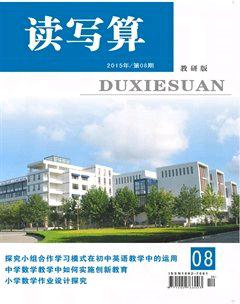海上丝绸之路与闽南戏曲当代发展
——东亚文化格局中的闽南戏曲二次创业研究
文‖王 伟 陈思扬
海上丝绸之路与闽南戏曲当代发展
——东亚文化格局中的闽南戏曲二次创业研究
文‖王 伟 陈思扬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闽南戏曲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走出去”与“走进去”,形成影响深远的“闽南戏曲文化圈”。闽南戏曲承载着闽南族群在地化、处身性的民间记忆,区别于在选择性过滤机制作用下之平板整一的宏大叙述,在全球本土化的时代语境中起着重述历史记忆与抵抗时间遗忘的重要作用。缘此,作为闽南族群重要的精神家园,闽南戏曲并非与现实无涉的休闲审美活动,其深刻表征海内外闽南人共有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记忆,成为闽南族群建构身份认同的路径之一。
现代性;文化想象;身份认同;原乡情结
一、闽南戏曲与历史记忆
2015年2月中旬在泉州召开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笔者以闽南戏曲在东亚、东南亚等地的流播作为切入点,具体论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闽南戏曲海内外传播的繁复关系,并以之为轴心将问题顺势扩展到海丝人文交流问题域特别是闽南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层探讨。笔者以为,古老常新、与时俱化的闽南戏曲,并非如某些学者依据经验、先入为主的理解那样,只是偏居华夏东南一隅、地处文化版图边缘的民俗曲艺;事实或许恰好相反,“内容通俗化、形式大众化、流传俗行化”[1]9的闽南戏曲,在古代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极其顺利地“走出去”,而且颇为成功地“走进去”,形成至今依然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闽南戏曲文化圈”,充分体现闽南文化的生命力与灵活性。职是之故,闽南戏曲早已超越原型层面的娱情遣兴、放松休闲,也跃出审美层面的悦耳悦目、悦心悦意,凝聚着海内外闽南人共有的文化记忆。
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的观点,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背后显影的乃是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具体言之,闽南戏曲与文化记忆的互动关系,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闽南戏曲与民间信仰、人生礼俗、岁时节庆等活动密切相关,真切体现了海内外闽南族群特有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情感心理结构。第二,闽南戏曲作为既颇“接地气”的世俗镜像又超越现实的造梦工程,深刻反映了海内外闽南族群日常伦理道德与价值评判标准。第三,曾经深入人心、大放异彩的闽南戏曲,还一度是闽南族群组织社会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其如盐入水般地深深嵌入在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总而言之,闽南戏曲发自乡土沃野、扎根民间土壤、服务庶民须求,与生俱来地承载着个体化、处身性、素朴性之杂语共生、众声喧哗的民间记忆,使其有别于平板化、整一化之本质主义的宏大修辞,于不其然间起着重述文化记忆、抵抗群体遗忘的重要作用。
正所谓,“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未来”。下文便在前人文献纪录与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上,遵循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领域的论述思路,一方面简要梳理闽南戏曲如何伴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播海外、走向世界,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初步探勘域外戏剧如何走进闽南、融入闽南,以及二者如何相互借镜、和谐发展,共同起着“组织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建构新式观念形态”[2]232-238的现实功能。
二、闽南戏曲的海内外传播
尽管囿于年代久远、材料有限等诸多原因,福建戏曲(曾经一度成为闽南戏曲的别名之一)海外传播的最初时间节点已然不可考,但是根据现存史料而追根溯源,可以推测至少远在明清时期,福建戏曲、闽南戏曲就在琉球、在泰国、在印尼等地广泛传播。例如,国内知名戏曲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王汉民先生在其扛鼎之作《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研究》一书中就以明代莆田人姚旅在《露书•风篇中》、清人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关于琉球等地的演戏记录等厚重翔实之史料,令人信服地指陈:“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的历史比较悠久,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明万历年间已有福建戏班到琉球及东南亚等地演出。”[3]6无独有偶,著名比较戏剧学专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主编的煌煌三卷本的《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亦意味深长地指出:“在爪哇从1603年至1783年华商酬神作戏的活动从未间断过,而且当地的华人富豪或赌场大亨还延聘漳、泉两州乐工、优人,教导自己蓄养的婢女(爪哇人)歌舞,日日演戏以娱嘉宾。”[4]804至于泉州地方戏曲史家郑国权老先生更
是在《泉州戏曲远播海外》一文中,细密爬梳诸种闽南戏文的明清刊本,如何经由来华商人或者众多游历者之手而漂洋过海流播于菲律宾、印尼群岛,进而辗转到欧洲大陆。在其看来,流传海外之戏文刊本的典型代表就有,“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福建建阳新安堂于明嘉靖丙寅(公元1566年)出版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此曲勾栏荔镜记戏文》”;“收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福建瀚海书林于明明万历(1604年)出版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收藏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福建瀚海书林景宸和霞漳洪氏于明万历间出版的《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一卷》”[5]等等。
当然,海上丝路与闽南戏曲的域外传播这一课题,绝非当代闽地学者自娱自乐的自说自话,其亦如巨大的磁石吸附着西方汉学家的关注目光。例如,英国牛津大学荣誉中文讲座教授的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先生,就数十年如一日爬梳尘封于历史深处的信札、日记等文献资料,让“被遗忘的文献”浮出历史地平线而重见天日。他在《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一文中辟有一节《1589——1791在海外的演出》,通过“东南亚和台湾的福建移民的记述”[6]21,多维阐述大航海时代中闽南戏曲的演出状况及西方殖民者对闽南戏曲的早期认知与纠结态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闯入者”的西方汉学家,在他异性的学术视域下,更加关注外来元素如何深刻改写闽南戏曲的原有面貌,以致先于本土学者指出南音这一“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7]14-17的形成,其实不无背谬地受到来自遥远中东地区音乐形式的巨大影响。比如,现任教于福州大学的当代著名法籍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先生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一文,就基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的学术范式,耐人寻味地强调南音(即“弦管”、“南管”)这一让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引以自豪的古老音乐,在诸多维度受到波斯文化的遥远影响,可以将之认定为中外音乐传统的交流结晶。他在细致刻画南音所受外来影响“痕迹”的时候,特别以《陈三五娘》这一梨园经典为典型个案,立体论述“南音不是作为一种中国职业音乐家演奏的音乐而产生的,而是由包含很多阿拉伯商人在内的泉州商业阶层精英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在南音曲目中占主导地位的陈三、五娘故事中有许多非中国式特征”[8]1319-1320。
总而言之,闽南戏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地方化、民间性的一般戏剧,其依循海上丝绸之路向域外传播,并且深深嵌入华裔族群甚至当地土著的休闲活动甚或日常生存,最终形成闽南——“东洋”——“西洋”(这一概念约等于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实质是以“南洋”为主体进而延伸到中东、北非等广大地区的地缘政治学名词)之间的戏剧关系网络。由此而来,闽南戏曲“既是建构公共记忆的重要媒介,本身亦构成历史记忆之所在”[9]54-57,其在不经意间联系着“多元、开放、跨界、混杂”这些极具后现代症候意味的关键词,成为国际移民艺术的图腾符号,直指广义全球化中的认同政治问题。
三、闽南戏曲的现代性经验
时至今日,或许闽南戏曲的辉煌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在现代性与传统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激荡的“后舞台”时代,闽南戏曲作为流淌在海内外闽南人血脉当中的民族DNA,依旧在海内外闽南族群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继续传承并且发展着海内外闽南人共有的文化记忆。例如,20世纪50年代,闽南戏曲与其新的媒介表现形式——闽南语戏曲电影,在新、马等地的一度流行,便是最好的例证。在笔者看来,这一文化事实至少说明以下三点:
其一,在海外生活和打拼发展的闽南人是闽南戏曲海外传播的重要支撑。离乡背井、为数众多的闽南籍华人华侨,构成闽南戏曲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观众群,前者为后者的海外传播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支撑,悄然构造并不断完善闽南戏曲及其影像作品的公共观演的生态系统。在当代媒体的主流叙事当中,富有雄强进取之开拓冲动与冒险精神的闽南族群,以“下南洋”过番谋生的勇敢之举,而与境内浩浩荡荡的“闯关东”、源远流长的“走西口”并称中华移民史的三大壮举。根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福建省志•华侨志》的记载:“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真腊、安南外,以祖籍福建的华侨占多数。”[10]13另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戴一峰教授在《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的大体估算,“自1845——1949的百余年间,经厦门移居海外的闽南华侨总数高达120万,而95%的闽南华侨分布在东南亚的新马、印尼和菲律宾等地。”[11]时至今日,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闽南籍华人已达2000万人之巨,毫无疑问,遍布五洲、数量庞大的这一群体,一方面构成了“新世纪我国联系海外、重塑‘海上丝路’的一支重要力量”[12];另一方
面也为“世界拥抱闽南戏曲”与“闽南戏曲走向世界”,奠定坚实而又牢靠的人口基础。
其二,闽南戏曲在当地传播以致落地生根,联系着海内外华侨华人的现代性乡愁。识者只须检视这一时段东南亚主流报刊媒体所刊登的演戏评论与映演广告,不难发现充斥其间的故土情思,其用意不言自明。仅以《南洋商报》所刊登的戏班广告与闽南戏曲电影广告为例,其间弥漫着铺天盖地却又直截了当的情感攻势。诸如“闽南侨胞喜讯”、“听自己的方言,看故乡的风趣”、“听家乡话,看家乡戏,倍感亲切有味”、“福建侨胞不可错过”、“福建侨胞看过来”[13]60-63此类等等不一而足。不惟如此,情感经济学背后关涉更为深广也更为根本的美学动因,即千千万万海外游子念兹在兹的文化乡愁。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身份迷茫与现代性焦虑,使得漂泊海外的闽南族群殷切期盼经由公共空间的观演仪式,纵情言说内心深处的怀乡之情与故土之思。众所周知,舞台上或者光影间的闽南戏曲,大都以“重乡崇组的思维观、爱拼敢赢的气质观、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山海交融的行为观”[14]1的来追溯历史,以“凝重深沉的时代悲怆和强烈浓郁的言志旨趣”[15]6-11切入审美时空,在去国怀乡的文化乡愁氛围中建构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满足当地华侨华人对公平正义的焦灼呼号和国族身份的认同想象。
其三,有道是“打铁还须自身硬”,闽南戏曲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走出去”,除了前面所说的文化生态,其调动观众情绪的艺术能量与被观众普遍认可的美感品质,也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包裹着闽南风味外壳的闽南戏曲及其影像文本,以“绵如雨、深如海、痛如天,波澜四涌、无法弥消”的爱情传奇,将日渐淡出现代生活却又挥之不去的乡土情怀,投射在舞台上、显影在银幕中,从而使历史缺席的传统情愫,变成现世在场的审美意象。这种将观演主体的审美体验有机嵌入返本开新的道德神话,于纵横交错、零乱裂解的现实情感缝隙之中,模塑或曰重建华人社群所分有、所共享的情感记忆。有鉴于闽南戏曲之现实与历史桴鼓相应的文化品性,及其与海外民众之审美期待视域的间性融合,使观众能够在物我齐一、情理交融的接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似已沉沦、想象之中的闽南文化的本体苦恋,悄然固化为一种“物恋”的美学形式。是以,无论是沉湎于前现代儒家文化之识见不多的草根阶层,抑或是浸润启蒙现代性欧风美雨的后起精英群落,果不其然地被戏文的编码者纳入重返故土的造梦工程之中而难以自拔。君不见,曾几何时,在《因哥送嫂》、《岭路斜崎》之动人心弦、百转千回的音乐声中,不少人的眼睛都红润潮湿以至模糊不清。
四、闽南戏曲的当下发展
不言而喻,今天我们讨论历史,绝对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状,进而解决问题。根据我们此前所做的调研,当下闽南戏曲的海外传播,或者推而广之到闽南文化的对外交流,存在着“六多六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外传播的效果。
第一,作为各式活动的配套环节的多,民间基层自发组织、自主推动的少。根据媒体的报道与坊间的议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很多时候、不少地方的剧团班社的海外演出,与更多依赖民间管道相邀“请戏”的历史传统有所不同,似乎都是由地方文化部门至上而下的主导力推,很少由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促进。事实上,这种地方宣传部门、文教机构主推下的交流活动,往往赋予戏曲传播更多的经济考量与社会意涵,使之在“文化搭台、某某唱戏”的声浪之中,失去了原汁原味、生动活泼的观演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剧种本身的草根本性与传统特征。第二,单向传播的多,双向互动的少,更多时候体现为一厢情愿式的以我为主的走出去。第三,间断性开展的多,持续性进行的少。尽管很多活动在开展之时锣鼓喧天、声势浩大,围观者多、应和者众,但却点
到即止、人走茶歇,都是因时、因势、因地,间歇式的举办,很少有持续性的长时间开展。第四,表象热闹的多,深层“发酵”的少。如前所言,举办戏曲展演活动的时候,可谓人山人海、旌旗飘扬,往往一票难求,真的非常热闹。可惜的是,往往成为一阵风,风过之时,可谓风行草偃,但是等风过后,真正产生深层次的长远影响,恐怕还是比较少的。第五,一般化的多,有针对性的少。很多时候戏曲传播还是停留在泛泛的“大众传播”,没有走向精准有效的“分众传播”,没有针对戏曲受众所属的不同的族群、年龄段、教育水平、社会阶层,进行市场细分、精准定位,采用不同的影响策略。第六,局部的、分散性、重复性的活动多,整体合作、协同创新的少。尽管一年到头,类似的戏曲“走出去”的活动很多,但是往往因为“闽南人个个猛”的情结使然,各搞各家、各自为政,没有相互托举、互相帮衬,更谈不上形成聚集的规模效应。很多活动分散发生、无序进行,缺乏宏观层面的整体性规划,出现力道相互抵消甚至不免互相拆台,没有形成合力与补台意识,导致事倍功半、内耗空转。另外,不少活动的模式单一、因袭重复、失去新意。
有鉴于此,我们在全球本土化的新形势下针对闽南戏曲的海外传播,给出如下建议。首先,要固本强基、开拓创新。所谓“基”,指的是海内外闽南人所共有的文化记忆。所谓创新,指的是戏曲活动要与时俱进,因事、因地而发展变化、推陈出新,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即使是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也要注重适应新形势、新媒体、新需求,进行相应改变。例如,有的地方一有国际性的展会活动,总是向来宾展示一些俗不可耐的民俗曲艺,这些节目乍看上去似乎很有特色,但是将之作为向全球推广的地方意象,恐怕有待商榷。其次,要均衡兼顾、重点突出。所谓均衡,意味着要在认真调研不同职业、社群、年龄层、教育背景的差异之后,尽可能推出不同的剧目,以适应不同受众群的不同需要,而不是寄希望于一出剧目吃遍天下、老少通吃。既要考虑老一辈戏迷的感受,更要关注年轻一代的需求,既要照顾社会菁英的审美理想,更要贴近庶民阶层的文化诉求。惟其如此,才不会坐吃山空或者“捧着金饭碗要饭”,戏曲传播之树才能长青,戏曲交流之花才能常开不败。复次,要加强互动,形成合力。闽南有句俗语,叫做“亲戚常走才能亲”。加强互动显然很有必要,不能只来不去,也不能只去不来,要既来又去,常来常去,双向互动、立体交流。推动闽南戏曲的全球传播,不能光靠地方的一腔热情、鼓吹呐喊,更不能只依托地方捉襟见肘的有限资源,而是应该充分调动起海内外华侨华人,特别是闽籍华侨华人的热情与资源,携起手来、共同推进闽南戏曲走向世界。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借用历史符号讲好当下故事。正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资源是稀缺的,资源是珍贵的,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如何才能以最低的消耗,达到最大化的运用,这就要求各个参与主体要有整体观念、大局观瞻、长远意识,抛弃一己的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协调好各个方面的诉求与利益,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用。
[1]林一.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黄科安,王伟.曲同调殊:戏改语境中的荔镜情缘[J].东南学术,2013(5).
[3]王汉民.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周宁.东南亚华语戏剧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5]郑国权.泉州戏曲远播海外[N].泉州晚报,2002-6-8.
[6](荷)龙彼得.明代戏曲弦管选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7]俞建芬.中华民族音乐的活化石——福建南音[J].音乐探索,2004(3).
[8](法)施舟人.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C].闽南文化研究——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下),2003.
[9]王伟.闽南地方传统戏曲的现代性经验[J].南方论刊,2014(9).
[10]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华侨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11]戴一峰.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3).
[12]林华东.“海上丝路”的影响与启示[N].人民日报,2014-10-19.
[13]郭崇江.试论20世纪50年代厦语片在新马地区的发展——以《南洋商报》(1953——1959)为中心[J].当代电影,2012(3).
[14]林华东.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15]王伟.台湾电影的现代性书写[J].集美大学学报,2011(3).
J80
A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三五娘”故事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1BZW107)阶段性成果;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东亚文化语境中的闽南戏曲二次创业研究》(201410399009)研究成果;泉州师范学院2014年度大学生科研基金项目《东亚文化格局中的泉州戏曲当代发展研究》(2014DSK14)最终成果。
王伟,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