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重藏和他的《正斋书籍考》
王晓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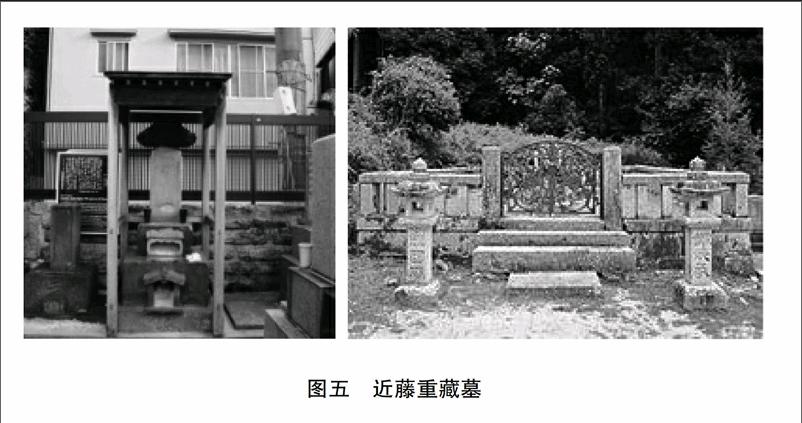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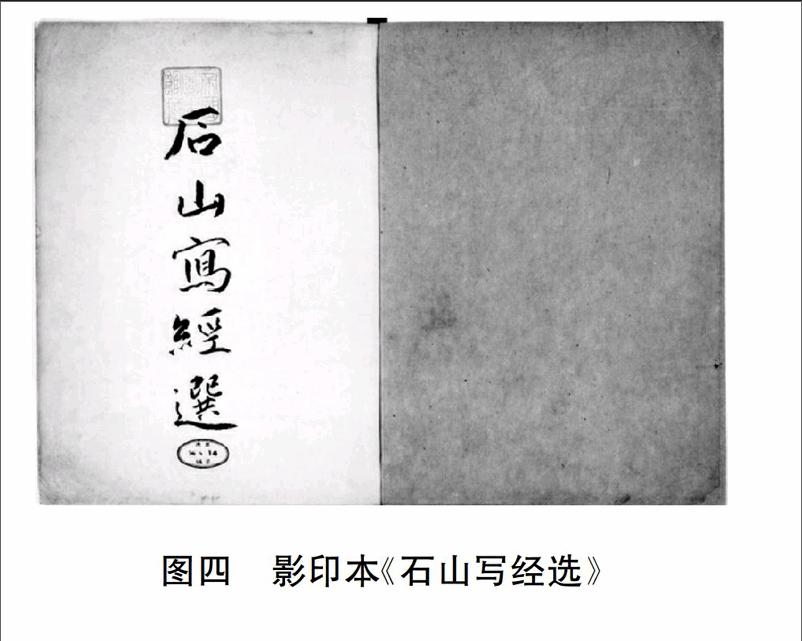
武士与农家发生商业纠纷,农家聚众打砸了武士的家。武士大怒,带着他的长子提刀闯进这家农户,斩杀了这家的主人,主人的女儿背着三岁小孩从外面回家,见此惨状,正想转身逃出去,也被来人追杀。
事情发生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而那率子提刀仇杀者,正是本文所说《正斋书籍考》(以下简称《书籍考》)的作者近藤重藏(1771—1829,以下简称重藏)。
图一近藤重藏画像
重藏是江户后期幕臣、探险家,讳守重,号正斋、升天真人,与间宫林藏、平山行藏并称“文政三藏”,师事山本北山,八岁始读四书。他所著《书籍考》对日藏汉籍作了周密考订,其中对写本的描述文献价值尤高。诚如明治时期汉学者依田学海所评价的“考证精确,文字致密,非粗心人所能辨也”,很难想象他同时又是一位凶杀犯。
《书籍考》是首部考述日藏汉籍的专书,早于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百年,它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辩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彰显,描述诸书刊刻传写的异同,编次增删的始末。不过,由于它为日文撰写,就轻易地滑过了赴日访书的杨守敬、罗振玉等人的眼睛,而书中那些有关日本写本记述的价值,还很少有人去认真研读过。
考原本——从哪里来
我国学者杨义在谈到秦汉之际的书籍制度时,曾论及简帛抄本传播的特点。他说,那时成书是一个过程,迥异于宋元以后的刻本的一版定终身。因此许多书籍都存在着类乎考古学上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辨真伪,而是究其原委,梳理其前世今生。他把这叫做“辨析叠压”的方法。这些说法大体也适用于那些流传到日本的我国写本。如果说,刻本的特点是“一版一世界”,也就是说同一版本的所有本子大致是一个面孔的话,那么写本则不同,它们是“一本一世界”,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写本,可以说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源于同一底本的抄本,也会因书写者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孔。
例如,重藏考证,《周易注》凡日本古抄本清家传本今之所存者,都是上下只有经文,是王弼注六卷本。重藏本人亦珍储一本,首页有“天师明经儒”的椭圆红记,即六卷本。伊势文库中,还有天文廿二年四月古抄本《周易》六卷。其所以是六卷,他认为,《隋志》中作“王注六卷略例一卷”,与晋韩伯康注别行,很可能也传到了日本。《经典释文》谓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王注不注系辞本,很可能也有单行本。他推测,或魏晋古本传入日本,也未可知。
又有《周易传义音训》,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是《周易》经传文字与程颐《伊川易传》、朱熹《周易本义》、吕祖谦《古易音训》的合编本,可谓宋儒易学之大全。日本有《周易传义》二十四卷本。重藏考订,日本人为该书作训点,是从萨摩禅僧、建长寺住持长老僧文之开始的。有宽永四年(1664)文之点,同年其弟子如竹开板的本子为证。重藏曾见《传义》古本,有文之手书跋语,注明“文禄癸巳之春”。则时当1594年,即明万历二十一年。重藏偶行于一浦,看到自朝鲜来归者持的经史。经史纷失,而无全一部者。其中有《周易传义大全》三册。他即求之,到另外的地方又求一二册,首未足者,令人书写补足。以后便深入研读,朱墨点校,焚香读诵,恒兀兀以穷七年。同时他给该书加上了日文训点。对此,他还感叹到:“吁!我不才,未得于辞,况于通意乎?所谓蚍蜉撼树,精卫填海之比,而多见其不知量也。后之人与我同志者,校之正之,幸也。”
图二1905年出版的《近藤重藏全集》
日本12世纪之前刊刻的汉籍,主要是佛经与实用之书,经史子集之书,唯赖写本相传,12世纪之后,虽然五山僧侣也刊刻了不少汉籍,但未刻之书较之已刊之书要多得多。至于小说一类,直到江户时代才有刊刻的机会。因此,至此几百年间,写本是探讨中国书籍东传的抓手。那一时代,如无写本,则汉籍传播无路,因而探讨中国图籍之东渐,撰写中日文化交流史,都不能缺少写本这一门。从这种意义上说,重藏所储之书与所考之书,都不能算是可有可无的。
考奥书——经何人手
古代将祭祀设神主或尊长居坐之处室内西南隅称作“奥”,也泛指室内深处。日本书志学中把文书等书写物左边末尾称为“奥”。这或许正是来自古汉语的本意。于是,一般把写在这个部位的文字称为“奥书”,也叫“识语”。写本的末尾中常常将书写的年月、书写者的身份姓名以及书写的来由等写在这个部位。所以,考察奥书就成为写本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关于书籍传承渊源的信息,自然也包括了有关书写者对书籍的态度与评价。日本的写本研究者历来重视对奥书的考订,重藏在这方面也是先行者。
日本所藏经书写本,以《论语》与《诗经》为最多。重藏对《论语》写本考订甚详。《论语义疏》十卷,在我国久佚,乾隆中初复归,《知不足斋丛书》收入。日本有《论语义疏》古钞本数通,重藏也收储室町季世的古本。他所藏室町季世传写《义疏》及《谚解》,其一则云关东传《论语》始於小野侍中云云。他认为,凡《论语》古本,皆六朝及唐代传本。故字句异同征于古书,精善而足以为据,如中国古本佚落,故邢昺的《正义》、朱熹的《集注》,都是据后唐长兴版本一通,未能与其他善本对校,而日本则有真本相传,能依古训,值得珍视。
现存日本古本《论语义疏》,为近三百年来中日《论语》研究者所重。重藏所闻见者,有相传为平安时代硕儒菅原道真手写卷子本一通,亦系大和国广濑村里正某所藏,后又为某侯家藏,每卷有贞和二年(1346)识语,为后人所题,仁治原本嘉历撰写一通外题书作“鲁论”,卷尾有识语称:“此书受家说事二个度,虽有先君奥书本,为幼学书之,间字样散散,不足为证本,仍为传子孙,重所书写也。加之朱点墨点,手加身加毕,即累叶秘说,一事无脱,子子孙孙传得之者。深藏匮中,勿出阃外矣。于时仁治三年八月六日,前参河守清原。”据考,这里的“参河守清原”,即清原教隆。仁治三年,即宋淳祐二年(1242)。日本经学依世袭传承,清原家是其中之大家。制作一个最可信赖的好本子作为教材,是将经学传授给下一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从识语看,清原教隆两度接受前人讲解的本子,虽然是有师长书的“奥书”,是专为后生书写的,但也存在文字驳杂混乱的问题,不足以作为“证”本,即标准教材,因而决定重新书写,并在上面用朱点和墨点,记录世代传授的秘说,以便以后向子孙传授。识语告诫后人,这个本子没有任何遗漏,子子孙孙可以放心使用,但要秘藏不露,绝对不许外传。这些奥书,汉语中偶有日文语法或习惯说法。文中的“二个度”就是“两度”的意思,所谓“手加身加毕”就是完成了在上面加上各种解读符号的工作。
考书写——特色何在
日藏写本属纸质文献,对纸张笔墨等物质层面的研究和书写规范方式等的考察,也是写本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除书写文字研究之外,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写本研究丰富的文化内容,正体现在其中。
图三石山寺藏《史记》写本
日本平安时代以后,贵族在文化交流中不再独占鳌头,五山僧侣扮演重要角色,很多汉籍写本出自禅僧之手,并完好地保存于佛寺之中。顾野王《玉篇》,原本在我国久佚,不得见其真面目。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石山寺书库往往传古经卷,多有卷子儒书之装背书佛经者。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世间楮纸少,不能不节省使用,正面写过仍不忍丢弃,反面还要写的缘故。重藏曾经过石山寺,就知足庵僧正阅其所藏。如《史记》《汉书》,直赫然李唐人之亲笔及日本天平年间之真写。现存书中,有《玉篇》装背书《大般若经》者,则顾野王原书真本。重藏说它们“虽为零篇,实吉光片羽,亦可谓奎耀之宠灵”,并为自己有幸目睹《史》《汉》及《玉篇》等之真本,又得影钞珍储而倍感庆幸。
日本所传石山寺抄卷子本《史记》残篇,天平年间抄字,即唐代传誊的真本,乃最古之奇本,海内之至宝,惜乎仅残缺,唯赖佛经而存。重藏游石山寺,亲眼目睹其真本,字体奇古,纸墨如新,赞扬其“可谓好书之幸甚”。
图四影印本《石山写经选》
重藏所见《汉书》有真本数种,其最古者如石山本,为天平年间之古抄,日本天平元年乃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其间有唐代的真迹;其次有宽治、保安、寿永、建保各年代的校本,俱唐代传本。继之有宋庆历本覆刻韩本,有庆元板建安刘之问本,有宋板元补刻本,俱为中国未尝言及的真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重藏所说的李唐真迹,以及后来的日本学者所说的“唐抄本”,是否都是唐人书写的,则是需要一一重新探讨的问题,有很多可能只是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人依据唐传本的重抄本甚至抄编本。即使这样,从保存文献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加以珍视的。
考刻本——写刻之变
同一书,写本往往是刻本的前生,刻本则是写本选择、校勘和整理后的产物,因而,可以说写本好比是河流的上游,刻本则是其下游,其中携带了写本的最重要的内涵。如果是自成一体的环境体系,刻本流通,写本消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如果是一书在两个体系中流动,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日本室町时代以后,博士家依然靠世代相传的以唐代写本为底本的转抄本教授后学,而宋椠本也传了进来,于是便有了用宋本来为写本作校勘的活动。学者在读所谓和刻本,即日本刻本的时候,也往往将其与日传写本对勘,以识语的形式将其心得保留下来。重藏对此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重藏发现,庆元版《后汉书》每卷尾“引异本此际授受之奥书甚多”,也就是该书每卷尾有不少记录该书在日本授受的文字。自宽仁、寿应、德元、永保、安保、元寿、嘉祯、文永至大永、享禄年间,识语栉比如麻,因而推测此书是“传写古博士家之传本”。他还发现,最可奇者,卷首有文字:“《帝纪》第一范晔《后汉书》一、唐章怀太子贤注。”旁以墨字细书“家本《后汉书纪》○— — — —○— — — —家本皇太子臣贤奉敕注”。以上识语中的○为圈句号,用于书名之首。短线为省代号,“— — — —”,即省代“后汉书纪”这四个字。重藏由此认为:“今考其奥书,亦相当于北宋时之所书,则所谓家本乃李唐以来传入此际之古写本,亦未可知。其证有卷子本皇太子臣贤,若为唐字,即唐之监本也。”
图五近藤重藏墓《五经活字板经注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所录经注正义的单本,皆与《隋书·经籍志》吻合,加之日本古博士家能宝蓄永用,故其古本能流传撰写于人间者不鲜。唐时写样之卷子钞本现存,亦足以窥见其一斑。《五经活字板经注本》,意当时古本有误写,故以宋板新雕之舶来为奇,却当据活本而檃栝校刊古本论宋据古括,实可谓经注之真本。
《书籍考》之外——武儒的AB面
重藏为后世留下60余种1500卷著述,《书籍考》是他利用担任幕府“书籍奉行”(掌管书籍的官吏)的便利,对日藏汉籍进行的一次清理,可谓有用之书。他特别注目于那些未刻之书,在凡例中突出强调日本古本其源乃自隋唐之所传,字句之精善,出于宋本之上者不鲜,认为自己目击李唐之真写《史记》《汉书》卷子本,《左传》《群书治要》卷子本实可谓“希觐之实帙”,“学者宜就其善本之最善者研核字句,以求古人精意之所在,是谓真正之鉴藏也。佚于彼而存于此之《玉烛宝典》《文馆词林》及近来《佚存丛书》所载之类,最足以珍重”。其对日藏写本的借奥书考传抄之原委,彰显写本的文献价值,是值得写本研究者认真一读之书。
图六近藤重藏像
依田学海《谭海》卷四《近藤重藏》说重藏“博览强记,无书不读,器识极高,仕幕府补书物奉行。尝使虾夷,洞察番情,著述百余卷,皆有用书也”。从读书知人来说,这只是重藏的半面。他的另一面则是“为人桀骜,谲诈自用”,因而“世爱其才而薄其行”。重藏父子最后因凶杀而被抄家流放,数年而没。
据载,死于重藏及其长子刀下的竟达七人之多。重藏友人朝川善庵说:“以近藤之学识,失身于一农夫,今则思之,不得其解也。”一把武士刀,一支毛笔,重藏将日本武士的凶蛮和文士的细腻都发挥到了极致。在重读《书籍考》有关写本的记述时,我们不能不对日本汉学多作些思考。历史上的日本汉学者不是一个经过什么“洗礼”后的“纯洁化”群体,有什么样的日本人,就可能有什么样的汉学者。重藏其人其书,足以打破我们对于日本汉学者的刻板印象,让我们警觉起来,对于日本汉学,需要我们深入了解的东西还实在太多。尽管《书籍考》一书对于汉籍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我们还是要看到,重藏时时没有忘记将日本古写本奉为“皇朝”文明的荣耀和昌明的象征。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